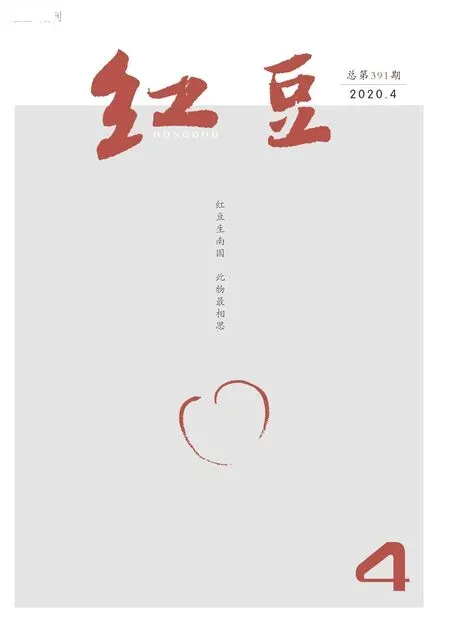恍然离世
2022-05-26张弛

张弛
一
夜色墨染,人声喧哗。头顶的串串灯宛如漫天星辰,直铺向远方。烟雾由近及远袅袅腾空,食客酡红的脸在烟雾里若隐若现。
两瓶啤酒下肚,辛培仁尖酸刻薄地挖苦单位同事。朱西昆觉得辛培仁越来越不像单位领导的样子了。他暗中掐指一算,意识到辛培仁已经五十六岁,且两年前就不任重要职务了,莫非辛培仁也到了破罐子破摔的地步?
朱西昆觉得,辛培仁的酒话说出了在清醒状态下不可能说出的事。
当时辛培仁仰起脖子又喝了一瓶啤酒,把瓶子往桌子上一顿,望着他说:“高马伐老婆失踪,你知道咋回事吗?”辛培仁一副兜售秘密的興奋神情,“他妈的,就是高马伐自己干的!”
朱西昆被震住了,脱口而出:“啊,真的吗?”
辛培仁瞟一眼左右,压低嗓门道:“当年专案组抓不到把柄。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就是他干的!那几年他和老婆已经到了鱼死网破的地步,外人不知道而已。杨福莲是他的邻居,清楚得很……”
多年来,藏在朱西昆心里的一种隐隐约约的猜测,终于从辛培仁的嘴里得到了印证。
二
传言渐盛,朱西昆再也睡不好觉了。有两个晚上,他半夜惊醒。辛培仁那天在夜市告诉他“高马伐杀妻”,他惊魂未定。他在夜市告诉刘智勇“高马伐杀妻”,他后悔得要死。
那颗定时炸弹被埋藏两三年之后,突然被引爆了。导火索是分两截燃烧的。第一截是一个小道消息,说被“冷藏”多年的高马伐就要“解冻”,来当他的领导了。高马伐在招商办的那几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按说早该被重用,可自从他老婆失踪后,他的进步之路仿佛被堵死了。据他说,无论他夹着尾巴踏踏实实做了多少事,甚至对小他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都俯首帖耳、言听计从,数年如一日,可就是不能进步……如此看来,如今组织上觉得对高马伐考验够了,终于要起用他了。尽管他任职的是是鸡肋岗位,但总算是当上了科室的一把手。
朱西昆是在办公室听到同事八卦这件事的。这种小道消息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这正应了“是草有根,是话有因”这句古话。自此,朱西昆心里就埋下了不安,不过他依然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
一种可能是刘智勇能把话烂在肚里,但这点他毫无把握。其实那个叫刘智勇的他并不熟悉,只听说过他也是本单位的,但在哪个部门他都不知道。正因为不熟悉,没有什么利害牵扯,那天在夜市喝高之后,他才会把“高马伐杀妻”吐露给他。还有一种可能更保险,就是他隐隐约约记得刘智勇已经死了。前年还是大前年春日的一个上午,他站在家属院门口的信息栏前,跟两三个闲人一起看一则讣告,死的人就叫刘智勇。他还记得一个闲人指着刘智勇的名字笑着说:“这下闭嘴了,不会再告这个告那个了。”
如今在这漆黑的夜里,躺在床上,那个春日上午的情形在朱西昆脑海里经过反复想象甚至加工,变得越来越鲜活,越来越逼真。尤其与闲人的对话,是在反复回忆的过程中从脑海深处打捞出来的。这意味着什么?难道那个叫刘智勇的竟是个告状油子?
朱西昆的不祥预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有坐实的倾向。此时,第二截导火索燃烧起来了。那天上午,他转到楼梯间里准备活动活动时,忽听见下面黑暗的楼道转弯处有两个女人在嘀嘀咕咕。他停下脚步犹豫起来,心想在这里嘀咕的多半是密谈。他不由得藏在墙拐角后面,竖起耳朵听下面的动静。
原来是人事科的王瑞对另一个女的说:“你记得吗?听说微信朋友圈里也有发的。眼下一边在封堵,一边在查人呢。初步定性是谣言。”
另一个女的一开口他就听出是李爱莲,她说:“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咋又翻腾出来了?”
王瑞说:“谁知道呢?最近一定要把嘴夹紧点。”
他当时就被震住了,紧张地分析起来。两个女人快要走到他面前时,他才反应过来。他突然一个急转身,与二人擦肩而过。他假装从兜里掏烟,感觉她俩要进办公室了,才偷偷瞟了一眼,却见王瑞正好回过头来。他霎时后悔刚才不应该转身,应该照直往前走,哪怕迎头撞上。这个急转身转得太不自然,让人觉得他不是偷听而是偷窥。
虽说“高马伐杀妻”是谣言,但传言日盛,朱西昆的后悔也日盛。睡不着的夜晚,朱西昆陷入难以自拔的思想怪圈。在这件事上,他始终围绕着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他为什么会告诉那个刘智勇?他为什么热衷于传播这类捕风捉影的八卦?他为什么要躲开单位同事,专门到那个夜市去买醉?痛定思痛,他不得不承认,他憎恶单位的同事,他憎恶单位那种特殊的氛围。正是这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憎恶,让他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报复加恶作剧的心理,故意传播单位的负面信息……
三
朱西昆思来想去,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那个叫刘智勇的到底是死是活。因讣告上没有贴照片,所以夜市上与他喝酒的那个人,究竟是不是讣告上的刘智勇,他拿不准了。查谣言的基本方法就是顺藤摸瓜,只要他们摸不着刘智勇那根藤,自然也就摸不到他朱西昆这个瓜。当然这个谣言从辛培仁那里就可能分岔了,顶多查到辛培仁头上。若辛培仁退休了,他来个死驴不怕狼啃,谁能把他咋样?苦就苦了他们这些在职的。新领导刚刚上任,不知是立威还是什么,在大会小会上声色俱厉地说新的工作要求空前严格,适应不了的人赶紧主动打报告分流,不要到最后让组织硬剥离,那就被动和难看了。想起自己在单位里的边缘化地位,朱西昆不寒而栗……
如何弄清刘智勇的死活?朱西昆反复梳理为他打探的人选。打听这种事最好问熟人。朱西昆意识到,这个事竟把他难住了。不知从何时起,办公室的同事都不太搭理他了。艾丽法、张羽高、李秉正、刘晓亮等人,他们常常聊得火热,就把他一个人晾在一边。每逢这种情况,他心里就会涌出一股酸涩难忍的滋味。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过去反思这个问题,他总觉得别人不搭理他,是因为他不搭理别人。而他之所以不搭理别人,是因为他有更高端的理想——写小说。每当写作被同事们的聊天打断的时候,他心中就会冒起一股火,不由得怀着一丝厌恶和轻蔑旁听他们的闲聊。他发现同事们的闲聊,极其无聊,除了满足低级趣味还能有什么用呢?
有时候,他也对自己产生过怀疑。但他想到曾经读过的一些书,里面说人际关系就是靠大量的废话来维持的。日常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大道理可讲?不就是些庸俗的日常趣味吗?言不由衷的恭维,吃吃喝喝,互相利用,柴米油盐……尤其是男女关系,都是日常趣味的重要养分、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尽管朱西昆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可是为时已晚,他已经成为众人眼里不太好交往的孤家寡人。如果要重新融入大伙儿之中,他就不得不涎着脸主动跟每个人搭讪。想到这一层他就感到一种深深的屈辱,面子上放不下。毕竟五六十岁的人了,到了该受尊重的年龄,又岂能低声下气去讨好年轻人?但如不低声下气改变自己,众人岂能为你一人而改变?他觉得他和办公室的庸众们渐渐陷入一种对峙状态。
你们不理解就不理解吧,孤立就孤立吧,嘲笑就嘲笑吧,你们的所作所为丝毫不影响我这份事业的高端性,更不影响我存在的价值。他常常这么给自己打气。
而此时此刻,他发现他的清高快要支撑不住了。找谁去打探刘智勇究竟是死还是活?他想起单位里那些表情冷漠的面孔。但为了心里踏实,为了走好下一步,他不得不跟他们套近乎。他按照书里的指导,努力把坏事往好处想,鼓起行动的勇气。他绞尽脑汁设计谈话方案,想着如何从日常琐事开始,最终把话题扯到刘智勇的死活上去。
李秉正、刘晓亮、张羽高,他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和他们逐一搭讪。他们有的手头正忙,爱理不理;有的正与别人聊天,话头插不进去;有的啥理由也没有,就是冷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却是“不知道”三个字。
冷静下来后,他想人家没必要和他过不去,或许他们真的不知道刘智勇这个人。他们单位人多,人员流动频繁,通常只有领导才有几分知名度。而这个所谓的刘智勇,他一想起看讣告时那个闲人的话,就觉得刘智勇八成是个边缘人物,觉得在他认识的有限几个人之中恐怕很难打听到刘智勇的下落。
有一次,他无意中在艾丽法的电脑里发现各科室的全家福。他一个个文件夹打开搜寻,无数张脸一一掠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发现了那张脸,他悄悄地把那张脸打印出来揣在钱夹里。
四
想在他熟悉的小圈子里弄清刘智勇的死活,恐怕希望渺茫了。就在他打算听天由命的时候,关铁梁忽然闯进他的脑海里。此人喜欢读小说,自从偶然读了他的小说后,对他大为钦佩,是他的热心读者。关铁梁就在纪委工作。那个看讣告的闲人不是说刘智勇是个告状油子吗?或许关铁梁能知道他的下落。
他四处打听刘智勇的下落,其实怕的就是纪委有朝一日会找他的麻烦。
他怀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踅摸到关铁梁办公室前,赫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正舞着双手,激动地向关铁梁诉说着什么。他定神对那背影细细一看,顷刻间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后撤两步竖起耳朵一听,原来是高马伐要见纪委书记,关铁梁正苦口婆心地跟他解释书记开会去了。
高马伐急着找纪委书记想干啥?他本来打算撤了,一想到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又不想走了。他想长时间躲在门外偷听也不是个事儿,就左右环顾,忽见关铁梁办公室的斜对面正是卫生间。他略略向左偏着头从关铁梁的门前飘然而过,一头扎进卫生间,装作如厕出来的模样拧开了水龙头,边洗手边通过面前的大镜子站到某个合适的角度,让高马伐的背影和关铁梁的侧影都出现在镜面里。他仔细观察、凝神聆听——他们好像在争某件事的结论。
“口头的话算什么?口头的话就像一个屁,风一刮就散了,我要的是正式文件,你们有吗?有一张纸也行啊,拿出来给我看看!”高马伐高声叫道。关铁梁抹了一把脸,哑口无言。高马伐为何如此激动?难道这里面横生了什么变故?不到五分钟,高马伐终于沉不住气了,气势汹汹地宣布:“我老婆失踪的案子出现了重大线索,雷亚明在三亚看见她啦!”
怎么可能?高马伐老婆都失踪二十年了,怎么会突然在三亚现身?还被一个有名有姓的雷亚明看见了……他晃了晃脑袋,耳朵里又出现了高马伐激动的控诉——控诉当年不经调查就对他采取的不人道措施,包括那三天的隔离审查;控诉这么多年来大家对他的歧视,耽误了他的大好前程;控诉这么多年来他所背负的精神包袱,晚上睡觉总做噩梦……高马伐要求纪委马上派工作组去三亚找雷亚明取证,协调当地公安机关查明他老婆的下落。最后他把话题扯到了当下,说直到最近还有人在微信朋友圈里造谣。他要求纪委把事情查明之后,一定把这些造谣诬陷者揪出来,看看他们阴暗的内心世界里都窝藏着些什么肮脏的动机……
五
老干部科的李科长没想到宣传科放着那么多一线科室不采访,竟然采访到他这里来了。可能因为激动或没个思想准备,接受采访时他有些语无伦次、结结巴巴。
朱西昆不得不把所谓的全面工作,化作一些具體问题。虽然采访是装装样子,是暗度陈仓,但不知咋的最近他忽然对退休后的生活关注起来了。
“李哥,我注意到单位每逢重大会议,都有退休老干部代表参加,好几十人呢,他们都是自愿参加的吗?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朱西昆问。
李科长神秘地一笑,说:“你算是问对了。你这是问到了退休老干部的管理问题。有的人一退休那就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可难管了。咱们单位呢,老干部不但不给组织上添乱,不给领导添堵,反而处处捧场。这里面有道道……”
一个不合时宜的电话忽然打了进来,李科长掏出手机一看就皱起了眉头。他对着手机,“嗯嗯”了几声,转脸对朱西昆说:“王主任找我谈点事。这样,我把刘英才叫来,老干部工作他有一本账。”
刘英才显然不像一把手站位那么高,他大大咧咧地侃道:“这些老干部呀,都是闲得难受。刚退下来的时候觉得很自由,但自由了两三年就着急了。没人搭理了能不着急吗?他们都想见人,还都有点摆架子。我们这一组织,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见面的机会。说好听点,叫找一点归属感或存在感。再说了,靠我们几个人哪能管得过来?但我们给他们分成了十个小组,选了十个小组长。有事了靠这些小组长跑动,他们积极着呢……”
隔壁活动室两个老头的声调突然越拔越高,显然是吵起来了。
一个说:“老子是一九四八年扛的枪!”
另一个说:“老子是一九四六年扛的枪!”
头一个厉声质问:“一九四六年扛枪你打的是谁?”
“你——你——你——”一九四六年扛枪的突然张口结舌,显然被对方捏住了七寸,而且被捏得不轻。
“坏了!”刘英才脸色大变,丢下朱西昆冲到隔壁。
机会提前到了,再不需要跟刘英才周旋下去。朱西昆利索地在刘英才的电脑里倒腾起来。突然他在E盘里发现一个“去世人员”的文件夹。一种直觉抓住了他,他觉得这个文件夹有点门道,点开一看,一股成功的喜悦涌上心头。里面是一个标注“去世职工干部丧葬情况登记”的文件夹,他用食指颤抖着点开了它。经过一番紧张焦虑的搜索,他终于看见了名为“刘智勇”的二级文件夹,点进去里面有张表格。他颤抖着手把表格点开一看,右上角有张照片,却压根儿不是他想找的那个刘智勇。
难道那个人还活着?他又想起高马伐的叫嚣,嘴里不禁一阵发苦……
刘英才回来了,边扯了一张餐巾纸擦脑门上的汗,边苦笑着解释说:“两个杠精,为了问干部病房的事杠上了,互相摆资格。老张说自己是一九四八年扛的枪,老魏一急,就说自己是一九四六年扛的枪。但他一九四六年扛的是国民党的枪嘛,一九四九年才过来的。让人家老张抓住把柄了,噎得够呛,差点要送医院……”
六
朱西昆呆坐在办公室里,反复思索着一些问题:难道真的一开始就弄错了?那个人压根儿就不叫刘智勇?他为什么会弄错?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纪委。他横下一条心了,想最后一搏。
关铁梁依旧待他很热情,打听着他小说创作的事。稍稍闲扯几句,他就开始问正事:“以前有个叫刘智勇的告状油子,你认识吗?”
“认识啊。”
“听说,他已经……”
他还没说完,关铁梁就说:“没错,他再也不会麻烦我们了。”
朱西昆咬着嘴唇,掏出那张事先打印好的表格,指着那张照片问道:“是这个人吗?”
关铁梁瞟了一眼表格上的照片,说:“老干科这帮人,这都能搞错!”
“这不是刘智勇?”他问道。
“不是,这是另一个,也死了。他们张冠李戴嘛。”
一阵激动的暖流涌上了心头,他有点冒失地从钱夹里掏出另一张打印的照片,指着这张折磨了他一个多月的脸,问:“那这个是刘智勇吧?”他的声音里既有紧张和激动,又带着一丝循循善诱的味道,像是诱供。
关铁梁仔细地看了一会,问:“你要干啥?为啥对刘智勇这么感兴趣?”
“我……”朱西昆突然灵光一现说,“这个人,跟我要写的一篇小说有关系。你就直说吧,是不是?”
关铁梁忽然说:“写小说?写小说最讲究悬念,对不?”他不知关铁梁是什么意思,只得茫然地点点头。
“那我告诉你,这位也不是刘智勇。”
他盯着关铁梁的脸,真想给他一记耳光。可他立刻意识到他是在求别人,只得强压怒火,硬挤出一脸低三下四的笑,说:“哥们!我可是认真的,这到底是不是刘智勇?”
“我也是认真的,这不是。”
七
夜色墨染,人声喧哗。头顶的串串灯宛如漫天星辰,直铺向远方。烟雾由近及远袅袅腾空,食客酡红的脸,在烟雾里若隐若现。
又是一个周末,朱西昆坐在烤肉摊前固定的位置上。两瓶啤酒下肚,他直愣愣地凝视着前方的舞台。台上两个浓妆艳抹的演员,正咿咿呀呀地唱着《霸王别姬》。他的注意力渐渐被那个虞姬所吸引。虞姬在台上妖娆地舞动着,端庄而悲切地唱着。看着看着,他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再仔细地观察辨认,终于发现这虞姬的妖娆只可远观不堪细看。她的骨架太大了。妖娆华丽的凤冠霞帔遮掩着大身架,让人觉得更加别扭。他不由得拿着啤酒跑到离舞台最近的一张空桌坐下。这离近了一看,便看出了端倪,这虞姬不但骨架大,手也是骨节粗大的男人的手。一唱起来,突出的喉结像只老鼠上下滑动。他几乎断定,这是个男的。
他觉得既倒胃口,又夹杂着一丝奇怪的感动。虞姬仿佛也注意到台下只有朱西昆一直在盯着看,竟回报以遇到知音似的一眼。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正是虞姬那粗重墨线勾勒的一对眼珠子,勾起了他一段似曾相识的记忆。
他盯着虞姬不放,一定要把那熟悉的记忆从脑海深处捞起来。虞姬下场,卸妆从后台走出来时,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刘智勇!那一刻,一种熟悉的惊恐和焦虑翻涌上来……
不过,他迅速地回过神來,浑身一阵释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退休两年了,按三十年工龄退的。
责任编辑蓝雅萍
特邀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