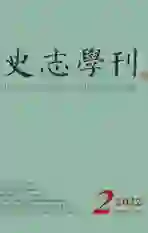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盐业经济
2022-05-25薛瑞泽
薛瑞泽
摘 要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盐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对盐业资源的认识逐步全面,不仅对以河东盐池为主的盐业资源有了深刻认识,而且弄清了沿黄河中游广泛分布的盐池,特别是对东部沿海地区海盐资源的分布有了新的认识。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盐业经济的发展与盐的经营即官营与私营交织在一起,折射出皇权与豪强势力角逐的历史场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盐业经济以国家经营为主,但在特殊的情况下,私营盐业经济仍然有所体现。
关键词 秦汉魏晋南北朝 盐业 盐池
盐铁大利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要财政收入,历来备受重视。随着先秦时期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开发,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有利于盐业经济的发展。秦汉时期对黄河中下游地区产盐地的认识逐步全面,盐的生产与销售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官府对盐业生产和经营实行严格的管理,使盐业经营收入成为官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盐业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盐业资源的分布
黄河中下游地区盐业资源丰富,分布非常广泛,既有以河东郡盐池为代表的内地盐业资源,也有在北方沿黄河两岸分布的一系列盐池,还有在沿海地区广泛存在的海盐盐业资源。广泛分布的盐业资源成为官府所依赖的支柱产业和财政来源之一。
首先,河东地区的盐池,在先秦时期即已成为有名的产盐地。《左传·成公六年(前585)》曰:“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杜预注:“盬,盐也。猗氏县盐池,是。”[1](P723)这说明在春秋时期已经对盐池有了认识。《山海经·北山经》云:“景山,南望盐贩之泽。”郭璞云:“即盐池也。今在河东猗氏县。”[2](P107)这表明至少在战国时期河东盐池已经成为著名的产盐地。秦昭襄王十一年(前296),齐、韩、魏、赵、宋、中山等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正义》:“《括地志》云:‘盐故城一名司盐城,在蒲州安邑县。按:掌盐池之官,因称氏。”[3]可见安邑县产盐并且出现了以“盐氏”命名的地名。秦国的“猗顿用盬盐起”,《索隐》云:“盬谓出盐直用不炼也。一说云盬盐,河东大盐。”《正义》案:“猗氏,蒲州縣也。河东盐池是畦盐。作‘畦,若种韭一畦。天雨下,池中咸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许坑,日暴之五六日则成,盐若白礬石,大小如双陆及棋,则呼为畦盐。”[4](P529-3260)河东所产的盐有“河东大盐”“畦盐”等不同的称呼。盐池所产的盐在战国时期已经外销,因为翻越太行山,路途极为艰苦。《战国策·楚策四·汗明见春申君章》云:“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以幂之。”[5](P497)汗明在这里虽然是赞美伯乐善于相马,但表明用马车将盐池的盐外销已经成为战国时期影响颇大的经济活动。贾谊《吊屈原赋》有“骥垂两耳兮服盐车”[6](P2493)之句描述这一经济活动。西晋潘尼《怀退赋》有“困吴坂之峻岨,畏盐车之严筴”[7](P472)。这是借用贾谊《吊屈原赋》表达对贤才被排挤的不满。曹毗《对儒》亦以“负盐车以显能”[8](P2387)对战国时期运输河东盐池所产盐的现象予以描述。
两汉时期,盐池受到官府的重视,西汉设有“盐官”进行管理。“安邑,巫咸山在南,盐池在西南。魏绛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有铁官、盐官。”[9](P1550)这里道明了盐池在安邑县的西南位置,汉代设有盐官进行管理。《续汉书·郡国志一》亦云安邑“有盐池”,刘昭注补引杨佺期《洛阳记》曰:“河东盐池长七十里,广七里,水气紫色。有别御盐,四面刻如印齿文章,字妙不可述。”无论司马彪《续汉书》或杨佺期《洛阳记》均成书于晋代,关于盐池的记述,至少反映了汉晋时期盐池的情况。正因为盐池的盐是重要的战略物资,除设盐官进行管理外,两汉皇帝对盐池巡视进一步彰显了对盐池的重视。西汉时期,元鼎五年(前112)三月,汉武帝借祭后土之际,“览盐池”。师古曰:“龙门山在今蒲州龙门县北。盐池在今虞州安邑县南。”[10](P3535)东汉时期,元和三年(86)八月,汉章帝“幸安邑,观盐池”。李贤注云:“许慎云:‘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一十六里。今蒲州虞乡县西。”[11](P156)汉武帝与汉章帝巡视盐池,正反映了盐池产盐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作为重要的产盐地,东汉盐池属于民曹所管辖,《续汉书·百官志》曰:“民曹主缮治、攻作、盐池、苑囿。”[12](P1014)熹平四年(175)六月,汉灵帝“遣守宫令之盐监,穿渠为民兴利”。李贤注云:“《前书·地理志》及《续汉·郡国志》并无盐监,今蒲州安邑西南有盐池监也。”[13](P337)从河东盐池设盐官,到汉武帝与汉章帝的巡视,及至汉灵帝特设盐池监的一系列变化可知,官府对盐池的盐业资源非常重视。
其次,除了河东盐池之外,在黄河中游地区还有多处盐池分布。《正义》案:“或有花盐,缘黄河盐池有八九所,而盐州有乌池,犹出三色盐,有井盐、畦盐、花盐。其池中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盐,掘取若至一丈,则著平石无盐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盐。畦盐若河东者。花盐,池中雨下,随而大小成盐,其下方微空,上头随雨下池中,其滴高起若塔子形处曰花盐,亦曰即成盐焉。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马尽汲此井。其盐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池中又凿得盐块,阔一尺余,高二尺,白色光明洞彻,年贡之也。”[14](P3260)由此可知,沿黄河分布着八九所盐池,盐州(今陕西省定边县)乌池有多色盐池,还根据生产方式不同有井盐、畦盐、花盐的区分。在今陕北榆林也有盐池,汉顺帝永建四年(129),虞诩《请复三郡疏》记载:“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李贤注云:“上郡龟兹县有盐官,即雍州之域也。”[15](P2893)龟兹县在今陕西省榆林市北。这说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着众多的盐池。东汉末年,北地郡以产戎盐而引起关注。所谓戎盐即岩盐,因产于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故名。《神农本草经》卷三《下经·戎盐》记载,戎盐又名胡盐,黄河中游地区以北地郡(今甘肃省庆阳市)最为有名。
在關中地区长安附近也有盐池分布,左冯翊莲勺县(今陕西渭南市东北来化镇村)有盐池。汉宣帝未即位前游手好闲,“常困于莲勺卤中”,如淳曰:“为人所困辱也。莲勺县有盐池,纵广十余里,其乡人名为卤中。”师古曰:“如说是也。卤者,咸地也,今在栎阳县东。其乡人谓此中为卤盐池也。”[16](P237-238)这是三辅地区的盐池,方圆十里,因靠近京城故而备受关注。从上述相关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黄河中游地区分布着各种类型的盐池,分布的地点以黄河中游的今山西省运城市、陕西省北部和中部地区为主。
再次,黄河下游濒临东部海域的沿海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重要的海盐产地。海盐主要是煮海水为盐。《尚书·禹贡》记述,青州“厥贡盐絺”。《索隐》云:“散盐,东海煮水为盐也。”[2](P3259)东海即今黄海、渤海滨海地区,盐业资源非常丰富。苏秦曾经说“齐必致鱼盐之海”[17](P2245)。张仪也说“齐献鱼盐之地”[18](P2296)。这说明齐地海盐资源之丰富。战国时期,尸佼《尸子》卷下曾提到“北海之盐”,似乎也应是指齐地的盐业经济。
两汉时期,海盐生产备受重视,形成了沿渤海湾沿岸众多的产盐地。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上,贤良大夫也曾说“齐之鱼盐”资源,“待商而通”[19](P7),足以显示齐地盐业资源的商业价值。汉元帝永光年间,平当巡视幽州流民,“举奏刺史二千石劳俫有意者,言勃海盐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师古曰:“恣民煮盐,官不专也。”[20](P3050)可见勃海郡盐池资源之丰富。扬雄《青州箴》云:“茫茫青州,海岱是极,盐铁之地。”[21](P113)熹平元年(172)四月《东海庙碑》中有“濒海盐□,月有贵贱”,应是言及海盐的价格。徐幹《齐都赋》有云:“若其大利,则海滨博者,溲盐是钟。皓皓乎若白雪之积,鄂鄂乎若景阿之崇。”[22](P657)徐幹以其形象的语言对齐滨海地区盐业经济发展的盛况进行了描写。值得令人注意的是,在汉代齐地甚至出现了以盐命名的地名。《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东平国”条云:“东平国,故梁国,景帝中六年别为济东国,武帝元鼎元年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为东平国。莽曰有盐。属兖州。户十三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口六十万七千九百七十六。有铁官。县七:无盐,有郈乡。莽曰有盐亭……”[23](P1637)东汉这里仍然有“无盐”城[24](P3452)。这里出现了“有盐”“无盐”“盐亭”等,应当与产盐地密切相关。胶水在当利县入海,“海南,土山以北,悉盐坈,相承修煮不辍”[25](P431),很明显也是重要的产盐地。当时还留下了盐生产的纪录,《风俗通》曰:“东海昫人晓知盐法者云:搅盐木水多日,每焦黑如炭。”[26](P3840)由此可知,两汉时期,勃海郡以及兖州、青州所辖的沿海郡国以海盐生产居多,也是黄河下游地区海盐生产的集中地。
先秦以来黄河中下游地区盐业资源的分布呈现出两种类型,一类是黄河中游地区以盐池为代表的沿黄河两岸众多盐池分布,另一类是黄河下游滨海地区的海盐资源。这两种类型的盐业资源在满足当地需要的同时,运销北方广大地区。
二、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盐业经济
盐作为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从秦汉以来就是官府专营的商品,盐的销售成为官府所关注的重要收入来源。又因为盐铁经营获利颇丰,盐的经营又成为权贵插手的重要财经领域,秦汉中央政府就是在与权贵争夺盐铁专营权的较量中逐步增加财政收入的。
秦代盐是作为专营产品由官府经营。董仲舒指出秦代“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如淳曰:“秦卖盐铁贵,故下民受其困也。”师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赋,而官更夺盐铁之利。率计今人一岁之中,失其资产,二十倍多于古也。”可见秦代盐铁专营获利颇丰。有鉴于此,董仲舒建议朝廷“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27](P1137-1138)。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这一建议,一方面理想化地提出堵塞豪强兼并,另一方面将盐铁的经营权放归民间。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此之前豪强兼并,与朝廷争夺盐铁大利已经趋于白热化,加之朝廷对外连年战争,财政非常紧张,盐铁官营显然能够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元狩三年(前120)秋,因为关东地区连年遭受水灾,朝廷不得不将七十余万人迁往朔方以南新秦中,为了维持这些人的生存需求,国库为之空虚。而富商大贾凭借经商获利颇丰,“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特别是富商大贾因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通过改革币制等一系列的措施对富商大贾把持盐业经营进行打击。为了彻底打击豪强势力,汉武帝选拔熟知盐铁经营的商人担任管理盐铁事务的官员,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汉武帝之所以任用东郭咸阳,是因为其为“齐之大煮盐”。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进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这是进一步强调盐铁官营的政策,并且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对“浮食奇民”私自经营进行管束,“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随后,汉武帝又派出“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28](P1425-1429)。汉武帝任用盐铁商人管理盐铁经营,是因为这些人熟悉富商大贾经营盐铁的策略,可以做到有的放矢。盐铁官营是汉武帝时期的显著特色,汉武帝此举被称为“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29](P3140)。因为杨可告缗对富商大贾的打击,朝廷收入迅速增加,“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30](P1170)。然而,在官府掌管盐铁官营之后,弊端开始出现,卜式为御史大夫时,“见郡国多不便县官(朝廷——引者注)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随着汉武帝灭两越,花费越来越大,“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元封元年(前110),卜式被贬为太子太傅[31](P2628)。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兼领大农,“尽代(孔)仅斡天下盐铁”,却导致物价上涨,于是“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32](P1174-1175)。汉武帝仍然是想通过设立平准以控制物价。汉昭帝即位之初,霍光掌权,“承奢侈师旅之后,海内虚耗,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至于始元、元凤之间,匈奴乡化,百姓益富,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于是罢酒榷而议盐铁矣”[33](P3624)。始元六年(前81)二月,“议罢盐铁榷酤”。应劭曰:“武帝时,以国用不足,县官悉自卖盐铁,酤酒。昭帝务本抑末,不与天下争利,故罢之。”[34](P223)西汉中期,豪强势力迅速膨胀,“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利用霸占的海洋资源,“煮盐”,并利用盐业经济的收入,聚拢民众,“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35](P42)。这足以说明豪强势力垄断盐业经营对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地节四年(前66)九月,因为水灾危害甚巨,在赈贷百姓的同时,汉宣帝诏曰:“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36](P252)汉元帝即位后,“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初元)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37](P1142)。初元五年(前44)四月废除盐铁官,永光三年(前41)冬,“复盐铁官、博士弟子员”[38]。这次恢复盐铁官设置,是因为永光元年(前43)后,“其后用度不足”,才“独复盐铁官”[4](P1142)。在大司农之下设有斡官,如淳曰:“斡音筦,或作幹。斡,主也,主均输之事,所谓斡盐铁而榷酒酤也。”[39](P731)这是朝廷内部专设管理盐、铁、酒专卖事务的官员。始建国二年(8)二月,王莽“初设六管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40](P4118)。这其实是通过专卖盐铁酒,实现官府的增收。
黃河中下游地区不产盐的郡县往往需要到产盐地将盐运回贩卖。王莽末年,南阳冠军人贾复为县掾,“迎盐河东,会遇盗贼,等比十余人皆放散其盐,复独完以还县,县中称其信”[41](P664)。这既反映了河东盐池运销的地域,也说明运盐的路途并不平安,时刻会遇到盗贼抢劫盐,进一步证明官营盐业对民众需求所造成的影响;而贾复将盐运回,其他十余人则抛下盐逃命,证明了运输途中损耗之大,这也反映了盐业经营过程之艰难。在盐的经营过程中已经有了新的认识,焦赣《易林·无妄之解》有“鹤鸣九皋,处子失时。载土贩盐,难为功力”[42](P255)之说,《说文》曰:“故宿沙煮海水为盐,盐咸也。”这说明贩盐也要把握时机。《九章算术》中记载运输盐的价格,颇有实录的性质:“今有取佣,负盐二斛,行一百里,与钱四十。今负盐一斛七斗三升少半升,行八十里。问与钱几何?答曰:二十七钱一十五分钱之一十一。术曰:置盐二斛升数,以一百里乘之为法。以四十钱乘今负盐升数,又以八十里乘之,为实。实如法得一钱。”[43](P324)这里收录运输盐的数量与距离应花费的钱的数量,说明运输盐是商业行为。
东汉时期,盐铁的官营与私营的角逐自始至终都存在,并且成为封建皇权与豪强势力强弱变化的晴雨表。建初六年(81),汉章帝“议复盐铁官”,李贤注云:“武帝时国用不足,乃卖盐铁,置官以主之。昭帝罢之,今议欲复之。”大司农郑众“谏以为不可”,但汉章帝没有采纳郑众的建议,最终推行了盐铁官营[44](P1225-1226)。元和年间(84—87),因征讨匈奴花费了大量财力,造成国库空虚,尚书张林上言:“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尚书朱晖则云:“盐利归官,则下人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诚非明主所当宜行。”结果汉章帝大怒,严厉责备诸尚书[45](P1460)。可见在朝廷内部关于盐铁的官营或私营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汉章帝主张官营,说明盐的官营对解决财政危机的重要性。章和二年(88)二月,汉和帝即位之后,四月即颁布了那篇著名的将盐铁经营权放归民间的诏令,其实当时汉和帝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听政,所颁布的诏令即是窦太后代表豪强势力侵吞盐铁大利的举动,诏曰:“昔孝武皇帝致诛胡、越,故权收盐铁之利,以奉师旅之费。自中兴以来,匈奴未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休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顺圣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46](P167-168)通过这一诏书我们可以看出代表豪强势力的窦太后似乎颇为关注民间疾苦,但其实当时东汉王朝经过光武帝、汉明帝和汉章帝的恢复与发展,豪强势力已经快速膨胀起来,为了迷惑民众,窦太后的诏书中首先回顾了汉武帝为了“诛胡、越”,“权收盐铁之利”以解决军费问题。永平年间,汉明帝为了边境地区的安全,“探观旧典,复收盐铁”。在她看来盐铁官营过程中,“吏多不良,动失其便”。所以,她借汉章帝的“遗戒”,果断采取措施,“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这一诏令其实为豪强势力垄断盐铁经营开启了绿灯。盐税作为朝廷重要的收入,有时甚至为权贵所觊觎,汉桓帝时,史弼任河东郡太守,中常侍侯览派遣儒生带信请求举荐其近属为孝廉,甚而“并求假盐税”,史弼大怒,当天就处死侯览所派的近属[47](P2111)。史弼之所以有此胆量硬抗宦官,除了其刚正不阿之外,盐税作为朝廷的重要收入宦官竟敢插手,也是史弼动怒的原因。
东汉时期,民间私人贩盐成为一时风尚。东汉初年,京兆长陵人第五伦感到为官难以升迁,就改名换姓携带家属客居河东郡,“载盐往来太原、上党”[48](P1396),这是民间私下贩盐的确证,贩盐的地点是河东郡临近的太原郡、上党郡。东郡太守羊茂,“常食干饭,出界买盐,致妻子,不历官舍”[49](P1222)。羊茂为了显示自己的清廉,不在自己担任东郡太守的东郡买盐,而是不顾路程遥远辗转到其他郡购买。《东观汉记》曰:“司空宋弘常受俸得盐鼓千斛,遣诸生迎取上河,令粜之。盐贱,诸生不粜。弘怒使遣。及其贱悉粜卖,不与民争利。”[50](P3692)宋弘从上河郡(今陕西省绥德县)受赐“盐鼓千斛”,且将其出卖,显示出官员出卖盐制品,且不与民争利。身为外戚的梁商将盐送给贫穷的百姓则深得舆论的赞美。《东观汉记》曰:“梁商,饥年谷贵民馁,辄遣苍头去帻着巾,车载米盐菜钱于四城门与贫乏,不语主人。”[51](P2184)《古艳歌》亦有“白盐海东来,美豉出鲁门”美句,表明东海地区的盐销往内地的情况。
盐的经营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置相关官员进行管理。《续汉书·百官志一》记载,在太尉府之下设有“金曹主货币、盐、铁事”。这一主管盐铁事务的金曹是朝廷管理盐铁事务的官员。地方上盐铁官从属两汉时期经历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变化,“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汉代少府也有征收盐税的责任,《汉官仪》曰:“田租、刍槀以给经用,凶年,山泽鱼盐市税少府以给私用也。”[52](P3590-3592)这是在歉收之年,盐税交给少府而不入国库。边域地区的郡县设有盐官,《续汉书·百官志五》云:“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刘昭注补引胡广曰:“盐官掊坑而得盐,或有凿井煮海水而以得之者。”盐官的设置是汉武帝时期开始的,从各地盐官的设置也可以看出朝廷对盐业经营的重视。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东郡安邑县,太原郡及其属县晋阳县,巨鹿郡,千乘郡,北海郡的都昌、寿光,东莱郡的曲成、东牟、、昌阳、当利等,琅邪郡的海曲、计斤、长广等,陇西郡,安定郡三水,北地郡弋居、上郡独乐、龟兹,西河郡富昌、博陵,雁门郡楼烦等郡县,均有盐官的设立。这些盐官的设立是为适应官府垄断盐经营的需求。
两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盐业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因素影响颇大。当朝廷实行盐的官营之时,往往是皇权较强时期,从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到汉章帝将盐的经营权收归官府来看,盐的经营权归官府所有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使豪强势力难以凭借经营盐的收入与朝廷相抗衡。当豪强势力掌握了盐的经营后,往往利用经营盐的收入,动摇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从西汉后期与汉和帝以后放宽盐铁官营政策允许民间经营即可得以体现。
三、魏晋南北朝黄河中下游地区盐业经济
盐业经济作为封建时代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原有的产盐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引起政府的重视。不仅河东郡的盐池、东部沿海地区的海盐生产持续引起人们的关注,到北魏时期,河套地区甚至漠南的盐池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河东的盐池成为时人记述的重要产盐地。《神农本草经》卷三《下经》云:“大盐,生邯郸又河东,卤盐,生河东盐池。”“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十六里。”[53](P90)这是曹魏时期对盐池最为全面的记述,较之于杨佺期记载的面积周长少21里。盐池在相关的诗文中也多有记载。孔融《同岁论》曰:“弊箅径尺,不足以救盐池之咸。”[54](P3362)卢毓《冀州论》有“河东有大盐”[55](P657)之说。晋代这种记载更多,郭璞《盐池赋》曰:“水润下以作咸,莫斯盐之最灵。傍峻岳以发源,池茫尔而海渟。”描述盐的形成有“颖跃结而沦成”佳句,描述盐池的景象有“狀委蛇其若汉,流漫漫以漭漭。吁凿凿以粲粲,色皜然而雪朗。扬赤波之焕烂,光旰旰以晃晃。隆阳映而不燋,洪涔沃而不长。磊崔碓,锷剡棋方。玉润膏津,雪白凌冈。粲如散茧,焕若布璋。”对于盐池的形成郭璞认为是集天地日月的精华而成,“兹池之所产,带神邑之名岳。吸灵润于河汾,总膏液乎浍涑”[56](P173-174)。可以说郭璞将盐池的形成、盐的品质以及盐的来源做了形象的描述,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张华《博物志》曰:“河东有山泽近盐。”[57](P791)孙楚《出歌》曰:“白盐出河东。”[58](P3846)王廙《洛都赋》云:“其河东盐池,玉洁水鲜;不劳煮沷,成之自然。”[3](P657)左思《魏都赋》描述“墨井盐池”有“玄滋素液”等滋水、液水的流入。李善注云:“河东猗氏南有盐池,东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59](P267-268)这些关于河东盐池的描述无一不是对河东地区盐池所产盐在社会经济中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黄河中下游地区东部沿海地区所产海盐也颇受关注。东海地区的盐多运销内地。石崇《奴券》“取东海巨盐”[60](P2694),潘岳《沧海赋》“煮水而盐成”,都是东海地区煮海为盐的真实记载。煮海为盐在十六国后赵时期依然兴盛。在清河入海的漂榆邑就是以煮盐出名,《赵记》云:“石勒使王述煮盐于角飞,即城异名矣。”成书于北魏的《魏土地记》曰:“高城县东北百里,北尽漂榆,东临巨海,民咸煮海水,藉盐为业,即此城也。清河自是入于海。”[61](P159)由于盐业经济的发展,北魏时期黄河下游地区沿海一带出现了一些以盐命名的地名。如在定州博陵郡安国县有盐石渊,在沧州乐陵郡阳信县有盐山神祠[62](P2463,2473),在兖州东平郡无盐县有无盐城,在南青州义塘郡归义县有盐仓[63](2521,2550)。这些以盐命名的地名与盐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很明显是对汉代产盐地的继承。
北魏时期,对漠南地区的一些盐池给予充分的关注。道武帝在登国六年(391)十二月,“车驾次于盐池(今宁夏境内)”。次年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盐池(今陕西省定边县)”。登国十年五月,道武帝再次“幸盐池”。天赐三年(406)九月甲戌朔,“幸漠南盐池(今内蒙古自治区商都县东南察汗淖尔)。壬午,至漠中,观天盐池(今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东北);度漠,北之吐盐池(今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左旗东北)”[64](P43)。另外,在河西有“白盐池”[65](P2055)。在雍州冯翊郡频阳县有南卤原、盐池[66](P2608),应当是北魏时期新形成的盐池。
综合上述盐池的分布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盐的产地较之于此前进一步增多,既有内陆的盐池,还有沿海地区的海盐产地。除了传统的河东盐池所产之盐是官府所关注的重点外,一些新的盐池名称引起人们的关注。上述盐池在河东地区,黑盐池在今陕西省定边县西北,属于黄河中游地区无疑。其他三个漠南盐池、天盐池、吐盐池均在漠南一带。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盐业经济作为与国计民生密切相连的产业,其生产与经营都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建安四年(199)十一月,曹操派治书侍御史河东人卫觊镇抚关中,当时流民逐渐返回本土,“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面对这种情况,卫觊给荀彧写信求助如何处理:“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荀彧将卫凯的建议上报给曹操,曹操听从了这一建议,“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服从”[67](P784)。这是将盐的经营收归官府,并设谒者仆射监盐官进行管理。这仍然是通过恢复盐的官府专卖,用盐的收入购买犁牛发展农业经济的举措。嘉平四年(252),关中发生饥荒,司马懿“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68](P785)。很显然曹魏末年,在京兆、天水、南安等渭水流域三郡均有盐池,且由官府管理。西晋时期,继续实行官府直接管理的盐业政策,在安邑盐池设有司盐都尉,《晋太康地志》曰:“安邑有司盐都尉,别领兵五千。”[69](P791)司盐都尉同时兼领五千余军队,应当是保护盐池的士兵。与此同时,对于私下煮盐现象,官府处理非常严格。《晋令》曰:“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主吏二岁刑。”[70](P3840)可见对于私自煮盐者,不仅违犯者要判处四年刑罚,主管的官员也要负连带责任,判处二年刑罚。杜预任度支尚书时,向晋武帝提出“较盐运”等在内的“内以利国”治国策略五十余条,晋武帝“皆纳焉”[71](P1027)。石虎在位六年后,针对“星虹之变”天象异常,下诏“解西山之禁,蒲苇鱼盐除岁供之外,皆无所固”[72](P2770)。这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允许私人经营盐业。魏晋时期,在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的背景下,盐的经营归官府所有,利用经营盐业所获利润解决流民安置、军队供应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问题。为了维持盐业官营的秩序,朝廷不仅对盐池派兵守护,而且对私下经营者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
盐业经济在北朝的发展与北魏对黄河中下游地区产盐地的全面认识联系在一起,正是在对产盐地的认识基础之上,盐业经济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盐税成为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之一。正因为盐业经济的重要性,北魏时期盐的经营采取的是官营与私营并存的政策。对河东地区盐池的认识、管理达到了极致,不仅设置专门的官员进行管辖,还驻扎军队予以维护。为了提高河东盐池的产量,官府设置了专门的盐户进行生产。在特殊的环境下,盐池的税收成为官府的重要财政收入,盐池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产地。关于北魏河东盐池的生产、经营情况笔者已经做过专门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73]。
北朝时期,沿海地区的盐业资源不断刷新记录,成为新的盐业经济增长地。特别是河阴之变后,洛阳城被毁,东魏迁都邺城,沿海地区煮海为盐,解决了东魏北齐的财政问题。“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74](P2863)这说明北齐时期海鹽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兴和三年(541),高欢下令“于幽、瀛、沧、青四州傍海煮盐。军国之费,粗得周赡”[75](P4909)。武定年间,“右仆射崔暹奏请海沂煮盐,有利军国”。高澄询问崔昂,崔昂曰:“既官煮,须断人灶,官力虽多,不及人广。请准关市,薄为灶税,私馆官给,彼此有宜。”[76](P1180)高澄采纳了崔昂的建议,对海盐生产的煮盐及经营予以管理。
随着盐业经济的发展,对盐的品种分类更加详细。太武帝进攻彭城,送给刘义恭、刘骏等毡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李孝伯说:“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食;黑盐治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而服;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盐。”[77](P1170)这里所列举的除了白盐可以食用外,其他几种盐均是药用盐。这一事件在《宋书》中也有记载。《宋书》卷四十六《张邵传附兄子畅传》:
魏主又遣送毡及九种盐并胡豉,云:“此诸盐,各有宜。白盐是魏主所食。黑者疗腹胀气满,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疗目痛。柔盐不用食,疗马脊创。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
北魏与刘宋之间关于盐品种的演绎,正反映了盐业经济快速发展趋势,也显示了黄河流域的盐业经济对南朝的影响。
作为能够带来可观收入的经济门类,盐业经营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关注的产业,盐的贩运已经成为获利颇多的商业经营。太武帝时,李惠任雍州刺史,曾发生了争夺盐的案件,“人有负盐负薪者,同释重担,息于树阴”,结束休息准备出发前,因一张羊皮二人发生争执,李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击之,见少盐屑”,最后李惠处罚了“负薪者”[78](P1825)。宣武帝时,咸阳王元禧“昧求货贿,奴婢千数,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79](P537),使宣武帝非常讨厌他。在洛阳城外的洛阳大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洛阳城最为富有者刘宝,“于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一疋,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80](P157)。”再次表明了富商大贾贩运盐的普遍性。
盐铁大利作为封建国家财政的基础,在北朝依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从国家层面来看,对盐业资源进行管控,将其纳入政府的管辖,是实现对盐业经济控制的基础。无论在其下游产业的生产还是销售等环节都有政府可以直接插手的渠道,生产环节上官府可以直接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销售环节官府可以直接进行征税或者直接进行专营,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盐业作为利润丰厚的产业,也成为权贵借机插手的行业,体现出商业与政治的密不可分。(责编:唐越)
The Salt Economy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Qin, Han,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Xue Ruize
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Qin, Han,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alt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gradually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salt industry resources is not only about that represented by Hedong salt ponds, but also about the salt ponds wide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t is especially a new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distribution of sea salt resources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lt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was intertwined with the management of salt i.e., state-owned or private, which reflected the historical scene of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imperial power and powerful forces. During the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salt economy was dominated by the state, but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it was also managed by private businesses.
Key words the Qin, Han,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alt industry Salt p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