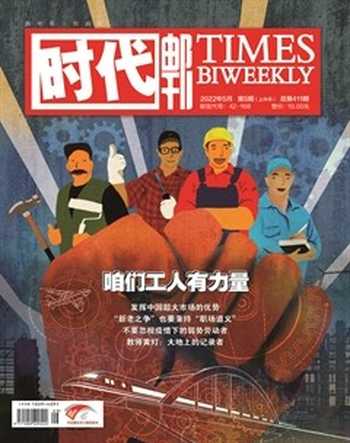走在研究“误诊”的坡道上
2022-05-20魏晞
魏晞

1985年,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部工作的陈晓红,画“正”字统计经手的死亡报告单。现在,71岁的她只要用计算机“跑一下”,有关误诊病历的数据就会出现在电子屏幕上。
究竟经手过多少份误诊病历报告?她记不清具体的数字了:“大约30万份吧。”
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就像攀登一座医学高山,分支众多的专科是从正面拾级而上,而研究误诊是从背面翻越,同样要经过陡坡和峭壁。如今,退休多年的陈晓红还在向上爬。
不是制造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
许多双眼睛关注着误诊研究:出版社时不时询问陈晓红的研究进度;程序员也加入研究,借助编程技术找到误诊疾病之间的相关性;科技公司找上门来,想收集她攒了30多年的误诊病历数据。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陈晓红和同伴完成第一版《误诊学》书稿时,却被出版社拒绝:“医生都要写经验,你这写的是反面。”为了让新书出版,她拜访当时的医学“大咖”,请他们帮忙写序。
吴阶平向她敞开了门。这位中国泌尿外科先驱者、诊治过周恩来总理的医生为了支持陈晓红,挨个通知当时在北京能找到的医学界院士参加新书出版的研讨会。“这也是我想做的事情,你们做了,我很激动。”“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也给她打气:“有人研究犯罪学,不是教人犯罪,是为了避免犯罪;同样,研究误诊不是教人误诊,而是要减少、避免误诊。”
1995年,陈晓红到《临床误诊误治》杂志当主编。那时医疗纠纷增多,承认误诊无异于“自找麻烦”。但一批老院士、老医生,愿意说“刺耳”的话,把封笔之作留在了这本杂志上。
如今,计算机帮助陈晓红找出了许多误诊规律。各级医院的医生都可能误诊:年轻医生误诊,大多因为经验不足,想不到是另一种病;老医生误诊大多因为经验太丰富,想当然。误诊不是A病被误诊为B病,而是A病可以被误诊为许多病,许多病可以被误诊为A病,不同问题互相交织。更麻烦的是,在今天,留给医生诊断的时间变少了。医生必须争分夺秒与疾病竞争,果断给出正确诊断。
扎进误诊研究几十年,陈晓红决定要做给临床医生提醒的人。“不让诊断走弯路。”为了提高杂志稿件水平,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晓红把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各个专科最资深的退休主任聘到编辑部,共同评审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
干了大半辈子临床的老主任们对这个新任务充满热情。有人常常边读稿边嘟囔:“我在临床见过这个案例。”有人看到稿件写得乱,忍不住上手逐句修改。还有人读着读着就拍桌而起:“这简直是草菅人命!”有时遇到连他们都没见过的案例,老主任们就一遍遍讨论、翻书。编辑部的几个大书架,很快就塞满了最新的医学书。
许多医生说,误诊推动着医生进一步認识人类的身体。其实,《临床误诊误治》的创刊人冯连元,最初也是为了汲取同行的误诊经验而创办杂志。当时,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很支持他,但也表示担忧:“这个名字会不会惹事?”思前想后,冯连元决定:文章隐去患者、医生名字,并适当修改一些细节,以免暴露患者个人信息。“办这个杂志,是要解决问题,不是制造问题。”
误诊是系统性难题
现代医学不断取得进步,但误诊依然每天在临床上发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生何权瀛认为,解决误诊是系统性工程。人类所掌握的医学知识越来越多,医学专科越分越细,许多医生只专注研究一个专科中的一种疾病,当患者有多种疾病时,就容易漏诊。
“就像用钻头打洞,越钻越深,最后看不见洞旁边的地方。”何权瀛研究睡眠呼吸暂停20多年,发现这个疾病可能引发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其他疾病。问诊时,他喜欢给病人列明各种疾病,细细提问,寻找每种疾病间的关联。但有的病人不愿回答过多问题:“你这个大夫这么烦人,给我开药不就完了。”
医患互相不信任,是导致误诊的原因之一。患者如今能从很多途径获取医学知识,但何权瀛认为,公众的卫生知识水平依然不够。前几年,《临床误诊误治》编辑部不时迎来“不速之客”——患者拿着一叠病历,希望编辑们评评理:“你们判断一下,我这是不是误诊了?”陈晓红总结,这种态度缘于知识不对等。当病人躺在床上接受检查时,他在仰视医生;但当医生看不懂疾病、下不了判断的时候,他也在仰视神秘复杂的医学宇宙。
误诊研究是医学发展的同行者。医疗检查技术的发展一度帮助医生作出正确判断,但陈晓红发现,过度依赖检查机器,成了新兴的误诊原因。几十年来,误诊的概念逐渐变广,对医生的要求更严格了。过去,医生诊断错了疾病才算误诊,如今即使诊断正确,但是治疗用药不恰当,或是初诊时判断错误,也算误诊。
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数据,临床医学的平均误诊率为30%,其中80%的医疗失误是思维和认识错误导致的。为了获取经验而办刊的冯连元,如今已在临床工作了近40年,攒足了经验。但他发现,即使有了经验,也还是可能误诊。
对于常见的疾病,医生要根据对应的诊疗指南用药、治疗,但指南里的标准,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每个病人。比如,按指南规定,煤气中毒病人要输液200毫克烟酸,但冯连元遇见过超出想象的情况:用2000毫克、指南所写的10倍量的烟酸,才救回病人。
超越诊疗指南用药,极其考验医生的勇气。如今,为了避免过度医疗,系统能自动识别医生的用药量,一旦发现超出指南的规定,会对医生罚款。而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将根据指南判定责任归属,医生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不按指南的规定开药。
冯连元总结,制定指南是大进步,但每个人适用的用药量是不同的,要理解个体差异。“就像把100个螺丝钉安装进孔里,某些螺丝钉就得垫张纸,才能精准安装。”于是,退休多年的他还在研究误诊。他引用数学模型,弥补不精准的问题,找到垫螺丝钉的那张纸。
医生们能够自省、敢于发声
孟庆义曾以主任医师的身份,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讲台上。坐在底下的从各地来进修的医生,都是在当地医院“跺个脚地都要抖三抖”的技术能手。他的第一课,不谈那些高大上的疑难病,就讲误诊,就从日常工作中那些“想偏了”的故事讲起。
一个老年人晚上睡觉后,家人呼不应、推不醒,连夜送到急诊。医生判断,处于昏迷状态一定有重病,于是开了各项检查,却找不到病因。直到早上6点,老人突然醒来,一脸诧异:“我怎么在这里?”原来,他只是吃了两片安定药。
“医生要不断给自己提问题,为什么是这种表现?会不会误诊?”他形容,医生的工作状态是“如履薄冰”,必须强迫自己突破现有的临床思维和认知。这门课程后来成了王牌课。
他常听到病人抱怨:“这个病在县医院没诊断出来,来了您这儿才知道是为什么。”孟庆义帮同行解释:“县医院的医生也不是水平差,你的疾病在早期没有明显表现。”他的正确诊断是在前人的诊断基础上作出的,不能贬低前人的诊断。
医学领域仍有许多谜题,等待解开。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每隔两个月,就有一群医生聚在一起,分享临床上遇到的“谜题”。各家医院的医生轮番上台,讲述他们经手过的疑难病例。他们介绍自己的经验时,也能够接受同行的审视。这过程中也不乏有案例初诊存在漏诊、误诊,随着患者病程进展,医生才逐渐梳理出患者的主要疾病以及同时存在的其他疾患。
这样的研讨会至今已经办了几十届,吸引了北京各大医院的急诊科医生,如今还有专科医生参与。他们定期坐在一起,没有藩篱地讨论彼此的误诊经历,并在日后极力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敢于面对误诊、漏诊的医生不少,但敢于开口的医生是少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主任米玉红曾给《临床误诊误治》杂志投稿,写她在急诊接触的一位右肺动脉缺如的病人,初诊被误诊为肺栓塞的过程。推动她大胆公布案例的动力是,她对自己专业水平有自信,想借此机会提醒同行:“我研究肺栓塞17年,我知道大家共同的难点在哪。”
但对于更年轻的医生来说,公开谈论误诊需要极大的勇气。大多医生更愿意关起门来,在行业内小范围地讨论误诊。这种“避之不谈”的氛围,也影响了陈晓红的研究。早年,在医学期刊发论文,能帮助医生评职称,这一度让陈晓红不愁稿源。但最近几年,基础研究、课题研究更容易受到重视。《临床误诊误治》杂志里,真正与误诊有关的文章越来越少。
她鼓励更多医生敢说,勇敢真诚地贡献临床上的误诊经历。只有這样,才能广泛地搜集到最新的误诊案例。陈晓红依然走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她能看到前方最光亮的地方,是医生接诊时,随时用上她攒了30多年的误诊病历和总结出的规律。
即便到了现在,医学界依然在“误诊有没有学”方面有争议。有的医生坚持误诊无学,只有医生零散的临床经验总结。但孟庆义却认为,“误诊是高级学问”,它应该成为医学研究那颗皇冠上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