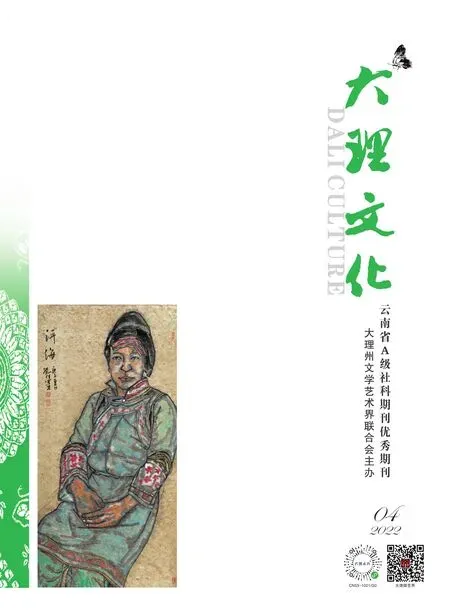与书店相遇
2022-05-17杜福全
●杜福全
一
从小生长于穷乡僻壤的山村,父亲早年在村子里当过几年民办教师。按说,我最先见到的书应该是小学课本,或者是父亲的教参书籍。但是,在童年的记忆中,我最先见到的书是《毛泽东选集》。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字,只知道那书是用线装订的,封面和封底都是硬纸壳,硬纸壳套进红色的塑料书壳里,书很厚,也很沉。我知道的这种书,家里有好几本。我开始上学读书认得几个字后,翻的第一本课外书居然是《毛泽东选集》,也是第一次从这些书上看到《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这样一些文章和“天下乌鸦一般黑”“蒯大富”这样一些句子或者名字,但好些字我都不认识,一些让我好奇的字我通过查字典记了下来,但一点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小学时,有次写作文,我在作文中用了“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话,老师问我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知道。老师问我从哪儿学来的,我说是从《毛泽东选集》上看到的。老师看了我一眼,不再说什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村街上没有书店,只有卖油印本《农家历》的地摊,一般也只有年底或者年初的时候才有。庄稼人一年四季的农事与农历的二十四节气等民间节令息息相关,翻土播种、破土动工、出门远行、红白喜事等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翻开《农家历》看个黄道吉日。当然,现在村街上还是没有书店,尽管现在的智能手机看日历已经很方便了,但老一辈的庄稼人还是每年都要到村街上买本《农家历》回来放在家里,随时翻翻。
我第一次看到摆着书卖的地方,是在乡街上的供销社柜台内一个角落的货架上,摆着一些出售的书。小时候,我每年春节都要去外公家拜年,去外公家要经过乡政府驻地,每次路过乡政府驻地,我都要去供销社看看,当然,也只是看看,没钱买任何东西。那时候,供销社的商品是最丰富的,很多商品都只有供销社才有销售。吃的东西固然是最吸引人的,但老是看着又吃不着,只能把口水从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往肚子里吞,那种感觉特别难受。于是,就去柜台的另一端,隔着柜台远远地看那些摆在货架上的书。当然,也不知上面是些什么书,只觉得那些书好看,因为隔得太远,也只能看到一些书脊或者封面,其他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为什么,幼小的心里,总是有那么一种莫名的好奇心驱使,莫名地向往着那个我一无所知的书中世界。
开始上学读书了,认得几个字后,每次去外公家路过乡政府驻地,还是要跑去供销社看看那些货架上的书,远远地看,呆呆地看,认得了一些书的名字,比如《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实际上,货架上更多的还是小画书,也就是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小画书的画儿画得好,画下面都有段文字,图文并茂,关键是便宜,才几分钱一本,大人孩子都喜欢看,也看得懂。我小时候也读过几十本小画书,像《金台三打少林寺》《岳母刺字》《兵临城下》《霍元甲》等,但这些书一本都不是我买来读的,是我一个在乡中心校读书的堂弟给我带回来的。
乡街上供销社里货架上的那些书,是我最先看到的摆着卖的书。很显然,供销社并不是专业的书店,卖书只是附带而已。在我几年的观察中,供销社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书,并不像货架上的其它百货那样销售得快,基本没怎么更新,所以一直摆在货架的最高处。那时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解决温饱问题才是第一要务,精神食粮是其次。乡村一带,人们整天忙着生计,读书没什么气氛,认得几个字的人都不多,加之没什么多余的闲钱,那些书自然也不好卖。
大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或者九十年代初,乡街上的供销社就不再附带卖书了。书从供销社的货架上消失后,乡街上就再也没有卖书的地方了。
二
与真正的书店相遇,是一九九三年秋季,我小学毕业考进县城一中读初中,在县城遇到了新华书店。
那时候,除了新华书店,整个县城也没一家正二八经的书店了。当然,如果从书店的历代叫法来看,也可以说还有另外的书店。中国古代的书店叫书肆,最早始于汉代,后来历朝历代还有书林、书铺、书棚、书堂、书籍铺等名称,宋代以后统称为书坊。不过,那时候的书店,不单单只是卖书,而是既做书又卖书。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有了书店这一名称。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店也叫书局。
除了新华书店,县城背街小巷还有几家以租书为主、卖书为辅的店子,这种店子极为简陋,甚至是沿街临时搭建的棚子,真有点像历史上的“书铺”或者“书棚”。实际上,这种书棚也不卖正二八经的书,店前搭个架子,铺上几块木板,摆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刊杂志,诸如“奇门循甲”“阴阳风水”“武功秘籍”“秘闻内幕”等等之类的书,当然,也还有一些电影画报之类的旧杂志,估计买的人也不多。店内的书架上,倒是摆满了真正的书,不过大多是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大多以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所作的武侠小说为主,言情小说主要以琼瑶等几位当时流行的言情小说家的作品为主,同时也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书架上的那些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是用来出租的,租一本书,交押金五元,一本书一天三角钱的租金。我在初二就读完了金庸先生的全部武侠小说,书就是从这种店子里租来读的。有时候没钱了,就用饭票去抵押,甚至可以把饭票当钱来用,租书的大都是学生,钱币和饭票可以互相兑换流通。为了尽量节约租金,我一般头天一早去租书,第二天下午去还书,这样店老板会按一天的时间来计算租金,一本三四百页的小说,一天一夜基本上就看完了,当然,晚上经常是通宵看,至少也要看到凌晨三四点钟。我的眼睛患上近视,其实是看武侠小说导致的,当然,也可以说是跟贫穷有关,如果不是为了省几毛钱的租金,我大概也犯不着通宵达旦赶着去读完一本书。读完金庸的武侠小说后,我对其它武侠小说再也提不起兴趣来,至今没再读过那种大部头的武侠小说,只是偶尔会读一篇当代作家写的短篇武侠小说。

周末,做完作业,我喜欢在县城的大街小巷溜达转悠。那时候,县城的面积不大,转一圈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在街头巷尾,会经常看到一些人躺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看书,凑近一看,大都是武侠小说,或者言情小说,或者就是《故事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读书风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是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非常流行的时候。金庸、梁羽生等一批武侠小说家的小说,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在电视上连播,琼瑶的言情小说也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在电视上连播,可每晚只播出一两集,还要插播很多广告,让人看不过瘾,等得人心烦,有些人就干脆去读小说原著了。
每次到街上去转悠,我都要转进新华书店去看看,去看看那些摆在书柜里的书,看看他们叫什么名字。那些书,一本几元、十几元、几十元不等,但我还是买不起书。那时候,新华书店主要是经营全县各中小学校学生用的课本,其它书的品类也不算多,估计书店的生意也不太景气,经常去看,也还是那些书,很少发现有新书进来。
我始终觉得,在县城,读书的气氛还是很寡淡,人们都不太喜欢读书,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很少。当然,书店对读者也是有一定的引导作用的,一个书店的经营理念和经营路径也会对一个地方的阅读氛围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记得,在县城读书几年,仅在新华书店买过三本书,一本是《现代汉语词典》,一本是《古汉语词典》,还有一本是钢笔字帖。近三十年了,这三本书还在我的书柜里待着。
三
一九九七年秋天,我考上师范学校,到昭通读书,遇见了更多的书店。昭通是一个地市级城市,城里大大小小的书店,有十多二十家,还有一些旧书摊,报刊亭也很多,卖各种各样的杂志,特别是文学期刊偏多,顺带也会卖一些畅销书。本来,我对读师范这事有点无可奈何,加之对昭通寒冷的气候很反感,刚去昭通读书时,心里有种失落的情绪。幸好,在昭通遇到了书店,让我的三年师范生活有了一个理想的去处,也从中获得了一些温暖。当时我到过的最远、最大的城市就是昭通,见到城里那么多书店,我以为越大的城市书店就越多。
周末,我喜欢到城里去闲逛,有时会约上一两个同学或者朋友,更多的时候是我独自一个人,因为只要我一逛进书店,一时半会儿都不会离开,其他人跟着我在书店里待不住,觉得无所事事的很无聊。那时候,昭通的书店大街小巷都有,只是书店的空间大小和书的品类各有不同。比如,在当时的馋嘴街一带,好像就有两三家书店,店面都不算大,但里面的书也不少。这么一个让人产生口腹之欲的地方,让人在吃饱喝足后,或者在等待吃喝的时间里,可以到书店里去转转,随便看看。只要你进去了,即使一本书也不买,也会让你短暂地脱离花花绿绿的世界,内心获得片刻的安宁。
记得当时在南正街上,新开了一家大型的购物超市,在二楼还是三楼,就专门用了一层楼来卖书,而且,里面的书都很不错。实际上,我记得,当时昭通的好几个大商场,里面都专门设置了一个卖书的区域。读师范那会儿,也还是穷,除了基本的生活费,包里没啥多余的钱,经常逛街,无非是为了满足一个农村学生对城市生活的好奇心。大商场是有电梯的,我是去昭通读书后才看到电梯是怎么回事儿的。那时候,经常进出大商场,一是为了坐坐电梯,觉得稀奇、好玩;二是去看商场里的书店,其他东西买不起,也没什么好看的,你一看,服务员就凑过来问你这样那样的,你又买不起,心里就不自在。当然,书也是买不起的,但图书区域似乎没有专门的导购员,你可以这儿翻翻,那儿看看,自由自在,消磨时光。
那时候,除新华书店外,昭通城里还有几家大型的独立书店,比如新知图书城,或者那时候是叫新知书店吧,有一家求知书店也不错,还有一家书林书店,里面有好多学术性的书,书的层次还比较高,还有的书店我记不起名字了。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逸品书店,当时应该是在青年路上吧,原谅我对琳琅满目的街道名称总是记不太清楚。
逸品书店在二楼,一楼是商铺门面,书店内的装饰和摆设都很好,一进门就感觉很优雅、古朴。里面的书很丰富,品类繁多,层次比较高,有些比较前卫和先锋的书,在昭通的其他书店看不到。那时候,我经常看见教授我们《阅读与写作》的陈老师包里装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主办的一本叫《读书》的杂志,我跑遍了昭通几乎所有的书店和报刊亭,都没有看到这本杂志,但我在逸品书店找到了它。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断断续续去逸品书店买《读书》,毕业参加工作后,年年都要从邮局订阅这本杂志,中间可能中断过一年或者两年,现在我还在订阅这本杂志。《读书》这本杂志上的文章,学术性和专业性太强,里面的好些文章我也读不明白,但我就是喜欢这本杂志,并且每期都保存了起来。那时候,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逸品书店,往往一去就是一整天,饿了出来吃点东西又进去。毕业后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我去昭通,专门去过一趟逸品书店,后来也很少上昭通,就再没去过这家书店了,也不知道还在不在。
在昭通师范读书三年,我的周末时间大部分都是在书店里转悠和闲逛,因为囊中羞涩,也没买过什么书,倒是在书店里认识了许多书的名字和许多写书的人的名字。那几年,在昭通书店里买的仅有的几本书——在逸品书店买的约翰·格雷的《人类幸福论》和朱大可、吴炫、徐江、秦巴子等的《十作家批判书》,在书林书店买的李泽厚的《美学四讲》和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求知书店买的《灯下书影》、夏晓虹编的《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和《冯友兰学术文化随笔》。二十多年了,它们陪着我从山上到山下、从乡村到乡镇、从乡镇到县城,一路颠簸着换了四五个地方,现在还好好地待在我的书房里。
四
这些年,走过不少地方,每到一个地方,一旦遇到书店,就想转进去看看。这种进去看看,也不一定要买什么书,就是进去看看,看看书店的空间设计,看看书店里面的布局,看看书店里都有些什么书,感受一下书店的气息,也让心灵放松一下,停歇一会儿,安静一会儿。在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在大城市,书店是一个让我想要停歇的地方,其它地方,就算是江南水乡的千年古镇,或者是奇山异水的风景名胜,或者是其它稀奇古怪的地方,都没有给我这种心理上想要停歇的冲动和欲望。或者,其它地方都让我觉得,我只是一个过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书店,让我的心灵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日本作家吉井忍说:“每一本书拥有自己的世界,书店则是所有世界的入口。”这么说来,我渴望在书店驻足和停歇,实际上是渴望在这个世界的入口处驻足和停歇。在大城市,一个书店给人心理上的面积,可能远比一个城市的面积还要庞大,还要丰富,同时,也很纯粹。
钢琴演奏家阿图尔·鲁宾斯坦曾说:“评价一座城市,要看它拥有多少书店。”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传统书店越来越式微,时不时又会看到某家独立书店关闭的消息,对于一个喜欢逛书店的人来说,心里是很不好受的。仔细想想,一座城市,不管它有多么宽敞的大街和摩天大楼,不管它有多么富丽堂皇的购物广场和银行大厦……如果整座城市见不到一家书店的话,置身于商业和物欲的世界里,空气中闻不到一点书香的气息,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大概在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李庄,居然在它的老巷道里看到一家书店——李庄古镇书屋,虽然整个书屋不大,里面也没多少书,大多是旧书,也没有多少好书,但它古色古香地镶嵌在长江边上的这个千年古镇里。几年前,我从李庄路过,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发现在古镇旁边的入口处,新开了一家环境优雅的书店,里面的书比较丰富,且富于现代气息,我在里面待了好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一个古镇,因为我知道的这两个书店,让我觉得这个古镇是有思想和灵魂的,它的古朴不是呆滞的和物化的,而是在人间流动的。今年冬天,我又去了一次李庄,在古镇巷道里转了两圈,那个古色古香的书屋似乎不见了,另一家书店的那个位置,可能是因为古镇正在改扩建,被围栏围了起来,也有可能搬迁或者拆除了。在古镇转了一圈,没有看见书店,心里有种莫名的失落感。
2021年的11月,我去了一趟上海,这是时隔十三年后我第二次到上海。有天晚上,同去的几个美女带我去淮海中路找好吃的,在淮海中路一带转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满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吃饱了出来,在街上闲逛,准备打车回酒店时,我突然看到了不远处的“上海香港三联书店”,这一发现让我特别兴奋。我买过不少三联书店出版的书,对“三联书店”这几个字有种特殊感情。“我去三联书店看看。”也不知道身边的几个美女听见没有,反正我已经快速朝书店那边跑去了。当我跑到书店门口时,很遗憾,书店已经关门了,但书店里面亮着暗黄的灯光,透过临街一面透明的玻璃墙,可以看到里面书架的布局和书架上陈列有序的书,给人感觉特别的美。我在书店外面徘徊,缩头缩脑地往书店里面瞧着,赶过来的几个美女见我这种德行,说我简直是个书痴,一见到书店就把美女都丢下了。一个美女说:“早知道你这样喜欢逛书店,就该带你去体验一下上海的云朵书院,又怕你有恐高症。”出门在外,特别是在大城市,我就是个路痴,也不善于在手机上寻找什么好玩的地方,所以,还不知道上海有这样一个书店。据说“云朵书院”建在五十二层楼距离地面二百三十九米的高空之中,里面的图书非常丰富,集观光、休闲、购物于一体,去之前必须预约,是上海新近打造的一个城市文化地标,一个城市文化符号,像东方明珠塔一样。我们明天就要打道回府了,“云朵书院”是去不成了,就让这样一个独特的书店留存在我的记忆中吧!
二百三十九米高空中的“云朵书院”,虽然我对它一无所知,但它却是上海留存在我脑海里的一个文化高度!
五
与书店相遇,不一定非要买书,相遇的本身,就是一种缘分和幸福。出门在外,买的东西多了,乘车坐飞机什么的,确实很不方便。互联网时代,网购也遍布城乡角落,我的大部分书都是在网上购买的。虽然如此,每次遇到书店,在里面逛得差不多的时候,我还是想买本书带走,至少可以做个纪念,也算是对实体书店存在的艰难表达一份自己的敬意,一本书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但至少要有这种仪式感。比如二十年前,我在宜宾市的新华书店逛了一个下午,结果就买了一本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十三年前,我在广州的白云机场候机的时候,因为随身携带的行李包还有空间,便匆匆地在机场的书店里买了两本书装进去,一本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本是波伏瓦与萨特晚年失明后的谈话录《一个与他人相当的人》。
十多年前,我与好友老夏去昆明逛图书批发市场。去之前,老夏说里面有些书是论斤卖的,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书,怎么能以斤两来计算和出售呢。我甚至以为,书后面的那个定价,其实是对做书的工序和纸张成本的定价,而不是对一本书本身价值的定价,定价只是书在人间流通体现的一种物质形式,而书本身在人间的流通价值,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我和老夏去逛了一圈,发现真的有个区域的图书是论斤出售的,不过都是一些老书旧书,仔细看看,有些书确实没什么价值,有点像废纸。在图书批发市场,我们没有买一本书就离开了,接着去了不远处的另一家书店,买了几本书带走。
前不久去大理古城参加笔会,第一天是实地考察学习,我们去了一趟沙溪古镇。实际上,从交通的情况来看,沙溪古镇位置有点偏僻,离开主干道公路后,我们乘坐的客车在狭窄的公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周围都是微微隆起的山脉,古镇坐落在一个小小的盆地。街道是用凌乱而有序的石板铺成的,上面刻满了岁月的印迹。房屋建筑大都是土木结构,也有少部分砖木结构的房子。一股清澈透亮的溪水在街边石头砌成的水沟里叮咚叮咚地流淌,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周围都是古色古香的白族民居建筑,游人不多,安静而清闲,别有一番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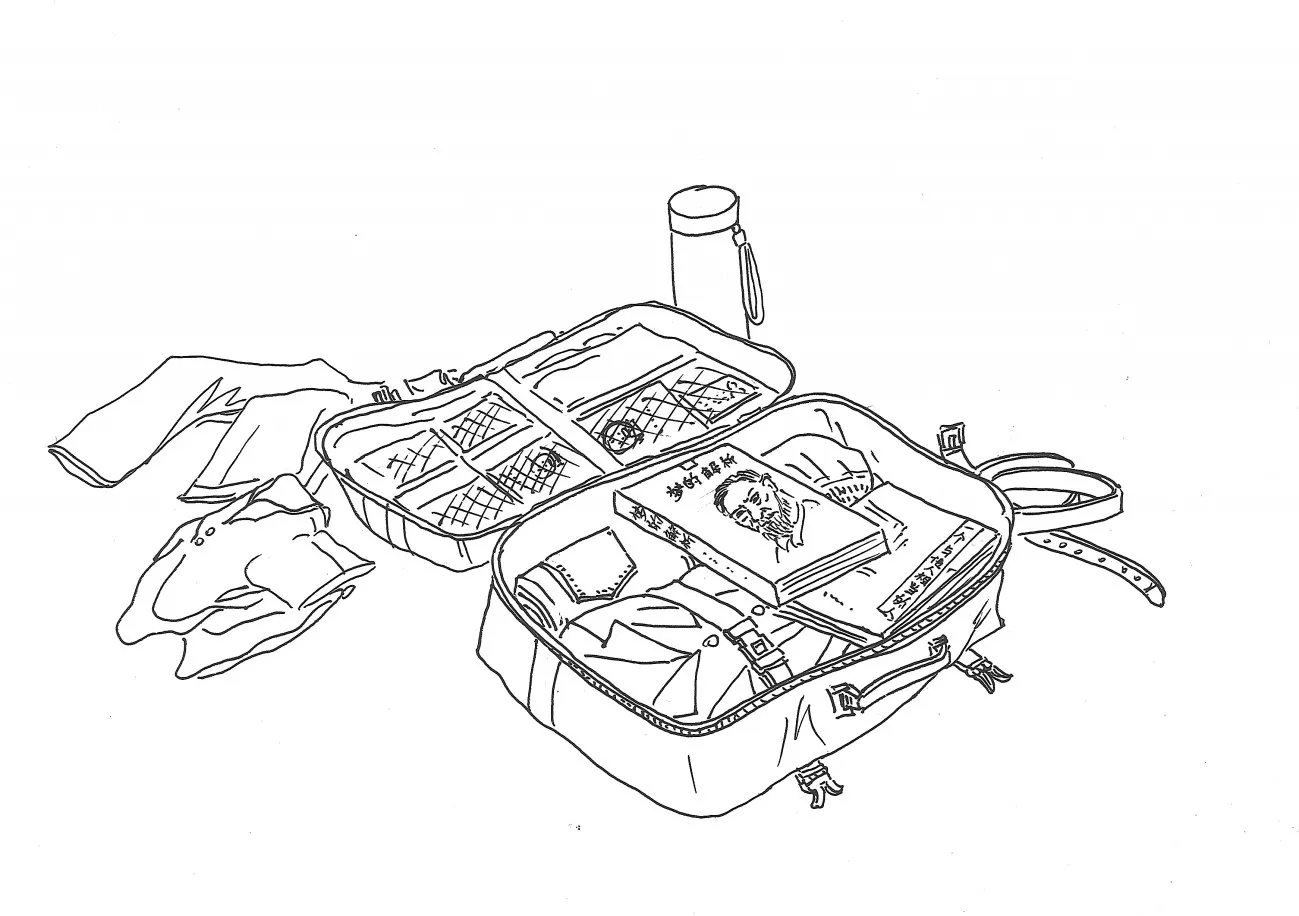
据说沙溪古镇有好几个游客“打卡”的地方,其中坐落在古镇北村后的“先锋沙溪白族书局”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同行的大理朋友说,据说这个乡村书店还不错,但是他也没去过,问我想不想去看看,步行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自然是想去的,但这样一家乡村书店,它究竟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感官效果,实在没什么把握。一行五六个人,顶着初冬明晃晃的太阳,沿着黑潓江河岸上的观景道走着,我与朋友漫不经心地聊着一些读书话题,不时用手机拍几张河边的照片,大概走了一个小时,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先锋沙溪白族书局”。
“先锋沙溪白族书局”,是一间背靠着白族民居土坯房搭建的钢结构房子,前面又是复古土坯房的模样,书店门口有一个院坝,旁边有一间阅览室。据说,这个乡村书店是由原来的粮仓改建而成的,饥饿年代它是储备物质食粮的仓库,现在它成了储备精神食粮的仓库,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从外观上看,这样一个号称“先锋”的乡村书店,与这个白族村庄融为一体,是那样协调,同时又是一个多么独特的存在。不过,在打量这家书店外观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在犯嘀咕,在这样一个地方开这样一家书店,先不说经营者能不能赚钱,最起码的一点,能不能生存下去,都是个问题。
走进书店一看,我有点傻眼,书店的四壁,从地面到屋顶,全是琳琅满目的书,仔细一看,书的品类繁多,一面是具有大理地域特色的各种各样的地方历史文化方面的图书,下面用木板做成梯步,供人们“打卡”拍照用。其余墙面的书柜里的书,囊括了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国内的、国外的都有。我仔细查看书的版本情况,发现这些书大都是比较著名的出版社出版的,也有小众出版社出版的小众读物。我在进门的左手边的一壁书橱里,居然看到了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社会经典图书——“理想国译丛”,而且是全套。沿着书橱移动脚步,又发现了由广西师范大学推出的“文学纪念碑”系列丛书。这些发现,让我心里感到微微的震惊,我赶紧跑到收银台去询问那个留着长发的店员小伙,问这个书店的书是不是他负责选进的。店员小伙告诉我,他只是参与了部分图书的筛选工作,他们有一个团队,专门负责为书店选书。我问他书店的营业情况如何,有人来买书么,都是些什么人来买。他说,开了两年了,目前看还行吧,来的游客比较多一些,有些游客走的时候会买一本两本带走,村子里也有人来看书和买书,但不多。我这才想起,先锋书店好像最早源于南京,这里应该是新开不久的一个分店。我觉得,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价值,这种价值远远高于它的商业价值。但我又想,人,首先是要吃饭的,开书店的人也一样。在这里开一家这样的书店,我想,作为开办者,可能更多的是基于它的文化性和公益性来考量的吧,如果完全从商业价值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它能存在多久呢?一个高层次的书店,存在本身就是价值。突然之间,我对我一无所知的先锋书店的开创者,心里生出由衷的敬意来。
我和朋友围着陈列满书籍的书架慢慢地看着、翻着,一边交流对一些书的看法,有时是泛泛而谈,有时会谈到具体的某一本书,不觉时光就去了两个小时。离开书店的时候,朋友买了一本法国记者、作家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写的传记《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我买了一本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雅诺的作品集《行走的话语》。
我喜欢“行走的话语”这个书名,它让我觉得,一家家书店就是人类文明在人间行走、驻足、说话的一个个驿站,你驻足聆听也罢,不屑一顾也罢,它都那样存在着,人类文明的话语,跨越历史的长河、民族、国界和疆界,或顺利地或艰难地,不停地在人间行走、说话。一个城市,一个地方,有了书店,我们就能看到文明的一抹亮光,看到文化的一抹春色,看到未来的一抹曙光。
当有一天,我们到一个地方再也看不见书店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得见我们人类自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