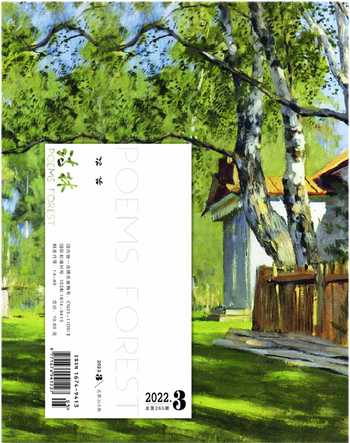以超常表现力,让想象在物事中突围
2022-05-13孙思
孙思
李云诗集《一切皆由悲喜》以禅心入名,道出了无尽宇宙的本质和一切生命的真相与原态。他让一切事物与己同在,任其取用,相入无碍,抵达未说境界。他以超常的表现力和创造力,让想象在普通的物事中,或被人们忘却和忽略的逸事中突围,生长出新的视野,并调动视觉、听觉和感觉,使其发出震荡,让我们体会其诗歌质感,以呈现出他诗歌强烈的生命力。他才思如水,行如泉涌,却又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他的语言如刀,带有锋利的质感,一刀切下,一股清冽和新鲜酷烈,迎面扑来。直觉与想象的双螺旋上升,让投射到他眼眸里的直观影像,最大限度地把“可能性”留给想象的无限性。于是,他的想象得水而活,得云而飘逸,得大地天空而开阔。
超常的观察力和控制力,对笔下事物锐角一般的斩决,渗透进他的写作与体验,成为推动他想象运行的意志和力量,让他诗中的色彩、形状、质感等同时具备了自然特征和艺术形态的双重审美意义,从而使他的诗成为无处不在的观察。
李云擅于在日常生活或普通的事物中,劈开一道豁口,寻找一种突破、一种绽裂,来弥合自身的愿望,进而再度出发,进行内省。他把笔锋深深地楔入他的想象里,譬如下面这首《大风》。视角、感受的反复叠合、冲击,由外部和内部的形象结合,场景对空间的轮替,使《大风》有足够的力量撑满和完成我们无法完成的共同的生命意志。
十万头抑或百万头,野象狂奔
起于青萍之末,起于海洋深处
起!无处不在的生命动词
与呐喊、狂飚、扫荡、摧枯拉朽有关
与改变、重建、毁灭、彻底否定有关!
十万头抑或百万头,野象足音
北方森林,南方海岸线
极地极光,东边龟裂的红土
沙漠的胡杨和都市人们眼底的渴望
需要!需要大风来临
飞沙走石也罢,倾盆大雨也好
台风!飓风!大风!风……
十万头抑或百万头,野象嘶吼
让虚假的广告牌倒下,危房倒下,无基的
山倒下
请扫走腐尸味和铜臭味,扫走无良者
把水和药备好,还有蜡烛和茶点
以及书籍和唱片,当然还有火柴一样的你
十万头抑或百万头,野象在笑或在哭
裹挟着种子,新的消息
来!让河水四溢,泥石流奔走
田园和城市是该换一换新面孔的时候了
断崖断去,坠石崩析
我不惜,我愿意
只是树和花草是无辜的牺牲者
我忏悔且无奈
但我依旧盼望大风快点来到
我要随它狂奔或舞蹈
要不死在其怀中,要不一路狂啸
淋漓酣畅,大风里长河之涛
我击浪而行。象群来了
我看见
十万头抑或百万头,野象走远
东方既白,大地寂静
我幸福地战栗——
——第一辑《大风》
作为一种精神表达,这首诗中的意象“野象”,让稍纵即逝的瞬间得以放大,延宕了流动中的速度感,使想象与实质之间的关系浑然天成。而“狂奔”“起”这两个绝对想象对绝对意义、绝对观念对绝对秩序的动词,成为这首诗的绝对起源和方向。紧跟后面的由这两个词带动的大风,以存在的又是超未来的神秘性、以抽象也是具象,一路摧枯拉朽、排山倒海。这是基于对现代人生存的洞察,是对生命努力挣脱束缚的一种救赎。最终“十万头抑或百万头,野象走远/东方既白,大地寂静//我幸福地战栗”,这一内核得到了非常好的暗示,表面与背面的张力都达到了深邃的层面,极具质感的动态画面,回归到寂静与本源。
诗中涉及的大量如森林、海岸线、红土、沙漠、胡杨、大风、飞沙、走石、大雨、台风、飓风、广告牌、危房、药、蜡烛、书籍、唱片、种子、河水、泥石流、田园、城市等等,这些诗人经过思考带着自己体温的名词,它们存在的自身也是它们的普遍,内中自带一种持续的自然与人性相融合的属性,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读随抓住你不放,让你不知不觉地浸入到它们中间,与它们一起跟着一个个动词,去席卷,去战栗。
围绕一个核心场景,将诗意层层展开,步步深入,等到核心场景的烘托和诗意的渲染到达一定程度后,再拈出一个与之相对或相反的场景和意象,卒章显意,从而将前面的诗意全面颠覆,是李云的又一审美特点。
早八点,一个昂头望向天空的人
一直立在那里,中午十二点,他还在
昂着头
车水马龙 众人随他一起仰望天空
天空是很空的空 放不下一枚逗号
傍晚六时,那个人打了半个喷嚏
擤了擤鼻子走了
众人的脸上阴云密布
低下头时,明天的雨就倏然下了
后天的风业已来临
——第二辑《阴天里》
诗人运用突反手法,让繁忙的日常留出一道缝隙,虽只是时代图景中的一瞥,沉默的场景,却承载着时代发展的隐痛。
诗从核心场景“早八点,一个昂头望向天空的人”开始,通过“中午十二点,他还在昂著头”“众人随他一起仰望天空”,诗人安排了规定情境,让读者不得不进入这个情境,跟着诗人的文字走。相近的场景,将诗意一步步展开、深入、烘托、渲染,然后拈出与之相对的场景“天空是很空的空 放不下一枚逗号//傍晚六时,那个人打了半个喷嚏/擤了擤鼻子走了”就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眼前推开一重又一重的门,让读者警醒、索隐,想觅取最后的端倪。最后“众人的脸上阴云密布/低下头时,明天的雨就倏然下了/后天的风业已来临”。结尾意义省略和情感跳跃为读者预留了发挥想象的巨大空间,使诗歌意蕴无限伸长。
如此普通又如此不普通的一个场景,被诗人捕捉,并在它原有的气息与特点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它所隐喻的意义。如此,诗结束了,诗人营造的场力还萦绕在眼前,久久不散。
悖谬是李云擅于运用的又一个手法,他将语义相对或相反的词语并置在一处,表面看来似乎违反了生活世界的物理逻辑,但实际上符合了心理世界的体验真实,它们的出现,使诗歌打破了常规的审美效果。
我早就住在那里,这是我熟悉的味道
石块和石级咬在一起,不松口的动物
凝固的不仅是小窗和箭孔
踩一脚就会呻吟的木梯和楼板
木床和条桌以及立橱和茶几
都在旧梦中生着霉苔和斑痕
我早就住在那里,油灯、灶火
社戏和祭拜喧嚣以及婚丧大礼后的日常
喜怒哀乐鸡鸣狗吠
我熟悉的味道 没变
苦辣酸甜咸百味杂陈……
其实,我一天也没住过那里
就像我不熟悉那里的味道一样
是的,我对我自己说谎
我对你坦白真相,是的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第三辑《古堡》
诗人常常在虚构里冒雨赶路,先是说自己“我早就住在那里,这是我熟悉的味道”,然后通过石块和石级、小窗和箭孔、会呻吟的木梯和楼板、木床和条桌、立橱和茶几、油灯和灶火、社戏和祭拜、婚丧和鸡鸣狗吠的细描,把读者的视线引入古堡。诗人的文字向畫面和声音的咬、呻吟、喧嚣、鸡鸣狗吠同时打开。最后坦言,“其实,我一天也没住过那里//是的,我对我自己说谎/我对你坦白真相,是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情愿的情愿,不肯定的肯定,让诗出乎读者意料地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与转折,似乎是在考验读者的清醒程度。
诗人在诗的最后去除遮蔽,清清明明,如同莲花和藕,如同哪吒削下来想要还给父母的节节肉身。其目光的凝聚和流淌,替代了语言的密度和速度,线条的选择和勾勒,置换了语词和意象视觉化的交替更迭,让遥远的起点抵达不可知的终点。
用语言和叙述方式改变时空,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是下面这首《大运之河》的特点。诗人描绘的运河,从现象的一个方面、部分和细节滑到另一个方面、部分和细节。从一个现象的各个方面进行彼此转换,并在被忘却的逸事中突围,让大运河的存在,本身形成一种对照和对应,并以此作为媒介进行博弈,让不同的生息来自四面八方,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大运之河》。
拓土之际,那腹肌板结
抽签之时,水路尚在瞳孔里暗流
京杭遥远间只有马蹄踢踏
需要液态的流动
是动脉或静脉
吸管,江南香米和白盐
以血红素的模样流淌
把所有的帆当成风筝
大河那根两千多里的
线,系着
一支短笛卧野
风吹过船桨之声和船笛
还有绷直的纤绳上跳跃的号子
这台不老的织机
每天穿梭的银梭金梭
南来北往的月牙
所有的码头都该是琴柱
长河 这架古琴
抛出水袖之后
就有了欸乃之声
踏岸而来,还有春潮带雨
这根银烛点亮
一座座城池一座座山
清亮亮的嗓子过了平原
这柄寒光内敛的古剑
撕开一道光的内部
可见到水下沉淀的
碎瓷、铜钱、骨骸、百宝箱
还有水上漂过的水烟、葫芦、菜蔬
无名漂尸
船在河道上行走
似精子在生命之河上逆行
这枚银针
扎在两个穴位上
一个叫京穴
还有一个叫杭穴
银针扎下,大地通体皆活
大运降下,河水流畅
我们承接万代的福泽
——第五辑《大运之河》
首先诗人在运河的脉络上,建构起一种想象力,以他者的角度对大运河作冷静客观的叙述,意在最大限度地逼近真相:“拓土之际,那腹肌板结/抽签之时,水路尚在瞳孔里暗流/京杭遥远间只有马蹄踢踏”……接下来,诗人将这条河流流逝的日常,江南香米和白盐、短笛卧野、船桨之声、纤绳上跳跃的号子,用形象化语言赋象运河不老的织机、古琴、水袖、银烛、古剑,再由动词穿梭、南来北往、抛出、踏岸、点亮、过、撕开、漂过、行走、逆行来带动,生活与记忆,河流与众生,在弥散中沉潜并生、生生不息。最后“这枚银针/扎在两个穴位上/一个叫京穴/还有一个叫杭穴/银针扎下,大地通体皆活//大运降下,河水流畅/我们承接万代的福泽”,整首诗到此结束。于是,一条突破了我们对原有感知限度的大运河,多元的、广阔的、朝向未来预示希望的“大运之河”,一条永远奔涌延宕在路上的可供涵纳的精神之河,带着向外辐射的力量,向我们奔腾而来。
而诗中的所有动词,几乎都带着切片的功能,在镜头下将现存的时日和物重新编织一遍,让读者们观看、进入,然后与诗人产生默契和共情。
世间的万事万物,本质上是人性难变的遗存部分,李云透过第三双眼,把它们变成具体的、形象的,可以抵达现代人阅读、认知与思维方式的文字。下面这首《磨刀事》就是诗人打破刀、石头和水的原生性,打破固有的观念和模式化套路,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它们,让它们彼此对话,于是刀、石头和水,有了生命和清晰的呼吸。
没开杀戒之前 刀和石头
谈锋正健 有时两者吵得火星四溅
水来安抚
决绝而去的刀
冲锋陷阵的刀 最终会
遍体鳞伤 回到石头上
疗伤
石头和有过血污的刀身
不再说话 任由刀自言自语
水陪刀暗自落泪
黎明之光在刀的额头和鼻尖闪亮
豁了的牙也被补齐了
血槽清洗干净
石头的腰佝偻
水的眼泪哭干
刀被持刀人携着重入江湖
石头和水没有送行
他们知道
刀的命运结局
它们都恨持刀的人
——第六辑《磨刀事》
诗人采用比喻中起兴的手法,以彼物刀和石头引出此物水,再用拟象中比拟的手法,将三种拟人化的物,进行了原生性的交替刻画。诗人的想象力打破了固有的观念和模式化套路,让想象力既探询了魂灵归属,又进行了人性的可能性预演。
诗的开头,“没开杀戒之前 刀和石头/谈锋正健 有时两者吵得火星四溅/水来安抚”,把我们看到却很难感受到的世界,推到我们面前,刀和石头刀枪舌战的场面,让我们仿佛亲临了一场辩论赛。但当刀和石头在真实的生活面前,不得不弯下腰服从的时候,诗人的语言开始凌厉起来,“决绝而去的刀/冲锋陷阵的刀 最终会/遍体鳞伤 回到石头上/疗伤//石头和有过血污的刀身/不再说话 任由刀自言自语/水陪刀暗自落淚//黎明之光在刀的额头和鼻尖闪亮/豁了的牙也被补齐了/血槽清洗干净//石头的腰佝偻/水的眼泪哭干//刀被持刀人携着重入江湖”——这些未被言说甚至不能言说的带着血腥的场面,原来如此清晰、坚实地存在。最后诗人凭借那一点微弱但又凛冽的光,把彼此找回来,让刀、石头和水续站在开始的地方。“石头和水没有送行/他们知道/刀的命运结局/它们都恨持刀的人”,诗人的语义如此锋利,又如此耀眼,不尽的含义,深长和幽深。
长诗《雪国》,在不可触及的张力中,同时创造着肉眼视内和视外所涉及甚至没有涉及的,它交错、奔涌、流淌、寻觅,它无法复制,更无法重思。它是现实的,又是超越的,是俗世与超越性之间的边界,是隐逸之地和世俗之地的分界处,它同时彰显了李云预见性的时代概括力,以及唯独属于他的一种充满奇迹的超验性体验。诗人的文字丰富而充满变化,同时跳动着火焰和冰块。为此,《雪国》既是人间的,也是宇宙的;既是空间的,也是无限的。
长诗《雪国》开始,两个极具形象的比喻就催生了一个特异的场域,难以言状的《雪国》逸出文字,向我们迎面扑来,“丹顶鹤是我雪国形象的代言/白山黑水 白羽长脚/丹顶红是我雪国高擎的灯盏或美人痣”,第二节开头,诗人打开通道,从中进入雪国,从而进入自己:“降温——一个冷的名词,此时,降临北方之北/卷刃的寒光里蕴藏着琥珀般的热血:水的表情凝固成铁的重、银的白。风把风打回原形/我得不停追逐或狂奔,不然冰会把呼吸焊在冰上//落在白桦树和黑针松上的白是白山黑水之上的睫毛之白/鸟比我的速度更快也更慢地飞入雪国的更快也更慢的心跳。”通过目光捕获成现象,再予以映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之间相互的词性转换、活用,扩大了现代汉语词汇的意义空间,充分挖掘了词语的表达潜能和张力,同时也增强了诗歌的审美表现力。
再看第五节,诗人运用感觉挪移,由此及彼,由想象抵达奇妙的心象描摹,“裹在滑板上的麂鹿之皮系上快乐又脱下快乐/只有林海和雪原知道,还有孩子和母亲们知道//拎着刻刀和酒瓶的父亲们大声走来/他们在朔风里完成了他们心里的众神冰雕像群/其实,大雪也完成对他们的雪塑”。接下来,诗人热血偾张,灵魂从空间里切割开,让我们见证了最为充盈的时刻:“要睡就睡在雪国的雪里,要葬就葬在北方的手心/枕着白山,濯着黑水,澡雪或冬泳/洗出一种清洁的精神,洗出心寒之后的热血偾张/沐毕,喝酒在篝火边/听萨满的鼓和铃声/一路耳蜗至心房和脑宇所踏出的节奏//把火烧死,把冰煮透,把酒炖烂,把爱烤香/把梦烹熟……”时间感觉延伸为空间意识,超越了一切的有限,没隐藏任何东西,却又有说不尽的东西。诗人用他的感觉,他的经验,他的灵魂,他的审美,与《雪国》对话,他说了很多,没说的更多……
诗集《一切皆由悲喜》,共选入了97首诗,其中一首为长诗。这些诗由诗人的想象创造力,将这个世界和自然、生命、人生均一严整的几何形平面变为三维形象,充溢着丰富的综合性。同时,由于李云赋予客观事物以强烈的主观色彩,把客观物境完全转化为意中之境,才使读者对诗中那些常见的客观事物重新生发意想不到的新鲜感,体验到新的魅力。
李云有超出常人认识世界的能力,这其中包含着他对现实和人性的判断,再由这种判断生产出想象力,这样的想象力必然充满敏锐的认知和感受。为此,诗集里的诗所选的每一个景点,每一个物事,合乎逻辑又反逻辑的想象,都是一个小宇宙,有着完全的独立和新发现,突破了经验边界与想象维度,其丰富非一般诗人的想象可烛照。
有时李云也隐藏在文字里,所以他的文字常常自带根须,进行旺盛的繁衍和生长,以此支撑着他诗歌世界的穹顶,而我们也跟随他居住在文字中,并在里面自由穿行。
于是,我看到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在深蓝色的天幕下,在月上柳梢、点点星光、浅浅半盏的风景里,正提一脉兰香、携带一缕微风,向我们缓缓走来,不绝如缕的情思和他浪漫的气质浑然天成。有时,他也会摇身一变,剑带侠光,如一位英雄,充满正义与侠义之气,在开阔的江边或是一眼不见尽头的原野上远眺……
他就是李云!
2021年3月10日于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