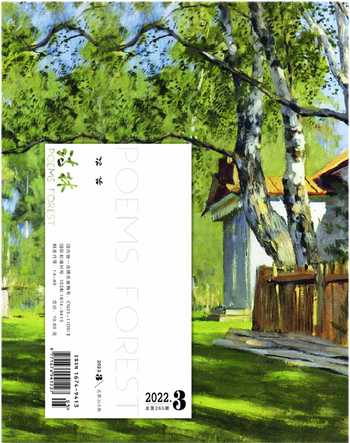重新发现诗人孙基林
2022-05-13赵思运
赵思运
最近十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新诗界的学者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诗歌创作的才华,构成了一个丰富的诗歌谱系。这貌似异军突起的现象,细究起来,恰恰表征出一个常识——诗学研究永远以诗性创造的感性经验作为先導,很难想象一个优秀的新诗学者却缺乏诗歌创作经验,在这个学者型诗人谱系中,孙基林无疑是尚未引起充分注意的一位。
虽然孙基林只“泄露”出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部分诗作,但可以窥见,其诗歌创作的基因很大程度上全息投射到了后来的研究之中。在他的生命年轮的核心,诗歌的感性经验和诗性创造力构成了不可遏制的诗学胚芽。随着季节轮换,诗性创造的感性力量伴随着学术理性的积淀,同步交融,茁壮成长,其诗顽强地通过诗学研究的年轮辐射出来。
孙基林的诗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叙述性,《原野上的葬仪》即是如此。他的诗歌叙述技术迥异于传统的叙事诗。传统的叙事文体往往更注重叙事要素,即使新诗的叙事也讲究内容的具体性和逼真感;孙基林的诗歌叙述,则更加注重叙述的整体性和象征性。对叙述艺术的实践,为孙基林后来开创的新诗叙述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丰沛的创作体验,使得孙基林的诗学建构不是纯粹的学理演绎,而是感性实践与学理演绎双重视域的交相辉映。这种诗学与实践的互文性,我称之为诗学重瞳现象。
孙基林的诗学重瞳现象还有一个表现:他的诗歌创作较早地突破了朦胧诗的意象诗歌模式,开启了第三代诗歌的口语表达式。这种诗歌实践的过渡性,使他更真切地洞彻了朦胧诗的内在紧张性与诗学困境,较早地敏锐于第三代诗歌的发生肌理与文本肌质。他在80年代的诗歌创作,似乎预示了他最早在《崛起与喧嚣: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中确立的当代诗学格局与诗学走向。
他的诗歌风格体现了从朦胧诗潮到第三代诗潮的嬗变特点,带有诗歌史的刻度意义。在语言表达方面,孙基林的诗作具有意象诗与口语诗过渡的辙迹。《黄昏的小树林》是典型的意象抒情,带有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唯美的死亡诗意;《原野上的葬仪》主要是意象叙事特征。这两首诗更多地表征出朦胧诗群的共性。
孙基林的诗让我想到韩东的创作,二人确实具有可比性。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们一起在山东大学读书,一起创办“云帆诗社”,韩东是以决绝的态度试图与传统的题材实现断裂,拆解了深度模式和不确定性,剥离物性与文化的粘连关系。如果说韩东的策略是“反题”,那么,孙基林的策略则是“正题”,是建设性的。两人殊途同归,实现对于传统诗歌意象的“疏离”。
孙基林的诗歌实践与诗学研究之间的重瞳现象,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隐喻性的解读。在上古神话的记载里,有重瞳的人一般是圣人;但在现代医学的解释里,这种情况属于瞳孔发生了粘连畸变,从O形变成∞形,但并不影响光束进来。我想,在诗人的眼里,在诗歌学者的眼里,建立敏感的双重“诗性视野”,突破常规意义的“正确性”,这种“畸变”恰恰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