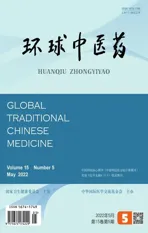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角度探讨中医“脑—肾—髓”理论指导下卒中后失语神经机制
2022-05-10黄佳钦谢巍曹云张丹莉雷筱菁周雨帆张梓寒常静玲
黄佳钦 谢巍 曹云 张丹莉 雷筱菁 周雨帆 张梓寒 常静玲
卒中后失语作为一种严重的获得性语言功能障碍,是脑卒中后主要的功能障碍之一,研究显示至少1/3的脑卒中患者会出现失语症状[1]。同时,由于语言沟通能力的缺失,卒中后失语常导致患者面临情绪管理、社会关系处理和日常生活能力等多方面问题[2-3],并增加中风病患者的护理成本[4]。中医药得益于长期临床实践形成的传统理论,在改善卒中后失语患者的语言功能方面具有优势,因此,传统理论作为中医药诊治疾病的基础,完备的理论体系更是其发挥临床疗效的前提,然如何结合现代医学阐释中医药理论内涵,客观体现中医经典理论的科学性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脑—肾—髓”理论作为中医传统经典理论之一,在卒中后失语的辨证施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如何结合现代医学探索中医“脑—肾—髓”中“肾”“髓”“神”的理论内涵,仍鲜有报道。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卒中后失语“脑—肾—髓”理论基础上,围绕神经内分泌学,以卒中后失语患者的HPA轴与神经可塑性为核心,在理论层面深度挖掘了卒中后失语“脑—肾—髓”的现代内涵,以期为具有传统理论特色、临床确有疗效的中医治法获得更全面、更客观的疗效证据奠定理论基础,最终从中西医结合角度为卒中后失语的临床治疗与评价提供参考。
1 卒中后失语“脑—肾—髓”理论以“形”与“神”为核心
“形神合一”理论作为中医学重要的学术思想之一,高度概括了人体生命活动与形态基础之间的关系,强调机体在正常生理活动状态下,“形”与“神”紧密联系,互不分割。卒中后失语作为卒中后的主要功能障碍之一,古籍中用“风懿”“癔痱”“喑痱”“风喑”“舌喑”“言语謇涩”等术语进行描述,然未予系统论述。在生理上,脑为髓海,是语言产生的物质基础,故脑及脑髓属“形”的范畴,语言为人体大脑皮层高级功能体现,属“神”的范畴,脑髓充沛是语言功能正常发挥的基础[5]。肾与脑之间的关系也主要体现在“形”(结构)与“神”(功能)两方面。在结构上,《难经·二十八难》与《灵枢·经脉》从经络联系上提示了“肾通于脑”的结构基础。同时,《黄帝内经》又从精、髓的关系角度阐释了“肾通于脑”的物质基础,指出肾藏先天之精,并主骨生髓,脑为髓海,脑之功能发挥有赖于肾精生髓以充脑。在功能上,《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记载“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与脑之思维、精神相关,此外,肾藏精,精舍志,进一步提示人体精神活动与肾精充养于脑有关[6]。在病理上,卒中后失语的病位在脑、肾,其病性以肾虚为本,风、痰、火、瘀为标,病机为诸邪相合,毒邪内生,脑窍闭阻,脑髓败坏,神失所养,从而发为本病。因此,卒中后失语的发病以“形”“神”概之,围绕肾精、脑髓、语言三者的关系,可概括为肾精亏虚、脑窍闭阻、脑髓败坏等“形”损日久,导致“神”的失调,继而语言功能出现障碍,亦即“无形则神无以生”“形谢则神灭”的具体体现。
2 卒中后失语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可塑性赋予了“髓”与“神”新的理论内涵
卒中后失语患者的功能恢复影响因素多而复杂,其中包括年龄、教育程度、Barthel指数评分和卒中亚型等[7],但其病理机制多与脑卒中后左侧大脑半球病灶周围和(或)右侧大脑半球进行语言处理任务时的神经可塑性受到限制相关[8]。神经元再生以及突触的可塑性改变是神经可塑性主要的两种方式,而突触可塑性又包括结构和功能两方面[9]。此外,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在包括神经可塑性在内的一系列神经发育和神经保护功能中是必需的,其表达的正常与否和神经可塑性密切相关[10]。系统综述研究亦发现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基因多态性与卒中后患者的语言预后有关[11]。因此,卒中后失语患者语言康复过程可能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介导的神经可塑性机制有关。
由上可知,神经可塑性作为卒中后失语语言功能修复的重要机制,包含神经元再生、突触结构与功能恢复两方面,与中医学的“髓”与“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脑髓作为神主导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脑髓有余,方能脑神得养,神明则形安,脑神充沛则形体得以灵活驾驭。神经可塑性机制中神经元与突触结构属人体形态基础,与中医“髓”“形”的内涵相符,而突触功能属生命活动体现,则与“神”的内涵相符。神经元再生与突触结构的修复是语言等神经认知功能正常发挥的载体与前提,而突触功能的恢复作为神经功能的重要表现,与卒中后语言功能康复效果密切相关[12],这与中医学“形神合一”中注重结构与功能、物质与活动、形体与精神相统一的传统理念一致,进一步阐明了中医学“形为神之宅,神为形之主”的“形”“神”互相依存的关系。随着神经影像学的日益发展,多种先进脑成像技术得以应用于卒中后失语语言功能评价,如集高分辨率三维T1加权MRI(high resolution three-dimension T1-weighted structure MRI, 3D-T1)、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弥散张量成像技术(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于一体的多模态MRI技术与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技术等,实现了卒中后失语大脑结构与功能的精准定量、定位分析,为卒中后失语神经可塑性机制的“髓”(结构)与“神”(功能)评价提供客观评价证据。因此,以评价反观治疗,在卒中后失语患者的康复过程中更应关注“形神同调”的重要性,注重神经元再生、突触结构修复与突触功能恢复的结合统一,为形成具有中医特色的现代卒中后失语康复方法提供新的思路,并围绕结构与功能两方面观察卒中后失语患者神经可塑性的激活,探索卒中后失语康复的“形神”机制。综上,以“髓”“神”为总纲,整合现代科学评价技术,基于中医“形神合一”经典理论进一步阐释卒中后失语患者语言康复的神经可塑性机制,具有一定的临床与科研价值,丰富了卒中后失语传统理论的现代内涵,并为临床治疗卒中后失语提供理论指导。
3 HPA轴功能的紊乱可能是卒中后失语“肾虚为本”的病理基础
脑卒中作为一种机体损伤,将引起机体产生应激反应,激活HPA轴,从而促进皮质醇的分泌增加[13],然而长期高水平的皮质醇则具有神经毒性,并影响疾病预后[14-15]。此外,HPA轴的异常激活及激素的水平与脑卒中病灶部位、病灶大小[16]及病情预后[17]均存在相关性。同时,语言与压力、情绪之间的关系逐渐被重视[18-19],而HPA轴作为生理应激系统,亦逐步应用于成人失语症应激水平检测的研究当中[20]。Laures-Gore J等[21]也证实了失语症患者存在皮质醇觉醒反应的异常及HPA轴功能的紊乱。糖皮质激素受体在海马体与前额叶皮质中广泛分布,两种结构在语言功能中均具有重要地位[22-23],这些研究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糖皮质激素能够影响语言系统。因此,在应激反应与情绪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卒中后失语患者HPA轴功能将发生变化,并与疾病进展密切相关,故分析卒中后失语患者HPA轴激素分泌水平有望成为疾病评估与预后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
中医学理论认为肾精亏虚,脑髓生化乏源,导致髓减神消,是卒中后失语的发病根本。肾精作为脑髓生化的主要来源,一则年老久病而肾精亏虚,精损无以生髓,二则风、痰、火、瘀邪气的产生亦与肾精亏虚相关[24],诸邪相合,蕴结成毒,败坏脑髓。由此可见,肾虚在卒中后失语的发病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现代有学者认为HPA轴功能变化与中医学中的肾脏生理、病理关系密切[25]。动物实验发现肾虚证大鼠存在着HPA轴的功能异常[26],而肾之功能正常发挥有赖于肾中阴阳调和,进一步的研究亦表明肾阳虚大鼠存在着HPA轴功能的低下[27],与之相反,肾阴虚则常与其功能亢进相关[28]。因此,中医学肾脏阴阳失调与HPA轴的功能异常相对应,为今后从客观角度证明中医肾中阴阳关系提供研究思路。许多研究亦证实了补肾药物对肾虚证动物模型的HPA轴具有干预作用[29-30]。其中唐璐等[31]证明了地黄饮子可通过改善脑卒中大鼠HPA轴功能发挥脑血管保护作用。上述研究进一步通过以药测证方式揭示了HPA轴紊乱与肾虚证存在着相关性。由此提示,卒中后失语患者HPA轴功能的紊乱可能为其肾虚本质。基于以上理论探索,笔者认为在卒中后失语中,肾精亏虚与HPA轴功能紊乱相对应,而髓海不足、脑神失养则可能与疾病神经可塑性机制相关联,进而猜测卒中后失语患者语言功能的损伤、恢复可能与HPA轴介导的神经可塑性机制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4 HPA调控的神经可塑性机制可作为卒中后失语肾精不足,髓减神消的现代医学内涵
既往研究发现HPA轴作为脑卒中后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主要应激表现,该通路激活引起的糖皮质激素分泌可直接或间接影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32],包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翻译、加工、转运及分泌等过程[33]。在由小鼠海马细胞建立的神经元样细胞中,糖皮质激素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后可调控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基因序列以达到抑制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mRNA表达的作用[34]。同时,体外研究发现,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也能够使海马神经元中依赖于促肾上腺皮质素释放激素受体1的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磷酸化增加[35],进而影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生成及神经突触功能[36]。因此,HPA轴可能通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调控脑卒中后的神经可塑性,其关键作用体现在过度分泌的糖皮质激素下调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从而对神经发生产生负面影响。

注:肾虚精亏,脑髓败坏,元神失养为卒中后失语关键病机。卒中后失语患者HPA轴功能紊乱为肾虚的病理基础,而其神经可塑性机制可从结构与功能诠释中医的“髓”与“神”。HPA轴功能的紊乱通过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磷酸化等过程影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生成、转运和分泌,进而导致神经可塑性下降,此发病机制可能是卒中后失语关键病机的现代内涵。
以上神经内分泌学机制与中医学卒中后失语“脑—肾—髓”理论具有高度相关性。肾虚相关的HPA轴功能异常具有介导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调控神经可塑性的作用,而神经可塑性包含中医“髓”与“神”两方面。因此,在病理上,肾精亏虚,脑髓不足,脑神失养的病机理论充分诠释了卒中后失语发生过程中肾精—脑髓—脑神之间的关系,而HPA轴功能紊乱导致神经可塑性下降的机制亦从神经内分泌学机制阐释了疾病关键病机过程。同时,在治疗上,纠正HPA轴功能紊乱以激活神经可塑性恢复的疗效机制,体现了卒中后失语补肾以填精,益髓以醒神的中医治则内涵。综合上述理论与实验研究,笔者认为以HPA轴调控的神经可塑性机制阐述“脑—肾—髓”理论指导下的卒中后失语关键病机及治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并赋予了卒中后失语中医“脑—肾—髓”理论现代生物学内涵,为今后探索中医理论的科学证据奠定理论基础。
5 基于HPA轴—神经可塑性机制的卒中后失语“脑—肾—髓”理论临床应用前景
卒中发生早期肾精亏虚,脑髓生化无源,抑或是毒邪内生,毒损脑髓,最终均导致脑窍闭阻,神失所养而致病,故醒神开窍,佐以扶正是临床早期治疗卒中后失语的治疗法则。至恢复期,脑髓空虚,神明受损,而病邪仍在,此期虽有正邪相争之局面,但正气亏虚为本,仍当以“益髓醒神”为主。又脑髓之充养以肾中先天之精为基础,故治疗上亦应不忘补肾益精,方能起到补先天以资后天的作用。
针刺在卒中后失语的临床治疗上具有一定的潜力,已有研究发现针刺对神经突触可塑性具有调节作用,是研究针刺作用机制的切入点之一[37]。同时,研究发现针灸治疗亦可通过调整HPA轴功能以改善抑郁模型大鼠情绪低落、快感缺失等行为[38],为针刺调“神”提供了客观证据。而以针刺调理脑、肾进而治疗脑病的机制则以经络学说为基础,首先强调膀胱经、督脉与脑在经络结构上密切联系,生理、病理上又相互影响。故以补肾、益髓、醒神为原则的针刺方案可能是提高针灸治疗脑病效应的有效途径。
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于“脑—肾—髓”理论指导下的“益髓醒神”针刺方案可显著改善卒中后失语患者的语言功能[39],该法以醒神为纲,益髓为本,开窍为要,最终达到补养肾精、调畅气血、养神明志的效果。同时,本团队进一步结合功能磁共振技术,从结构与功能两方面探索了“益髓醒神”针刺方案干预卒中后失语的脑网络机制,结果发现该方案结构上刺激双侧白质纤维束修复,而功能上则增强左侧语言相关脑网络间的功能连接[40],为该方案调节卒中后失语的神经可塑性机制提供客观影像学证据。因此,基于临床确有疗效的“益髓醒神”针刺方案,进一步集成神经影像学、分子生物学等现代技术,更客观、全面地探索针刺治疗卒中后失语的干预机制,为中医针刺疗效的科学性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临床与科研意义。
6 小结
综上所述,“形神合一”理论指导下的卒中后失语“脑—肾—髓”理论从生理、病理全面论述了卒中后失语的发生与发展,其发病以肾虚为本,风、痰、火、瘀邪气为标,脑窍闭阻,脑髓败坏,脑神失养为病机要点。针对卒中后失语关键病机,本课题组前期已形成成熟、规范的“益髓醒神”针刺方案,并初步探索发现了该方案具有提高卒中后失语神经可塑性的作用。然而如何基于“脑—肾—髓”理论,整合神经影像学、分子生物学等多项技术,更全面揭示“益髓醒神”针刺方案干预卒中后失语HPA轴调控下的神经可塑性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本文通过探讨HPA轴功能调控与神经可塑性机制激活的相关性,从现代医学角度阐释了卒中后失语“脑—肾—髓”理论中“肾”“髓”“神”三个关键点及其关系的科学内涵,为临床探索卒中后失语的发病机制与疗效机制提供新的思路,亦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