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指标
2022-05-07王宁
王 宁
派出所的赵振东找到明明的时候,他正蹲在塌了一边的土坯房子前面抽烟。昨天晚上一场白毛大雨,把早就摇摇欲坠的房子,压垮了半个角,刚好砸在家里的大水缸周围,连挑水都省了。好在床还在,就是发霉的被子又湿透了,耷拉在床上像一条濒死的鱼。
早上没吃饭,到中午明明饿得眼花。骄阳正中,山坡上一丝风都没有,他又咽了咽口水,昨晚没洗干净的煤灰还挂在两侧脸颊,鼻子里窜出一缕躁人的烟气儿。明明想着抽完这根烟就去煤场那里把煤下了,要上几个钱把晚饭解决掉。
大西北的天气怪杂得很,昨晚下雨下得像天塌了一样,今天就大太阳高照,晒得人头皮子发麻。赵振东就是这时候来的,从老化工厂后门出来,沿着山坳里的羊肠路,走不了多远就能看见明明在半山坡上的家——以前看厂子的老李带着狗临时歇脚的一个土坯子房。老李病死以后,他的狗在这儿守了几年。后来化工厂倒闭了,厂子里的小年轻们四散而去,没人再来后山喂狗,时间一长,连狗都熬不住跑了。明明这才搬了进来。
明明是大岩头煤矿的一个孤儿。
大岩头煤矿位于中国大西北最贫瘠的山沟里,万里黄沙,一年四季刮不完的风,戈壁滩上除了初升的月亮是干净的,其他一切都笼罩着亘古不变的土色。这里1958年建矿,20世纪60年代初期,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在一片戈壁滩上搭窝筑巢,操着各地不同的方言,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愿,生下各具优劣的娃儿。
明明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生的,他有印象的只是从小跟着红旗幼儿园的后勤赵大爷一起生活,吃在幼儿园,长在幼儿园,直到赵大爷去世,明明就自动“滚”出了幼儿园。学也上不成了,大字还不识几个,成天跟在一帮混子后面。有吃的就混着吃点,有喝的就跟上喝点。打架的时候倒也不怂,人家喊一声:“明明,走,跟我收拾个人走!”他也不问,跟着就去了。派出所里进去了好多次,好多次又都放回来了。一个孤儿,要钱没有,要脸也没的,年龄又小,派出所收押连个签字的监护人都找不着。
时间久了,派出所的警察挺同情明明,找了个小矿的招工主任,给明明安排了一个焦化场里卸煤的临时工。每天的基本工资是十五元,卸煤一吨一元。
就这几百块一个月的工资也不稳定,有活儿的时候从早干到后半夜,眼珠子都干冒火星儿了,场长老马还扯着嗓子喊:“都没一个好好干活儿的,日弄鬼呢嘛!”没活儿的时候闲得只能和煤场里的野狗眼对眼,加上明明时不时还得进局子,老马给明明发钱的时候都忍不住说:“明明,就你挣的这俩钱儿,还不够狗吃的,你挣撒着呢嘛你。”
……
今天本来打算抽完烟就到老马那儿下煤去,没想到赵振东来了,明明转了转眼珠子,生锈的脑子盘算了一下,好像是快十一国庆了。那就对了,派出所的任务又来了。明明站起来拍了拍后腰上蹭的土,主动和赵振东打招呼:
“赵哥,你等一下,我把被子晒上了再走。”
“晒撒呢晒,你进去了要待几天呢,被子放到外面,两天风就给你刮成棉絮子了。”赵振东啐了一口嘴里的土味儿,“房子咋还塌了,你一天到晚干撒着呢,弄得窝囊着。”
“哦。那成呢,哥,我收拾个衣服。”明明一缩脖子就往房子里走。
“赶紧的,你还有个撒衣服可收拾的……几天就出来了。”说着,赵振东踢了踢脚边的土块,“你这房子还能住人?到煤场里让老马给你弄个预制板的房子,他那儿多着呢。”
这时阳光大好。远处倒闭了的化工厂空地上腾起一小撮土旋风,几只野狗围着叫唤,高一声低一声的。赵振东扭过头看了看,又转过来说:“你看你把个房子弄成啥样子了,老李的狗住到这儿的时候都比你干净。”
明明没敢搭腔,进屋随便捡了两件衣服一裹,找了个塑料袋一兜,转身出来,赵振东伸出手,拍了拍明明的肩膀:“行了,这次再帮哥完个指标,后面把单位上发的胡麻油给你拎上一桶……一桶油那贵得很,让你娃好好过个节。”
明明一张煤灰脸上立刻挤出灿烂的笑容,两个眼角飞起来,嘴上却是微微让着步:“哎,我还过撒节呢,吃个饱饭就行了。走吧,赵哥。”
赵振东前头走,明明在后头跟着。羊肠小路还挂着昨晚大雨后的泥泞,赵振东一边跳来跳去地躲着泥洼地,一边叮嘱明明:“你也注意着点儿,我开车来的,你那个鞋底子的泥把我车都能糊上呢。”
“那不会,我上车就把鞋脱了放塑料袋里。”明明讪笑着。
“嗯,公家的车!车接车送的,你娃还成领导了。”赵振东也笑了,甩开膀子小跑了两步。
明明快步跟上,把他半塌的土坯房远远地甩在身后。
绕过了化工厂的后门,就是一条新修的水泥路,水泥路的对面是一眼看不到头的荒滩野坝子。远远地能望见野坝子里的焦化场,几个烟囱正呼呼地往外冒黑烟。
“今天估计活儿多,这烟囱冒的烟这么壮。”明明心里想着老马那张整天怒气冲冲的脸,怕是又站在场子里大声叫骂:“明明这个懒怂,有活儿的时候见不着人,没活儿了过来跟狗抢食。”
明明忍不住问:“赵哥,这次还是吸毒嘛还是撒?”
赵振东听了,一边用钥匙开车门,一边摆摆手示意明明上车:“吸毒的够了。这次弄个打架伤人的……你的就是个打架,伤人的有个前几天市场上把人家卖菜的头打伤的,已经拘了。”
明明拧身上了车,把车门拉上。赵振东扭头看了他一眼,叮嘱道:“反正你去了撒也不要管,把字签了就行了。这次给你换个号,上次那个号子里好几个吸毒的,没瘾都闻出瘾了。”
赵振东带着明明走进十字街派出所大门的时候,被正要外出的胡所长看见了。胡所长的脸立刻就耷拉下来:“东东,你成天就是找个明明呗,撒正事都没有!刘队上次给你咋说的,啊?明明再不能用了,分局都知道‘指标明’了。明明年龄也大了,拘得多了,以后工作、找媳妇咋弄呢。还有昨天让你把那个打人的娃娃转走,你转了没有。一天到晚见不着你人,你比局长都忙。”
赵振东赶紧拉了一把明明,说:“哎!我也和明明说着呢,这是最后一次了。主要是大队那边催得急,这次过节每个所都压着指标呢,咱们不用明明,那其他所也就用了。”
胡所长撇了撇嘴。又冲着明明抬了抬下巴,算是打招呼:“明明,还是要好好干活儿呢。这么下去,你以后啊,麻烦得很啊……”
明明赶紧点头哈腰:“哎,哎,哎。”
接着紧走几步,低着头跟着赵振东进了派出所的办公小楼里。
一进楼里,赵振东就忙得不见人影了。明明一个人坐在楼道里,无所事事地看着窗外的树叶。
一个多月前,他也是坐在这个位置上。那时候正值盛夏,院子里那几棵大杨树长得正旺,肥大的叶子在空气中忽闪着,树皮上全是眼睛形状的树疤。明明看着,就觉得那眼睛一只只的好像都有了灵魂,直勾勾地盯住他,要把他往地狱里拉。
去年冬天,他好像也是坐在这个地方。那天风很大,漫天飞土,各种颜色的塑料袋子被风卷起来,挂上杨树的枯树杈子,像一面面招展的旗。明明想起来小时候跟着赵大爷住在幼儿园的日子,六一儿童节一到,幼儿园里挂满了各种颜色的彩旗,他和别的小娃娃一起站在旗子下面唱: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
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明明想着,忽然哼唱起来:“娃哈哈啊娃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一边唱着,他还一边扭了扭脖子,像在幼儿园里表演一样。路过的小警察看见了还损他:“哟,明明,想撒好事儿着呢,笑成这样。”明明赶紧收敛了脖子手脚,端端正正坐起来,继续看着枯树杈子发呆。
今天,他又坐在这儿了。好像这里留给他了一个专属的位置一样,这让他居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归属感来。他和这里的警察一样,他们看到的一年四季的风景,他也看到了,而且比他们都看得仔细。赵振东都不一定知道,第三棵杨树顶上有个老鸹窝,很大。他亲眼看到过老鸹站在上面发骚叫对子,尾巴撅起的,像吃坏了肚子……突然,明明的肚子咕噜噜地叫唤起来,他才想起今天到现在还一口饭都没吃。
他站起来想要点水喝,往前走了两步,又突然慌慌张张地停下来回到椅子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肚子憋成一把勺子状,想将咕噜噜的声音憋死在腹腔里,但是那声音太大了,好像撼天动地一般。明明突然羞愧极了,两个眼睛往四下里滑了一圈,用手里的塑料袋子往肚子上捂了捂,生怕别人听到他这一刻的窘迫。
等到赵振东来找明明的时候,太阳都挪到最西头的杨树树梢上了。
赵振东说:“今晚还得加班,明明你先回去。明天一早你自己过来吧。找上次那个胖胖的小金,他帮你办。快的话,明天你和之前的几个人一起体检,办手续。”
明明愣了愣,然后顺从地说,“哦。那成呢,明天我再过来。还要体检嘛,每次都体检,麻烦得很。”
赵振东一挑眉毛:“你还麻烦得很?不体检,人家拘留所能收你吗!明天来再别带衣服撒的了,人家到时候都给你收了。你都是老号子了,不用我再交代。明天早上早点过来,别让人等。”
明明点点头。站着没动。
“赶紧走,你还站到这儿干撒呢?一会儿胡所回来看见又要说半天。”赵振东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明明还是没动,从鼻子里吭出一缕细若游丝的声音:“我今天还没吃饭呢。”
赵振东一听,气笑了:“你个狗怂,老子还得养你呢?”说完,从上衣口袋里摸索出一把杂七杂八的零碎儿,有皱巴巴的卫生纸,有几张写着字的纸条,中间夹杂着几张纸币。赵振东抽出一张十元钱,一边递给明明,一边骂着:“老子还得给你这货发工资?”
说着话他把钱往明明手里一塞,还不忘朝明明屁股上踹一脚:“赶紧滚!”
明明被胃酸催动着,像被点着了的火箭,拿着赵振东给的十块钱一口气窜出了派出所。大门口就是大岩头矿最繁华热闹的十字街,明明像一只饿极了的大灰耗子,钻进人群,忽而就没了影儿。
明明吃了一大碗牛肉面,还蹭了一根面馆伙计的烟抽,打着饱嗝儿叼着烟,手里甩着中午带出来的塑料袋子,慢慢地走向四元的录像厅。
这时候,夜幕已经迫不及待地扑了下来,十字街上的每一盏灯光都亮得摇摇欲坠。这是大岩头矿一天当中最温柔的时刻,街上会走过很多下班的人、很多白天见不到的好看姑娘,夜色笼罩之下的每个人都散发着与大西北煤矿格格不入的柔和。
他走过夜市上的各种小摊子——羊肉串、什锦砂锅、凉面、热苞谷、炒凉粉……它们也都像一个个面目鲜妍的姑娘,等待品尝。明明的胃里还鼓胀着牛肉汤的味道,却还是馋得舌头打转。他心里发狠地想着:以后有钱了,吃牛肉面要顿顿加肉。把四元也叫上,天天吃、顿顿吃。
正想着,明明已经走到了利民桥旁的一间录像厅门口。墙上挂的两个黑漆漆的大音箱里传出来武打片的声音,沉重而粗糙,震得墙面地面都在颤动。门头上挂着一个焦黄的大功率灯泡,照着录像厅的招牌:老地方。
——老地方录像厅,是四元租下的铺面也是他的家。
四元是明明在大岩头矿唯一的朋友,生得方头大耳小眼睛,和明明都是临时工。但是四元不一样,四元有文化,是煤炭学校的大专生。写字也好看,写出来的字和他本人一样方方正正,容不得一丝圆滑。
四元的妈死得早,剩下四元爸一个人在各个小煤窑里下井挖煤,养活四元。两年前,四元爸所在的小煤窑发生了冒顶事故,砸死了三个人,四元爸是其中一个。小煤窑窑主花钱消灾,给每个死亡工人的家属补偿了两万元。四元去领钱的时候,发钱的人还羡慕地和四元说,这是历年来赔钱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死的外地人顶多八千。
四元问明明:“你知道不,明明?我爸的骨灰,才四斤来重。你猜猜多少钱是四斤重?”
明明摇摇头。
“大概二十万吧。这次死了三个人,总共才赔了六万。明明,你说说,钱多贵重……”四元顿了顿,抬起头看着天空,“我拿到我爸的骨灰,我才知道这世上钱才是最重、最贵的。”
说完,四元的眼泪从脸上一路落进脖颈子里。
后来,四元拿了他爸抚恤金的一部分,租下利民桥旁边一个小铺面,开了个录像厅。不大,但是摆上长条凳,坐下三四十个人没问题。录像厅后面还连着一个小房子,能住人。四元和他的女朋友一起搭伙做饭,在录像厅里摆开了生活的架势。
明明常去录像厅帮忙。帮着拉煤卸煤、打水扫地,偶尔安静地坐在最后一排看会儿录像。四元和他女朋友都不在的时候,就让明明管账。多少人来看录像,收了多少钱,卖了几盒烟、几包瓜子,明明都很认真地画下来——他会写的字实在是太少了。每次给四元交钱的时候,每张钱都被整理得平平整整,连一分钱都不会少。四元时不时地会请明明去吃一碗面,或者打几把台球,还经常收拾出一些不常穿的衣服送给他。因为这些恩惠,明明在录像厅干活更加卖力了,经常把那个小小的录像厅弄得很是干净温暖,连小屋子里都收拾得窗明几净,比自己的狗窝还照看得好。
……

明明今天从派出所里出来,吃饱了饭,第一时间就先去了录像厅。刚打起门帘走进门,就看见赵振东坐在里面。明明心头猛地一跳,像被装满煤的矿车磓了一下。赵振东刚好也抬头看见了明明,在音响轰轰隆隆的声音里,朝明明招了招手,大声嚷着:“过来!我给你说个事。”
四元和明明一起把赵振东让进了后面的小屋里。小屋太小了,一张床、一张桌、一个炉子,就已经放不下啥东西了。一下子进来三个大男人,愈发逼仄。赵振东瘪了瘪嘴,笑道:“你们两个真绝了。一个住的狗窝子,一个住的狗笼子。”
说着,自顾自往床沿上一坐,顺手拿起桌上一个小盘子里的几颗枣,往嘴里送,刚嚼了两下,就酸得呸了一口。皱起眉头抱怨:“四元,你这撒枣子!哦呦,酸得人头都掉呢。”
“那我给哥洗几个好的去。”四元说着就要端盘子。
“别弄了,我给明明说完就回去值班了。”
明明一听,马上从四元的影子里走出来,佝偻着腰,像被谁打了一顿。
“明明,我说你娃这次运气好呢。你前脚刚走,胡所就开会回来了。说是指标减了,你明天不用过来了。害老子跑一趟,我刚才十字街上把你没找着,我就知道你肯定上这儿来了。行了,你别再把个脸垮下了,胡所说了,以后都不找你了。让你娃过好日子呢!”
明明听完,脸上就像老妖道布云布了一半让人抽了法力,从乌云卷滚刹那间云破日照,整张脸也活泛起来,从长年累月积攒下的煤灰里,散发出欢喜的光芒来。
四元比明明反应快多了,一把抓住赵振东的手,激动得声音都在发抖:“赵哥,真的吗,赵哥!我就说嘛,昨天晚上下着大雨呢,我听见房头咋还好像喜鹊叫着呢。我媳妇还说我耳朵让驴毛塞了,听声音都带着驴叫。”
说着,一手抓着赵振东的手不放,一手从口袋里往出掏钱,录像厅晚上刚开门没多久,兜里没几个钱。四元赶紧又去拉桌子下的抽屉,手哆哆嗦嗦地还没拉开,赵振东一把拦住了。
“我说你这是干撒呢!我缺你这两个钱儿呢!半吊子个鬼混子还学人家送钱呢,你有几个钱?”
赵振东阻止了四元拉抽屉,骂完四元转头又骂明明:“明明,你看看你这个狗怂东西,老子晚上没吃饭,哎,专门找到这儿。你狗头缩到角落里,不知道想撒着呢!前面胡所和我说的时候,刑警队的刘队长也在呢,两个大领导都点了头了,你娃真是福气到了!从今往后多跟人家四元学一下,有个人样子。我听你们马场长说,这次矿上最后一次临时工转正,人家四元排第一个。你呢,啊?转不了正,你娃打算一辈子临时工干到撒时候呢?”
四元看赵振东又要发脾气,赶紧打圆场:“哎,赵哥,再别和这个水脑子说话了,一时半会儿他反应不过来。主要是明明这多少年了,都落下病了。一到快过节的时候,他哪儿都不敢去,就到山上房子里等着派出所的人呢。这些年,严打的、过节的、开个撒大会的,明明就没停过。每次过节我叫他吃饭,他都不敢走,怕你们找不着他。这个怂人傻得很,憨得很……”
说到后面,四元说不下去了。眼睛往地上一沉,连声音都重了起来。
赵振东听了这话,也有些难受。眼眶子热了,但是很快压下去,哆嗦着声音问:“明明,唉,我也是……咋说呢。确实是可怜娃娃,家里也没个人……明明,你把我恨上了吧,这几年?”
明明用鞋底蹉着地上的灰,头也没敢抬,声音有点哽咽:“那没有,赵哥。我没有恨谁,我把谁也不恨。都对我好着呢,我心里有数呢。”
一时间,三个大男人都有些眼湿。气氛刚要尴尬起来的时候,外间传来喊叫声:“四元!四元!赶紧出来看来!录像机卡掉了!”
四元听了,答应了一声,抬脚就要出去。
赵振东也趁机站起来迈了一步,说:“我还要值班呢,我也要赶紧走。这饭还没吃上呢……唉,真把老子饿死了,十字街派出所就没人干活儿了。”
四元、明明和赵振东都笑了起来,一起走出了小屋。
四元忙着收拾录像机去了,明明和赵振东走到了录像厅外面。一阵风吹过来,把门上挂的黄灯泡吹得摇摇晃晃。
明明说:“赵哥,那你赶紧先把饭吃上。那个撒……明天,明天我就不到所里去了。”
赵振东拍了明明后脑勺一下:“刚说了半天,你听了个撒?你耳朵才让驴毛塞住了吧?明天你还来干撒呢?又要坑我十块钱走呢嘛!狗怂娃娃,贼得很!”
说完,赵振东眼睛里带上了笑意,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出一两分长辈的温情。
明明啥也没说,突然弯下腰给赵振东深深地鞠了一躬。
赵振东愣了一下,眼神暗了暗,接着又啐明明道:“赶紧滚!还学上人家读书人来这一套呢,你赶紧进去给四元看场子去。老子饭都没吃,看你在这儿唱戏拜祖宗呢。”
说完扭头走了。
明明站在灯下,看着赵振东远去的背影,深秋的风里突然飘来一股香甜的味道,好像是小时候幼儿园里的槐花香又好像是街头爆米花的香。太久没闻过这么香的味道了,明明像狗一样把鼻子仰起在空中,嗅来嗅去,一脸的满足。
第二天早上,马场长骑着摩托车还没进焦化场的院子,远远就看见场院大铁门旁站着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气得肝儿疼。
离老远就骂上了:“我把你个狗怂娃娃弄死呢,昨天上哪儿去了?死到狗窝子里了嘛?你忙撒着呢?”还没骂几句,摩托车已经一路扬着煤灰开到了明明跟前。
“明明,我问你着呢!你忙撒着呢成天,我看咱们大岩头矿的矿长书记加起来都忙不过你一个人,你还来干撒呢?”
马场长双腿跨着摩托车,左手扶着车把,右手的食指又粗又糙,像一根黑木炭直直地指向明明的鼻子。明明吓得半天不敢吱声。
“说话!你眼珠子翻来翻去的,想撒坏招呢?”
“前天晚上不是下大雨么,我和雷娃、四元一起把场子里的煤盖了,回去都晚上两点多了。我那个房还塌了一处,我弄了弄就睡了。睡到昨天中午,本来就要过来下煤……”
“你少给我绕五子(耍手腕为搪塞他人而指东说西),我问你昨天为撒没来,你说前天下雨着呢,你咋不从去年开始说?”
“哦。我这不是说着呢,昨天中午我刚要过来,赵振东过去找我了……”
“赵振东?”马场长顿了一下,“他又找你干撒呢?”
马场长想了想,脸上先露出一副了然的模样,接着又换上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木炭样的手指头仿佛要戳破明明的脑门子,“你呀你呀!上次我给你咋说的,啊?人家矿上马上就要清理临时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人家是转一批、清一批。最后一批指标给临时工转正,另外再清理一批,清理掉就不要了。你再进一次局子,你以后都进不了我这个焦化场的门了,你知不知道?”
明明点头如捣蒜:“知道呢。”
“知道呢?你知道下个撒?啊?明明!我的神仙祖宗,我的娃娃!你再给赵振东完一次指标,你这辈子就真成了狗了!成了鬼了!”
马场长从摩托车上下来,踹下脚蹬子,痛心疾首地绕到明明脸前。
“明明啊!你把你马叔的话听上一句,成不成?赵振东这家伙,我上次和他说过了再不能找你了,再找你就把工作丢了,他这亏心货咋还找你呢?……你昨天又跟上他去了?你个瓜怂!”
明明赶紧解释:“马叔,你别着急。我昨天跟他去了,但是后来他又让我回了,说是以后也再不找我完指标了。”
“啊?撒?他说的?”
“也不是他说的,胡所长和那个刑警队的大队长一起给他说的,以后再也不用我了!”
“真的吗?明明!”老马的黑脸上也难得出现笑容,“那就好啊!你娃这下就有救了。我就说嘛,哪能把个老实娃娃往死里欺负呢。老天爷也长下眼睛着呢么,这些人做事不能做绝么!你以后好好干,就算这里转不了正,过几年到别的矿上说不定就能给你转!”
明明听了这话,就像雨里开出的花,眉毛鼻子眼睛嘴巴全都在煤灰色的脸上舒展开来,一张黑脸上龇出白白的两排牙,反射着耀眼的太阳光。
到了中午,马场长找到正在洗手的明明,问他四元咋一早上都没过来。
明明说可能是录像厅昨晚又放得晚了,过会儿肯定就来了。
马场长嘴上还是有点不高兴:“四元这个娃娃,刚和他说转正呢,就给我皮皮拉拉的,活儿都不好好干了。等他来,我下午收拾上一顿给他紧紧皮子,都是欠收拾的货!”
正说着呢,场院大门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人。一边跑,一边大声喊人:“马场!马场!明明!明明!哎呀坏事了,坏事了!”
马场长一仰脖子:“嗥撒着呢,撒坏事了?”
来人把手往前一招,喊道:“你们场子的那个娃娃,四元!早上在十字街那个樱花舞厅门口,让十字街派出所给抓走了!你们赶紧过去看一下去!”
马场长的脖子像被人在空中掐住了,两个眼珠子瞪得老大,额头上青筋迸出:“撒?你说撒?谁让人抓了?”
来人说话间已经走到马场长眼前:“就是你们方脑袋的那个娃娃,四元嘛!我看了一眼,警察抓的那娃娃头方愣愣的,就是四元。我听说是在舞厅把人给打了还是咋了,没仔细问。这不赶紧过来给你们说一声。”
明明一听,兜了一把水往脸上呼啦了一下,甩了甩,整张脸绷得紧紧的,像一块挂着水的煤块。“马场,把你摩托借一下,我去看看。”
“哎!我也去!我把摩托骑上,你坐我后头。”马场长赶紧拿钥匙往摩托车跟前走,“明明,你别着急,四元那个娃娃我知道呢,人家有数着呢。还不知道是撒事情呢,咱们过去看看再说!”
说话间,马场长双腿一蹬,摩托车“轰”的一声窜出去了。
带着后座上半天没吭声的明明一起,扬着漫天灰土,一路向十字街驶去。
马场长的摩托车停在十字街派出所门口的时候,赵振东刚好从里面走出来。看见马场长和明明,他脚步停了一停。想转身往回走,又顿了顿,扭过身子迎上来,冲着马场长和明明做了个让他们走的手势。
明明想问几句话,但是看见赵振东的嘴巴抿得紧紧的,眉毛也拧在一起,像山一样压在额头,就没敢出声,拿胳膊肘顶了顶马场长的后腰。
马场长也没敢上前离得太近,就着几米远的距离,尽量压着声音问了一句:“东东,四元他,在里面?”
赵振东还是没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这时候,明明觉得一列火车呼啸着从头顶开过,耳朵眼里嗡嗡直响,啥也听不清了。
马场长的脸瞬时垮了下来,转头叫明明:“明明,你把摩托推走,找地方停下。我和东东说几句话就过来。”
明明没说话,推起摩托车,向不远处的商店门口走过去。
马场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走向派出所大门旁的后巷。赵振东两边看了看,也默契地往巷子里走。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向里面越走越深,明明的心也跟着一点点越沉越深。
过了好一会儿,马场长从后巷里先走了出来,面无表情地走向明明。
此时的明明听见那列火车还在脑子里盘亘着,轰隆作响,一刻不停。
明明把车推到马场长跟前,马场长说:“明明,先上车,咱们回去说。”
明明果真一句话没问,直愣愣地跨坐在了摩托车后座上。他仰起头,看了看太阳。
要说大西北秋天的阳光真是太舒服了,从高远的蓝天上满满登登地倾泻下来,就像温吞吞的洗澡水,把人从头到脚完完整整地兜住,还要再晃上两晃。猫儿啊狗儿啊,稍微挨着点儿阳光就能睡一个饱觉。明明仰起头,温暾的阳光将他抱住,好像是四元的声音从哪儿传过来了。明明眨眨眼睛,“呜”的一下子,泪水酸掉了半张脸。
回到了焦煤场,马场长的摩托刚一进院子,雷娃和几个工人就围上来了。马场长心烦不已,赶他们去干活,两脚四拳地轰了几下,工人们也就都散开了。
马场长转身一把拉住明明,两个人一起走进了场长办公室。一进门,马场长反手把门落了锁,让明明坐到椅子上去。再从桌子上端起保温杯子,咕咚咕咚喝了大半杯水,抹抹嘴。又拿出一个一次性的纸杯子,倒上凉开水端给了明明。明明默不作声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接过杯子,微微点了点头又坐下了。
马场长也拉了把椅子,坐下,腿抖了两下,这才张了口说话。
“明明啊,四元这回啊,有些麻烦了。”他顿了顿,明明端杯子的手抖了。
马场长告诉明明,上午四元到她对象上班的樱花舞厅去,刚好看见一个醉汉拉着他对象往包房里走。两个人厮打得很厉害,四元对象上身的衣服也都给撕得差不多了。早上舞厅里没有人,只有一个负责打扫卫生的老太太还在后院收拾垃圾,根本听不见里面的动静。四元一看对象上半身都光了,脑子一热冲上去就打。
马场长深叹一口气道:“四元个愣娃子,还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个水果刀,把那货捅了几刀……”
明明听到这里,突然感到脑子里那列火车像疯了一样乱窜,他整个头皮都麻了,耳朵里钻进了金属的搅拌机,轰鸣声炸得他脑浆子都快钻出来了。
“我听赵振东说,那货到总院就剩一口气了,大夫说是把肠子扎断了。你想呢,肠子断了,那屎啊尿啊的……还有大出血,好像有一刀还影响性功能了咋的,反正严重得很。这边矿区总院治不了,人现在已经往省人民医院送了,还不知道活得成不……”
说着,马场长狠狠拍了一下大腿:“哎呀!这个四元呀!咋就惹下这么大的祸事出来了!打架就打嘛!你动刀子干撒呢么!”
明明听着听着,泪水像开了闸,哗哗地涌了出来。他拿手背抹了两把,又用掌心呼啦了几把,还是止不住。他抬起胳膊,一双眼睛捂在袖子上,再也拿不下来了。
马场长眼睛也红了,他挤了挤眼角处的酸意,泪水竟也流了出来,夹在眼角深深的几道皱纹上,像山上的梯田洇住了雨水。
“行了,明明,你也别哭了。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哭有撒用呢。”马场长安慰道,“我听赵振东说前几天不是刚有个人把个卖菜的打进了医院,今天四元又弄了一个重伤的。这马上要十一国庆节了,派出所从上到下一根弦绷紧着呢,连续出事就不好交代了。估计这次啊,四元麻烦大了。”
马场长一边说,一边要给明明的杯子里添水。
明明用手轻轻地挡了挡,然后用两边胳膊狠狠地抹了抹眼睛和面颊,从椅子上站起来。
马场长看了看他的脸色,声音放轻了说:“明明,这事儿咱们也只能等等看,到底那个人抢救的情况咋样。这个事情暂时不要给任何人说。赵振东也说了,他想想办法,我也想想办法找找人。你别着急,也别乱跑,听见没有!”
马场长后面啰唆的几句话,也不知道明明听见了没,他两步就到了门口,打开门走了出去。
马场长颓丧地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弹。
晚上的时候,明明才见到了四元的对象。
他用钥匙拧开录像厅的门,里面没开灯,黑漆漆的,只有后面小房子里透出一点光亮。明明顺着光亮走过去,撩开门帘子,只看见四元对象一个人坐在床沿上发呆。两个眼睛又红又肿,脸好像也肿着,灯光下看不太清。
四元对象听见响动,有点慌张地转过头,看见是明明,嘴角往下一撇,哭了。
明明叫了声:“姐。”然后就蹲在地上,手指头划拉着地面,没再吭声。于是,满屋子只剩下四元对象呜呜咽咽的哭声。
“明明,”四元对象鼻音浓重地叫他,“今天的事情,细的我就不说了。反正我是把罪造下了,四元这次是死是活、是判个十年八年,我都有准备。”
“明明,”四元对象低下头,继续说,“我这里还有一万八千多块钱,是四元他爸的赔偿金,去掉开录像厅的钱,再加上我们这两年攒下的几千块,你都拿上。”
四元对象又抽泣了几声,接着说:“明明,姐是外地农村人,在这矿上认不下几个人。你把钱拿上,给四元找找路子。就这些钱,不多,能帮四元多少就帮多少。哪怕是买点烟酒给人家号子里的人送一送,让四元少受些罪。”
“我听你说号子里面进去了,把人挂起来打腰子呢,”四元对象泣不成声,“四元以前下煤的时候让煤块砸过一次,腰上本来就有伤,这一进去了,让人打得受不住,可咋整呀!”
“姐,”明明站起来,立在一旁说,“我想办法。我们马场长也说想办法呢,还有赵振东,我们场子里的人都到处打听着呢。四元人好,把人都围下着呢,马场长还说要找矿上的大领导出面说情,你先不要慌。钱你拿着,我们把人找对了,真要用钱了,再说。”
两个人互相安慰了几句,明明就离开了录像厅。
这一晚上对明明来说是有生以来最折磨的一个晚上,以前号子里挨打的时候他也没这么痛苦过。拳头打在他身上他早就不觉得疼了,但是一想到四元进了派出所,明明浑身就像动画片里被抽了筋的小白龙,疼散架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明明就到了大岩头矿测绘处的大门口等着。
他听号子里的人说过,测绘处计划科的副科长,姓彭,是副矿长的儿子。那个人本事大得很,有个抢钱的下午进的号子,还没来得及挂上打呢,就来人给放出去了,晚饭都不耽误——就是彭科长背后使的力气。
恰好这位彭科长和马场长走得近,他时不时到焦化场找马场长要无烟煤的细煤,马场长每次都是小货车亲自拉过去。明明就帮忙打下手,帮人家上下煤,有时候还能得一包好烟抽。一来二去,也算熟人了。
那人总是笑容满面的,和人也挺亲近。明明沾着煤灰的手,人家也不嫌弃,说握就握,还说明明眼睛大,长得像个港台明星。
明明在土坯屋子里,想了整整一个晚上。自己认识的,有大本事、大后台的,也就这位彭科长了。
明明在测绘处门口蹲了快一个小时,才等到有人陆陆续续来上班。他没敢站得太显眼,躲在旮旯里,像个贼娃子一样探头探脑。到了快八点半的时候,彭科长来了。
明明“嗖”的一下窜出去,吓得彭科长后退了两步。站稳了仔细一看,是明明。彭科长果然又笑了,说:“哎!明明!咋是你啊!吓了我一跳,这一大早的。你干撒呢,不去上班老马不拾掇你吗!”
明明不好意思地低了低头,说:“我想今天请你吃个饭呢,彭科长。”
彭科长一愣:“请我吃饭?有撒事情呢,请我吃饭。”
“没撒事。”
“没撒事,你一大早不年不节的,你请我吃撒饭呢?”彭科长又笑了。
明明只好解释道:“我有个朋友,犯了点小事儿,想看看有没有路子帮帮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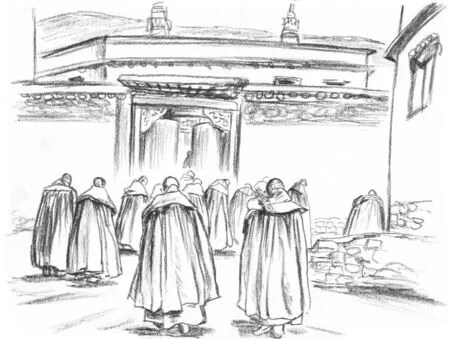
“撒事情嘛,我听听。”彭科长笑眯眯地问。
“这单位门上说不方便。要不到中午,我过来找你行不行?”
“你别一趟趟跑了……这样吧,你知不知道福满楼?”彭科长问。
明明一听这话,心下了然:“知道知道,那中午在福满楼见面,成不成?”
彭科长又笑起来:“哎呀,马场长老说你是个榆木脑袋,我看着不像嘛!机灵得很啊!那成呢,咱们中午,福满楼。”
说完,有人和彭科长打招呼,他转身就和那人说说笑笑地走了。
明明一想到彭科长如果能帮忙,那四元这个事儿说不定真的有转机。他的嘴忍不住咧开来,两排大白牙明晃晃的。
到了焦化场,马场长看见明明就招呼他:“明明,你来我办公室,我有话说。”
明明跟着马场长进了办公室,关门落锁。
“明明,有个好事儿我要告诉你,”马场长拍了拍明明的肩膀,“昨晚矿上转正的指标下来了,咱们场子就只有一个名额。我之前报的四元,这不是四元出事了,报上去这指标也就废了,所以我今天一大早就赶紧和上头商量了,想把你顶上去,上头目前也初步同意了。”马场长欣慰地看着明明,“明明啊,我也没想到,你这又沾了四元的光了!”
明明听完,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大岩头矿最后一批临时工转正指标,居然真的落在了自己头上。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这两天居然都发生了。明明双眼呆滞地望着马场长,马场长狠狠拍了一下他:“咋了?不信?我给你个怂娃娃先把难听的话说到前面,你可别再像四元一样,临门一脚给我闹个事儿!四元这个娃娃命苦的呀,昨天上午抓进去的,晚上人家会开完指标就下来了。你说说,这不是鬼挡路嘛!”
“行了,别傻站着了。到旁边财务室去,找小刘要个转正表格填上。就这两天还能再改,人家最后的转正榜一公示,再没有你娃的机会了!抓紧时间!快去!”马场长催促着。
明明转头去了财务室。财务小刘正坐在办公桌前等他呢,看见明明赶紧把表格和笔拿给他。“明明,运气好哦!这个表格我已经都填好了,你在最后申请人那里签个名字。马场长的字都签好了,下午就要交到矿上人事那里。”说完了,小刘又问了一句,“明明,四元他那个事儿,是不是严重得很?不然为撒连转正都给停了?”
明明低着头,没说话。他看着申请表上的字,大部分都认不得。他没见过转正表,也不知道一张决定人生命运的表格居然这么简单,就只有一张纸。
明明没有犹豫,拿起笔,找到了表格最后申请人的地方。
想起四元前些日子说的,签字的时候,他手抖得握不住笔,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咋写了。只好右手握笔,左手握右手,强吊住一口气,才把名字签上去了。
现在明明自己握着笔,手却一点都没有抖,他一笔一画在“申请人”后面写下三个字:马国明。
眼睛猛烈地疼起来。明明以前签名的时候,前面的三个字都是“嫌疑人”。今天换成了“申请人”,他突然觉得眼睛疼,特别疼,一下子疼到心尖尖上去了。
中午,明明到了十字街最东头的福满楼。
他仰头看了看招牌,想起来四元和他说过的,以后转正了要请他到大岩头矿最好的餐厅吃饭喝酒,那个餐厅就是福满楼。明明没等到四元请客,却等到了自己请彭科长吃饭。
明明坐在位子上,没多久,就看见彭科长也走了进来。他站起来挥挥手,彭科长一眼就看见了他,还是那样笑容满面。两人寒暄后入座、点菜,不多时,几菜一汤,外加两瓶酒都上了桌。
彭科长说:“下午还要出去开个会,今天中午我可不能多喝,小喝几杯。”
明明不知道他说的小喝几杯究竟是几杯,但是酒能喝上、话就能说上。明明不懂领导们酒桌上的规矩,只好按自己煤场里兄弟们喝海碗的方式,上来二话没说先敬了敬彭科长,然后连干三杯。
血红色涨潮一般涌上明明的脸。
彭科长乐了:“到底是个愣头青娃娃。你先吃上几口了再喝,这么喝伤胃。”说完,伸出干净修长的手指,剥了几粒花生米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明明把自己两只黑煤手悄悄收到了桌子下面。今天为了请人吃饭,他把脸仔仔细细洗了,但那双手却是洗不净了,黑黢黢的,干枯粗糙。煤灰像一层薄膜,裹进了皮肤,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明明,你到底撒事,赶紧说。”几杯下肚,彭科长的话也多了起来。
明明咽了咽唾沫,往前探探身,盯住彭科长的脸,声音放得很低:“科长,昨天那个樱花舞厅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樱花舞厅?杀了人那个?”彭科长也不由得探过身子,压低嗓音。
“没有,没杀人,就是捅了几刀。”
“你不会是让我帮这个事儿吧?”
“捅人的是我哥,叫四元,以前给你拉煤的时候他也去过一次。”
“那我不记得了……这个事儿我可帮不成。人命的事情,就是矿长也帮不成!”
“四元的女朋友让人欺负了,他才动的手。”
“女朋友让人欺负了,就能杀人?”
“他没杀人。”
“和杀人差不多!”
“他也是为了女朋友,一时糊涂。”
“女朋友?那也叫女朋友!舞厅里的,能叫女朋友?”
“那不是女朋友,还能是撒?”
“还能是撒?”彭科长往椅背上一靠,手里的烟递上去,嘴里就开始冒烟,修长干净的手指被窗户映过来的阳光照得发亮、透明。
“——鸡。”
明明的脑子里又开起了火车。铁轨和车轮互相重击之下,泛出青白的光,明明现在不但耳朵响,眼睛也被这光刺得睁不开了。
“鸡?”明明半张着嘴,鲜少洗干净的脸上透着迷茫的神色,“科长,我姐不是鸡。她在里面只是卖酒的。”
“卖酒?明明,你傻还是我傻?不卖肉咋卖酒?”彭科长用漂亮的手指放下烟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酒就这么好卖?你还叫她姐?你哪儿来的姐?”
“四元是我哥,她就是我姐。”
“你姐?你有个屁的姐!你连爹妈都没有,你哪儿来的哥和姐?”
明明挤了挤眼睛,眼前的青光伴着火车的轰鸣,越来越近。
“彭科长,四元他们就是我的哥和姐。我姐昨天说了,只要能帮四元,她可以给钱。”
“她给钱?她能给多少钱?明明,你知道杀人是撒罪不?”
“四元没杀人。”
“你又和我绕回来是不是?一个挖煤的临时工,一个鸡!你跟我说说,他们有多少钱,打算办多大的事?口气还大得很!”
“一万八。”
“多少?”彭科长的笑容一下子加深了,他打了一个酒嗝,脸上也泛起红潮,“一万八?哈哈哈哈,明明,你说撒着呢?给死人烧钱也嫌少了!”
“那你说多少。”
“我说?我说就是——算了!该干撒干撒去。”彭科长又拿起烟抽了一口,透亮的手指好看极了,“明明,今天这个事就当你没说,就当我没听见。”
“彭哥……”明明刚张嘴,彭科长就摆摆手,说:“哎,别!你叫我彭科长,叫我小彭、老彭,都行。不要叫我哥。”
“彭科长,我姐说……”
“你姐说撒我不管,这个事儿我办不了,你听见了吗,听懂没有。”
“听懂了。”
“明明,你那个姐我也见过。你兄弟四元,是个冤大头。找撒不好找个鸡?”
“我姐不是鸡。”
“嘿哟,明明!你个娃娃嘴还硬得很,你给谁发狠呢?”彭科长不高兴了,“别说你姐了,你知不知道就你亲妈,那个不要你的妈!也是个……哎,不然能死得那么难看么,都说不出口……唉,算了,不说了。”
明明的眼前一道刺眼的强光闪过,脑子里像开矿炸山一样,天崩地裂。
他的记忆里的确有个瘦瘦的身影,那时候在幼儿园,赵大爷总是和那个人背着身子说话,说完了那个人给赵大爷塞点什么东西就走了。他隐隐约约听到过那个人的声音,虽然很轻很小声,但是很好听,像春天小河里刚化开的水,还带着点亮晶晶的冰凌子,清清冷冷的。
彭科长一句话却把这水给炸毁了,山洪一样滚下来,把明明给淹了。
“彭科长你说撒呢。我妈咋了,你再敢说一句。”明明眼睛红了。
“哎——你个娃娃你给谁瞪眼睛呢,啊?老子今天就不该来!看你个怂样子,我还不是给马场长个面子,你当你是谁,你请我吃饭我就来?撒泡尿看看,你算是个撒东西!”
彭科长酒精上头,手指像马场长一样伸出去,指着明明的鼻子:“下煤的烂怂临时工,还给我上话要办事呢,一家子鸡,一窝子臭鸡蛋……”
明明的脑子里,此时洪水滔天,他在其中翻腾,已近奄奄一息了。火车从远远的天上俯冲下来,砸得他整个头都要炸了。他看着眼前那根漂亮的手指,比马场长得好看不知道多少倍的手指,他猛地伸出手去……
中午,人群熙攘的十字街。最东头的餐馆里突然鬼哭狼嚎。
“打人了,杀人啦……”穿得花花绿绿的服务员们惊声尖叫着,食客们也都慌不择路往外面冲。
不久,刺耳的警笛声响起,几辆警车从十字街西头开到了东头。
120 救护车也来了,整个十字街乱成一锅粥。
福满楼里。
明明晕晕乎乎地站着。
地上躺着的,是断了一根手指的彭科长。
他头上也挨了两酒瓶,脑袋后面洇出一摊血水。
明明抬起头,看见有警察跨进大门。
那个警察一看见明明,就呆住了,继而大声叫着:“马国明!你祖宗的!你不想活了吗!“
有人来拉明明的胳膊,明明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是谁,嘴里嘟囔着:“我哥没杀人,我姐不是鸡,我妈也不是。你妈才是……”
赵振东疯了一样地摇晃着明明:“明明!明明!你这是咋了呀!你咋了!我和胡所、和大队上的人说了多少好话,以后都不用你完指标了,咱们好好做个人……明明!你咋回事嘛,明明呀!”
明明抬了抬眼睛——此时窗户外面街道上挂满了红旗,比小时候幼儿园里挂的鲜亮多了。国庆节就要到了,满大街都是喜气洋洋采买东西的人们。
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明明看着赵振东,好看的眼睛也笑弯了,露出两排白白的牙,像一个腼腆的读书人。
“我知道呢,哥。这次,我到底还是把指标帮你完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