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诗经》(之二)
2022-05-06张定浩
张定浩
采采卷耳
方玉润《诗经原始》卷首论诗旨引章潢:“《风》首《关雎》,而夫妇之伦正;《小雅》首《鹿鸣》,而君臣之情通;《大雅》首《文王》,而天人之道著;《颂》首《清庙》,而幽明之感孚。”大体上,《国风》的重心在以夫妇为核心的家庭关系中,而其中女性的作用尤为关键,《周南》起始三篇《关雎》《葛覃》《卷耳》,毛诗序分别以“后妃之德”“后妃之本”“后妃之志”释之,对我们而言,与其将这里的“后妃”简单地凿实成类似文王之妃太姒这样的具体女性,然后再或附会或批驳,不如将之视为一种女性典范的借喻,这也正是《诗大序》所谓的“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无论《诗经》中每首诗的具体作者姓甚名谁,是男是女,是贵是贱,他或者她要表达的,几乎都是一种集体性和普遍性的情感。他或她一旦在诗歌中发声,就不仅仅是代表个人在发声,换句话说,就诗歌的抒情主体而言,和诗人的经验主体是可以完全分开的,这种区分的意识,不单是到了现代诗歌才有,古典诗歌中其实一直都存在。
《关雎》的抒情主体是清楚明白的第三人称,《葛覃》显然是女性口吻的第一人称叙事,而《卷耳》的发声者,却一直扑朔迷离。人们都认可这是一首千古怀人名作,但究竟是谁在怀念谁,却难有定论。过去通常有两种流行说法,一种认为是妇人思念征夫,另一种认为是行役者思家,这两种说法彼此相反,却都面临诗中七个“我”的第一人称抒情主体难以统一的困惑,也因之在每一处关键字词的节点都生发出各种各样的诗学解释,如女子可否登山饮酒,男子可否借卷耳起兴,全诗写法是直赋其事还是有悬想托言的成分,等等,若细细梳理,歧路之中又有歧路焉。

近年来另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诗,如李山借助《孔子诗论》里“《卷耳》不知人”一句的阐发,认为所谓“‘《卷耳》不知人,是说《卷耳》的诗篇是两个人在歌唱,他们同在一个舞台或曰典礼场合上相互思念却不相交接。这样的唱法,在今天戏剧舞台上也有,叫作‘背躬戏”。此种对唱的解释,可以很好地平息之前有关抒情主体前后混乱的困扰,但在具体诗句的男女归属问题上,似尚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李山认为《卷耳》第一章为女子所唱,后三章为男子所唱,但为了维持二人对唱的工整性,女子需要在男子唱第三、第四章之前分别再重复一遍第一章,“今天看到的《卷耳》文本不重复,可能是在写成文本或传写时有意无意被省略的结果”。这种猜测,似乎不太有文献上的支撑,并且从诗经现有文本来看,复沓的诗章是很多的,但都是在重复中略有变化,再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说,随意为现有经典增字乃至增章,也是尽可能要避免的状况。
既然是对唱,就需要某种对称性,李山的增章解经也由此而来,但其实我们抛开章与章对应的惯性思路,深入这首诗的内部,无须增加任何章句,依旧可以发现两个恰好对称的声部。
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曾分析《诗经》的十种曲式,其中第十种是“在一个曲调的几次重复之前,用一个总的引子;在其后,又用一个总的尾声—例如《国风·豳风》中的《九罭》:
[引子] 九罭之鱼,鳟鲂。我觏之子,衮衣绣裳。
[一] 鸿飞遵渚;公归无所,于女信处。
[二] 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
[尾声] 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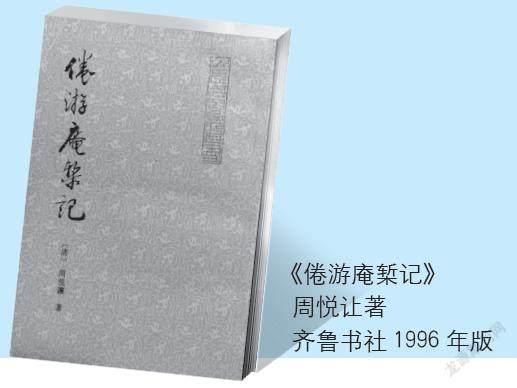
若拿《卷耳》与《九罭》对照,会发现句法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第一章相当于一个引子,随后引出第二、第三章的重复,再最后转入由同一个语尾助词构成的急調。如下:
[引子]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一]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二]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尾声]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由此,对于《卷耳》这首诗,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精致的结构对称性,即第一、第四章之间的遥相呼应,以及第二、第三章内部的紧密对应,如果再附上男女声部,整首诗的结构大体上会是这样:
[引子]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女)
[一]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男) 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女)
[二]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男) 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女)
[尾声]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男)
“采采”一词,历来有两义,一是动词,指“采之又采”;二是形容词,指盛多之貌,如“蒹葭采采”和“采采芣苡”之“采采”。这两种意思,可以说都是古义,后世都有沿用,如陆机《拟涉江采芙蓉》“采采不盈掬,悠悠怀所欢”,南朝陶功曹《采菱曲》“采采讵盈掬,还望空延伫”,用的是第一义;而祢衡《鹦鹉赋》“采采丽容,咬咬好音”,陶渊明《荣木》“采采荣木,结根于兹”,用的就是第二义。就这首诗而言,汉以前的诸家解释皆作第一义讲,未可轻废。卷耳究竟为何种植物,在博物学上也一直是个问题,刘毓庆《诗经二南汇通》引用清人黄中松的考证,据说卷耳有异名二十种,且至少有四种以上以卷耳命名的植物。不过,就这首诗而言,名物的析判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的理解,因为还有句法在帮助我们,“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意思类似于“终朝采绿,不盈一掬”,可以说是古诗中的一种套语,顷筐和一掬,都是极浅之空间,然而竟都始终无法填满,用以形容思念之深,无法专心于所做之事。
“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这两句堪称《卷耳》的核心,种种歧义与深意,都由此而来。“怀人”,毛诗和朱熹《集传》皆做动宾结构理解,即思君子,但今人刘永翔从句法入手,分析《诗经》中以“嗟”起首的四字句,如“嗟爾君子”“嗟尔朋友”“嗟我妇子”“嗟我兄弟”等,发现“嗟”字句代词后二字没有一个不是名词,所以他认为“‘怀人在这里应当看成是一个由偏正结构组成的名词,作‘我的同位语”,这种从语法角度展开的以经解经的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但他接下来将“怀人”解释为“伤心人”,认为“整首诗的‘我字都是指的是一个人,是行役的诗人自己”,这个看法与台湾的李辰冬暗合,略有不同的只是李辰冬将“怀人”解释为“归人”。他们两位的看法,在前人那里也可以找到印证,如南宋袁燮的《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和清人周悦让《倦游庵椠记》。但这种看法,既然长期并未得到广泛接受,我想一定自有其原因。虽然“怀”字在古训里确有“伤心”和“归”的意思,但将“怀人”就此从“怀念某人”扭转为“拥有怀乡之情的人”,似乎还是过于曲折了一点,并且没有足够的同类语证予以支持。其实,古代诗人中还有一个人很喜欢“怀人”二字合用,那就是陶渊明。他在《停云》一诗中就有“愿言怀人,舟车靡从”的句子,古直做笺注时就引《卷耳》“嗟我怀人”为其出典,此外,《答庞参军》“我求良友,实觏怀人”,《悲从弟仲德》“借问为谁悲,怀人在九冥”,尤其在这后两处诗句中,“怀人”显然是作名词来解的,即“所怀念之人”。而“愿言怀人”里的“愿”既已有思念之意,“言”为助词,那里的“怀人”也自然应该是名词。陶渊明距古未远,且深得《诗经》真义,他对于“怀人”的使用,或许是接近《卷耳》本义的。而如果“嗟我怀人”的“怀人”可以解释为“所怀念之人”,那么,就既满足“嗟”字句法上的惯例,在句意上也不致过分曲折。
“寘彼周行”,这句诗如何解释,是与“嗟我怀人”紧密相连的,因为涉及主语是谁的问题。如果我们能确定“嗟我怀人”是指向“我所怀念的人”,那么“寘”这个字作“弃置”解最为自然,而“彼周行”也是一个常见搭配,如《大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即“那周国的道路”。这两句诗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叹息啊我所怀念的人,弃置在那周国的道路上。
“我”所采摘的卷耳在筐里,“我”所怀念的人则在路上;筐子始终填不满,因为自己的无心;道路似乎也总走不完,因为命运的无情。而从“我”到“彼”的快速转折,则将我们的视线拉向舞台的另一侧。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这句诗中的“彼”,显然是顺着上句“寘彼周行”而来,道路上不乏崇山峻岭,我们于是听到那个行路的男子开始唱无望的歌,“登上那险峻的山巅,我的马累得四腿发软”。接下来的“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其人称归属一直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这里的“我”和前句“我马虺隤”的“我”是一个人;另一种认为不是一个人,甚至这后一种意见还要更古老一点。毛诗就认为前二句是设想在外奔波的臣子行状,后二句是国君设酒宴犒劳臣子。林羲光《诗经通解》讲到这第二章时也说,“上二句设为行役者言,其下则作诗者自言,言且饮酒以遣其悲”。
从男女对唱的角度,将这第二章的前二句和后二句分属给两人,似乎也更自然一点,更有舞台的张力。“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是女子回到家中,为排遣愁肠,拿出身为贵族的丈夫的酒器,对彼酒器如对彼人,遂自饮以图解忧。钱锺书《管锥编》解这个“彼”字解得好,“‘彼字仿佛指示‘高冈、‘金罍等之宛然赫然在眼前手边”。《卷耳》中的七个“我”字,六个“彼”字,历来歧义众多,缠夹不清,如从男女对唱的角度,似乎便可廓然一清。要而言之,凡“彼”字皆起到一个指代引导的作用,把我们的注意力由女歌者引向男歌者。如“嗟我怀人,寘彼周行”的悠悠女声引出男声,他直截了当地唱出彼处行路的艰难,随后,“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再回到女声,回到女子借酒浇愁思念男子的孤寂之中,“维以不永怀”亦是对前面“嗟我怀人”的照应,宽慰自己说若是醉酒就不必长久思念,恰恰表明清醒时思念的强度。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男)/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女)”这一章继续重复男女的对唱,并强化这种境殊情同之感,“当携筐采绿者徘徊巷陌、回肠荡气之时,正征人策马盘旋、度越关山之顷”(俞平伯语)。玄黄,是马匹更严重的病况;兕觥,是更大的酒器。远方的艰困和此地的伤怀,都在加剧,并构成越来越强的张力。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最后一章突转急调,不仅马病得已无法前进,连赶马车的仆人也病倒了,我们最后听到的,是远方男子无可奈何的忧叹。这末章的“吁”,隐约与首章的“嗟”呼应,但那个家中的女子能听到么,她或许已经醉倒了。
倘若将这首诗还原到典礼上的歌唱,我们所听到的,就不是一种单向的思念,而是两处同时向着对方展开却都无法抵达的牵挂。《孔子诗论》里“《卷耳》不知人”的判断虽戛然而止,但日后古诗十九首中“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南北朝鲍照“两相思,两不知”的诗句,或皆可为《卷耳》的诗意做一个更生动的写照。《关雎》里君子的追求,《葛覃》里少女的希望,到了《卷耳》中,都化作夫妇之间平凡又恒久的相思。根据《仪礼》的记载,这三首诗通常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三连奏乐章出现在宴饮上的,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国诗中的乐与哀就是这样的循环往复,借助这世间的男女,从一时一地,蔓延至广大无垠的时空。
汉之广矣
近世解《诗经》,时常会有一种文化人类学的倾向,即考证某诗源自某种原始礼俗,如认为《关雎》《葛覃》描述的是婚前性隔离教育和庙见之礼,《卷耳》涉及高山祭祀或婚后返马之礼,论者或许都多多少少能找出一些文献的依据,这种解法的好处是踏实,言之凿凿如小说评论中的索隐派,特别适合“求知派”读者,但离诗学和经学都已很远。
有时候,就连这个踏实都可能是一个振振有词的表象。比如流沙河解《汉广》,认为这首诗写的是祭祀河神的民俗活动,即老百姓在这一天送汉水女神出嫁,“言刈其楚”,是砍下柴薪点燃放在水中如放河灯,“言秣其马”的“马”是比喻女神驾驭的波涛。这样解,这首诗的意思倒似乎一下子变得清楚了。然而他的论据,仅仅是钱塘江潮水确可以比作万马奔腾,仅仅是江汉一带确实存在放河灯的民俗。我只能说老先生很有想象力,但他的想象力不是用来帮助一首诗展现它自身的美,而是一下子把它拖拽到地上按住不动。
诗教,是一种性情的教育,而一个诗人写一首诗的过程亦是调伏其心的过程,而在这样的过程中诗人所动用的经验,也绝非某一种特定时刻的所见所闻,而是过往生命中全部的经验,如里尔克《布里格手记》中那段论经验的著名表述:
為了写一行诗,必须观察许多城市,观察各种人和物,必须认识各种动物,必须感受鸟雀如何飞翔,必须知晓小花在晨曦中开放的神采。必须能够回想异土他乡的路途,回想那些不期而遇和早已料到的告别;回想朦胧的童年时光,回想双亲,当时双亲给你带来欢乐而你又不能理解这种欢乐(因为这是对另一个人而言的欢乐),你就只好惹他们生气;回想童年的疾病,这些疾病发作时非常奇怪,有那么多深刻和艰难的变化;回想在安静和压抑的斗室中度过的日子,回想在海和在许许多多的海边度过的清晨,回想在旅途中度过的夜晚和点点繁星比翼高翔而去的夜晚。即使想到这一切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回忆许多爱之夜,这些爱之夜各各不一,必须回忆临盆孕妇的嚎叫,脸色苍白的产妇轻松的酣睡。此外还得和行将就木的人作伴,在窗子洞开的房间里坐在死者身边细听一阵又一阵的嘈杂声。然而,这样回忆还是不够,如果回忆的东西数不胜数,那就还必须能够忘却,必须具备极大的耐心等待这些回忆再度来临。只有当回忆化为我们身上的鲜血、视线和神态,没有名称,和我们自身融为一体,难以区分,只有这时,即在一个不可多得的时刻,诗的第一个词才在回忆中站立起来,从回忆中迸发出来。
而在中国古典传统中,“诗”这个字本身所拥有的志、持、承三训,也可为此做一个注解。“盖人生宇宙之内,处人群之中,于世(外)则承其风会之盛衰,憭于是非好恶之剖判;于己(内)则承其遭际之违顺,感于身世之悲愉;故必有一己之志焉。承内外之遭遇,以述己之志,形于声文之辞,是即诗也。此承与志之义也。而诗之发,要基于性情之真,或是非之正;故善为诗者,足以内持其心,外持其行,恒优游于敦厚,罔失坠于僻邪。此持之义也。其或志不足以持情,发而为流荡之思,乖悖之见,国史亦序其事而垂为世戒,以潜持将来之人心。此持之又一义也。”(王礼卿《四家诗恉会归》)简而言之,承,即承受内外各种经验;志,是由这些经验所形塑的种种感情;持,是对这感情的消化整理乃至审视。“承内外之遭遇,以叙己之志,形于辞而为诗,足以内持其心,外持其行;或垂为鉴戒,而持后世之人心。是即承志持三者之义也。故诗一名而具三义,亦必融三义而诗之为义始贯。”(同上)
因此具体到这首《汉广》,我所见到的,是顾随解得好,“《关雎》《桃夭》是写恋爱的成功,此篇是写失败。‘之子于归,‘于归的是他家,真是全军覆没,失败到底。……看《汉广》多大方,温柔敦厚,能欣赏,否则便不能写这一唱三叹的句子。不颓丧又不嫉妒,写的是永久的人性”(《说诗经》)。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首诗里的“思”字,皆作语气助词解。“休”的本义,按照裘锡圭的意见,是人在树荫下休息,而这句诗用的正是本义。过去有些注家认为前两句的意思,是说乔木枝干上竦,所以就没有树荫,故不可以据之休息。这实在有点迂腐,因为乔木不是电线杆,它的枝干再怎么高耸,也能多多少少提供一点树荫。《汉书·孝成班婕妤传》引用班婕妤的《自悼赋》,有“依松柏之余休”的句子,颜师古注:“休,荫也。”而松柏都是乔木,可见在诗人那里,乔木可以提供树荫休息,这实在是一个常识。“南有乔木,不可休思”的“不可”二字,其源头并非在“乔”,而在“南”,乔木虽好,却远在南方,可望不可即,这“不可”,是地理距离所造成的不可能。“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水边游玩的女子,正如南方的乔木那样,也是可望而不可求的,而这个距离,是诗人所体认到的人与人之间的遥不可及。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高本汉引《邶风·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认为“泳”既与“游”对举,意思自当有所差别,游是浮在水面上游泳,泳则是行走在水底,涉水而行。《毛传》:“方,泭也。”泭,即竹筏。但竹筏不正是用于水上么,为什么说“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也成了关于这首诗的一个疑点,余冠英因此将“方”解释为周匝、环绕,即江水太长,没办法绕行而到达对岸,这样解释倒是意思通了,但缺少训诂上的有力证据,故也难以通行。其实,如果对照屈原《九章》里的句子,“乘泛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就会知道,竹筏不同于有桨的船只,无法自己掌控方向,也经不起风浪,在平静的溪水中也就罢了,若是在漫长的江水中,坐竹筏顺流而下就随时会撞上礁石或被浪涛掀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长江漂流轰动一时,但先后有多人相继遇难,可见其危险程度。因此这两句诗的大意就是:汉水太宽广,不可能涉水而过;江水太悠长,不可能凭竹筏漂流而下。

这第一章中的四个“不可”,过去的经学通常将之解释为“不可以”,或一种有条件的禁止。它的运思逻辑是这样的:木可休,但乔木不可休,因其没有树荫;以此比兴女可求但游女不可求,因其没有媒妁;进而再将这样设想出来的条件句式折射至自然领域,即江水可渡可行但不可以简单地涉水或漂流,需要借助舟船,以此暗喻女子可以礼聘而不可妄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运思逻辑中,已经添加了诸多诗歌文本中没有的东西,比如媒妁、礼聘,舟船,同时,它还依赖一个如前所述极不可靠的大前提,即“乔木无荫”。
奥登曾经谈论过希腊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的差别,“较之英语诗,希腊诗歌更加原始,亦即它处理的情感和主题比我们的来得更简单和直接,另一方面,语言的表现方式则要比我们的更错综复杂。原始的诗歌用迂回的方式述说简单的事情,现代诗歌则试图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言说复杂的事情”(《希腊人和我们》)。同样,我们在阅读《诗经》时,也要知道这些先秦诗歌所处理的情感原本也是直接和简单的,它日后在解释学中的复杂化源自两种力量,一是汉代经学出于教化的需要主动添加了很多东西到诗里面;二是宋代以后的解释者将自己时代日益精细复杂的情感经验和美学表达有意无意地应用到对早期诗歌的理解中。
综上,《汉广》所吟唱的“不可”之歌,与其被迂曲地解释为有条件的不可以,不如简单直接地理解为无条件的不可能。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诗经》中的“言”字句式,在“言+动(名)”结构中,尤其又和上句或下句中的某个代词或人称上下对举时,基本都作“我”解,并非无意义的语气助词。《汉广》这四句最为典型,类似的句式还有《小雅·采绿》“之子于狩,言张其弓;之子于钓,言纶其绳”。这首诗的第二章,从第一章末尾一片浑茫江水的远景中拉回至此时此刻的抒情主体“我”身上,也是抒情诗惯用的手法。“翘翘错薪,言刈其楚”,字面意思,是说在众多茂盛的可以伐为柴薪的草木中,我砍伐其中最好的荆条。而它的比喻义,要和下两句结合起来体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这两句谈到女子嫁人,但没有明确说嫁给谁,所以就有两种解释,一种说这是希望那个女子嫁给自己,秣马是用喂马来借代驾御迎娶的马车,根据这种解释,“言刈其楚”就是在比喻自己娶妻就要娶最好的女子,如果她愿意嫁人,我就会按照最正式的礼节(以秣马为喻)来迎娶她;另一种,大约是从朱熹开始,认为这是说那个女子将嫁给别人,而自己甘愿为她秣马送亲,“错薪”“刈楚”二句只是一个起兴,“以错薪起兴而欲秣其马,则悦之至;以江汉为比而叹其终不可求,则敬之深”(《诗集传》)。

第一种解释,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奇怪,或者说,是典型的男权社会成型之后的想法:我既然是要娶最好的女子,所以我看上你就是你的荣幸,你要是同意嫁给我,我会亲自驾着马车把你娶进门。这种霸道总裁式的求爱思路,即便到现在,依旧还是很有市场。第二种解释,相对而言就温厚很多。魏源《诗古微》:“三百篇言‘取妻者,皆以‘析薪起興。盖古者嫁娶必以燎炬为烛。”可以烧火的柴薪,在古代既是重要的生活资源,又是嫁娶礼俗必备。以此为基础再细究这两句的隐微之义,“言刈其楚”,当是表示自己有能力养家,并能够做到最好;而“言秣其马”,则表示我也能做诸如饲养送你出嫁之马这样卑微无望的事。“言刈其楚”,是自强自信,是高高山头立;“言秣其马”,是在可望不可即的爱人面前的沉默俯身,是深深海底行,两者都是“我”所能做之事,既相互对比,又共同与第一章的诸多不可能之事形成对照。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四句诗在第二章的结尾再度出现,把我们的视线再次拉至远处的苍茫,却不仅仅只是第一章情景的重复,而更像是一种自我审视之后的确认,将个人的无望以及对这种无望的接受,映射到宇宙自然中,从而获得安慰。《孔子诗论》中关于《汉广》有两则:“《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知恒乎?”孔子论《汉广》单拈出一个“智”字,智慧即知道什么是不可能得到的,不勉强自己也不勉强他人,所谓知恒守常。或许,有人会问,如果不去努力追求,如何就断定说不可能?然而这样的追问,一定是个体意识觉醒之后的现代主体才能问出的问题。《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心也。”既为天地之心,就要感应、体察和遵循天地之间的种种限制,而不是与天斗与地斗。就整个古典社会而言,对人的有限性的接受,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节制,是一切礼法的开端。

《汉广》的第三章,和第二章相比只更动了两个字,在意思层面并没有太多变化,可以视为一种重言,但这种重言式表述不单单只是一种重章叠咏的修辞,它实则要表明,在第二章中所呈现的“不求不可得”,并非一时兴起的丧气之语,而是经过人世经验反复的确认。西谚有云,“只发生一次的事情等于没有发生”,偶然性时刻操弄着我们的人生,而从“刈楚”到“刈蒌”,从“秣马”到“秣驹”,唯有这第二次的反复言之,才能将这样的情感纳入恒久的日常。
傅斯年《诗经讲义稿》论及《汉广》:“此诗初章言不可求,次章卒章言已及会晤,送之而归,江汉茫茫,依旧不可得。”傅氏虽自谦“凭一时猜想”叙《国风》大义,但他将第二、第三章落实,变遥不可及之单恋自省为男女相见后的诀别,倒是似乎更得风人之旨。所谓“悲莫悲兮生别离”,即便是在写有关神的乐歌,令抒情诗人动容的也永远是人世间的离合,但丁尼生不是也在诗里写过吗?“宁可爱过又失去,也不愿从未爱过。”写下《汉广》的那个人,或许也是一个爱过又失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