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客来茶当酒
2022-05-06周朝晖
周朝晖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杜耒《寒夜》
隆冬之夜,寒气凌人,书窗外,一轮孤月挂天心。意兴萧疏之际,有朋来访,欣然起迎,烹茶以待。红泥风炉上,竹炭渐渐转红,火苗雀跃“哔剥”有声;铁釜上水汽氤氲,釜中开始冒气泡,起初细密如蟹眼,顷刻间鱼眼大小的水泡“咕噜咕噜”密集上冒,釜中“呼呼”如松风过耳,沸汤注入茶盏,主客细细啜饮,谈兴盎然。炉火、水汽与茶香,使得寒夜变得生机盎然,天上的一钩冷月似乎顾盼有情,窗外一树梅花暗香浮动……这是南宋诗人杜耒在《寒夜》一诗中所描绘的意境,其中“寒夜客来茶当酒”一句,被奉为茶与诗珠联璧合的杰作而备受称道。
诗中展现的寒夜烹茶接待来客的情趣,温馨而优雅,很容易联想起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不过细细品味,会发现这两首写作时间相隔三百余年的寒夜诗尽管意境相近,但在待客之道的情调与趣味上有很大的不同:白乐天以酒飨客,杜耒以茶当酒。酒是温热的,扩散的,是破愁散,是忘忧汤;茶是淡雅清新的,内敛的,清醒的,意境幽远的。杜耒寒夜里的一盏清茶蕴藉淡雅,令人其乐融融宠辱皆忘。但能尽兴,烹茶足矣,何须煮酒?再读白居易的“能饮一杯无”,不觉有略嫌多余之感。在詩中,“茶”与“酒”,除了饮料性质上的不同,还有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很多宋诗选本都收了杜耒的《寒夜》,耳闻目染之余,我也就轻轻放过了。但一次无意中从《金性尧选宋诗三百首》里读到对这首诗的点评时,顿觉眼前一亮:
此诗曾选入《千家诗》中,大家亦很熟悉,但它却是写美感心理之转变的一首很成功作品。旧本《千家诗》注云:寻常亦是此月,但觉今夜梅花芳香,其倍佳于他日也。单从梅花芳香上去理解,就显得泥了窄了。
金性尧先生的目光太独到了,他从这首茶诗中看到了某种审美心理的时代变迁。这一独出机杼的见解也给予我很大启示:“寒夜客来茶当酒”的意趣,在中国文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所引发的影响,不仅在日常生活,也在文化审美领域上。因而“以茶当酒”的待客方式和旨趣,无论在茶文化史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值得一书。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一部酒的历史,几乎等同一部中华文明史。在古代,酒的原料是粮食、水与酒麹,将蒸熟的粮食与水、酒麹拌匀,发酵后得到的液体就是酒。酒含有酒精,通过刺激大脑中枢,能促进血液循环,使心跳加快情绪贲张,可以助兴,过量则会癫狂,所以诗人艾青很形象地称它具有“水的外形,火的性格”。酒自出现起,就成了各种场合中不可或缺的饮料,上到敬天祭祖、国事大典,下至宴会雅集、居家待客,酒都充当了重要角色。古往今来,酒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诸多溢彩流光的诗篇,当然也不乏种种因狂饮无度而招致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下场的记录。
但是,随着饮茶习俗的出现,特别是茶成为一种新兴饮料就受到了越来越多文人雅士的青睐,并开始与精神文化生活发生联系,饮茶从日常七件事之一渐渐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比起饮酒,饮茶要晚得多。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原乡,茶树与茗饮习俗起源于我国大西南横断山脉的云贵川地区,那里至今存在着大片自远古时代延绵而来的古茶树群落,可以推断饮茶的历史理应与酒一样悠久,只是限文字资料的阙如,相关文字记录很晚才出现。顾炎武说“自秦人取蜀,始有茗饮之事”,战争打破了封闭,西蜀茶事随着秦汉帝国的扩张经营逐渐向九州各地传播。魏晋之后,随着国内交通的拓展,各地往来频繁,茶叶开始流向长江中下游的广大江南地区,饮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食桌和客厅的必备饮品,这不仅改变当时的生活习惯,并且随着饮茶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与文化创造相联系,在丰富了文学表现领域的同时,也引起文化意识领域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轨迹,从饮茶在魏晋与唐宋的文学领域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也大致可以看到某种端倪。

文学史上,对上述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学特色分别有“魏晋风度”与“唐宋风流”之类的说法。从文化上看,魏晋风度与唐宋风流不同。这种不同,虽然有很多原因,但是饮茶风气的普及,并且由于这种新饮料的流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引起社会经济及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言及魏晋风度,不得不提当时在士人中风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服药、清谈、放诞、狂狷、任性、游山、乐水、写诗、弹琴、长啸、享乐、颓废,等等。这些“在乱世中如何精彩地活着”的人物与故事,很大程度上都与酒的激发有关,可以说在魏晋时期,整个社会都浸泡在酒缸里,难怪鲁迅要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题来阐述当时的士人生活与人生态度。
魏晋名士以竹林七贤最为代表性。所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篇的说法是指陈留人阮籍、阮咸,谯国嵇康,河内山涛、向秀,琅琊王戎。七人气味相投,日日聚集于竹林之下,狂歌笑傲,肆意酣畅。竹林七贤,个个是酒徒,《晋书》和《世说新语》中,记载他们酒后行状的文字不但多而且传神,试举几例—
刘伶,自称“天生酒徒”,撰有《酒德颂》。常乘鹿车,携一酒壶,使人插锄头而随之,谓曰“死后埋我”。
阮籍,善诗,建安七子之一,尤嗜酒,《晋书·阮籍传》:“嗜酒能啸,善弹琴。”据说他当官是为了喝酒,“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储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山涛,善饮,《晋书·山涛传》说:“涛饮酒至八斗方醉,武帝欲试之,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
嵇康,《世说新语》:“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倾。”

这个酒鬼名士榜还可以罗列下去,流气所及,可以说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莫不受其浸染。不仅文人名士,高官重臣乃至基层公务员也不乏高阳酒徒,像渤海太守孔融,饮酒无度,公然对抗曹操的“禁酒令”,最终被诛,祸及家人,连族亲故旧也未能幸免。永嘉之乱后,大量北方衣冠士族纷纷南渡,受时代风气的感染,也涌现了很多狂喝滥饮的酒徒,如《晋书·谢鲲传》就记载:“(鲲)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而经常与谢鲲酗酒的毕卓“常饮酒废职”,甚至有过喝醉酒到大户人家偷酒被擒的劣迹。
魏晋名士纵酒,有着深刻的时代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
魏晋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生态极为险恶,文人名士一不小心就会招来不测。为了躲避现实环境,只能韬光养晦,沉醉在酒缸里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选项,正如《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因此魏晋名士酗酒乱酒的行为,不但没有受到世人指责,反而获得欣赏,甚至被视为一种“风度”加以推崇,就是因为在诸多士人嗜酒的背后,隐含着一種在乱世中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
《晋书》中记载了很多身处于大动荡时期因酒避祸的名士。阮籍家有好女初长成,晋文帝为皇子向他提亲,阮籍推不得躲不得,只好躲进酒瓮里,连醉六十日,弄得上门说媒的只好放弃。顾荣出身南方高门望族,晋灭吴一统天下,顾荣与陆机、陆云兄弟被招到洛阳当官,他拼命饮酒,终日昏酣,借酒醉避祸,并且对朋友张翰说“惟酒可以忘忧”。就像在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套中人》中,“套子”是人们在新旧交替的乱世中逃避现实的隐喻一样,“酒”就是魏晋士人的“套子”。
魏晋士人的嗜酒、纵酒,不仅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同时也受到时代意识形态的感染。魏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都面临重大的转型。儒家、经学因其凝固、僵化无法适应魏晋时期的社会变动,人们开始从儒家以外寻找能够适应乱世的思想资源,于是老庄思想开始复苏,包括从道家衍生出来的方术神仙思想。由于呼应了乱世中的人们渴望从现实社会中超越与升华的需要,缓解其内心的绝望感和茫然感,神仙思想受到了人们的推崇。修仙即是“修真”,起源于老庄哲学,庄子《大宗师》有云:“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于是厌倦了现实残酷的政治斗争,从庙堂抽身退出的名流高士纷纷踏上求仙之路,登高山,履危岩,探水源,临清波,盘桓林下,采集灵草,寻找现世之外的乌托邦,即所谓“老庄告退,山水方滋”。这种访仙问道的时代风尚,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游仙诗、招隐诗和志怪文学的流行。它们都是乱世中人们渴望高蹈于尘世之外,挣脱现实羁绊愿望的反映。当愿景在现实中碰壁,文人就开始服药饮酒,以求得麻醉和解脱,因此在神仙思想的推动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养生服食进入全盛期。
神仙思想以及随之而生的服食习俗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通过服食药物达到祛病健体、延年益寿甚至羽化登仙的观念早在战国时期就在方士间流行开来。服食药物根据药性和功效分为草木类药引和金石类药引两种,前者主导调理身体、维护健康;后者才是道教中能达到长生不老的。所谓服药,即服“寒石散”,一名“五石散”,由丹砂、雄黄、云母、石英、钟乳五种矿物,再加入金银等贵重金属研磨成粉混合而成。五石散性至寒,须用热酒送服才能发散,这也是魏晋名士嗜酒的另一个要因。热酒再加上刺激性很强的五石散,服食之后获得迷醉幻化的快感,而且体内往外发热,大冬天也可衣裳单薄,广袖飘然,望之俨然仙风道骨。魏晋名士就是从服药饮酒中获得暂时的麻醉,达到修仙成道的体验。于是,酒与丹药,成了魏晋时期上流士族文人的两大嗜好,尤其是以金石为药引炼出的丹药更是奢侈品。

金石类药饵不仅制作繁复且成本高昂,葛洪《抱朴子·仙药篇》中开出的一份金石类服食药饵清单可见一端:“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这类丹药,就价格来说,长期服用者仅限于帝王、贵族、富豪、巨贾之流,对一般士人而言无异于难以问津的高岭之花。
另外,服食丹药往往伴随着风险。金属矿物质中含有毒素,又借助酒精的刺激作用,服食后会带来强烈的生理反应,呕吐、晕眩、皮肉溃烂,甚至癫疯发狂;而在制作丹药时比例不当,或服食方法出现偏差,也常常致人中毒,危及健康和性命。因此,如有一种饮料,既能满足社交需要,又能醒酒,价格又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那么它一定能在这个时代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时候,随着两晋以后饮茶越来越频繁介入到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茶的认识不断深化,茶成为酒之外的重要饮品,开始对社会文化生活发生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茶文化的形成期。唐人裴汶《茶述》说:“饮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
这一时期,发源于巴蜀之地的饮茶文化随着楚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的互相融合而扩展到整个南方地区。从茶叶产地的空间分布看,魏晋南北朝的产茶地区在分布特征上已经与唐代基本一致,数量规模较之前代有了很大改观。这一时期与饮茶有关的叙事开始在各种文献记载上出现,活跃在首都洛阳的文人,很快接受了南方的生活方式并首先成为茶这种新型饮品的享用者、倡导者和书写者。于是,饮茶习俗在时间与空间的流动之中,与自觉的人文意识和传统文化的相互交融感应,既带动了技术演变,也影响了人们的精神追求。在这个互动过程,比较完整的茶文化体系开始形成。茶文化体系一旦形成,就会对当时的生活习惯乃至整个文化领域产生影响。
《三国志·吴书·韦曜传》中有这么一则记事:吴王孙皓晚年耽于酒色,宴饮无度,还逼着臣下也跟着狂喝滥饮,每有宴饮,凡入席者必须喝足七升酒。喝不下的,孙皓会让侍者强行将酒灌进他们嘴里。不在此列的只有史官韦曜。韦曜文笔好,有史才,酒量却不济,每次二升到顶,孙皓对这位博学的老臣格外开恩,不但不为难他,总是密赐茶汁,让他在宴会上代酒。这一则记事,在茶文化历史上意义不同凡响:首先,这是正史中第一次有关茶事的记载;其次,显示了在三国时期的江南地区,茶已经成为宫廷等上层社会的饮品;最后,茶与酒开始相提并论,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表明茶饮作为一种社交饮料正式登场。
饮茶进入社交宴饮,与当时人们对茶饮功能认识的深化密不可分。三国时期的学者张辑在《广雅》中提出茶具有清神醒酒、振奋精神的功效:“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茶还能纾解愁闷,东晋以“闻鸡起舞”的典故名垂历史的刘琨,也是一个资深的茶人,他自言“体中愦闷,恒假真茶”,指出茶有怡情养性的功效;茶还有助于修行,南朝药学家陶弘景《杂录》说,“茗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云云。茶能助兴,又能解酒,使人清醒,有利于养生成道,这种认识后来渐渐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在某些社交场合中就出现了茶与酒同时成为宴会饮料。《世说新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太傅褚季野南渡,一次东游到金昌亭(今属苏州),偶遇几个吴中豪绅宴集于此,被邀入座。对方不知他来头而怠慢他,一个劲给他倒茶,却不给菜肴或点心。褚并不在意,喝饱了一肚子茶水起身告辞:“我是褚季野,谢啦!”在席者一听是大名鼎鼎的褚太傅子,大惊失色,纷纷逃席。这则故事意在称道褚季野的洒脱风度,却也反映了彼时吴中民间也出现了以茶待客的方式。以茶代酒,表面上是某种饮食生活习惯的变迁,却是某种文化意识形态转变的前奏,虽然这种转变缓慢而迂回,但如从唐宋已经蔚然成风的现象来追本溯源,魏晋时期无疑是这种转型的孕育期。
隋唐之际,茶在社会生活中还远没有普及,初唐文学中罕见涉及茶事的诗文即是旁证。甚至到了开元、天宝之际依旧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李杜诗中占据压倒性数量的饮品是酒,而不是茶。盛唐文学基调还是酒,水一样的外形,火一样的性格。
李杜之后,涉茶的诗文才开始多了起来,这与唐朝中期以后喝茶的风气进入兴盛期有关。杨晔所著《膳夫经手录》虽是食谱之书,但其中近一半的篇幅在谈论茶,尤其是当代的饮茶,有云:“茶,古不闻食之。……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陆羽《茶经》中也写道:中唐时期长安、洛阳与荆楚、西蜀之地,茶店多得鳞次栉比。经营茶叶或提供饮茶服务的茶铺密集出现,表明茶已经高度商业化,这是茶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唐代饮茶习俗开始普及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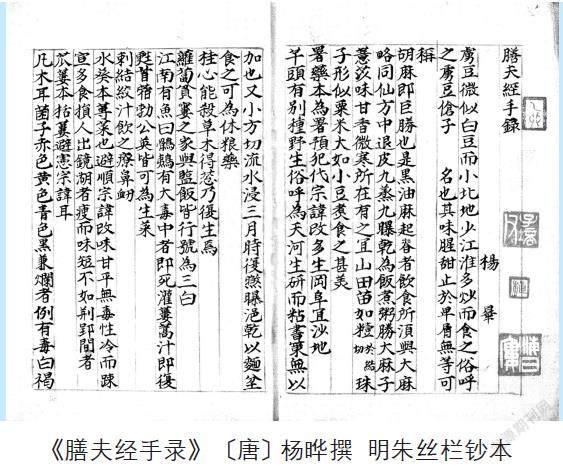
在饮茶习俗普及的基础上,茶会、茶席在上流社会间流行。茶会、茶席,通称“茶宴”,就是以茶代酒的飨宴。唐代茶宴,茶作为一种新型饮品取代酒,或者席间虽置酒,但只作为辅助饮料。这在无酒不欢、无酒不成宴的唐人餐饮来说,虽不是破天荒,却也是一种新兴时尚。以茶代酒的茶宴的出现,不仅与伴随着茶叶生产制作和交易的繁盛所带来的饮茶习俗流行有关,还与中唐时期的社会生活有着微妙的联系。
茶在中唐社会异军突起,飲茶风气空前浓厚,与当时国家的禁酒措施有很大关系。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喝酒人口多了就会影响到粮食的正常供应。历史上,因天灾或战争导致粮食供应紧张的时期,政府就会通过法律厉行禁酒,典型者如东汉末年曹操颁布的“禁酒令”。唐代实行禁酒令乃是为了缓和人口膨胀与粮食供给不足的矛盾。唐代在最初的一个世纪内,人口由三百万户激增至八百万余户,对粮食需求成倍增长。然自安史之乱以来战祸频仍,农民破产逃亡的很多,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乾元元年(758)唐朝首先在首都长安厉行酒禁,规定除朝廷的祭祀宴会外,任何人不得饮酒。唐代宗广德二年(764)确定全国各州的经营酒业的户数,此外不论公私禁止卖酒。与此同时大幅度提高酒价,乾元年间(758-760)酒价一路上扬,在长安任左拾遗的杜甫经常哀叹“街头酒价常苦贵”(《逼仄行·赠毕曜》)。酒价高腾的程度,与同时期的茶叶价格相比差别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杜甫诗云:“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重过何氏五首之三》),即一斗酒三百文,比照当时的茶价每斤五十文,则每斗酒钱可买茶叶六斤。饮酒过多,破财伤身。在酒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势下,人们不得不节制饮酒,尤其是靠俸禄为生的士大夫阶层,很多原本好酒的人转向了茶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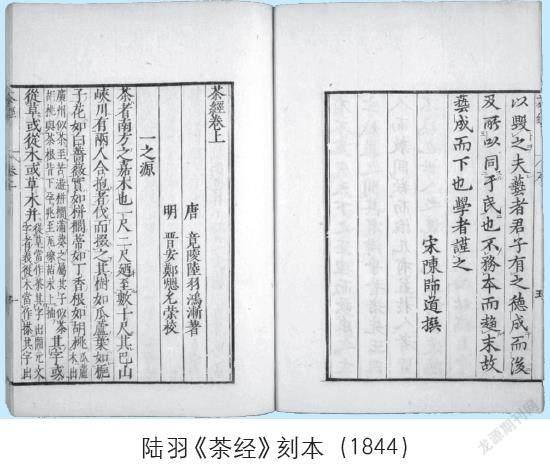
“以茶代酒”在中唐蔚为风气,还与当时的社会文化风尚有关。饮茶最终要与酒相提并论,还在于茶要具备酒类饮品所具有的特殊功能。酒类饮品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刺激性与愉悦性,或者说上瘾性。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茶叶中含有咖啡碱、茶多酚等成分,能加快血液循环,刺激中枢神经,产生轻度的兴奋。茶的这一功效体验被文士诗人写入作品中而得到宣传。文人社交场合中的饮茶,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发挥助兴调气氛的作用,这是茶能成为宴会中酒精饮品的替代品不可忽视的要因。
中晚唐以后,不仅饮茶诗大量密集出现,而且反映“以茶代酒”在文人作品中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前代。这种文学上的巨大转变,在钱起、吕温、白居易、李德裕、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诗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甚至可以说,正是上述诗人创作的一系列茶诗,填平了从“对酒当歌”的魏晋风度到唐宋风流的文学鸿沟。
“茶宴”,一名“茶䜩”,作为一种以饮茶为主题的新的宴饮形式,最早出现在大历年间(766-779)著名诗人钱起的《与赵莒茶宴》一诗中:“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诗中描绘了宴饮的情景,茶宴在竹林幽篁中举办,由赵莒主持,用的是当时顶级的阳羡紫笋贡茶。与喧嚣哄饮的酒宴不同,宾主之间举盏清饮,洗尽尘心,情怀意趣尽在茶中,这种微醺陶然令人有羽化登仙之感。中唐之后,随着陆羽《茶经》倡导清饮之法,“茶道大行”,茶宴进一步在文人间流行开来。“茶不醉人人自醉”,以茶代酒的妙处,唐贞元年间(785-805)的名宦吕温用一篇短短的《三月三日茶宴序》描述得淋漓尽致:
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香枝,闲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吕温(772-811)与白居易同龄,他不但擅文,也善诗,是柳宗元、刘禹锡的好友。这次聚饮的名目“禊饮”,即“修禊事之宴饮”,是农历三月三日上巳节的民俗活动,文人聚饮,席间作诗酬唱,然后编辑成诗集流布,一如东晋王羲之笔下的兰亭雅集。宴会本应饮酒,但与会诸人都建议“茶酌而代”。比起使人迷醉的酒宴,以茶代酒的茶宴,不仅清雅,也助文思,令人陶然而不迷醉。这篇小序表现出来的情趣和心境,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再来读同样活跃于贞元时期的女诗人鲍君徽的《东亭茶宴》:
闲朝向晓出帘栊,茗宴东亭四望通。
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弦管水声中。
幽篁引沼新抽翠,芳槿低檐欲吐红。
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
唐朝的文人承续魏晋名士的斯文遗风,喜欢在茂林修竹的清幽之处举办诗宴雅集,“一咏一觞,畅叙幽情”,但是他们已经不像竹林七贤那样聚啸推樽,肆意酣畅,放浪于形骸之外,而是以茶代酒,清谈雅叙。这种新兴的宴饮方式,清雅内敛,余韵悠长,在意趣上与醉生梦死、纵酒狂歌的做派迥然有别。
诗僧皎然和尚的《饮茶歌》云: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可以看出,唐朝诗人文士,已经从饮茶中探索到一个飘然欲仙的新境界,这种精神感受,与魏晋名士依赖酗酒吞药来获得癫狂体验以超脱世间无奈的追求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
这一风气,到了宋代,随着茶文化的兴盛而被发扬光大,两宋文坛巨匠,如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一直到杜耒,诗家之外几乎都有一个“茶人”的头衔,他们在文学书写中将饮茶提升到一个诗情禅意的境界。有如大江大河在经过激流险滩“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之后拐了几个弯,进入了“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境地,這在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二○二二年二月二十日寒雨中
修订于海沧嵩屿渔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