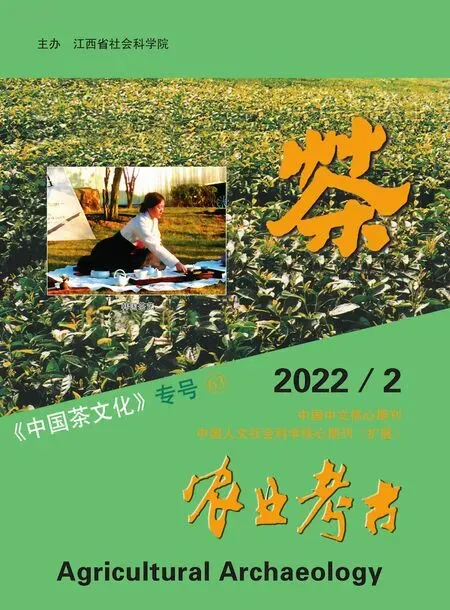北宋茶诗与文人茶会
2022-05-05杨艳如冯文开
杨艳如 冯文开
茶会起源久远,较早可追溯到西晋时期,《晋书》载:“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饮,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他们的茶会并非正式的文人茶会,他们用茗茶招待宾客的目的是示俭,并非一种高雅的文人品茗聚会,表明文人茶会在当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正式的文人茶会兴起于唐代,“茶会”一词的出现也正始于这一时期。刘长卿《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等以“茶会”为诗题,描述了文人齐聚一堂、品茗赋诗的雅事。一些唐诗以“茶宴”为题描述文人相聚,品茗唱和,如鲍君徽《东亭茶宴》、李嘉祐《秋晓招隐寺东封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松花坛茶宴联句》等。其实,文人茶会与茶宴都是一种以饮茶为社交媒介的文人聚会,只不过茶宴比一般的茶会规模要稍大一点,侧重对友人与宾客的宴请。再者,一些唐诗虽然在题中没有以“茶会”或“茶宴”直接点明文人聚会品茗,但诗中仍描述了这种雅事。因此,它们也应该是描述文人茶会的茶诗,如王昌龄《洛阳尉刘晏与府掾茶诸公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陆士修等《五言月夜啜茶联句》、僧皎然《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等。
至北宋,文人茶会远盛于唐代。《萍洲可谈》载:“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这种盛景与北宋饮茶风习有着密切关联。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云:“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茶会是北宋文人聚会的一种高雅方式,而其间的品茗赋诗成为他们创作诗歌的一种高雅形式。文人茶会虽然仅是北宋茶文化的一个方面,内蕴却较为丰富,北宋茶诗所描述的茶会是一种有情、有境、有性灵的文人佳事,处处显示文人茶会中品茗者的情趣、气度与风神。本文以北宋茶诗为考察对象,切实具体地探讨北宋茶诗所反映的文人茶会及其特质与文化内涵,阐述茶诗与文人茶会的互动关系,以求对北宋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有着另一个层面的理解。
一、品茗择人的旨趣
北宋文人茶会的形式丰富,但是参与的人数没有严格的规定,它既可以是两位文人的对啜,也可以是三位及以上文人的聚饮。两人的茶会是两位志同道合的文人在一起品茗,享受其间茶境情趣的一种品茗方式。一个人独自品茗比较随性,自由自在,不受旁人的羁绊与约束。两人对啜也是一件快意之事,独自品茗有时会因为没有知音与己共品佳茗而变得索然无味。吴则礼《法云期曾存之不至》:“解鞍就尘榻,聊与幽人期。寒花受微雨,清香散前墀。莲舆杳不来,坐恨白日迟。茗瓯无复共,何以慰相思。”诗人与友人相约一起品茗,但是友人却没有如约而来,因此吴则礼赋诗慨叹他无心在“寒花受微雨,清香散前墀”的雅致之境中品茗,而是徒增了他对友人的思念之情。饶节《待不愚入山未至》有云:“酌泉煮茗汤欲竭,弥天道人犹未来。”因为没有知音对啜,饶节品茗的兴致消失殆尽,甚至觉得品茗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一些文人在诗歌中直接表达了自己渴望与知音共享好茶的心情,如李之仪《访僧不值》的“我来独爱南天竺,公去谁烹北苑茶”。李之仪喜欢与知音对啜品茶,深谙对啜的妙处。
两人茶会的妙处虽不如独啜那样随意自适,易于澄心静虑和享受幽静安谧,但也别有情趣。文人与其志趣相投的人共同品饮上佳的茗茶,可以消解独啜带来的孤寂,可以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邓肃《次韵二首》:“蓬筚已无原宪室,江山要饱子长游。西庵轩槛多风月,幸子时来共茗瓯。”诗人觉得一个人月下品茗,气氛显得清冷孤寂,幸而友人来访,与友人品茗赏月让诗人身心俱悦。吴则礼《过欧阳元老草堂》:“草堂足幽趣,茗饮共留连。新诗出锦囊,火齐堆我前。”吴则礼与友人在幽雅的草堂品茗,惬意自不待言,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情趣下应景应情作出新诗以飨友人。对啜还可以品茗论道,达到其意不在茶的境界。郭祥正《休师携茶相过二首》之二:“晚风吹坐忽生凉,旋碾新茶与客尝。我本无心无所证,沉烟何事结圆光。”诗人与高僧相坐于石头之上,品茗参禅。张耒的《宿柳子观音寺》:“野僧治饭挑蔬至,童子携茶对客煎。夜久月高风铎响,木鱼呼觉五更眠。”寺院的薰香袅袅,自有一股让人神清心怡之感,张耒与客人在此煎茶对啜,更多是对佛禅的体悟与人生世事的洞察。
三人以上的饮茶聚会是一群文人聚在一起共品茗茶,清言畅谈。梅尧臣《金山芷芝二僧携茗见访》:“一游江山上,日日吟不足。双锡忽来过,衣霜带初旭。况能持茗具,向此烹新绿”“还将尘虑涤,自愧冠缨束。何以报勤勤,驰奴扣云谷。”与禅僧品茗,不仅在于欣赏怡人的自然风景,品赏茶中的个味,也在于参禅论道。这种清谈的妙趣便在于涤尽梅尧臣心中的尘虑,使他萌生挂冠隐逸之心。当然,如果梅尧臣没有礼佛之心和明心见性的悟性,那么无论高僧讲得如何天花乱坠也是枉然。洪刍的友人也曾携带名茶与他一起品饮,共享乘风飞仙与超凡脱俗的茶境,洪刍《次韵和张掾新泉三绝句》对此描述道:“水之美者三危露,邂逅清甘一勺同。两客携茶煮汤鼎,归来应御玉川风。”洪刍借用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玉川风”的典故道出了他与两位友人一起品茗的特殊感受,写出了饮茶后身体轻灵以及产生的那种欲乘着清风归来的幻境。
文人通常还会怀揣上佳的茗茶,邀请其二三友人一起品茗,如刘挚的《同孙推官迪李郎中钧督役河上叙怀三首》之二:“平湖胜势抱南城,花气濛濛馥近坰。黄变柳条归老绿,红残桃叶换尖青。春乘病后成多感,事向闲中见未形。日日携茶唤宾友,吴泉烹尽惠山瓶。”刘挚不仅是一位非常喜好品茗的文人,也是一位十分好客的品茗者。在与两位友人的品茗过程中,刘挚选择的品茗地点视野相当开阔,湖光山色,水绕南城,花香四处飘逸,柳条与桃叶焕发出春机。这种自然美景让刘挚携带茗茶,唤上友人一起品茗。在与友人品茗的过程中,他们叙说内心的感怀,品味闲适与领略美景。有时,文人会拿出珍贵的茗茶,与数十位文人聚饮品茗。黄庭坚《博士王扬休碾密云龙同事十三人饮之戏作》:“矞云苍璧小盘龙,贡包新样出元丰。王郎坦腹饭床东,太官分物来妇翁。棘围深锁武成宫,谈天进士雕虚空。鸣鸠欲雨唤雌雄,南岭北岭宫徵同。午窗欲眠视蒙蒙,喜君开包碾春风,注汤官焙香出笼。非君灌顶甘露碗,几为谈天干舌本。”这首诗歌描写了黄庭坚与友人们一起品饮密云龙茶的茶会场景,体现了文人闲适自得的生活乐趣。黄庭坚既有一种以品尝到珍稀且象征着地位尊贵的密云龙贡茶为荣耀的满足感,又婉转地批评文人空谈虚无与志趣庸俗。
文人茶会的关键在于参与品茗的文人引为同调,熟习品茗,善赏鉴品饮,这样他们才能深得茶中个味。因此,北宋文人茶会大多强调对参与共同品茗的友人的拣选。司马光《题赵舍人庵》的“清茶淡话难逢友,浊歌狂歌易得朋”指出了饮茶的知音难觅,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的“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嘉”指出了品茗择人的重要性。一些文人拒绝与那些非自己知音的人品茗,如阮阅的《开利寺》:“修篁乔木水西涯,古屋颓垣达磨家。持钵但闻僧乞供,杜门不为客烹茶。”
二、诗思启发
品茗能够引发品茗者的诗兴,催生他们的诗情。释智圆《谢仁上人惠茶》:“寄我山茶号雨前,斋余闲试仆夫泉。睡魔遣得虽相感,翻引诗魔来眼前。”释智圆指出了品茗能清神解睡,让品茗者产生创作诗歌的冲动。黄庭坚《次韵杨君全送酒》中的“秋入园林花老眼,茗搜文字响枯肠”,写诗人借助饮茶来增益诗思,帮助他精心构思和推敲将要创作出来的诗歌。品茗能够激发文人的创作灵感,文人在茶会上诗思涌动,创作出一些与茶道、茶境有关的佳作。元祐五年(1090)禅僧参寥在钱塘构筑精舍,命名智果院,旧址的石间流渗着一股泉水,参寥凿开石头,细加整理,挖掘出涓涓而流的清泉。是年,他邀请了苏轼等十六人参与自己举办的会饮,取用智果院的清泉煎煮刚刚采撷来的新茶。在茶香的触发下,这些文人们纷纷赋诗,苏轼《参寥上人初得智果院会者16人分韵赋诗轼得心字》便在此时所作,其中“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一句对茶的描述,是苏轼对佛禅的参透,即与笋、松等其他万事万物一样,茶也是佛性的显现,要以空灵澄澈的内心和抛弃世俗利害的眼光观照万事万物,才能直接楔入茶禅境界。这是苏轼在这个品茗参禅的茶会上得到的一种禅悟。
文人茶会唱和用韵的现象在北宋的其他茶会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嘉祐三年(1058),时任建安太守的蔡襄自福建将上供给宫廷的建安龙团分寄给了欧阳修,欧阳修择选上好的天气与梅尧臣等一些茶友一起饮用这种名品新茶。在这次茶会中,欧阳修与梅尧臣往复酬唱,欧阳修创作了《尝新茶呈圣俞》,梅尧臣依次用原韵、原字按原次序相和创作了《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欧阳修以《次韵再作》再和,梅尧臣又以《次韵和再拜》再和。这些唱和诗涉及龙团茶的生长、采摘、制作、烹饮、功效等各个方面。元祐二年(1087),黄庭坚在秘书省兼史局任职,其间与王扬休、黄裳等13人举办了一个茶会,黄裳《次鲁直烹密云龙之韵》中的“相对幽亭致清话,十三同事皆诗翁”, 描述了这次 茶会上以诗 互相唱和的情形。元祐七年(1094),身在扬州的苏轼携带着毛渐(1036—1094)赠送给他的茗茶,在端午节那天邀请了一些好友在石塔寺集会品茗,写下了《到官病倦,未尝会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戏作一诗为谢》,其中“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金钗候汤眼,鱼蟹亦应诀。遂令色香味,一日备三绝”,指出了茶会的主持人对参与的茶友具有选择性,他们都志趣高洁,素心同调。而且,从这首诗也可以看出苏轼对品茗的环境、茶器以及水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将饮茶视为一门休闲的艺术,用审美的眼光品鉴着茶的色香味。参与这次茶会的晁补之对苏轼这首诗有回应,即《次韵苏翰林五日扬州石塔寺烹茶》:“唐来木兰寺,遗迹今未灭。僧钟嘲饭后,语出饥客舌。今公食方丈,玉茗摅噫噎。当年卧江湖,不泣逐臣玦。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节。轻尘散罗曲,乱乳发瓯雪。佳辰杂兰艾,共吊楚累洁。老谦三昧手,心得非口诀。谁知此间妙,我欲希超绝。持夸淮北士,汤饼供朝啜。”晁补之在品茗过程中对苏轼的官宦沉浮与名刹的百年沧桑感慨万千,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但是,在真正融入茶的世界里,他涤清了胸怀,暂时抛却了胸中的垒块,享受品茗带来的轻松与闲适,领悟了更深奥的人生道理。
文人除了在茶会上创作诗歌之外,他们也参禅论道,这与茶使人神清气爽与思路畅通的特性密切相关。在儒、禅汇合与交融的局面下,北宋文人参禅已经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林逋、魏野、欧阳修、梅尧臣、郭祥正、苏轼、苏辙、黄庭坚等许多北宋文人都与禅僧有着交往,常以茶结交僧侣,与禅僧一起品茗参禅。司马光《效赵学士体成口号十章献开府太师》的“招得老僧红外至,啜茶挥麈话松轩”,描写诗人准备好了茗茶,邀请高僧前来品茗,希望与他在清幽的松轩里参禅论道。王安石《同熊伯通自定林过悟真二首》的“与客东来欲试茶,倦投松石坐欹斜。暗香一阵连风起,知有蔷薇涧底花”,描绘了诗人与友人斜坐在山间的石头上,闻着从山涧里飘逸而来的花香,观赏耸立的青松,聆听风吹松树发出的声音。在这样幽远的环境下,他们品茗参禅,清谈人生,且陶醉于其中。
茶与诗同味,文人在茶会上往往乘着茶兴吟咏诗歌,诗歌唱和由此便成为文人茶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反之,茶会也因为诗歌而倍增文雅,因为诗歌而提升它的品格。也就是说,文人茶会与茶诗相得益彰,品茗诱发文人的诗兴,令他们诗思清畅,吟咏情性,创作佳作。同时,诗歌又为茶会增添雅趣,更显示出文人茶会风雅的品格。
三、人文茶境
北宋时期茶会已经成为文人休闲生活的一个部分。文人在茶会上不仅以斗茶来追求一种闲适高雅的精神享受,而且将品茗与琴棋书画关联起来,进而构成一种风格独特、富有艺术美感的人文茶境。这些在北宋茶诗里有所反映。
文人经常在茶会上进行斗茶的活动,这是北宋文人注重品茗技艺的体现。所谓斗茶,即比茶、赛茶,又称“茗战”,是一种鉴别茶汤品质高下的活动。因斗茶要按质论价,所以文人斗茶之时确实要以战斗的姿态争斗一番。王庭珪曾以诗歌《刘端行自建溪归数来斗茶大小数十战予惧其坚壁不出为作斗茶诗一首且挑之使战也》向茶友刘端行下战书,逼友人与他斗茶。文人斗茶通常为三五好友在茶会活动中鉴别茶汤品质。唐庚《斗茶记》载:“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宋稗类钞》载:“苏才翁与蔡君谟斗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苏劣,用竹沥水煎,方能取胜。”文人在斗茶中既可以增进相互之间的情感交流,也能在切磋茶艺中提高他们对茶的认识,从而有益于他们对茶文化的深刻理解。宋代涌现出大量的斗茶诗,如晁冲之《陆元钧寄日注茶》的“争新斗试夸击拂,风俗移人可深痛”、祖无择《斋中即书南事》的“京信因求药,宾欢为斗茶”等,可见当时的文人对斗茶的兴趣之浓。斗茶将茶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境界和生活境界,赋予其“雅”的品格。
斗茶的关键在于斗汤色与水痕。茶汤色泽贵白,青白胜黄白;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的“造成小饼若带 锛挎,斗浮斗色倾夷华”,便描绘了斗茶中的这一关节。其次,斗茶的胜负还要取决于汤花咬盏持续时间的长短,正如梅尧臣在《次韵和再拜》中所说的“烹新斗硬要咬盏,不同饮酒争画蛇”。宋代主要饮用团饼茶,饮用前先要将茶团茶饼碾碎成粉末。如果研碾细腻,点汤、击拂都恰到好处,汤花就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如果汤花泛起后很快消散,不能咬盏,盏画便露出水痕。所以水痕出现的早晚成为茶汤优劣的依据,水痕早出者为负,晚出者为胜。
描述斗茶的佳作,当推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它详细地描述了斗茶的情形,其中“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心雪起。斗余味兮轻醍醐,斗余香兮薄兰芷”。描述了斗茶使用的茗茶、取用的水以及点茶时茶的色、香、味,这些都直接关系着斗茶的胜负。《艺苑雌黄》将这首茶诗与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惠茶歌》相提并论,认为二者不可以优劣论。《苕溪渔隐丛话》持不同意见:“《艺苑》以卢范二篇茶歌皆佳作,未可优劣论,今录全篇。余谓玉川之诗,优于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语稳贴,得诗人句法;希文排比故实,巧欲形容,宛成有韵之文,是果无优劣邪?”
弈棋也是文人茶会上的一种闲暇消遣活动,如释德洪《崇仁县与思禹闲游小寺啜茶闻棋》中的“隔墙昼永闻棋响,阴屋凉生见树幽”、李光《三月十一日独寓经阁民先元发商叟见过纵步长廊因至旼师房爱其洁雅携棋瀹茗竟日而归因成鄙句》中的“当轩翠竹根根净,对手拈棋局局新。”饮茶与弈棋都是一种闲适的文化艺术,茶味在“清”,棋道在“思”,“静”与“闲”是茶与棋的共同的旨趣,而且它们都象征着清远高逸,在文化的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下棋非常耗费脑力与精力,而茶可以提高弈棋者的专注力,能够让弈棋者提神醒脑。文人以品茗弈棋的方式修身养性,于其中感悟世事人生。这些描写品茶弈棋的茶诗既展示了文人士大夫们幽静闲逸的情趣,又充分体现了宋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
援琴也是文人茶会中常见的活动,宋代文人将品茗援琴视为一种雅致之举,旨在追求琴茶同韵。梅尧臣《依韵和邵不疑以雨止烹茶观画听琴之会》:“弹琴阅古画,煮茗仍有期。一夕风雨来,且喜农亩滋。”张耒的《游楚州天庆观观高道士琴棋》:“围棋尽扫一堂空,烹茶旋煮新泉熟。弹琴对客客卧听, 悦耳泠泠三四曲。”显然,茶香的飘逸与琴声的悠扬在一起,彰显了茶的高雅与琴的幽逸,而这种生活艺术与音乐艺术的结合使得茶会具有了声情之美,增添幽静深邃,使人忘却尘俗,从而提升茶会活动的文化品位。这正是文人士大夫们喜好品茗援琴的原因。
茶须静品,画须静赏,两种闲适高雅的艺术虽然形式各异,但是给予人们的美感却有相通之处,都追求“静”的境界,其过程都具有流动之美,气韵生动,因此茶会将这两门艺术密切地结合起来也是在情理之中。《宋人轶事汇编》载:“经筵承受张茂则,尝招讲官员啜茶观画,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识画。’竟不往。”这则笔记从侧面反映了文士喜欢将品茗观画结合以资幽远静闲之雅趣。文同是北宋著名的画家,尤善画竹。他《送通判喻郎中》中的“惟于试茶并看画,以此过从不知几”便描述了品茗赏画的妙处。苏轼《龟山辩才师》的“尝茶看画亦不恶,问法求诗了无碍”认为,品茗与观画并不相碍,反而相得。赏画让品茗更具有雅趣,使它更富有艺术的气息,而茶的静也让诗人能够静心赏鉴丹青。“琴棋书画是文士的专利,是他们身份的象征,是他们学识修养的标志,也是他们陶冶身心的工具。文士们在品茗中,或听琴或下棋或书或画,相伴相生,雅味十足,充分体现了文士的儒雅风流”。
文人茶会是北宋文人群体雅化生活的一种活动方式。不论是两人对啜还是三人以上的聚饮,大家都在其间得到欢娱享乐,既悦耳目,又愉悦心意,还获得参禅悟道的理性满足。同时,文人茶会也是一种创作的集会。文人们往往在茶会上切磋诗艺,品茗赋诗,互相唱和。这些诗歌与唐代描述茶会的诗歌不同之处之一在于诗人没有直接以“茶会”“茶宴”“茶集”等命题,而是经常在诗题中便交代聚会的背景、参与聚饮的文人、作诗的方式等,甚至还有相关的自注。文人茶会还是一种竞技聚会,其间除了诗歌的竞技外,还有茶艺的竞技,这必然推动了北宋社会茶艺的提高,使得北宋的茶艺更加精致,更显闲淡雅致与清逸高洁。文人茶会更是一种艺术与审美的集会,它与听琴、弈棋、观画等艺术结合在一起,营造了一种具有深厚人文意蕴的艺境。上述这些与文人茶会的相关内容都可以在北宋茶诗得到总结归纳与印证。可以说,北宋茶诗对考察北宋文化、文人茶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藉此我们可以窥知北宋文人茶会的风貌、文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及其他相关内容。这也证明,将北宋茶诗与文人茶会关联起来进行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宋代文人茶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