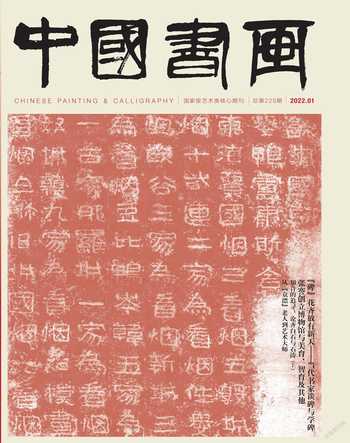从“京漂”老人到艺术大师
2022-05-03万君超
万君超



当今的齐白石研究是一门“显学”,有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难以计数,但真正既有史料价值而又具有思辨性和可读性的却屈指可数。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因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并非“采铜于山”,而是“买旧钱废铜以充铸”。故而此类著作,诚如孙过庭《书谱》中所言:“或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苟兴新说,竟无益于将来。”在资讯日益发达与便捷的时代,十之九皆鸡肋,令人不屑一读。
近读张涛博士的新著《君是人间惆怅客:齐白石京华烟云录》一书,可谓近年来齐白石研究专著中的一部“出蓝”之作。本书共有十四篇文章,从齐白石1919年春(56岁)第三次到北京谋生时起至1957年9月病逝北京,几乎是一部近四十年的艺术大师“京漂”奋斗史。作者长期致力于齐白石研究,对于存世的齐白石日记、书信、诗文、画作等第一手原始资料皆烂熟于心,再辅之以民国报刊文献的检索,从而使得本书的史料来源真正是“采铜于山”,也使得其学术原创性,令人信服的展现。
本书中的《五四来了》和《花甲新人》两个章节,对齐白石当时所处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做了较为深入的学术考察,将齐白石“衰年变法”起因和成功放置于五四运动以及一系列新文化运动的范畴(如民俗学、白话文的兴起等)来进行统观,极具启发意义。当时的北京绘画界处于新文化运动的边缘地带,故少受其影响与波及。但当时北京整体的文化氛围已经发生了极大改变,也就是说,以往精英式文人画开始向中下层市民及都市商业化的绘画下沉,绘画的消费群体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质变与量变。而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与倡导者们,就是要力求将中国绘画去精英化,从而取得平民化、通俗化的社会与文化效应。或许可以理解为:“时代选择了齐白石,也从而成就了齐白石的时代。”如果当年仅凭在京的湖湘籍“名公巨卿”人士的有限资助、提携及推广,齐白石后来未必能够大紫大红而成为“海国都知老画家”。作者在通过对新文化运动史的观察与辨析之后写道:“没有北京整体文化氛围的熏陶,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包括绘画受众的观念嬗变,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新式文化精英的观念转向,那么艺术史上的‘齐白石’很可能会是以另外一种形象存在。”(本书第10页)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其《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说过:“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就难以理解任何的历史现象。”上述两篇文章,充分体现了作者专业的学术视野和通透的史观格局,颇有高屋建瓴之感。
在上述的两篇“宏观”论述之后,作者选取了齐白石居京时期的十二个个案,通过生活、画作、交游、情感、亲情等一系列的“微观”细节,展现了齐白石从初来乍到的“京漂”艰辛,到适应环境与市场的“社会人”,以及大半生的心路历程、人生感悟和尘世恩怨。而那些看似琐屑的“碎片”,却竭尽所能地还原了当年的真实场景,从而引起读者的思考或代入感。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我想用这些所谓的历史‘遗迹’,尽可能拼贴起一个真实的齐白石。更想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一个所谓‘社会人’一生的变与不变、坚持与放弃、个性与圆融。换成我们,会如何自处?会如何选择?会何去何从?”
由于本文的篇幅所限,難以在此对全书的每个章节均予以展开详评,故只能选择其中的部分片段,简略且肤浅地写一些个人的读后之感。在齐白石传奇或“神话”的一生中,曾得到过许多“贵人”的鼎力相助,其中徐悲鸿亦是“贵人”之一,此方面文章已多若夜空星斗。本书中《夸我很难吗》一章,讲述徐悲鸿一手促成的《齐白石画册》(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7月)出版后,徐、白之间由此在友情上发生的“微小波澜”。这是齐白石平生出版的第二本画册,且又是徐悲鸿亲自操办,所以他对此充满了期待,但未想当见到画册后竟然大失所望。此画册共有二十六页,而徐悲鸿手书几百字的《序》却占九页,其中对齐氏画作评价仅三十余字,颇有鸠占鹊巢之嫌。且所刊印的画作并非为人所青睐的花卉草虫,而是饱受“差评”的山水画。作者在文章中梳理了徐、齐两人对此画册各自不同的诉求。徐尽管不无欣赏齐氏的大写意花鸟,但却推崇其“独创一格,深合自然”(徐氏语)的山水,其实也是在宣扬自己的现代绘画理念。而齐则更为关注的是自己作品的市场效应。由此双方产生了分歧。好在两人都是人情圆融,故各自及时调整心态,从而冰释前嫌,亦可谓君子和而不同。齐白石当年对于自己山水画的自我调侃,有一则逸闻不妨转录于此:齐氏同门、杨度之弟杨钧在其《草堂之灵》一书中有云:“凡书画润格之列于高价者,皆惮为之品。余询白石曰‘:君之山水,亦可得高值耶?’白石曰:‘因不能为,故高其值,以进为退,撑门面法也。’”
本书中的《红豆生》和《生意经》两章,均涉及齐白石与四川军阀王瓒绪(曾先后任四川盐运使、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四军军长等职)之间的一段“恩怨”往事。齐白石是通过其四川弟子姚石倩(1917年拜门)引荐与王氏产生“交集”的,王氏由此购藏了许多齐氏画作精品(今有部分收藏于四川博物院、重庆三峡博物馆),可说在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金主”,并曾多次邀请齐氏入蜀一游。齐白石遂于1936年5月中旬到达成都,同年8月下旬离开,前后有四个月时间,不料此行后来竟引起了齐白石的极大不满。据齐氏后来在致姚石倩的信中有言,当初入川前,姚曾传话王氏许诺此行将予以酬金三千元(或是法币)。但当齐氏离川时,仅得四百元,落差之大,故其失望与愤懑之情可想而知,直言“曾许赠之三千元不与,可谓不成君子矣”。此是齐白石研究中的一段著名“公案”,今研究者已多有论述,但均莫衷一是,难有定谳。作者通过对相关日记和信札的梳理与辨析后写道:“身为‘四川王’刘湘曾经的心腹大将加只手遮天的一方诸侯,会亏欠一个许诺给北平老画家区区三千元的旅费?落一个无信无义的‘小人’骂名?齐白石信了。我不信!”作者从信札、日记等原始文献中,寻找或还原那些无法抹去的历史细节与生活场景,让“历史自己说话”,而不人云亦云或拾人牙慧,的确难能可贵。且文字风趣诙谐,并适当运用时下的某些流行语句,令人忍俊不禁。齐白石平生对金钱的吝啬及锱铢必较,其实与他早年贫困的生活经历有关,今人不应过于苛责,应予以了解之同情。
本书中的《铁拐李》《桃花源》《废墟》三个章节,是有关齐白石所画“八仙”之一铁拐李题材和自藏《借山图册》(今存二十二开)的图像意义及创作缘由。在研讨这类画作的过程中,从而理解齐白石早期绘画中所隐喻的“画言志”和“畸人”心态,以及拟建自成体系的“图像自传”的象征意义,可谓独具视野,启人思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根本上就是“为人生的艺术”,艺术家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其实也是通过作品来体现自己人生观的落实和统一。
齐白石是由于两个形同水火的新旧文化阵营一致“合力”而逆袭成功的独特个例,1949年以后,又因鼎新革故而再次将其推上“神坛”。尽管这一传奇个例再也无法复制,却极具学术研究的价值。《君是人间惆怅客:齐白石京华烟云录》一书,也为齐白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部难能可贵的范本。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