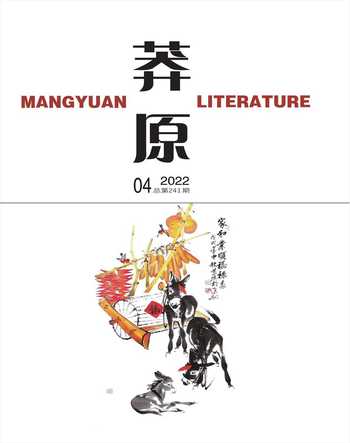风吹落叶
2022-04-29熊西平
熊西平
一
老石磙睡到七点还没起床。他老婆梅花赶紧拍着房门喊,睡过头了,睡过头了!里屋没动静。梅花心里一惊,忙狠劲踢了几脚门,大声喊,老东西,你咋了?里面洪亮地咳一声,喊,我没死!梅花拍拍胸口说,阿弥陀佛,我以为你死了呢,你咋不去上班呢?里面回道,我病了!梅花嘟囔道,病了,昨晚喝多了吧?一个人喝半斤老烧酒,闹的!里面喊,去你个球!老子喝半斤酒还照样抱鼓风机!梅花说,那咋不去抱鼓风机了呢?门哐的一声拽开了,老石磙披件灰色单衫石碑一样立在梅花脸前,对着她的鼻子喊,老子不给他抱鼓风机了!老子钱挣够了!梅花吓得赶紧往后退,嘟囔着,看你能的,酒劲儿没过,还在发酒疯。
梅花盛了一大碗炒油盐鸡蛋干饭,放在厨房门前的圆石桌上,加一碟小菜,并不看老石磙,对着老梨树喊,老爷——吃饭了。老石磙洗脸、刷牙、清嗓子,扣扣子,半天才坐到石桌前,拿起筷子停一板喊,拿两个大蒜瓣子么。梅花取个大蒜头来,掰开了丢在桌子上,递两瓣给老石磙手里。老石磙用牙磕破蒜瓣子皮,一口咬下一半,三扒两咽,一碗米饭到肚了,响亮地打个嗝,满足地眯眼看太阳。梅花抵近老石磙的脸小心地问,咋不去抱鼓风机挣钱呢?嫌钱烧腰包啊?老石磙说,肚子胀气,不得劲儿!梅花问,毛孩子熊你了?老石磙说,他敢!梅花说,他是你儿子?他可是你侄儿。儿子有理打他爷呢。
老石磙碗一推站起来,梅花也赶快直起腰站起来。老石磙六十岁了,仍膀大腰圆,胳膊腿赛木桩子,说话像打雷。梅花怵了他几十年。他站着,梅花就不敢坐着。儿子侄儿都惧他三分,他说什么,大家都跟着说好,不赞同的意见也只能以沉默相对。老石磙把檐下多时不摸的铁锹掂过来用废鞋底擦擦,自言自语说,下地去,不给他狗日的吹树叶了。梅花阻拦他,说地里稻子都割了,就剩一地黄稻茬,你去看个啥鬼?老石磙梗着脖子,头也不回,说看稻茬。锹横在肩膀上,往西冲里走。
出了院门,往西冲望,满眼金黄。稻子半月前就收回家了,金黄的是稻茬。今秋天好,稻茬没淋雨,不变色,不倒茬,真是田黄好个秋啊。种了几十年田,感到庄稼亲,看着稻茬也舒服。他用手抚摸稻茬,很柔韧。成群的麻雀突突突地起落,欢天喜地,这才是庄稼人的伙伴啊,看着比城里飞跑的车让人放心。城里的鸟儿都飞得高,比树梢、楼顶还高,它们不敢在地面上自在飞落。那些稠密的各色车子个个都像野兽,一发威,叫人瘸胳膊掉腿,丢小命,莫说鸟儿了。老石磙的一个同事往路上放锥桶转身慢了,叫一個开车半生不熟的女人给轧断一条腿,现在拄个拐棍儿再也不能去扫落叶了。
说起扫落叶就让老石磙难受。真扫街还好说,把丢在路上的垃圾、树叶扫干净,那也算个活儿。他们老兄弟干不到这活儿,那是环卫工人的事儿。他们是没事找事,把树下花带里的树叶用大鼓风机昂昂昂一路吹到路上去,再扫进车里拉走。他们负责的那段路三十里长,两边两米宽的花带,合在一起六十里。他入秋以后就天天抱着鼓风机从早到晚把树叶从花带里吹到道路上。你想,这不是吃饱撑的吗?树叶落在花带里刚好沤肥,长花长树。树叶吹走了没肥力,春天就挎着化肥往花带里撒,一撒就是十几车。化肥是肥吗?化肥是害人精!
他给侄子说,这不是干活儿,这是胡折腾。他侄子毛孩子是承包商,有点不耐烦,说,叔,钱就是这样赚的,东倒西,西倒东,大蒜换根葱。什么都交给风交给雨,我这宝马车从哪来?你们每月的工钱从哪来?
毛孩子总是有理,这一条路他把持了十多年,他就吃这一条路喝这一条路呢。路边先是栽的法国梧桐,说梧桐长毛刺激人长癌,砍了,侄子栽栾树。过了几年,说栾树花不香,新来的市长说换树,砍了栾树栽桂花树。原来说桂花树不落叶,谁知道,那是假的,它是一批一批替换着落叶,春天落,夏天落,秋天也落。老石磙抱的鼓风机吹得就是秋天落的桂花叶呢。老石磙说,咱不能找点别的活儿干?我咋觉得这钱赚得昧良心呢。毛孩子不高兴了。毛孩子不搭话就是不高兴了。老石磙连抽了毛孩子递过来的两支黄金叶,抱起鼓风机昂昂昂一路向西吹过去。毛孩子说,叔,有劲儿就吹风,别闲操心。说罢,钻进黑色宝马越野车跑了。老石磙就憋了一口气在心里,像一个猪尿脬吹足了气,涨得慌。
老石磙抱着鼓风机一路气呼呼地吹过去。他侄子一走,五六个老伙伴都上来起哄,说老石磙,你想把俺们饭碗子都敲碎啊?我看你侄子比你能。他不给吹落叶的机会,今天钱往哪赚?老石磙不理茬,抱着鼓风机一路向前吹,落叶翻飞,把人行道弄得乌烟瘴气。骑车人就骂,吃饱撑的,好好的落叶碍啥事儿,吹出来干啥?老石磙气往上顶,猪尿脬还在涨。虽然离十里井住家只有十里路,但毕竟这在城里。城里是海,他不敢乱趟。他关了鼓风机,回望吹过的地带,三四行洁白的韭菜兰被吹得东倒西歪,还有花瓣被吹落。他心里念一声罪过。他最喜欢的花就是韭菜兰,院子花盆里除了几朵菊花,大都是韭菜兰。韭菜兰,就爱听这名字,比梅花好听。梅花,听着像没花。她爹当年咋给她起这个名字?他把鼓风机宽带子从肩上取下来,鼓风机搁在路沿石上,坐下来抽烟。他肚子咕咕响,胀气。
他在城里随着侄子干活多年了,受人言高语低不是第一回,可今天肚子胀得特别厉害。他看着伙计们扫地装车直到收工没再动。太阳快坠到西城楼的时候,他把鼓风机放进电动三轮车送到侄子公司里去,转身骑车回家。他一路都在问自己,明天还干不干这昧良心的活了?回家喝着小酒也在想,睡在床上也在想,没个结果。他觉得自己简直要失眠了,一咬牙,赌咒说,再去干吹落叶的事儿,我是他侄子,我喊他叔。发过誓,就呼呼睡着了,像吃了过量的安眠药,直到梅花踢门。
二
白鹤灰鹤三五成群地往稻田的各个角落里飞,长腿插在稻茬里,脖子高高地昂起,四下里瞭望。老石磙知道,那里还有水,至少还有泥糊,里面有小鱼小虾活着,有卧在稀泥里的小螺蛳小河蚌。鹤不是来拾稻穗的,它喜欢荤菜,是坚定的荤食主义者。
老石磙坐在横放的铁锹把上,想着泡稻、育秧、插秧、薅稗子、浇水、割稻,一揽子活儿都叫机器和农药代替了,自己都没湿手,稻子就收进屋了,心里很过意不去。自己还是个农民吗?天不亮往城里跑,天不黑不回家,奶奶的,大长一年的日子能剪个角子给庄稼,吃饭心里也不噎着。城里有活干,有个大本事的侄子,能一天弄一百块钱。这稻子要是像人恁绝情,一咬牙,绝收一年,饿死一帮子王八蛋。当然,也把自己饿死了。城里好,城里长金黄的稻子吗?长白花花的大米吗?不亲亲稻子,不亲亲大米,总有一天饿断肠子。还是稻子善良啊。
一群麻雀齐刷刷地落到他脚前,无惊无惧地找稻粒草籽吃。它们可能把老石磙当作稻草人了吧?过去他在田边竖着一排稻草人,虚张声勢吓唬麻雀。麻雀何其聪明,三两天之后,它们吃了稻子就蹲在稻草人头上肩上小憩,还把粪便拉上面。到稻子成熟,稻草人糊了满身的油彩,简直不像个人了。小麻雀不知道,这尊只有眼球和嘴巴动的石头一样,连草帽彩布条子都没有的老头,才是个能抓能打的危险分子呢。老石磙真的想叫麻雀们吃饱了飞到他头上歇歇,并告诉它们,那稻草人都是假的,是他插上打扮的,不要怕;连自己都不要怕。麻雀一代代应该理直气壮,它们吃下的稻粒是它们辛勤捉虫交换来的呢。他还没来得及等它们吃饱,手机响了:“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老年机声音奇大,轰——麻雀都惊散了。
老石磙掏出手机,一看是毛孩子打来的。毛孩子声大如雷,叔,八点多了,咋还没来工地呢?老石磙喊,老叔不得劲儿啦。侄子喊,哪不得劲儿呢?老石磙喊,心里不得劲儿。侄子喊,我去接你到人民医院看看?老石磙喊,不用看,死不了。老石磙把手机挂掉了。毛孩子再打,老石磙就不接了。他起身,把单衫脱了扔田埂上,手机扔单衫上,拎起铁锹,沿着田埂起田墒。过去,他在队里起田墒可是出了名的,快,直,墨线打的一样。他起墒的稻田,能把最后一滴水空出,割稻时候地面干爽爽的。他一口气起了两丈长,眯一只眼看看,仍像线打出来的。一阵自豪袭上心头,自己还是好农民,虽然他知道这很可笑。他拎起衫子往脸上擦一把,铁锹往稻茬上擦擦,明亮亮的,照照胡子拉碴的大脸,他满意地笑了。
四下望望,田野里一个鬼影都没有,没人欣赏他这绝活。人呢?天一亮,路上都是逃难般缕缕行行骑车往城里奔命的人。他们都是种田人,可田被他们扔到身后,向着颗粒不收的城市奔命。他老石磙曾是起早贪黑往城里赶的人,被人笑话为城里人。想起来他觉得脸上发烧,揪一把自己的耳朵,想,死了还进城?死了就埋在这田边高包上吧。看,这儿多好。一年四季陪着庄稼生长,看着庄稼成熟,闻着庄稼香气安睡。田埂上茅草厚厚地铺一层。草没人割了。家家都不养牲口,养牲口的大户都喂饲料。烧锅都用煤气,用电,被称作“黑牛”的锅灶不许用草。过去干活累了,抬头一看到庄子上歪歪斜斜地飘炊烟,就知道快要收工了。老石磙在茅草地上躺了一会儿,又打了个滚儿,才慢慢爬起来,拎起铁锹磨磨蹭蹭往回走。真死在这里,一会儿半会儿还真没人知道。
才到宅子外面,老石磙就看见毛孩子的轿车停在门前。他想躲开,中午坐在稻田里不回来,躺在稻茬上睡个午觉,叫太阳把自己玉米棒子一样晒透,不接手机,叫他找不到自己。但转念一想,这屁大的旮旯地方,除非钻黄鳝洞里,哪里毛孩子找不到呢?
他故意打雷一样咳嗽一下,梅花和毛孩子一起从院子迎出来。毛孩子问,叔,麻雀还偷稻穗?老石磙说,我去数稻茬。自己先进了院子。石桌上摆着卤菜,两瓶剑南春酒,一条黄金叶烟。他当做没看见,对着梅花喊,老板来了,杀个鸡,炖排骨。梅花嘟囔着说,对自己家的亲侄子说话还酸不拉几的!老石磙把锹放在屋角一个木墩上,说省得生锈。这把锹跟他多年,他孩子一样看待。毛孩子说,锹用不上了,生锈就生锈,还当宝贝。老石磙白了他一眼。梅花把酒菜都摆上了,老石磙拿过剑南春拧开,倒了两茶杯,端起来就喝一大口,对侄子说,你那个鼓风机我是不能给你弄了,你那瞎鼓捣的钱我也不赚了。毛孩子端起酒杯跟老石磙示意一下,说,叔,你咋说都行。你不去了,别人咋看我?我爹死得早,你待我像亲儿子。这谁都知道,亲叔都不跟他干了,那我还有脸在圈子里混下去啊?叔可以不抱鼓风机,干啥由你,你不干了,你那几个伙伴怎么办?再说了——老石磙截断话说,就看在大家的面子上,我去。丑话先说前头啊,我可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毛孩子忙说,好,好!叔咋说都好。喝酒,喝酒。
老石磙下午在庄子上转悠,中午喝多了,走路腿打飘。庄子上到处都是老人,一家小卖部门前摆三桌麻将,哗啦呼啦一片响。大家见了他感到很稀奇,像平地里见了一头骆驼,问他咋没去挣钱啊?他推说腿疼,歇歇。有人问,歇歇给工钱吗?他说,给呀,自己亲侄子么!大家都一脸羡慕。回到家里,梅花说,下周大孙子过生,你准备拿多少钱啊?老石磙说,去年两千,今年还是两千,说过了,考上本科大学,拿一万。梅花说,牛吹出去了,就好好挣钱,三个孙子呢。老石磙说,叫他们都好好考,考一个一万!
三
老石磙第二天不早不迟到了地方。五个老伙伴都在等着了,毛孩子坐在车里抽烟也早早在等他。毛孩子对其他五个工人说,我叔昨天不舒服了,今后这抱鼓风机的活儿你几位分担。大家都说,老板放心吧。毛孩子对老石磙说,叔,有啥不舒服给我打电话。老石磙不搭话,点了一支烟,说我负责扫地。
几个老伙伴你一段我一段抱着鼓风机从花带里往路上吹树叶。树叶像受惊的蝴蝶,慌乱无助地向人行道上逃,逃到路上的无序地拥挤着,东一堆,西一堆。路过的人偶尔也会被鼓风机的轰响和纷乱的树叶吓一跳。三十多斤的鼓风机从你怀里到他怀里,不到半天,个个都气喘吁吁,衣衫湿透。中途坐下喝水,你一言我一语,都赞佩半天不说话的老石磙。有说中午吃饭给老石磙多叨两块五花肉,有说中午兑钱买瓶白牛二给老石磙喝。老石磙一直抱把扫帚扫边道,这活太轻,就像当年生产队扬场“打落儿”的,专给老弱病残准备的配活儿。六个老人中,都是亲戚熟人,他身体最好,自己抱个扫帚扫半天,心里不免产生愧意。他牛腿一样的胳膊一摆,说去去去,什么酒啊肉啊,这鼓风机还是我抱。大家互相望望,一起说你身体不得劲儿啊。老石磙一笑,除了捆头牛我捆不住。
休息结束,老石磙先起身抱起鼓风机,宽大的带子往肩膀上一挂,一把拽开鼓风机,昂昂昂——草丛中的树叶受惊着朝路边飞起来。大家都各归其位,谁开车,谁铲树叶,谁扫树叶,各安其位,按部就班,效率一下子提起来,再没谁感到不适了。休息时,都给老石磙递烟,大家抱了半天鼓风机一下子更明白了老石磙的重要性。老石磙也看出来了,心中多少有点暗暗得意。
两天后老关过生。六个老伙伴有个约定,谁过生就拿一瓶酒,大家吃午饭时一起乐呵乐呵,就算庆生了。老关早上从家里带了一瓶白牛二来。按毛孩子安排,往常他们六个人午饭放在一家小快餐店里搭伙,一个荤菜火锅,米饭随便吃。要想多添个菜须自己掏腰包。今天老石磙添了一盘油炸花生米,一个卤豆腐卷,十块钱,为老关生日助兴。有两个不喝酒的,老关要了四个小酒杯,酒过三巡,瓶酒过半。老关提议,平时老石磙多提带几个老兄弟,就此机会每人敬他一杯。几个都呼应说好,老石磙也不推辞,敞开怀一口气喝了三杯,顿觉四肢添力,胸脯饱胀,带着酒劲儿说,这鼓风机呀,我还能抱十年,老弟兄还搁一坨搅和。老兄弟几个顿时振奋起来,又敬老石磙几杯,一瓶酒被他喝了一半。
吃过饭,就地喝几杯茶,都又去上路。老石磙抱起鼓风机觉着比平时重多了,但他不能说,说了人家以为他酒量不行了。他一口气吹了一百多米,觉着乏力就取下鼓风机靠着桂花树坐下睡着了。他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梦里隐隐约约听到有音乐声,正侧耳听,想起来去看热闹,忽然身上飚一股冷水,一激灵,醒了。睁开眼,洒水车早开过去了。他双手摸一把脸,一股怒火蹿上顶心,他以手撑地站起来追过去,没跑几步,脚下一滑摔倒了。他试着爬起来,试了几次,又滑倒了。几个老伙伴赶忙跑过来扶,搀着他慢慢移到人行道边上去。他嘴里骂着洒水车,大喊追上他,追上他!可老伙伴们没一个敢去追的,都在他身上找伤口,给他喂水,眼见着那庞然大物唱着歌逍遥远去。
老关反应快,掏出手机给老板打电话。毛孩子一会就到了,他喝酒了,打车过来的。一下车就火急火燎地喊,送医院检查,送医院检查。老石磙站起来,晃晃胳膊,踢踢腿,跳了两跳,说没事,去医院干啥?省俩钱爷们买酒喝。毛孩子说,医院说没事儿才没事儿,你说的不算。老石磙两眼一瞪,说,就我说的算。毛孩子说,我先送你回家吧?老石磙摆摆手说,我喝杯水,干活。毛孩子对几个老人说,叔没大碍,我那边有事,离不开。你们看着我叔,有啥事儿立马给我打电话。
老石磙光着膀子穿上红马甲去抱鼓风机,大家都阻拦,他不听。平时大家都穿马甲,他不穿,因为他身份特殊,没人强求他。他就把马甲挂在三轮车把手上,他说穿马甲像犯人。毛孩子说,犯人穿的是蓝色的,这是红色的,醒目,保护自己的。说好说歹,他不穿。现在他穿上了。大家都以为他接受教训听话了,都很高兴。老石磙抱着鼓风机昂昂昂向前吹,很慢,很慢,吹了不到两百米停下来。他把鼓风机交给老关提前回家了。红马甲扔在了老关的三轮车上。
梅花正在院子里喂鸡,见老石磙回来,吃了一惊,说鸡还没上宿咋就回来了?老石磙没理她,说吃荆芥面条。梅花问他,红马甲呢?老石磙说扔了,不干了!梅花看他有酒意,不敢多问,就去擀面条,掐荆芥,下熟了,老石磙趴在石桌上连吃两大碗。家里就那一个大碗了,他自己专用,只小孙子偶尔回来感到稀奇哭闹着要用一下。吃过饭,老石磙洗洗就睡了,把房门掩上,关了灯。这让梅花感到稀奇,每晚上老石磙都把新闻联播从中央看到地方,不看完不睡觉,第二天干活好给别人天南海北地卖弄学问呢。
老石磙睡下了,梅花给毛孩子打电话,得知老石磙摔着了,忙进屋倒水,问身上疼不疼。老石磙没理她,喝了两口水又睡下了。她给保温杯里又灌满水才出来,没忘叮嘱一句:别把门插上了,有事喊我。梅花坐门前摇着扇子,直到听见山摇地动的呼噜声才放心。这老头子不打呼噜不算睡,在想心事儿。
第二天,毛孩子来看老石磙,带了烟酒。第三天来了,第四天来了。老石磙告诉他,自己老了,城里活儿干不了了,让他另请高明。毛孩子告诉他,停活两天了,没人能替代他。老石磙说,总有一天你要换人的,我老了。再说,我也看不上这吃饱撑的活儿呀。毛孩子叫叔想想,啥时候想去,言语一声。他给叔留着挣钱的位置。
四
一周后,老石磙又进城了。他像过去一样一大早出门,日落后回家。他骑着电动三轮车,速度很快,像鱼在水中滑。他进城不再去吹落叶,他去收破烂。他在街头上买了人家收破烂的一个电喇叭,充上电可以无休无止地喊:收冰箱、收彩电、收电瓶车、收破烂……他骑着车子在大街小巷滑来滑去,他不张口,有人替他喊,怪有意思。电喇叭不知是谁的声音,怪怪的,有点油腔滑调。他有时候想自己喊,又怕嗓子受不了,也有点害羞张不开嘴。收破烂的,不好听。他把草帽压得很低,不让人家认出自己的脸。实际上也没几个人认得自己。城市恁大,他骑上车子走,也不过像一颗石子扔进池塘。他经常在一个巷子里遇到三四个收废品的,有的车厢装得满满的,更多人车厢没啥货。他的车厢就经常空空的。几天下来,他觉得收废品的比卖废品的人多。都在喊,以不同的嗓音在喊,有的喊得顺溜,有的喊得别扭。头一天,他只顾开着车子跑,午后车子就没电了,急的撅着屁股推着车子找个一元充电才救了急。他跑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挣一百块钱,还没他去吹风一天挣得钱多。他想,挣的钱少是没摸到窍门,总有一天会挣得多的。
那天,他刚进了交通巷,车子被一个人抓住了。他正想发脾气,那人大声喊起来,叔,你咋弄这呢?这一天挣几个钱,比抱鼓风机多吧?老石磙不高兴了,喊道,毛孩子,放手,别耽误我挣钱。毛孩子嬉皮笑脸地说,叔今天不用挣钱了,我请你喝酒。该挣的钱我给。
旁边就有个小酒馆。毛孩子喊人上茶,毛孩子喝一口自己带着的信阳毛尖茶说,叔,我正用人,找不到合适的。你收破烂,赚不到钱,这是我们爷俩的损失啊。为啥不能还像过去一样爷俩双赢呢?老石磙问,你咋知道我赚不到钱呢?我每天挣得比过去多。毛孩子笑了,说我盯你几天了,见你收不到废品,你不是干这活的料。老石磙脸红了,说反正我不去抱鼓风机了。毛孩子说,我那里活儿你想干啥干啥,薪水嫌少我再添。爷俩啥话都好说。
菜上来了,毛孩子从车里拿一瓶剑南春,给老石磙倒一杯,说,叔别喝多了,回家还有段路。我不能喝,下午去火车站接人,剩下的酒叔带回家喝。老石磙没说话,端起酒杯喝一口,抹一抹嘴,说,侄儿,我把酒喝了,我可没答应去你那干活啊。毛孩子说,叔,你想想再说吧。
老石磙没再去收破烂,他骑着车子径直回家。路上,他一再问自己,我真的老了,没用了,连收破烂也不够格了?走到半道,他把车子里的十来斤硬纸板子扔进路边的灌木丛里。
到家后他洗个澡,对梅花说,晚上吃干芝麻叶擀面条。梅花说,也就干芝麻叶下饭了,没钱买荤菜了。老石磙说,不是还有几十只鸡几十只鸭子吗?想吃荤杀一只。塘里还有鱼呢,园里还有菜呢。梅花说,我是说这一个月工资还没发呀?毛孩子还拖欠他叔的工资呀?老石磙不高兴了,说有一年不是年底一次发工资吗?资金周转不开。梅花撇撇嘴说,等年底领工资吧!刚刚毛孩子打电话给我了,说你在收破烂,根本就没去他那干活,瞒来瞒去想干啥呢?想当破烂王发大财?我看一天一百块钱怪保险的,也不怕收破烂丢脸啊!老石磙打断她说,饿了,擀面去。梅花又撇撇嘴,满嘴酒气,中午才吃了酒席就喊饿,肚里长了掏食虫!
老石磙一早起来就到西冲里去,一坐就是半天。毛孩子打电话他也不接,坐饿了才回来。梅花说他魂儿掉那儿去了,老石磙说西冲里草长得真旺,齐裆深。他想买一群羊回来放,算算,到年底比给侄子干活强。毛孩子说,叔,带尾巴财靠不住,发了羊瘟,本钱都丢了,你六十岁了,哪是投资发财的年龄呢?老石磙默然。毛孩子说,叔,我把修剪路边树的活儿包下来了,您带个队,每年秋冬把树枝修剪一下就行,树也不大,不用爬高上低,站在地上,小枝用树剪,大枝用带把儿的电锯,呜——一声,树枝就跳下来了。老石磙一听就笑了。
五
桂花树栽上四五年,三四米高,拉成线长,真好看,像一群年轻人在路边列队欢呼唱歌。老石磙很喜欢这些树,它们直溜,每根枝子都直溜。他紧贴树干锯掉枝子,尽量把茬口留小点,不伤及树干。弄完了,又带着两个伙伴清理树枝。他把树枝全都截成一米长,拉回家,余下的当作垃圾处理。
老石磙每天拉回家的树枝都堆在院子东墙外面,码成两垛。梅花问他,烤火用啊?他不理她。烧锅用啊?他不理她。他不许她动他的树枝,她说金条啊?你问问庄上有人要吗?送,得能送掉啊!有人烤火吗?有人烧锅吗?还当作宝贝蛋呢!
院子外面有三分地,过去是菜园,孩子都在外面,吃不了多少菜,后来硬化四分之三养鸡。等到鸡散养,就闲置了。现在,老石磙在心里给它设计了一个用途,做羊圈,养羊。他算好了,现在西冲里全部种稻子,一年一种一熟,稻子在田里满打满算四个月,其余八个月都空闲着。满埂满坡的草,可以养多少羊啊?稻期的四个月羊关在圈里,秋天收垛稻草,积点荒草,加点料就够了。一只羊羔春天一百块钱,入冬能卖六七百块。满坡的羊跑着,咩咩叫着,西冲就活着,不会显荒了。田野需要动物,动物能叫着,乡村就活着了。水稻很卖力地生长,但它默默生,默默长,不会发声,田里就是沉默的。虫鸟不能让田园的声音更接近人。它们更接近庄稼和草木。有牛哞羊咩地吵着,田野村庄才是活的。老石磙想把他选做墓地的高包上搭个棚子,能避避风雨,搭大点,能帮羊羔孕羊避避风雨。羊遇雨虽然膻味重,但羊多温顺啊,这世上所有的动物加在一起也没有羊那样温顺听话。抱个小羊羔在怀里走走,比那些时髦人抱个猫狗可爱得多。猫狗有传染病,有尖利的牙齿,小羊羔没有啊。想到这儿,老石磙为自己的念头得意地笑了。
入了深冬,道边的树枝修剪完毕,叫毛孩子验收一遍,老石磙就不去上班了。他把树枝沿菜园密密实实扎成栅栏,坐北朝南修了一道简易房,把他心中的羊圈從蓝图变成了现实。他算算面积,松松坦坦关五十只羊。五十只羊,撒在西冲里算不上一片白云,至多也就是松松散散的一些白菊花。
羊鞭子做好了,用布条编成的,打在羊身上不疼。羊不用猛打,很通人性,喝喊一声,它就有条有理地乖乖上路,越窄的路走得越上线。老石磙也打了赚钱的算盘,五十只羊一年下三十只羊羔,第二年就只管卖,不用买了。
老石磙举起羊鞭子炸一声,啪,清脆响。声音没落,就被毛孩子接过去了。毛孩子大声喊,叔,听说羊圈扎好了?明年过年送礼我就不用买人家的羊筒子啦。老石磙有点不好意思,问,听说了?毛孩子说,听说了。买羊羔用钱吧?老石磙说,攒的有。忙拉住侄子往屋里坐,说,叔是老了,可还是想做点事儿顺顺气啊。毛孩子说,好好,叔,中午喝酒,边说边聊。
爷俩喝完一瓶剑南春,老石磙就醉了。老石磙摸着墙回屋里睡下,头还没挨着枕头就雷声滚滚打起了呼噜。他梦见和梅花在西冲里割稻,才割一趟,梅花忽然说肚子疼,要生孩子。他把梅花拽上稻田埂,梅花哎哟一声坐地上,拧着眉喊生了生了,赶快脱裤子接出来。老石磙笨手笨脚解开梅花的大腰裤子,倏溜倏溜,竟跑出三只驼绒色小羊羔。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