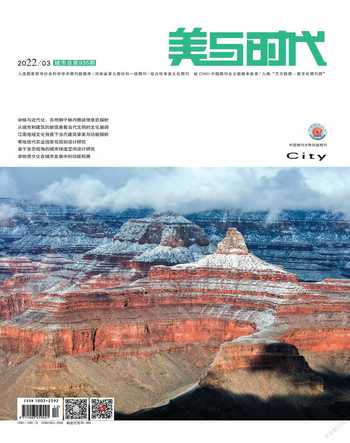本土文化再生的原住地居民主体作用研究
2022-04-25胡梦婷冯艳陈治军
胡梦婷 冯艳 陈治军
摘 要:原住地居民主体作用在本土文化保护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原住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关系还是主体态度等,都影响着本土文化再生。通过分析本土文化核心精神流逝,以及主体与文化本身分离脱节等现状,提出了本土文化再生应以当地居民为主导,保障文化保护意识上本土居民的认同觉醒,同时需要本土居民的参与和实际行动,发挥居民本体作用,参照本土文化再生过程中原住地居民作用,以求推动当代本土文化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本土文化;原住地居民;文化再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新文科、新医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文科下对接城乡突出环境问题的环境设计专业跨界融合改造升级探索与实践”(2020wyxm078)研究成果。
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在过去建立的历史街区、历史环境、历史建筑等,可以反映某个地域的歷史、科学、艺术价值且具备传统和地方特征,而本土化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是其在保护、发展过程中继续维护地域性特色的关键。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提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体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1]。其实,社会共同经验是一种生活中的文化,是依附特定的空间环境、人群以及历史经验的“活态文化”,是本土居民将在本地区的生存习惯和思维模式进行积淀打磨而成的,结合各种外来文化加以重新阐释的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本土性。然而,由于保护措施的不完善、保护理念的偏离,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传承过程中出现了地域特色缺失、不同文化遗产间的同质化、文化传承主体断层等现象。因此,本文从本土文化再生角度,强调原住地居民在促进本土文化再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相关的研究有利于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特色,有利于增强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地域性,对实现建设美丽、特色城镇具有重要意义。
一、本土文化再生中原住地居民主体作用发挥现状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布迪厄提出了文化再生产概念,他认为文化再生产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动态演变进程,文化经过不断的再生产来维持其本身发展的均衡,使得社会得以延续。被再生产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体系,而是在既定时空之内各种文化力量彼此作用的结果,文化以再生产的形式不断演进,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2]。而文化保护的核心就是本土文化的传承、再生,其是一个地区所传承的优质文化基因与文化核心元素,以及二者在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延续发展,即便是在日益变化的全球化大浪潮中,也成为本土文化的遗传基因和当地居民文化身份的核心标识。故而,本土文化地域特色缺失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首先,本土文化核心精神流逝导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同质化,地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本土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在“地球村”以及现代化浪潮中逐步模糊与丧失,进一步迷失在喧嚣缤纷的多样文化潮流之中,找不到自身文化特性,又或者是担心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不敢接受,越来越陷入固守僵化的沼泽中无法脱身。同时,面向发展的历史文化旅游类遗产,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追逐热点,往往存在着某种预设前提。在这种前提之下,对本土文化的保护传承以及内涵阐释等易成为被动的状态,其目的在于吸引游客。而以市场需求为预设形成的旅游产业链,往往伴随一些与当地文化核心精神不相符合的、流于形式的噱头民俗。一些外来的不熟悉当地文化核心内涵与精神的专家和设计者,为了吸引游客,往往会设计出一些徒有其表的“假乡土”景观。游客们最开始看到这些噱头民俗的时候会感到好奇、新鲜,然后在得到了体验感的满足之后,便也失去了对本土文化核心精神的探究、对历史遗产的尊敬。当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噱头民俗成为本土居民的日常,文化遗产传承的主体也就是本土居民,对历史文化遗产中的本土文化精神的阐释往往有误读部分,久而久之本土文化中的核心精神也就无人问津、逐渐流失了,而本土文化的传承行为也往往被弱化了。
其次,主体与文化本身分离脱节,导致出现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结构性问题。当本土文化开始被商品化,被贴上用于制造利益的某种文化标签之后,本土文化就和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脱离开来了。这种文化遗产也就没有了群众基础,更没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后劲,缺少了发展的源头——居民日常生活和行为实践。这样的“本土文化”就变成了真正的本土文化的一个附庸商品,成为“游离于本土居民的一件展品或观赏品”[3]。相应的,缺少了当地居民的实践参与,本土文化的再生也就变成了表面上的形式延伸,而不是贴近当地文化内核的真正的文化再生。
最后,本土文化核心精神流逝,以及主体与文化本身分离脱节,这两种情况往往是保护者或设计者对当地本土文化了解不透彻不熟悉导致的。绝大部分本土文化是和居民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它们是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的一部分,比如一些节日民俗、舞蹈形式、居民建筑等。这些本土文化形式在历史的长河中亘古不变,作为遗产它们是沉默无言的,但是一旦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它们就变得鲜活有生命力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遗产并不是不变的,在历史河流中前进的文化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充盈着居民的活动痕迹。
二、本土文化再生中原住居民的主体作用
文化遗产和居民是相互独立而又不可分离的关系,文化遗产本身一旦脱离大众,就失去其承载的主体;反过来说,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对文化遗产的依附有需求,需要借助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因此,二者的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整体。
一般而言,本土文化再生应以当地居民为主导,强调对当地居民居住区域的文化氛围的保护,重视居住地居民对区域文化改造的认同,保护本土文化核心精神,这样的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才具有特征和意义。201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全球战略由“4C”改为“5C”,在可信度(credibility)、保护(conservation)、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沟通(communication)的基础上增加了社区(community)的理念[4],强调了当地社区在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只有当地居民认同本土文化遗产的意义与价值,并愿意付诸实践将其活化,本土文化才能在时代下连续演进再生,这也就是文化再生了。“风”带来的雨水养料是有用的,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文化却只会生根发芽于“土”里,从某种意义上讲,居民就是本土文化的“土壤”,是最了解本土文化的,并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践行着本土文化。故而,居住地居民应当是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主体,而不是让外来的设计者成为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核心实践者。否则当地居民会对自己生活的空间环境营造懈怠,形成被动接受现状的状态,进而削弱本土方案的可实施性,使本土文化失去传承的“土壤”。
同时,以本土居民为主导而实现文化再生策略,主要体现在文化保护过程中居民对于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也就是文化保护意识上本土居民的认同觉醒。本土居民长期生活在当地文化精神所滋润的空间场所环境中,其实他们的日常行动与生活也被当地文化精神所浸透,祖祖辈辈的行动与思想中也早已被当地文化精神耳濡目染。因此在居民的内心深处,当地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一直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只需稍加引导便能如雄狮苏醒一般。基于此,相关政府部门与社会媒体应该积极发挥宣传带动作用,通过各种媒介或是政策性引导加快促使居民对本土文化认同感的觉醒。对那些早有觉醒意识的代表性居民进行宣传,使其起到前浪带动后浪的领头作用。如20世纪90年代的杭州市 “旧城改造”运动,原本改造方案中清河坊街建筑群都将被拆除,拆除前,杭州某市民给市政府写了封紧急呼吁信,在此期间媒体也发布了相关保护资讯文论与专题报道,并從各种层面、角度激发当地市民重视古都传承发展的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这引发了社会对清河坊街保护问题的关注,并唤醒了杭州市民对清河坊街的文化认同感和保护意识[5]。最终,这次市民的集体呼吁促使市政府停止了拆迁并提出了保护的决定,使清河坊街一带成为杭州的重要历史文化景观和旅游胜地。故而,本土居民在文化意识上认同的觉醒对于保护传承本土文化有着重要作用,意识的觉醒也能保证保护后期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
事实上,文化再生与保护的前提,不仅需要当地居民文化意识的觉醒,对居住地文化内涵的珍惜,还需要本土居民的参与和实际行动,发挥居民本体作用。当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地区的人们都拥有对当地文化的保护认同感,社区之间就会形成默契感和氛围感,并在意识的能动性驱动下参与当地文化保护以及文化再生的过程。居民们会在日常实践中去发掘和欣赏当地文化的特殊性和闪光点,并把它作为文化印记潜移默化地变成了日常生活习惯,以此完成本土文化在当代的文化再生。当地政府部门也应该为居民提供参与实践的平台和机会,这样不仅能传播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也能逐步完善市民保护参与机制。同样,在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申遗过程中,多位遗产保护先行市民以他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保护行动推动了申遗过程。除了这些自己在生活中坚持参与实践文化保护的市民行动之外,杭州市也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目的在于接收当地市民对保护传承西湖文化景观管理上的一些问题和建议。纵观最近几年,杭州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融合度已经算得上是国内走在前列的,而西湖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发展也在市民的积极参与中越来越有当地特色。
三、结论与启示
本土文化再生不是对一个个“文化碎片”或者“文化孤岛”的“圈护”,而是对文化全局的关注,不但要保护文化遗产自身及其有形外观,还要注意它们所依赖和应用的结构性环境[6]。然而,文化遗产在离开了人类之后,其服务于居民日常生活的那部分社会文化价值也随之丧失了,与此同时也失去了时代的烙印,永远停留在了时代的角落。目前,本土文化再生过程中原住地居民主体作用受到广泛关注,面临诸多问题,也具有挑战和机遇。
第一,让原住地居民生活融入本土文化,成为保护与发展的一部分。本土文化再生的主要途径,是本土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源于社区居民作为文化主体持续参与文化遗产的再创造与维护过程。让本土社区的居民亲自参与保护和传承的过程,将保护意识融入本土社区和本土文化,这就要求设计者回归“日常生活”视角看待文化遗产,而不是刻意地区分“保护”与“发展”。2021年2月份,一场严重的大火将被誉为中国部落文化最后的“活体”翁丁古寨的百余栋房屋烧毁得仅剩三四栋。这样惨痛的代价凸显翁丁古寨保护与开发忽视了原住地居民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强行使村民离开了寨子,出现了村子的守护者和村子分开的“人村分离”现象。因此,尊重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尊重原住民和文化遗产的共生关系,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必须践行的重点,要使原住民作为文化主体持续参与当地文化的再创造与维护过程。
第二,充分发挥原住地居民主人翁作用,使其珍惜、爱护本土文化。本土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一个主体去延续和发展,这个主体既不能是“空降的”专家,也不能是直接主导的政府,而必须是本土文化原住地居民。只有对当地文化十分熟悉的原住民参与认同当地文化并对其进行日常化的实践,文化遗产活态化保护传承才有了意义。在社区居民作为文化主体持续参与文化遗产的再创造与维护过程中,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就变成了本土文化在当代的践行,由此形成了本土文化实践—文化意识—再实践—文化意识再提炼的螺旋上升的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加深本土居民的文化认同感,为下一个文化保护参与实践提供意识主导。
第三,挖掘原住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精神元素,并融入本土文化。文化历史遗产的活态保护要求更多地从日常生活场所、居民的生活方式的视角去理解文化历史遗产的价值。真实的日常生活关系才是文化遗产依存的原真性所在,而本土居民的参与认可也正是居民在本土文化保护过程中能体现出真实日常生活关系的重要方式。文化历史遗产最初是以实现人类生存和发展为核心价值的,而空间形态也不过就是文化遗产的物质外观伴随它而产生的自然结果。即便是其物质外观在当今时代发生了剧烈改变,只要其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依旧能被当地居民所继续传承发展下来,那被赋予了当代意义的遗产的精神方面依旧能反映文化遗产物质方面的内容,这就是遗产保护的弹性所在,也就是文化遗产的文化再生。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3.
[2]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22-25.
[3]金光亿.实践中的文化遗产:看文化不见人[J].西北民族研究,2018(4):70-79.
[4]田婷.老城保护中的遗产管理规划研究[D].南京:南京工业大学,2013.
[5]阮云星.文化遗产的再生产: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世界遗产保护的市民参与[J].文化遗产,2016(2):36-45.
[6]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整体性原则[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4(4):1-8,19.
作者简介:
胡梦婷,安徽建筑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设计。
冯艳,硕士,安徽建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城市化及城市景观规划研究。
陈治军,博士,安徽建筑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