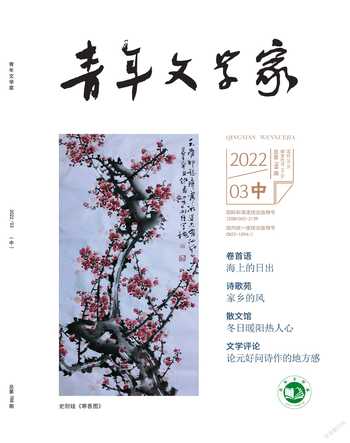论元好问诗作的地方感
2022-04-25张艳
张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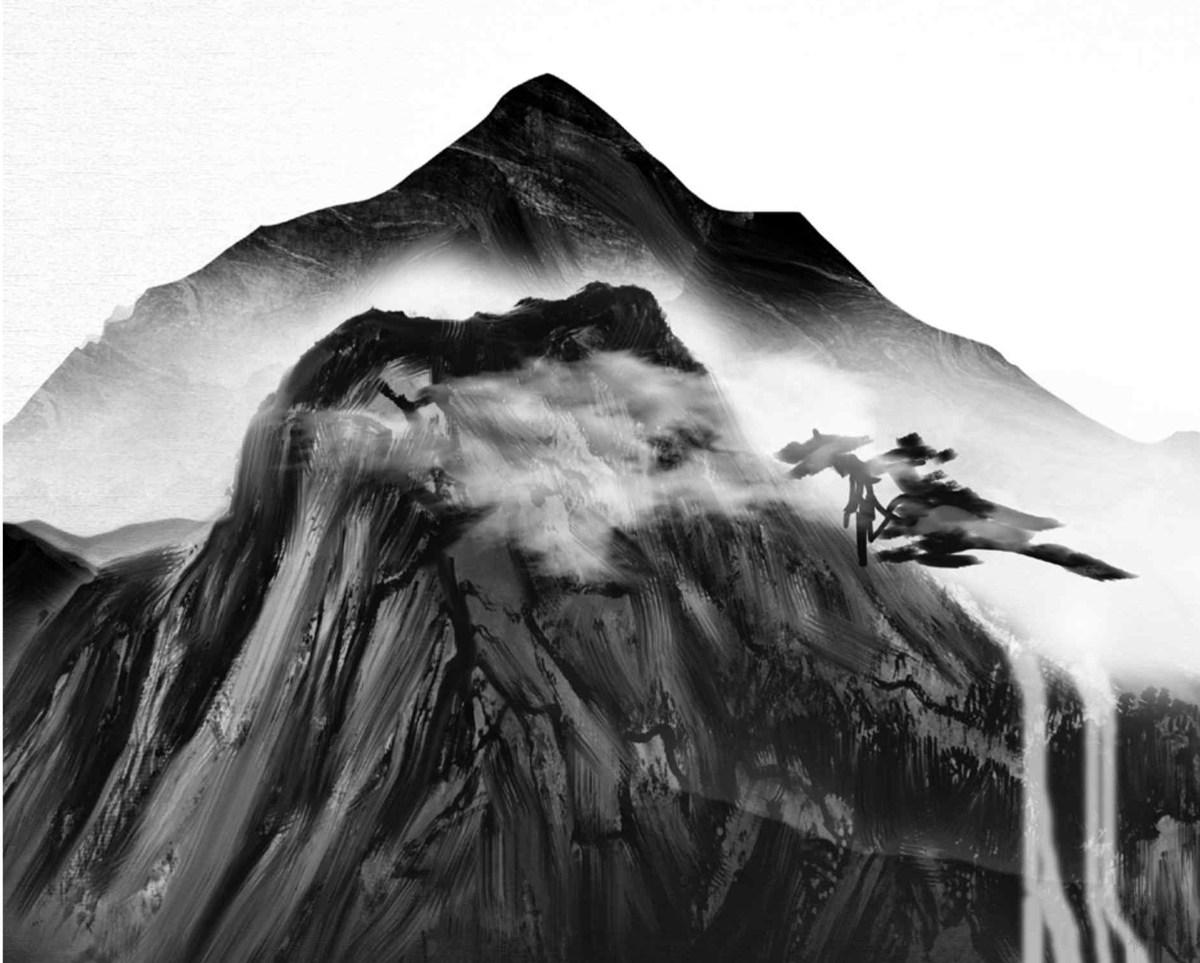

元好问经历了金末元初社会动荡的时代,随着时局的变迁和身份的变动,他几乎走遍了我国华北的各个省份,他的诗作诞生于游走各地的过程中,在文本表层意象方面,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蕴含着对家园故土的精神依附感和裹挟乡愁情结的身份认同感,以及野生真淳。富有深度的语言力量感。
元好问是金代后期的一位著名诗人和学者,也是我国金末元初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他出生于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年轻时从郝经求学,其后曾经入朝为官,也曾经隐居避兵,晚年才得以重归故里,潜心著述,蒙古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元好问病逝于故乡忻州。元好问一生辗转多地,或因为入仕,或因为隐居,甚至曾在金朝沦亡后被俘,他的足迹几乎遍及现在的华北各地,他的诗作就反映了他一路的所见所闻。本文将在文学和地理学的视域下,对元好问的诗歌创作进行观照。
一、鲜明的地理时空要素确定感
狄宝心先生编写的《元好问年谱新编》记载,元好问出生于太原秀容,因为避兵、应试等缘故,他先后居住于太原、三乡、登封、汴京、镇平、内乡、聊城、冠氏、济源、忻州、燕京、真定等地,主要游览过洛阳、昆阳、济南、太行山、雁门、应州、浑源、河北、五台山等地,他的出生地以及行迹都影响着他的创作,是其创作产生的地理基因,也构成其创作的地理空间背景。
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是由一定要素构成的具体可感的审美空间,“研究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首先应研究这种空间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可分为两个系列:一是隐性要素,包括情感、思想;二是显性要素,包括景观(地景)、实物、人物、事件。这两个系列的要素通过富有个性的语言和相应的结构方式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地理空间”。元好问的诗作有着鲜明的地理时空要素。金宣宗贞祐四年(公元1216年),金兵与蒙古兵交战,元好问为避兵辗转于太原、洛阳、女几等地,这一阶段的诗作反映了他在这场兵戈之祸中颠沛流离的生活状况,如《洛阳古城曦阳门早出》:“乘月出曦阳,黎明转北冈。荒村自鸡犬,长路足豺狼。天地怜飘泊,风霜忆闭藏。微吟诉行役,凄断不成章。”随着元好问行迹的变化,地理空间的变更也影响着他的创作,金宣宗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蒙古兵攻打太原,元好问偕母亲、妻子等家人移居避祸,六月间定居河南三乡。三乡有险可守,风景优美,所以被时人当作理想的避兵之地,许多文人汇集在此,元好问即其中之一。三乡优美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为元好问的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作为地理空间要素反映在他的诗作中,如《三乡杂诗三首》:“梦寐沧洲烂熳游,西风安得钓鱼舟。薄云楼阁犹烘暑,细雨林塘已带秋。”“尖新秋意晚晴中,六尺筇枝满袖风。草合断桥通暗绿,竹摇残照漏疏红。”“溪南老子坐诗穷,穷到箪瓢更屡空。五凤楼头无手段,碧鸡坊外有家风。”这三首诗都是写景抒情之作,元好问以“钓鱼舟”“薄云楼阁”“细雨林塘”等要素构建了“三乡”这一地理空间,在诗中描绘夏末秋初时池塘、竹林的优美风光,抒发自己的悠闲自得之情,用自己的主观将客观的地理环境内化为了个人的审美精神,“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
二、对家园故土的精神依附感
元好问生于金末元初朝代更替的时代,朱东润先生这样论述他的身份:“好问自从公元1190年金章宗昌明元年出生以来,就应当算是金朝人,直至公元1234年金亡,北中国沦陷于蒙古以后,他应当算是蒙古朝人……不过由于汉人的文明程度远远高出于金人和元人,他所受的文化影响,还是属于汉人的。”元好问出生于金朝,生活于金末元初胡汉冲突、王朝交替的时代,但在学术和文学方面,他主要受到的还是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接受、吸纳了汉族文化与汉民族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展现在民族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下,主要体现为一种对家园故土的精神依附感。
元好问出生于太原秀容,六岁起就随嗣父元格辗转移居掖县、冀州、中都等地,后寓居河南,直至蒙古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才回归故乡忻州,忻州作为他的故乡,带给他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在离家流寓期间,元好问写下大量怀念故土的诗篇,以抒发羁旅思想之情,如《八月并州雁》:“八月并州雁,清汾照旅群。一声惊晚笛,数点入秋云。灭没楼中见,哀劳枕畔闻。南来还北去,无计得随君。”此诗作于金宣宗贞祐四年(公元1216年)元好问寓居河南三乡,秋季北方群雁南迁,南归故乡,然而诗人自己却漂泊异乡,有家难归,詩人有感于此,唏嘘万千,发出了“无计得随君”的感叹。又如《阳翟道中》:“长路伶俜里,羁怀苍莽中。千山分晚照,万籁入秋风。频见参旗缩,虚传朔幕空。故园归未得,细问北来鸿。”诗人路经阳翟道,望着眼前的长路与秋夜秋风萧瑟的景致,感叹离家许久,只有寄思乡之言于北来的鸿雁。
蒙古乃马真后三年(公元1244年),元好问离开燕京,作《出都二首》:“历历兴亡败局棋,登临疑梦复疑非。断霞落日天无尽,老树遗台秋更悲。沧海忽惊龙穴露,广寒犹想凤笙归。从教尽铲琼华了,留在西山尽泪垂。”诗人登临远眺,远望“落日”“老树”,感慨汴京的陷落、金国的灭亡,借萧瑟秋景抒发王朝更迭、世事变迁的感慨,展现出深痛的怀念之思。蒙古定宗元年(公元1246年),元好问返回故乡忻州,路过镇州时作《出镇州》:“汾水归心日夜流,孤云飞处是松楸。无端行近还乡路,却傍西山入相州。”诗人借“汾水”这一具有故乡特色的意象表达思乡之情,又提到“归心”“还乡”,足见诗人急于回乡的心情。
三、裹挟乡愁情结的身份认同感
一个文学家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去接受客籍文化的影响,以及如何选择、吸纳和消化客籍文化都受他早年所接受的本籍文化的支配,元好问出生于金朝,是金朝的官员、士人,又接受汉民族传统的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认同的是自己文人、儒者的身份,这种认同带来的是比乡愁更高层次的国愁。自金宣宗贞祐四年(公元1216年)北方战乱,元好问携家南渡以来,他不断地思念着他的故乡故土,并为此写下许多羁旅思乡的诗篇,如作于蒙古军攻占山西,诗人从三乡移居登封后的一首《郁郁》中有“并州旧日风声恶,怅望乡书早晚回”之句,在这些诗篇中,他不仅思念家乡,同情百姓,也随着战事的发展而批评时政,对连战连败、消极应战的金朝表现出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又如《秋蚕》一诗有“东家追胥守机杼,有桑有税吾犹汝。官家却少一絇丝,未到打门先自举”之言,借官吏收税这一场景,展现了金朝政治腐败、税收繁重的现状,在金国沦亡、元好问本人被俘后,这种怀念故国的情感在他的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再如《洛阳》一诗有“千年河岳控喉襟,一日神州见陆沉。已为操琴感衰涕,更须同辇梦秋衾”之言,诗人在诗中远眺神州,面对熟悉的山河,发出金元易代、物是人非的感叹。
金哀宗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五月,元好问自北渡黄河往山东聊城,途中作《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塞外初捐宴賜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沈。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著青城阅古今。”诗人以一个历史见证者的身份叙述金王朝覆灭的史实,记述金末元初战火纷飞、改朝换代的历史。对于金王朝覆灭的原因,诗人在诗中也做了深刻的反思,哀痛金朝统治者的“灞上儿戏”,抒发国破家亡、物是人非的感慨,展现了深痛的爱国思乡之情,正如赵翼《瓯北诗话》所说:“七言律则更沈挚悲凉,自成声调。”蒙古与南宋联盟灭金后的和平并没能持续很久,百姓仍然没有安定的生活,元好问又有《得侄搏信二首》:“今日鄜州侄,知从虎穴还。百年阴德在,几日鬓毛班。隔阔家仍远,羁栖食更艰。谁怜西北梦,依旧绕秦关?”“虢驿传家信,坤牛玩吉占。团圆知有望,悲喜亦相兼。过眼书重展,伸眉酒屡添。关河动高兴,百绕望清蟾。”他目睹社会动乱、兵戈不息的现状,思念阔别已久的故乡故土,诉说动荡的社会中骨肉分离、家信珍贵的痛楚,哀叹自己在国破家亡后的无力。
四、野生真淳富有深度的语言力量感
清代学者李淦的《燕翼篇·气性》中提到:“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元好问出生于北方,也生活于北方,自然具有北方人“质直”“俗俭朴而近于好义”的特点,这些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同时他又出身书香之家,饱读诗书,秉承汉民族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曾大兴所著《文学地理学概论》将元好问及忻州元氏划分至三晋文学区中,对于三晋文学区的文学地域特征进行了论述,“三晋文学的地域特征与晋人的性格特点是紧相联系的,可用八个字来概括:重农、尚俭、崇实、多忧”。
金哀宗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元好问作《叶县雨中》:“春旱连延入麦秋,今朝一雨散千忧。龙公有力回枯槁,客子何心叹滞留。多稼即看连楚泽,归云应亦到崧丘。兵尘浩荡乾坤满,未厌明河拂地流。”在旱灾与战乱的双重压迫之下,百姓食不果腹、颠沛流离,元好问的创作关心现实,关心政治与百姓,他的诗作真实地记述了金元易代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展现了深深的家国情怀,如《岐阳三首》《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等。又如《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翠被匆匆见执鞭,戴盆郁郁梦瞻天。只知河朔归铜马,又说台城堕纸鸢。血肉正应皇极数,衣冠不及广明年。何时真得携家去,万里秋风一钓船。”“惨澹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知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这两首诗创作于金哀宗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这一年是蒙古军攻占金朝国都汴京的前一年,元好问时任左司都事,留守汴京,对于当时国都即将沦陷、国家即将沦亡的景象,他深深为之痛心,却又难以力挽狂澜,只有在诗歌之中抒发哀痛之情。金哀宗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这一年春天,金朝国都汴京陷落,元好问作为俘虏被押往聊城,在北渡黄河时,他写下了这组诗,描绘蒙古军攻破汴京时以及汴京陷落后的情形,不作无病呻吟之语,而是直接描绘当时的社会现实,感叹风云变幻,痛惜人民所受的深重灾难,用血与泪书写了对侵略者的控诉与谴责,感情浑厚、浓郁,可与杜甫“三吏”“三别”相较。
元好问的诗作语言精练,不事雕琢,感情深刻,蕴藉深远,元代徐世隆赞其诗作“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这种风格也影响了金元时期甚至以后诗人的创作。元好问的诗作极少有奇特的想象和华丽的辞藻,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元好问诗作感情的丰富与深刻,元诗的力量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诗歌所陈述的内容以及蕴涵在其中的感情,抒发家国之思的作品占据他诗作的大多数,在这些诗作中,他感叹乱世风云的变幻,目睹百姓所遭遇的天灾人祸,并深深地为之忧愁,他的忧愁不单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民族的、国家的,他关心百姓、关心国家,这种忧愁内化于他的诗作中,呈现出感情的质朴纯粹,完全来源于他作为一名诗人、儒者的责任感。
作为金元易代时期的一位诗人、文学家,元好问置身于动荡的社会中,一生游走,流寓于山西、河南等北方多地,他的诗作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也受到不同地区的景物和文化的影响,因此而具有鲜明的地理空间要素,展现了对家园故土的深深依附,我们也能从他的诗作中感受到他对自己儒家学者身份的认同,他的诗作语言野生真醇,富有深度,富有力量,显现了自身“积久功深、厚积薄发的日常功夫”,元好问本人也无愧于“一代宗工”这一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