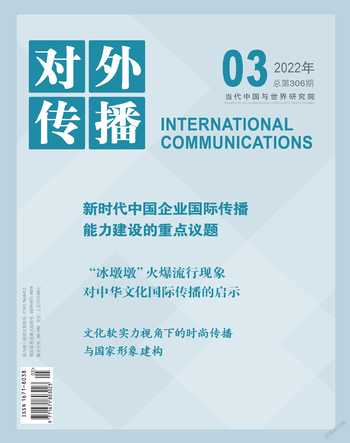从中国经验到世界语境:象群北迁的国际传播启示
2022-04-20温志宏
【内容提要】2021年4月开始的云南亚洲象群北迁事件实现了较为积极的国际传播效果,究其原因,一方面得益于技术赋能为当下视觉导向的受众群体呈现了弥足珍贵的野象图景,同时这一内容具有的中国特质跨越了文化语境差异,娱乐性与传奇性背后更为深层的生命关系成为其“生命叙事”的情感内核。面对人象冲突以及象群的命运,中国人的行动能力与观念变迁深刻体现了基于共生关系的价值选择,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推动实现了与国际受众的关系链接和情感共振。这对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启发包括两点:首先是主动进行议程设置的同时需要切实提升叙事能力与效果,有意识地去辨析和表达中国独特的“情感动力源”,进而实现以去符号化的方式传播中国经验及观念;其次是生发于社交网络空间的非精英性世界文化正在成为对外传播不可回避的新场域,把握传播场域特点是最大程度实现共鸣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象群北迁事件 讲好中国故事 跨媒介叙事 情感动力源 话语新场域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凸显和世界热点地区新旧矛盾叠累加剧的当下,讲好中国故事并提升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更具全球性意义。在对外传播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首先意味着培育发展一种有意识的叙事能力与行为,其在将中国发展经验与思想蕴涵以文化力量的方式保留并释放的同时,也是在以“叙事”这种独特的理解模式和沟通方式,推动中国的现实生活嵌入一个共同的世界语境,从而将中国与“同时代人共同存在的多样性联系起来”①,以为世界读懂新时代中国奠定基础。
云南亚洲象北迁事件即是一个具有上述国际传播意义的中国故事,多层次的叙事建构推动中国行动与经验实现了较为良性的国际传播效果。这群亚洲象原本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1年4月中旬,向北迁徙的象群历史性地突破了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活动范围,越来越靠近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罕见的野生动物生活场景、神秘的象群迁徙原因以及不断迫近的人象冲突可能吸引了大量媒体追踪,从2021年5月底到7月中旬,包括西方主流媒体在内的多国机构不断发起有关报道叙事,比如美联社形容社交平台上到处出现的中国大象十分“滑稽可爱”,日本多家电视台对中国追踪和保护象群的行为与实力赞叹不已。这一独特的中国故事也在境外引发了较为良性的舆论呼应,用优兔平台观看量排名前十视频的评论生成词云图,一些共同的高频词包括“野性”(wild)、“美丽”(beautiful)、“可爱”(cute/adorable)、“让人惊叹”(amazing)等。上述这些积极反馈提示我们,有关亚洲象北上的中国叙事既是一个天然具有新奇性和娱乐性的新闻故事,也是一个讲述发展与变化的中国故事,更是一个中国经验与世界语境相互融通从而引发国际公众情感共振的世界故事。
一、语境化的新闻叙事:冲突、悬念与影像
富兰克林在《新闻学关键概念》中讲到新闻与叙事的关系时指出,好新闻的核心在于一个“好故事”,完成这个“好故事”需要背景、冲突和结果,其中“冲突”额外重要,因为“冲突”意味着不同寻常,新闻叙事的叙述形式通常会从冲突开始,这也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新闻及其意义的感知和理解。②他还借用哈罗德·埃文斯的观点指出了影像在新闻中的独特价值,“照片对于理解我们所不能亲眼见识的世界具有独特的贡献”③,在吸引受众方面能量巨大。对于象群北迁的新闻叙事来说,正是上述两个特征极大提升了其传播价值。
首先是悬疑性的突发性冲突语境。当15头亚洲象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人口密集区域的县城公路上,当地人惯常的生活节奏被打破,一个极具普遍意义和新闻价值的话题便凸显出来,即大自然以及存在其中的生命关系。这种生命关系既体现在野生象与传统栖息地、象群与人类定居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也体现在北迁原因及其影响、应对措施与行动、象群状况与最终走向等多个未知的悬念。不同层级的冲突与悬念构成了媒体所热衷的突发性新闻语境,这种突发性也为中国媒体设置新闻议程提供了契机或者说先机,中国媒体发布的有关图片与数据被国际各类媒体频繁引用转发,从而较为广泛地影响了国际传媒与公众议程。
其次是视觉性的观看语境。视觉性图像与影像及其营造的观看语境构成了这一新闻事件的关键媒介性表征,是“观看创造了情感”④。数月时间里,在无人机和远红外等多种技术视野中,隐秘的象群迁徙场景与活动细节都被记录并传播开来。从采食嬉戏到排队“逛街”,从“自助”饮水到相拥而眠,有关象群的独特视觉信息通过互联网与数据算法赋能而以更快的传播速度和更精准的受众目标到达网民终端。英国《卫报》就在有关报道中,将成年大象簇拥着幼象睡觉的图片列为事件进展的里程碑之一,认为这张图片对于引发国际关注具有重要作用,它直接激发了观众的情感直觉和审美反应。
可以说,正是得益于一个突发性的“好故事”,象群北迁事件在视觉性极强的传播互动语境中建构起了奇迹般的新闻姿态,受众得以从中对亚洲象群进行想象性感知与亲近,“短鼻家族”也因此成为万人瞩目的“网红”。
二、跨媒介的中国叙事:行动、观念与文化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际议题来说,受限于时间、空间、认知背景以及知识能力等诸多因素,多数境外受众难以身临其境地进行直观感知。人们生活在传播世界里,借助媒介观察世界,如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所说,媒介内容带来的想象性认知先于甚至替代了现场体验,进而塑造了人们有关世界和他者的观感与概念。西方世界长期控制国际媒介体系,在历史上把自己视为普世参照点,“他者们据此而被界定为特殊体”⑤,但随着全球传播越来越多在互联网体系和社交平台展开,中国的事实有了更多机会在世界舆论中得到公允呈现,⑥中国的发展经验与行动观念經由跨媒介叙事性传播,构成了世界语境中独特的中国声音。
这种“中国特质”也成为象群北迁事件引发国际舆论呼应的第二层叙事因素。纵览境外有关报道,中国的环保成效、治理实力以及观念变化等内容频频出现在叙事话语中。如英国广播公司(BBC)、美联社、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NBCnews)和《纽约时报》等媒体都提到象群北迁的可能原因之一是中国严控伤害野象,多年的环保举措使象群规模增加。美联社、《卫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关注中国地方政府应对策略,包括部署应急人员和车辆,投喂数十吨食物,数十架无人机24小时监控行踪,其配备的红外相机自动提取和识别野象照片等。在CNN的报道中,迷失的象群成为中国的举国焦点,从庄稼地觅食,到误闯农户住所,再到雨林中象群亲密相拥安静入眠,人们在数月时间里和它们感同身受;《卫报》提到,一条当地人关心象群是否会误食雨季毒蘑的热搜新闻点击量超过1.2亿人次。
不难看出,大量中国事实与发展经验有意无意地呈现在象群北迁的国际传播叙事之中。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上野生动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状况备受关注。但长期以来,中国在野生动植物保护及管控打击非法贸易等方面的投入与努力并不为国际社会所了解,野生动物保护因此成为很多国际组织和媒体抨击中国的热点话题。在此背景下,西方媒体主动讲述或传播的象群北迁的故事,既包括对一种具有广泛认知的地球生物的天然注目,无意中也超越了传统视角中有关中国的刻板印象,外媒及受众惊异地发现了中国的国力变化与观念变迁,发现中国已经具备了改善生态环境问题的强烈意识与综合能力,其环保意识与观念符合甚至超越了西方价值观的叙事逻辑。与此同时,这也并非一个单纯充斥着种种高科技媒介的机械过程,这个有关中国人行动经验与观念变迁的故事不仅让人感到轻松、亲切,还传递出了人们对野生动物深厚的情感关怀,乃至带动整个社会对生态发展历史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思考。在这个跨媒介的叙事过程中,一个真实、立体、有人文关怀的中国形象无形中便树立起来。
三、通融中外的世界叙事:对视、对话与共鸣
作为一条与中国深度关联的好新闻,象群迁徙事件之所以同时成为国内外的传播热点,第三个关键因素在于其新闻叙事跨越了不同背景的文化差异,中国行动经验与世界语境相互融通,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实现了与受众的关系链接和情感共振。
首先,应对象群北迁的积极行动及生态关怀与西方生态主义价值观相契合。科学的机械哲学和浪漫的自然哲学是西方近代认识论中并行的两个方向,机械哲学希望将自然的一切力量都归结为机械力量,而自然哲学则希望将各种现象和非机械力量统一到一个有机整体中。⑦基于自然哲学的生态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国家萌芽,到80年代末,时任挪威总理布伦特兰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指出16世纪从欧洲开始并扩展到全世界的经济与工业模式缺乏长期发展观,造成了日益加重的环境问题,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生态运动代表思想家莫斯科维奇提倡对近代以来形成的理性至上等价值观念进行反思,认为自然危机已经成为21世纪的普遍性问题,来自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大气变化以及生态失衡的危机和威胁正急剧变成日常生活的现实。时至今日,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让人们深刻体会到这点。象群北迁事件属于生态范畴,关乎人与野生动物的共生关系。野生象群从自然深处缓缓走来,跟随着它们的步伐和身影,人们仿佛重新发现了大自然,发现了这个有生世界的生动与可爱之处,这个过程也再次唤起对更多生态问题的注目与反思。与此同时,媒体报道中的行为主体——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国人,充满了浓厚的生态精神和行动自觉,与往常一些备受西方关注的环境问题不同,保护象群行动持续展开且投入巨大,但并非迫于外在的舆论压力,而是源于对当地民众、对野生动物、对大自然乃至全球生态安全的责任感,这种向生命说“是”的主体性姿态和文化自觉构成了中国叙事在世界语境中展开“多样性对视”⑧,进而与其他声音“构成生成性对话”⑨的首要条件。
其次,在现实层面,象群北迁新闻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性焦虑背景下催生了媒介化的共感与共鸣。瑞士苏黎世大学学者露西卡·朱莉安(Lischka Juliane)等人就社交媒體新闻制作逻辑进行了研究,发现在脸书上,新闻价值和新闻编辑越来越受到用户参与的驱动,其核心表现即社交媒体编辑最喜欢用情感性(emotional)或新奇性(surprising)的叙事元素顺应用户需求。⑩全球性社交平台优兔的数据也显示,其75%的成年用户主要在平台上寻找更具情感倾向的怀旧类内容(nostalgia),而非专业知识或信息类新闻。11这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社交时代微观化和情感性跨媒介叙事广泛兴起的传播现象,“强烈的情感承载”成为媒介化社会的显性特征之一。从2020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突发性的全球灾难撕裂了基于理性与技术的惯常知识图景,放眼全球,旧有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与疫情叠加,各种抗议、混乱和失序严重抵消了对抗疫情的努力。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未知与恐惧等种种负面情绪强化了公众的情感庇护需求,象群北迁新闻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各类拟人化报道手法建构出一种生动又形象的情感性语境,人们通过社交平台短暂地沉浸于这个罕见而有趣的想象性场景,不仅对野生动物生发出一种集体性的情感表达,自身也由此而获得治愈。在情感理论看来,这种被赋予集体力量的情感表达与行为正是共鸣得以发生的实质。12这也可以被看作是象群北迁跨媒介叙事最为深层的话语影响力所在:在中国经验与世界语境的契合中,世界上更多的人们从相互对视到彼此对话,体验到了情感性和治愈性的共鸣经验。
四、国际传播实践启示:“情感动力源”与话语新场域
象群北迁事件之所以实现了较为积极的国际传播效果,一方面得益于技术赋能为当下视觉导向的受众群体呈现了弥足珍贵的野象图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内容具有的中国特质跨越了文化语境差异,娱乐性与传奇性背后更为深层的生命关系成为其生命叙事的情感内核,面对人象冲突以及象群的命运,中国人的行动能力与观念变迁深刻体现了基于共生关系的价值选择,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推动实现了与国际受众的关系链接和情感共振。
在全球性社交网络时代,去中心化的技术平台给每个个体都赋予了成为思想起源的空间与潜力,媒介的历史性变迁正在世界范围内成就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对于中国故事海外传播来说,象群北迁事件或具有以下一些启示。
首先是主动进行议程设置的同时更注重提升叙事能力与效果。“叙事”是构建行动、身份与观念认同的重要途径,提升去符号化、去范式的叙事能力将赋予中国故事更多生命底色,软化价值观植入与意义构建意图,从而实现更为广泛的国际情感共鸣。乐黛云在其跨文化方法论中指出,真正实现文化对话的首要条件是观点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对话的基本目的是理解和尊重“在他者的自身文化多样性”中的他者,这种文化多样性作为一个文明独特的“情感与知识的动力源”13,构成了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关键所在。提升叙事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即是有意识地去辨析和表达中国所具有的独特的“情感动力源”,进而以“去符号化”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象群北迁国际传播案例同时也提示我们,科技发展带来万物皆媒的传播态势,跨媒介叙事能力的建构与强化势在必行,其核心路径在于以更加丰富的媒介形态有效地发起或介入国际场域的互动叙事。把握互动叙事的历史性与发起时机也异常重要,由新冠肺炎疫情而来的焦虑人群及对生态问题的反思就成为象群北迁事件现象级传播的重要时机。
其次,生发于社交网络空间的非精英性世界文化正在成为对外传播不可回避的新场域,把握传播场域特点是最大程度实现共鸣的关键之一。当前,伴随新场域的新受众和新媒介特征,需要新的叙事回应。在传统的对外传播实践中,西方社会及其精英阶层是最为重要的受众指向,但互联网带来了根本性改变。个体性和个案性的生命交互与意义生成在网络传播中普遍凸显,非精英性网民群体成为不可忽视的受众主体。以优兔为例,73%的美国成年人和81%的15-25岁的美国年轻人使用这一平台,同时在其超过20亿用户中有80%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14象群北迁事件短时间内引发全球网民围观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发生在遥远中国西南一隅的跨时空景观通过社交平台持续激发了数百万网民追踪跟进。互联网及社交平台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场域,当“沉默的螺旋”进化为“喧嚣的网络在场”,非精英性网民大众的情感、认知与行动直接影响到国际传播实践是否精准有效,应该成为相关话语策略的重要基础性考量。
最后,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消极话语制衡”15,构建不同层级指向且多元化的传播话语体系十分必要。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战略性话语策略、宽泛异质环境中的文化符码分享与文明对话,以及更多象群北迁式的突发性和个体性传播实践将互为助力与补充,推动达成话语共识并提升国家与文化影响力。同时,需要机制化并行推进对国际主流话语策略及非精英性世界文化的系统性追踪与研究,尽可能深入与前瞻性地把握不断迭代新生的话语场域与内容需求,以放大互联网时代复杂多面国际话语场中的中国声音。
温志宏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注释」
①王正中:《叙事建构论的四重关系》,《当代文坛》2017年第4期,第23页。
②[英]鲍勃·富兰克林等:《新闻学关键概念》,诸葛蔚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6页。
③[英]鲍勃·富兰克林等:《新闻学关键概念》,诸葛蔚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9页。
④[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⑤[英]戴维·莫利:《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⑥魏舒歌:《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魏舒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8页。
⑦[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7页。
⑧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26页。
⑨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49页。
⑩OMNICORE,Juliane A Lischka:Forces in Social Media News Making[EB/ OL],https://www.academia.edu/36385084/Forces_in_Social_Media_News_ Making_pdf.
11OMNICORE,Youtube by the Numbers:Stats,Demographics & Fun Facts[EB/ OL],https://www.omnicoreagency.com/youtube-statistics/,2020.
12[德]哈特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9页。
13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33页。
14OMNICORE,Youtube by the Numbers:Stats,Demographics & Fun Facts[EB/ OL],https://www.omnicoreagency.com/youtube-statistics/,2020.
15袁莎:《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第85页。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