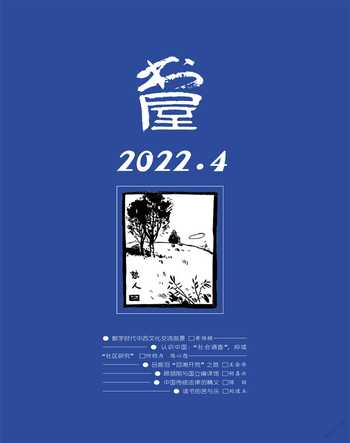大地上的尺度
2022-04-20邢哲夫
邢哲夫
去年,务工人员读海德格尔成了热搜话题,这不禁让人想起《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阅读史。毕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和人们对乡土中国的刻板印象形成了某种张力,仿佛圪崂里只能唱“羊肚肚手巾三道道蓝”。其实,这种刻板印象正源于人们观念中城乡结构的二元对立,以及以城市为本位,将乡村作為边缘和他者予以俯视的现代性格局,而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乡土文学叙事的前提,是现代化进程中建构起来的差异。
罗雅琳的《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以下简称《上升的大地》)则试图弥合城乡二元格局的断裂性,用另一种态度审视和想象中国乡土在现代社会的另一种可能。《上升的大地》虽然是以乡土文学作为理解乡土中国的切入点,但选取的作品并不是经典乡土书写的常见文本,如鲁迅、沈从文小说直到张艺谋、陈凯歌电影,而别出心裁地选取了《黄河大合唱》、《平凡的世界》、打工诗歌、刘慈欣科幻小说等作品。虽然《黄河大合唱》《平凡的世界》早已纳入当代经典谱系,但刘慈欣科幻小说、打工诗歌作为主流文学的边缘,在有待经典化的状态下恰恰拥有更多的阐释空间。
在第一章《西部中国的“现代”形象》中,作者没有马上切入文学文本,而是选取了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几篇关于中国西北的新闻文本: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通过不同的叙事态度的比较,作者试图告诉我们,乡土中国的不同面相不是自然而然的镜像反映,而是由不同的视野和立场建构起来的历史理解。如陈学昭带着“我们江浙人”的现代都市文明的优越感,便只能得出西北落后原始的结论,而斯诺带着对“红色中国”的无比热情,自然能够感受到西北大地的无穷生命力,以及对于现代化的强大包孕力。这揭示了乡土文学叙事的一个元命题:视角是事物的尺度。都市文明的视角和人民革命的视角,都可能包含对乡土中国迥异的理解和想象。在这一前提下,一种不同于乡土中国经典书写的文学想象呼之欲出。
第二章《黄河的古今变奏》选取《黄河大合唱》进行阐释。作者敏锐地注意到《黄河大合唱》不同于以往抗战歌曲单纯的控诉趣味,而是让人民群众以一种崇高的主体姿态去唤醒黄河,而黄河作为五千年古国文化的象征符码在抗日救亡事业中被重新演绎,也隐含了现代性在乡土中国曲折展开的另一种逻辑:“这里的人民之‘新并非建立在与传统的断裂之上,而恰恰是对于文明传统的‘返古开新。”孟悦女士以《白毛女》为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恰恰是以喜儿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对民间伦理秩序的维护和重建的渴望作为心理基础的。对两部红色经典的再解读告诉我们,这种将传统文化吸纳其中的现代性样式,恰恰是乡土中国的在地经验,现代性并非都市文明的专利和同位语。
而讨论《平凡的世界》的《打开“城乡交叉地带”》一章,则在超越都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视野中,审视了孙少平式的“农村青年读海德格尔的现象”。农村青年阅读“高端书籍”其实是现代性有色眼镜(柄谷行人所谓的“装置”)下的景观,它产生于农村配不上“高端”文化的粗暴逻辑。而假如对农村多一些了解之同情,对城镇少一些傲慢之执念,对现代性的想象持一种开放多元的态度,我们便不难发现:“农村人并不会因为经济水平的落后而缺乏获得‘精神生活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正是这种艰难困苦为他们提供了磨砺精神的必要条件……在农村和农民被视为‘愚昧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是路遥为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农村青年找到的通往高贵的道路。”在作者的理解中,孙少平并不只是一个向往高贵的“凤凰男”,相反,孙少平身上乡土文化孕育出来的朴素美德,使得他在入城后也没有“自我原子化”,而是始终保持着对家人的眷恋、对他人的温情,带着一种传统共同体的温度融入原子化的现代社会。这让人想起《士兵突击》导演康洪雷对许三多的评价:“许三多体现了农耕文明的美德。”孙少平、许三多的形象之所以能够感染人、征服人,恰恰是因为这种乡土中国孕育的精神力量。作者还将《平凡的世界》置于柳青《创业史》的精神谱系中审视,这不仅因为他们都诞生于陕北大地,而且在精神品质上都体现了乡土中国通向现代中国的强大内在动力。
《走出乡愁乌托邦》则针对以城市为中心的乡土书写的浪漫主义趣味,让打工文学作为离乡者的现身说法,由边缘走向前台自我发声。而作者在对怨而不怒的打工诗篇的绎读之后,别出心裁地解读了刘慈欣《中国太阳》的打工/科幻叙事,为这种“怨”开出了一个升华的空间:向宇宙进军的打工人,身上蕴含的不仅是孙少平式的追求高贵的可能,更是实践崇高的可能。和“打工人”的身份跃迁一样,现代乡土中国也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但其终点不仅可以是物质性的富裕,更可能是精神性的崇高,既是丰收的大地,也是“上升的大地”。
文化是共同体内部自然形成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而乡村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统中国,乡村就是人们生活世界的最基本范围,千百年中沉淀下了稳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质和底色。无论是乡土中国里日常生活的丧葬嫁娶,抑或是精神谱系的诗礼传家;无论是自下而上的“礼本乎俗”,抑或是自上而下的“化民成俗”,作为“俗”的一维,乡土中国都是中华文化得以展开的基本场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文化的根在乡村,中华文化的不断生成在乡村,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也在乡村。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农村包围城市”开辟了中国革命的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与广大农村相结合,开创了文化上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而在改革时代,农村改革开启了全面改革的大幕,《平凡的世界》里的大半场景便上演在乡村。无论是革命时代还是改革时代,乡村不仅没有缺席,而且为时代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荷尔德林有诗:“大地上可有尺度?绝无。”然而,大地没有尺度的前提是大地与天空的悬隔。而只要想象大地的上升,那么大地便有着无限接近天空的可能,便是诗意栖居的空间。乡村振兴的过程也是大地上升的过程。拥有无穷力量和无尽可能的中国大地,必然能穿越星辰大海,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量天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