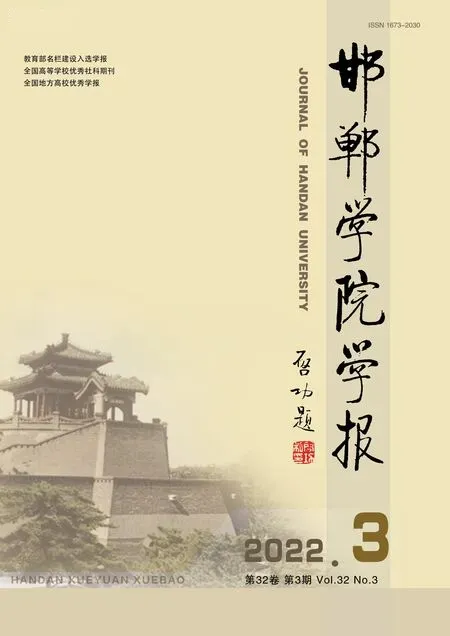“心”与“欲”之间:荀子道德动机探源
2022-04-17叶晴
叶 晴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
儒学的特质在于其是一种肯定道德可能性、并提倡道德教化的学问。在儒学视域下,只有人才有道德;或者说只有道德才能称为人。由于道德是一种应然的要求,但现实中却有不道德的人存在,因此儒学的旨趣在于使人和社会道德化,从而实现人与道德的同一。对于儒学而言,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是人道德动机的来源问题,即为什么人会主动从事道德行为,是什么促使一个人想要成为道德的人?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谈论成为道德的人的现实途径。
孔子已经涉及对于道德动机的讨论,他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与“欲”分别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揭示人从关心自我到关心他者的道德逻辑,但孔子并未回答这种由己推人的道德动机是如何产生的。而孔子也把“好德如好好色”和“从心所欲不逾矩”作为人生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这意味着人不仅行道德之事,而且乐于行道德之事,或者说行道德之事与人的主观欲望是一致的。虽然其设立了欲望和道德统一为儒家道德的理想境界,也仍没有对二者统一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依据。基于孔子理论体系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后世儒家做出了不同径路的推进。孟子认为,人性本具有善的端芽,扩而充之即可为善,这为道德转化的可能提供了先验人性的保障。在孟子的理论径路中,道德动机被先天地赋予了,人行善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由此把“主观的欲望”通过人性善的建构转化为了“客观的欲望”,做道德之事是符合人自然倾向的,道德动机在孟子那里具有现成性。
但对于主张性恶的荀子而言,道德动机的来源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荀子主张人性好利欲得,那么对天然为恶的人而言,道德的可能性从何而来?即使荀子强调人可以“化性起伪”而为善,但“化性起伪”本身何以可能,人如何有克服自然欲望而实现自身道德转化的动机?可见,在荀子的理论结构中探寻道德动机的来源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解释在性恶论的前提下,主体道德如何可能。
本文将在回顾学者对荀子道德动机不同解释的基础上回到荀子文本,着重于“心”与“欲”之间的转化依据以探寻道德动机的来源。本文认为,荀子所论的自然情性有与道德“意气相投”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心能本于其再通过认识去实现“心之所可”对自然欲望的道德转化。这能够帮助我们从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去理解荀子体系中道德动机的生成。
二、荀子道德动机的当代研究
荀子道德动机的来源在学界已有很多讨论。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荀子实际上是以“心”的能力去实现道德转化的可能。其中主流的观点是把“心”作为“认识心”,强调通过后天的认识和学习,人具有能“化性起伪”去实现道德的可能。也有一种观点把“心”作为“道德智虑心”,赋予了“心”根本的道德能力,如梁涛认为:“荀子的心并非人们所认为的认知心,而是一种道德智虑心,不仅能认知,也能创造,具有好善恶恶、知善知恶和为善去恶的能力,荀子的心首先是道德直觉心。”[1]但是这种方案把荀子的心作为道德直觉心处理,超越荀子思想本身而赋予了“心”现成的道德属性,则与孟子的“道德本心”难以区分。
而以“认识心”说明道德可能性的方案,也面临许多的质疑。比如牟宗三指出,荀子以“智性”规定人,荀子的主体是一种知性主体,尽管认知能力确实可以认识道德之理并约束自身,但如果把道德的建立寄托在认知上,则缺乏道德的动力:“然以理自律,须赖其自己之最高道德感,道德感不足,即不能自律,而又无外力以控制之,则即横决而漫无限制……”[2]204牟宗三后来对朱子之理“只存有不活动”的批判,也延续了这一思路。如果把道德之理作为外在的被认知对象,人虽然可以认识理,但是仍然缺乏道德动力的活动性,那么他律转化为自律是缺乏根源的,道德主体性难以建立。
与牟宗三的质疑相似的是,当代许多学者援引休谟问题进一步质疑荀子理论体系中道德动机的缺乏。休谟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否能从“实然”推出“应然”,即事实命题能够推出价值命题吗?具体在道德心理学上,休谟认为“信念”和“欲望”是两种与行为相关的不同心理状态,信念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欲望则是为我们做事提供动力,信念和欲望与世界的符合方向是相反的,二者的结合是困难的①安斯康姆指出,信念与欲望对世界的符合方向是相反的,信念表象着世界,因此它真假的根据是它是否恰当表象世界,其符合方向是从心灵到世界;而欲望不表象世界,当与世界不符因此不能得到满足时,它(欲望)不需要被改变,其符合方向是从世界到心灵,人们往往想要改变世界以符合我们的欲望。由于二者的符合方向不同,休谟主义者认为二者不可能作为单一的心理状态而存在。G.E.B Ansombe,Intention. Oxford: Blackwell,1957,section2.。在缺乏欲望下仅依靠理性(或知性)并不能提供动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产生道德动机是困难的。②“单是理性既然不足以产生任何行为,或是引起意志作用,所以我就推断说,这个官能[理性]同样也不能制止意志作用,或与任何情感或情绪争夺优先权。”“理性是完全不活动的,永不能成为像良心或道德感那样,成为一个活动原则的源泉。”参阅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452-453、 498 页。所以,如果简单采取理性主义的径路,说荀子是以心的认识能力为道德可能的基础,会面临休谟问题的诘难。比如杨泽波借助休谟问题指出了荀子性恶论的根本困难:
一门道德学说要有效能,能够变为道德践行,必须有充足的动力,否则再完整再系统也只是一个死理,没有实际的意义,而这种动力只能由仁性提供,智性没有这种功能。因为荀子对仁性没有透彻的理解,不了解仁性的先在性和逆觉性,致使其学理中仁性缺位。这一缺陷对荀子道德学说有严重的消极影响,因为如果在一套理论中缺少仁性,单靠智性是没有办法获得足够动力,保证由知变为行的。[3]5-12
在荀子的理论体系中,人可以依礼义而行,但是行为缺乏内在的根据,没有提供作为动力的东西,则礼义法度没有成为人的自愿行动,甚至可能与人的自然欲望冲突,荀子忽视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巨大鸿沟。杨泽波就此认为,道德学说的动力只能通过“仁性”提供,这可以说是对荀子的性恶论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4]48-56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确实无法从荀子思想内部找到替代“仁性”的道德动机?
万百安、克莱恩和黄百锐等海外学者对于荀子道德动机问题的讨论可以为我们探寻荀子的道德动机提供有益的视角。万百安认为荀子与孟子不同,其否认人天生的道德欲望(innate moral desire),强调自我教化的过程是以“心之所可”(mind’s approval)来克服欲望并完成自我转化的。①“心之所可”的说法来自于万百安对于《荀子·正名》的分析:“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固难类所受乎天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其认为,荀子区分了“欲”和“可”,指出了人的行为不是由欲望决定的,而是由其“所可”,决定的,而“所可”基于心的认识能力对善恶的认识而进一步的认可。万百安对此的解释似乎在于强调,人们一开始是顺从礼义,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引导自身欲望,使之与“道”和谐,从而实现“礼义”从手段到目的的转化,让礼义成为个体内心道德的表达。孟荀的差别就在于,孟子认为一个人行善是因为欲求行善(desire to do good),而荀子则认为行善是因为他认可行善(approves of doing good),“心之所可”构成荀子的道德动机。②Bryan Van Norden, “Mengzi and Xunzi: Two Views of Human Agency,”in Virtue, Nature, 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 ed by T.C.Kline Ⅲ and Philip J. Ivanhoe,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 2000, pp. 123—124, p.128.万百安的径路和以认知建立道德主体性的径路具有相似性,即强调人是通过外部的认识和事件,从而在心认识进而认可善的前提下去行善。基于休谟式的问题,“心之所可”和“欲望”却代表两种不同的和世界适合的方向:“心之所可”其实就是在认识基础上被赋予于心灵的“信念”,其符合方向是从心灵到世界(mind to world),如我通过认知改变我的信念以使其符合外部社会设定的礼义。而“欲望”的符合方向是从世界到心灵(world to mind),这种符合是通过改变外部状况而获得的,如我欲求利益,则我通过改变我的经济状况来使得我的欲望得到满足。这两种符合方向相反的心理状态使得万百安的思路遭遇休谟问题:我如何能够通过“心之所可”去克服我的欲望,从而让我对世界的欲望和世界对我的道德要求(我对善的认知)是一致的?或说“心之所可”如果能够克服欲望,其克服欲望的根据是什么?延续万百安“心之所可”的方案,海外学者对此进一步做出了讨论。克莱恩指出“可”与“欲”可以是独立的动机,“心之所可”表示另一类动机,既有认知,也有意动(conative)的因素。③T.C.Kline Ⅲ,“Moral Agency and Motivation in the Xunzi”, in Virtue,Nature,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 ed by T.C.Kline Ⅲ and Philip J. Ivanhoe,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 2000,pp155-175.意志决断可以独立于“行”之外成为行为实现的原因,“心之所可”可以理解为不同于“如此这般欲望”的动机机制,表现的是心的自由能动一面。但依这一解释,这种心“自由能动”的能力是开放性的,充其量是道德实现的必要不充分条件,而并不能保证道德的转化从而作为“道德动机”存在。
黄百锐对万百安的“心之所可”提出了强解释和弱解释两种方案④David B.Wong,“Xunzi on Moral Motivation,”in Virtue, Nature, 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 ed by T.C.Kline Ⅲand Philip J. Ivanhoe,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 2000, p. 141, p. 142, p. 141.。强解释方案认为“可”与“欲”是斗争关系,心从其所可实践道德,要求的就是对欲望的控制,但如此“心之所可”是独立作为动机的机能,要求建立在某种内在性或者先天性的结构基础上,而荀子的理论中并不存在这一结构⑤黄百锐认为,这种“心之所可”只有两种解释是可能的,要么“心之所可”是建基于对不可化约的道德属性的知觉上,这是柏拉图式的处理方式;要么“心之所可”是建基于纯粹理性活动的基础之上,这是康德式的处理方式。由于荀子不认为存在不可化约的道德属性,同时他也不相信“心之所可”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功能,因此“强解释”的模式并不适合荀子的“心之所可”。。弱解释方案近似于把“心之所可”看作是“长视的利己主义者”的选择,人基于满足长久性欲望的理性考虑,有克服当前欲望的动机。①黄百锐指出这是:“一个人当下的口腹之欲与一个人经由对长远利益的反思而生起的欲望之间的抉择”;“心之所可的东西最终要建立在那些能长远最能满足主体欲望之总体的东西的基础之上。”David B. Wong, “Xunzi on Moral Motivation,” in Virtue,Nature, 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 p. 141, p.142, p.141.在弱解释模式下,“心之所可”就与“欲望”一致,本质是以“欲望”作为道德动机的来源,只不过这一欲望加上了一重认识理性的加工[5]205。如果采取这一方案,则“任何通向自我转化的途径,皆必须从人的自利天性开始,而不是从能够独立地激发自利的心之所可的能力开始。”②这一方案具有非常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色彩。David B. Wong, “Xunzi on Moral Motivation,” in Virtue, Nature, 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 p.141,p.142, p.141.依据这一方案,荀子理论体系中第一个圣人如何能够在没有先设的礼法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道德转化并能制作具有道德属性的礼法,也仍然存在问题③在设置了礼法的前提下,普通人或许能够根据自身的认知理性能力去判断“遵守礼法”或者“不遵守礼法”何者是从长远来看更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但是对于设置礼法的圣人而言,没有外在的规范作为被认识对象以提供选择和参考,这一情况下圣人制作礼法似乎并不仅仅依靠基于对外在认识的利益考量,而要求某些内在性的构成使其具有关心他人的利益和欲望,从而制作含道德价值之礼法的动机。。
黄百锐由此进一步去探究一个人如何能够从以自利的情性欲望为行为动机转化出一种能够接纳和融合他人欲望和利益的道德动机。即“心之所可”的力量不仅是克服了欲望,而且是转化了欲望④在这个意义上,欲望不是被“心之所可”取代而消失了,而是在“心之所可”的基础上被转化为一种参与构成道德动机的“欲望”。。他提出了转化欲望为道德动机的两种可能:一种是穆勒式的在习惯过程中实现手段向目的的转化,但对于这一方案,则圣人如何能够在没有设定的“手段”的过程中实现转化仍然有问题⑤在穆勒(J.S.Mill)看来人们之所以把道德本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其实是出于某种习惯性的联想。比如金钱本身是快乐的手段,但是由于人们长期把金钱和快乐联系在一起,使得金钱逐渐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同样的在这里,也有可能道德本身是满足欲望的手段,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习惯性的关联使得道德成为了目的本身而悄然转化了本身的自利性欲望变为了对道德的欲望。参见[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黄百锐的另一方案延续了倪德卫以荀子之“义”为人特有的“义务感”的思路⑥倪德卫基于荀子的“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提出荀子的思想中包含对人之“义”的承认,由此其认为,道义论意义的动机和功利主义的动机在荀子这里可以共存,在不同层面独立发挥作用。但是倪德卫的“义务感”使人把某种义务当作道德义务来认识的淡出能力,而没有积极的内容。倪德卫:《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329-330 页。,他认为除了“义”之外,荀子的自然情性中有与道德“意气相投”的部分。⑦黄百锐认为,这种人之有义的能力(或者是情的能力)如果要发展为有道德内涵的能力,有三个要求:第一,当把其归结于人性时,与荀子的性恶论不矛盾;第二,这种能力本身没有道德的内容;第三,但是当义务产生的时候,这种能力又必须能够作为动机。正是这些先天内在于人的自然情感为人们最初的道德感养成提供了动机和条件,这些情感并不天然是道德的,但是其能够在受到外在环境的感发下而激发出转化为道德动机的可能。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个外部环境即圣人设立的礼乐;而对于制作礼乐的圣人而言,是在人之“群”的生活状态中实现情感的积累和由知之能力带来的道德自我转化。由此,黄百锐说明了自然欲望得以转化的内在依据,为性恶之人道德的初始转化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也为我们探寻荀子的道德动机来源提供了线索。
本文将延续黄百锐的这一思路,探析荀子性恶论结构中自然存在于人之特质何以与道德“意气相投”而有转化为道德的可能。尤其以“情性”为重心,探讨“心之所可”如何能够基于“情”转化“欲望”,最终在弥合“心”和“欲”的前提下提供道德动机。在此基础上,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荀子的政治哲学其实是在因顺人情的基础上谈论礼法之制的。
三、心与欲之间:基于自然情性的荀子道德动机再探
荀子在《性恶》篇指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人之性生来有好利的欲望;也生来具有“情”的内容,而如果因顺这种自然的欲望和情性,则会走向乱。
其中“情”在荀子那里是个比较复杂的范畴[6]55-60。荀子既承认自然之情性有倾向于恶的一面,如“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性恶》)“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苟》)若是顺情或纵情,则会导向暴、乱,无法达到治。但荀子似也认为“情”有与道德相合的层面,如“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礼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乐论》)这意味着,在荀子看来“情”具有和礼乐相应的特征,礼乐本质是顺人情之制。如果是这样,那“情”就有可以激发出道德的可能。综上,荀子的“情”似乎包含可导向恶也可导向善的两重维度,或者说其本身是一个自然的存在,不包含实质的恶和善,但是又可以转化出恶或者善的动机。
事实上,“情”本身如果不加入道德判断,就是人自然而有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而言,它是没有善恶价值的自然存在,这也是一部分学者认为荀子是性朴论的原因[7]36-68,[8],这是从“性是什么”的角度去界定“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性本是“生之谓性”,是自然、中性的存在。但是如果从道德的角度看,“情”顺之则有变为恶的倾向,因此这并非是“性朴论”或说无善无恶、可善可恶论。荀子强调,如果“情”完全不加其他东西的引导,则“情”与人性中自然趋利的“欲”是一致的。荀子如此定义性、情、欲的关系:“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正名》)物双松解释为:“情之应也,情之感应也。”冢田虎则说:“情之应也,言情之所应物而动也。”[9]923李涤生解释了了性、情、欲三者之间的关系:“性成于先天之自然,情是性的本质,欲是情的反应,三位一体,有生命就有欲望。”[10]529他们都指出,这里是说欲望是情之感应的反映,欲的内因在于情,希望欲望的事物可以得到并去追求,这是不能避免的情感情向。其结果是依据自然欲望,则因为人皆欲求自利而趋向争夺混乱之恶,因此“情”与性恶论是相融贯的。“情”虽然包含了可导向恶也可导向善的维度,但是导向恶的倾向是自然而然的,而导向善的倾向容易被恶所遮蔽,其显现是需要辅佐以一定条件去激发的。而现实生活中的“情”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结构,就人之内部结构而言,“心之知”可以对情进行加工,又如与父母先天的血缘关系使得“情”包含孝情层面;就外部而言,人之群的生活状况、礼义法度等又通过被心所知影响“情”之存养的面向。因为“情”能够在“知”的影响下被激发出向善的那一面,作为“情之应”的欲在现实中也能有从自然所欲被“心之所可”转化为道德欲望的可能。
这里有必要再简单解释一下荀子对“心之知”能力的肯定。荀子认为人具有认识自我和外物的能力:“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变也。”(《解蔽》)也就是认知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而物理是可以被人所认知的。“心”则是认识的重要场所。荀子说:“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天论》)“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正名》)眼耳鼻口等是人的感觉器官,它们所获得的是杂乱的感觉,但是心具有认知理性,能够通过认知理性对杂乱的感觉材料进行加工,赋予其一个秩序,从而使得其符合道。在认知的过程中,荀子也指出要通过虚壹而静的方法使得心知道,从而能够达到一种最整全的认识状态,而有实现最高秩序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心通过“知道”,进而能够形成对外物的是非判断,从而有对善恶价值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心”意味着一种“知道善恶”的具有认识理性之心。
基于这种认知,“心”能够对自然的“情”进行选择,“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正名》)此时人不是被动地受到情的支配,而是通过“心”的功能把“情”中与后天理性之知相应的部分摘选出来。这意味着“心”不是去逆转自然情性,而仅仅是激发自然情性中与道德相应的那一部分。荀子说:“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正名》)杨倞注曰:“天性有欲,心为之节制”“此明心制欲之义”“所可,谓心以为可也”。[9]922即此时“心”参与进了自然之“欲”的现实构成。因此万百安认为荀子主张人的行为并不由欲望决定,而是由“所可”(by what he approve of)决定的。“所可”是心在知道的基础上对于事物形成了认可的限度,其“受乎心”,因此是“心之所可”。在这里“心之所可”参与进了人之“欲”,并使得自然欲望转变成了与“心之所可”一致的“心之所欲”。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之所以能以“心之所可”转化欲望,其根源和依据就在于“心之所可”与自然情性有相合的部分,由此“心之所可”作为道德动机并非去逆转人之自然情性,而是人之自然情性为其提供了道德动机其实内在于人性结构的依据。或者说,在这里“情”和“心之所可”实际上共同构成了人转化欲望的道德动机。
所以对于普通人而言,通过设置礼义法度的外在约束、通过心的认识能力,人可以认识到礼法的道德价值,进而以激发自然情性与“心之所可”相投的部分,使自身产生道德的倾向。由此普通人能够转化自身的自然欲望,实现道德转向,从他律到自律从而生成自身的道德主体性。
而对于圣人而言,由于礼义法度不是现成的而是被其制作的,一开始并没有外在的道德规范去对其进行道德教化,圣人原初性的道德转向与普通人有所不同。首先,圣人的认知能力特别强,尤其是其能通过虚壹而静使心能“知道”。但对于凡人而言,由于心可能被“蔽于一曲”(《解蔽》)而未必具有整全性的认识。因此圣人能够“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性恶》)那么,圣人“伪起”而“生礼义法度”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呢?仅从“知”去论证这个道德制作的源头则会遭遇第二部分我们业已讨论过的种种问题。因此,对于圣人而言,同样需要本于自然情性去转化出道德动机。而在没有先设立的礼义的前提下,这一转化的条件可以以人的其他特质去说明。荀子承认人还具有一些生而不同于禽兽的特点,如“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王制》)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总结出,“义”和“群”也是人的特性,“义”在荀子这里强调的是能够使人组成等级区分的社会,与“分”和“群”是关联的。对于人而言,人自然趋向于一种基于“义”之“分”的区别性群体生活,在这一社会状态中,个体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种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对于知性能力强大且习惯性思考生活状况的圣人而言,在这个具有天然区别性的群体生活条件中,激发了其自然情性中与道德意气相投的层面,由此引发其去寻求一种能够规范社会生活的恰当方式,而有了制作礼乐的道德动机。这便是完成从自然欲望到道德欲望的转向。因此圣人制礼的过程其实是在这种“群”的生活状态中“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的过程,其并非完全依靠独立认知能力完成,而是本于与自然情性的相称才具有最初的制作礼法的初始道德动机。
可见,无论对于圣人还是常人而言,“心之所可”之所以能转化自然欲望,是因为自然情性中有与之相合的部分,在必要的条件下为道德动机的转出提供了内在依据。认知理性并不是直接转化欲望,并不会遭遇休谟问题,这是“知”在本于“情”的基础上对“欲”的转化,最终表现为信念和欲望一致于符合道德的内在状态,“心之所可”也是“心之所欲”。欲望和信念的心灵和世界的符合方向不是相反而是在道德意义上实现了统一:依照休谟主义者,欲望是世界对心灵的符合,但此时欲望也是心灵对世界的适合,即欲望表现为与礼法道德的一致性;信念本来是心灵对世界的符合,但是此时也是世界对心灵的适合,即信念也是外部的礼法规范与人自然情性的符合。二者并不矛盾,而是成为一个统一的心理状态。这意味着荀子的思路本身可以为反思休谟的伦理困境提供思想资源。
四、从治民到化民:荀子政治哲学的道德内核
以上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荀子的政治哲学。荀子虽然强调“隆礼重法”的礼法之教,但是可以看到,“礼法”的设立本身不是完全外在于人的规范,而是与人自然情性相合的设立,而教化民众的可能也正是基于二者相合的基础。因此,“情”在沟通人性和礼法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也使得人们能够从对礼法的被动遵从转向主动追求,从他律走向自律,建构自身的道德主体性。
一方面,礼法是可以节制自然人性的,这是从礼法起初作为外部规范而言。在民还没有完成自身的道德转向时,礼法最基础的功能就是“治”,通过强硬的规范而去约束人们的自然欲望,从而避免社会因为人之自利走向乱,荀子指出:“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埶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性恶》)若不加礼法去规范自然情性,则会导致国家无序,无从治理,礼法是治道的重要手段。
另一方面,礼法在“治”的同时也潜在地发挥了“教”的功能。比如荀子指出:“礼以顺人心为本。”(《大略》)“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论》)礼乐能够作用于人的内在部分,如人心、人情,这意味着礼乐本质上是顺从人性的。荀子论述三年之丧是“称情而立文”(《礼论》),也就是礼义法度等是在与人情相称的基础上订立的。既然礼法与人情有相应的部分,那么人从被动顺从礼乐进而到主动转向礼乐是具有内在依据的。因此在行礼乐之治,礼乐之教的过程中,一方面其是顺人情的,另一方面其又进一步规范人的这种自然情感,使之能够转化为道德情感。[6]55-60
所以,当民在遵从礼法、被礼法教化时,其对礼法由一开始的对象化践行,进而在礼法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完成自身道德转向,从而礼法成为人内在道德状态的外在表达、自然呈现。礼法之治最终是从治民,本于顺民情、制民情而走向化民。因此使民化于道是荀子政治哲学最高的追求:“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不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埶恶用矣哉!”(《正名》)“道”在《正名》篇中指向的是王者之制名,即是礼法之规范,使民化于道在现实政治层面其实就是化于礼法,走向对礼法的内心认同和自觉遵从,民不随意制名以乱名,而是统一于礼法之治;这为政治统治的稳定性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由此荀子的道德哲学在政治上表现为礼法之治和教化的结合,在个体层面表现为对遵循礼法、认识礼法基础上的道德自觉转向。荀子虽然强调隆礼重法,但其仍是儒家而不是法家的根源就在于他强调的是外在礼法和人之内在情性的符合,强调人民依循礼法是具有内在道德根基的;而不是如法家单纯以礼法约束、规范人民,而不考虑道德的引导。荀子的政治思想保有儒家德治的核心要义。
五、余论
欲望被“心之所可”转化基于人之自然结构的内在部分,由此提供了道德动机的先天依据和后天途径,解决了荀子理论体系中道德动机的来源问题,可以对一些认为荀子因为不承认人性本善而丧失大本的批判做出反驳。
荀子并不像一些学者所批判那样因为“性恶论”而失去了儒家之道德的“大本”,只是其道德动机和道德的转向具有更为复杂的生成机制。与孟子设立先天的善端从而为道德提供现成依据不同,荀子不承认个体存在现成的道德动机和倾向,而是强调道德的渐成性;但是人的自然情性也仍然可以为道德的形成提供内在的结构支撑。在荀子这里反而是通过“心”认识活动的生成过程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肯定了道德建立的可能,这毋宁说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肯定了道德主体性。重新审视荀子在先秦儒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是十分必要的。而荀子一方面是强调道德主体的过程性发展,一方面也能因此开出政治上强调礼法,同时礼法又不失于顺民之本而化民的政治思想。虽然与孟子强调“仁政”不同,其强调的是礼法的层面,但其所重视的仍然在于从礼法之治走向礼法之教,教化万民,使民形成内在的德性,这与孔子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乐之教和德政是一致的。因此荀子既没有脱离儒家内外并重、强调道德之为根基的大本,也因为更强调外在礼法而开出了法家径路。
此外,荀子的思想还能为解决一些重要的伦理学问题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比如对于休谟问题的反思。而其本于自然情性为道德动机的初始转化提供可能的方案,结合了理性和情感两个维度,这一理解或许可以避免简单以情感和理性截然划分孟荀的方式,同时也能帮助于理解和调和当代德性伦理学之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径路①德性伦理学在于从主体德性品格出发为道德提供动机,当代德性伦理学大多从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出发基于理性主义基础而主张对人类的道德动机。当前,如斯洛特等学者也注意到从英国道德情感注意和关怀伦理学中吸取资源,这种基于行动者的德性伦理将对行动的评估奠基于情感,从而以情感寻求人道德的动机和人类普遍关切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思想中“情感”维度的挖掘及其与认知理性的关系具有有益的启发性。,为中西伦理学共同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致思路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基于休谟问题的框架去看荀子的道德哲学建构本身具有一定的视野局限性,实际上也许可以从一些不同于休谟立场的道德哲学,如道德实在论去寻找更恰合荀子思想体系和解释荀子道德动机的融贯方案,这或许是本文进一步探索的方向②相关讨论可以见于刘纪璐:《荀子如何调解“其善者伪也”与道德实在性的冲突——荀子的道德理论是道德建构论还是道德实在论?》,《人文杂志》2019 年,第4 期:第22-34 页。从道德实在论的立场出发,道德价值具有客观性,则认识客观的道德本身或可以提供动机,如此可直接以圣人对“道”的认识解释圣人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的来源。但如果从反道德实在论出发,则我们认为道德的建构需要基于某些人类的共同结构,由此就必须诉诸理性(康德主义)或者情感、欲望(休谟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