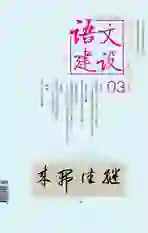把琐屑的素材升华为情理交融的经典
2022-04-13孙绍振
孙绍振
真正读懂苏东坡这首词的艺术和思想,在方法上有两点应注意:第一,他处于逆境,但是没有像同样处于逆境的词家那样直接写忧愁,要将其还原到词学历史中进行比较;第二,看他如何把琐屑的素材升华为情理交融的经典。
一
苏东坡流放黄州以后,所写第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前有小序,如下: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这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游玩途中遇雨,没有雨具,同行的朋友都为难免淋雨而狼狈不堪,苏东坡却没有感觉,坦然得很,即便淋雨也无所谓。不久雨就停了,狼狈的和不狼狈的都没有被淋。这件事作为素材,虽有具体的时间(公元1082年,三月七日),还有具体的地点(沙湖,今湖北黄冈东南三十里),但是,有意思、有诗意、有哲理吗?好像都没有。将其拿来写一篇札记,如《记承天寺夜游》那样的小散文都勉强,可苏东坡却把这样的遭际升华为词史上情理交融的经典: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此时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他从一个叱咤风云的中央政治大员变成了犯官,名义上还算在编制内,实际上不但没有任何职务,而且连住房、薪俸都没有着落,只能在一家僧寺中寄食。不久前还是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朝廷得剑皇帝欣赏,在文坛拥有欧阳修这类领袖人物的赞赏,在民间拥有众多粉丝,一下子沦落剑可能被政敌追杀的地步。一个公众人物突然处丁一种精神上孤独的境地,他须要适应。最初身边虽有一个儿子陪伴,但儿子并不能解脱那兀处不在的压抑着他的孤独感。朋友来往的书信稀少了,发出信札可能成为政敌诬陷的材料,于是叮嘱最可靠的密友阅后即焚。
这样的精神孤独是他不能忍受的,无人、无处诉说,唯一的解脱只能是在词作中抒发。但是他不像辛弃疾那样把恢复中原的壮志难酬的愤懑作直接抒发:“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落口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甚至不能把一腔郁闷正话反说:“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更不能像李清照那样,沉浸于个人的孤寂和忧郁,反反复复诉说着孤独的忧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苏东坡以词解愁,却不着一个“愁”字而尽得艺术和智者的风流。
二
《东坡乐府》卷上《西江月》白序说:“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词曰:“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似乎意味着接受噩运的安排,豁达淡定,寄情山水,超越礼法,放浪形骸,名士风流,此生足矣。
在札记和书信中,他多多少少有犯罪感,有痛苦甚至悔恨,但是在词中,他没有自怨自艾,没有怨恨,不宣泄痛苦,一心寻求无所作为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定风波》就是在这种探索中,达剑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统一的情理交融的境界。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下雨了,没带雨具,免不了淋雨,同行的人毫无例外都“狼狈”。苏轼却“不觉”,无所谓。有什么严重后果呢?如果有,就会有情节,至少可以写成散文。但是,不久天晴了,啥事也没有。这样的素材,苏东坡却把它写成了千古绝唱。
“莫听穿林打叶声”,写雨,又不直接写雨,而是写雨的效果,雨来得有声势,穿林打叶有声。但是,“莫听”,一不在意风雨,二不在意“狼狈”。不但不去看,而且不去听。
唐宋诗人笔下,雨的诗意,不仅是看,更多是听,因为听更有距离感。例如:“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李商隐)“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韩愈)“细雨梦同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李璟)“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苏东坡倒是写过暴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一看而过,精英文人更偏爱细雨:细雨隐含着心绪宁静,经得起默默欣赏,体验自我心情的微波。细雨不是漫不经心地一瞥,而是静静地观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看不见,听不见,兀声的雨才更经得起欣赏:“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兀声。”(刘长卿)“随风潜人夜,润物细无声。”(杜甫)这里渗透着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奥秘,寄托在景观中的情感是微妙的,情感越是微妙就越精彩。司空图号称“二十四诗品”,但是总体上倾向于“冲淡”,其意往往是“独”“淡”“默”,其境则是荒旷、虚寂——“素处以默,妙机其微”。
但是,用冲淡来形容苏东坡这样写雨,似乎并不确切。因为他的姿态并不冲淡,而是“何妨吟啸且徐行”,不是与雨拉丌距离,而是在雨中行走,连淋湿衣衫都不在乎。这已经很出格了,还要“吟啸”,吟是吟诗,啸是古代文人撮起嘴唇吹气,大致相当丁吹口哨。跑到雨中去吟诗,还吹着口哨,这种从容不迫的姿态、满不在乎的精神状态,是苏东坡的特立独行。李白在诗中再放肆地做出狂傲的动作,也不会在雨中唱歌。“竹杖芒鞋轻胜马”,穿一双草鞋,把竹竿当柺杖,也比当官骑马更轻松自在。
接着是“谁怕”,大白话,不怕淋雨感冒。有什么理由不怕?下面是情志的聚焦:“一蓑烟雨任平生”。“任平生”三个字,让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三月七日”的雨,也不是原生素材“沙湖道上”即来即逝的雨,雨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成了平生的雨,普泛的雨。从性质上说,它不再是让人狼狈的雨,不是来势汹汹的穿林打叶有声的大雨,而是变成了“烟雨”,烟就是雾,蒙蒙细雨。这在唐诗中早成传统意象,让人赏心悦日。例如:“江山跨七泽,烟雨接三相”(崔湜),“巫峡苍苍烟雨时”(刘禹锡),“千里枫林烟雨深”(元结)。这里的“烟”字很奇特,它本义是形而下的人间烟火,是没有诗意的,而“烟雨”就很高雅,“江上柳如烟”(温庭筠),烟带上春天的柳色更高雅。而烟与云结合在一起就又不同了:过眼烟云,有了贬义。这里的烟雨和“平生”联系在一起,就与苏东坡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生命的自如、自在、自得蕴含在“一蓑”之中。现实的雨要用雨具来遮挡躲避,而词中烟雨只要“一蓑”,且不用来遮挡,而是逍遥在细雨中,不是一时,而是一生。这“一蓑”是漁翁的传统意象。“蓑”本来是名词,这里用作量词。同样的词法有:两袖清风,一代风流,一鼓作气,一头雾水,一帆风顺,一叶知秋,一斑窥豹,一唱三叹,一笔勾销,一步登天,一筹莫展,一发千钧,一肚子坏水,一寸光阴一寸金,这种构词法的概括力很强。“一蓑烟雨”,加上“竹杖芒鞋”,一共四个意象,构成了朴素逍遥的图景,而且将令人狼狈之大雨,提升为享受人生之烟雨。
不得不承认,这个形象境界并非苏东坡的原创,而是化用了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然而,张志和的烟雨只是在顺境中逍遥,而苏东坡却是在逆境中吟诗吹口哨。“任平生”的“任”很传神,就是一生都在风风雨雨之中,顺其自然,潇洒走一回。“一蓑烟雨任平生”就这样成为人生观的格言。
这是情志交融的总结。前面的句子都是为这一句铺垫,在意脉上蓄势。为了这个肯定性的格言,前面的句法语气极尽变化之能事。第一句“莫听”是否定句,第二句“何妨”是反问句,第三句“竹杖芒鞋”是肯定句,第四句“谁怕”是反问句,蓄势已足,才用肯定句作思想和艺术的聚焦——“一蓑烟雨任生平”。这样多变的句法,并不是词牌规定的,而是苏东坡的匠心,以此丰富的句法结构,超越散文实写,高度概括为人生观,是直白,而不是隐含在景观之中。这样的直白,带来了理沦问题。
我国古典诗歌理论的主流,是情景交融,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尧臣),“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戴叔伦),“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图)。第一,抒情离不开景观;第二,情要隐藏在景观之中;第三,情不能直接表白出来。也就是司空图所说的:“不著一字”,才能“尽得风流”。严羽把抒情说得更形象:“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一切后来被王国维简单化为“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不但得到后世一致的认同,而且被认为是提高品位的不二法門。但是,诗人的感情难道只能以景来表达吗?显然不是。间接抒情并不是唯一的法门,直接抒情也比比皆是。《毛诗序》讲抒情就是比较强烈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显然是直接抒情,而且是强烈的感情的直接抒发。借景抒情并不全面,为什么具有这样高的权威?因孔夫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感情不能太强烈,以含蓄隽永为上。毕竟孔夫子的权威更高,间接抒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取得了优势,象外之象、言外之意高度成熟,乃为神品,在理论上积淀为中国特有的范畴“意境”。
直接抒情,不讲意在言外,不讲含蓄隽永,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法门,也有源远流长的传承。从《诗经》《楚辞》剑汉魏乐府古诗的经典,大都是直接抒情。
苏东坡在雨中吟诗长啸,就是强烈的直接抒情:“谁怕”,把感情直接倾泻出来,根本不讲究什么见于言外的不尽之意,不经营意境;“一蓑烟雨任生平”,把人生观的理念都讲出来了。这样的艺术,有别于间接抒情的意蕴。我们来细读文本。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料峭春风吹酒醒”,这里有想象的大幅度跳跃,原本只是吟啸徐行,并没有饮酒,也就谈不上醉,这是提示“吟啸徐行”的效果,富有陶醉到忘却现实风雨的意味。如果一直醉下去,意脉就停滞了。“料峭春风”刺激他醒过来,在程度上定性为“微冷”。寒冷的程度太强,与全词的智性情调不合。接着是夕阳斜照的暖色调,不太强烈的光线,二者对比中和谐互补,陶醉而清醒。归去,像陶渊明那样归去吧。很散淡,潇洒到“也无风雨也无晴”。前面“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观还承认有风雨,而这里却没有风雨,也没有晴天,料峭春风微冷也好,斜照夕阳温暖也好,都一样,没有区别。这就不是小序中那现实的雨,在佛家哲学的基础上,苏东坡把形而下的雨升华为形而上的雨,把散文升华为情理交融的诗。
三
苏轼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后世的共识。俞文豹《吹剑录》说: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这个说法,把苏轼为代表的豪放风格和柳永为代表的婉约风格加以对比,说得很感性、很生动,后世论者遂以豪放派的桂冠加之苏轼。但是从理论上看,这个说法只举了《赤壁怀古》一个例子,是不是全面呢?如果当时有人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拿出来,怎么办?让关西大汉执铁板引吭高歌,似乎豪放不起来,让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之,也婉约不起来。因为柳永的词,主要是红巾翠袖,浅斟低唱,充满儿女柔情。而苏轼的这首经典之作,既不能归入豪放,又不能归入婉约。那就说明,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并不能涵盖宋词艺术风格的全部。在这两种风格之外,是不是应该有第三种风格?
其实,即便柳永的词,也并不完全是儿女情长的,如《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对于这第三种风格,古人没有概括出来,可能是留给今人给予创新的命名吧。历史积累了这么多资源,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超越古人呢?这是机遇,也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