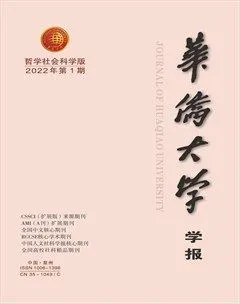侵权法中机会丧失理论之构建
2022-04-13冯德淦
摘要:因果关系不明案件一直以来都是侵权法最为棘手的难题。就因果关系不明的原因,分为偶然和必然的因果关系不明,前者属于证据层面的问题,后者则属于客观规律层面的问题。机会丧失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客观规律层面的因果关系不明案件。比较法范围内存在拒绝救济和赞同救济的两种方案,但这两种方案都存在局限性。我们应当区分风险提升和机会损失两种加害行为,只有后者才具有一般的可救济性。可救济机会的确定是一个评价问题,需要法官在个案中进行实质考量,结合多因素最终确定。未来侵权法损害赔偿理论,仍然应当坚持“条件说”,通过对损害层面的修正,将可救济的机会看做损害,以此维系因果关系。风险提升的加害行为,在例外情况下也应当予以规制,侵权法只有对风险提升和机会损失的行为进行区分规制,才符合实质救济的要求。
关键词:侵权法;因果关系;机会丧失;风险提升;机会损失
作者简介:冯德淦,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学(E-mail:deganfeng1990@163.com; 上海 200120)。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究项目(2021ECNU—YYJ017)
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22)01-0135-14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侵权法在责任成立的判断上,借助于事实因果关系所秉持的“条件说”,初步判断加害人是否需要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通常情况下只要借助于经验规则,我们就可以认定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事实因果关系,因而传统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受到太大的挑战。但在现代侵权法中,如果多个原因结合共同造成了损害,不能确定具体哪个原因导致损害的发生,此时加害人是否需要及该如何承担责任,在应对该问题时传统侵权法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如果在因果关系偶然无法认知的情况下,具体的案件中考虑加害人的主观状态,运用证明责任调整的方法,尚能妥善解决问题,但如果在因果关系能够借助于科学统计概率进行分析,此时仍然秉持“全有全无”的判定方法,似乎难以妥善平衡加害人和受害人两端利益。比较法上和我国学者对于该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许多新的责任承担理论应运而生。
机会丧失理论正是为了解决传统侵权法困境而被提出,通常以机会丧失为主题讨论以下问题:即加害人侵害受害人的某些获利的机会,或说破坏了受害人避免损害的机会,这在侵权法上是否可以得到救济。机会丧失必须与传统直接对机会侵害相区分,后者是对未来必然利益的侵害,在判定之上并不存在因果关系问题,而前者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能以概率的形式来
表达,或转述为丧失了多少机会,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对丧失机会的救济。针对这一广受关注的主题,理论上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机会丧失本身是否构成损害,机会是否属于侵权法保护的客体。为了合理地反思机会是否可以纳入侵权法中进行保护,下文将从传统路径解决方案出发,在其困境分析的基础上,对机会和损失的关系予以探究,并通过区分风险提升和机会损失,来对机会丧失理论予以构建,以求能在《民法典》施行的背景之下,对侵权责任编的解释适用有所裨益。
二传统路径和批评
(一)假设案例情况
甲因自身原因,突发心脏病。如果及时送到医院,根据医学统计的概率,他将会有80%获救的机会。就在救护车运往医院的过程中,行人乙因自身过错横穿马路,导致救护车发生交通事故,甲因此被耽误了20分钟,导致甲获救机会从80%降低到40%。在甲被送到医院之后,医生丙认为自己喝咖啡比甲及时接受治疗更重要,还错误认为甲心脏病发作并没有太大的危险。由于丙的重大过失又耽误了20分钟,此时甲获救的机会已从40%降低到0%。在该案中,甲最终因自己心脏病突发、乙过失及丙重大过失三个原因共同造成了甲的死亡结果。针对本案,乙和丙是否构成侵权,如果构成侵权,他们应该如何对甲承担责任,责任所对应的客体又是什么?
如果按照传统的事实因果关系所采纳的“条件说”判定方法,我们很难说乙或丙的行为是甲死亡的必要条件,因为在上述案件中,因果关系并不明晰,仅能够以统计概率的形式展现出来,无法确定地借助经验给出结论。此外,即便借助于多数人侵权中的“累积因果关系”“择一因果关系”和“共同因果关系”仍无法合理地解决假设案例的责任承担。上述案例并不是具体哪个原因导致甲死亡的偶然不確定性案例,而是科学技术导致的必然因果关系不确定案例。针对甲的死亡,就乙和丙的加害行为,我们并不能说任何一个行为是死亡的必要条件,因为在上述案例中即便乙或丙尽到自己合理的谨慎义务,我们也只能说在100个案件中,可以避免40个死亡情形。由于概率是根据统计得出的,我们并不能说乙或丙的行为是甲死亡的原因,我们仅可以说乙或丙的行为对甲的死亡有减损度,或说降低了生存机会。
传统理论的出发点是乙或丙的行为是否与甲的损害具有事实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乙或丙的行为和损害之间是否满足“条件说”的判断,因此,在判断的时候必须看是否如果没有乙或丙的行为,甲的损害就不会发生,只有在该种判断成立的时候,事实因果关系才能被证成。首先就乙的加害行为而言,传统理论一般认为,由于后续独立于乙和丙的重大过失,导致因果关系链条中断,因而乙无需对丙之重大过失导致的后续损害负责。就丙和损害的关系而言,从事实因果关系角度来看,虽然丙离损害更近,直觉上似乎是丙造成了损害,但即便丙谨慎治疗,在100例中也仅有40例能够获得救治,其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程度似乎还没有达到承担责任的要求。从这个层面来看,乙和丙与损害的因果关系通过经验均无法给出结论,只能借助于科学概率统计来作出揭示,该种概率性的揭示,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表现出机会可能性,但该种机会可能性是否可以纳入侵权法的保护,不同的国家给出了不同结论。英国法和德国法表现得相对困难,法国法和荷兰法由于侵权保护客体的开放性,在解释论层面并无任何障碍。
(二)拒绝救济的解决方案
就上述案例而言,英国法要求乙和丙的行为是损害的必要条件,此时乙和丙才需要对损害承担责任。法院在处理的过程中,一般会考量除了乙或丙的行为,是否有其他原因更有可能造成损害的发生。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乙或丙的行为和损害的因果关系概率都不超过50%。也就是说,即便没有乙或丙的行为,甲同样有可能死亡,因而无法证明乙或丙的行为和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针对这一教条,英国法在McGhee v. National Coal Board案的判决中,似乎质疑了这种严格要求条件的立场上议院在这里认为,如果受害人已经可以证明加害人对损害具有“实质性的助长”作用,那么足以建立因果关系。但这种对传统因果关系的突破,现在已经在Hotson v. East Berkshire Health Authority案,特别是在Wilsher v. Essex Health Authority案中又重新回归到原来的因果关系要求上。布里奇勋爵解释道,在McGhee v. National Coal Board案判决中,法官并没有就因果关系的认定创设任何例外,在该案中从概率平衡的角度,被告的行为和原告的损害一定程度上满足“条件说”的要求,但对该案的相关论证,还有许多不明晰之处。
德国法在证明标准上与英国法存在一定的差异,德国法在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上,一般要求达到高度盖然性,这意味着法院在处理事实因果关系之时,需要排除合理怀疑。许多案件想要证明存在因果关系十分困难,即使是引入一些因果关系特殊规则——诸如“累积因果关系”“择一因果关系”和“共同因果关系”等规则,也没有办法解决所有问题。德国法原则上不允许突破上述因果关系限定,但在特定领域,基于主观过错考量因素,可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具体而言,在个案中法官如果想帮助受害人,重大过失总是很容易发现的,尤其是在医疗侵权中,只要医生违反了医疗规则,那么实践中总可以认定为重大过失。在假设案例之中,因丙的行为违反了医疗规则,已经构成了重大过失,按照德国法的规定,应当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举证责任倒置之后,丙举证免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因果关系本身就无法明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其他案件中,如果丙的行为并不构成重大过失,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此时甲就没有办法证明丙和损害之间构成因果关系。同样的道理,在上述案例中,因乙并不存在重大过失,而且乙也不属于特殊领域的侵权,因而其对甲损害的因果关系同样难以证明。
(三)赞同救济的解决方案
“全有全无”的完全赔偿原则在现代侵权法中确实会受到许多例外的挑战,许多学者都对完全赔偿原则提出反思,认为应当突破“全有全无”的两极判定。从具体的路径选择来看,主要有两个路径,一个是通过对因果关系的突破来完成,另一个则是通过对损害的突破来完成。借助于因果关系来突破完全赔偿原则,主要是通过概率因果关系来完成,而借助于损害来突破完全赔偿原则,则主要通过机会丧失来完成。两种路径都从传统侵权责任构成的某一要件入手,通过对特定要件的修正扩大侵权法的救济范围。
概率因果关系理论主要源于奥地利等国家,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判决采用该种理论。在处理加害行为和偶然因素结合的案件之时,比德林斯基认为在该种案件中全部赔偿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全部不予赔偿同样也是不合理的。为了得到上述结论,比德林斯基认为应当类推适用《奥地利民法典》第1304条,根据该条规定,如果加害人和受害人具有共同过错,那么加害人就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来承担责任。在此基础上,比德林斯基认为受害人必须自己承担偶然因素造成的损害,因此如果加害人和偶然因素结合造成损害,那么受害人只可以向加害人主张部分责任。就具体的论证来看,概率因果关系总是伴随着损害的重新认定。然而在具体的设计路径上,则又体现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种方法。就实体法而言,主要是借助于损害额酌定制度,瑞士的学者主要是借助《瑞士债务法》第43条第1款对损害额酌定制度进行了规定,认为法官可以对损害的规模进行确定,一定程度上迂回地实现了因果关系的概率认定。就程序法而言,瓦格纳认为应当借助程序法的方法,来对比例责任进行解释,只要能够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7条确定特定加害人的加害份额,那么比例责任相较于全部责任就具有优先性。瓦格纳的上述观点也贯彻到医疗侵权之中,他认为在医疗侵权中重大错误情况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并不具有正当性。恰当的做法是,在任何医疗错误的情况下,对因果关系普遍降低证明标准,无论医生错误是轻微的还是严重的,医生都需要对自己造成的损害负责,而该种损害则由法官依赖于因果关系的概率性来确定。
机会丧失理论主要源于法国等国家,我国司法实践中亦不乏借鉴机会丧失理论的例子。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人的任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因其过错致该行为发生之人应当赔偿损害。”法国法并没有像德国法一样采用小的一般侵权条款,区分权利和利益进行保护,而是采用了宽泛的大的一般侵权条款,保护的客体同样为权利和利益,但在保护的方式上并没有在立法论层面予以区分规制。法国法上并不以权利为连接点来构造,而是采用了相对开放的模式。因而即便是机会丧失,同样可以纳入侵权法的保护客体之中,并且无需像德国法那样借助于违反保护性法规或主观者背俗来构造。荷兰法与法国法采用了相同的方式,因而将机会丧失纳入侵权法中保护也并无任何障碍。此外,许多国家也开始在裁判中逐步纳入机会丧失理论。在英美法系中,如1911年經典的英国案例Chaplin v.Hicks,该案中被告举办了一场选美比赛,在角逐的最后一轮中,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通知原告参赛,原告起诉被告赔偿损失,最终陪审团支持了Chaplin小姐获胜概率的保护。大陆法系中同样存在类似的趋势,1989年瑞士苏黎世州法院做了一个相对有影响的判决,一个病人因肿瘤进入苏黎世州医院,却由于医生的错误诊疗,导致淋巴晚了7个星期才被切除,1年后病人死亡。最终法院认为如果及时治疗可以获得60%的生存机会,最终法院支持了该种机会的救济。
(四)传统路径批判
无论是拒绝还是赞同救济的解决方案,在实践中都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前者以“全有全无”的方式展开,许多事实因果关系没有办法达到要求的损害,无法在“全有全无”模式中得到救济。后者以概率因果关系或机会丧失突破完全赔偿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打开救济阀门的风险,行为人很有可能动辄得咎。在上述假设案例中,需要注意如下几点:第一,乙和丙都使甲的生存机会丧失了40%,但就乙和丙单独来看,甲已经处于一种更有可能死亡的状态;第二,虽然乙和丙对甲生存机会的摧毁都是40%,但他们之间仍然存在差异,乙某种意义上仅提高了甲死亡的风险,但丙则毁坏了甲所有生存的机会;第三,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机会丧失在何种情况下需要救济?内部是否有区分的必要性?
如果一味秉持拒绝救济的方案,在德国法中只有加害人重大过失之时,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受害人才可以获得救济,而就一般过失的行为,并不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受害人无法获得救济。需要反思的问题是,过失程度真的可以直接导出侵权责任吗?有学者会强调让重大过失的加害人承担责任,主要是出于侵权法惩罚功能的原因,但单纯地依靠惩罚功能是否可以完全架空侵权法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强调对侵权法惩罚功能的坚守,那么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之间,仅因过失程度的细微差别,举证责任的分配就完全不一致,而且在上述假设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几乎就意味着责任的承担,这显然与侵权法惩罚功能所需彰显的比例原则不符。当然,还需注意的是,举证责任倒置一般情况下是为了解决事实存在争议的情况,只有在客观事实应该存在真相,但却因现实世界缺乏回溯可能性,没有办法查明到底是谁造成了损害。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通过举证责任的调整,让加害人承担责任在许多情形下是合理的。但如果像上面假设案例所描述的机会丧失情形,其实并不是证据层面的问题,每个行为人对损害的作用实际上是明晰的,各方主体之间基本也对导致机会丧失达成共识,该种不明晰往往是科学技术造成的,此时如果仍然坚持用程序法规定来解决,其正当性基础又何在。
英国法虽然在证明标准上较之于德国法要低,但即便如此,许多机会丧失的案例中,加害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未达到50%。在上述假设案例中,甲自身发病因素导致死亡的概率是20%,乙过错致甲死亡的概率是40%,丙过错致甲死亡的概率同样是40%。单独考察甲自己和任何一个加害人的关系,他们之间导致损害可能性的比例都是1比2,因而从概率上来看,每一个加害人导致损害的概率都大于受害人自身的因素,仅因有其他加害人的介入,就无需对损害承担任何责任,这种价值取舍是否合理确实值得怀疑。英国法一直以因果关系达到50%为界限,如果总是让低于50%的加害人不承担责任,这种做法是否总是合理?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德国法还是英国法,其实并非对机会丧失的问题没有解决方案,他们存在的问题是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在因果关系层面恪守证明标准的限定,这让许多损害没有办法得到救济,即便加害行为已经对损害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这显然与现代侵权法理念相背离。
赞同救济的解决方案则又呈现出不同的问题。法国法、荷兰法,又或是奥地利、德国和瑞士学者所提倡的解释方案,似乎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所有的机会丧失都可能被纳入到救济的考量,救济的闸门打开之后,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将受到严重侵害。第一,就奥地利等国家通过共同危险行为引入概率因果关系,这种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择一因果关系问题而衍生的,继而开始处理加害人和偶然因素结合的案件。但在奥地利司法实践中,概率因果关系主要是为了解决证明困难的案件,诸如共同危险行为,或是偶然因素和加害人结合的案件。这些案件其实仅是证据的问题,由于现实世界證明的困难,人们没有办法查明具体的加害原因,在这些案件中并不存在基于科学统计而形成的概率,案件中的概率只能借助于法官的自由心证来完成。第二,就法国等国家侵权法保护客体扩张的方法,通过不区分权利和利益保护,直接将机会丧失纳入到侵权法保护范围中。这种解决方案带来的疑惑是,是否所有的机会丧失都需要保护。在假设案例中,乙的行为并没有直接造成死亡的结果,其是否需要对损害承担责任?第三,如果在假设案例丙的行为只导致了甲生存机会降低30%,言外之意甲还有10%的生存机会,如果此时甲最终并没有死亡,此时乙和丙是否需要对甲丧失的机会进行赔偿?这些问题在权利和利益不区分保护的模式下,似乎都有救济的可能性,但该种做法是否合理,则需要进一步进行推敲。
三风险提升和机会丧失
机会究竟是什么?机会丧失是否需要予以救济?是否所有的机会都可以纳入到侵权法的救济范围内?这些问题都是机会丧失理论需要解决的。为了发挥侵权法救济和预防功能,一方面我们必须得承认某些机会的丧失构成损失,侵权法对此需要予以救济,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得承认,并不是所有机会的丧失都可以纳入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中。为了理清机会和损失的关系及将可救济的机会单独提取出来,下面将对机会和损失分别进行阐释,以确定可救济的机会具备哪些特征。
(一)机会的基本内涵
所谓机会,从法律层面来理解,一般可以将之定性为获得利益或避免损害的可能性。机会往往是与风险相伴而生的,通常情况下我们说获得利益的机会,实际上反映的是获利可能丢失的风险,避免损害的机会则体现的是损害可能发生的风险。探讨机会丧失是否需要予以保护,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加害人造成的风险是否需要予以救济。
从机会的本质来看,机会总是伴随着假设及数学概率计算。如果利益已经丧失或损害已经发生,此时机会已经不复存在,但如果回溯损害发生的进程,损害的发生实际上也是机会丧失。但机会丧失问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机会是否会丧失存在不确定性,只能够借助于科学统计来确定可能性的大小。因此一切原则上可以查明的,仅是因证据问题无法确定的案件,都不是机会丧失的问题。这里主要有两个典型的反例,一个是缺乏加害行为案件,另一个则是共同危险案件。就缺乏加害行为的案件而言,如瑞士法曾经有一个例子,即一个房间内有四个人曾经进去过,最终房间的主人丢失了一个钱包,不能确定具体是谁盗窃了钱包。再如有一个小镇,只有四辆出租车,三辆蓝色出租车由一家公司经营,一辆黄色出租车由另一家公司经营。如果一个人在不知道其颜色的情况下被四辆出租车中的一辆撞倒,这些都不是机会丧失的问题,仅是证据证明的问题。就共同危险的案件而言,如经典教学案例,甲乙两人由于过失在山顶分别落下一颗石头,刚好砸落在路过的丙头上且造成丙的损害,此时可以确定甲和乙中只有一个人造成了损害,但不能确定具体是谁造成了损害。共同危险案件同样不是机会丧失问题,而是由于证据缺乏造成的责任承担困境,且不论共同危险案件是否需要引入比例责任,即便需要引入比例责任,也不是以机会丧失理论作为根基。
机会到底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其本身可否被当作保护的客体,这在理论上受到两种批评:一种批评认为机会实际上是概率的字义表达,它源自于人们的幻觉,仅是因缺乏信息而产生的主观不确定性,客观世界中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即便我们没有办法具体知道,但并不能改变其必然性;另一种批评则认为世界上就不存在机会这个东西,我们只能失去生命或相关金钱利益,并不会失去生存机会或获利机会,失去机会是一个人造的概念,在具体损害没有发生之时,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受害人遭受了损失。从现实世界来看,上述两种批评意见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分析,其实抽象性和不确定性并不能彻底否定机会作为侵权法保护客体的可能性,理论上仍然有建构的可能性。
就第一种批评意见而言,法律并不总是要关注哲学世界的真实本质,法律关注的更多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从这个层面上看,机会概念对于我们理解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许多案件中,无法确定最终的加害原因不仅是证据问题,许多情况下是客观世界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因而机会概念成为我们理解客观世界的重要元素。基于法律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二分观点,第一种批评意见并不可取;就第二种批评意见而言,机会实际上是具体损害發生进程中的抽象存在,从正当性角度,没有人会怀疑我们假设案例中丙对甲机会侵害保护的必要性。当然,丙也许会提出如下抗辩,即便自己谨慎治疗,甲也未必一定获救,又或即便自己不谨慎治疗,甲也未必死亡。在该种情形下,对甲生存机会保护的合理性则存在疑问。不过从统计学概率分析的角度来看,生存机会与最终的死亡结果之间确实存在内在联系,尤其是在加害人将受害人仅有的生存机会降低到几乎没有的时候,或说机会的变化对于受害人具有重要意义之时,基于对生命权或其他终局权益保护的要求,我们不能忽视对受害人机会的保护。因而,即便客观世界中机会并不是实然存在,但在法律世界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机会概念是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机会的丧失就应当予以救济,到底哪些机会的丧失需要予以救济还需要结合损失要素进一步分析。
(二)损失需要限定
机会丧失在客观世界中无处不在,如果对所有的机会丧失予以救济,会不恰当地打开纯粹经济损失救济的阀门。此外,不加区分的救济,有时还会造成十分滑稽的现象,例如在假设案例中,虽然乙降低了甲的生存机会,但经丙谨慎治疗甲并没有死亡,此时如果仍然对甲就乙的行为所丧失的机会予以救济,其中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更为极端的案例是,假设案例中乙和丙的过错均存在,但丙并没有使得甲最后的40%生存机会完全丧失,而是仅降低了甲20%的生存机会,最终甲并没有死亡,此时如果让乙和丙对自己造成甲丧失的机会承担责任,似乎也没有道理可言。因而,机会丧失的问题至少需要在损害最终发生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予以考量是否需要对它进行救济,这种损害既可以是健康权受损,也可以是生命权受损。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对如下两种情形予以谨慎,一种是看起来像机会丧失案件,但本质上是“共同因果关系”的案件,另一种确实是机会丧失案件,但本质上仅构成风险,并不能看作受害人损失的案件。下面将先对这两种混淆情形予以分析,在此基础上再阐明机会损失的特征。
1.我们要区分“共同因果关系”案件和机会丧失案件。在许多案例中,加害人的加害行为虽然存在先后顺序,但各个加害人和损害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并不需要借助于概率统计来确定机会。在典型的“共同因果关系”案件中,各个加害人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损害的发生,每个加害人和损害之间都满足“条件说”,都是损害的必要条件,事实因果关系的证明并不存在不确定性。在机会丧失案件中,虽然我们可以笼统地说几个加害人造成了损害,但损害到底会不会发生及损害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其中具体的细节由于信息的缺乏,我们并不能彻底的探究清楚。因而“共同因果关系”案件和机会丧失案件属于不同的类型,前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证明的障碍,至于究竟承担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则是一国法价值选择的问题。我国《民法典》第1172条对“共同因果关系”案件有明确规定,虽然与比较法上立法例存在差异,但亦有其合理性。
2.我们要在机会丧失中区分风险提升和具体损失。个案中,如果加害人的行为降低了受害人的机会,但该种降低并非实质性造成损害,此时救济的必要性就值得怀疑。在假设案例中,受害人丙因自己心脏病发作处于危险之中,乙因自己的过错引发了交通堵塞,乙的行为虽然降低了甲的生存机会,但乙并没有导致甲生存机会完全丧失,甲依然具有40%的生存机会,甲所面临的危险仍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因而从具体的理解上来看,乙仅增加了甲的风险,并未造成具体的损害。此外,从对最终呈现出的损害预见可能性角度来看,乙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会造成损害,存在主观上预知的不确定性,因而缺乏让乙承担责任的正当性。丙则与乙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区别,丙较之与乙更加接近所呈现出的损害,并且丙使得最后的机会完全丧失,主观上也能预见损害的发生。从侵权法保护受害人权益的角度来看,或许丙造成的损害并不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全部损害,但丙所造成的机会丧失确实有保护的必要性。因而,通常情况下,导致机会完全丧失的加害人承担责任的必要性要比前置阶段降低机会的加害人高。当然这仅是给风险提升和机会损失的区分提供了一种参考的评价因素,具体的鉴别还有赖于多因素共同协作评价。
上述两种区分有其必要性,第一种区分主要借助于是否存在不确定性来判别,这在技术上相对容易,第二种区分则相对有一定的困难,在许多情形中,很难具体划分究竟哪些是风险提升,哪些是具体造成损害。例如在假设案例中,因乙的过错,甲的生存机会被降低到只剩10%之时,或更低但并不是零的时候,此时乙究竟是风险提升还是造成损害,在判断上则更加具有困难性。英美法系在判例中引入了机会实质消灭的概念,意在从根源上去对机会丧失进行评价。我国司法实践应当借鉴上述做法,引入机会实质性消灭的概念,法官在具体判定加害人的行为到底是风险提升还是机会损失之时,需要进行实质性判断。一旦加害人的行为导致受害人的机会几乎不存在之时,或法官认为加害人对受害人呈现出来的损害具有实质作用之时,机会的丧失对受害人具有重要意义的情况下,该种机会的丧失予以救济的正当性程度就越高。当然无论是导致机会几乎全部丧失,还是机会丧失对受害人具有重要的实质意义,都是衡量的价值判断方向,并不必然的可以被认定为机会损失。就此而言,到底哪些机会的丧失可以纳入到侵权法的救济范围,则还需要进一步反思。
(三)可救济的机会
正如上文所述,比较法范围内就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大的一般条款模式,另一种则是以德国为代表小的一般条款模式。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之间的差别,学者之间已经形成了共识,在我国也不乏学者对于该问题予以深入研究。但两种模式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仅停留在立法论层面,而在解释论上两种模式并没有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即便在法国也不可能对所有的利益都同等保护,立法之所以没有对此加以区分,实际上是权利和利益难以区分的困境造成的。司法实践却无法像立法那样逃避该问题,因而对权利和利益区分保护的构造同样贯穿在法国实践之中。我国《民法典》第1164条和第1165条,在立法形式上与《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和第1383条起到相同的作用,勾勒出我国侵权法保护范围大的一般条款模式。但在理解上,我国司法实践也宜遵循德国法的做法,在具体运用之时,仍然需要对权利和利益区分进行保护。对于权利的保护,一般情况下采用的是完整保护模式,但对于利益的保护,解释论和实践中我们需要对利益进行实质评价,以区分哪些利益需要保护,哪些利益需要为行为自由让位。
生存机会或获利机会对于民事主体的价值不言而喻,對于机会的保护与避免让受害人遭受最终的损害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各国宪法要求法律对个人的权利进行保护,对于机会的保护往往直接关系到最终权利的保护,尤其在许多案件中,仅只存在机会之时,对机会进行保护的意义则更为明显。侵权法在必要的时候必须对机会进行保护,承认机会本身就构成一种损害,这也是宪法的基本要求。但在对机会的保护程度上,有的学者认为只要是机会就应当给予保护,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当在机会内部予以区分,部分机会需要保护,而部分机会则不需要保护。就哪些机会需要予以救济,我们要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如果损害最终并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各个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并没有最终造成损害,他们所造成的机会丧失最终也并没有导向现实的损害,那么加害人无需对机会丧失承担责任;第二,如果损害最终发生了,并不是所有造成机会丧失的人都需要承担责任,应当严格区分风险提升的加害人和造成损失的加害人,前者原则上无需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后者则需要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第三,导致机会丧失并且属于造成损失的加害人所赔偿内容,并不是具体最终所呈现出的损害,尤其在生存机会丧失之时,加害人赔偿的内容并不是生命权,仅是自己所侵害的机会可能性。
除了上述几点前置考量之外,我们还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在具体判断机会损失之时,应当采用何种判定方法。现阶段,我国学者在讨论机会丧失之时,往往会将本来属于评价的法律问题,直接转化为数学概率计算的问题,并且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数学统计知识,最终得出一个需要救济的机会比例。客观地说,上述讨论对于我们认识机会及确定机会的大小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但机会是否需要救济,往往并不能以机会可能性的大小作为唯一参考因素。比较法上存在许多判例,对于机会丧失小的进行救济,而对于机会丧失大的却没有进行救济。例如在Herskovits v.Group Health Cooperative of Puget Sound案中,受害人自己染上肺癌,由于医生的医疗过错,将受害人可以存活5年的概率,从39%降低到25%,虽然概率降低只有14%,但联邦最高法院最终以6:3的比例,认为应当对受害人的生存机会进行保护。但在Hotson v. East Berkshire Health Authority案中,13岁的受害人从3.5米处摔下来,如果医生谨慎治疗受害人有25%的机会骨头不会坏死,但最终由于医生没有谨慎治疗,最终这25%的机会丧失,上诉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受害人的赔偿主张。从上述两个案例来看,机会丧失的多少及机会减少到零,虽然和机会损失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仅能作为考量因素之一,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必然和机会损失直接关联。
综合来看,机会丧失的救济绝不是一个数学计算的问题,它应当是一个综合考量的评价问题。从现阶段比较法和我国案例中所呈现出的考量因素,以生存机会丧失作为讨论对象,至少如下几个判断需要予以在个案中考量。第一,将机会直接降低到零的加害人,对机会丧失予以赔偿的必要性要高于一般机会降低的加害人;第二,受害人所面临的固有风险越大,且医生所采取的治疗措施越容易之时,机会丧失的救济必要性也就越大;第三,机会的丧失对于受害人具有决定意义,而且机会丧失的保护对于提高医生医疗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之时,该种机会丧失予以救济的必要性也就越大。当然机会纳入侵权法的救济最终的考量还需要结合个案裁判中不断发展出来的评价因素及充分参考鉴定机构给出的相关度认定等一系列指标。这种评价应该在个案中予以公开化,而不是像我国司法实践中现阶段的操作,直接依照公平原则来予以判决。
侵权法在机会丧失问题的处理上,其实不单单是侵权保护客体的问题,在许多案件的评价上,需要结合过错的认定和客体的保护两个层面共同来认定,两者之间呈现出动态互补的态势。如果加害人存在重大过错之时,其所侵害的机会保护必要性,较之于一般过失所侵害的机会利益要高很多。当然加害人过错的认定,其实也和机会的重要性呈正相关联系,例如重病的救济则需要医生更加谨慎,而轻病的救济对医生谨慎程度的要求则相对低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机会丧失的保护在未来裁判之中,需要以上述评价根基作为依据,在个案中予以单独评价,审慎认定需要予以救济的机会损失。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要件式的侵权构成认定,通常情况下只能为责任的成立提供大的方向,具体个案的裁判还需要注重各个要件之间的连通性,协作完成最终的评价。
四机会丧失理论的构造
(一)以“条件说”判定为基础
就侵权责任承担的问题,侵权法主要考量损害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传统侵权理论往往是先确定具体的损害,然后再判断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德国民法典》第249条确立了“全有全无”的赔偿原则,在损害的计算上采“差额说”的方法,该种做法对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该理论的影响下,传统民法针对责任确定的技术手段就是因果关系,分别是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事实因果关系主要判断责任是否成立,而法律因果关系则用来判别责任的具体范围。事实因果关系认定上采“条件说”,在“条件说”的主导下,加害行为需要和损害之间满足“若无则不”的判断,加害人才需要承担责任。机会丧失救济问题,最大的争议集中在事实因果关系的判定上,这主要是因加害行为和表现出来的损害之间有时不能直接满足事实因果关系。如何在该种困境下对损害赔偿问题予以重构,则是现代侵权法理论需要直面的问题。
在机会丧失的案件中,传统理论一般将最终呈现出的利益损失看做是加害人造成的损害,按照该种损害的认定,加害人和损害之间难以认定存在事实因果关系。为了化解上述困境,许多学者对传统理论进行突破,开始反思完全赔偿原则,并且提出概率因果关系理论,主张利用比例责任的责任承担方式代替完全赔偿原则。司法实践中也不乏裁判认为应当放弃事实因果关系的判定,直接用法律因果关系进行规范评价,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在对损害的范围予以确定。但放弃传统侵权法所坚持的“条件说”,引入概率因果关系理论,这种做法与侵权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侵权损害赔偿的根本要义在于矫正正义,而不是分配正义,只有损害是加害人造成的时候,加害人才需要对损害承担责任。概率因果关系理论放弃了直观的条件判断,转用概率性的因果关系理论,在司法实践中会将损害赔偿架构在分配正义之上,如果操作不当反而会滋生主观任意性,甚至有可能将过错责任演变为公平责任。从理论的选择角度,这应该是万不得已的方法,以这种激进的方式改变侵权法的形式将是立法者的权力,而不是法官的权力。因此,现阶段我们仍然应当在传统理论下构造机会丧失案件的解决方案,而机会丧失理论恰恰迎合了传统理论。
机会丧失理论最大的价值在于,其将因果关系判定的难题,通过对损害概念理解的变革,直接转化为损害赔偿层面的问题。在假设案例中,丙导致甲丧失了40%的生存机会,这40%的机会丧失本身就是损害,因而加害人和损害之间因果关系概率是100%。机会丧失理论将因果关系问题转化为损害确定的问题,在该种转化之下,事实因果关系所秉持的“条件说”理论得以继续沿用。不过,在实践中,加害人很有可能提出“即使没有自己的行为,损害同样可能会发生”的抗辩。基于类比的思想,其实不难发现,该种抗辩缺乏合理的正当性支撑。我们可以通过侵害传统具有经济价值的标的作为类比,如果侵权行为人毁坏或窃取了受害者要在赌场中花费的金钱,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因为受害者可能会损失或花费金钱,而辩称自己实际上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在传统具有经济价值的标的案件中,因为传统标的本身就是可救济的损害,因而在处理之上并不存在困难。同样地,机会丧失理论将机会的丧失当作一种损害,该种机会本身对受害人具有重大的价值,就如同传統具有经济价值的标的一样,不管从传统视角看该种机会是否具有概率性,侵权法都需要对此予以救济。因而,在机会丧失的处理上,加害人提出“即使没有自己的行为,损害同样可能会发生”的抗辩并不能作为自己免责的理由,因为机会本身就是一项利益。
(二)区分风险提升和机会损失
我国学者在继受德国法的基础上认为权利和利益的区分提出了三个教义学标准,分别是“归属效能”“排除效能”和“社会典型公开性”。学者们认为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标准的就是权利,如果无法满足上述三个标准的就是利益。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认为权利应当在过错原则下给予全面的保护,而利益则应当采取例外保护的态度,主要集中在如下两种情形,分别是违反保护性法规和故意违反善良风俗。现阶段机会并不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其利益或权利轮廓也仍然存在许多不明之处,从理论接受性上考量,很难将机会上升为一项权利来保护。综合来看,机会确实对主体具有价值,但其本身也仅可以定位为一项利益。不过在利益的保护上,是否一定需要在违反保护性法规和故意违反善良风俗情况下,才需要予以保护,则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有些利益在轮廓上已经接近权利,和具体权利有紧密联系,对于利益主体具有重要价值,加害人也能够预见到利益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并且加害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损害的发生,此种利益当然需要给予一般性的保护。机会的保护究竟应当保护到何种程度,何种机会可以予以保护,何种机会无法予以保护,应当是侵权法解释的一个难题。机会保护上同样存在着一般性的风险提升和机会损失的差别,前者属于一般利益,后者则属于需要特殊保护的利益。
从形式上看,如果以最终呈现出的终局损失作为损害的话,风险提升和机会损失之间似乎并没有区别,他们都降低了受害人的机会。不过正如上文所述,因两者发生的阶段不同,从加害人主观对损害的预见性角度及客观最终损害发生的可能性角度,风险提升和机会损失之间仍然存在本质区别,我们仍然有必要对此加以区分。现代社会纷繁复杂,风险也是多种多样无处不在,我们知道我们总是面临着别人给我们造成生产生活上的风险,自己也在给别人造成各种各样的风险。因而,作为社会中的主体,我们总是将风险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不会将所有的风险当做是损害。如果受害人想要对风险制造者提出索赔,必须依赖于风险已经转化为损害,也就是说风险最终实现,否则受害人无法对风险制造者提出赔偿请求。因而在具体侵权损害救济之时,风险提升的加害人只有与最终呈现出的损害,诸如受害人的死亡,或丧失的全部利益,具有一般性的事实因果关系之时,他才需要对损害承担责任。一如上文所述,机会损失与一般的风险提升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机会损失本身对于利益主体具有重要价值,是较为特殊的风险,其本身就可以直接看做是可救济的损害,因而加害人只需要与机会损失之间具有事实因果关系即可。
例如在假设案例中,丙造成了甲的机会损失,但乙仅增加了甲的风险。即使没有丙的行为,乙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因他并不是甲死亡的条件,他同样没有侵害甲的生存机会,因为在乙的行为之后,甲仍然有40%的生存机会。在司法实践中,乙一般会提出如下抗辩:第一,甲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其心脏病发作使自己处于异于一般常人的危险中;第二,自己并没有侵害甲的生存机会,因为甲仍然有很大的生存机会,其所面临的风险仍然在合理限度内。丙则不同,丙的行为导致甲生存机会实质性减少,并且最终导致死亡,丙的行为排除了甲其他生还的可能性。当然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丙作为最终侵害机会的加害人,应当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最终的损害,从预防损害发生的角度来看,丙的行为对于损害具有实质性意义,因而使机会彻底丧失的加害人的行为,应当有纳入侵权法规制的可能性。归结而言,在分析具体案件之时,判定机会丧失是否构成损害,应当结合机会保护的重要性、受害人所面临风险大小、避免机会丧失方法难易程度、加害人的可归责性和加害人对机会的认识程度等因素综合实质考量,这也是一项利益纳入侵权法保护的限制途径,避免侵权法救济的泛化。从这一角度我们也不难看出,相较于传统绝对权的保护,机会纳入侵权法的救济,在许多因素考量上要更为严格。
(三)多元化机会救济途径分析
生存机会或获利机会对于民事主体的价值已经不言而喻,承认对机会损失的保护有利于实现侵权法的预防功能,在特定的情形下,亦可以避免在加害人存在违法性和过错之时,因为因果关系不明晰无法承担责任的窘境。因而无论是从宪法保护民事权利的角度,还是基于侵权法自身固有的预防功能,法律应当将机会纳入考察的范围。从现阶段的司法实践来看,其实我国并不排斥对机会损失的救济,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往往直接认定因果关系成立,然后再在最终的损害计算上确定一定的比例。其实德国学者也不乏如此主张,认为可以对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加以放宽,从而将损害纳入救济的范围之中,最终在损害的计算上,也就是损害范围的确定上再予以限制。上述方法虽然从结果上来看,确实可以解决一部分机会丧失救济的问题,但在具体操作上依靠举证责任倒置来完成,随后又基于公平思想对责任范围进行限定,该种做法已经偏离了规范意旨。此外,这种将机会保护问题借助于程序法来解决的途径,终究没有办法妥善地区分哪些机会需要予以救济,哪些无需救济,因而仍然应当直面机会保护的正当性。
如前文所述,并非所有的机会都应当予以救济,在具体操作之时,我们应当合理区分造成风险提升和机会损失两种加害行为,前者属于一般化的社会风险,后者则是可救济的机会。在判断哪些是需要救济的机会之时,则需要结合机会保护的重要性、受害人所面临风险的大小、避免机会丧失方法难易程度、加害人的可归责性和加害人对机会的认识程度等因素综合实质考量。对于可救济的风险,侵权法在具体的操作上,应当像对权利进行保护一样,只要加害人过错造成机会损失的,就应当予以赔偿。我国《民法典》第1164条和第1165条在保护范围上并没有采用小的一般条款,解释论上将机会损失纳入救济并无任何障碍。就侵权损害的构成上来看,因为机会损失本身就是一种损害,也是侵权法上可救济的损失,因而对因果关系的判定并无突破的必要性,仍然应当坚持传统理论所构造的“条件说”,采用“若无则不”的判定方式。对于一般化的社会风险,原则上无需纳入侵权法的救济范围中,但机会终究属于一项利益,在例外情况下依然应当予以保护。该种区分保护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来自于我国司法实践在处理权益保护时的选择。
在机会丧失的保护上,区分风险提升和机会损失,分别赋予不同的保护力度,该种做法有利于避免风险提升者承担责任的不确定性,防止诉讼闸门不恰当的打开。如前文所述,在机会损失的认定上,我们应当结合机会保护的重要性、受害人所面临风险的大小、避免机会丧失方法难易程度、加害人的可归责性和加害人对机会的认识程度等因素综合实质考量,以此来确定哪些是需要全面救济的机会损失。当然该种考量是各种因素之间的综合权衡,解释论上很难先验性地给出结论,需要法官在实践中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来予以判断。在区分机会损失和风险提升的基础上,对机会损失一般采取全面保护,对风险提升我们则采取例外保护的方式。我国学者也主张,在加害人违反保护性法规和故意违反善良風俗情况下,侵权法依然需要对受害人的利益予以保护。在机会丧失案件中,经常出现的是故意违反善良风俗破坏机会风险提升,该种加害行为依然需要予以规制。因此在具体操作中,风险提升的加害人也并非完全不予以规制,如果其在主观上符合故意背俗条件的,由于主观不法程度较高,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客观利益保护强度欠缺要件,实践中针对该种情形,也应当纳入到侵权法规制范围中。当然未来具体的发展还有赖于法官在具体案件中,不断地进行类型研究,合理地界定哪些机会需要予以救济,哪些机会仅是一般风险。
侵权法中的机会丧失理论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拒绝救济的解决方案和赞同救济的解决方案自身都存在一定缺陷。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应该严格区分风险提升和造成机会损失的行为。前者属于一般化的社会风险,原则上加害人无需进行赔偿,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需要赔偿。造成机会损失的行为不同于一般风险提升的行为,它有自己的特定含义,需要结合机会保护的重要性、受害人所面临风险的大小、避免机会丧失方法难易程度、加害人的可归责性等因素综合实质考量。如果丧失的生存机会对于利益主体和提高医疗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该种机会利益有一般化保护的必要性,侵权法应当对之予以一般化的规制。在上述区分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明确机会丧失理论是损害层面的问题,并不涉及因果关系的修正,侵权法所秉持的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并没有受到太大挑战。出于矫正正义的要求,我们未来仍然应当坚持事实因果关系“条件说”理论。我国侵权法在立法上选择了大的一般条款模式,我们不能忽视条文固有的包容性,机会丧失理论纳入我国侵权法框架中并无太大障碍。此外,我国解释论上亦有向小的一般条款转型的趋势,因而我们亦应当注意一般风险例外情况下纳入规制的可能性,多元化的救济途径更加有利于我国侵权法功能的实现。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Opportunity Loss in Tort Law
FENG De-gan
Abstract: The cases of unclear causality have always been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in tort law. In terms of causes, the unclear causality can be divided into accidental and inevitable unclear causality. The former belongs to the level of evidence, while the latter belongs to the level of objective law. The theory of opportunity loss is mainly to solve the cases of unknown causality at the level of objective law. Within the scope of comparative law, there are two kinds of remedies: denial and approval, but both of them have limitations. We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risk enhancement and opportunity damage, and only the latter is generally remedied. The determination of remedial opportunity is an evaluation problem, which requires the judge to make substantive consideration in the case and finally determine it in combination with multiple factors. In the future, the theory of damage compensation in tort law should still adhere to the “condition theory”. Through the remedy of the damage level, the opportunity that can be remedied should be regarded as damage, so as to maintain causality. The injurious behavior of risk enhancement should also be regulated in exceptional cases. Only by distinguishing the behavior of risk enhancement and opportunity loss in tort law can the tort law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ubstantive remedy.
Keywords: tort law; causality; opportunity loss; risk enhancement; opportunity damage
责任编辑:龚桂明陈西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