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想象与现实 启迪创作和阅读
2022-0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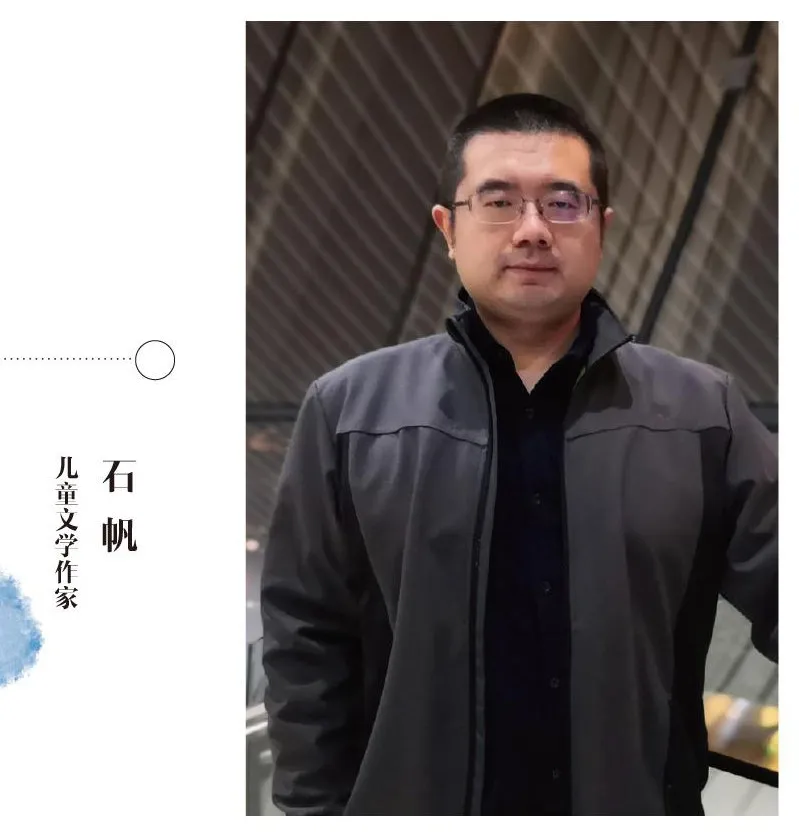

本期话题:
童话最初来源于民间,当作家有意识地为儿童创作成为主流,民间故事和人文传统里的许多要素都被童话吸收了。对于中国的读者和创作者来说,童话这种体裁天然带有舶来品的意味。近年来,许多童话作家尝试将本土的民间故事和人文传统融入原创童话,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作品。怎么看待童话作家的这种主动积极的变化?如何让童话更好地传达我们的人文传统和民族精神?
立足民间文学的根柢,继承并创新
胡丽娜
儿童文学研究学者
如何以童话的艺术形式更好地传递人文传统和民族精神,一直是伴随着本土童话发展进程的重要议题。五四前后,在安徒生、格林童话等域外经典影响下,叶圣陶、郭沫若、张天翼、陈伯吹等人走上儿童文学的创作道路之始,就致力于探寻适宜于中国文化土壤的童话风貌。他们将视线投向民间,搜集、整理、改编各地的童谣、民间故事和传奇,努力将优秀传统的质素融入作品。
陈伯吹在20世纪80年代,对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进行了总结与反思。他剖析自己在创作上走了“弯路”,“舍本逐末、弃近求远地走进了狭隘的胡同”,没有写出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原因在于过度倾心于西洋的文学与儿童文学,有意识地以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为学习蓝本。系统省思之后,他指出欧洲较早、较著名的童话作家的辉煌硕果,都生发自民间文学的根柢,作品流传不衰的秘诀在于对本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充分吸收,及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加工和推陈出新。
当代童话作家对于民族资源的吸收和转化进入了更为自觉地创新阶段。在儿童本位立场的坚守下,以文学性、趣味性对传统资源予以批判性阐释与现代化创造。如熊亮、蔡皋、周翔的系列创作,在图画书领域多维度地对民间资源进行艺术探索,彰显了中国美学特质。同时,周静的《天女》、“鸭蛋湖系列”,汤汤的《水妖喀喀莎》,陈诗哥的新作“牛粪书系列”等,也都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独特的灵性与才情和对传统素材别具一格的现代发展。
离地一尺的故乡
周" 静
儿童文学作家
很久以来,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有神仙相伴的。老人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于不可见处,有神明的眼睛在闪闪发亮。我们都是神明的孩子。在那些看不见的目光中,人们心中有了一套行为的准则。
这个看不见的神明世界,存在于故事里,存在于生活的细节中,是我们精神家园当中离地一尺的故乡。这个故乡发源于那个神话的时代,人们用敬畏之心开疆拓土,群策群力,用漫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建设而成。
这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可惜,这项文学传承,就像那些带着体温的手工艺一样,被挤兑到了角落里。于是,这个离地一尺的故乡变得若隐若现。我看到它并想以自己的方式将它呈现出来。于是,我以“鸭蛋湖”系列童话开始了这个领域的创作。“鸭蛋湖”是从我脚下的大地上、从漫长的时间中、从民俗生活的细节里生长出来的。它来自于我短暂却古老的记忆。
融入我们人文传统和民族精神的童话,是作者给予自己的精神慰藉,也是为这个故乡砌下的砖瓦、雕刻的花窗。我希望,这些故事,当一个人—一个孩子或一个成人读过的时候,会记起那藏在我们基因中的、关于故事的古老传承,唤起他们心中那若有若无的一丝熟悉感。这样,基于在不同的想象中共同建立的故乡就会跨越距离和时间,成为真实的存在。这个真实,是想象的真实,更是文化的真实。
中国神话中的情感密码
葛" 竞
儿童文学作家
童话的外在自由而变化无穷,想象的香气弥漫,给现实打开一道透气的窗;而童话的内在则是从人们的心灵里生长出来,是每个人与儿时的自己对话。童话的虚幻恰恰对应着一种刻入内心的真实。
每个中国孩子都是听长辈讲的神话故事长大的,那些故事仿佛是种在幼小心灵里的一颗种子,伴随着人的成长,种子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融入了血脉。作为中国的童话作者,自然而然地会把这种真情实感带入自己的创作。同样,中国读者需要这样血脉相连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才能走进他们的心灵。
正因为童话的象征意义,创作时作者需要更深入的思考,才能有准确的表达。这里有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情感的深刻理解和体会,有对中国人特有叙事方式的熟练运用,还有对中国神话题材的了解和积累,更要找到恰如其分的讲述切入点。当我写《永远玩具店》的时候,就找到了中国玩具这个小而美的载体。玩具本来是孩童手边的小物,却承载了中国童年的温暖情怀,包含了亲情与友情、陪伴与期待等多重含义。许多民间玩具背后既有神话故事,又有民间传说,还有民风民俗,我想用小小的玩具来书写属于中国人的大爱,那些深厚绵长却羞于表达的爱,那些无条件也无所畏惧的爱,那些充满牺牲精神忘我的爱,那些能穿透时间与生死的永恒之爱。
中国神话中藏着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密码,需要童话作家们破解它,带着现代的中国孩子走进这座灿烂美妙的文化宝库。
走上舞台的中国童话
石" 帆
儿童文学作家
我小时很爱听故事。故事有两种,外国的故事有异域的光彩,大多用“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开头;中国故事一般用“从前”开头。这些“从前”的故事,听起来很亲切,往往与我仰望的天空星辰、鞋底沾到的泥土花草有关。
我想,这就是中国童话的魅力,它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泥土里生长,和每个中国孩子喝同样的奶水,吃一样的盐巴长大。这是一种血缘上的亲近,更是文化上的认同,同时也是中国作家的写作责任。
作为一个作者,我也深知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童话写作的艰难。把创作放入古典中国的语境中,实现沉浸感是困难的。但是反过来讲,中国作家讲中国故事,理应最得心应手。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的写作可以自然而然地生发于此。中国的文明延续不断,我们今天的文字、语言,还是五千年前的那棵文明树上结的果实。这种历史和传承是鲜活的,是极其宝贵的。
中国童话是不是可以尝试中国绘画的质感,比如工笔画的细腻,水墨的写意?中国童话是不是可以借鉴中国手工艺的传统,让文字实现某种精细和火候的把握?中国童话是不是可以抵达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比如思想的深邃、宽广,甚至物我两忘的境界?
如果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各种文化符号潮水般涌入中国儿童的内心,那么,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当中国逐渐站到世界舞台中心,我们还要继续讲述西方的超人、魔法师和半兽人吗?我相信,中国孩子的根不在于此,中国作家的眼界一定也不止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