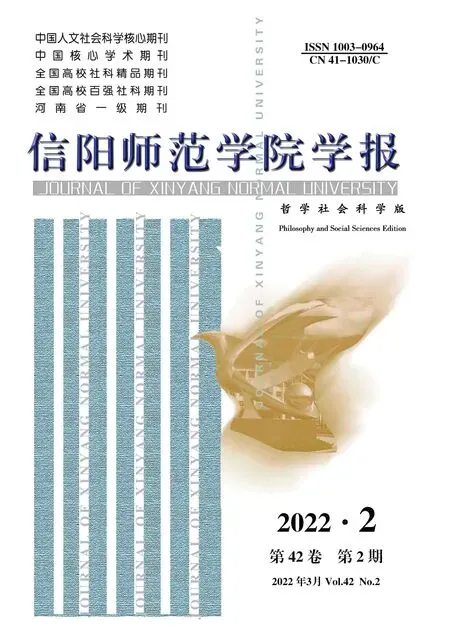民国时期淮河流域黑热病长期流行的原因探析
2022-04-08杨立红朱正业
杨立红,朱正业
(1.安徽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2;2.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黑热病(Kala-azar)又称内脏利什曼病(Visceral Leishmaniasis),是由杜氏利什曼原虫(Leishmanis Donovania)引起、经白蛉叮咬传播的慢性地方性传染病。该病于19世纪中叶盛行于印度阿萨姆山区,患者因肤黑发热,故中文译为“黑热病”。1904年,德国医生Marchand确认其在一名侨居中国青岛的德国死亡士兵脾脏、肝脏和骨髓巨噬细胞内发现的小体为利什曼原虫,初次证实中国有黑热病存在[1]。在中国,患者典型临床症状为脾脏、肝脏肿大并变硬成块,故又有“痞块病”“大肚子病”“大肚子痞”之称。该病于清末民初传入淮河流域,主要分布在农村。在多种因素的耦合作用下,黑热病蔓延迅速,至1937年,淮河上下游一带,“几无县无之”[2]。从流行病学角度看,传染病在人群中传播,必须具备三个环节,即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只有这三个环节同时存在,传染病才能传播与流行。纵观民国时期淮河流域黑热病流行史,正是上述三个环节的相互作用、不断强化,导致黑热病在淮河流域长期肆虐。那么,引致这三个环节不断强化、黑热病愈演愈烈的深层次因素又有哪些?就目前所及,尚未有学者对此问题做专门研究①。鉴于此,本文拟从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三个层面,对民国时期淮河流域黑热病长期流行的原因做一探析。
一、“无力就医”——传染源越来越多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农家主要以农作物经营收入为主,畜业及副业收入为数极少;而农作物的经营,因土地贫瘠及生产技术落后,收入很低。收入甚微决定了其消费水平亦较低,为了维持最低生存需求,淮河流域农家习惯于“量入为出”,即便如此,多数农家仍处于入不敷出、朝不保夕的贫困状态。
收支情况是反映百姓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维度。根据卜凯调查,1921—1925年,怀远县124户农家平均年收入189.94元,年支出185.16元,其中,食物支出107.17元,占总支出的57.88%;宿县286户农家平均年收入258.99元,年支出259.26元,其中,食物支出153.48元,占总支出的59.20%[3]85,512。两县收支情况与消费结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农民生活十分贫苦。1922年夏,马伦等对宿县558户农家收入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详见表1。

表1 1922年宿县农家年收入情况一览表
由表1可见,宿县558户农家总收入为153 973元,户均275.94元。其中,年收入在200元以下者共计400家,占总户数的71.68%;年收入在200—300元者50家,占总户数的8.96%,户均256.04元;年收入在300元以上者108家,占总户数的19.36%[4]96-97。从调查情况看,介于户均收入区间者最少,高于户均收入者其次,低于户均收入者最多,以卜凯调查的宿县户均年支出259.26元为参照,约80%的农户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
由于材料缺乏,我们无法对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农民的收支情况做出一个准确统计。但通过上述收支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出,其时淮河流域广大农村呈现一种“共同贫困”的局面,大部分农民终岁勤劳,收入仍不够支出,解决温饱成为其生活核心问题,用于医药方面的支出微乎其微。根据卜凯调查,1921—1925年,怀远县124户农家年均医药支出3.77元,占总支出的2.04%;宿县286户农家年均医药支出3.03元,占总支出的1.17%[3]85,512。诚如麦克尼尔所述:“医学对人口的影响还是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很少有人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用。”[5]194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部分医院虽已有疗效较好的进口药可以医治黑热病患者,但价格高昂。1920年,连云港境内开始用吐酒石、新斯锑波霜等进口药治疗黑热病,医治1例需30元[6]2464。1925年前后,沭阳县使用土酒石进行治疗,但需注射30—40次才能达到总剂量,一个疗程往往需要几个月,每例药价折合小麦500斤[7]172。1934年,沛县西医使用新斯锑波霜进行治疗,每支收取20元,治疗1例药费折合小麦1 500斤[8]33。1937—1940年期间,莒南县使用锑剂治疗,每例折合500—1 000斤粮食或5—10斤生丝[9]101-102。1943年,西医吴兴邦在凤台县刘楼使用新斯锑波霜治疗黑热病,每例折合小麦近1 000斤[10]587。1946年,虞县杨集一带采用德国进口的斯锑黑克治疗黑热病,每例折合小麦400斤左右[11]443。由上可见,使用进口药治疗黑热病的费用没用统一标准,因时因地而异,但总体上讲费用奇高,治疗1例折合小麦400—1 500斤,故此病也被群众惧称为“钱块”或“钱痞”。
淮河流域一带罹患黑热病的多为贫苦农民,“生活且不可得,医费复从何来?”[12]因此,他们虽明知有进口药可以救命,但因支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不得不放弃治疗。众多无钱医治的患者不仅随时有死亡的危险,而且在中华白蛉吸食人血时,它会将疾病传染给患者家人或周边人。有人指出:“这个人家只要有一个人死了,接下去就有第二个生病,第二个死亡,等到第二个死亡时又有第三个患病了,这样一个两个死下去,往往不到两三年,可以把一个人家的人完全死光。”[13]1927年,沭阳县龙庙区仲湾乡18户人家中有18人患黑热病,先后死亡16人[7]172。1932—1935年,宿迁县来龙乡双张圩子27户患黑热病,死亡82人,其中张统龙一家16人、张继英一家6人全部死亡[14]105。1934年,在涟水境内病区,竟有多数村庄,“死亡至不剩一人者”[15]。据调查,淮阴黑热病患者因未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死亡率高达90%以上[14]105。因此,在淮河流域民众中流传着“得了痞块病,全身没得劲,有钱打新霜(药名),无钱就送命”[16]680-681,“大肚子痞缠了身,阎王拴着脚后跟”,“大肚痞,快三月,慢三年,不快不慢活半年”,“得了大肚子痞,十患九人死”等民谣[17]150。
患者是淮河流域黑热病最主要的传染源。因此,对患者进行药物治疗,使其早日恢复健康,是防控黑热病蔓延的有效措施。然而,“劳动人民因无钱医治,国民党政府不予问津”[8]33,淮河流域染患黑热病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生长于斯的人们被黑热病的超长传播链所缠绕,没人能预知谁是下一个“倒霉蛋”。以苏北为例,黑热病最初传入时,不过数人患病。至1935年,苏北各县“竟有十余万人之众,且蔓延迅速,愈传而愈众,村舍为墟,整个社会而呈朝不保暮之势”[18]。据调查,淮阴农村82%的村庄都有黑热病,户口感染率有的高达83%,几乎每户有1—2人患病。涟水县50万人口就有15万多人发病[14]105。人类宿主数量的不断激增,使黑热病在淮河流域的地理扩张变得异常容易。至1948年,苏北各县患者高达120万人,农民及难民占63%。其中,仅淮阴、淮安、泗阳、涟水4县患者就有30万人[19]。
二、“生有白蛉子”——传播媒介的天堂
黑热病在我国分布很广,曾在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河北、湖北、四川、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16个省、市、自治区665个市县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其中,尤以淮河流域为重[20]。中华白蛉为我国黑热病的主要传播媒介,性喜阴暗,多居于潮湿的房屋,喜欢夜间出来吸食人血,飞行时声音很小,不易察觉[21]。雌蛉吸吮患者血液后,即把病原体利什曼原虫吸入胃内,逐渐生长成为带有鞭毛能活动的原虫,并且一个分为两个,两个分为四个,愈变愈多。当其再去吸食另一个人的血液时,便如同注射针剂一样把利什曼原虫注入人体内。因此,中华白蛉数量的多少也是决定淮河流域各地黑热病流行程度的重要变量。
中华白蛉主要分布于北纬180—420,东经1020—1240的广大地区,其地理分布与我国黑热病的地理分布相一致。除新疆、内蒙古和甘肃西部外,凡是有黑热病流行的地方,均有中华白蛉存在。尤其在黑热病流行比较严重的淮河流域地区,中华白蛉占已鉴定蛉种总数的8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高达90%以上,而在长江以南的非黑热病流行地区,这一蛉种极为罕见[22]285。时人研究发现,“苏北一带乱草污土之间,生有白蛉子一种,此为传染黑热病之媒介物”[23]。“这种小虫在长江以南不大见到,在苏北、淮北、山东、河南等处却是最普通的虫,所以黑热病也在那些地方流行着”[24]10。1948年1月,上海卫生局巡回医防队为各区难民诊病,先后发现黑热病患者9人,分送几处医院隔离治疗。“上海发现黑热病”的消息在报纸上刊登后,不仅卫生局急忙着手防治,而且也引起了市民的恐慌。然而,经过多天防治,除那9位患者外,再没有人被传染上此病。在淮河流域如同洪水猛兽般肆虐的黑热病为什么在上海没有蔓延开来?通过流行病学追踪得知,那9位患者是在苏北染上黑热病后来到上海。他们虽然患了病,但上海没有白蛉,“这种病就决不会传到别人身上的”[24]10-11。人—中华白蛉—黑热病这一循环链的中断,使得在淮河流域异常“活跃”的黑热病在上海戛然而止。从流行病学角度看,自然环境因素决定了中华白蛉的分布及其在不同蛉种中的数量比,进而决定了长江成为我国黑热病流行区与非流行区的地理分界线,同时亦是淮河流域成为黑热病流行重灾区的关键性因素。
与农村相比,城市人口相对集中,人们之间交往与流动的频率亦较高,这也意味着城市罹患各种传染病的风险更大。然而,黑热病的分布则恰恰相反,人口相对分散稀疏的农村反而成了黑热病横行的“乐园”,这主要与城乡不同的生活环境与卫生状况密切相关。如在睢宁农村,“一座小茅草屋,可以容纳全家的人口。屋子的建筑,也特别简单:只要四围用泥涂起来,上面盖一点草就成功的。乡间最坚固的屋子,是纯粹用泥土筑墙的一种,大多数是用芦柴或是高粮(粱)杆子札(扎)成一个篱笆,外面加上几寸厚的泥土就算完事了。他们的住屋,从来没有窗子,那是为防御土匪的枪弹的”[25]。在淮河流域农村,不仅百姓住屋低湿阴霾,而且百姓的卫生意识也极为淡薄,“其畜有鸡、鸭、猪、犬等者,往往距离宿所仅隔一蓬壁耳,几与人喧夺几席”[26]37-38。一床被,从新到烂也不洗一次。“他们整日里工作到晚间极疲惫的时候,可以随便地倒床上睡去,这样,身上的污泥和汗液排泄出来的内部分泌物,在他们的衣服上和被褥上,都可以找得到。如此的衣服和被褥,正好被虫子(白蛉)找到了,于是虫子繁殖起来。由于虫子的传染,痞块病应运而生,很普遍地流行了”[26]。相较于农村,“城内家畜既少,缺乏繁殖牲畜之场所,白蛉必少,或竟无此种昆虫”[27],因此城里染患此病的人较少。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农村生活条件低下,民众卫生意识淡薄,村民居所多为低矮潮湿的“草屋茅庐,十数人寄居一室”[28],衣被不洁,人畜杂处,厕所粪坑紧邻住房,垃圾盈门,便溺遍地,一到夏季,虫蚤蚊蝇触目皆是,且为贪图凉快,百姓“夜间袒背露宿,与白蛉以吸血之机会,而病人即增多乎”[27]。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居环境,淮河流域广袤的农村都堪称是中华白蛉理想的栖息场所。患者、传播媒介与易感人群小则生活于同一屋檐之下,大则聚居于同一村落,每个生活于此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被白蛉强行“吸”入黑热病传播链。就这样,在白蛉“美餐”之际,微小病原体轻松完成了在宿主与易感人群中的不间断转移,于是,黑热病在淮河流域农村肆意流行开来。抗日战争前,民国中央卫生署孙志戎曾在苏北组织黑热病研究队深入农村,“努力扑灭这种小虫,黑热病也跟了逐渐减少。战争中,无人顾及此事,以致黑热病又在苏北猖獗起来,并且蔓延到河南、山东各省。据考察的报告,单是苏北已有四十万以上的病人”[24]10。这也是中华白蛉数量的多少与黑热病流行程度成正相关的力证。
三、“营养不足”——人群的易感性极高
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与农业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农村土地瘠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终日辛勤劳作,仍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如在睢宁,每亩地最多只能收七八斗麦子,平常只能收五六斗粮食。所以,即使有10亩田地,也不能养活三四口人的小家庭。就是有三四十亩田地的人家,每年也只能收十数石粮食,除掉家中生活所需之外,余下的一两石粮食所卖的钱,根本不够满足全家日常最低限度的花销[26]。由于经济衰微,生活水平低下,农民的饭食非常粗劣。在泰县,佃农、半自耕农及自耕农等,一年到底只吃大麦粥,蔬菜大部分只有野菜,“盐和豆油都是不肯滥用的,至于荤味更不必说了”[29]。在睢宁,农民一年当中吃得最适时的食物是用麦糠做的。纯粹的麦面,虽然也存一些,但那是专门留着过年过节或是招待贵客食用的。到了农历九至十月收获了白芋,每日两餐都“放白芋在酸汤里吃”,这种生活由十月到下一年四五月间收获新麦才结束。即便是这种食品也还算是好的,有的人家到了春天,连白芋都吃不上,只好将红萝卜切成很细的丝,搓成像肉圆子的样儿,放在锅里煮熟了吃。这样的食品,也只能在每天上午10时左右和午后4时左右吃上两顿。农民们“那许多食物,写来都还是可以进得嘴的东西,实际上不如说是垃圾箱里的污秽的杂物来得切当”。吃得不好,又时常“在饥饿的圈子里打转”,一眼望去,农民脸上“堆满了憔悴的神情和牛皮纸一样色彩的皮色”[26]。在正常年份里,“半糠半菜”的生活,虽然令农民不致有立刻死亡的危险,但却无法从食物中摄足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资。营养不良、抵抗力低下是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农民的普遍样态。
在“望天收”的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经济极其脆弱,在一般情况下,勉强可以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一旦遇到天灾人祸,立即就被抛到死亡线上。民国时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社会持续动荡不安,淮河流域成了水、旱、蝗、蝻等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光顾的区域。每遇较大灾害,庄稼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在灾荒中幸存下来的灾民为了保命,正常年份连牲畜都不吃的所谓“食物”都成了稀缺的抢手货。如1928—1929年,水、旱、蝗、风、霜、雹各灾交相侵袭河南。灾民除食用麸子、粃糠、榆树皮、棉籽、棉饼、榆叶、杏叶、桑叶、柿叶、楮树叶、柳絮、杨花、荞麦花、荞麦叶、苜蓿、红薯叶外,鲁山等县甚至以观音粉、临汝等地以蛤蚧充饥。除上述所食之物外,“其他不堪作为食品,竟为灾民求之不得者甚多”[30]119-122。
食物粗劣匮乏,大大小小的灾荒接连上演,食不果腹成为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农村常态。国医姜贯虹指出“寒暖不匀,饮食不周,未病而身体先伤”[31]实为淮河流域贫苦农民大量染患黑热病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的农民,身体素质与免疫力普遍低下,对任何传染病都格外敏感,几乎全部农民都成为黑热病潜在的易感人群。
四、结语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地瘠民贫,天灾人祸交相侵袭,到处都是衣食不周、身体羸弱、缺乏免疫力的易感人群。适宜的自然生态条件,低湿阴霾的人居环境,不良的卫生习惯,使淮河流域广袤的农村成为中华白蛉生活的天堂。由于贫困与卫生观念淡薄,他们未病不知防范,已病没钱医治。于是,黑热病如同恐怖的野火一般,在淮河流域人与人、家与家、村与村之间恣意蔓延。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除了黑热病广泛流行外,天花、霍乱、伤寒等急性传染病亦轮番登场。相较于黑热病,这些急性传染病更能引发社会关注。因此,政府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种痘、伤寒、霍乱等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对于黑热病这种广泛流行于农村的慢性传染病“事前多疏于预防,及此病发现,因医药人才设备方面,俱感缺乏,对于患者之施行诊治,殊感困难,以是流行颇烈,死亡甚多”[32]。此外,频发的战乱、灾荒以及现代交通的发展,时常引发人们的聚集与长距离移动,作为一种“副产品”,黑热病也随之被带到更广阔的地区。同时,科学研究的滞后,相关知识与卫生常识宣传的不力,人们“不知该病系借何种方法传染,则防止工作,无从着手”[28]。于是,民间出现诸如鬼神司疫、口鼻传染、皮肤侵入[33]、湿痰瘀血[34]、沙蝇田鼠传播[35]等种种对黑热病的错误认知,甚至认为病尸、能烧得出水的黑窑碗、吃病人痰液的母鸡所孵出的鸡蛋等,都可能是传染的媒介[36]。相应地,诸如针刺手指、用刀割拇指与掌心相连处、外贴各种化痞膏、按摩[37]、扑灭沙蝇田鼠[35]、摔掉黑窑碗、不吃鸡蛋[38]等五花八门的治病防病方式亦纷纷登场。在诸多无效的应对中,越来越多的民众染患黑热病。
人类活动与致病微生物之间的关系是共生互动的。上述每一种因素以相互支持的方式耦合起来,不间断地交互作用着。其中,任何一个变量的强化都以不规则的频率改变着疫病的规模,尤其是某些关键性变量的增强,必将引发新一轮的疫病暴发。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三个环节相互支持、不断强化,于是,患者愈来愈多,流行范围愈来愈广,死亡也愈来愈众。当今,如何有效防控传染病,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与任务。历史经验证明,在研究与制定传染病防控策略时,除想方设法切断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三个主导环节外,还要高度重视医疗卫生条件、生活习惯、居住环境、习俗信仰、人口流动等引发传播链不断延续的因素。
注释:
① 相关研究成果有:朱甲利《保障生命健康:阜阳专区的黑热病流行与防治(1951—1958)》,《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杨金客、朱正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淮河流域黑热病传播及救治》,《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杨立红、朱正业《民国时期淮河流域黑热病分布研究》,《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杨立红、朱正业《民国时期淮河流域黑热病的社会影响》,《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王凯、朱正业《国家与社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淮北黑热病的防治》,《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报》2017年第6期。上述成果主要对民国时期淮河流域黑热病的流行状况、分布特征、防治举措与社会影响等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