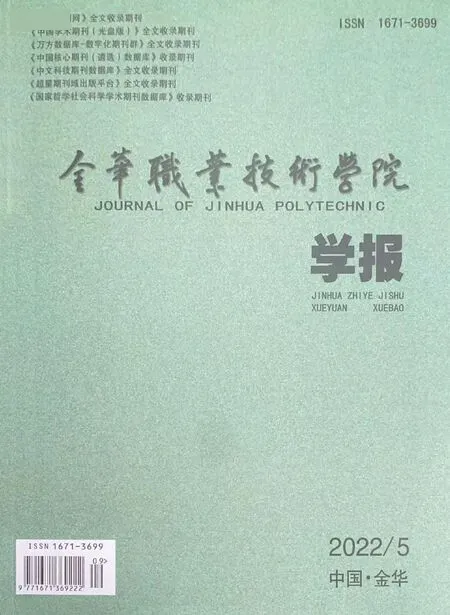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混沌美学特征
2022-04-07张笑
张 笑
(青岛工学院,山东青岛 266300)
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混沌美学
(一)“混沌”一词的来源
“混沌”一词源于早期人类想象的天地被开辟以前宇宙模糊的状态。《周易·卦经》有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1]6混沌不只是一种状态、一种现象,也是中国古人认识、感知、体悟宇宙无穷奥秘的一种思维方式。早在春秋时期,老子有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2]15其中提出了“道”的混沌之美,也初步提出了宇宙起源于混沌的哲学思想。庄子继承了老子这一思想,其“混沌之死”的语言与《庄子·外篇·天地》中提到的“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3]43与《老子》第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洁,故混而为一。不激,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2]22中强调的“恍惚”的“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庄子的思想更进一步,他将关注点聚焦于天与人、物与我的关系,指向世界原始的和谐,在其阐释下,“混沌”被赋予了更为深厚的人文内涵。
(二)中国混沌美学的来源
建立在“混沌”理论基础之上的混沌美学是我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范畴之一,可以说,混沌美学中的“混沌”理念是构成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在文明刚刚萌芽之际,先民从身体力行的实践生活中汲取了自然的启示,用阴阳平衡、五行八卦的理念试图了解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这种世界观的背后隐含着祖先们对世界的敬畏,他们认为世界变幻莫测并不可知,宇宙自然充满了混沌神秘,虽然以现在的目光看待当时华夏先民的世界观会认为其并不完全客观科学,但是这种对于“混沌”的认知也并非全都是负面消极的。正如《周易·乾卦》有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1]77在我们的先辈看来,蓬勃盛大的乾元之气构成了万事万物赖以生存的动力之源,它统贯于天道运行的整个动态过程之中。“混沌”也是如此,它蕴藏了一种巨大的能量,具有一种高度的完美性。“混沌”理念贯穿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之中,并影响着传统艺术的产生及发展。
(三)混沌美学的特征
混沌美学的第一个特点是整体性,这种整体性的呈现与在西方思维的对比中更加明显。关于中西思维方式,“傅雷先生曾说过:‘东方人和西方人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东方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同。’”[4]实际上,傅雷所说的这种东方思维方式,就是混沌思维方式。混沌思维的基本特征之一正是整体性,其基本思路就是从综合、归纳、宏观的角度对待问题,以全局视角进行思考。老子哲学虽然强调“无为”,但这种“无为”并不是真的不作为,被动消极地接受自然变化,这种“无为”实则包含清净和有序,所谓“混而为一”就是关于混沌整体性的描述,“天地母”就是“混而为一”的整体状态。庄子哲学的基本观点“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始于玄冥,反于大通”中的“根”“玄冥”“大通”指混沌的整体性状态。清代画家石涛在《画语录》中有言:“笔与墨会是为絪缊(氤氲),絪缊(氤氲)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画于山则灵之,画于水则动之,画于林则生之,画于人则逸之。得笔墨之会,解絪缊(氤氲)之分,作辟混沌手,传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5]这其中包含了深刻的老庄道论思想,石涛从混沌的角度论画艺,认为一画虽简,却能够在笔墨指法的完美配合中超越具体可感的形象,实现整个画面的有机统一,贯穿艺术、人生、天地三重境界,达到混沌之美的纯粹之境。
混沌美学的第二个特点是自然性。《老子》中,这种具有丰富人文意味的混沌意象已初露端倪,而这种具有人文意蕴的意象落实到艺术创作中时便体现为自然性。《老子》十四章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洁,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激,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2]15这个无声无形、恍恍惚惚的“一”便是《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中的“一”,也是《庄子·天地》所谓的“混沌”。庄子的“混沌”理念建立在老子对“混沌”概念阐释的基础之上,其观照的范围发生了转向:从对宇宙天地的宏观描述到天与地、物与我的关系上,为人生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最终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系中。在庄子的混沌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极力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的自然主义立场。庄子认为“天地一体”(《天下》)“人与天一也”(《山木》),人与自然、天地实则是一个和谐共存的整体。《庄子》中有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举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之,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3]65庄子理想中的混沌状态在此得以体现,混沌美学中对于自然性的追求也在此呈现,它强调的是物我两忘、和谐统一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性体现在混沌美学中则表现为一种艺术创作者融真情实感于创作中的“真”和“自然”。这种“真”是一种与世俗之“伪”相对立的自然而然的天然本性,是物我交融、天人合一境界之根本。正是由于艺术创作者在创作时流露出真情、真性,方能领悟自然之本,并与之交融,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崇高艺术境界。
混沌美学的第三个特点是超越性。前文提到“真”对于“混沌”的重要意义,如《渔父》中所言“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3]18。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真”,摒除对于身外之物的杂念,化解机心,得其本真呢?庄子给我们提供了答案:“意!心养。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滓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3]24其中,“堕尔形体”是忘己,“吐尔聪明”是忘知,“伦与物忘”是忘物。一个“忘”字完美地提炼出达到物我交融至臻境界的不二法门,简单一个“忘”字,使得被世俗束缚的心得以解脱,真性和真情喷薄而出,与天地万物大同,使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混沌”之境。这种“忘”,实际上是对个人的一种超越,是人内心对世俗物欲的一种超越,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忘记了七情六欲,超越了追逐各类欲望的心态,保持纯洁、虚空的心灵,达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艺术境界,使得天地万象、尘世百态都涌入胸中。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所言:“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人。”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创作者的作品也被赋予了超越性,获得了超越自身意象之外的全新意境。
二、中国戏曲中的混沌美学特征
在我国传统美学领域中,我们不难发现早期“混沌”“浑沌”“浑涵”等组成了“混沌”的审美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中华民族文化特性与哲学思辨精神的混沌美学,成为我国传统美学体系中的重要分支。一个艺术门类的产生与发展,必然受到一定哲学思潮的影响,戏曲艺术作为我国本土的古老艺术,自然也受到我国本土的古老艺术和混沌美学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戏曲文学的“无物之象”——混沌美学整体性的体现
混沌思维的整体性在艺术作品中具体表现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审美意境。以中国画为例,我国传统画作与西方绘画作品的一个巨大差异在于散点透视法的使用,做到冲破时空局限,不受束缚地表现画家的“胸中之竹”。我国传统画之所以不像西方画作一样采用焦点透视法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更好地呈现描绘对象的整体性特征,正如同苏轼的诗句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传统画创作者眼中,要更好地表现自己的“胸中之竹”,就不能只从某一个特定角度去观察,而应把握观察的多重视角作高屋建瓴的描绘,不仅要把自己的所见跃然纸上,更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得融入作品,真正达到一种具备整体性的混沌美境界。
由于混沌思维具有整体性这一最显著的特征,因而深受这一思维影响的古代艺术家们非常注重作品的写意性及艺术表达的整体性,表现在戏曲艺术中就是戏曲文学作品中“无物之象”意境的建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谈元曲的文章结构时提出:“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6]也就是说,元曲的精妙绝伦之处在于意境的描绘。在传统戏曲中,曲作家所勾勒的情境也是戏曲的意象之一,“情境也是戏曲作品的意象之一,因为它们都在创作过程中被融入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7],创作者的艺术思维与实际的物象始终是一个整体,因此戏曲作品无论是仅供阅读的“案头之作”,还是舞台上呈现的“场上之曲”,其中的意象都是清晰可见的。以我国古典戏曲杰作《西厢记》为例,《西厢记》辞藻优美又不乏质朴,且感情真挚,无论是作为“案头之作”还是“场上之曲”欣赏都有极强的观赏性,佳句频出,有的可谓字字珠玑。楔子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的“花”“水”“东风”均为意象,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又构成了一种充满愁绪忧思的意境:花儿被风吹落在水中,溪水都被染红。内心的万般愁绪,说不明理不清,难以言说,只能怨东风把花吹落。表达了怀春少女崔莺莺内心由相思而产生的莫名幽怨。《长亭送别》一折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中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北燕”“霜林”等意象的组合构成了一种萧瑟凄苦的艺术意境,烘托出张崔二人离别之际的悲切。意象的组合不仅是辞藻的简单罗列,更是剧中人情感抒发的手段,而意境正是在意象组合基础上的“象外之象”“韵外之旨”。晚唐司空图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构成意境的意象要与真实生活相符合,要做到真实自然,同时由意象构成的意境应当辽远、深刻。彭吉象则将意境概括为一种若有若无的朦胧美、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越美、不设不施的自然美。总之,中国传统戏曲的文学意境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呈现出情景交融的整体性美感。
(二)戏曲表演的“乘物游心”——混沌美学自然性的体现
混沌美学中流露的自然性,不仅表现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空间中,也体现在人类精神的寄托里。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协调”“和谐”,特别注重人之“情”的存在和参与。戏曲与人情相生相伴,人情融于戏曲,因而戏曲经久不衰、感人至深;戏曲又融入人生,因而古代人民能够“诗意地栖居”。自在是古代道家推崇的精神境界,这种自在的精神体现在戏曲上则表现为唱词和表演的宛自天成以及情感的自然流露。《易传·系辞》有言:“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1]77说明“意”是无法完全用语言去表达的,但是通过一个立体可感的形象能够达到“尽意”的效果。意境,实际上是由混沌美学思维的模糊性衍生出的一种艺术境界——游于象外,趋于无限。
戏曲艺术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对于演员的个人能力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尤其注重表演个体的悟性、灵性和非逻辑性的混沌性特征。从根本上说,审美经验中的“悟”这一范畴,从个体艺术接受、感知、领悟、再创造等方面的敏感性控制着接受者的审美心理结构,从而影响着接受客体的再创造,因而艺术“悟”性又显示出超乎寻常的非自然性特征。戏曲艺术对表演者的悟性方面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在对表演过程的理解、反思、再创造等方面,并不完全符合等量加合性的质变特点。也就是说,戏曲演员的自然天赋要大于后期努力,并非每个人都适合成为一名戏曲演员。与注重刻苦练习的某些艺术门类相比,戏曲更讲究秒悟、顿悟、迁想妙得,强调表演主体在表演过程中处于完全无意识、无目的的状态之中,忘知忘我,超乎象外,获得精神自由,物我相忘,与剧中人高度“合一”,乘物游心又弃物逍遥。“神思”一词最早见诸刘宋宗炳《画山水序》,刘勰把它引入文论,对之作具体而深入的探讨[8]。刘勰的神思论特别强调“思理为妙,神与物游”[9]。此与理论思维相区别,理论思维舍弃具体的个别物象,采取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形式;艺术思维则与实际的物象紧密相连,始终不离“物”。“心”与“物”的相反相成,解释了艺术思维中心物交融的特征。物与神游的合一,即是心中有物,物中有心的结果。此时的“物”,不再是一个静止、孤立、被动的物象,而是成为了一个融入“情”的意象。
戏曲艺术表达的自然性也表现在程式的使用上,程式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每个程式都有其独立的意义,然而这种独立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其在戏曲演出中可以独立存在,因为程式独立的含义虽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动作串联,但一旦缺少了上下连贯的表演情境就会显得突兀、奇怪。例如,“起霸”这一程式,是戏曲演员的基本功,是武将上场之前所做的整盔、束甲等一整套动作,由于这段形体舞蹈以生活为基础,在规定情境中恰当地表现霸王的人物形象,此后,在这种规定情境中表现将帅风度及威武英姿时常被套用。但是,这套程式也不能在任何武将身上使用,在表演起霸这套程式时,无论是大的技巧、缓慢的运动,还是亮相停顿都应力求稳重,因为这同人物身份、性格、铠甲的沉重以及服装的下垂感的特点是统一的。相反,起霸在审美特点上最忌讳的是“浮、躁、漂”,这也是张飞、李逵等性格暴躁的人物很少用起霸的原因,体现出戏曲艺术对于混沌美学中自然性特征的吸纳。
(三)戏曲舞美的“技近乎道”——混沌美学超越性的体现
戏曲的舞台美术具备混沌美学中的超越性,是在高度虚拟化的戏曲情境中展现的,它既不同于影视场景的“真”,又不同于话剧舞台场景的“实”。舞台设计具备强烈的象征意味,这是由于我国传统戏曲追求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真实,而是高度凝炼了的生活。在这种高度写意的表演“场域”中,配合演员高度程式化的动作,传递近乎于“真”的生命理想,在虚空之中表现现实,于朴素之中呈现繁华。传达出炎黄子孙的独特气质和生命观念。戏曲舞台道具的有限性为戏曲演员表演的无限性开拓了道路,戏曲表演中注重“神似”境界,通过写意和白描的手法对社会生活进行高度的浓缩和概括,较其他艺术门类,我国传统戏曲具备高度的写意性,呈现出一种超然象外的意境。戏曲舞台美术的超越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舞台环境的确定以人物活动为依归,正是由于人物的舞台活动才有相应的舞台环境,人物的活动赋予了超越舞台之外的意义,离开人物的活动,戏曲舞台也只是一个抽象的空间;第二,在同一个场景中,通过人物的活动可以超越一定的时间空间限制,这就使得戏曲舞台具备了超越性。
为了获得这种超然象外的意境,戏曲的创作者往往不受形与神、情与理、虚与实关系的束缚,思接千载、目视千里,让才思自由穿梭于艺术舞台与现实人生之间。戏曲舞台之上,一两人即是千军万马,三两步走遍海角天涯,一桌二椅也能塑造一个方寸世界,在对现实人生的夸张变形中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境。一桌二椅、演员的举手投足都是写意化的呈现,却能与观众达成一种默契,观众与舞台、演员之间保持着戏曲意境的和谐完整。《拾玉镯》一出中,孙玉姣坐在门前绣花,演员手中并无针线,但是通过演员小心翼翼穿针引线的动作,观众就会认为演员确实是在绣花。《苏三起解》一出中,苏三被诬陷,解差崇公道提解苏三自洪洞去太原复审,一路上苏三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演员只在舞台上走了一段路,却让观众认为这就是从洪洞去往太原。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在舞台美术设计上别具匠心,将古典戏曲舞台和现代设计理念融会贯通,为观众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假、如梦如幻的舞台效果。其中“游园惊梦”一场在舞台气氛的营造上成为业内津津乐道的典范,坚持朴素简洁的舞台设计,从舞台布景到服装道具,处处透露出空灵简洁的中国传统风采,于方寸舞台之上呈现出我国传统艺术表达的超越性。
传统戏曲的风韵,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思想和传统哲学范畴的浸润中孕育发展。我国的戏曲艺术凝聚了多种艺术精华,是我国传统民族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奔流不息,任凭岁月更替仍然熠熠生辉。戏曲以其“离形取意”的虚拟化、写意性表演风格,在虚实之间、于方寸舞台之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芒,照亮广袤无垠的九州大地,用歌舞的力量给予华夏儿女无限的精神力量。无论是风格迥异的唱腔、丰富多样的舞台形象、精致巧妙的头面服饰,还是蕴藏于作品之中的动人故事、环环相扣的情节设置、充满人格魅力的主人公,都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宝贵财富。戏曲将美学与诗学紧密联系并倾注到人对于诗意生活的向往和人的感性审美生产之中,通过舞台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个体审美体验的深化与精神境界的超越。正是这样的戏曲艺术,彰显着中国特色,承载着中国风格,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理念、道德观念、人格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