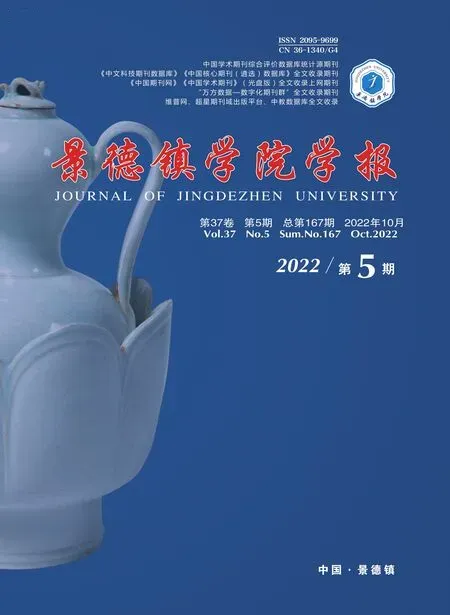重复的魅力
——《惊恐记》神话原型之解构批评
2022-04-07孙晔
孙 晔
(太原工业学院外语部,太原 030008)
20世纪60年代后期,解构主义思想被引入文学批评的范畴,为解读文学作品和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开辟了全新的途径。如今,解构主义作为理论思潮的热度已退,但其独特的批判视角、非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完善的理论体系早已融入文学批评的洪流中,持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美国耶鲁解构主义批评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J.希利斯·米勒,在其代表作《小说与重复》中独创性地提出了“重复”理论,将小说中的重复现象分为三类:细节的重复、情景的重复和跨文本的重复。“重复”理论,即在解构主义策略下,通过分析小说中的重复现象,剖析人物内心活动和发展,掌握小说结构和脉络,阐释作者的写作意图。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复合组织[1]。无所不在的重复不仅搭建起小说的内在结构,还决定了小说与外界的联系,如作者的个人经历、社会背景、小说的意识形态和神话或寓言、传说中的典故等。
E·M·福斯特作为英国文坛现代小说的开创者之一,擅长借助异域文化和神话寓言,构架超脱现实的反讽小说。人文主义精神是福斯特小说的灵魂和核心,他倡导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并蓄,对大自然的歌颂和回归,批判人与人之间冷漠疏离的关系,反思工业文明对人性的蒙蔽。《惊恐记》是福斯特所创作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一经出版便获得赞赏。小说借助希腊神话中潘神的形象,勾勒出主人公尤斯塔斯在受到潘神的感召下,试图逃离工业文明,成功回归大自然的离奇故事。福斯特赋予潘神以自由原始的力量,象征人类最本真的品质,即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回归自然,亦是回归纯真,回归人性。小说传达出一种反叛精神,并非是对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的反叛,而是对人们盲目从众的无知和毫无自我的愚昧的反叛。小说《惊恐记》中重复出现多种意象、情节和场景,这些元素均能在广为流传的潘神的神话故事中找到对应原型。在神秘的心灵之旅和幻想世界的冲击下,引发对社会秩序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思考。因此,在“重复”理论和神话原型理论的指导下,小说的内涵得到更深层次的挖掘。
一、细节的重复
重复理论的第一种重复现象是小说细节和意象的重复:通过对寻常事物的重复刻画,引起读者的关注,从而显现重复意象背后的暗含含义。《惊恐记》重复出现的意象分别是“哨子”“山羊蹄印”和“白玫瑰”,三者均被福斯特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
(一)尤斯塔斯的哨子和潘神的排箫
福斯特在《惊恐记》中使用的首个重复意象是尤斯塔斯的“哨子”(whistle)。哨子指代潘神手中的排箫。希腊神话中,潘神是半人半羊的神,以森林为家,守护农牧人和动物,被看作是大自然的化身。他擅长音乐和舞蹈,手持一支排箫(Syrinx)。他时常在森林中吹奏排箫,与众神欢歌起舞,歌颂大自然。潘神曾象征农牧业时代的繁荣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欧洲中世纪的到来,宣告多神崇拜的时代结束,基督教在政治、宗教和文化等领域起绝对作用,“潘神已死”,追求自由和谐的美好愿景被基督教的繁文缛节所代替。
福斯特借助“潘神已死”的题材用以怀念和追忆农牧业时代的人文关怀和包容并蓄。福斯特厌恶工业革命带给英国人心灵上的满目疮痍和冷漠淡然,他向往农牧业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联结,渴望唤醒人文主义情怀,但现实社会的客观环境只会添加无力感和疏离感,唯有借助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异国之旅来表达其创作意图。
主人公尤斯塔斯的哨子形似排箫,被看作是潘神排箫的指代;吹响哨子,预示潘神即将到来。众人来到卡罗索喷泉山谷的一片空地上,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筹备午餐,尤斯塔斯“磨磨蹭蹭地砍下一根树枝做哨子”[2],喊他来帮忙,他却“躲到一棵树旁边,开始削掉哨子上的树皮”[2]。福斯特巧妙地利用尤斯塔斯看似不合群的独处场景为后续的转折和高潮做铺垫,先前平和的假象与后续即将到来的戏剧性冲突的极大反差是福斯特构建丰满的圆形人物的一大写作特点(类似的人物构建在福斯特的另一短篇神话小说《始于克娄纳斯的路》中亦有使用)。众人聊着“潘神已死”的话题,而尤斯塔斯“正在打磨他的哨子”[2],与其制作哨子的默默不语形成对比的是众人对是否存在潘神和“潘神已死”的激烈争论。就在此时,“一切绝对静止,全然无声,一种悬疑悄然而生”[2]。“突然间,我们都像触了电似的,被尤斯塔斯的痛苦哨声吓了一跳”[2],尤斯塔斯用刺耳的哨声打断众人热烈的讨论,犹如潘神吹着排箫在林中穿行,百兽驻足聆听。在读者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森林中偶遇潘神的幻象,将读者带向对大自然的奇妙探究。哨子的重复出现为接下来人们所感到的莫名惊恐进行铺垫,渲染出寂静中的诡异氛围。伴随哨声,寂静和恐惧接踵而至。
刺耳的哨声代替尤斯塔斯发声,这使得尤斯塔斯郁郁寡欢却愤世妒俗的性格特征鲜活起来。众人都听到了哨声,唯有顽劣少年尤斯塔斯被自然之美感化,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反倒被文明束缚,缺乏想象力和勇气,使作品蒙上“亦真亦幻”的神秘色彩,从而极大地调动读者的再创作欲和想象力,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对恐惧产生“欲拒还迎”的幻觉。
(二)地上的羊蹄印和潘神半人半羊的形象
潘神的形象是头上长有犄角,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羊。文中出现的山羊蹄印和山羊形象暗示潘神现身。
突如其来的惊恐过后,众人发现“树下的湿泥上有几个羊蹄印”[2],但这一带是没有山羊出没的,诡异的氛围即刻被烘托出来,读者的好奇心也被调动起来。当尤斯塔斯“看见了那些羊蹄印,便躺在上面打滚”[2]。这样的奇怪举动使人惊诧,尤斯塔斯不善言谈却也心志正常,通过此反常举动,福斯特试图引起读者的注意,从而引发读者的思考——为什么尤斯塔斯要在山羊蹄印上打滚?山羊蹄印有什么特殊意义?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潘神降临。通过一系列的解构分析,读者推翻尤斯塔斯的固有形象,深层次地探究尤斯塔斯和具有山羊下半身的潘神之间的联系。在地上打滚的行为是大部分动物展现友好和示弱的一种表现,农牧之神潘神,自然受到动物的膜拜和亲近,尤斯塔斯在山羊蹄印上打滚实则是对潘神示好。
此处的反差设计使故事显得离奇有趣,让读者在多次重复的细节中探寻答案,彰显福斯特精湛的写作技艺。当一群人准备离开森林时,“尤斯塔斯在前头碎步疾跑,活像一头山羊”[2]。他受到潘神的感召,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生机,像只精力充沛的山羊一般在森林里奔跑跳跃,与小说前半部分其羸弱的形象形成反差,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力,体力充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仿佛脱胎换骨,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
(三)白玫瑰与纯洁友情
福斯特在描述真纳罗和尤斯塔斯的互动中多次使用白玫瑰这一意象。白玫瑰本身是纯洁友谊的象征,而“白玫瑰的阴影”和“过早的凋零”则被赋予另一层消极悲观的象征含义。
尤斯塔斯苍白的面色和不发达的肌肉使其略带女性气质;而在森林中受到潘神感化后,他一改之前唯唯诺诺的样子,变得活泼开朗。他一见到真纳罗,便双手搂住其脖子,而真纳罗将尤斯塔斯抱进了旅馆,并拒绝使用敬语称呼他——暗示着两人之间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3]。
原来,真纳罗也曾在森林中受到潘神的召唤并获得潘神的力量,这使得两人惺惺相惜,不需要言语便可理解对方的想法和情感;两人纯真质朴的情感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是其余人所不具备的特质。白玫瑰象征纯洁而真挚的情感,但其阴影则暗示真纳罗背叛尤斯塔斯,是对白玫瑰象征意义的解构和推翻。白玫瑰是大自然的产物,在利益的诱导下,背叛友谊的行为是物质文明对自然的吞噬和腐蚀。在福斯特笔下,纯洁美好的事物也有其不可言说的阴暗面,而腐朽不堪的事物也暗藏勃勃生机,事物的二元对立以及对事物的多维度探究,亦是福斯特对现代文明的人文关照。“那年过早凋零的白玫瑰把阵阵花雨洒到他的身上”[2],白玫瑰或是指代尤斯塔斯的心性纯洁,或是指代两人难得的友谊,在本应绽放的时刻提早凋谢。
小说结尾,真纳罗在帮助尤斯塔斯成功脱逃后却意外身亡,“又有许多玫瑰叶子落在我们身上”[2]。白玫瑰再次出现,暗指真纳罗内心的简单善良最终战胜物质欲望,他无私地救出尤斯塔斯,不计回报与付出,值得用白玫瑰来祭奠,落在众人身上的玫瑰叶更是为这样的结局增添一份伤感之情。
二、情景的重复
情景的重复是小说中常见的第二种重复类型,多指同一场景或相似场景的多次出现。福斯特围绕“惊恐情绪”和“潘神感召”两个主要情景展开叙述,旨在凸显看似积极和谐的现实生活中潜藏的冷漠疏离在被具有神幻色彩的突发情况揭开遮羞布的瞬间,展现出的千疮百孔与荒诞可笑。福斯特通过文学作品传递出一种强烈信号:人类在进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应保持对精神文明的崇拜和尊重,秉承对多元文化的包容,这一理念无疑是超前的。
(一)惊恐情绪和潘神到来
潘神使“对于意外地冒险进入他领地的人类,他会让他们感受到惊恐——突然的、毫无理由的害怕,任何无不足道的原因。比如小树枝的折断、树叶的飘动,都会使人心头涌上想象中的危险,疯狂地想要逃离自己被唤醒的潜意识,受害者就在这种惊恐的逃跑中丢掉了性命”[4]。这便是英文单词“panic”(惊恐)的由来。借由潘神的回归表达福斯特对自然和人文的热切盼望,试图通过小说向读者传达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表达在工业时代仍然具有无法比拟的现实意义。
第一次惊恐出现在午饭后。原本美好的午后时光仿佛停奏的钢琴曲一般戛然而止:“一切绝对静止,全然无声,一种悬疑悄然而生”[2]。这死寂被哨声打破,紧接着,“可怕的寂静又降临了”[2],众人感到莫名恐惧,一刹那间都撒开腿沿着山坡奔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所有的感性和理性渠道都被堵塞了……它是一种粗暴的、带征服性的肉体恐惧”[2]。
哨声宣布潘神的到来,伴随着寂静中的恐惧。重复出现的恐惧使当事人的感官体验逐次加深,最终引发众人自发的逃离。福斯特对这一关键情景的刻画入木三分,从视觉、听觉和感官三方面入手,呈现出一个既狼狈不堪又令人匪夷所思的逃跑画面。此时的尤斯塔斯,安静地躺在草地上熟睡,全然感受不到一丝恐惧,反而享受难得的片刻安宁,反衬出潘神对其的喜爱和感召。
第二次惊恐出现在花园,另一处自然场景。泰特勒先生“感到一阵令人心寒的恐惧——不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感到恐惧……而是对还会发生什么感到恐惧”[2]。恐惧又一次毫无征兆地出现。如果说森林中的恐惧源于潘神本身,那花园里的恐惧则来自被潘神召唤的尤斯塔斯。此时的少年已然是潘神的代言人,他守护自然,向往自然,竭尽全力挣脱工业文明的束缚。完成精神蜕变的少年,无法在毫无生机的“文明”社会生存,唯有逃离,才是继续生存的唯一办法。这亦是福斯特的发声,对农业文明纯真美好的回归,对工业文明冷漠无情的批判。
恐惧的重复出现,构建起一个跨越真实与虚幻的桥梁,使读者不禁联想到众人之所以感受到恐惧,是因为潘神的到来,因此证实潘神存在的真实性,也增加小说的神奇色彩和趣味性。潘神来到人们身边,将恐惧之感降临在不相信他的人身上。因此,小说题目“The Story of Panic”的引申意义便是“一切因潘神(Pan)而起”。正是由于小说中不断出现“景物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读者在其引导下,力图深入触及作品的内核……这种风格特征并不是零散的、断断续续的。一旦读者在一个细节中发现偏离字面意义的情形,他便会对每一个细节产生怀疑”[1]。
(二)相似的经历和不同的结局
此外,小说暗含一个重复情节,即在山谷中受到感召的人都会在当晚经历一次心灵蜕变和思想升华。尤斯塔斯如此,真纳罗如此,卡泰丽亦如此。困住三人的房间,代表文明社会的繁文缛节,象征工业社会的文明枷锁,捆绑住人们亲近自然的行为。正如真纳罗所说“第一夜到来的时候,我可以跑过树林,爬上岩石,跳进水里,直到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2]。
真纳罗、卡泰丽和尤斯塔斯都受到潘神的召唤,他们的经历具有重复性,但又不是完全相同的。三人相似的经历编织出一张纵横交织的网,互相叠加,使得潘神的召唤变得更加立体:真纳罗比以往更加超脱地生活着,身心都是自由的,他热爱自然,理解世间万物,却没能抵得住金钱的诱惑;卡泰丽被关在房间里哀号,她对自然的渴望被门窗隔断,诉求不被家人理解,她绝望地哭泣,最终悲愤而亡;比起卡泰丽,尤斯塔斯是幸运的,在真纳罗的帮助下,他挣脱世俗的束缚,奔向森林和湖泊,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获得潘神赋予他的力量,脱胎换骨[5]。
三人得到潘神的感召,表现出对大自然美好乐章的向往和亲近,不顾一切地想要融入自然,歌颂自然,唯独无法理解的是冷漠的人类。此情节的对比描写,一方面,是为了佐证潘神的召唤真实存在,增加小说的说服力和可读性;另一方面,揭示被召唤者的不同结局,满怀对大自然的热爱继续生存下去,或者被困在现代工业的牢笼中死去。福斯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截然相反的结果呈现出来,将选择权抛给读者: 是继续浑浑噩噩地在工业机器中苟延残喘,还是挣脱束缚,回归本真的美好。
三、跨文本的重复
重复理论的第三种类型,即一部作品和其他作品的重复,更为宏观和抽象,多体现在故事框架、主题、人物性格塑造、情节发展、写作动机和写作技法等方面。这种重复是跨域单个文本范畴的跨文本性重复,它的构建赋予文学作品更深刻的内涵和更丰富的意义,而这种跨文本重复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2]。
借助神话故事构建小说,从本质上是赋予主人公一个英雄形象,开启一段英雄之旅。主人公离开舒适圈,进入完全陌生的环境。福斯特在其小说中常用的场景多发生在意大利(如《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希腊(如《始于科娄纳斯的路》)、印度(如《印度之行》)等异邦;亦可具体到一个场景,如树洞(如《始于科娄纳斯的路》),森林(如《惊恐记》《树篱的另一边》),山洞(如《印度之行》),梦境(如《天国公共马车》)等。主人公通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实现内心转变和灵魂升华,正如福斯特在其文学评论《小说面面观》中提到的圆形人物,在故事结尾,心智、精神和观念等各个方面均发生质的变化:从死气沉沉到活力满满,从刚愎自用到包容并蓄,从狭隘到宽容,从自私到无私,通过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带读者一同感受小说的魅力。
在以神话为模板的小说构建中,可以找到相类似的环节,由此形成跨文本的重复。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作者根据写作意图和情节设计,灵活选择所需要的环节。小说模型,可以分为十二个阶段:正常世界—冒险召唤—拒斥召唤—见导师—越过第一道边界—考验、伙伴、敌人—接近最深的洞穴—磨难—报酬—返回的路—复活—携万能药回归[6]。
福斯特的小说情节设置亦遵循此模式。在《惊恐记》中,出现以下的重复环节,或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呈现,或以隐晦比喻的方式呈现。
(一)正常世界
主人公“从平日里的世界冒险进入一个充满超自然奇迹的地域……”[6]平日里的世界,既正常世界,窥探其中,可以获悉主人公在开端承受何种使命或负担,内心有何种挣扎或煎熬,奠定故事的基调,预示主人公的命运走向。
《惊恐记》中,尤斯塔斯随众人前去森林游玩,闷闷不乐且不合群,人物性格突出,为后续故事中“潘神”降临时,他与众人天壤之别的反应做出铺垫。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时常借叙述人介绍背景,呈现正常世界,如《仲夏夜之梦》中,主人公赫米亚为反抗父亲的逼婚,与心上人拉山德逃到城外的森林,碰巧遇到精灵仙王和仙后闹别扭,从而上演了一出啼笑皆非的戏中戏,亦是从现实世界跳脱到奇遇世界。
《惊恐记》开头众人游玩的欢快基调与之后“潘神”降临时紧张惶恐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正如美国作家弗兰克·鲍姆的成长小说《绿野仙踪》里,以黑白方式呈现的正常世界与色彩绚丽的奇遇世界“奥兹国”构成对比。
(二)冒险召唤
小说主人公所处的正常世界大多是表面平稳却暗藏躁动,只需一个偶发事件或一系列巧合作为触发点,可以是来自外界的直接刺激,如亲人离世、遭受背叛或天灾人祸,也可是源自内心长期积累的无意识觉醒。本质上讲,是人类共同的内在需求驱使主人公肩负起“唯有改变才能生存”的使命。
《惊恐记》中尤斯塔斯将树枝削成哨子,吹出众人闻之蹙眉的声响,恰巧唤出擅长演奏排箫的“潘神”。尤斯塔斯在暗示“潘神”足迹的山羊蹄印上欢快地蹭来蹭去,主动回应冒险召唤,因为在正常世界,他格格不入,唯有做出改变,打破僵局。但是,不是所有的冒险召唤都是积极正面的,更多的是暗示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走向。如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尤利乌斯.恺撒》中,有人在恺撒遇刺前警告他“小心三月十五日。”在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海洋小说《白鲸》中,有疯老头警告船员此次冒险凶多吉少,故事最终,亚哈船长及船员同白鲸莫比·迪克同归于尽。
(三)考验、伙伴、敌人
主人公进入惊险刺激的非常世界,“充满了古怪、流动和含混形貌的梦境般景色,他在那里必须通过接连不断的试炼”。[6]《惊恐记》中,主人公尤斯塔斯在主动回应冒险召唤后,与众人一同经历“潘神”的考验,极致静谧引发的恐慌“如同一只大绿手”伸向众人,众人在无端的恐惧的支配下四处逃窜,唯有尤斯塔斯泰然自若地继续享受大自然的宁静悠闲。考验,这一环节是非常世界最为精彩的高潮部分,只有经受住考验,故事才能继续开展。希腊神话中,丘比特与普赛克的爱情故事便有典型的考验环节:普赛克为了赢回丈夫的心,接受女神阿弗洛狄忒提出的三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凭借善良,在伙伴的帮助下,完成任务,得到宙斯的赦免和封神。
主人公在考验和磨难阶段,会遇到伙伴和敌人,前者给予帮助,后者制造麻烦,分清敌友,需要主人公看清局势,明辨是非。《惊恐记》中,伙伴身份的真纳罗在金钱的引诱下,险些倒戈,经过内心挣扎后,以生命为代价帮助尤斯塔斯成功脱逃;众人由于无法感知“潘神”的冒险召唤,企图将尤斯塔斯关在房间,无意识之下充当敌人的角色。
伙伴的典型形象,星期五,是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知恩图报且忠诚智慧的配角,他陪伴主人公鲁滨逊一路化险为夷,最终一同获救并成功融入文明社会。美国作家司机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的贪婪和背叛最终导致主人公盖茨比的悲惨结局。在但丁的《神曲》中,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灵魂带他穿过地域和炼狱,情人贝阿特利切的灵魂引导但丁来到天堂,见到上帝。借助主人公冒险途中的各色人物,本质是在认识实现主人公的自我觉察,挖掘主人公的内在和认知变化。
(四)磨难和复活
在英雄一路披荆斩棘的道路上,读者最喜闻乐见的环节便是在主角光环的笼罩下,主人公“大难不死”或“起死回生”。几乎所有故事的主人公都会戏剧般地面临死亡或死亡级别的磨难,且凭借一腔孤勇或在伙伴的帮助下,在实际意义上或象征意义上获得重生。
《惊恐记》中,磨难环节聚焦在众人从森林返回旅馆的夜晚,尤斯塔斯险些被关在房间,倘若如此,便会和同样受到“潘神”召唤而被关在房间的卡泰丽一样,一命呜呼。命悬一线之际,真纳罗挺身而出,尤斯塔斯才成功进入森林,继续接受“潘神”的感召,从而完成彻底的蜕变。
最为典型的起死回生场景,便是基督耶稣为救赎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在第三天复活。典型的磨难环节在另一跨文本的重复,当属《荷马史诗》下《奥德赛》,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乘船返回,途中在海上漂泊十年之久,尝遍人间疾苦,最终得以返还家乡。在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伟大前程》中,主人公匹普意外得知自己的资助人马戈维奇是在逃犯,难以面对现实,偏离正常轨道,但最终在乔(伙伴身份)的帮助下,战胜虚荣,回归良善。
《惊恐记》是福斯特早期颇具代表性的一篇短篇小说,是福斯特首次尝试“操控主题”式的写作,亦真亦假,亦虚亦实,创造出一个游离于现实和神话的平滑空间。借助潘神的神话形象表达福斯特对工业时代逐渐取代农业时代的悲叹之情,“潘神已死”,人类对大自然的热爱和珍惜也淹没在工业时代对物质的狂热追逐中。小说中重复出现的意象、情节以及小说对希腊神话的框架重复都是福斯特精心构架的一个平行空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有了重复的元素,读者才能够从看似平常却又反复出现的细节中发掘到小说中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