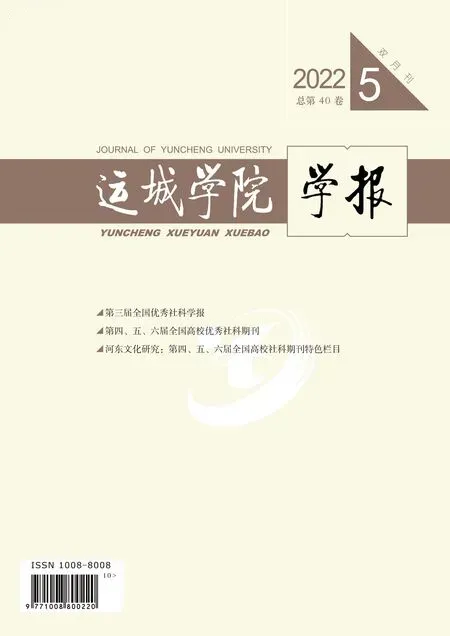从“以实见虚”到“以虚观实”
——老子“虚”“实”思想刍议
2022-04-07郝二伟
郝 二 伟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虚”“实”作为《老子》中重要的范畴,是老子用以论述道体及道物关系的重要概念之一。历代学者对于“虚”皆有所关注并着墨颇多,但对于与“虚”相对待的“实”却讨论甚少;事实上老子固然重视“虚”,但在老子看来“虚”并非是“无待”的,而是与“实”紧密关联、甚至是以“实”为本才能体现“虚”并借以发挥其效用的。因此,在老子思想体系中并非是“重虚轻实”,而是“虚实并重”。
一、《老子》“虚”“实”之历代相关研究
最早注意并发挥老子“虚”思想的人是庄子。(1)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问题,学界多有争议,本文采用较为流行的说法,即认为老子与孔子同时而稍早、《老子》一书亦为老子出关前所作之说,而《庄子》也认为为庄子本人所作,且为老子之后而在稷下道家及荀子之前。《庄子·人间世》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在老子那里并未明确说明“虚”中具体内容为何,但庄子将之发挥为“虚”即气,郭象就此注曰:“遣耳目,去心意,而付气性之自得,此虚以待物者也。”[1]也即虚空其心,只余气性之寂泊方能应外物。庄子也是最早将“虚”与气相联系的思想家,(2)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1、122页。陈鼓应先生认为《管子》本于《庄子》,而《孟子》某些思想又源于稷下道家。他甚至认为道即气[2]——“人之生,气之聚也,……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由此可见,在庄子看来“虚”不仅不是一无所有之“无”,反而是被气所充满,乃至于“通天下一气耳”,气则是“构成万物的质料”[3],就连人之生死亦不过是气之聚散,说明庄子对老子之“虚”的发挥是指向实存的。稷下道家对老子“虚”的概念也做了重要的引申和发挥。《管子·心术上》云:“虚无无形谓之道”,(3)此处之“虚无无形”应作“虚无形”,《文选》注引此句有的本子即作“虚无形”,《黄帝四经·经法·道法》“虚无形,其寂冥冥”是此辞例,王念孙则以“虚无无形”作“虚而无形”。参见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45页。直接将“虚”等同于道之代名词,又说“天之道,虚其无形。虚而不屈,无形则无所位;无所位,故遍流万物而不变”,则直接继承老子之“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表述,同样认为“虚”绝非一无所有,而是将“虚”之道具象化,对老子形上之道进行了创造性继承与转化,“将原本抽象渺远之道具象化而为精气”[3],也即以“精气”与“虚”加以联系。稷下道家对“虚”的发挥还体现在认识论方面,《管子·心术上》说“虚之与人也无间,唯圣人得虚道……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能虚矣。虚者,无藏也。”表明稷下道家对“虚”概念的理解接续老子对“虚”之认识论的理路继续加以拓展,“‘虚’成为主体得以如实认识客体所必须具有的前提,此前提即是‘无求’的心态,亦即排除主体之成见与贪欲”。[3]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稷下道家不仅关注老子之“虚”,也同样关注“实”的一面。《管子·内业》说:“凡心之形,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这些篇章在强调心之性(“虚”)的同时无疑也是在强调实存的心之形体。整体而言,稷下道家仍然重“虚”而相对轻“实”。荀子继承了庄子及稷下道家将“虚”与心相关联的理路,他说:“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荀子·解蔽》)。(4)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72页。陈奇猷先生认为荀子此处所言之“虚”正是《韩非子·解老》篇中所言“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之“虚”。原文作:“《荀子》所云正是此文(指《韩非子·解老》中此段文字)‘虚’字之义。”在荀子看来,“虚”亦与心紧密相连,他认为“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能“致虚”,正因为这一功能,“心”才能体道,可见荀子也是在认识论的层面论述“虚”。而先秦最早注解《老子》的韩非子说:“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虚者之无为也”(《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将“虚”与“无为”相联系,他认为能“致虚”者方能“无为”,可见韩非子将“虚”引向了实践的进路。王弼则是将老子之“虚”引入形上的进路,他说:“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4]可见王弼将“虚静”做一种形上之境界加以诠释。以上学者大致皆重老子之“虚”而相对忽略了老子思想中“实”的一面。降至宋代,国家、民族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导致了社会风气普遍尚“实”,许多学者开始对老子之“实”的一面有所注意。王安石就“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评论说:“‘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也。”[5]116陈鼓应认为王安石是对‘无之为用’而忽略‘有之为利’的情况之批判。[5]116也就是对前人只强调“虚”之用而忽略“实”之利的批判。苏辙也对老子之“实”做了一定程度的凸显,他说:“夫是以贤者用而民不争……是不亦虚其心而不害腹之实、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强也哉……则是心与腹皆实也。若举而废之,则是志与骨皆弱也。心与腹皆实,则民争;志与骨皆弱,则无以立矣。”[6]可见在苏辙看来老子既重视心之“虚”、志之“弱”,同时也强调腹之“实”、骨之“强”,二者不可偏废、更不可混淆。对于老子“实”概念的强调最激烈者或当属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老子衍》中王夫之说:“造有者,求其有也。孰知夫求其有者,所以保其无也?经营以有,而但为其无,岂乐无哉……”[7]如果说前代学者对于老子“虚”、“实”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仅强调“虚”,以及在强调“虚”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实”这两大派的话,那么王夫之则属于第三派——他强调“实”才是老子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虚”只是“实”的附属品。但到了现代,许多学者并未继承前辈学者研究《老子》时开创的尚“实”之风,将之进一步引申、发挥,而是又开始延续历史上研究老子重“虚”而轻“实”的路径。
无论如何,老子“虚”“实”观念历来受到学者重视。但在论述“虚”时多由“虚静”入手,而对于“虚”本身内涵的探讨却模棱两可;此外对于与“虚”相对的“实”关注也相对较少,相关讨论亦显得支离破碎,对于二者关系的讨论更是语焉不详。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究《老子》中虚、实及其关系以系统梳理并揭示《老子》中“虚实并重”之真意。
二、虚实对待——存在论角度之虚实
(一)老子之“虚”
《老子》以“虚”论道体及道物关系,但这个“虚”究竟是何意义呢?从存在的角度而言,老子提到的“虚”,并不等同于真空或零。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5)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页。王弼注曰“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穷”,可见此处应作“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而非“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四章)冲,古“盅”之假字,傅奕本《老子》此处作“道盅而用之”,另外《说文》:“盅,器虚也。《老子》曰:‘道盅而用之。’”俞樾认为此处的“冲”乃“盅”之假字(6)同上书,第13页。,此处之“冲”所指代者正是“虚”。《老子》十一章又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正与此处的“冲而用之”相对,可见在老子看来此处之“冲”与十一章的“无”(“虚”)是相同意义的概念。而“虚”正与“实”“盈”相对待,若“虚”为真空,将何以“用之”?又如: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五章)。严复云“‘屈’音掘,竭也。‘虚而不屈’,虚而不可竭也。”[5]可见若此处之“虚”指的是真空或零,又将何以“不竭”?“中”亦非指儒家孔孟所讲的“中庸”“中道”之“中”,而是指“虚”。(7)王弼注曰:“橐龠而守中”。楼宇烈、陈鼓应等皆认为此处之“中”指“虚”,见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第17页、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第95页。因此在老子看来这里所说的“虚”是指“混沌”“窈兮冥兮”、气一类的东西。“冲”“不盈”“渊兮”都是老子以“虚”来说明“道”之“形象”“性质”的词。然而道本无形,既然无形就无法以有形之物比拟、言说,“不盈”“渊兮”“橐龠”也不过是“似”“或”,但这些对“道”之“虚”勉强的比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并非完全的空无一物或真空状态,如橐龠中空但毕竟有橐龠之体;山谷虽虚但却有由岩石、土壤所构成的山谷之架构;盅内虽虚但周围却也有由陶土所烧制而成的杯沿和杯体。可见“虚”只是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必须以“实”为基础才能彰显、体现。无论“虚”成何种程度,毕竟不可能完全为零或真空。陈鼓应先生指出,道虽“虚”,但这个“虚”却并非一无所有,而是在内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创造性因子,(8)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最新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1页。作者认为:“道体是虚状的。这虚体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它却含藏着无尽的创造因子。因而它的作用是不穷竭的。”所以才说其作用“不屈”(不竭)。“虚”必须寄寓于“实”并与“实”相结合才能发挥出其作用并彰显、体现,否则就成了零、真空。也就是说,老子之“虚”是“有待”的,其所“待”者,正是“实”;若离开“实”,则“虚”不仅无法彰显、体现,无法发挥其功用与价值,也会沦为彻底的“无”(零或真空)之状。
(二)老子之“实”
正如重视“虚”一样,在论道及道物关系时,老子也极力强调“实”。那么何为“实”?《老子》说:“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谷无以盈,将恐竭”(三十九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四章)、“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四十五章),上文已提及,谷、冲在《老子》中指代中空,即指代“虚”[5];那么“盈”与谷、冲相对待,也即“盈”与“虚”相对待,则此“盈”,也就是谷之盈满、冲之填充[5],自然指向“实”。如果这里仅仅是老子对“实”的抽象概述,那么他接下来说的“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9)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作“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乙本作“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则是在形上与形下两个方面将道、德之“虚”与物、器之“实”置于并重的地位,曹峰先生就认为在此处老子是将作为形上本根的道、德与作为形下万物的物、器作为并列的概念而列出。[8]可见老子还将与“虚”之道、德相对应的实存之物、器作为“实”而与之并列。此外,《老子》第十一章中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可见在老子看来,辐毂、埏埴、户牖等实际存有的、有形有质的,且与辐毂、埏埴、户牖之中空处相对待者就是“实”。而此处老子以车毂、埏埴、户牖说“有”,而以三者之中空论“无”,显然与第四章、第五章提到的“虚”义一样,在此章中提到的“无”所指者亦器具之中空处,“有”指的则是实存之器具。同时,王弼认为“有”“无”需要相配合,“有”给人们的便利只有与“无”相配合时方能实现(10)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页。王弼注曰:“言无者,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实存之器具自然属于“实”,而器具之中空处则显然属于“虚”,但此虚空亦非指零或真空,否则何来“利”“用”?对此陈鼓应先生强调说:“一般人只注意实有的作用,而忽略空虚的作用……老子特别把这‘无’的作用彰显出来。”(11)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最新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7页。作者认为:“一般人只注意实有的作用,而忽略空虚的作用。老子举例说明:一、‘有’和‘无’是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二、无形的东西能产生很大的作用,只是不容易为一般人所觉察。老子特别把这‘无’的作用彰显出来。”而任继愈先生则就此处批评老子说:“老子认为对一切事物起决定作用的是‘无’,而不是‘有’。这里老子忘记了,如果没有车子的辐和毂、没有陶土、没有房子的砖瓦墙壁这些具体的‘有’,那些空虚的部分又从哪里来?又怎能有车、器、房子的用处?”[9],由此任先生认为老子把“有”和“无”,即“实”和“虚”的关系完全弄反了。[9]事实上老子此处之本义并非一味强调“无”(“虚空”)而忽略“有”(“实存”),而是在重视“虚”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实”,只是对二者的重视程度有所差异而已。老子固然重视“无”、“虚”之用,但此“用”必须在“以盈”、“大盈”(皆指向“实”)的基础上才能被彰显、体现,否则就会“将恐竭”、“穷”;在凸显“当其无”的同时,也一直在强调“有车”“有器”“有室”;重视“无之以为用”的同时也凸显“有之以为利”。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老子》所说的‘道’,是‘有’与‘无’的统一。因此它虽然是以‘无’为主,但是也不轻视‘有’。它实在也很重视‘有’,不过不把它放在第一位就是了。第十一章说……这一段话很巧妙地说明‘有’和‘无’的辩证关系。房子里面是空的,可正因为是空的,所以才起了房子的作用。如果是实的,人怎么住进去”。[10]可谓允当。
值得注意的是,在《老子》中“有”“无”范畴出现次数较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指代的正是“虚”“实”。如十一章中“有”“无”明显指“实存”之器与器具之中空处(“虚空”)。“虚”“实”必须相互配合才能真正发挥出作用,为人们提供便利。正如陈鼓应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本章所说的‘有’‘无’是就现象界而言的……这里所说的‘有’就是指实物,老子说明只有当它和‘无’(中空的地方)配合时才能产生用处。老子的目的……更在于说明事物在对待关系中相互补充、相互发挥。”[5]由此可知,老子并非一味强调“虚”,而是在突出“虚”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在极力凸显“实”。
(三)虚实对待
老子论虚实,意在论道体及道物关系。从道物关系出发,他认为虚实之间是类似于“虚以生实”、“实中藏虚”,且“以实为利”“以虚为用”的关系。事实上老子之所以构建“道”而又以包括虚实等概念描述道、宇宙及道物关系,其出发点、最终归宿并非宇宙论,仍旧是着眼于人生界、现象界。(1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94页。徐先生认为:“老学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在于宇宙论的建立,而依然是由人生的要求逐步向上推求,推求到作为宇宙根源的处所,以作为人生安顿之地。因此,道家的宇宙论,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哲学的副产物。他不仅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来发现人的根源,并且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来决定人生与自己根源相应的生活态度,以取得人生的安全立足点。”而一旦与人生、现象相联系,必然要强调“实”,因为对于人生、现象而言,无论是作为认识的对象、还是存在形体,皆属于“实有”范畴。老子其实从未吝啬于强调这一点,如: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道体虽然是“虚”的,但这个“虚”并非一无所有之无,也即并非零、真空状,而是蕴含着无穷的创造性因子。[5]冯友兰先生也认为老子说道是“无”,并非指抽象概念,它所指的正是无形无名的元气或精气;所谓的“有”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所指的就是天地万物。因此道一方面惟恍惟惚,一方面又是“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10]“虚”必须作用于实物,透过实物的媒介作用而得以显现它的功能。[5]在老子看来,“虚”与“实”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才能彼此彰显的关系。道体为“虚”虽然“恍兮惚兮”“窈兮冥兮”,但“虚”中却实实在在蕴含着“实”——“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惟恍惟惚”“窈兮冥兮”固然是“虚”,但“其中”蕴含着的“象”“物”“精”“信”这四者显然是在“恍惚窈冥”之“虚”中所生之“实”;原本微不可见之“虚”经物之“实”作为媒介才彰显其存在与作用,因此,老子才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也即以“实”为利,以“虚”为用。
三、“为学”向实与“为道”向虚
从认识论角度而言,老子亦在重视“虚”的同时注意彰显“实”。陈鼓应先生指出:“《老子》论‘虚’,一方面涉及空间义之‘虚’,如谓‘天地之间,虚而不屈’,另一方面则就心境而言‘致虚极’”。[3]但陈鼓应先生同时认为到了稷下道家时老子中的“心境之‘虚’”才转化为认识论上的概念。[3]如果就存在而言说老子之“虚”涉及空间义,那么就认识而言老子之“虚”则早已涉及陈鼓应所说的心境义进而及至认识论层面,而不必等到稷下道家时才为其发挥了。《老子》第四十八章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作为实存但没有任何固定性质之道体既“虚”,人若想体道,将何以知之?“道”本身包含道体与道之功用两种内涵,体道与认识道之功用所采取的路径并不相同。道体本“虚”,因此体道的进路必然指向“虚”;而道之功用则必须通过“实”之器物才能彰显、体现,因此认识道之功用的进路必然指向“实”。也就是说,体道(指向“虚”)与认识道之功用(指向“实”)的路径截然相反。在老子看来,认识道本身(指向“虚”)所遵循的路径是通过“损”的方式,即消解掉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对现象界实有万物之经验而产生的知识,回到“闷闷”、混沌、寂兮寥兮、恍兮惚兮的道之本身(“虚”),其中不包含任何“实”之性质,因此他强调“为道日损”。而事实上老子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主张“损”思想的人,可以说老子是“损”“益”分别思想的创始人[11]。与之相对,认识道之功用(指向“实”)所遵循的路径则是通过“益”的方式,即通过积累、扩充的方式,不断增加对世间实有万物的经验性知识方可实现对道之功用的认识。因为道贯穿万物,道之功用亦即万物之功用,通过认识万物之功用这一进路自然也就可以认识道之功用,也即通过认识万物之“实”的各种性质,进而认识道之功用,所以老子强调“为学日益”。而事实上作为无形无相、“惟恍惟惚”“窈兮冥兮”的“虚”之道,本来不可“道”、不可“名”,但为了认识它,只有先通过“许多经验世界的名词去说明,然后又一一打掉,表示这些经验世界的名词都不足以形容”,[8]才能引导、启示人们认识道之实存性。由于道体本虚,既不可“道”又不可“名”,人们无法像认识万物一样通过感官去认识道,因此老子以“反显法”,以“实”为载体,以彰显道体。也就是说要想认识道、体会道,老子给出的方法是通过“实”去体验、去觉察、去认识。这就要求人们首先了解“实”,而“实”也就是世间万有,含有各种性质,需要通过积累的方式去认识,也就是“为学日益”。这种认识的方式也为庄子所发扬,《齐物论》中就说“以指喻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陈鼓应先生认为庄子的意思是说“从‘此’的一方作衡量的起点,不如反过来从‘彼’的一方作衡量的起点,如同郭象所说的彼和此能‘反复相明’”。[12]在此处,也就可以通过万物、人为之“实”来认识道之“虚”了。
“为道日损”,固然是提倡在“体道”、在道的层面要“虚心”。这是因为在老子看来“道”之本身指向“虚”,超脱于一切万物之“实”尤其是人为之“实”。作为主体的人要想认识道、体验道必须也做到“虚”,即脱离一切“实”尤其是人为之“实”方可真正与道合一;但只有首先通过认识万物(“实”)从而意识到道之实存,继而与道合一才能真正认识道。既然与道合一,道又贯穿万物,那么认识道也就是认识自己、认识万物;而作为“实有”之万物、人,生活、思考皆立足于现象界,活动时空也都限于现象界,真正为人所认识、体验、生存之必须者、须臾不可离开者乃是道之功用。如果我们承认老子之前所描述的道之本体指向“虚”,则道之功用无疑指向的乃是与“虚”相对的“实”。而与“实”相联系的正是各种“名”(世间万有)所代表的属性、经验、知识,要想认识这些“名”,只能依靠积累、依靠由小扩展至大、由简易扩展至复杂。因此老子并不反对“为学日益”(四十八章),反而强调通过“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样的方式先认识“实”,以“实”为媒介,在经验层面、通过积累知识和经验以提高对事物(“实”)的认识这一进路,之后再配合“日损”来达到认识道的最终目的。“日损”不仅是一种认知、体道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工夫、修养方式。鉴于所“损”者非一日而就,老子刻意强调“损之又损”,而且“损”之后“以至于无为”,“无为”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有为”,因此老子最后补充说“无不为”。由此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体道、认知以及修养的进路。而在这一进路上,老子显然并非是在一味地强调“虚”(“日损”),而是同时也在强调“日益”“无为”“无不为”,“日益”者何?“无不为”者何?只能是“实”。
四、从“以实见虚”到“以虚观实”
老子以“虚”论道、用,以“实”论物、利,最终还是要回到认识的主体——人生中。也就是最终还是要从“虚”回到“实”中。鉴于老子的出发点是人生,继而“逐步向上推求,推求到作为宇宙根源的处所,以作为人生安顿之地”[13]然后再“归根”,即回归到人生。这一进路也就是先由“实”(人生)见“虚”(道),再以“虚”现“实”(人生),对于究竟如何才能实现这一进路,老子给出的方案是“观”。
体道之“虚”要通过“观”,认识道之功用、万物之“实”亦需通过“观”方能实现。《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第十六章)第一章也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里的共同点是都突出了“观”这一方式的重要性,那么何谓“观”?所谓观,就是站在事物本身的立场,以事物本来的面貌去关照、看待、认识事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并非皆指感官之“看”。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观,要照事物的本来面貌,不要受情感欲望的影响……必须保持内心的安静,才能认识事物的真象。”(1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1980年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9页。原文如此。人要“观”道,必须站在道的立场,按照道的本来面貌才可能体会道、认识道;而道体本虚,“看”是不可能“观”道的,而是人必须达至“虚”的境界才可能体验道。因此老子才强调人若想体验“虚”之道体,必须“致虚”、“守静”,自己首先站在“虚”、“静”的角度,也就是站在道体本身之角度,才能真正体道。这里的“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亦然。对于前一句,王弼注曰“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14],很显然王弼认为此处之“妙”指向“虚”,也即道本身指向虚——只能通过体认、直觉加以认识而不是靠感官、知识和经验(这些对应的对象皆为“实”);“常有欲以观其徼”,“徼”字有作“归终”解者、有作“曒”(广大光明)解者,亦有作“边际”(大路旁之小路)解者[13],无论何种解释,此处无疑均指向“实”。
老子固然重视“以虚观虚”,但他同样重视“以实观实”。《庄子·天下》说“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冯友兰先生解释这句话说“《老子》讲无,这就是空虚。可是这个空虚并不是要去掉万物。《老子》所讲的无,其实就是有,无和有是异名同谓。它所讲的虚,其实就是实。”[15]道体本虚,作为万物之初始,其超越经验,无法通过感官加以认识。但人要体道,必须首先通过观察世间万物获得经验、知识,然后再通过命名的方式意识到道之实存,而这正是通过“观”的形式得以实现的,也就是“以实观实”。老子强调认识万物之“实”确实离不开命名,“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不命名则不可道,但要警惕命名的局限性,因此老子也是“强为之名”。一旦轻易去以命名方式认识万物之“实”,则“非常道”、“非常名”,也不免会陷入《齐物论》所揭示的知性悖论(14)即《庄子·齐物论》: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但“虚”本身就模糊不清,只有通过命名所指向的器物之“实”认识道之“虚”的实存性,也即通过山谷、橐龠、户牖等启发、引导人们去认识那个悠远玄妙、混沌不分、不可言说的“虚”之道的本来面目,即“以实见虚”。完成了这一步,才能进入“以虚观虚”的阶段。到了这一步还不圆满,毕竟只有当道与万物结合,“虚”寓寄于“实”才能被彰显、体现,才“有意义”;老子论道的最终目的也并非宇宙论的建立,而是“求得人生的安顿”,[14]因此老子在实现“以虚观虚”之后还要进一步实现其“以虚观实”“以道观物”“安顿人生”的最终目的。因此老子强调“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这里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实则已经是老子在“致虚极,守静笃”之后站在道(“虚”)的高度去观察万物、关照人生(“实”)了。(15)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增订本),卷一,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234页。作者认为此处之主体已经驻于无为、驻于道之高度,以此视角来关照道之超万物,亦观照万物之依于道。
由此可以看出,老子认为体道、认识道及万物之功用皆需通过“观”的方式,而要想观,必须首先做到“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在老子看来道先于万物而存在,万物皆由道以生且贯穿万物之始终,即“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五十一章)。因此要想“观道”,必须自万物身上着手。但道毕竟指向“虚”,而万物则为“实”,只有自“虚”方能观“虚”,因此老子在这里做了一个区分——他认为人作为主体之“实”,只有“心”方能胜任这“致虚”一功能,故而曰“虚心”“弱志”,严复就此解释说:“虚其心所以受道,实其腹所以为我;弱其志所以从理而无所撄,强其骨所以自立而干事。”[8]87这里的“虚”、“弱”作为老学特有的用词,与“实”“强”一样都是正面、肯定的意义[8]87。而一旦能够实现“虚心”“弱志”,并且能达到“致虚极,守静笃”的境界,就可以通过观察“万物并作”,继而“观复”了(16)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页。王弼注曰:“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所谓的“观复”正是指“面临万象而观其所依之道之意。”(17)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增订本),卷一,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233页。此外陈鼓应先生也认为十六章中的“观复”指的正是规律性的道(陈先生认为老子之道包含实存意义之道、规律性之道、生活准则之道三种),参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最新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35页。
就存在形式而言,心、志固然是有形质的具体之“实”存,但作为“观道”的主体,心有“致虚”的功能,因之能观道。但人除了心的功能以“致虚”外,无法统统实现“虚”“弱”,冯友兰先生就此强调说如果“把这个具体个体也损去,那就没有人了。没有人还有什么人生呢?”,[16]老子论道、论虚实,其起源、归宿皆在于人生。因此老子在强调“虚其心”“弱其志”以观道的同时,也重视要针对个体的人“实其腹”“强其骨”。只有首先实现了“腹实”“骨强”,才能在此基础上“虚心”、“弱志”以实现“观道”的目的。
就如何实现“以实观实”进而“以实见虚”,然后“以虚观虚”最终“以虚观实”这一回路中,老子的逻辑进路非常严密。比如这里老子指出在“实腹”“强骨”的基础上“虚心”“弱志”是体道的必要进路,对于具体该如何实现“虚心”老子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涤除玄览”。然而在论述这一过程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老子之所以采用这一方式的背景。
“以实见虚”的悖论
道,必须要“道”,即通过言说、命名、概念等方式加以表达,否则无法被彰显。无疑,无论是言说、命名或概念皆指向万物之“实”,这种指向“实”的方式来表达道之“虚”,即“以实见虚”,毕竟还是有局限的。以命名的方式认识道很容易将之具象化、形质化甚至歪曲化。但若不通过命名,实存之道本虚而又“惟恍惟惚”无法被体现,更不可能被人所认识。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那么老子是怎么做的呢?显然,即便老子清晰地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他为了使得道被体现、彰显,“终究还是选择了言说”[16],选择了“强为之名”,这才有了《老子》这本著作。而老子又是如何处理这一“悖论”的呢?他分了两步:一是从实存之万物着手,通过观、命名、积累等方式“为学日益”,在这一进路中逐渐认识到“实中藏虚”。在完成第一步的过程中,老子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即以模糊、含混不清的命名、概念(皆指向“实”)来描述道体、道的状态(指向“虚”),但即便如此仍然有将道具象化的嫌疑,他只能极力注意尽量弱化命名的具象、分辨功能,试图以此达到既能彰显道的目的,又能尽量避免道的形质化。因此老子多用“或”“似”“若”等模糊性的词以及谷、一、玄牝、橐龠等加以比喻。第二步则是在第一步基础上再将心中业已形成的对万物之“实”的印象、经验、知识统统舍去,“为道日损”且“损之又损”。这就需要“涤除玄览”(18)马王堆帛书乙本《老子》作“涤除玄监”,通“鉴”;北大汉简本《老子》亦作“涤除玄鉴”。此外高亨认为即便是通行本之“涤除玄览”,亦应读作“鉴”,古字“览”“鉴”二者通用。参见高亨:《老子正诂》,开明书店影印版,第24页。的工夫了。所谓“涤除玄览”,就是去掉、摒弃心中一切知识、成见、杂念、欲望,使得心灵像一块镜子一样,以关照自心之本明(19)冯友兰、高亨、陈鼓应、郭齐勇等学者皆作此说。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60页、高亨《老子正诂》第24页、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第113页、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第233页。,即通过“涤除”的方式使得内心达到“虚”的境界,以关照道体之“虚”,也即“以虚观虚”。涤除玄览、至虚守静皆是直观式的体道方式,也可以称之为“静默式”。或许在老子看来静默式(去除命名、概念的方式)的直观才是体道(实)理想的方式[17]236(“以虚观虚”)。但万物之“实”(命名)是静默(“虚”)的前提。只有首先经过命名的方式,对万物之“实”有所认识进而达到能通过“实”认识到“实中藏虚”,才能进行“涤除玄览”“静观”等静默式“以虚观虚”的体道过程。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那样:“人往往需要先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17]”,即先“以实见虚”,然后才是“以虚观虚”,最后达到“以虚观实”的境界并以此关照、指引人生。
道以虚的方式生成万物,实为体,虚为用。即:强调道之虚,是从用的角度来说的,只有虚才可能生成万物;强调道之实,是从存在论的角度而言的,“虚”固然是道体之“本性”,但道毕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有、无、虚、实都是用来形容道的。道本身包含着道体与道之功用两种内涵,老子强调“虚”是为了正确、完整、全面地认识道,若人们一味强调“虚”而忽略“实”,则“虚”道之功用反而无法彰显,亦无法为人所认识。只有“以实为体”,同时“以虚为用”,通过万物之“实”以彰显道体之“虚”,虚实结合才能使得人们正确认识道、体验道,进而更好指引人生;也只有与“实”之利相配合,“虚”之用方能得以展现。劳思光先生在解释“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时认为“损”(指向“虚”)之后的“无为”本身以虚静守之,本为“破执”,乃以超越义,而欲以“无为”而转至“无不为”,则由超越界转至经验界,此时超越义之虚静之道的无为必须具备经验界事物的实质性内容,即守柔、不争、小国寡民,(20)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卷一》(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232-236页。也即虚静之超越义的“无为”之展开“无不为”——即由“虚”转向“实”。
结语
虚以实为体,实以虚为用。“虚”既是一种通过修养而归于本初之道的法门,同时也是老子想象中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但这种境界不仅强调虚静,也强调实强。对于具有形上哲思功能的“心”固然要虚,而对于实存强有的腹、骨等却要实,因为心之“虚”只有寄托于腹、骨之“实”中才能被彰显、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至虚”是老子提出的一种修道、体道之法门,但最终仍要以“虚”观道,继而“以虚观实”实现对人生(“实”)的指导与安顿。总之,老子虽然极力强调道的虚无,但实在也很看重道之实有。由此可见老子“虚实并重”而非偏重“虚”而忽略“实”之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