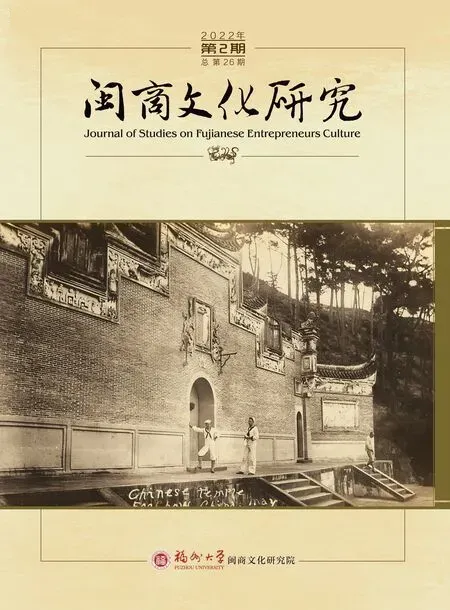向井元升《知耻篇》所见日本与隐元东渡异文化之碰撞
2022-04-07黑冈佳柾
[日]黑冈佳柾
何美玲译*
1654 年中国福建省福清万福寺隐元隆琦禅师(1592—1673)东渡至日本长崎,对当时日本禅宗界产生巨大影响,广为人知。已有的研究文献表明,隐元东渡携带了食物、明朝体等黄檗文化传入日本,并融入日本社会。而关于长崎,一般认为长崎作为当时日本锁国政策下唯一可开港与海外进行贸易的地区,因吸收了异文化而形成了独特文化。然而,隐元东渡日本带来的异文化碰撞,并不只有积极肯定的一面,当时日本对日本人迎合中国文化这一外来文化是存在批判声音的。其中批判者之一向井元升(1609—1677)著有《知耻篇》,本文通过解读该书,意在弄清其批判的实际内容,并通过器官移植比喻异文化碰撞,探讨向井的批判对于黄檗研究以及异文化交流理论的重要意义。
一、隐元东渡及其功绩——多种文化交汇之地长崎
(一)隐元东渡传入之物
福建省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主持隐元抵达日本之时,是日本承应三年(1654)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执政时期,正是日本实行锁国之后的第13 年。日本四度诚邀,促成隐元东渡的实现。①木村得玄:《初期黄檗派の僧たち》,东京春秋社,2007 年,第12 页。平久保章指出,当时正是日本强化锁国政策时期,禁止日本船只出海,禁止海外日本人归国,只限于长崎允许中国船只进入。②平久保章:《隠元》,东京吉川弘文馆,1962 年,第34—35 页。关于该历史背景下隐元东渡的原因,存在多种说法,有明末避乱归化日本的“避乱归化原因”说,有曹洞派之争失利到日本的“济洞僧诤原因”说等。③平久保章:《隠元》,东京吉川弘文馆,1962 年,第34—35 页。但一般的观点是,隐元是应邀东渡日本的。日本佛教界于1615 年完成法院制度,寺院之间、僧侣之间关系趋稳,佛教各派受严格的阶级观念所支配而限制了发展。长崎唐人寺院僧侣及信徒受阶级观念所支配,并受自身宗教信条的束缚,恳请隐元东渡普法。一般认为京都的临济宗万福寺,是德川幕府支持隐元建立而成的。因此可以认为隐元并非归化日本或者逃亡日本,而是受日本方面正式邀请前往日本的。当时长崎隆重欢迎隐元的到来。与隐元东渡同一历史时期住在长崎的向井元升写道“僧俗奔赴拜见隐元者,数以千计”④向井元升:《海表叢書·知耻篇》,木村得玄编:《黄檗宗資料集成》第二巻,东京春秋社,2015 年,第17 页。,由此可见,僧侣和众多百姓热烈地欢迎了隐元。小木裕文提到,隐元在日本创立的“黄檗宗对当时的禅宗影响甚大,以西日本大名为核心的武士阶层皈依者众多”。⑤小木裕文:《僑郷としての福清社会とそのネットワークに関する一考察》,《立命館国際研究》2001 年第14 期,第83 页。可见,隐元东渡受到当时广大人们积极的接受,虽然与妙心寺派有对立之实,但隐元创立的黄檗派(后来的黄檗宗)后来成为了日本宗教界的一大潮流。①关于与妙心寺对立及黄檗宗的后来进展,详见以下文献:平久保章:《隠元》,东京吉川弘文館,1962 年。禅文化研究所編:《隠元禅師逸話選》,京都禅文化研究所,1999 年。竹贯元胜:《隠元と黄檗宗の歴史》,京都法藏館,2020 年。
隐元的诸多功绩在日本佛教界内外影响颇广。小木裕文指出:“随隐元到日本的高僧、文人、工匠对日本佛教建筑、佛像雕刻、书画、素食、医药、园艺、印刷等方面影响广大。”②小木裕文:《僑郷としての福清社会とそのネットワークに関する一考察》,《立命館国際研究》2001 年第14 期,第83 页。日本吸收的黄檗宗文化从书法、绘画、印刷技术到木鱼明朝音乐、南京官话(明朝长江以南使用的语言)等等。此外,现代日本餐桌必不可少的隐元豆(四季豆)、豆芽、茄子以及普茶料理、煎茶、圆桌用餐等均是黄檗宗影响日本文化的实例。③アジア太平洋観光社编:《和華》2019 年第21 号,第22—31 页。隐元及其随从一行带来的文化不仅影响了宗教界,在饮食、语言等方面,亦潜移默化融入到现代日本生活,现代日本人甚至全然不觉这是外来文化。
(二)异文化交流之地——长崎
那么隐元最初抵达的日本长崎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已有研究多讨论了长崎的特殊性,主要观点有:显然长崎自古以来与中国交流频繁;近代日本与中国往来活跃时期是中国的明朝末期、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江户时代日本江户幕府禁止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基督教国家到日本,亦禁止日本人进出东南亚国家,实施了管制贸易的锁国政策。长崎是锁国政策下唯一可与荷兰和中国的通商之地,因而成为日本人与荷兰人、中国人交流之地而繁荣发展。如高山干忠所述,“17—19 世纪日本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长崎作为日本的对外门户,与中国等国贸易往来频繁,盛极一时”。④高山干忠:《中国から見た長崎の歴史的意義―要人来訪・長崎市・福州市との交流状況―》,《現代社会学部紀要》2012 年第10 期,第104 页。因此,单从长崎与中国的关系来看,一般也认为长崎是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交融之地。⑤参考以下研究文献:寺尾善雄:《中国伝来物語》,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82 年。大庭脩编:《長崎唐館図集成――近世日中交渉資料集六》,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3 年。根桥正一:《江戸時代長崎の中国人遊客》,《流通経済大学社会学部論叢》2014 年第24 期,第93—124 页。如山本纪纲指出“长崎的风俗习惯以及民间诸多活动,受外国影响很大,这是日本其他地方少见的”,特别指出长崎与中国交流深入,中国的风俗习惯至今仍影响着长崎人的生活。⑥山本纪纲:《長崎唐人屋敷》,东京谦光社,1983 年,第79 页。王维把长崎定位为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融合之地,指出:“自古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风俗习惯不断传入长崎,并融合了日本的百姓文化,被传承下来,时至今日仍交织着日常生活习惯、料理等出现在各种节日活动中,成为长崎独特的文化。”①王维:《日本華僑における伝統の再編とエスニシティ――祭祀と芸能を中心に》,东京风响社,2001 年,第3 页。锁国时代,长崎作为日本唯一的对外开放门户,与允许进出的中国人交流频繁,成为了不同文化交织的地域,现代长崎仍利用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发挥作用。即长崎是在与中国人的贸易往来中,“中国人的节日和风俗流行于日本社会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融入百姓生活,得以传承”的地域,其文化是“超越地域的文化”和“扎根于地域的文化”的经常性融合,是地域化的同时进行地域文化再生产而发展成的“长崎文化”。②王维:《「地域振興」における「文化」の受容と操作―「長崎おどり・ちゃんぽんフェスタ 2001 の創出過程から―》,《香川大学経済論叢》2001 年第74 期,第93、124 页。
对于长崎,现在的一般观点是长崎是异文化的融合之地,并基于这一观点去讨论长崎的节日活动和观光资源。例如藤村和宏、王维持续关注长崎观光资源中的异文化性,指出“该异文化性乃是长崎在历史上与日本国内外多地域不断交流的过程中,通过本土社会接受、编辑其他地域文化而创造出来的。”③藤村和宏、王维:《異文化性が生み出す観光価値を活用した観光戦略――長崎の「祭り」を中心に――》,《香川大学経済論叢》2016 年第88 期,第1 页。从地理上看,长崎位于日本西南角,邻近上海、宁波等中国沿海都市,北起韩国釜山,南至冲绳,与福建以及东南亚各地紧密关联。在此地理环境条件下,加上德川幕府实施锁国政策制约贸易,使得长崎接受他国文化的流入,发展成异文化交流之地。“日本锁国约400 年,长崎积极吸收外来文化,长崎人根深蒂固持有一种对异文化和外国人开放的、肯定的思想”,现在的游客和外国人也普遍认为长崎是热情的城市。④藤村和宏、王維:《異文化性が生み出す観光価値を活用した観光戦略――長崎の「祭り」を中心に――》,《香川大学経済論叢》2016 年第88 期,第29—30 页。
如上所述,诸多研究认为隐元东渡对日本宗教、文化等方面,均具有积极的意义,隐元最初抵达之地日本长崎是接受异文化、融合异文化的地域。但笔者仍有诸多疑问,对于隐元东渡与长崎是否只要肯定的言论?当论及长崎时,对本国文化和异国文化使用“融合”一词,既然是“融合”,就难以分辨异文化和本国文化的边界。藤村和宏、王维指出对外来者的开放性是长崎人的特色,但是否就不存在排斥外来者的封闭的一面?一味开放,如何分辨得清何为外何为内?关于隐元的研究,谈及隐元把隐元豆带到日本的言论,有积极肯定的一面,其结论是隐元豆被接纳了,在日本社会扎根,但说不定隐元豆曾有过破坏日本生态,顶着生态破坏者的恶名。在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对隐元与长崎的研究,谈及异文化时是否均可用“接受”“融合”“理解”“影响”此类稳健的词语来表述史实?正因为是异文化和外国人,当其进入内部时,应该会有被消极对待的一面吧。
接下来即将论述,向井元升把隐元本人看作是外国人——正因为是看作是外国人才进行批判,并把追随隐元的日本人看作是可耻之徒。这里如实反映出,当异文化中的外国人进入到自己国家、进入到本土文化时,向井将之作为“异物”进行排除、排斥的事实。那么,向井元升如何展开隐元批判的?以下将根据向井元升的《知耻篇》进行探讨。
二、向井元升《知耻篇》所见隐元东渡
(一)黄檗研究中对《知耻篇》的定位
向井元升是名儒医,出生于佐贺县,生活于长崎,在锁国时期特别喜欢研究长崎的国外书籍,有“海外思想的过滤器之担当”。①若木太一:《京都向井家墓碑考――文人向井元升の家系――》,《長崎大学教養部紀要·人文科学篇》1993 年第33 期,第1 页。隐元东渡之年向井46 岁,与隐元并不相识。1655年向井47 岁时,化名为“拾弃奴”著写《知耻篇》,宣扬神儒思想,对基督教、佛教以及隐元东渡新带来的黄檗宗给予强烈的批判,鲜明地表达“对异质文化、宗教/思想的态度的或接受或抗拒的姿态”。②若木太一:《向井元升著述考――東西文化の接触――》,《雅俗》2001 年第8 号,第130 页。根据竹贯元胜所述,黄檗宗研究者对向井的《知耻篇》关注度并不高。③竹贯元胜:《隠元と黄檗宗の歴史》,东京法藏馆,2020 年,第21 页。但向井实际亲身见闻经历了隐元东渡,并将当时长崎的情况写入《知耻篇》,向井对隐元等黄檗僧人的到来以及日本僧俗的皈依进行批判之后隐元前往京都,从以上事实可见向井的《知耻篇》是研究隐元以及黄檗诸僧对日影响的极其重要的资料,对于思考异文化碰撞,亦具有重要意义。
但《知耻篇》并非系统的、理论性的文章,而是偏向随想随笔,正如菰口治所指出的,《知耻篇》缺乏客观性,时有感性表达,但另一面也说明这是“江户时代初期长崎地方知识人士坦率流露所思所想”。④菰口治:《向井元升の『知恥篇』素描――神道・仏教・キリシタン観――》,《中国哲学論集》1993 年第19 卷,第68 页。《知耻篇》是对隐元及黄檗僧人等异国人士的碰撞带来“冲击”的语言化。该冲击是发生在对异文化理智理解之前,是“接受”这一俯瞰视角的最基础部位。因此,在黄檗宗研究中积极使用《知耻篇》资料,将此作为线索去探索隐元东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探究异文化带来的冲击亦具有相当意义。以下基于这一出发点解读《知耻篇》⑤以下引用均源自向井元升:《海表叢書·知耻篇》,木村得玄编:《黄檗宗資料集成》第二巻,東京春秋社,2015 年。。
(二)向井对隐元东渡一事的的批判及其射程
首先来看下向井的描述,看当时长崎人是如何面对隐元东渡一事。关于隐元到达长崎的情景,向井如是写道:
承应甲午七月上旬,隐元禅师乘船抵达长崎港口。居住长崎的唐人僧俗无一不前往迎接。亦有众多和僧出迎。围观群众急不可待,大胆到道上观望队列。只见隐元禅师乘轿而来,合掌默念,轿前唐僧皆手持燃香,引领队列。前来迎接的和僧均穿戴整齐,倾首奔忙,足不停歇。①《海表叢書·知耻篇》,第87—88 页。
由此可见隐元东渡引发了长崎迎接的狂热盛况。隐元抵达长崎,驻长崎的中国僧人自不必多言,日本僧侣以及一般民众也摩肩接踵夹道相迎。以上描述可见隐元不仅受到长崎僧侣的热烈欢迎,亦受到广大普通民众的欢迎。“男女老少参见,三拜者不舍昼夜”②《海表叢書·知耻篇》,第102 页。,可见无论男女老少,夜以继日参拜隐元住所。向井在记录长崎民众对隐元的态度时,对大家的态度提出了质疑。原文如下:
僧俗奔走参拜隐元者,数以千计。和僧中,参拜隐元者无不一改和僧装束,甚至诵经称名、言语礼节、饮食衣服等,皆有变化。禅师顺势而为。③《海表叢書·知耻篇》,第17 页。
此处向井指出的是,欢迎、参拜隐元者中,不只是参拜,在语言礼节、饮食方法甚至服饰上,都模仿隐元以及黄檗僧。简而言之,向井对日本人丢弃自身文化,为中国风的文化所感化,并去模仿一事表示忧虑。向井所批判的并非隐元本身,而是那些追随隐元、狂热地一改日本风为中国风的日本人。向井向这类日本人呼吁“知耻吧”:
聚集到隐元禅师处的众和僧无不改日本僧风为唐僧装束,甚是滑稽可笑。和僧装束本是传统正式服饰,无故改装,实在可耻。④《海表叢書·知耻篇》,第39 页。
向井的见解是日本僧侣因隐元东渡而一改日本传统习惯、风俗,轻易迎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实在可耻可悲。日本僧侣的中国化行为,只徒留日本人之名。对于这些舍弃日本传统风俗习惯的僧侣,向井表达了极度的厌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随唐风习俗,喜好唐俗服装者,滑稽可笑。其气质有如隐元手下僧众。日本儒者因而唐俗装束,日本人皆成唐人,日本徒有国土,徒有日本之名,实是中空。如此易俗,遗憾之至,可耻之至。⑤《海表叢書·知耻篇》,第40 页。
对日本而言隐元是外国人,携带异文化入日本一事本身,向井并不至于批判至此。向井认为关于欢迎隐元此事,日本人不应该追随外国人隐元到此地步,特别是打扮成唐僧装束、模仿隐元等中国僧的风俗习惯,否则不能称之为日本人了,他们已成中国人了。如此一来,日本这个国家徒有虚名,失去了本质。向井对此状况是深感失望,因此认为他们是日本之耻。
隐元及黄檗僧的研究者,或许对向井的批判并无过多思考,一般认为日本僧侣和普通民众都愉快地欢迎隐元,认为日本接受了黄檗派文化。倘如坦诚地看到向井的批判,就无法高度地肯定评价黄檗文化的接受问题。隐元东渡一事对向井而言,一方面是对他国文化的接受,一方面是影响到本国文化的“威胁”,淡化这部分“威胁”,仅仅截取对隐元和黄檗派文化的接受,隐元及黄檗派的研究就不完整。从异文化碰撞这点看来,片面肯定是过于稚拙的讨论。在向井看来,隐元及黄檗派文化流入日本,是让日本人不成日本人的“威胁”,是无法用“受容(接受)”二字所概括的事态。那是让本国的“法”屈从于他国的“法”,这是损毁自古以来神道指引的日本人的本性,向井在这一点上敲响了警钟。
日本人应尤其深以为耻的是从异国规矩,用异国法,媚于异国人。……因而乱了日本人本性,背驰天道,弃神道。此乃入邪教,其灾难波及子孙后代。此次隐元禅师来日,众人参拜禅师,尊其胜于拜佛。僧俗男女心神不宁,不得平静。甚至日常诸事见乱,应引以为耻。稳定心神,为妥。①《海表叢書·知耻篇》,第40—41 页。
由此可见隐元东渡的确受到当时长崎人们的欢迎,但向井认为日本人不应丢弃自国文化和风俗习惯,去模仿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日本人更不应遵从他国之法。这超过了日本对隐元和黄檗文化的接受,向井认为是日本之耻。因此向井如是写道:“因而无故立异邦之法,言语礼节、饮食、服饰均不尊从日本佛教传统规矩,而是模仿唐僧风,岂非日本僧人之耻辱?日本僧人之耻辱即日本之耻辱。”②《海表叢書·知耻篇》,第86 页。向井对隐元东渡一事进行批判的是日本人舍弃自国文化,归从黄檗文化,变得日本人不成日本人,成了中国人,认为那是“耻”。“模仿异国风俗习惯,是耻。”③《海表叢書·知耻篇》,第87 页。
以上向井批判的射程最终涉及到异文化碰撞时该如何考虑本国与他国的边界。隐元东渡一事让日本人模仿异国中国的文化。向井指出这一点,日本人应该回到自己的位置,日本人应知耻,修正之路应是神道。“唯有用神道,方能雪耻。神道是我日本归属之路。顺从异国之法,耻辱之至。神道方是正道,是本来规矩。”④《海表叢書·知耻篇》,第64 页。向井为了分清自国日本与他国中国的边界,提出了尊神道。
向井指出日本人自古以来以神道为指引,对此笔者无力讨论,向井的言论多少体现了感性的反动态度、国粹的态度,但对于研究隐元东渡和黄檗文化的对日影响,对于重新审视异文化碰撞,向井的言论是重要的。异文化的碰撞不仅只有接纳外来文化的一面,当然也包含像向井这样一味抗拒外来文化的一面。先有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才有本国文化接受他国文化的言论,如果忽略抗拒的运动,就是片面的。从结果上看,对日本而言隐元及黄檗文化是异国文化,日本接受了,但是对该国来说属于外部文化的异文化与本国的内部文化接触的瞬间,决非是“接受”的终止,而是反抗和排斥的开始。向井的《知耻篇》如实地反映了这种反抗和排斥,不只是对黄檗文化,在异文化交流层面也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接受异国的指教,不应该变成异国人”①《海表叢書·知耻篇》,第43 页。,“丢弃日本之道,遵从外国之法实是大耻辱”②《海表叢書·知耻篇》,第73 页。。向井的言论,对于研究黄檗文化对日的影响是重要的资料,它提醒我们不应只看到肯定的一面,异文化接触不只产生了他国与本国之间的融和/融合,向井的言论也引发我们去思考如何分清两者并思考冲突。
三、异文化碰撞中向井批判的意义
上述得知,在隐元及黄檗宗文化的已有研究中,隐元等人的功绩不仅仅在宗教方面,在饮食、语言等文化方面亦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颇受关注,被积极肯定。关于隐元最初抵达的长崎,一般观点是长崎文化是接受异文化、融合异文化而发展而来的。隐元东渡在日本确实影响巨大。但日本有不同的声音将这一史实看成是日本人在风俗习惯上一味模仿中国,是损毁日本固有文化的事件。因此研究隐元及黄檗宗时,有必要回应上述的批判。从这点看长崎,不尽能用“接受”、“融合”等词进行描述。
那么这一发现该得出什么结论?在此将外国人隐元东渡、异文化碰撞比喻成器官移植进行讨论。之所以运用器官移植进行比喻,是因为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记述了自身心脏移植经历,把移植他人的心脏与自身身体的关系,用来研究“外国人问题”。③Jean-Luc Nancy,L’intrus,(Paris: Galilée,2000).移植指的是将他人身体的一部分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让其生长在自己身体内。隐元及其异文化的碰撞,从器官移植的视点看,是隐元及其异文化在日本这个身体内部,作为他人身体的一部分存在的。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身体排斥反应及身体对排斥反应的抑制问题。器官移植,并不是把他人身体的一部分植入自身身体就结束了。移植他人器官的人,余生总是要不断对抗对他人器官的不适反应。多田富雄对此简洁表述如下:“移植要成立,前提是需要给予足够量的免疫抑制剂抑制免疫反应。那免疫抑制剂往往必须足以使个体失去防御能力,接受移植的人可能终生需要保持这种抑制状态。”①多田富雄:《免疫の意味論》,东京青土社,1993 年,第18 页。向井的言论正像是对他人器官的排斥反应产生了抑制作用。向井对作为他者/外国人的隐元及黄檗文化流入的史实,以感性论说进行对抗,由《知耻篇》可见一斑。即向井的《知耻篇》是可以看作是一部纪录片,记录作为他者的隐元及黄檗文化侵蚀日本这本体时,身体内部对异文化产生的排斥。因此对于隐元及黄檗文化流入日本一事,不得不从器官移植视角思考了向井的排斥反应。这是在文化传播、接受、融合时,异文化碰撞的冲击所不可避免的事件。
以上从器官移植视角,考察了隐元及黄檗宗的对日影响及向井的批判,想必对研究异文化碰撞中消极的一面及其详情方面是有益的发现。已有研究探讨过“文化侵略”现象是如何产生的。田莎莎就日本动漫输入中国,作出以下论述:
对国家而言“哆啦A 梦”显然是他者,是定位于日本这个国家范畴之中。中日关系良好时,“哆啦A 梦”是中日友好的象征,是肩负互相交流的桥梁作用。但当中日政治关系出现摩擦,“哆啦A 梦”便成为限制的对象,变成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象征。②田莎莎:《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製マンガ・アニメの受容―「ドラえもん」を事例として―》,《人間文化創成科学論叢》2016 年第19 卷,第3 页。
以上文字把文化侵略原因归于政治原因,但本来政治原因产生的前提,正如本论文已经阐明的,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上,必然有对异文化的排斥反应。异文化对本国文化的渗透同时伴随着对异文化的排斥反应,正是有对异文化的持续的“对抗性”,才有了为了守护本国把特定的对象列为“文化侵略”现象而进行排斥的运动。如此看来,在考察隐元及黄檗宗对日的影响以及对长崎的研究上,向井的批判是有益的,它向我们揭示了文化与文化相遇之际不可避免的“排斥反应”,为现在我们研究异文化的碰撞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不同文化之间对外国人的接受问题,与雅克·德希达提到的异邦人的“好客”问题有关。③Jacque Derrida,De l’hospitalité (Paris: Calmann-Lévy,1997).这将作为今后的课题再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