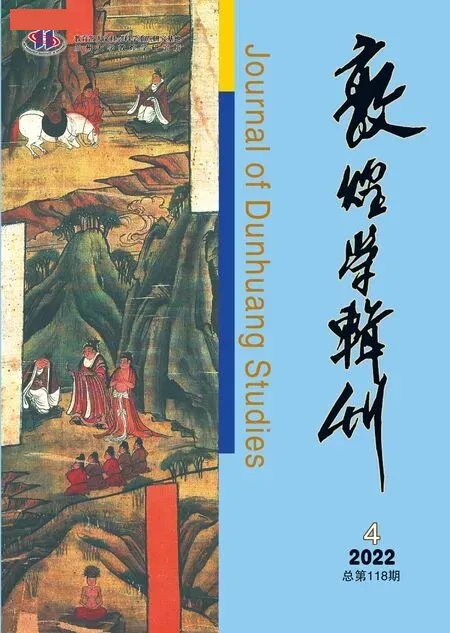再说北突厥莫贺咄其人
2022-04-06陈恳
陈 恳
(中国文字字体设计与研究中心,北京 100085)
一、引言
《旧唐书·回纥传》载:
贞观中擒降突厥颉利等可汗之后,北虏唯菩萨、薛延陀为盛。太宗册北突厥莫贺咄为可汗,遣统回纥、仆骨、同罗、思结、阿跌等部。回纥酋帅吐迷度与诸部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遂并其部曲,奄有其地。(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5《回纥》,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5页。
与之记载非常接近的是《册府元龟》卷九七三:
(贞观二十二年)是年,回纥菩萨遣使入贡,以破薛延陀功,赐宴内殿。先是,擒降突厥颉利等可汗之后,北虏唯回纥、薛延陀为盛,帝册西突厥莫贺咄为可汗,遣统回纥、仆骨、同罗、思结、阿跌等部。至是,回纥酋帅吐述度与诸部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2)[宋]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卷973《外臣部·助国讨伐》,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865页;[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3《外臣部十八·助国讨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65页;案“吐述度”当为“吐迷度”。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51页。
此处被太宗册为可汗遣统回纥等部的北(西)突厥莫贺咄究系何人,至今仍众说纷纭。这一问题涉及到贞观年间唐朝对漠北与西域关系处理的政策演变,确认该莫贺咄的真实身份将有助于增进对太宗制订东、西突厥与薛延陀、回纥相关决策的理解。冯景运对诸家观点已有很好的梳理。(3)冯景运《“北突厥莫贺咄”考辨》,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第1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年,第149-150页。此处再稍作补述。之前影响较大的观点是:北(西)突厥莫贺咄可能是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的伯父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此说不妨称之为“俟毗说”。早期研究者多有所保留地指出这一点,但并未进行系统的考证。(4)岑仲勉《突厥集史》,第205页。该说在日本学界也较为通行,除冯氏已提到的佐口透之外,(5)冯景运《“北突厥莫贺咄”考辨》,第149页。内藤みどり也认同“俟毗说”。(6)内藤みどり认为,在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时代,被弩失毕诸部拥戴的咄陆可汗(泥孰莫贺设)是西面可汗,受太宗之命统领回纥、仆骨、同罗、思结、阿跌等东方铁勒诸部的莫贺咄俟毗可汗则是东面可汗,两者都是小可汗。参见[日]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8年,第100页。段连勤认为,该莫贺咄疑为东突厥某贵族,究竟是颉利可汗何人虽无定说,“但分裂薛延陀汗国是当时唐朝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因此可能实有其事。唯此举大概由于铁勒诸部不愿再受突厥贵族的统治而未果”。(7)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吴玉贵早先曾间接地认为是阿史那思摩,(8)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76-377页。后又提出是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9)吴玉贵《〈旧唐书〉“四夷传”证误》,《文史》2007年第4辑,第197页。晚近则怀疑是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夷男之子莫贺咄叶护颉利苾——此说不妨称之为“颉利苾说”。(10)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4页。案岑仲勉已经注意到颉利苾有“莫贺咄叶护”的称号,并指出其可以与太宗册北突厥莫贺咄为可汗一事相联系,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708页。近年冯景运首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辨,倾向于认同吴玉贵早先的看法,即太宗于贞观中所册北突厥可汗莫贺咄为阿史那思摩的可能性极大——此说不妨称之为“思摩说”。(11)冯景运《“北突厥莫贺咄”考辨》,第149-155页。
本文尝试论证,上述“俟毗说”与“思摩说”都不能成立,而“颉利苾说”成立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即:贞观中被太宗册为可汗、遣统回纥等铁勒诸部的北(西)突厥莫贺咄其人,既不是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的伯父莫贺咄俟毗,也不是东突厥的阿史那思摩,而很可能是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夷男的庶长子颉利苾。
二、莫贺咄叶护颉利苾
正如冯景运所指出的那样,贞观二年(628)弑侄自立为大可汗、仅仅两年后即被杀害的西突厥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既无史料证明其经太宗册封,又不太可能遥领漠北的铁勒诸部,故“俟毗说”很难有成立的空间。(12)冯景运《“北突厥莫贺咄”考辨》,第150页。另一方面,“思摩说”如欲成立也面临不小的困难,较突出之点是缺乏史料证明思摩拥有“莫贺咄”这一名号,此外,作为东突厥贵族的思摩在贞观年间被太宗册封的是漠南突厥诸部的可汗,故其同时遥领漠北铁勒诸部的可能性也不高。回到“北突厥莫贺咄”史料的上下文。在《旧唐书·回纥传》及《册府元龟》之外,《新唐书·回鹘传》与之相关的记载是:
突厥已亡,惟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强。菩萨死,其酋胡禄俟利发吐迷度与诸部攻薛延陀,残之,并有其地。遂南逾贺兰山,境诸河。(1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12页。
前引《旧唐书·回纥传》及《册府元龟》卷九七三的史料,出现在颉利可汗的北突厥(即东突厥)汗国灭亡之后至继起的薛延陀汗国灭亡之间的叙述中,主旨在于说明贞观年间回纥兴盛强大的曲折过程,即其先曾臣属于更为强大的薛延陀,后来到贞观末年时才击败薛延陀并取而代之。对比《旧唐书·回纥传》与《新唐书·回鹘传》的上述相关记载,可以发现,《旧唐书》的“太宗册北突厥莫贺咄为可汗,遣统回纥、仆骨、同罗、思结、阿跌等部”这句话十分突兀——之前刚刚记述了突厥颉利等可汗已经投降亡国,剩下诸部中只有回纥和薛延陀最强盛,而之后的一句则是说回纥联合铁勒诸部击败了薛延陀,那么中间的这一句又说太宗让北突厥的可汗来统领回纥等铁勒诸部,并且其中完全没有提到薛延陀,这就令人非常疑惑。吴玉贵提出,《旧唐书·回纥传》这处记载中的“北突厥”及《册府元龟》卷九七三这处记载中的“西突厥”,怀疑都是“薛延陀”之误。(14)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第204-205页。如果把相关记载中的“北突厥”或“西突厥”改为“薛延陀”, 上述史料就会变得更容易理解;再结合《新唐书·回鹘传》的相关记载,可以将上述史料阐释为:东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北边诸部中本来是回纥和薛延陀最为强盛,但回纥稍逊一筹,故其暂时臣属于薛延陀,归可汗莫贺咄统领,其后,回纥复起联合诸部终于击败了薛延陀的多弥可汗。以下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论证,这个被太宗册为可汗的莫贺咄,其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载:
(贞观)十一年……薛延陀遣子达度设颉利苾来朝。(15)[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970《外臣部十五·朝贡第三》,第11229页;岑仲勉《突厥集史》,第215页;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第107页。
在这一记载中,薛延陀君主有子名为颉利苾,官号为达度设,曾在贞观十一年(637)入唐朝觐,但其官号中未出现“莫贺咄”字样。然从次年的册封诏书中,可以见到其人更完整的官号。贞观十二年(638)九月的《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诏》记载: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其子沙躭弥叶护拔酌、达度莫贺咄设颉利苾,并志怀敦确,气干强果,或深竭忠款,乃心阙廷;或远经朝觐,拜首轩陛。言念册诚,良以嘉尚。宜锡徽号,用申褒宠。拔酌可四叶护可汗,仍赐狼头纛四,鼓四。颉利苾可汗达度莫贺咄叶护,赐狼头纛二,鼓二。(16)[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964《外臣部九·封册第二》,第11168页;亦见于[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28《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91页。另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215-216页;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第110页;唐太宗《册封薛延陀二子为小可汗诏》,载吴云、冀宇校注《唐太宗全集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87页。案其中的“四叶护”或作“肆叶护”。
岑仲勉指出,此文中“颉利苾可汗”之“汗”字衍,该句应复原为“颉利苾可达度莫贺咄叶护”,此人即前一年入唐朝觐的“达度设颉利苾”,其旧官号全称为“达度莫贺咄设”,经太宗册封之后的新官号全称作“达度莫贺咄叶护”,是叶护而非可汗。(17)岑仲勉《突厥集史》,第216-217页。然《旧唐书·铁勒传》载:
太宗以其强盛,恐为后患。十二年,遣使备礼册命,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1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第5344页。
其称贞观十二年太宗册拜薛延陀二子皆为小可汗,这与诏书中所记册封一为可汗一为叶护相矛盾。前贤对此的解释是:上引《册府元龟》的记载来自《实录》,可能《实录》中很早即已存在衍字“汗”,使得《旧唐书》的编者对诏书内容进行了误读,引发《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其他史料在参考《旧唐书》时以讹传讹,遂误以为贞观十二年太宗将薛延陀真珠可汗二子都册拜为小可汗。(19)岑仲勉《突厥集史》,第216-217、686页;包文胜《铁勒历史研究——以唐代漠北十五部为主》,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40页。据此观之,贞观十二年的册封虽然涉及了薛延陀的达度莫贺咄设颉利苾其人,但并未将其册封为可汗,而只是将其册封为叶护。那么,《旧唐书·回纥传》及《册府元龟》卷九七三中所载太宗册封莫贺咄为可汗统领回纥等部之事,就并不是这一次册封。
三、真珠毗伽可汗的诸子
在考订达度莫贺咄叶护颉利苾何时被太宗册封为可汗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到底有几个儿子。兹将前贤对此问题的看法稍作梳理。
岑仲勉认为,被册封为达度莫贺咄叶护的颉利苾与自封为突利失可汗的庶长子曳莽“名既不同,显是两人”,再加上嫡子四叶护可汗拔灼,则夷男应有三子。(20)岑仲勉《突厥集史》,第216-217页。胡如雷也认为,颉利苾与曳莽决非一人,此外还有大度设也是夷男之子,再加上拔灼,则夷男至少有四个儿子。(21)胡如雷《再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兼答熊德基先生》,《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133页。段连勤、刘美崧、薛宗正和王世丽都认为,夷男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拔灼、曳莽和颉利苾(达度设),只是对于三子所统区域的看法稍有不同。(22)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第78、96、106页;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09-110页;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88-389、402页;王世丽《安北与单于都护府——唐代北部边疆民族问题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页。吴玉贵认为,薛延陀真珠可汗有三子受封,唐朝对真珠可汗之子的册封有两次,第一次在贞观十二年(638),受封者为拔酌与颉利苾;第二次在贞观十九年(645),受封者为曳莽与拔灼。(23)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第113页。
另一方面,熊德基认为,“夷男庶长子即曳莽,初称为颉利苾,后译为突利失”,且“不但曳莽与颉利苾为一人,他还曾兼过‘大度设’”,“比较诸书,可知曳莽初称颉利苾,白道川之战又为‘大度设’主兵,兵败故国人怨之,后封突利失可汗”。(24)熊德基《对胡如雷同志〈再论唐太宗民族政策〉一文的答复》,《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140-141页。简单提及而未予论证大度莫贺咄叶护(颉利苾)与曳莽为同一人的,还有其他一些学者。(25)艾尚连《薛延陀汗国与唐朝的关系及其兴亡》,《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第14-15页;词条《曳莽》,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综合卷》,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352页;卫永锋《唐与薛延陀的和亲及薛延陀的平定》,《文史杂志》2002年第3期,第58页;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包文胜认为,达度设颉利苾就是曳莽,贞观十五年(641)白道川之役中薛延陀军队的统帅,《旧唐书》记为达度设而《唐会要》记为曳莽,“二书所载应指同一人”,并举出一条旁证,白道川之役的首倡者曳莽所统领的正是薛延陀汗国东部的杂种部落;包氏还提出,后来“史料中曳莽以突利失可汗的身份出现”,原因不明,但突利失可汗的官号可能不是唐朝册封而是其自封的,白道川之役的发生疑与贞观十二年太宗未将其册封为可汗有关,“曳莽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官爵,使人容易误解。《新唐书》杂采诸书史料时,就误以为达度设和突利失是两人,并把夷男子‘突利失’和夷男兄子‘突利设’混在了一起”。(26)包文胜《铁勒历史研究——以唐代漠北十五部为主》,第138-139页。
上述各种看法中,争论的焦点在于颉利苾与曳莽是否是同一人。现有材料中,颉利苾只在前期史料中出现,曳莽只在后期史料中出现,两者在时间上绝不重合,的确颇令人怀疑为同一人。颉利苾主要见于《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卷九六四、《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及《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其中《册府元龟》卷九七〇是贞观十一年入唐朝觐之事,其余三处均是贞观十二年太宗册封之事。曳莽主要见于《唐会要》卷九六、《新唐书·薛延陀传》《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及《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在这些记载中与曳莽被封为小可汗相关的部分,全都是在夷男死后进行的追述,均以“初”或“始”开头,而具体的发生时间并不明确。(27)熊德基《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试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与胡如雷同志商榷》,《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第127页。值得注意的是,与“颉利苾”一起出现的嫡子总是写作“拔酌”,与“曳莽”一起出现的嫡子总是写作“拔灼”,两者始终匹配地出现,说明其史料各有来源,前者的史源很可能与贞观十二年册封夷男二子的诏令有关。而这两种提法同时出现在《资治通鉴》的卷一九五和卷一九八及《册府元龟》卷九六四,说明《资治通鉴》与《册府元龟》的编撰者在编选史料时没有顾及到前后一致,在同一部书甚至同一卷书中出现了同一个人的名字却有“拔酌”与“拔灼”两种不同写法的情况。另外,“拔灼”的写法还见于《旧唐书·铁勒传》,而《新唐书·契苾何力传》则采用的是“拔酌”的写法。(28)对于其中“少子拔酌杀其庶兄突利失自立”的记载,岑仲勉指出,据《唐会要》卷九六,拔酌是名,突利失是号,一名一号,说明《新唐书》编者对于外族名号未正确理解,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798页。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大度设(即颉利苾)在贞观十五年(641)的白道川之役后再也没有在史料中出现。(29)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第117页。熊德基提出颉利苾、曳莽与大度设都是同一个人,惜其论证不足,部分观点缺乏确切依据;包文胜则根据不同史料关于曳莽与大度设在白道川之役中作用与表现的记载,推测大度设与曳莽实为同一人。(30)熊德基《对胡如雷同志〈再论唐太宗民族政策〉一文的答复》,第140-141页;包文胜《铁勒历史研究——以唐代漠北十五部为主》,第138-139页。如果大度设与曳莽不是同一人,那么大度设在薛延陀汗国后期的消失不见以及曳莽在薛延陀汗国前期的默默无闻就较难解释;并且,所有论述薛延陀汗国分部统领的史料无一例外都提到汗国划分为两部,由二子分将之;另外,夷男参与争立的儿子如果超过两个,也将与下述来自契苾何力的相关观察产生明显矛盾。作为与薛延陀部大首领夷男地位相当的契苾部大首领,且祖父歌楞为大业年间契苾—薛延陀铁勒汗国的大可汗(夷男祖父乙失钵为小可汗),契苾何力对薛延陀内部的情况相当了解。早在贞观十四年(640)对高昌出征的军事行动中,担任葱山道行军副大总管的契苾何力即与助唐出军的薛延陀军队打过交道,深悉其情,(31)许程诺指出,在出征高昌的大军中,交河道行军之外另有葱山道行军,由契苾何力任副大总管,阿史那社尔任总管,分别统帅契苾兵和突厥兵,另外还有薛延陀军参与,而且投唐后的契苾部与薛延陀发生直接联系并导致后续契苾族人将契苾何力绑架至夷男处,其起因可能就与该次行军有关;此外,阿史那社尔之前对高昌及可汗浮图一带很熟悉(西突厥肆叶护沙钵罗可汗曾是其手下败将),并且其敌视薛延陀(曾与新成立的薛延陀汗国大战意图恢复东突厥汗国),故其所统突厥兵能起到监视、牵制契苾兵投往薛延陀军的作用,参见许程诺《贞观十四年唐伐高昌行军线路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8-11页。白道川之役的次年(642),何力在回部落省亲时被手下部酋劫往薛延陀,深入漠北,面斥夷男,更进一步探察到其内情,回到唐朝后,何力提出了“夷男性刚戾,既不成婚,其下复携贰,不过一二年必病死,二子争立,则可以坐制之矣”的政治预言,相关情报来自漠北羁留期间的亲身考察,故其对于夷男二子相争的议论可信度较高。(32)[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7《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六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00页;吴飞《漠北回纥兴起历程若干问题研究——以回纥与唐朝关系史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62页。根据《新唐书·契苾何力传》的后续相关记载,何力所说夷男相争的二子一为少子拔酌,一为庶子突利失,这里的突利失应该就是前述《唐会要》卷九六、《新唐书·薛延陀传》《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及《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等史料中记载的居东方的突利失可汗曳莽。如前所述,相关史料中与嫡子“拔酌”一起出现的庶长子总是写作“颉利苾”,那么何力所说的与少子拔酌相争的庶子“突利失”很可能是颉利苾的后期官号,不无巧合的是,颉利苾的前期官号“大度设”正是在白道川之役之后消失的。何力的情报来自前方第一线,应相当准确,只是相关史料未记载与拔酌相争的另一子的名字“颉利苾”,而只记下了其官号“突利失”。不过,“突利失”是出现在夷男死后二子争立的记载中,并不能倒推出何力在漠北亲身考察时其已有“突利失”的官号。但即便如此,何力所云与嫡子“拔酌”同时出现的庶子“突利失”已经足以证明,突利失其人就是一直在与拔酌进行政治竞争的颉利苾。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夷男只有两个儿子参与争夺大可汗之位,而何力探察到二子相争情报之时,大约正处于庶长子颉利苾的官号由“大度设”转变为“突利失”的过渡时期。
四、夷男二子官号的演变
在考订颉利苾何时被太宗册封为可汗之前,还需要先考察一下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夷男二子官号的演变情况。由于之前较长时间处于西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受其强烈影响,薛延陀汗国的官号也大多呈现西突厥式的风格,其中不少都系模仿甚至直接取材于同一时期西突厥汗国内诸可汗及首领的尊号(epithet)。例如,薛延陀汗国建立者夷男的可汗号中有尊号为“真珠”,其称汗前一年西突厥雄主统叶护可汗派往唐朝的使者官号即为“真珠统俟斤”,(3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下》,第5182页;[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下》,第6057页;[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六二七)》,第6046页。稍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有子颉苾达度设号“真珠叶护”。(34)[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964《外臣部九·封册第二》,第11169-11170页;[宋]王溥撰《唐会要》卷94《西突厥》,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694页;[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下》,第6062页。再如,夷男嫡子拔灼早先任“沙躭弥叶护”,后升级为“肆叶护可汗”,袭杀庶兄曳莽自立为大可汗后又称为“颉利俱利失薛沙多弥可汗”,这三个名号中,“薛”与“肆”都来自西突厥常见的尊号“肆”(Syr / Sir),“沙躭弥”与“沙多弥”都来自西突厥始祖的尊号“室点密”(Istämi),(35)岑仲勉《突厥集史》,第217、688、1012页。内田吟风也注意到了薛延陀肆叶护可汗后来称沙多弥可汗,这里的“沙多弥”就是“室点密”的异译,参见[日]内田吟风《北アジア史研究 鮮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第433-434页。而“肆叶护”(Sir Yabγu)既是室点密的另一个尊号,(36)岑仲勉《从西史及突厥语推出室点密汗之尊号》,载《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16-119页。也出现在统叶护之子的可汗号中,(37)全称“乙毗沙钵罗肆叶护可汗”,628-632年在位。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307页。“颉利俱利失”则是西突厥常见可汗号“乙屈利失”的另一种对音。(38)岑仲勉认为《新唐书·薛延陀传》及《太平寰宇记·薛延陀》中的“失”与“薛”两字之一为衍字,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698、704页。案此处其实并无衍字,“俱利失”与“薛”各有其原文,岑氏认为“俱利失”是“俱卢设”的异译,而如前所述“薛”也是“肆”的异译。祖耶夫(Ю. Зуев)将拔灼的大可汗号复原为*Ель-Курши-Сер-Аштамы(对应汉字“*颉利·俱利失·薛·沙多弥”),参见Ю. А. Зуев, Каганат Се-яньто и кимеке (к тюркской этногеограф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середине VII в.), Shygys, 2004, № 2, с. 17. 夏德(F. Hirth)依照《旧唐书·铁勒传》中的“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将其复原为*l-kül-sir-šаtоmi,虽然脱落了“俱利”之后的“失”字,但其也将“薛”复原为*sir,参见[德]夏德著,陈浩译《薛延陀考》,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译丛》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49页。芮跋辞(V. Rybatzki)则将“乙屈利失”复原为*el kulug šad,参见Volker Rybatzki, “Titles of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44, No. 2 (2000), pp. 216-217. 西突厥汗国有乙屈利失乙毗可汗(639-640年在位),是咥利失可汗之子,乙毗射匮可汗之父,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97-298、310页;另同一时期拔野古大首领俟利发的尊号“屈利失”也是“俱利失”的异译,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1012页注43。又如,庶长子颉利苾早先任“达度设”,又有尊号“莫贺咄”(Baγatur),而同一时期西突厥汗国有莫贺咄可汗,(39)至少有两位西突厥可汗的尊号中含有“莫贺咄”。其一于628-630年在位,即杀害统叶护之人,是统叶护的伯父,全称“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可复原为“*莫贺咄俟屈利失俟毗可汗”,其中的“俟屈利失”是“乙屈利失”的异译,也见于拔灼的大可汗号中,作“颉利俱利失”。其二即前述639-640年在位的咥利失可汗之子、乙毗射匮可汗之父乙屈利失乙毗可汗,又称“莫贺咄乙毗可汗”,故其可汗号全称或可复原为“*莫贺咄乙屈利失乙毗可汗”。由于可汗号极为相似,这两个可汗容易被弄混,但其世系不同,活动年代各异,所以并不是同一人。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310页。有莫贺咄叶护,(40)阿史那弥射与贺鲁之子咥运都曾任莫贺咄叶护。参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下》,第5188、5186页。还有乙毗咄陆可汗之子颉苾达度设,这里的“颉苾”很可能即是“颉利苾”的另一种对音。此中隐约存在一个模仿抑或巧合:628-630年,后统叶护时代的西突厥汗国内是肆叶护与莫贺咄在争夺大可汗位,以后者败亡告终;638年唐册封薛延陀二子,两人的官号中也各自包含尊号“肆叶护”和“莫贺咄”,而最终也以肆叶护袭杀莫贺咄自立为大可汗告终。

贞观十二年(638)太宗册拜夷男二子时,颉利苾的官号从达度莫贺咄设升级为达度莫贺咄叶护,由此可知,该次册拜没有改变二子的两翼分布,颉利苾在册拜前后都是达度(右翼)的首领,其官号中的尊号“莫贺咄”也没有改变,只是官称(title)从“设”升级为了“叶护”;同时可以推知,另一子拔酌是突利失(左翼)的首领,在册拜后从沙躭弥叶护升级为了肆叶护可汗。于是能够确认,在该次册拜之前,薛延陀汗国的两翼首领情况是:突利失(左翼)的首领是叶护,即沙躭弥叶护拔酌;达度(右翼)的首领是设,即达度莫贺咄设颉利苾。(47)岑仲勉《突厥集史》,第477页。这一情形较为接近后突厥汗国初期,即以左翼为尊,其首领叶护的官称高于右翼的设,通常也具有更高的地位。(48)在古突厥官号等级中,叶护一般要高于设(《周书·突厥传》:“大官有叶护,次设”)。然而据汉文史料记载,骨咄禄自立为可汗后,以弟默啜为杀,咄悉匐为叶护,案“杀”为“设”之异译,则此处默啜的地位似乎要高于咄悉匐。不过,卢尼文《阙特勤碑》东面第13-14行中的对应记载是:“(我父可汗)就按照我祖先的法制……在那里组织了突利斯及达头(两部)人民,”“并在那里(赐)给了叶护及设(的称号)”,似乎又表明突利(左翼)与叶护的地位要高于达头(右翼)与设。相对而言,在后突厥汗国初期的骨咄禄时代,就本题而论,卢尼文材料记载的可信度或许更高。参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24页。结合相关史料,可以进一步确认,这一情形也与薛延陀汗国立国初期的形势相符合。《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载:
初,突厥颉利既亡,北方空虚,薛延陀真珠可汗帅其部落建庭于都尉犍山北、独逻水南,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拔酌、颉利苾主南北部。(49)[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5《唐纪十一·太宗贞观十二年(六三八)》,第6140页。
此处称拔酌、颉利苾,其史源可能与贞观十二年册封夷男二子的诏令有关,“南北”应作“东西”,(50)岑仲勉认为,《旧唐书》《唐会要》及《资治通鉴》此处之“南北”都应作“东西”,参见岑仲勉《旧唐书一九九下铁勒传(同文本)校注》,载《突厥集史》,第686页。其详细论说参见岑仲勉《编年》天宝六载校注,载《突厥集史》,第475-478页。则拔酌与颉利苾二子作为左右两翼的首领,一为叶护,一为设,正好分主东西两部。《旧唐书·铁勒传》与《唐会要·薛延陀》仅称“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5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第5344页;[宋]王溥撰《唐会要》卷96《薛延陀》,第1726页。未记二子名字,而“南北”同样应作“东西”。《新唐书·薛延陀传》载:
胜兵二十万,以二子大度设、突利失分将之,号南北部。(52)[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下》,第6135页。
其中的大度设即右翼首领颉利苾,突利失即左翼首领拔酌,则此处除“南北”应改作“东西”之外,(53)岑仲勉认为,此处之“南北”系沿用了《旧唐书》之讹误,参见岑仲勉《新唐书二一七下薛延陀传(竹简斋本)校注》,载《突厥集史》,第701页。还应将大度设与突利失的列举顺序加以交换。由上述考论可以得知,薛延陀汗国前期的两翼首领分别是左翼的拔酌和右翼的颉利苾,拔酌初称叶护后称可汗,颉利苾初称设后称叶护,左翼首领的地位始终高于右翼首领,至少从贞观四年一直到贞观十二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均是如此。从颉利苾的官号来看,上述夷男二子的官号能够从结构上进行分析,其完整形式可以写作“翼名·尊号·官称”,在贞观十二年册封前后,颉利苾的翼名和尊号都没有变,只是官称由“设”变成了“叶护”,即分别是“达度·莫贺咄·设”和“达度·莫贺咄·叶护”;拔酌在册封前后翼名未变,其完整官号可以复原为“[突利失·]沙躭弥·叶护”和“[突利失·]肆叶护·可汗”。(54)方括号内为推测的复原内容,下同。
然而,到薛延陀汗国后期,两翼制度及其首领官号的情况出现了明显变化。前述提到曳莽被封为小可汗的诸史料都以追述的方式记载了时间不明的另一次册封,其中《唐会要·薛延陀》载:
初,延陀请以其庶长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居东方,所统者杂种,嫡子拔灼为四叶护可汗,居西方,所统者皆延陀。诏许之,并礼以册之。(55)[宋]王溥撰《唐会要》卷96《薛延陀》,第1728页。
其中所记嫡子拔灼的尊号和官称较之前未有改变,仍为“四叶护可汗”,(56)《唐会要·薛延陀》与《册府元龟》卷九六四作“四叶护可汗”;《新唐书·薛延陀传》与《资治通鉴》卷一九八作“肆叶护可汗”,“四”“肆”同音,可视为同一词的异译形式。但言其居西方,显已转为右翼首领,其翼名应变为“达度”;与之对应,庶长子曳莽即颉利苾则转为居东方的左翼首领,且官称不再是“叶护”,而已升级为“可汗”,依照上一次册封时尊号未变的前例,其尊号很可能仍为“莫贺咄”。这一变化不可谓不大,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嫡子拔灼被调居西方,统领嫡系的延陀部落,右翼的地位随之上升,压过了以杂种部落为主的左翼。这样一来,其两翼制度便更为接近后世鄂尔浑回鹘汗国初期的情形,即以右翼为尊。
综合上述讨论,可以将夷男二子拔灼与颉利苾官号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薛延陀建国初期至贞观十二年,二子的完整官号分别是“[突利失·]沙躭弥·叶护”和“达度·莫贺咄·设”;第二阶段是贞观十二年至汗国后期某年,二子的完整官号分别是“[突利失·]肆叶护·可汗”和“达度·莫贺咄·叶护”;第三阶段是汗国后期某年至夷男死后二子火并的贞观十九年,二子的完整官号分别是“[达度·]肆叶护·可汗”和“突利失·[莫贺咄·]可汗”。
再次回到本文开头部分提出的问题,《旧唐书·回纥传》所载太宗在贞观中册北突厥莫贺咄为可汗,遣统回纥、仆骨、同罗、思结、阿跌等部一事,就有较大的可能是指上述第三阶段开始的时间不明的第二次册封,其中的“莫贺咄”正是颉利苾/曳莽被册为可汗之前的尊号,也有可能继续保留在其可汗号的尊号中,而其被遣统的部落,也正是汗国左翼的杂种部落,(57)这里的“杂种”并非混血之意,而是表示不同于汗国统治部落薛延陀的其他诸部落,就左翼来说,参考突厥汗国时期的情形,主要包含北面的铁勒诸部及南面的奚、契丹、霫、室韦、靺鞨等部。参见谢思炜《“杂种”与“杂种胡人”:兼论安禄山的出身问题》,《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70页;郭万里《突厥汗国左翼若干问题研究》,第30-36页;包文胜《铁勒历史研究——以唐代漠北十五部为主》,第132页。如此便完全符合“突利失·[莫贺咄·]可汗”的统辖范围。包文胜指出,在白道川之役中,薛延陀汗国的主力军是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等居于汗国东部即左翼的部落,而曳莽所统领的正是汗国东部的非嫡系部落,且该次战役的首倡者亦是曳莽,故而推论曳莽是亲率属部前来征战,并将其作为达度设颉利苾即曳莽的一个旁证。(58)包文胜《铁勒历史研究——以唐代漠北十五部为主》,第139页。这里的“同罗、仆骨、回纥”与北突厥莫贺咄可汗所统部落列表的前三个完全重合,只是列举顺序稍异;莫贺咄所统的第五个部落阿跌名列薛延陀汗国建立初期漠北六大强部,(5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第5344页载:“贞观二年……时太宗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从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贡方物,复建牙于大漠之北郁督军山下,在京师西北六千里。东至靺鞨,西至叶护,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大部落皆属焉”。[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3《唐纪八·太宗贞观二年(六二八)》,第6061-6062页记载与之略同。但第四个部落思结不在其列,需要稍作申论。思结部落的主体曾在颉利可汗的北突厥汗国灭亡时随突厥本部南下降唐,(60)参见杨圣敏《回纥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5-56页;吴松弟《唐代铁勒诸部的内迁》,《西北史地》1994年第1期,第16、22页;陆庆夫《思结请粮文书与思结归唐史事考》,《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58页;包文胜《铁勒历史研究——以唐代漠北十五部为主》,第96页;[日]铃木宏节《唐の羈縻支配と九姓鉄勒の思結部》,《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015), 30: 239。故其在漠北薛延陀汗国建立初期并没有成为薛延陀的属部,而是作为北突厥的属部被唐朝安置在今山西北部的忻州、代州一带,(61)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8-419页;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16、146、151页。当白道川之役发生之时,位于代州五台的思结部落约四万众叛唐响应,多数都冲破了唐朝军队的拦截,投向了漠北的薛延陀。(62)有些史料说叛唐的思结部落被唐军全部剿灭,但事实并非如此,被剿灭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思结部众都返回了漠北,参见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第424页;汤开建《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9页。这就意味着,仅当白道川之役结束之后,思结部落的主体才返回漠北成为薛延陀汗国的属部,亦即成为左翼(突利失)诸部之一员,因此,太宗对莫贺咄的第二次册封不可能早于白道川之役,而只能在那之后。被册立为突利失可汗后,颉利苾/曳莽成为了左翼铁勒诸部的主君,那么,他在夷男死后被拔灼袭杀,其后曾经随他参加过白道川之役的回纥、同罗、仆骨等部攻击多弥可汗拔灼的举动就有了一层新的解说背景,那就是,作为突利失可汗颉利苾/曳莽的旧部,回纥等部可以将“替旧主复仇”作为号召,求得政治上的合法性,这或许也是史家将太宗册莫贺咄为可汗遣统铁勒诸部的史料放在《旧唐书·回纥传》中“回纥酋帅吐迷度与诸部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之前的别一种寓意。
五、从大度设到突利失可汗
按照上面的推测,曳莽在薛延陀汗国前期以大度设或颉利苾的名号多次见载史书,相当活跃。637年出使唐朝,638年被唐朝册封为莫贺咄叶护,641年力主出兵攻打漠南突厥阿史那思摩,曳莽的这些行动可能均与其出身非嫡子有关。为了在继位竞争中增加政治筹码,曳莽热衷使用武力,(63)[宋]王溥撰《唐会要》卷96《薛延陀》,第1728页载:“曳莽自知非正嫡.部落又少.意常不协.性又疏扰.而轻用兵.白道之役.即曳莽倡首.拔灼二之”。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六四五)》,第6228页载:“曳莽性躁扰,轻用兵,与拔灼不协”。积极建立自身的各种功绩,力图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凡此种种,在将颉利苾与曳莽视为同一人的框架下也能够获得更好的解释。特别地,颉利苾/曳莽的官号中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尊号,即“莫贺咄”(Baγatur),意为“英勇无畏”,(64)[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下编《失韦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42-44、52-54页;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3页。与颉利苾的性格特征也较为符合。同时期其他有“莫贺咄”这一尊号的突厥—铁勒系名人大都武德充沛、能征善战,如阿史那咄苾在出任东突厥颉利可汗之前为莫贺咄设,史载其“恃强好战”;(65)[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3《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六三〇)》,第6075页。又如契苾何力之父契苾葛号莫贺咄特勤,史载“其酋哥楞自号易勿真莫贺可汗,弟莫贺咄特勒(勤),皆有勇。”(6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下》,第6142页。此外还有西突厥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莫贺咄叶护阿史那弥射等,无不是武力强健之辈。以“莫贺咄”之尊号而论,大度设颉利苾/曳莽可谓实至名归。阿史那思摩则不然,一擒于启民,(67)思摩在仁寿、大业之际趁漠北混乱无主曾被短暂地推立为俱陆可汗,但迅即败降于启民可汗。参见艾冲《唐太宗朝突厥族官员阿史那思摩生平初探——以〈李思摩墓志铭〉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年第2期,第61页;李丹婕《比较视野下入华突厥酋长的身份与认同——以阿史那/李思摩为例》,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99页;冯景运《“北突厥莫贺咄”考辨》,第151页。再擒于唐朝,(68)指思摩在颉利败亡时与其一同被唐朝俘获。在归附东突厥汗国之后,也多以谋略见长,不靠勇武出名,(69)《新唐书·突厥上》载其“性开敏,善占对,始毕、处罗皆爱之”,《李思摩墓志》云“始毕没,颉利可汗立,改授罗失特勤。于是军谋密令,并出于公”,均突出强调其“智”,而非其“勇”。参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上》,第6039页;吴钢主编,王京阳等点校《全唐文补遗》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38页。而在投降唐朝之后抵抗薛延陀南侵的白道川之役中,思摩独战大度设也少有胜绩,故其罕有可能被称作意为“勇猛强健,骁勇无敌”的“莫贺咄”。因此,关于阿史那思摩曾有尊号“莫贺咄”的推测成立的可能性极小,而该点作为“思摩说”的关键论据也将大打折扣。(70)冯景运推测,思摩可能是在启民时期被授予“莫贺咄”的官称名号。参见冯景运《“北突厥莫贺咄”考辨》,第152-153页。案此推测并无任何直接史料证据支撑。尚需指出一点,即颉利苾在贞观十二年的册封中获得的官号是“莫贺咄叶护”。这一官号在西突厥传统中可能具有特殊的含义,或近似于室点密嫡系独有的储君称号,(71)内藤みどり认为:“莫贺咄叶护”(Baγatur Yabγu)是室点密可汗直系正支的标志性官号,具有特别含义,在室点密之孙、达头之子都六的诸后裔世系中,仅见于嫡子射匮一系,故“世为莫贺咄叶护”、后又被封为“大可汗”的弥射可推定为射匮之嫡孙。参见[日]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233-236页。该号庶几可以与拔酌被封的“肆叶护可汗”的称号相匹敌,(72)据岑仲勉考证,室点密的尊号为“四叶护可汗”,参见岑仲勉《从西史及突厥语推出室点密汗之尊号》,《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16-119页。地位极其尊崇。另外,即使颉利苾后期被调至左翼统领非嫡系部落,其官号“突利失可汗”仍然有很高的地位,在早先的突厥第一汗国时期,由于担任“突利可汗”的小可汗多次继位出任大可汗,使得中原人甚至一度将该官号意译为“太子王”。(73)《旧唐书·刘季真传》及《资治通鉴》载刘季真“自称突利可汗”,《新唐书·刘季真传》则载其“自号太子王”,表明时人似乎将“突利可汗”的官号理解为了某种储君称号,庶几相当于中原的“太子”,参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56《刘季真》,第2281-2282页;[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87《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第5856页;[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87《刘季真》,第3732页。关于突利可汗在突厥汗国时期准储君地位问题的相关探讨,参见薛宗正《突厥史》,第109-119页;肖爱民《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第116-119页;郭万里《突厥汗国左翼若干问题研究》,第66-69页。上述讨论说明,夷男生前似并未对二子表现出明显的偏爱和倾向,以战功与战力而论,曳莽继位的可能性或许本来更高,(74)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综合卷》,第352页,词条“曳莽”就认为:“十九年(645),夷男死,本应袭位,为弟多弥可汗拔灼袭杀”。所以拔灼只有采取偷袭的方式才能得手除去曳莽,然后继位。
在贞观十五年(641)的白道川之役中,渡碛南下的薛延陀军队由大度设统率,此人应即夷男庶长子颉利苾,但三年前其明明已经被册封为“达度莫贺咄叶护”,为何此时仍被称为“大度设”?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时人或史籍在提到某人的官号时经常使用此前习用的旧称,即使其官号已经变动仍然不用其新官号,此情况并不罕见。例如,苏尼失在突利可汗降唐之后被颉利可汗册封为小可汗,但史籍在记载其抓捕颉利时仍称其为之前习用的旧官号沙钵罗设(始毕可汗所封),完全不提其新封的小可汗号。(75)《新唐书·突厥传》载:“(贞观)四年正月,靖进屯恶阳岭,夜袭颉利……颉利得千里马,独奔沙钵罗,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禽之。沙钵罗设苏尼失以众降,其国遂亡……八年,颉利死……俄苏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启民可汗弟也。始毕以为沙钵罗设……颉利政乱,其部独不贰。突利降,颉利以为小可汗。”参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上》,第6035、6036页;另参见[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3《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六三〇)》,第6074页。同样,思摩在颉利时期被改封为罗失特勤,而史籍中一般仍用其在始毕时期的官号旧称夹毕特勤。(76)《旧唐书·突厥传》载:“其叔侄内离,颉利欲战不可,因遣突利及夹毕特勤阿史那思摩奉见请和,许之。”参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第5156页;艾冲《唐太宗朝突厥族官员阿史那思摩生平初探——以〈李思摩墓志铭〉为中心》,第61页。另外,突厥木杆可汗在《周书·突厥传》中多以官号旧称“俟斤”见载;(77)岑仲勉《突厥集史》,第517页;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7-148页;袁刚《552-555年柔然余部史事稽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20年第6期,第71页。而后突厥毗伽可汗的官号旧称“小杀”在其即位可汗之后仍旧经常出现在史书中。(78)《旧唐书·突厥传》载:“毗伽可汗以开元四年即位,本蕃号为小杀……暾欲谷以女为小杀可敦……小杀既得降户……小杀又欲修筑城壁……小杀由是大振,尽有默啜之众……且小杀者仁而爱人,众为之用……小杀与其妻及阙特勤、暾欲谷等环坐帐中设宴……(开元)十五年,小杀使其大臣梅录啜来朝,献名马三十匹。时吐蕃与小杀书,将计议同时入寇,小杀并献其书……二十年,小杀为其大臣梅录啜所毒,药发未死,先讨斩梅录啜,尽灭其党。”参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第5173-5177页。以此类推,颉利苾虽然晋升为达度莫贺咄叶护已有三年之久,但其之前担任大度设(达度设)的时间长,影响大,因此一般仍以该官号称呼之。
如前所述,在薛延陀汗国前期,颉利苾统领右翼,主兵西面,那也是汗国立国初期的主要用兵方向。史载薛延陀以步战的方式先后击败了西突厥沙钵罗肆叶护可汗和东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79)《旧唐书·铁勒传》载:“先是,延陀击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等,以步战而胜”,参考《资治通鉴》的对应纪载“初,薛延陀击西突厥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皆以步战取胜”可知,该沙钵罗是西突厥的肆叶护可汗(全称“乙毗沙钵罗肆叶护可汗”),不是东突厥的沙钵罗设苏尼失,参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第5345页;[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6《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五年(六四一)》,第6171-6172页;参见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第102页。关于该沙钵罗是东突厥沙钵罗设苏尼失的推测,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686-687页;尤中《中华民族发展史》(第1卷 先秦-南北朝隋唐五代),昆明:晨光出版社,2007年,第557页。交战的地区都在漠北西部,也即是颉利苾所负责主管的区域。联系到白道川之役中大度设统率的薛延陀军也对唐军使用步战,似可推测以步战取胜是大度设颉利苾的专长。白道川之役中,大度设的步战阵法被大唐名将李勣击破,其所率薛延陀族亲兵主力三万(即擅长步战者)遭受重创,(80)白道川之役又称诺真水之战,较新的研究认为薛延陀参战的军队不是二十万,而是仅有八万南下,且直接与唐军交战的只有三万人,参见陈星宇《唐与薛延陀诺真水之战真实战况考略》,《兰台世界》2017年第22期,第106页。导致颉利苾/曳莽在内争中的势力和实力受到打击,故而地位有所下降,这或许是他随后被调往非嫡系的左翼东面、进而被册立为突利失可汗的原因之一。
在白道川之役结束后,“大度设”不再见诸史籍,其名字“颉利苾”也消失不见,史籍中开始出现官号“突利失”,而其另一个名字“曳莽”则要到更晚的追溯性记述中才出现。此处对其间过程略作探讨,以大致确定颉利苾/曳莽被册立为突利失可汗的时间范围。
据《旧唐书·铁勒传》记载,太宗对薛延陀绝婚之后,“既而李思摩数遣兵侵掠之,延陀复遣突利失击思摩,至定襄,抄掠而去”。(8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第5346页。这似乎是“突利失”之名在史籍中首次出现,其事发生的时间无直接记载,据《唐会要·沙陀突厥》,似应在贞观十七年(643)夷男被拒婚至贞观十九年(645)夷男卒逝之间。(82)[宋]王溥撰《唐会要》卷94《沙陀突厥》,第1696页。岑仲勉认为,该事发生于贞观十八年(644);(83)岑仲勉《突厥集史》,第236页《编年》未直接明说,但由两条记载可推出在644年,第688页关于《旧唐书·铁勒传》认为在645年之前,第696-697页关于《通典·薛延陀》认为在644-645年之间,故综合起来其认为应在644年。段连勤也认为是在贞观十八年;(84)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第116、139页。李大龙认为是在贞观十六年(642);(85)没有给出具体考证,但认为该突利失就是突利失可汗,参见李大龙《由使者来往看唐王朝与薛延陀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第47页。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在贞观十七年。(86)艾冲《唐太宗朝突厥族官员阿史那思摩生平初探——以〈李思摩墓志铭〉为中心》,第63页;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第166页。
上述诸说中,段连勤的看法与岑仲勉相近,论证较细,其说可从。据此,突利失被首次提及是在644年,而大度设在641年白道川之役后便不再被提及,若两者为同一人,则颉利苾/曳莽之被册立为突利失可汗一事必发生在这两个年代之间。
根据岑仲勉《突厥集史·编年》、段连勤《薛延陀历史大事年表》及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突厥第二汗国前史编年辑考(六三〇—六七八)》,(87)岑仲勉《突厥集史》,第223-239页;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第138-139页;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第136-202页。从641年到645年薛延陀与唐朝之间的相关动向如下:
641年,唐太宗欲封泰山,薛延陀大度设南侵思摩,李勣于白道川—诺真水击败之,五台的思结部落北投薛延陀;
642年,薛延陀遣使谢罪、请婚;契苾部首领劫持契苾何力北投薛延陀;唐朝许婚薛延陀,换回契苾何力;
643年,薛延陀夷男遣侄突利设谢许婚,继而聘礼不备,契苾何力劝太宗绝婚;
644年,思摩攻击薛延陀,夷男遣突利失逾漠南下反击,李勣击却之,思摩部落大部叛还河南;
645年,4月,唐太宗亲征高丽;9月,薛延陀夷男卒,二子争国,拔灼杀死曳莽,继位为沙多弥可汗。
综合上述,所谓“太宗册北突厥莫贺咄为可汗,遣统回纥、仆骨、同罗、思结、阿跌等部”一事,背景当为唐朝对夷男二子的第二次册封,其时间范围可确定在641年至644年之间,具体而言,则较有可能发生于白道川之役的次年即642年唐朝许婚或者再次年即643年突利设谢许婚之时。在许婚与绝婚之间的关键时刻,太宗将夷男庶长子颉利苾/曳莽册封为突利失[莫贺咄]可汗,或可视作早前离间薛延陀二子之策的延续。唯对于此次册封,与薛延陀直接相关的其他史料均失载,赖《旧唐书·回纥传》及《册府元龟》卷九七三保存之。
六、结语
通过本文的上述考证,基本可以认定,贞观中这个被太宗册封为可汗统领漠北回纥、仆骨、同罗、思结、阿跌等铁勒诸部的“北(西)突厥莫贺咄”,既不是西突厥的莫贺咄俟毗可汗,也不是在漠南被册立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的阿史那思摩,而应是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夷男的庶长子颉利苾。“莫贺咄”的尊号对于骁勇好战的颉利苾来说,乃是名副其实。至于这次册封可汗的时间,则既不是颉利苾被封为达度莫贺咄叶护的贞观十二年(638),也不是夷男去世的贞观十九年(645),而是介于贞观十五年(641)大度设南下侵思摩的白道川之役与贞观十八年(644)突利失南下反击思摩两事之间,其中的“大度设”与“突利失”都是颉利苾的名号。有可能正是在确认了夷男二子相争不已的情报之后,太宗将夷男庶长子颉利苾的官称由上一次册封的“叶护”升级为了“可汗”,而“突利失可汗”的官号也足以与嫡子拔灼“肆叶护可汗”的官号相匹敌,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二子之间的竞争态势,为数年后薛延陀汗国内讧覆灭、唐朝趁势平定漠北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暂时屈服于薛延陀统治的回纥的再度崛起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