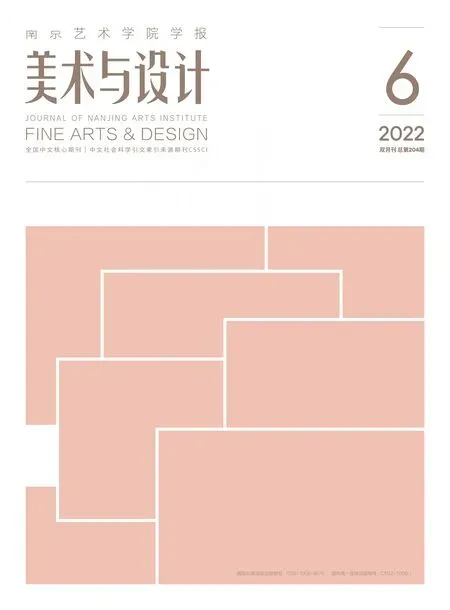文质·神彩·才性
—— 关于张怀瓘一组书法美学范畴之考察①
2022-04-06王延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13
王延智(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关于书法由写字上升为审美创造的必要性,张怀瓘给出了这样一种阐释:“夫草木各务生气,不自埋没,况禽兽乎?况人伦乎?猛兽鸷鸟,神彩各异,书道法此。”[1]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隐含了“文质”“神彩”和“才性”三个范畴的相关问题。“草木”“禽兽”和“人伦”(人才)之所以具有“不自埋没”的可能性,是因为各自气禀不同、质性相异,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形式,从而彼此之间天然地建立区分以彰显自身。文本揭示的问题,从本质论层面来看,属于“文质”范畴;从主体论层面来看,属于“才性”范畴;从审美论层面来看,属于“神彩”范畴。而这些在张怀瓘的书学著作中都能得到充分的论证,可以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中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来把握。本文旨在以“文质”“神采”和“才性”三个既相互独立又互有关涉的范畴为基点,通过文本的细读及相关命题的疏解,以期阐明张怀瓘书学思想研究中的一些未发之覆。
一、“文也者,其道焕焉”:“文”在张怀瓘书学思想中的意涵与理论价值
在张怀瓘的书法品评体系中,“神”属于最高审美境界,与神相关的品评范畴有“神气”“风神”“神俊”“神彩”(亦作“神采”)等,尤以“神彩”最为突出。翻阅文献不难发现,研究者或者将“神彩”这一范畴等同于“神”“风神”,或者将“神”“彩”二分对待,却混淆了“文”与“妍”的内涵,从而弱化了“文”的审美价值。这对于理解张怀瓘的书学思想无疑形成了一定的遮蔽。其实,“神”属于“质”的层面,而“彩”属于“文”的范畴,是“神”的审美形式,“神彩”可以说是“文质”范畴的深化和具体化。②吴兆路认为:“文就有文采、采、及丹彩、言、辞、形、表、华等,质则有志、情、理、意、神、道、事、实、里、风力等。因此,古人又常常从言意、情采、辞理、形神、华实、表里、风力丹彩等不同角度切入来研究作品的文质关系。”黄霖、吴建民、吴兆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M].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355.张怀瓘推扬“神彩”,本质上强调的是书法应当文质并重,表里充实而光辉炳耀。
(一)张怀瓘书学范畴“文”之审美价值辨正
为何“文”在张怀瓘书学思想中的价值鲜有充分发掘者呢?或许是因为根据张怀瓘“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或“深识书者,惟观神彩,不见字形”之论,[1]在文本研究上往往将“风神骨气”等同于“神彩”,将“妍美功用”等价于“文”,从而忽视了“文”在张怀瓘书学思想中的意涵与理论价值。
“文”与“质”,从本质论的角度来看,揭示的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即外在之文饰与内在之实质的对立统一;从审美论的层面来看,揭示的是华美与质朴两种审美形态的对立。就文质论的两个层面来说,在不同语境中张怀瓘更多地使用了更加具体化的范畴。其笔下与“文”相关的具体表述概念有“华”“美”“华艳”“妍华”“妍”“妍美”“妍媚”“娟好”“浓”“绮靡”等,然而当我们置之于具体文本中仔细考察与辨析,就会发现它们的意涵并不等同于“文”。比如“华”指华采,属于正价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等价于“文”;而“浓”指浓艳,属于负价概念,指繁密而空洞的审美形式形成过度之“文”,“文”之过度则失去了“文”之理所当然的审美价值。如张怀瓘《评书药石论》批评“浓”这种审美形态曰:“况复无体象,神貌昏懵,气候蔑然,以浓为华者,书之困也。”[2]再如《书断》批评庾肩吾过度追求妍美之形式曰:“变态殊妍,多惭质素,虽有奇尚,手不称情,乏于精力。‘文胜质则史’,是之谓乎?”[1]过度追求妍美、繁密、绮靡的书法形式则会掩盖“美质”之呈现,其结果就是“文”而不文,“质”而非质。王夫之云:“文之靡者非其文,非其文者非其质。……文萎而质不昭。”[3]就揭示了这种辩证关系。
关于“文”的功能,张怀瓘《文字论》给出了明确的论断:
文也者,其道焕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城阙朝仪,人之文也。字之与书,理亦归一。[1]
这段材料甚为切要。“文”之审美内涵的发现是书法走向艺术自觉的重要标志之一。“天文”“地文”和“人文”涵盖了从天地以至人类实践历史之礼乐文明的一切“大文”。张氏认为“文”的功能就在于焕发光彩,那么,天、地、人三才逻辑性地展开并历史性地垂示的“文”之审美价值,正是张怀瓘明确书法应自觉发掘“文”之审美内涵的重要根据。换言之,倘若无“文”,书法便不足以称为艺术了,“文”使书法由单纯的写字上升为审美创造。
(二)书法之“文”的内在规定性与生成变动之机
就审美创造而言,书法之“文”有自己的内在规定性。在《六体书论》中,张怀瓘揭示了书法之“文”与“象”及书法之诸多要素的关系,并进一步作了本体论的阐发:
臣闻形见曰象,书者法象也。心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尽于心,虑以图之,势以生之,气以和之,神以肃之,合而裁成,随变所适,法本无体,贵乎会通。[2]
张氏这一论断根底于《易传》哲学。《周易·系辞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4]154一切可感、可见、可触之现象、形象可统称为“象”,学习书法就需要观象取法,会通诸多要素,以“虑”思谋之,以“势”生发之,以“气”调和之,以“神”统摄之,从而进行合理地剪裁,随其所宜而变化相适,在错综变化、推荡交杂中生成书法之“文”。
张怀瓘《书断》“序”对书法之“文”的生成变动之机作了精妙的阐释:
尔其初之微也,盖因象以瞳眬,眇不知其变化。范围无体,应会无方。考冲漠以立形,齐万殊而一贯。合冥契,吸至精。资运动于风神,颐浩然于润色。[1]
张怀瓘描述了书法之“文”生成过程中一种不可捉摸的状态,可以说非常合乎“道体”的变动之象——倘若欲对其范而围之,则其无固定之形质,倘若欲应而接之,亦无固定之方位,这就需要在虚寂恬静中逐步清晰其形貌,并用一以贯之的“道”将森然万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周易·系辞上》云:“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4]147“无体”是指没有具体形器,而“无方”乃阴阳消长变化莫测之谓。因而,在张怀瓘看来,书法艺术需要天机与挥运相冥合。“至精”者本杳冥玄妙而微不可察的存在,其“象”如“道”,无形无体。《淮南子·主术训》云:“唯神化为贵,至精为神。”又云:“至精之象,弗招而自来,弗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为之者谁,而功自成。”[5]亦即书法之“文”与“至精之象”亦相合相似,书法的艺术形象是“至精之象”的显现。可以这么说,书法艺术的根本之“法”是“道”之冥合,书法“文”之生成变动就需要合乎道而中乎节,从而生成“文采”彪炳的艺术形象。
对于书法艺术形式因素的组织过程,张怀瓘《书断》云:
至若磔髦竦骨,裨短截长,有似夫忠臣抗直,补过匡主之节也;矩折规转,却密就疏,有似夫孝子承顺,慎终思远之心也;耀质含章,或柔或刚,有似夫哲人行藏,知进知退之行也。固其发迹多端,触变成态。或分锋各让,或合势交侵。亦犹五常之与五行,虽相克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岂物类之能象贤,实则微妙而难名。[1]
通过一系列的象喻,张怀瓘阐述了书法创作中种种形式要素之间的关系。张怀瓘这里提出的“耀质含章,或柔或刚”,大体表明了书法之“文”是既光显书法之“质”又内含华美之“文”。书法艺术之“文”的生成乃“发迹多端,触变成态”,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非刻意的雕琢粉饰。
概言之,在张怀瓘的书学思想中,书法之“文”的生成变动之机乃合乎“道”,合乎“自然”——“考冲漠已立形,齐万殊而一贯”。书法艺术的创作过程也合乎“道”之健动流行的结构特征。张怀瓘《书断》“序”描述了这种“合而裁成,随变所适”,随之纷沓而来的书法艺术形象:
尔其终之彰也,流芳液于笔端,忽飞腾而光赫。或体殊而势接,若双树之交叶;或区分而气运,似两井之通泉。庥荫相扶,津泽潜应。离而不绝,曳独茧之丝;卓尔孤标,竦危峰之石。龙腾凤翥,若飞若惊。电烻,离披烂熳。翕如电布,曳若星流。朱焰绿烟,乍合乍散。飘风骤雨,雷怒霆激,呼吁可骇也。信足以张皇当世,轨范后人矣。[1]
所谓“终之彰”即指书法作品创作完成之后“文采”之彰明炳耀,所谓“信足以张皇当世,轨范后人矣”,这正是张怀瓘对书法之“文”的礼赞。
二、“风神骨气者居上”:关于书法之“质”相关范畴的展开与阐扬
与“文”对立统一的范畴是“质”,而“质”作为书法的内涵,对书法的审美属性和内在价值起着决定作用。与“文”一样,“质”也具有统领的性质,在不同的批评家的笔下也具体展开其意涵,向着更加明确的方向发展。在张怀瓘的书法品评语言中,与书法之“质”相关的正价范畴往往围绕着“风”“神”“气”“骨”等范畴具体展开为更加精准的概念范畴,从而阐扬了其审美思想。兹略检数例以证:
使夫观者玩迹探情,循由察变,运思无已,不知其然。瑰宝盈瞩,坐启东山之府;明珠曜掌,顿倾南海之资。虽彼迹已缄,而遗情未尽。
伯英祖述之,其骨力精熟过之也。索靖乃越制特立,风神凛然,其雄勇过之也。[1]
八分者,王次仲造也。点画发动,体骨雄异,作威投戟,腾气扬波,贵逸尚奇,探灵索妙。[2]
(王廙)其飞白,志气极古,垂雕鹗之翅羽,类旌旗之卷舒。
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风神盖代。
尔其(王献之)雄武神纵,灵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或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察其所由,则意逸乎笔,未见其止。盖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钟、张之神气。
及其(萧子云)暮年,筋骨亦备,名盖当世,举朝效之。
(欧阳询)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1]
从文质论的维度来看,“迹—情”“意—笔”“风神—润色”这种对举的结构实质上就是“文质”范畴的具体化与精确化。以上所举的诸条例证中,“质”之内涵具体化为“风神”“风骨”“神气”“志气”“情”“意”“骨”“骨气”“筋骨”“骨力”“体骨”等正价向度的概念范畴,表明了张怀瓘主张书法艺术应当振起充实丰厚、雄逸刚健的审美质素,自觉地追求风发气爽、神完力足的审美价值。
张怀瓘进行负价向度的品评时,较少使用严明的负价概念。例如:
今大令书中,风神怯者,往往是羊也。
(阮研)其隶则习于钟公,风神稍怯。
族子(虞)纂,书有叔父体则,而风骨不继。
(梁武帝)好草书,状貌亦古,乏于筋力,既无奇姿异态,有减于齐高矣。[1]
这些列入能品的书家,大都能在艺术规则方面绍继古人,而审美内涵的传达方面缺乏相应的主体精神。张怀瓘以“怯”“不继”“乏于”对“风神”“风骨”“筋力”这些正价概念进行了一定的负价限定,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对书法审美价值的推扬与维护。
让我们再回到张怀瓘《书议》中的那个著名论断:
然智则无涯,法固不定,且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1]
“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这一阐述,向我们揭示了“风神骨气”与“妍美功用”之间的对立关系与审美价值取向。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者”字作为焦点标记,提示前面是命题的重点内容,而“风神骨气”和“妍美功用”均由两个并列的范畴构成,在张怀瓘的书学著作中,几乎找不到类似的句式。另外,从严格的文法来说,“风神”的对语应为“文采”,“骨气”的对语也不是“功用”,而“妍美”亦非负价概念,如张怀瓘赞誉王羲之“真行妍美,粉黛无施”。那么,这一命题应当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这里的“妍美功用”是指为了“功用”而片面追求书法形式语言的“妍美”,即缺乏相应审美内涵的形式化艺术效果。例如《书议》之所以将王羲之的草书列于诸子之末,是因为张怀瓘认为“逸少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1]以此类推,“风神骨气者居上”这一命题的核心指向是,书法艺术当以“骨气”立本,使“风神”凛然充沛,令观者可以从中感受到运化不息的精神气度,获得一种真力弥满、振拔刚毅的审美感染力。
三、“不可文质先后而求之”与“齐圣跻神,妙各有最”:关于古质今妍“达道论”之批评
(一)走出“古质”“今妍”优劣论的阐释困境
在书法发展史上,围绕着“四贤”(张芝、钟繇、王羲之和王献之)书艺成就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讨论,对于这一公案,不同时期的批评家给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审美倾向和品评标准。无论是梁武帝意欲复兴钟繇、张芝之“古质”,还是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的“尽善尽美”,均未能走出古质今妍优劣论的思想困局。孙过庭立足于“文质彬彬”的审美理想而提出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弘通之论,然在“四贤”书艺优劣论的解释上亦有牵强之嫌,尤其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批评王献之“自称胜父,不亦过乎”,得出“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惑疑焉”这一近乎武断的结论。①围绕着 “四贤”之 “古质”“今妍”优劣问题展开的辩论折射了六朝至初唐的书法审美趣味变迁史,同时也反映书法艺术自觉以来的艺术实践与接受品评之间的矛盾,这既是书法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书法本体论认识的深化过程。参见拙文《从虞龢到孙过庭——从“四贤”品评看南朝至初唐书法 “文质说”思想之嬗变》,《美术与设计》,2019(2):58-62.以此可见,自六朝至初唐,以“四贤”为中心的“古质”“今妍”孰优孰劣的讨论一直未能给出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阐释。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批评家均欲以一种绝对标准作为书法的公认准则,即所谓“达道”者。
张怀瓘注意到了这个悬而未决的理论困局。《书断》“序”云:
昔之评者,或以今不逮古,质于丑妍。推察疵瑕,妄增羽翼。自我相物,求诸合己。悉为鉴不圆通也。亦由苍黄者唱首,冥昧者唱声。风议混然,罕详孰是。[1]
对于这个问题,《书断》“评”给出了充分的阐释:
夫椎轮为大辂之始,以椎轮之朴,不如大辂之华,盖以拙胜工,岂以文胜质?若谓文胜质,诸子不逮周、孔,复何疑哉?或以法可传,则轮扁不能授之于子。是知一致而百虑,异轨而同奔。钟、张虽草创称能,二王乃差池称妙。若以居先则胜,钟、张亦有所师,固不可文质先后而求之,盖一以贯之,求其合天下之达道也。[1]
审美属于主观判断,无论“古质”,还是“今妍”,一旦作为审美的绝对标准,在书法品评中的有效性也要打个问号了。张怀瓘回顾了汉魏六朝以来的书法品评史,批评了几种常见的品评观。首先,文本第一句对一味崇“质”者进行了批评,这里用了“椎轮”“大辂”之喻,二者均具有车之“质”,而朴拙的椎轮在形貌方面自然比不得华美的大辂,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张怀瓘认为如果一切以“质”为标准的话,“拙”理应胜过“工”,倘若如此,华美的大辂岂不是比不上拙朴的椎轮了?其次,张怀瓘又对一切以“文”为尚者进行了批评,即如果认为“文胜质”,那么,竞尚浮华的诸子又怎么能比得上质实的周公、孔子呢?由此可见,以“质”或“文”为绝对标准来衡量一切书法是不足取的。第三,张怀瓘以轮扁不能传技于其子的典故,批评了以“法”为尚者。第四,以钟、张、二王先后称妙入神为例,批评了以“先后”“古今”作为评判标准的观念。在张怀瓘看来,这几种品评观的主要问题都在于试图用一种绝对标准衡量所有的书家及书法艺术。
张怀瓘认为古今诸多名家不仅才性气禀不同,而且对不同书体的审美感知力与创造力也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不可一概而论。就“质实”与“文华”两个风格维度而言,张怀瓘认为“三古谓实,草隶为华,妙极于华者羲、献,精穷于实者籀、斯”。[1]因此,张怀瓘认为书法品评要有针对性。张怀瓘说:
虽则齐圣跻神,妙各有最,若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无施,则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极致高深,则伯度第一;若章则劲骨,天纵草则,变化无方,则伯英第一;其间备精诸体,唯独右军,次至大令。①(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9[G].明津逮秘书本.按,“齐圣跻神”,津逮本《法书要录》作 “齐圣齐深”,据四库本《墨池编》校改。[1]
这段文本解释精准地概括了钟繇、王羲之、杜度、张芝、王献之的书法艺术贡献。根据不同书体的审美特征和书家先天才性,张怀瓘提出的“齐圣跻神,妙各有最”之论,为古质今妍“达道论”画上句号。
(二)“书复于本”其意云何
在张怀瓘的书论研究中,有个与“古今”审美相关的问题还需要予以澄清。《评书药石论》云:
当今圣化洋溢,四海晏然,俗且还淳,书未返朴。今之书者,背古名迹,岂有同乎?视昔观今,足为龟镜,可以目击。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复本谓也。书复于本,上则注于自然,次则归乎篆籀,又其次者,师于钟、王。夫学钟、王,尚不继虞、褚,况冗冗者哉![2]
既然张怀瓘认为“质”“文”先后而各有擅胜,为什么这里又提出“书未返朴”?这里的“返朴”和“书复于本”究竟有何所指?首先需要辨析这个问题提出的语境,张怀瓘的古今质文观是针对杜度、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齐圣跻神”者提出的,这些书家均属于“各能尽心而际于圣”[1]者。《评书药石论》又云:
从宋、齐以后,陵夷至于梁、陈,执纲者失之于上,处卑者惑之于下,肥钝之弊,于斯为甚。贞观之际,崛然又兴,亦至于今,则脂肉稜角,世俗相沿,千载书之季叶,亦可谓浇漓之极。……陛下宏开至德,讲论六艺,迈踪上古,化行尧、舜之风,书盛汉、魏之日。臣愿天下之事,悉欲尽美尽善,宁以书道独能谢于前代乎?然大道不足崇,而书法亦当正;若忽之,则工拙一也,若存之,亦当年妙有。[2]
由此可见,张怀瓘所主张的“返朴”是针对宋、齐、梁、陈以来“浇漓之极”的浮艳疲敝之书学风气而提出的。《评书药石论》作为奏御之作,张怀瓘欲借帝王之力,改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以期当时书学成就达乎汉、魏之盛。张怀瓘有云“本立而道生”,[2]故“书复于本”乃复之于真正的“书道”。张怀瓘“宁以书道独能谢于前代乎”即表达了“书复于本”的文化诉求。
四、“顺其性,得其法”:论“才性”与“法”在书法审美创造中的关系
与“齐圣跻神,妙各有最”之论关系殊为密切的是“才性”范畴。毫无疑问,张怀瓘是“天才论”者,先天才性是第一位的,后天习学是第二位的。张怀瓘认为,书法艺术的学习与创作需要“顺其性,得其法”,书家应当遵循自身才性选择适合自己的修习方法,尽可能发掘自身才性的特殊性,从而成就属于自我的艺术风格。
张怀瓘《书议》云:
或问曰:“此品之中,诸子岂能悉过于逸少?”答曰:“人之材能,各有长短。诸子于草,各有性识,精魄超然,神彩射人。逸少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銛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是以劣于诸子。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举世莫之能晓,悉以为真、草一概。若所见与诸子雷同,则何烦有论。”[1]
这是因历代草书艺术成就之评骘而引发的议论。张怀瓘认为,不同的书家在草书艺术上具有不同的天分与才性,王羲之的草书虽然圆润妍美,却缺乏草书应有的风神骨气,而王羲之的才性主要表现在真书与行书两体的成就上。就“二王”父子而言,张怀瓘注意到:“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1]也就是说,不同书家的先天才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外化为艺术风格。基于这种认识,张怀瓘更加辩证地把握了主体才性与艺术创造的关系。
就“才性”来说,张怀瓘将主体“才性”分之为“上才”“中才”“下才”“无才”四个等级,《评书药石论》云:
假如欲学文章,必先览经籍子史。其上才者,深酌古人之意,不拾其言。故陆士衡云:“或袭故而弥新。”美其语新而意古。其中才者,采连文两字,配言以成章,将为故实,有所典据。其下才者,模拓旧文,回头易尾,或有相呈新制,见模拓之文,为之愧赧。其无才而好上者,但写之而已。书道亦然,臣虽不工书,颇知其道。圣人不凝滞于物,万法无定,殊途同归,神智无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著,至于无法,可谓得矣,何必钟、王、张、索而是规模?道本自然,谁其限约。亦犹大海,知者随性分而挹之。[2]
张怀瓘以学作文章为喻,所谓“上才”是指能够会古通今而不拘泥于形式语言者,“中才”是指能够掌握前人笔墨语言、形式技巧者,“下才”是只能陈陈相因前人笔墨语言而食古不化者,“无才”则是指毫无艺术性的写字者。就“书道”而言,张怀瓘认为“无法”为最上,是“圣人不凝滞于物”的境界,其才智卓绝,其妙用有方,是“得道”者之境界。由于“道”体本来就自然而然,其变化运动没有固定的程式。因此,深会“书道”者,就不必以钟繇、王羲之、张芝、索靖等书之圣手作为效法之楷范了,更不必刻意师法他们的技巧、韵律、用笔、结字等形式因素了。这可以看作张怀瓘对主体能动性的至高境界之肯定。
基于此,张怀瓘《六体书论》云:
如人面不同,性分各异,书道虽一,各有所便。顺其情则业成,违其衷则功弃,岂得成大名者哉!夫得射法者,箭乃端而远,用近则中物而深入,为势有余矣;不得法者,箭乃掉而近,物且不中,入固不深,为势已尽矣。[2]
既然主体才性来自先天规定,后天的教化学习就要与之相应。从文质论的角度来说,“顺其性”则能使主体才性更好地舒展开来,“得其法”在于有效地掌握书法的艺术规定,从而“文”“质”相称,互相成就。《六体书论》云:
若乃无所不通,独质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则逸少为最。所以然者,古质今文,世贱质而贵文,文则易俗,合于情深,识者必考之古,乃先其质而后其文。质者如经,文者如纬,若钟、张为枝干,二王为华叶,美则美矣,如彼桃李,戛兮铿兮,合乎宫徴。……故学真者不可不兼钟,学草者不可不兼张,此皆书之骨也。如不参二家之法,欲求于妙,不亦难乎!若有能越诸家之法度,草隶之规模,独照灵襟,超然物表,学乎造化,创开规矩,不然不可不兼于钟、张也。盖无独断之明,则可询于众议;舍短从长,固鲜有败书,亦探诸家之美,况不遵其祖先乎![2]
张怀瓘认为,世人但知王羲之“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却不知其内在要旨。正如《书议》中所论王羲之书法艺术之奥旨:“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学;其理隐而意深,故天下寡于知音。”[1]那么,张怀瓘认为如要“深酌古人之意”,就需要对古人有一番考索,而考索的准则乃是“先其质而后其文”,因为“质”是书法艺术之经线,“文”乃书法艺术之纬线,经线在于立“骨”,纬线在于增“华”,二者缺一不可。这里之所以分先后,是就逻辑关系来说的,并非出于审美价值判断,我们也不能因为“先质”“后文”的逻辑顺序而武断地判定张怀瓘具有重质轻文的思想。就古人书法来说,钟繇、张芝乃书法之“质”,“二王”乃书法之“文”,“得其法”就是要以钟、张来立“骨”,以“二王”来增“华”。具体说来,学习楷书,则不得不师法钟繇,而学习草书,则不得不师法张芝,师法此二人可以确立楷书和草书艺术的审美内涵。张怀瓘亦认为,倘若有人能够师法“造化”,从天文地理中得其变化之“法”,创开千古之“规矩”,就可以不用师法钟、张了。不过,张怀瓘的潜意识中似乎并不认可这种超绝之才的存在。
五、结语
作为具有独立批评意识的书论家,张怀瓘运用概念、范畴时十分审慎与精准,对于张氏书学核心范畴的研究,需要置之于特定的语境中深入文本而还其本义,然后从中发掘其内在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观念。基于存在论的“文”“质”关系,张怀瓘以自然人文世界为审美观照对象,揭示了“神彩”的审美内涵与审美价值。“神彩”作为审美价值追求,并不是一种特定的风格,风格根底于主体的先天“才性”。张怀瓘说:“故与众同者俗物,与众异者奇材,书亦如是。”[2]这就揭示了个体风格的不可消失性,书法作为一种自觉的艺术活动,书家主体应当审视自身才性,完成具有独立精神和独特风格的审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