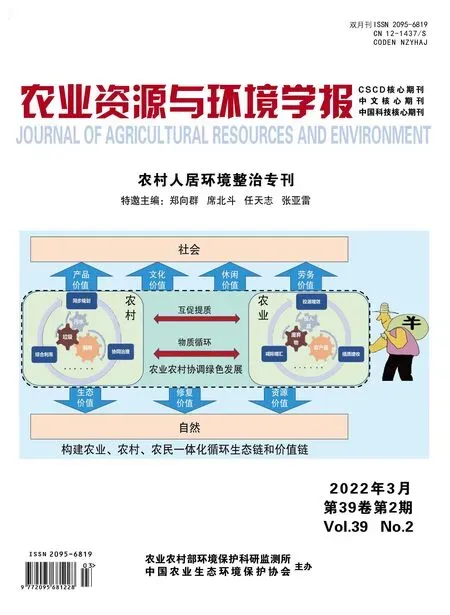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现状及整治框架
——以重庆某县为例
2022-03-31王永生施琳娜朱琳
王永生,施琳娜,朱琳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2.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重庆 400715)
人居环境是人类工作劳动、生活居住、休息游乐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场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引起人类生存方式不断变化的结果。20 世纪50 年代,希腊学者Doxiadis 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迅速成为建筑、规划、地理等学科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1]。21 世纪初,国内对人居环境的相关研究逐渐兴起,吴良镛先生[2]创建“人居环境科学”,并将人居环境定义为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指出其是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居环境也从自然转向人工,从低级走向高级,从分散居住向村庄、乡镇、城市、城市群演化发展[3]。
村庄在空间上从散点分布,逐步向点与点连接、点与多点连接、点与域面交融演变;在时间上先后经历低效均衡发展、优势村落极化发展、点域要素互馈发展、城乡交互融合发展阶段[4]。农村人居环境也伴随着村庄发展历程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工业革命以前,传统农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有限,生产、生活和生态关系和谐;工业化以来,化肥、农药等农业化学物质持续投入,现代生活方式产生的垃圾,以及城市和工业废物转移等不断影响农村人居环境[5-6]。乡村地域系统环境污染也从单一污染逐步演变为复合污染和立体污染[7]。目前,对于农村人居环境的定义较多,但内涵基本相同。农村人居环境是生产经营和生活居住的自然生态、地域空间、人文环境等要素组成的有机结合体,是农村居民生存和福祉的重要载体[8-10]。农村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农村生态环境关系到农村经济、乡村旅游与农业可持续发展[11]。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乡村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有利于乡村空间重构、组织重建和产业重塑[12]。
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条件及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差距巨大[13]。资源利用不当、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改变[6],致使村镇建设用地空废、农村水土环境污损等“乡村病”日益凸显[14],农村人居环境的短板问题日益严峻[10],制约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此外,农户的人居环境治理与保护观念落后于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区域的环境保护与人居环境整治落后于城市区域[15],致使农村人居环境的短板问题备受关注。因此,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人居环境空间差异、演化机制、整治策略与优化路径等相关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16-17]。
人居环境质量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8],是衡量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农村人居是人居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8],农村人居环境可以划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是与农户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要素和地域空间的总和,包括生态环境质量、居住条件和农村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整治与建设有助于优化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推动乡村空间重构;软环境主要是指与生产生活相关的非物质要素,如组织管理、文化氛围和社会服务等,软环境整治与建设有利于吸引企业与资本下乡、青壮年与农家子弟返乡等,有助于培育新型经营与管理主体,促进乡村组织重建[1,12]。农村人居环境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实践研究成为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于法稳等[19]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总结,2015 年之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方面,之后的研究则注重整治模式、路径与政策等方面;未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应关注主体、内容、优先序、模式、保障、考核等方面。农村人居环境的评价研究多集中在国家、省域和县域尺度,基于村庄调查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相对缺乏,尤其是缺少从村庄层面和农户层面的人居环境调查研究。
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区域,农村人居环境是农村发展的短板之一,也是国家乡村振兴的重点建设内容。精准扶贫解决了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滞后的难题,改善了区域性贫困问题,补齐了乡村发展的部分短板[20],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期,更需要准确识别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现状,明确人居环境整治的理论框架和主要路径,确保脱贫地区乡村转型、发展和振兴。因此,本研究通过梳理近20年来国家人居环境政策演变历程,结合典型县域村庄层面和农户层面的人居环境现状调研,提出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框架,为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理论支撑。
1 国家农村人居环境政策梳理
农村人居环境关系到农村居民的身心健康,是保障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21]。我国政府持续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整治工作[22],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和“两管五改”运动,改革开放后的“厕所革命”、文明村镇建设、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等措施显著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面貌[23]。特别是2004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关注农村人居环境,从要素-结构-功能视角,可划分为三个阶段:①要素补给阶段(2004—2009年),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补齐人居硬环境短板,如水电路房建设、发展农村清洁能源、村庄规划与治理、推进乡村清洁工程等;②结构优化阶段(2010—2013 年),强调村庄环境整治,开始关注人居软环境建设,如水土保持与治理、农村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等;③功能提升阶段(2014 年至今),软环境与硬环境并重,持续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如农村环境集中连片整治、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补齐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美丽家园建设等(图1)。

图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梳理Figure 1 Summary of national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olices
党的十九大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中央相继出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因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成为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践行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和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重要内容。
2 调查县农村人居环境现状
2.1 材料与方法
2.1.1 研究区概况
调查县位于重庆市东部,地处三峡库区腹地,是成渝经济区重要节点城市,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旅游资源丰富,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国家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试点县。2014 年底,贫困村95 个,贫困发生率约为12.1%,2017 年实现脱贫,是重庆市首批、全国第二批脱贫“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脱贫以来,县委县政府积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围绕农村垃圾治理、厕所革命、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任务,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助力乡村振兴。
2.1.2 问卷调查
2020 年5 月,项目组围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资源利用、环境现状等方面设计县域村庄层面和农户层面人居环境现状调查问卷,邀请调查县303 个村庄(街道、居委会)负责人(支书或主任)填写调查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296 份。问卷主要关注点:村庄层面的地膜、棚膜、农药瓶、化肥袋、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处理方式,以及垃圾箱、污水处理、公共厕所、学校、卫生室、文化室、广场等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农户层面的农房和厂房废弃与闲置、卫生厕所普及率等现状。
2.1.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通过问题选项所涉及村庄数量占调研村庄总数量的比例,反映村庄农业废弃物处理、基础设施普及现状;通过农房倒塌率和废弃率、厂房倒闭率和废弃率、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反映农户层面农村人居环境现状。数据处理和绘图均采用Excel 2010。
2.2 调查结果
2.2.1 农业废弃物
在调查的296 个村庄中,地膜和棚膜回收的村庄占比分别为70.67%和77.49%,低于农药瓶回收的村庄比例(86.73%)和化肥袋回收的村庄比例(96.60%);作物秸秆还田利用的村庄比例为67.25%,用作饲料的村庄比例为19.51%,直接焚烧和丢弃的村庄比例分别为10.80%和5.57%。67.25%的村庄将家庭养殖粪便腐熟还田,而养殖企业粪便腐熟还田的村庄比例仅为52.92%;家庭养殖粪便直接还田和直接排放的村庄比例分别为19.51%和5.57%,均高于养殖企业的10.83%和1.67%;家庭养殖粪便集中处理的村庄比例仅为10.80%,显著低于养殖企业的38.75%。此外,在有加工企业的122 个村中,有94.26%的村庄加工企业废水采取集中处理措施(表1)。

表1 调查县农业废弃物处理方式Table 1 Agricultural waste disposal in the studied county
2.2.2 基础设施
从村庄基础设施普及率来看,在调查的296 个村庄中均设有垃圾箱,但仅有28.78%的村庄建有污水处理设施,48.31%的村庄建有公共厕所(图2a)。分别有90.07%和89.92%的村庄建有卫生所和文化室,但幼儿园、小学和广场的村庄普及率分别为42.55%、58.08%和58.55%(图2b)。

图2 调查县村庄基础设施普及率Figure 2 Popularizing proportion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studied county
2.2.3 农房厂房
在调查的29 747座农户房屋中,闲置率和倒塌率分别为21.93%和13.28%(图3a);在调查的519 家种植企业和549家养殖企业中,企业倒闭数量分别为21家和25 家,倒闭率分别为4.05%和4.55%,在倒闭的种植企业和养殖企业中,厂房废弃率分别为71.43%和40.00%(图3b)。

图3 调查县农房及厂房废弃情况Figure 3 Abandonment of rural housing and workshop in the studied county
2.2.4 卫生厕所
《2018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底重庆市和全国的卫生厕所普及率分别为66.20%和81.80%。参与卫生厕所普及率调查的村庄中,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为57.44%,低于重庆市和全国平均水平。
3 讨论
3.1 调查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状及形成机制
贫困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之一,贫困地区的人居环境整治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研究发现,2010—2015年,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较差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21]。重庆市乡村地域广、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24]。1997—2015年,重庆市通过改善民生、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等措施使乡村人居环境协调指数持续上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向好[25]。2018年以来,重庆市制定颁发了《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3 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将全市8 015 个行政村划分为3类,有序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在厕所改造、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治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村容村貌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厕所改造中粪污处理利用不到位、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治理体系不完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缺乏、村容村貌提升改造滞后等问题[26]。
在本研究中,从村庄层面的人居环境整治现状来看,仍然有部分村庄没有采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措施,存在棚膜、地膜和农药瓶缺乏充分回收、作物秸秆直接焚烧、家庭养殖粪便和企业废水直接排放等问题。另外,配置生活污水处理的村庄比例低于30%,建有公共厕所的村庄比例也不足50%,仍然有41.45%的村庄没有健身广场(图2)。原因在于:首先,村庄层面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改善是调查县扶贫期间的主要任务,对于村庄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宣传的投入相对较少;其次,调查县以山地为主,仅在河谷、山谷间有狭小的平坝,村庄布局分散,修建生态设施的难度较大;第三,由于部分村庄人口外流,空心化问题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修建公共厕所和污水处理等设施的必要性。虽然,幼儿园和小学的村庄普及率也仅有42.55%和58.08%(图2),但学校建设已经充分考虑村内学生数量、学校辐射范围,可充分保障学生的入学要求,又避免了资源浪费。从农户层面来看,农房闲置和倒塌率较高,部分倒闭的企业厂房缺乏循环利用,废弃率较高,卫生厕所普及率低于重庆市和全国平均水平。
农户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之一,农户的需求分析和参与机制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19]。农户层面的房屋加固、院墙改造、庭院绿化和厕所改造等工作是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12]。总体来看,调查县中村庄层面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优于农户层面,但村庄文化层面的内容亟待加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非农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最主要来源,但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影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处于“城乡两栖、往返流动”状态,农村原有住房缺乏维护修缮、耕地污损与撂荒问题日益凸显,农民难以安居乐业[11,14]。虽然,国家出台了大量关于村庄水、电、路、房建设等方面的措施,也强调乡村建设中的农户主体性和参与性,但针对农户层面的适用性环境整治技术和设备等相对缺乏,农户对村庄规划建设的参与度不足[19]。此外,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的考核评估指标多集中在村庄层面,对于农户层面的考核指标主要侧重在家庭收入和住房安全等方面。2019 年,调查县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分工方案》,重点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村庄规划、村民习惯改正等工作。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业绿色发展,要求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和农膜、农药包装物回收行动,加强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调查县应继续加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补齐乡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公共厕所配置短板;同时特别加强农户层面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尤其是盘活废弃闲置的农房厂房资源、推进适用性强的卫生厕所普及工作,实现农村资源高效利用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双赢,改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
3.2 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策略
农村人居环境是复杂开放的巨系统,是农户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有机结合体[10],承载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27]。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系统工程,也是长期工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环境健康是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27]。精准扶贫期间,国家持续重视贫困地区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2018 年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通知,要求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优先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条件基础上,实现人居环境干净整洁的基本要求。2019 年11 月,农业农村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扎实有序推进贫困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通知,促进脱贫攻坚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效融合。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式,促使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向贫困地区倾斜。在村庄层面,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相结合,通过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以及生态脆弱区易地扶贫搬迁等措施,改善贫困地区农村的生活、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提高农村生态宜居水平。在农户层面,注重解决吃穿、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问题,增加家庭收入,激发内生动力,提升农户的精神风貌(表2)。

表2 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策略Table 2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n poverty-free areas
随着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地区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贫困群众精神面貌明显变化,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累了宝贵经验[28]。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注重村庄生活垃圾与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方面,强调农户环境与健康意识和主体参与性[19]。由于精准扶贫对象主要是贫困村和老弱病残等贫困人口,脱贫后仍然面临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相对短缺、村庄发展和治理能力弱等问题[20]。因此,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期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需要充分调动政府、社会与农户的积极性,通过政府筹集配套资金、安排帮扶队伍、开展政策宣传,选择党员、能人、乡贤等家庭进行示范带动;鼓励社会资本下乡,开展结对帮扶,创新适用性强的环保技术与设备;充分发挥农户的主体能动性、积极性和参与性,确保农户实际需求与环境整治相结合。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决策和社会组织及农户“自下而上”参与的有机结合,构建“省、市、县、乡、村、组、户”人居环境整治网络。在工作内容上,要继续补齐村庄层面的污染治理、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短板,加强村庄规划和污染物监测评估,谋划乡村资源配置、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系统目标[29],建立乡镇企业、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与城市污染转移的监测网络[7]。此外,应更加关注农户层面的卫生厕所、污水收集等卫生设施配套,推进农户移风易俗,增强环保意识。我国乡村地域类型多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应充分考虑农村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等差异,应因地制宜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实践,确保乡村建设的实效和可持续性。
4 结论
(1)我国持续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整治工作,2004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关注农村人居环境,从要素-结构-功能视角,可划分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个阶段。
(2)调查县村庄层面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优于农户层面。部分村庄存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程度低的问题,如棚膜、地膜回收率低,作物秸秆直接焚烧、家庭养殖粪便和企业废水直接排放的村庄占比较高。配置生活污水处理的村庄比例低于30%,建设有公共厕所的村庄比例不足50%,41.45%的村庄缺少健身广场。此外,农房闲置和倒塌率较高,部分倒闭的企业厂房废弃率较高,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低于重庆市和全国平均水平。
(3)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期,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决策和社会组织及农户“自下而上”参与的有机结合,构建“省、市、县、乡、村、组、户”人居环境整治网络;在工作内容上应体现农户的主体性,加强农户层面的卫生设施配套、移风易俗推进以及环保意识提升等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