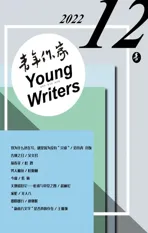找童年
2022-03-26周东
周东
打儿洞
那一年是妈妈带着我步行去大罗的。走过龙洞沟水库,又走过松树坪和白门子,公路边有个装着菩萨的洞,妈妈说那是打儿洞,想生儿子的人捏一块石子或者土块,向打儿洞投进去,如果能打到菩萨身上,菩萨就会保佑他生儿子,很灵验。我似懂非懂,反正自己不生儿子,也没有捏一块石子投向打儿洞打那菩萨。
打儿洞一直待在去大罗场必经之路的岩石旁,想生儿子的人遇见打儿洞时,总是往里面投石子。
洞里的菩萨是微笑着站在那里的,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观音菩萨,不知她站了多少年,也不知她保佑了多少人生了儿子。她的周围布满了红布,脚下摆满了供品,还点着一炷炷冒着香味的香。看来真的很灵验。
后来我有了儿子,却没有投一块石子进去,因为童年过后就没有再去大罗场,也没有经过打儿洞。
今天,又一次经过打儿洞,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置身事外的老人,远远地看见依旧的打儿洞,正想问问里面的菩萨是否保佑过曾经经过她脚下的我,可汽车飞驰而过,只有把那些疑问留在打儿洞,来不及听菩萨给我的答案。
董家梁
越来越熟悉的路像一条土色的云带铺在我的眼前,汽车很轻盈地在云里穿行,像一只飞进天空的燕子。
那一年,父亲拉着我的小手走进一户姓戚的农户,父亲说他在这里包户,常住在这里。
晚上我在灶前看到农户家和我一样大的宝娃子正在用一根竹筒吹火,便来了兴致,我想要那个能吹火的竹筒。
宝娃子说竹筒是吹火筒,我就更想要,一晚上睡得很不踏实。半夜上厕所,忍不住悄悄地把那根竹筒拿到自己的床前,还是觉得不踏实,又把竹筒压进席子下,硬硬地抵着脊背,才渐渐睡去。
天一亮,我看见宝娃子正用一根新竹做的吹火筒吹着火,心想这一下自己昨夜藏的吹火筒就属于自己了。
等回家的时候,自己便带着吹火筒,一路小跑。
董家梁是大罗的一个村,那时叫五大队。父亲说公社领导都要每年驻村,在农民家吃住,抓农业生产,抓粮、棉、油等等。
暑假里,我常和父亲待在五大队,住在姓戚的农民家,我在这里看早晨的云雾、听黄昏的鸟鸣。在六月间和宝娃子刨地瓜、捉知了、抓竹牛,还吃他爸爸打的野鸡,很是惬意。
父亲却很忙,总是整天转田坎,晚上还要看书、写笔记,召集乡上干部开会,说要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
三年后,大罗乡受到省上的表彰,奖品是一台丰35牌大型拖拉机,父亲常开着这台拖拉机跑遍大罗有路的地方。
又是一年七月,五大队的田间地角都飘来了阵阵黄花香。几年后,还是七月,中宣部带着中央媒体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地方,拍了部新闻纪录片,那一年我第一次听到了录音机里有我说话的声音,第一次在放电影前看到了播出的关于大罗乡的新闻纪录片,里面有父亲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影子,还有姑娘们搭着梯子采黄花的样子,美极了!
董家梁村是黄花的发源地,大罗黄花渐渐地成了长盛不衰的特色产业和地方标志性品牌。
八字桥
当年董家梁的新人几乎都从八字桥上面走过。
当地有个风俗,新人结婚之前,媒人都要把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要去,找算命先生看看,合了八字才可以订婚结婚。
董家梁的新人不用合八字,董家梁的新人只要从八字桥走过,走得稳当就能结婚,就能百年好合。
走得稳当就是男女在经过八字桥时不摔跤不晃悠。
那是一场古典的婚礼,新郎是乡政府的蚕桑技术员。
袅袅烟云升起,把八字桥的四周填满。青松翠柏在云雾里跑来跑去,像一个个顽皮的孩子,要偷看新人热闹的婚礼。
新郎拉着新娘的手,唢呐在云雾里漂浮,一直响到天际,天上的彩云伸出一只手,把那唢呐声摁回八字桥的河里,河里传来彩色的回音,让人感觉这时候好甜蜜。新娘的红花布衣裳,在桥上发出璀璨的光芒,新郎的微笑感染着周围生灵,那些光和笑容包围着八字桥的后生和姑娘,以及像孩子样穿云钻雾的青松翠柏。
八字桥幸福地过着一天天的小日子。
八字桥总是云蒸霞蔚,雾气重生,似人间仙境。那时候,我也想牵着一个姑娘,走过八字桥,当一回云雾里的仙人,是啊,八字桥就是人间仙境呢。
更多的时候,我在八字桥河里洗澡,在那小小的水潭里戏水、捉螃蟹,躺在河里的大石头上看天上飞翔的云朵,望水里奔跑的小鱼和它身后划出弯弯的线条反吐出的泡泡。
看四周的山影一寸寸落进水里,由亮变黑。很多时候,我掏空脑袋,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扔到石头上,坐在那儿痴痴地发一下午的呆。
险岩子
跑步到险岩子就回去,大罗场的人几乎都这样。
我总是在这里跑步,总是在这里滚铁环,那些脚步和铁环的回响像楔子,嵌入我的脑子。
其实不走公路也可以从险岩子走过,那是一条小路,没有通公路时的必经之路,人们说它险,因为坡陡,直上直下,可是我们小孩子一般不走公路,喜欢直上直下的险岩子,还常常在这里比速度,看谁爬得快。
到了夏季的黄昏,来这里散步的大人也很多,我们也跟着他们来这里散步。夜来了,人们开始回家,一些小伙子有时候就突然跑起来,还会边跑边吼:鬼来啦,鬼来啦!于是小孩子也跟着跑、跟着吼:鬼来啦,鬼来啦。有人把鞋子跑掉了也不敢去捡,要等到第二天白天才去找。
险岩子哪里有鬼?久了才知道是那些小伙子想吓唬我们小孩儿,再久了,我们也敢晚上去险岩子玩了。
险岩子有个石坝,那里是我们的乐园。夏天乘凉,我们三三两两地随着家里的大人去那个石坝,带着簸箕或者凉席,在石坝上一放就可以躺下去,或者聊天,或者看天上的星空,偶尔看见流星划过,隔壁就有年长的人说谁谁逝世了等等。
险岩子总是那样迷人,尤其是夏天的晚上,那些流星在天空像一只只萤火虫飞过,带走我的沉重和祝福。
那些晚上,我也会想起逝去的和我们躺在簸箕里那些无尽的哀伤。
老 街
站在老街的街口,寻找青石板上残存的那些关于童年的影子,寻找那些在脑海和自己说话的儿时伙伴。
来到戏楼和街口之间,仿佛传来新春娃儿和秀群女子的争吵,你看我的飞机飞得多高?你看我的飞得多久多远?你们的都落地了,它还在飞耶!
秀群女子翻着自己的眼睛,露出白白的一大片,很是鄙视地对着新春娃儿吼出她的大声音。新春娃儿在她的白眼珠里找自己的影子,污着一张脸傻笑。
戏楼上又传来秀群女子好听的调子,她唱的红灯记真好听。我们在戏楼下疯跑,秀群女子的声音像她吐出的杏子核,打在我们的身后,把地板打得尘土飞扬,她的声音总会让我们放慢奔跑的脚步。虽然那些戏文我们都把它放在戏楼上,还给秀群女子,不记得了,也不管她是不是李铁梅还是长娃子演的李玉和,我们只顾玩我们自己的,即使那些好听的调子让我们放慢步伐,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戏楼下疯跑。其实秀群女子和长娃子也想和我们一起疯跑,他们才不想演《红灯记》、唱那些无聊的戏文,可要完成老师的任务,不得不去。
登上戏楼,就要丢掉快乐,长娃子和秀群女子都说过。
夏天里,长娃子死了,说是一个叫“钩端螺旋体”把他害死的,我们不相信,昨天还和我们一起打球,昨天还和我们一路抬水,咋可能就死了?
冬天里,秀群女子也死了,我们还是不相信,那天晚上还看见她站在戏楼上唱《红灯记》,演李铁梅,把一根长辫子一会儿放在肩上,一会儿又甩得老高,朝气十足嘛。虽然先前听说她患有肺病,但是又听说前不久就治好了,可是咋也死了?
可是他们真的都死了,才十岁啊。
儿时最好的伙伴新春娃儿,他的老汉是一个医生,房子依旧在街口立着。我站在他家的门前,听他弟弟说,这几年新春娃儿很不如意,现在成都打工,一家人都去成都了,勉强过着日子。
我不知道这勉强有多勉强,但愿还好吧。
我依旧站在街口,看那戏楼,像风化了的沙石,不敢抚摸,怕一摸就会塌下去。可是我又很想摸摸,或许能摸着长娃子和秀群女子那些跑过的脚步,摸着他们儿时的小手,还有他们和新春娃儿递过来还冒着热气的苞谷馍馍。
对面的老屋是邓同学的家,我记得那个名字从我的脑子里跑不见了,我只记得姓邓,有弟兄几人也忘了,可还是能记住儿时他神秘地说什么鲁班书,说什么走阴那些东西,大了知道鲁班、知道走阴是迷信的东西。只是他神秘的样子还是那么神秘。
妈妈的国营食店在老街最繁华的地段,那天,门口来了一个疯姑娘。她污污的脸庞,一身脏衣裳掩不住姑娘的迷惘,口里总是唱着只有自己才能听懂的歌谣,很多时候都在自顾自地抱怨着。一双赤脚在风中瑟瑟抖动,几个冻疮流着黄水,两只大眼睛暗淡无神,长长的头发遮住了半边脸,嘴里吐出微弱的呼吸,好像很久都没有吃饱饭了。
妈妈把姑娘领回家来,叫她洗澡,把自己的衣服给姑娘换上,还给她炖了一只鸡,又领她去理了头发。姑娘就变了样子,只是呆滞的眼神还是表明她不正常。父亲回来,又找来医生给她治病。等病情稳定了,把她交给隔壁王婆婆看管,渐渐地,姑娘的神智恢复了一些,大家知道她是青云乡的人,因为逃婚跑出来了。又过了一年,姑娘彻底好了,有人来做媒,不久姑娘就嫁人了,又回到青云乡。
姑娘离开的那天,不住地给妈妈磕头,要认妈妈为干娘。妈妈拿出几百块钱塞进姑娘的手中,姑娘和妈妈都哭了。
站在街口,我的眼眶湿润起来。
那些记忆也站在这个街口,随着一阵阵风扑向我,时而温暖,时而又把我撞得一身疼痛。
老 人
沿着老街向下走去,一排排木板房依旧整齐地安放在青石板街道两侧,古镇的气息扑面而来。我闻到了那年的腊猪蹄炖萝卜的味道,我多喜欢吃那样的腊猪蹄啊,味道依旧,可是炖肉的人哪儿去了,他们还在吗?
那间裁缝铺子的门还开着,我迈过门槛走进里间。我认出他来了,姓何的裁缝,小时候我经常被爸爸带到这里吃饭,逢年过节也来这里“坐席”。
何叔叔,我这样叫了一声,他很认真地看着我,你找谁?我没有说我是谁,我说小时候我经常来你家吃饭。
你头发白了。他还是很惊奇地盯着我,我说我是某某的幺儿子。喔,喔,你是?他竟然叫出了我的小名。我拉着他的手,他也拉着我的手,想不到你长这么高?现在变成这样子了?头发都白了,离开大罗场近五十年了啊,当然当然。
你高寿?八十三了,比你父亲小两岁,我和你父亲是小学同学呢。陈姨呢?我记起他夫人。我去喊我去喊,他几步就走到后面去,后面是一条公路,通到粮站的,我也记得。于是我跟着何叔叔来到公路上,看到一个也是白发还长满皱纹的妇人正朝家里走来,她看着我,也不能叫出我的名字。我想起了她总能煮一桌好吃的十大碗,冒着热气工整地摆放在桌上,我坐在桌旁,情不自禁想先夹一片猪耳朵,那时父亲就会摁住我的手,用眼睛瞪着,意思要等主人家把话说了,喝过一口酒才能动筷子。
你是?陈姨也叫出来我的小名,她把手放在腰间,她说,那时你这么高。我释然。
看到他们我又想起父母,在不经意间,我竟然就失去了父母,顿时,也失去了那些在这个桌子上的美味。
你父亲什么时候走的?咋不通知我们?我们也好送他一程,他是个好书记啊。说这话时,他们眼睛有泪,我转过身去,向他们挥手告别。
他们也转过身去。
终于又迈出门槛,就要离开那间裁缝铺,我朝他们的背影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心里祈祷着,祝福两位老人长命百岁。
一条路
那天早晨,天还没有亮,父亲把我抱上丰35拖拉机的座位上。父亲开着丰35驶出了农机站。
转过弯就上了新修的那条公路,才铺上碎石的路让这辆拖拉机颠颠簸簸,蜿蜒的山路似乎没有尽头。父亲一言不发,开着车灯,灯光拉着拖拉机在黑暗中慢慢爬行。
到了一个叫元石盘的地方,天就亮了。父亲停好拖拉机,先在地上找着什么,我发现地上有很多血迹。
父亲说昨天这里放炮有民工被炸死了,今天来参加追悼会。我又看见还有一些凌乱的足迹和炸飞的血肉丝。父亲眼里就有了泪光。
上午九点追悼会开始了。父亲拉着民工家属的手说,我代表大罗乡一万五千人感谢你们,感谢你的丈夫,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修路的英雄。这条路凝聚了我们大罗乡上万名老百姓的心血和梦想,我们要想过上好日子,就要修通致富路。我们有了通往县城的公路,我们还需要通往地区的公路,这条通往青云乡的路就是通往地区的路,这条路通了,我们离城市就更近了,离好日子也不会远了。
这条路是青云乡和大罗乡自己组织农民修通的。
那一年冬天,这条公路通了。
稻子梁
我住在乡政府,乡政府的背后有一座山,这里的人叫它稻子梁,稻子梁上没有种稻子,种着无数风景。稻子梁上有棵大松树,是大罗场的标志。
归家的人只要远远地看见这棵大松树,就知道马上到大罗场了。
读书的学生有很多去稻子梁玩耍,那里像一个公园,风景极其美,有松鼠有小鸟,有花有树,春夏秋冬总是呈现不同的颜色,一条小路直通学校。稻子梁总能把孩子们引进自己的怀抱,让他们在怀抱里撒娇撒野,放飞自我。
大松树上有取不完的松油,松油可以照明,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总是带着一个小瓶去大松树下取松油,还有人取松香,久了那大松树被伤了,于是附近的老百姓就用刺把树围起来,这样,那棵大松树又才活过来,依旧矗立在稻子梁上,让那些来大罗场的人能很远就看得见。
其实大罗场不用写路牌,只要看见稻子梁以及稻子梁上的大松树就知道这是大罗场了。
曾经的乡政府已经修了民房,还是一样的公路,我走在上面,远远地望着那棵大松树,稻子梁依旧郁郁葱葱。我儿时的伙伴好像在我面前一个个跑过,呼唤着我的名字,拉着我的手,要带我跑向稻子梁,跑向大松树。我们站在大松树下,看远处的云彩,看远处的人们,看远处归家的父母。还看邮递员骑着摩托车像一只小小的蚂蚁在公路上爬行,转过险岩子,直到完全消失影子。
有一天,我们一家人搬出大罗场,经过稻子梁,望着梁上的大松树,眼里装满了泪水。我知道我们要离开这里了,离开这块生长着我童年的土地,我多想再上一次稻子梁,抚摸那棵大松树,听松枝发出呵呵呵快乐的笑声。
我再次站在稻子梁上,再次走到大松树下。
今天,我看谁?看不见父母,看不见儿时的伙伴,也看不见那个蚂蚁一样的影子,却还执着地想那些关于童年的故事,像松涛阵阵,在脑海卷起圈圈涟漪。大松树又发出那些熟悉的笑声,从耳畔飞过,从稻子梁出发,又回到脚下。
大松树在笑啥?我不知道。
我在这里找童年,找啊,找啊,只能找出一个瞬间。
我在这里找童年,找啊,找啊,找不见过去的光影。
我走下稻子梁,向大松树挥挥手,是啊,我可以离开了,我的童年长大了,长成现在的自己,长成拥有一头饱经风霜的白发时光。
我还是静静地离开吧,不要打扰那些快乐的时光。毕竟,我来过这里,找到了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