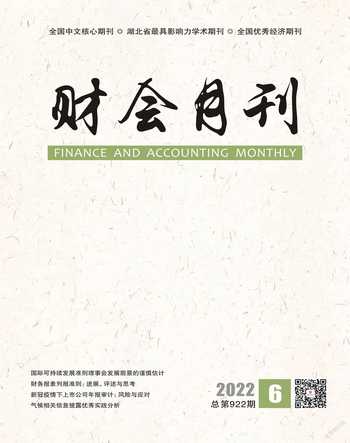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综述与展望
2022-03-26赵军张华峰
赵军 张华峰
【摘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 发现学者们对人口机会窗口及人口红利的概念已逐渐达成共识。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归纳出人口红利的测算及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 并对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未来的可能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经济增长;实现条件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2)06-0133-5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 我国经济迅速增长, 并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 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逐渐放缓,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通过探究这一变化的原因, 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口红利形成于人口转变的过程中, 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然而, 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不是必然发生的, 而是需要一系列条件才能得以实现的。 从人口转变的规律来看, 人口红利不能长期存在, 一旦人口条件发生显著改变, 人口红利必然下降, 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随之放缓。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历了急剧的人口变化, 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 总抚养比不断下降。 在破除一系列政策制度障碍后, 我国成功实现了第一次人口红利, 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 但在2010年进入拐点后人口红利逐渐下降, 经济增长也随之减速。 由此可见, 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探究我国如何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在决定经济增长的诸多生产要素中, 劳动力供给的数量、质量和周期变化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 学者们对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长盛不衰。 基于此, 本文对国内外有关人口红利的概念及拓展、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测算、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及变化趋势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并对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未来的可能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及拓展
1. 人口红利的概念梳理。 1998年Bloom和Williamson[1] 在分析东亚奇迹与人口变化的关系时, 发现人口增长速度及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高度关联。 他们认识到以往的学者更多关注20世纪50 ~ 60年代东亚人口转变的“负担”阶段, 而忽视了60年代后的“馈赠”阶段。 人口“馈赠”代表了潜在经济增长, 而它的实现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2001年Bloom、Canning和Sevilla[2] 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 他们认为人的需求和经济行为在人生不同时期存在差异, 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会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人口中大部分是劳动年龄人口, 他们所提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产生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但前提是利用人口红利的政策已经落实到位。
自从人口红利概念被提出后, 国外许多学者和机构对人口红利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国外学者Mason和Lee[3] 认为在人口转变第二阶段的早期, 生育率的下降导致少儿人口数量增长缓慢, 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 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被抚养人口时, 被释放出来的资源主要用于投资经济和增加社会福利, 因而人均收入明显增加, 这时就出现了人口红利。
在Bloom、Canning和Sevilla[2] 提出的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 国内许多学者也集中探讨了人口红利的概念, 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从已有的众多文献可以看出, 大部分学者将人口红利界定为特定人口条件拉动经济增长的额外收益。 蔡昉[4,5] 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比重大的有利人口结构产生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吴雪和周晓唯[6] 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 人口抚养比重较低, 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极为重要的结构性红利——人口红利。 崔凌云[7] 认为人口红利产生于以下情境: 死亡率下降, 尤其是婴儿死亡率下降, 同时出生率也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加。 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 一方面使劳动力供给增加, 另一方面提高了储蓄率, 最终促进一国经济增长。
有学者将人口红利界定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 车士义、陈卫和郭琳[8] 认为人口红利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 也就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大, 而抚养比较低。 杨成钢[9] 认为人口红利实质上是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对经济增长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状态。 也有学者将人口红利定义为一个特殊的时期。 孟令国和李超令[10] 指出人口红利是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而为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唐代盛[11] 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是总抚养比相对较低, 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对经济发展有利的黄金时期。 此外, 有学者将人口红利看成是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贡献。 陆旸和蔡昉[12] 认为人口红利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当一个国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和抚養比下降的特殊阶段时, 尽管缺乏技术创新及改革, 但也会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 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还有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是一种特殊的资源。 杨帆、黄少安和Picault[13] 认为从本质上来看, 人口红利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里一种有时间限制的资源, 它只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这种资源是在人口转变期中所获得的额外生产要素。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优势, 则人口红利就会刺激经济发展。
2. 对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认识。 在有关人口红利的文献中, 常常出现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 学者们对这两种说法持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认为人口机会窗口等同于人口红利, 另一种认为两者不能等同。 大部分学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Mason和Lee[3] 认为人口转变期间, 实际抚养比(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之比)持续上升的阶段被定义为“人口窗口”或“机会窗口”。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 及时抓住这个窗口期, 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样, Ross[14] 也将机会窗口看成是一个时间段, 他认为人口红利不会永远存在, 机会窗口是有时间限制的。 原新、高瑗和李竞博[15] 认为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其中人口机会窗口是人口发展阶段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期, 而人口红利是在匹配的社会经济政策下所实现的经济利益。 人口机会窗口是收获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 而人口红利是经济学概念, 前者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人口红利, 与人口机会窗口匹配的政策制度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16,17] 。 穆光宗[18] 认为人口机会窗口不是人口红利, 它只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 王广州[19] 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但两者又有重要关联, 因为人口机会窗口是人口红利产生的必要条件。
3. 人口红利的拓展。 随着对人口红利的深入研究, 学者们又将人口红利进一步细分和拓展。 Mason和Lee[3] 将人口红利划分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 其中, 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产生以生产性强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为必要条件。 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迅速上升, 而人口抚养比下降时, 此时的人口负担较轻, 社会储蓄倾向大, 这种情况有利于资本积累。 如果将储蓄用于各种投资, 则会增加人均收入, 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第一次人口红利终将消失, 当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后, 老年人口总量和占比持续增加, 此时若能制定富有远见、有效的政策, 则会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 结合人口红利的形成原因及我国的实际情况, 学者们对两次人口红利进行了区分。 王树[20] 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是人口结构红利, 第二次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人口预期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 原新、高瑗和李竞博[15] 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是数量型红利, 第二次人口红利是由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产生的人口质量红利。
对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产生, Mason和Lee[3] 认为当第一次人口红利下降后, 尽管在中短期老年人口增加导致人口负担加重, 出生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但是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 这种人口年龄结构也意味着个人消费减少、储蓄倾向增加, 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而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除高储蓄率外,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也会引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从我国的国情看, 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于老年人, 年轻人退休时所具备的综合素质将明显高于当前退休的老年人。 第二、三产业的高新技术领域及制造业对劳动力综合素质要求较高, 符合要求的劳动力供给相对有限, 年轻劳动力因其素质较高而比老年人更适应延迟退休政策, 因而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将增加[4] 。 蔡昉[21] 认为人口的传统增长动力依然存在,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充分挖掘: 一是继续推进户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二是改善人力资本结构。
三、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测算
1.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几十年来, 经济学家们都在争论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尤其是近年来, 从发展中国家人口变化趋势来看,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显著。 不同年龄组的人有不同的经济需求, 因而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有重要影响[22] 。 当少年儿童和老年人较少时, 总抚养比较小, 又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大, 人口具有较强的生产性, 社会储蓄率高, 这种情况促进了经济增长, 从而产生了人口红利[1] 。
Bloom、Canning和Malaney[23] 认为1965 ~ 1990年人口变化在亚洲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东亚的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创造了“东亚奇迹”。 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 1965 ~ 1990年东亚崛起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劳动年龄人口比抚养人口增长得更快。 Lindh和Malmberg[24] 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时, 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对OECD国家人均GDP总值的增长有显著影响。 Cruz和Ahmed[25] 扩展了1950 ~ 2010年实证分析的时间范围, 检验了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异质影响, 结果表明, 劳动年龄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 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6个百分点。 James[26]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测算印度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 结果表明, 劳动年龄人口的激增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Malmberg[27] 使用改进的罗默模型对1950 ~ 1989年的数据进行检验, 发现瑞典的人口年龄结构真实影响了经济增长。 当成年人口比重较大时, 经济实现快速增长; 当被抚养人口增加时, 人均收入增长速率下降。 Fougère和Mérette[28] 利用OLG模型检验七个OECD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表明, 当模型具有内生性增长时, 对人口老龄化长期经济影响的估计会发生显著改变, 人口老龄化可以促进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从而减少人口老龄化对人均产出的负向影响, 进而刺激经济增长。
2.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自人口红利被广泛研究后, 学者们开始利用多种方法计算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蔡昉和王德文[29] 使用多元回归的方法计算出1982 ~ 1997年因生育率下降所导致的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24%。 王丰[30] 使用实际抚养比作为第一次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 利用宏观模拟的方法计算第一次人口红利, 得出当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固定时, 第一次人口红利在1982 ~ 2000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5%。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实际抚养比不同于通常使用的总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 总抚养比是一个理论抚养比, 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并非真正就业的人口, 也包括失业或未就业的人口, 然而只有真正就业的人口才能创造社会财富, 所以这里用有效生产者区别于劳动年龄人口。 陈友华[31] 使用数学模型计算了人口红利因素对我国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 结果表明2006年人口红利的贡献为13.36%。 杨成钢[9]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测算1990年后我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结果显示1990 ~ 2000年间贡献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 但2001年后人口数量红利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尤其是在2010年后下降明显, 之后人口质量红利替代了人口数量红利。
四、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及变化趋势
1. 实现条件。 在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中, 特别是东亚国家, 其人口转变与高速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强相关性[32] 。 虽然人口转变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可以自动实现。 通常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具备适当的政策制度, 人口机会窗口才会开启, 也才有可能将潜在人口机会转变为现实的经济红利[15] 。
有关实现人口红利的条件, 国内外的学者从政策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Mason和Lee[3] 认为, 东亚国家人口红利的实现是政策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包括大量的就业机会、高生产效率、高储蓄水平、良好的投资环境、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 Bloom、Canning和Sevilla[22] 认为重要的政策包括: 公共卫生、计划生育、教育、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贸易开放和储蓄等。 陈友华[31] 也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 它的实现需要创造有利的条件, 包括一些宏觀条件、经济和生育政策, 以及人力资本政策等。 蔡昉[33] 认为人口红利的实现除了需要具备有利的人口结构, 还需要适合的政策制度配套。 如果没有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政策, 劳动力就会出现大量剩余, 从而造成大量失业或就业不足, 甚至会出现“人口灾难”。 陈岱云和张世青[34] 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并不一定转化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开启既需要人口机会窗口这一必要条件, 也需要其他社会经济条件, 如劳动力参与市场劳动的意愿、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以及保障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
在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 学者们也进一步探讨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 Mason和Lee[3] 认为第二次人口红利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似, 两者的实现依赖于有效的经济政策。 张学辉[35] 认为, 第二次人口红利是传统人口红利中通过储蓄机制完成的部分。 第一次人口红利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 正是因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 才弥补了资本报酬递减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当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后, 老年人口随之增加, 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最终导致老龄化程度加深。 进入老龄化社会后, 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具备四个重要的条件, 即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老年人口就业、提高老年人口收入和消费力、努力提高人口的预期健康寿命[36] 。 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正逐渐减少, 在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时难度加大, 更多地需要依赖人力资本积累及制度改革[37] 。 蔡昉[4] 认为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比, 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要求更高, 需要教育、就业、户籍及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
2. 变化趋势。 第一次人口红利具有时效性, 减弱和消失是必然的, 学者们普遍认同我国的第一次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弱。 郭晗和任保平[38] 将人口因素纳入稳态增长的公式中, 以此测算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结果显示我国于1987年进入人口红利期,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 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导致人口红利在2010年出现拐点, 之后持续下降, 与此同时老龄化不断加剧。 改革开放后, 人口健康状况的持续改善及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导致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升。 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是提升各年龄段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 尤其是老年人口, 从而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36] 。 相关数据显示, 未来10年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口数量将大幅增加, 人口红利也将从数量型走向质量型[39] 。 原新[40] 认为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正在减弱, 但仍然存在, 同时质量型红利正在增强, 所以我国正处于同时收获数量型红利与质量型红利的机遇期。
五、总结与研究展望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 发现自21世纪初提出人口红利的概念后, 学者们对人口红利的概念逐渐达成共识。 本文发现改革开放后, 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急剧转变, 通过破除一系列政策制度障碍, 并实施劳动力转移、经济政策及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和健康政策等, 我国收获了第一次人口红利, 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然而, 人口红利并不能长期存在, 在劳动年龄人口步入减少通道、抚养比不断上升的不利人口结构下, 我国的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阶段, 以人力资本和低龄老年人口供给为依托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正在开启, 然而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还存在一定的难度, 不仅需要依靠人力资本积累, 更需要深化教育、就业、养老保障等政策制度的改革。
在我国从人口数量优势转向质量优势的关键历史节点上, 虽然第一次人口红利正在减弱, 但仍然存在; 与此同时质量型红利正在增强, 所以未来在如何保持数量型人口红利或延缓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减弱速度, 全力挖掘、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领域还存在较大的空间: 第一, 紧密结合我国经济和人口红利的现状与问题, 探讨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和经济增长新常态以后, 尤其是老龄化深度发展阶段, 如何合理统筹运用延迟退休、鼓励生育、深化教育改革与城市农村户籍制度改革,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大力发展老年经济, 深入推进科技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完善各类改革的配套保障政策等, 努力保持数量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全力挖掘并释放质量型人口红利, 保障我国经济增长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 第二, 依据人口红利的内涵, 探讨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本质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内在形成机制。 第三, 从实现人口红利的角度, 具体分析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的有效政策制度。 第四, 基于人口红利的演变规律, 分析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及测算第二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Bloom D. E., Williamson J. G..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3):419 ~ 455.
[2] Bloom D. E., Canning D., Sevilla J..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J].NBER Working Paper,2001(8685):1 ~ 87.
[3] Mason A., Lee R.. 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J].Genus,2006(2):11 ~ 35.
[4] 蔡昉.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 J].中国人口科学,2009(1):4 ~ 12+113.
[5]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J].人口研究,2004(2):2 ~ 9.
[6] 吴雪,周晓唯.人口红利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及启示——基于二战后日本人口结构变化的分析[ 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101 ~ 109.
[7] 崔凌云.人口红利的作用:一个研究综述[ J].西北人口,2017(3):18 ~ 25.
[8] 车士义,陈卫,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 J].人口与经济,2011(3):16 ~ 23+77.
[9] 杨成钢.人口质量红利、产业转型和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J].东岳论丛,2018(1):46 ~ 53.
[10] 孟令国,李超令.我国二次人口红利的困境摆脱与现实愿景[ J].改革,2013(1):149 ~ 157.
[11] 唐代盛.中国人口红利动力转换及其发展策略[ J].人民论坛,2020(23):84 ~ 87.
[12] 陆旸,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 J].世界经济,2014(1):3 ~ 29.
[13] 杨帆,黄少安,Picault P.. 中国人口红利结束了吗?[ J].山东社会科学,2017(4):82 ~ 89.
[14] Ross J.. Understanding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R].Washington, DC: USAID,2004.
[15] 原新,高瑗,李竞博.人口红利概念及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再认识——聚焦于人口机会的分析[ J].中国人口科学,2017(6):19 ~ 31+126.
[16] 原新,高瑗.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与人口红利[ J].人口研究,2018(6):3 ~ 14.
[17] 李竞博,原新.如何再度激活人口红利——从劳动参与率到劳动生产率:人口红利转型的实现路径[ J].探索与争鸣,2020(2):131 ~ 139+160.
[18] 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 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5 ~ 13.
[19] 王广州.中国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再认识[ J].中国人口科学,2021(3):2 ~ 16+126.
[20] 王树.“第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理论渊源、作用机制与数值模拟[ J].人口研究,2021(1):82 ~ 97.
[21] 蔡昉.中国如何通过经济改革兑现人口红利[ J].经济学动态,2018(6):6 ~ 16.
[22] Bloom D. E., Canning D., Sevilla J..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M].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2003.
[23] Bloom D. E., Canning D., Malaney P. N..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00(26):257 ~ 290.
[24] Lindh T., Malmberg B.. Age Structure Effects and Growth in the OECD(1950-1990)[ 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1999(3):431 ~ 449.
[25] Cruz M., Ahmed S. A.. On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Change on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J].World Development,2018(105):95 ~ 106.
[26] James K.. Glorifying Malthus: Current Debate on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India[ J].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08(25):63 ~ 69.
[27] Malmberg B.. Age Structure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Swedish Evidence[ J].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94(3):279 ~ 295.
[28] Fougère M., Mérette M.. Population Age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even OECD Countries[ J].Economic Modelling,1999(3):411 ~ 427.
[29] 蔡昉,王德文.中國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 J].经济研究,1999(10):62 ~ 68.
[30] 王丰.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 J].人口研究,2007(6):76 ~ 83.
[31]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58 ~ 63.
[32] 张车伟.“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前景[ 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0(8):14 ~ 15.
[33]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4] 陈岱云,张世青.新中国7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红利效应嬗变[ J].江海学刊,2019(4):15 ~ 21+254.
[35] 张学辉.人口红利、养老保险改革与经济增长[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
[36] 蔡昉.如何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 J].国际经济评论,2020(2):9 ~ 24+4.
[37] 原新,刘厚莲.中国人口红利真的结束了吗?[ J].人口与经济,2014(6):35 ~ 43.
[38] 郭晗,任保平.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J].当代财经,2014(3):5 ~ 13.
[39] 陆杰华,林嘉琪.中国人口新国情的特征、影响及应对方略——基于“七普”数据分析[ 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3):57 ~ 67+2.
[40] 原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新时代的国家战略[ J].人口研究,2018(3):3 ~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