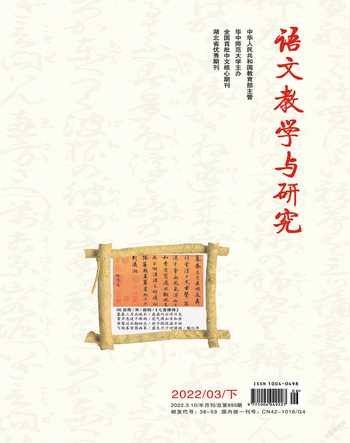《十六年前的回忆》的写作艺术
2022-03-26王德禄
《十六年前的回忆》是一篇回忆录,是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为父亲遇难十六周年时写的。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回忆了父亲被捕前后的情形,读来感人肺腑,令人泣下。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革命先驱者李大钊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无私,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强信心。我们永远难忘的是,革命先烈们血洒江山换来后辈的美好生活,赢得今天祖国的繁荣昌盛。这是一曲颂扬革命先烈的赞歌,是一篇闪耀革命光辉的红色经典。既有可供品鉴的文学价值,也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文章深深打动我们的不单是伟人形象的崇高,还在于作者饱含浓浓深情的抒写。
一、语言质朴,蕴藏丰富的内涵
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是打造人物形象的媒质,文章内容决定语言特色。本文歌颂的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作者遣词造句十分质朴、平淡,但朴而不俗,平而不浅。字里行间跳动着作者深沉的情感,内容含蓄蕴藉,富有韵味儿,耐人咀嚼。这里挑选几个句子说明。
如写白色恐怖时期,局势越发严重,“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去了”。这里连用两个“每天”,再加一个“又”字,语言平白如话,不事雕琢。让我们感到父亲革命工作的紧张繁忙,感到当时局势的严峻,也暗示他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我”经常拿许多幼稚的问题询问父亲,无论工作多忙,他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给“我”讲解。而这次“我”问他为何烧带字的纸张和书籍时,他回答得很含糊。这里用“无论”和两个“总是”,说明父亲平时对女儿十分和善和关爱,很顾及孩子的情绪;答话的“含糊”,说明文件和书籍很重要,关涉革命大事难于几句话解释明白,也无须让懵懂的孩子知道后担惊受怕。这些朴实的词语蕴含丰富,令人深思。
在法庭上,亲人们见到父亲,放声哭喊。父亲只是眼睛“瞅了瞅”我们,表情“安定沉着”。从他的模样看,他受过严酷的刑具折磨。据史料记载,敌人在关押期间,对他进行过无数次的各种灭绝人性的拷打,如坐老虎凳、拔指甲等,他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血迹斑斑,伤痕累累。但强烈的信念支撑着他,他强作若无其事,脸上没有流露出半点疼痛和哀伤。一方面他要以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压倒敌人的嚣张气焰。再就是以表情暗示家人不要悲哀,不必担忧,要化悲痛为力量。这反映了他对家人的爱护,显示出一位慈父形象。另外,文章首尾两次提及李大钊牺牲的具体时间,语言简洁而朴实,既说明作者难于忘记父亲被害的惨事,也表达了作者对敌人灭绝人性行为的愤慨。
总的看来,作者笔触客观冷静,于平淡的娓娓叙述中,含不尽之意在言外,蕴蓄着深沉而浓烈的情感。作者没有激昂的言辞,没有澎湃的抒情,让情感在平静的叙事中缓缓流淌,读之感人至深,令人泣下。
二、对比映照,凸显崇高的品质
不见山之巍峨,就不知地之平坦。同理,就写人来说,有对比才有鉴别,人物相比方能彰显不同的待人处事特点和思想境界等。对比,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对比,可以是一个人在不同境遇下自身前后不同态度的对比,可以是人的外形及外部表现与内在的思想实质的对比等等。对比能形成反差,突出人物性格,凸显人物品质。本文运用对比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来:
①父亲对待“我”的态度。父亲在家人的心目中是主心骨、顶梁柱,是一座巍峨而沉稳的大山,是家人坚实的依靠。父亲对每个孩子都是疼爱的,从来没有打骂过,是一位慈祥温柔的父亲。对于“我”五花八门的甚至十分幼稚可笑的问题,父亲没有不屑一顾,没有疾言厉色。总是显得兴趣很浓,放下手头忙碌的工作,不厌其烦地耐心地给“我”讲解,一次都没有疏忽过。但有一次“我”看见父亲正在烧书和文件时,便询问缘由,他回答是含糊其辞,语气也没有以前的温和可亲。父亲对待“我”前后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这让“我”感到意外,不得其解。其实,父亲的“含糊”是一种对大人们该做的事业的隐瞒,是一种对小孩子的爱护。从这个对比中,我们能体会到李大钊对革命机密的严守和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
②父亲身临险境的态度。当时形势危急,敌人疯狂地要熄灭大革命运动之火,到处制造白色恐怖,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我党领导人李大钊的工作更加紧张,处境更加危险。军阀张作霖通缉四处抓他,大家都为他担心。朋友劝他离开北京,难于改变他的主意,母亲也极力劝说,仍然无果,他说工作紧张,不能离开。面临险境,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毅然决然地留在龙盘虎穴的北京工作。这是局势的紧急与坚决的态度形成的对比,凸显了李大钊舍身忘死、勇挑革命重担的崇高品质。写他被捕时,也用了对比,敌人的慌乱嚣张与李大钊的镇定自若对比,敌人的人多势众与李大钊的孤军奋战对比,敌人的邪恶与李大钊的正义对比。无论敌人怎样嚣张跋扈,他始终“保持着惯有的严峻态度”。正反人物之间形成强烈对比,凸顯了李大钊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③父亲遭受酷刑后的态度。作者写父亲被提审时“没戴眼镜”,想必眼镜一定被敌人打碎了;长发“乱蓬蓬”的,这是关押时间长,非人性折磨的结果。至于身体消瘦、脸色苍白、眼圈浮肿、血迹斑斑等惨不忍睹的情况只字未写,作者不忍写,这也给读者留下想象余地。可以想到,敌人各种刑具对他身体的折磨会造成多大的创伤。尽管如此,他仍然沉着镇定,面无惧色。他想让敌人看到一个坚不可摧的共产党人形象,更不想让家人痛苦担心。这是将李大钊惨遭酷刑折磨的样貌与“平静而慈祥”的神态形成强烈的对比,凸显出李大钊面对死亡泰然自若的顽强意志。
三、多维着笔,展现立体形象
人物形象有立体感,才能打动读者,才能让读者产生铭记在心的深刻印象。要展现人物立体形象,就要从多方面正面刻画人物,如外貌、动作、语言、心理等,这是写人不可少的基本手法,多维着笔,立体感就强。本文没有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根据写人的实际需要,有所选择,择取最具触动作者心灵而又是自己耳闻目睹的方面精心描摹。
我们先看李大钊的语言。在风雨如晦、黑云压城的危急时刻,敌人已经得知他就是北方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布下天罗地网要抓捕他,同志劝,妻子催,他就是不肯出去躲。他坚决地对妻子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这几句纯属口头语言,从“常对你说”,可看出妻子平时处于对他安危的考虑,对他劝说很多次了,也可看出李大钊对家人的教育和影响之大。“现在是什么时候”“多么重要”,可见,他把党的工作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先用一肯定句“不能”,再加一反问句“哪能”,表现了他坚决的态度和高度的工作责任心。敌人在屋外传来激烈的枪响和纷乱的大叫,“我”不解地问父亲发生了什么,父亲明知自己危在眼前,安慰孩子不要怕,这显示出李大钊面临危险的沉着、镇静。在法庭上,敌人指着“我”问父亲是不是最大的孩子,“我”机警地回答自己就是最大孩子。父亲赶忙说妻子来自乡下,孩子年幼,啥也不懂。父亲主动承担责任,保护了家人,表现了厚重的父爱。
我们再看李大钊的动作。他感觉自己已经暴露,敌人有备而来。他没有慌乱,在家“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将进步书刊和字纸“投”进炉火。简单的动作,可看出所烧内容的重要,他对党组织的忠诚。敌人来逮捕他时,他是不慌不忙从抽屉拿出小手枪往外走,显示出他面临险境的沉着冷静。
作者对李大钊的外貌描写也很生动。他被押到法庭上时,穿着灰色旧棉袍,未戴眼镜,长发蓬乱。“旧棉袍”说明他虽为大学教授,但一心革命,生活过得俭朴;“未戴眼镜”“长发蓬乱”暗示敌人限制了他的双手,动用了酷刑。在敌人面前他的态度始终是“严峻”的“沉着”的,表现出铮铮铁骨、大义凛然的形象,在亲人面前的表情是“安定”“平静”“慈祥”的。面对一家人哭,父亲没说话,只是“瞅了瞅”,万千语言尽在不言中。“瞅”中有对亲人的心理安慰,有精神的鼓励。他用自己的表情感染家人,暗示要他们要坚强地生活。李大钊为何这般态度,这来自于他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
李大钊牺牲时才38岁,他临刑前留下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自若,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可见他面对死亡,没有丝毫的慌乱和悲哀,惯有的神态显示出一位共产党人的伟大形象。文章通过对人物的多维着笔,展现出立体的感人形象。
四、侧面描写,烘托伟大人物
文章除了正面多维着笔,还用了侧面描写。所谓侧面描写,是为了突出某个人而描写与此人有关的其他人物或事物。运用侧面描写能以此显彼、以次衬主,以反显正,更有力地烘托人物多方面的特征。这是一种间接的表情达意,使文章会更显含蓄、客观,中心会更突出。本文侧面描写较突出的是对反面角色的刻画,很好地烘托了伟大的人物。
比如写李大钊被捕时,作者浓墨重彩用较多的篇幅侧面着笔,写捉拿李大钊的敌人。先交代来者身份之杂,有穿灰制服的宪兵,有穿黑制服的警察,有穿便衣的侦探,各色人马全部到场抓捕他,可见李大钊身份之重要。后交代来人之众,满满地拥挤小屋。为抓捕一个文人竟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可见敌人的心虚怯懦。再看看敌人来时的氛围。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李大钊还没有看到敌人,门外就传来各种声响:尖锐的枪声,纷乱的喊叫,沉重的皮靴声,粗暴的吼声,咚咚的踹门声。这些杂乱的响声渲染了紧张、恐怖的氛围,突出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按理说,抓人为防止打草惊蛇,应该秘密进行,可敌人偏偏要弄出各种声响,唯恐别人不知道。为何要这般虚张声势,说到底就是为了掩盖自己恐惧的心理,为自己野蛮行径壮胆助威。我们再看看敌人的表现:他们连踢带撞,强行入门,蜂拥而上。抓捕时,一律枪口对着父亲和“我”。然后是“夺”父亲手枪,“搜”他全身,用绳子“绑”他胳膊,强行“拖”走,“关”进警察厅的院子。这些粗鲁的行为,足见他们人多势众、蛮横无理。敌人的容貌也十分令人憎恨,凶神恶煞,犹如“魔鬼”,身体肥胖,满脸横肉,一脸冷笑,一副副丑恶的嘴脸显示出凶残的本性。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反面人物的嚣张、残暴的种种丑陋表现,这是从侧面衬托李大钊的面对逮捕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的高大伟岸形象。
还有被绑着胳膊用绳索牵着的工友阎振三,他脸色苍白,披散着头发,显然受过酷刑,但他未显示胆怯。这既从侧面透露出敌人的凶残,也衬托了李大钊的精神力量对身边同志的影响。面对敌人的到来,“我”的心“剧烈”跳动,眼光十分“恐怖”,这都有力地衬托了父亲的冷静,说明他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
以上,对人物有反面衬托,也有正面衬托,人物在衬托中,形象更加鲜明突出。
五、前后呼应,形成紧凑的结构
本文按时间顺序写了李大钊逮捕前、逮捕时、法庭上、牺牲后的情形,前后一贯,首尾圆和,同时在叙事中又前后呼应。在结构上,呼应使文脉更加顺畅,文章内容勾连紧凑,能唤起读者审美愉悦;在内容上,呼应也是为表情达意、突出人物形象服务的。本文呼应的地方有四处:
一处是写父亲烧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问父亲为何要烧这些东西。若“呼”而不“应”,读者就不明晓。文章后面就交代了父親此举原因,原来是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搜查,为了保护党组织不遭破坏,不得已才要烧毁这些。作者后来才明白当时父亲面临处境的危险性,明白父亲含糊回答“我”疑问的原因,明白了他早出晚归忙碌工作的重要性。这反映了李大钊高度的警惕性,突出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
二处是前文提到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购东西,直到深夜也未归。后面在逮捕李大钊时发现军警里面用绳子拴着的阎振三。写阎振三的失踪,暗示局势严重,革命处于最关键时期,这也是李大钊一直要坚持在北京工作的原因,同时为李大钊的被捕设下伏笔。这后面的照应既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李大钊的精神对身边的同志产生的深刻影响,阎振三宁可自己遭受酷刑,也不泄露党组织的机密。这也更加突出了李大钊处危不惊、革命事业高于个人生命的大无畏精神。
三处是敌人来抓捕时,父亲从小屋抽屉不慌不忙拿出小手枪往外走,后面写他被捕时,敌人夺下他的手枪,并搜遍全身,这是一种前后呼应。这样写让读者明白李大钊拿枪是为了万不得已就进行反击。李大钊明白自己在敌人眼中是重要的人物,与其抓住后受尽酷刑折磨,最终难逃一死,不如开枪打死几个给自己垫棺材。但他没有开枪,那是为了不让家人受到丧心病狂的暴徒伤害。危险在即,他首先考虑的是家人的安危,坦然应对眼前的一切。
四处是开篇交代父亲遇难的时间,结尾写母亲要孩子们记住父亲遇难的日子。首尾呼应,点明李大钊烈士牺牲的具体时间,强调这是非同寻常的日子,也突出了作者对父亲的无限怀念之情。
作者用深沉的笔触,质朴的语言,刻画了一位伟大的形象,给人们留下永恒的记忆。学习本文,不仅仅是学习精巧的构思艺术,还要学习老一辈的坚定革命信念、顽强的斗争意志和高尚的理想追求,努力传递红色精神。
王德禄,甘肃省通渭县马营教育学区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