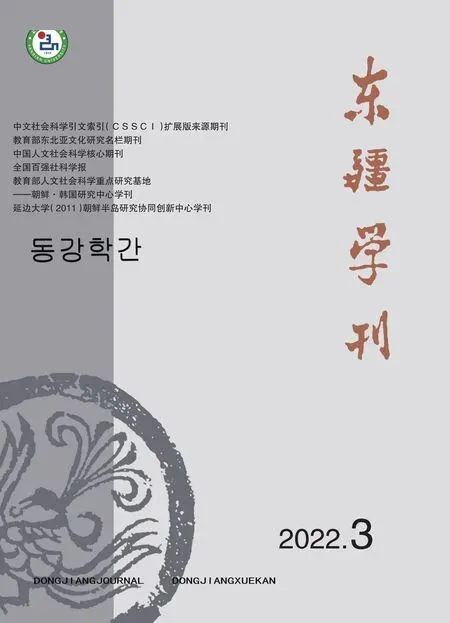论高丽朝对唐代御史制度的接受与变异
2022-03-24张春海
张春海
现在学界多将对唐代制度的认知套用于高丽朝,认为御史台是高丽朝的总检察机关。[1](36-39)实际上,高丽朝御史制度虽借鉴了唐制,但贵族制的基本国情使之发生了重大变异,御史台由王权的耳目与爪牙之司一变而为制约王权的机构,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一、监察权的变异
从形制上看,高丽朝御史台是唐制的缩小版。《高丽史·百官志》载:“(御史台)掌论执时政矫正风俗纠察弹劾之任……有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忠烈王元年,改监察司……忠宣改为司宪府……恭愍王五年,复改御史台,大夫如故。”[2](2146-2147)唐王朝对御史的首要定位是皇权的耳目与爪牙,作为君主的鹰犬搏击群臣,监察百官,是御史的基本职责,弹劾权是其最核心的权力。高丽朝成宗在模仿唐制创法立制时,企图强化王权,故亦将弹劾官员设定为御史的基本职权,即所谓“本朝之制,都堂总百揆,颁号令。宪司察百官,纠风俗”。[2](2670-2671)
但在高丽朝特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这种制度化权力很快就发生了变异——向制约王权的方向演化——御史逐渐取得了对宫内系统人员的弹劾权。明宗八年(1178)三月,御史台奏:“内侍茶房实踰定额”,国王只得下制:“削内侍林正植等十二员,茶房六员。”[2](611)御史台权力的扩张,使弹劾权的性质从王权的延伸变为对王权的制约,内官系统乃至王权与御史间的积怨越来越深。毅宗十年(1156)九月,“御史台吏脱内官禁服,王怒,囚其吏”,[2](548)而“宦者郑諴谋陷台谏,密诱散员郑寿开诬告台省及台吏李份等怨王,谋推戴暻为主。王惑其言,欲去之”。[2](2837)
由于御史逐渐演变为贵族权的一极,与王权形成了制约乃至“对抗”关系,故常需以团体的力量抗衡乃至“压迫”王权,集体行动成为他们履职的基本方式。如王权坚持己见,御史们便以集体罢工的方式迫使其收回成命。仁宗时,朴挺蕤被擢为殿中侍御史,“论议务举大纲,不为苛细。尝与知御史台事崔灌、侍御史印毅、崔述中、安淑等,论枢密使陈淑尝讨西京,受人奴及宝带,伏阁三日不报,皆杜门不出。”仁宗召谕令视事,“挺蕤与述中,固争不就职。”[2](3036)仁宗十年(1137)五月,“御史大夫任元濬等以贡院试题错误上奏,请追夺今年及第名牌,改试,不报。元濬等退而待罪,台空凡七日。”[2](482)郑道传论御史权力云:“君有佚豫失德,悖乱亡道,荒政咈谏,废忠慢贤,御史府得以谏责之……君至尊也,相与将至贵也,且得谏责纠劾之,余可知也。”[3](393)御史们以“府”为单位行动,对王权进行“谏责”是其权力行使的基本特性。
弹劾权在性质上的这种根本性变化,使御史们拥有了对君主在施政乃至个人行为上全方位的监察权。如上文郑道传所言,他们不仅已完全谏官化——取得了“谏”的权力,而且取得了“责”的权力,即贵族化了。“责”,意味着地位上的对等性,实质是将君主视为官僚机构中的一个职位。这只有在贵族政治的语境中才能理解。郑道传在其《经济文鉴》“谏官”条中又云:“先朝有为台谏者,上谓之曰:‘朕不欲台谏奉行宰相风旨。’则对曰:‘臣非惟不欲奉行宰相风旨,亦不欲奉行陛下风旨。’壮哉斯言。”[3](397)御史的全面谏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项权力的逐渐取得上。
首先是从复请权到驳执权之系列性权力的取得。所谓复请权,指台官在其建议或弹劾案被君主驳回后,要求国王收回成命并接受提案的权力。《高丽史·赵冲传》:“御史台上疏曰:‘郑邦辅、赵冲望贼畏缩,莫有斗心,弃军惊走……请免其职。’不允。御史台复请罢职,从之。”[2](3150)由此可见,复请权针对的已非官员,而是王权。
与之相似的还有复驳权。文宗元年(1047)三月乙亥,日食,御史台奏:“春官正柳彭、太史丞柳得韶等昏迷天象,不预闻奏,请罢其职。”文宗制:“原之。”御史台“复驳”曰:“日月食者,阴阳常度也。历算不愆则其变可验。而官非其人,人失其职,岂宜便从宽典,请依前奏科罪。”[2](182)复驳权由复请与驳奏两项权力组成。首先是复请,坚持己见;如国王不从,则可依法据理,予以驳斥。
更进一层,御史们还可直接驳回国王的决定,即与谏官们共与享“封驳”权。忠烈王曾“命随驾军士预给禄,御史驳之”。[2](958)御史台又享有“执奏”权,即坚持己见的权力,这两项权力的结合即为“驳执”。文宗元年(1047)八月,御史台奏:“近日除李希老、洪德威为监察御史。希老性躁急……俱不宜风宪,请黜之。”国王不允。御史台“再驳切直”,国王“从之”。[2](184)复驳权这一从弹劾权衍生出来之权力的取得,使御史台成为和宰相、谏官一样的以监督与制约君主为主要职责的机构。
其次是署经权的取得。唐代御史的监察权针对的是官员们的履职过程与结果,对官员的任命不具有任何权力,因为从终极的角度讲,任命权归于皇帝,御史作为皇权的爪牙,无权过问皇帝人事权的行使。高丽朝御史的监察权却由官员们的行政过程与结果逐渐向上延伸到作为他们出仕源头的君主。君主任命官员,御史们对其任命具有否决权——“署经权”。如御史们拒绝在国王签发的告身上署名,则该项任命不能生效。毅宗时,金敦中为殿中侍御史,“王拜宦者郑諴阁门祗候,敦中不署告身”。[2](3029)尹贤被国王任命为典法佐郎,“台官不署告身。贤昏夜乞哀”。[2](3764)从表面上看,署经权仍是一项针对官员的监察权,但由于其制约对象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故其性质亦彻底改变。
郎舍亦拥有署经权。郎舍乃门下省官员,大致相当于唐代的谏官系统加上以给事中为主的封驳系统,唐中书省以中书舍人为主之撰拟诏令的系统亦属这一范围。《高丽史·百官一》:“门下府,掌百揆庶务。其郎舍掌谏诤封驳。”[2](2404)郎舍的组成人员被称为“省郎”,主要包括司议大夫(左右谏议大夫)、给事中、舍人(中书舍人)、起居注、起居郎、起居舍人、献纳(左右补阙)、正言(左右拾遗)。他们均为谏官——“谏诤,省郎之任”。[2](3267)就制度的规定而言,乃先由谏官署经,[2](3897)再由台官署经,御史处于最后把关者的位置。[2](3056)宰相的告身亦需台谏署经。[2](3744)署经权的取得是御史谏官化的重要表现。御史台与谏官机构的职能基本重叠,他们为制约王权而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连带关系的“命运共同体”。
高丽朝御史之所以能取得此项重权,乃是由朝鲜半岛贵族社会的权力格局所决定。这一权力的实质,是在制约君主的同时,严格把控王朝仕路,以维持世家大族“小集团”的性质及本集团成员在文化与道德上的优势。
最后是进谏权与论政权的取得。台官的谏官化,使他们取得了与谏官一样的进谏权,这一权力被明确表述为“与天子争是非”。《崔娄伯配廉琼爱墓志》载:
吾自司直传右正言知制诰,君喜动于颜,曰:“吾贫几济矣。”吾应之曰:“谏官非持禄之地。”君骂曰:“傥一日子立殿陛,与天子争是非,虽荆钗布裙荷畚计活,亦所甘心。”此似非寻常妇言也。[4](675)
如国王不听谏诤,御史们会面折庭争。毅宗五年,国王“以郑諴权知阁门祗候”,台官“以宦者参朝官无古制,争之”。[2](2381)如国王仍不采纳他们的谏言,御史们将以集体罢工的方式迫使国王就范,此乃高丽朝“君弱臣强”的政治现实在具体权力运作过程中的体现。后世朝鲜王朝的君主们对此十分清楚,成宗即曰:“前朝之季,君弱臣强,言事者辞职,退家废事,至于二三日,人君敦谕至再三,乃出视事。”[5](958)
在唐代,御史的基本职掌为“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6](378-379)不具有当然的论政权。在高丽朝,台官的谏官化使他们拥有了论政权。“论执时政”甚至被规定为御史的首要权力。文宗六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论时政得失。”[2](198)御史拥有的权力在性质上已与宰相相似。辛禑十六年十月,宪司上书:“古之为国者,必先立纪纲……殿下即位,大开言路,相臣宪臣,各陈时务……坚如金石,信如四时。”[2](679)相臣与宪臣乃并列关系,他们常一起论“时政得失”。[2](182)在重要性上,御史仅次于宰相。郑总为郑道传《经济文鉴》作序时就讲:“予观是书,其首之以相业者……人君当以择相为先……次之以台谏者,台官纠禁风俗之恶,谏官论奏人主之失,实国家之所重。”[3](411)
御史在谏官化的同时又贵族化,这使台谏官常与宰相共同行动以制约王权。《高丽史·郑袭明传》:“仁宗朝……与郎舍崔梓、宰相金富轼、任元敳、李仲、崔奏等上书言时弊十条,伏阁三日不报,皆辞职不出,王为罢执奏官,减诸处内侍别监及内侍院别库,召梓等令视事。袭明独以言不尽从,不起。右常侍崔灌独不与上书,供职如常,议者鄙之。”[2](3031-3032)宰相集团、台谏官均以集体行动为基本原则,是朝鲜半岛贵族社会政治过程的一个基本特点。
御史与宰相权力上的重叠,还表现在其他权力的行使上。首先,宰相和御史共同行使复请、驳执、谏诤、论政等权力。睿宗四年十一月,“宰相崔弘嗣、李敖、任懿等与台谏复请尹瓘等罪。”[2](375)下年五月,“宰相崔弘嗣、金景庸与台谏上疏论尹瓘、吴延宠等败军之罪,王不听便入内。弘嗣等诣重光殿东紫门固请,至晡,竟不允。宰相谏官皆归第不出,省中一空。王召平章事李敖、中书舍人李德羽等令直省中。弘嗣等累旬不出,王遣近臣敦谕起之,谏官亦出视事,时人讥之。”[2](377)
其次,对于署经,宰相们也要“参署”。毅宗十一年十一月,“命左承宣直门下省李元膺、右承宣左谏议大夫李公升传旨门下省,督署郑諴告身。宰臣及谏官,论执不可。公升往来再三,复传旨曰:‘卿等不听朕言,朕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平章事崔允仪、右谏议崔应清及元膺、公升等,不得已署之。”[7]我们有理由怀疑,最初,署经权是宰相机构用以制约王权的一项权力,之后御史台贵族化,亦获得了此权。
二、监察内容的变异
高丽朝御史职权的谏官化,是台谏合流的一种表现,与中国唐代以后在谏官台官化基础上的台谏合流完全相反。中国宋代以降的台谏合流以皇权的提升为背景,高丽朝台谏合流的背景则是贵族社会的巩固。高丽朝御史职权的谏官化乃其地位贵族化的表征,贵族化趋势又使御史的监察内容发生了变化。尹鳞瞻在毅宗朝为侍御史,“言事忤权贵,降授左司员外郎,转起居注。时宫人无比得幸于王,生三男九女。崔光钧为无比女壻,因缘内嬖,超授八品,兼式目录事,士夫莫不切齿,谏官不署光钧告身。王召鳞瞻及谏议李知深、给事中朴育和、司谏金孝纯、正言梁纯精、郑端遇,督署之。郎舍畏缩,唯唯而退。有人嘲之曰:‘莫说为司谏,无言是正言。口吃为谏议,悠悠何所论。’”[2](2988)在贵族体制下,出仕资格是“公论”的核心。
世家大族以血缘为基础之小集团的性质,是高丽朝贵族制维持的前提。朴褕曾上疏曰:“我国本男少女多,今尊卑皆止一妻。无子者亦不敢畜妾,异国人之来者则娶无定限,恐人物皆将北流。请许大小臣僚娶庶妻,随品降杀,以至庶人得娶一妻一妾,其庶妻所生子亦得比嫡子从仕,如是则怨旷以消,户口以增矣。”在男少女多的现实下,为增加人口,朴褕建议允许国人娶妾,这在传统社会特别是在中国制度的参照下,本不应成为问题,可结果却是“妇女闻之,莫不怨惧……时宰相有畏其室者,寝其议不行”。[2](3276)
所谓妇人抱怨、宰相畏室不过是说辞,问题在于能娶妾,甚至娶多妾之人大多是世家大族中人。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导致贵族集团人口的膨胀,威胁到其小集团的特性。而“庶妻所生子亦得比嫡子从仕”的制度设想,更直接涉及官职资源的分配。在朝鲜半岛的体制下,贵族既不力农,也不从商,只有做官一途。官职乃稀缺资源,不可能无限供给。人口增加与庶子比嫡子从仕,必将带来既有出仕制度的根本性改变。一句话,朴褕的设想破坏了贵族制的基本原则,使贵族制本身有崩坏的危险,故遭到宰相们的反对。忠烈王时,为了增加户口,也曾采取过“令士民皆畜庶妻……其子孙许通仕路,若不顾信义,弃旧从新者,随即罪之”[2](3168)的政策,因同样的原因无法实行。
为维持统治群体小集团的特性,不仅要限制家庭规模,维持家庭内部森严的等级秩序,还需设计出相应的制度,以各种标准对贵族家庭成员进行筛选与淘汰。在选官、任职、升迁等关键性节点,设置一些限制性标准,将一些人排除在外,便成为这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这些标准大致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血统,一是道德。体现血统标准的是“世系”。在高丽朝,官员们的仕途与世系密切相关,门荫全靠世系自不待言,与门荫并列的另一重要出仕途径“科举”也有世系要求——“国子监以四季月六衙日集衣冠子弟,试以《论语》《孝经》,中者报吏部,吏部更考世系,授初职。”[2](3053)是否任官及任什么级别、哪些部门之官,首先取决于世系。科举时,考生必须在卷首写明世系,法律规定:“氏族不付者,勿令赴举。”[2](2305)如果违反了与世系相关的法律,后果相当严重。《高丽史·孙抃传》载:
抃官累枢密院副使……以妻派联国庶,不得拜台省、政曹、学士、典诰,妻谓抃曰:“公因我系贱,不践儒林清要,敢请弃我,更娶世族。”抃笑曰:“为己之宦路,弃三十年糟糠之妻,吾不忍为也,况有子乎?”遂不听。子世贞,亦不得赴举。[2](3140-3141)
对官员们“世系”的监察成为高丽朝御史行使监察权的重要内容,此为唐代所无。不得赴举之人及他们的后代,大多只能从事各种“贱役”,不可避免地沦落到社会下层,直接导致家族的没落。
御史们对官员世系的监察,主要通过署经权实现。忠惠王时,嬖臣崔安道之子崔璟“年十余,不学得中试”。结果“台官以璟借述登第,祖母又贱,不署依牒,凡九年”。[2](3766)《高丽史·康允绍传》:
康允绍,本新安公之家奴,解蒙古语,以奸黠得幸于元宗。累使于元,以功许通宦路……忠烈王元年,拜军簿判书、鹰扬军上将军。时群臣以新官制改衔,唯允绍系贱,为监察司所论,未改。允绍自出视事,复为监察司所劾免。[2](3725)
御史对世系的监察,需以发达的档案制度为依托。在高丽朝,各种身份上的差别,均被详细记录在案,对当事人及其家族与后代产生决定性影响。与此档案制相应,又有一套相应的法律。以教育领域为例,仁宗朝的“式目都监详定学式”规定:“凡系杂路及工商乐名等贱事者、大小功亲犯嫁者、家道不正者、犯恶逆归乡者、贱乡部曲人等子孙及身犯私罪者,不许入学。”[2](2360)不能入学基本意味着失去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有了这样的档案系统与配套法律,御史们对世系的监察就相对容易了。《高丽史·崔冲传》:“(崔冲)为式目都监使,与内史侍郎王宠之等奏:‘及第李申锡不录氏族,不宜登朝。’”[2](2940)御史可以不录氏族为名,对相关人员不予署经或直接弹劾。
贵族制之所以能长久维持,并非完全依恃武力,更依赖一套在当时被公认具有合理性的文化标准,道德是此种文化标准的重要一维,因而也是御史们监察的主要内容。《高丽史·黄裳传》曰:“御史台劾裳通判密直辛贵妻康氏,败乱风俗,请鞫之。王爱裳骁勇,且以有功,只免官……辛禑时与诸将屡御倭有劳。裳于父忌日娶元氏,元氏亦以世家女夫死未期无媒嫁裳,宪司劾之,请杖流远州。”[2](3940-3941)这已是高丽朝末期的事例,可见一直以来,执行得都相当严格。
如当事人或其祖先被认为有“痕咎”“痕累”,就会对他本人及其后代产生严重影响。庾仲卿为工部尚书庾逵之子,国王令他依门荫出仕,却遭到了以首相李子渊为首之十一人的驳议:“仲卿舅平章李龚,奸兄少卿蒙女,生仲卿母,仲卿不宜齿朝列。”[2](2961)
关于“痕咎”“痕累”等道德上的瑕疵,高丽朝也有一套相应的法律进行规制,在选官、任职、升迁时,必须考察当事人的“家状”与“痕瑕”,负责具体操作的机构正是御史台。御史台在核查相关人员的“家状”与“痕瑕”的真实性后,对不适格者不予署经或径直弹劾。金续命在恭愍初拜监察执义,“与大夫元顗、持平洪元老协心弹纠,执法不阿。凡拜官者有疵累,辄不署告身。”[2](3393)这正是高丽朝贵族社会得以维持的基础,因而也是御史们行使监察权的主要内容。
三、任职条件的变异
贵族化的演化趋势使高丽朝对御史任职条件的设定亦与唐代有重大差异。在唐代,对御史的首要要求是“有搏击器”,高丽朝却是“先威望后博击”:
台官,当以威望为先,弹劾为次。何则?有威望者,虽终日不言而人自詟服。无威望者,虽日露百章而人益不畏。盖刚毅之志,骨鲠之操,素不熟于人心,徒挟博击之权,欲以震肃群臣,清正中外,则恐纪纲未振而怨谤先兴也。[3](392)
成文法上的制度不是高丽朝御史权威的主要来源,所谓“虽日露百章而人益不畏”,他们的权威主要来自“熟于人心”的非制度性因素,正是这些才使人们发自内心地对他们“畏”与“服”。质言之,御史们的权威乃基于社会结构本身,及由此决定之由他们自身身份而来的社会与文化权力。《□ 东辅墓志》称:“□ 居□□□监察御史。公素有威望,及乘騐指顾,肃然□□霜威,人多胆落。”[8](934)御史们在履职时对平素“威望”的依赖,是一个被各种史料证明的事实。《崔梓墓志铭》载:
公讳梓,字大用,其先孔嵒县人也。曾祖厚累,赠太子少师;祖頴累,赠太子大师;父翥,守光禄大夫刑部尚书。世袭衣冠,其来尚矣……授大府注簿权知监察御史,阅数月,除权即真……仁考闻而嘉之,擢拜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处于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为之震恐三载,于是加尚书刑部郞中……公天资刚正,清俭寡欲,特立独行,无朋党之交,自小官至宰相,不营第宅。[4](700-702)
任御史者如不具备此类社会与文化的资本与权力,徒欲依恃制度,不仅难以履职,更不可能彰显其“刚毅之志,骨鲠之操”。总之,“威望”与“搏击”之辨,从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唐与高丽对御史定位的差别,实质体现的是两国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权力格局。
在唐代,御史是皇帝的爪牙与耳目,只需搏击,他们的“威望”乃由皇权所赋予,故“清苦介直”“敝服羸马”为他们的基本形象,所谓“御史多以清苦介直获进,居常敝服羸马,至于殿庭”。[9](693)这类符号与仪式性行为,彰显的是御史们无特殊利益,完全以“天下”(实质为皇权)之利益为依归的事实,在与官僚群体拉开距离的同时,又缩短了与皇权之间的距离。
在高丽朝,御史的权威主要来自结构性的社会与文化资源,与他们自己的身份及文化与道德上的优势密切相关。他们是执政之贵族集团道德上的标杆。对御史们“威望”的要求,又具体体现于对任职条件的严苛设定。郑道传云:“至若台谏、监司,当重风采而尚气节。风采重则人敬,气节尚则人畏。人知敬畏则权奸之心沮,而挠法乱政之萌绝矣。”[3](410)在行为举止、气质、气节等方面有缺陷者,均不能任台谏官。李需“善谐诙戏谑,以故不得除台谏”。[2](3136)李希老“性躁急,历仕中外无成”,被认为“不宜风宪”。[2](184)在道德上有瑕疵者更不得任御史,裴景诚“取倡女为妻”,被任命为知御史台事,谏官上言:“风宪尤非所宜”,且“论执不已”,仁宗只好改任他为“知吏部事”。[2](514)职是之故,御史们权重势高,地位显赫。朝鲜太宗三年(1403)二月,司谏院上疏云:“故前朝盛时,台谏胥徒,人莫敢挫;居是官者,争相励节。”[10]
对于御史履职的风采,社会评价正面积极。《金冲墓志》云:“公讳冲……至戊戌年擢丙第,不经外寄,直就禄仕……除监察御史……自谏官出守全州……性资高爽,知时险艰,权不锋锐,从容世途,扬历清显,不曰贤哉。”[8](949-950)《张允文墓志》云:“公讳允文……迁监察御史,奉公竭节,人不敢非义相干。”[8](947-948)王朝亦给予御史们以相应的礼遇。宣宗十年(1093)六月判:
文武官职事四品以下、散官三品以下于中丞,职事五品以下、散官四品以下于杂端、侍御,职事六品以下、常参以上、散官五品以下于殿中侍御、监察御史,皆避马。若吏部侍郎、尚书左右丞、给舍,既准诸曹三品,且以侍臣在公侯之上,与中丞马上相揖。知制诰亦非常例,一从官品,马上相揖。郎舍补遗勿论官品,与杂端以上并马上相揖。若大夫,则除宰臣、枢密、左右仆射、近臣外,并皆避马。[2](2662-2663)
据《高丽史·百官志》记载,高丽朝前期,御史中丞为从四品,御史杂端与侍御史均为从五品,殿中侍御史为正六品,监察御史为从六品。也就是说,在制度上,其他部门的官员,要对同品或低一品的御史避马致敬。另外还有其他非制度性惯例,“台官虽有罪,当罢台后就狱”[2](2852)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环境下,“除授之际,动兼台谏”[4](651)成为莫大荣耀,郑道传甚至认为“御史之荣”要“过于宰相”,是高丽时代最尊荣的职位。[3](392-393)
不过,“重风采而尚气节”仍只道出了对台官要求的一面,而未指出对台官要求的另一面,即对他们世系与身份的要求——出生卑贱者原则上不能任台谏官。历史上,虽间或有出身低微者任御史的事例,但这些人多有杰出才能且立有军功,只是例外。如康拯,“家世微……为吏役,十年……与女真战,累有功。肃宗初,除监察御史。”[2](3012-3013)许载“由刀笔吏起,积劳出调铁州防御判官……女真来攻,载与兵马副使李冠珍等固守数月,城几陷,励士卒,一夜更筑重城以拒之,虏乃退。以功拜监察御史”。[2](3047)
在武人执政时期,既有制度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出身低微者任御史的情况多了起来,但并不被认可。武人政权首领崔怡“拜私奴之子安硕贞为御史中丞,人皆愤之,至有上疏言者”。[2](3905)宋吉儒“起于卒伍”,因谄事崔沆拜御史中丞,“有司以系贱不署告身”。[2](3719)在高丽朝,妾生子(庶孽)地位低贱,他们或与他们有联姻者亦不得任台官。金汉忠虽为新罗大辅阏智之后,但其妻乃“文宗婢妾之女也,以故虽至达官,不得入台省”。[2](2966)李槢“娶高宗宫妾之女,号国壻……忠烈即位,兼知御史台事,以国婿为宪官,人皆讥之”。[2](3730)朝鲜朝世宗曾问大臣曰:“且妾子承重者,授职无限品,至于赴试,何不通论乎?”右议政权轸答:“登科则通仕路,而至为台谏,故不许赴试。”[11]在高丽时期,此类规定当更为严格,庶孽完全没有任御史的机会。
因御史台为制约王权的贵族性机构,外戚不能任台官。[2](3391)在高丽朝,对僧侣多有限制,僧人之后亦不得任台官。[2](3255-3256)更有甚者,不娶妻者亦不得任台官。高丽朝之所以有此规定,是为了保证台官的妻族无世系与道德上的瑕疵。
由于严格的条件限制,御史多由高门大族中一些非常优秀的人物出任。文宗朝宰相李子渊出身高门庆源李氏,其子有多人任宰相,而这些人在任相之前多数均出任过御史,如李资谅,“睿宗朝,从尹瓘征女真有功,授监察御史”。[2](2946)李资仁“文宗朝登第,累迁侍御史”。[2](2947)被称为“海东孔子”的靖宗朝宰相崔冲,其子孙登宰辅者多达数十人,不少人在任相前亦曾出任御史,如崔思诹在宣宗朝“除御史大夫”,[2](2967)崔惟清,“授侍御史,转御史中丞”。[2](3049-3050)朴龙云发现:“御史台的长官总是任命贵族家门出身者担任,一旦被任命此职,日后就会逐渐成为宰相乃至首相。”[12](132)他还指出,台谏成为“贵族的重要仕路。其中的绝大多数均为名门贵族出身”,“台谏制是贵族社会构造内的一种制度性存在”。[12](148)在贵族制的整体环境中,作为贵族阶层中的佼佼者,御史具有世系、才能与德行各方面的优势,他们日后升任宰相毋宁说是一种必然。
四、司法权的变异
谏官化与贵族化还使高丽朝御史的司法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唐代,御史台主要负责审理皇帝交付的“诏狱”,审理后径行上奏皇帝,由皇帝做出最终裁断,——“凡有制敕付台推者,则按其实状以奏”。如御史台所推为“寻常之狱”,则要受正常司法程序的制约,所谓“若寻常之狱,推讫,断于大理”,[6](379-380)经常出现“又案事入法,多为大理所反”[13](660)的情形。质言之,对普通案件,唐代的御史台只有审讯权,而无定罪与量刑权。
高丽朝御史的司法权较唐代要大得多,不仅拥有审讯权,而且拥有定罪与量刑权。史料中相关的案例不少。例如,肃宗六年(1101)正月,“注簿李景泽妻金氏欲杀夫之继母,阴使婢置毒于食以进,母知之,以告御史台。金不服,御史台请更鞫问。王曰:‘犯状已白,宜即论决。’以金先朝外戚,减死,流安山县。景泽死狱中。”[2](2687)
分析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御史台首先有接受诉状的权力;接下来,御史台又有审讯的权力;审讯结束后,也非如唐代那样交给大理寺,而是直接定罪量刑。高丽朝御史台取得了包括逮捕、审判和执行等整个司法链条中几乎所有权力在内的完整司法权,这与它在高丽朝官制中的地位及同时制约王权与官僚机构双重属性的特点相符。
正因如此,高丽朝御史台不再如唐代那样仅是一司法监察机构,而是一个自成一体、独立运作的单独司法机构。从这个角度看,它与王朝作为专职司法机构的刑部,几无区别。河允源被擢为大司宪(御史大夫)后,书“知非误断,皇天降罚”八字于旌,“每赴台必挂之,然后视事”。[2](3433)巨大的权力给御史以相应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对王朝的司法几乎具有决定性影响,高丽人常将御史台与刑部(典法司)相提并论。恭愍王上书元顺帝:“小邦有监察司(御史台)、典法司掌刑听讼,纠正非理。”[2](1211-1212)辛禑王也在下教中说:“刑法,圣人所恤……仰都评议使申敕司宪府(御史台)、典法司、都巡问、按廉使,详究情法,毋用律外之刑。”[2](2711-2712)
但御史台和刑部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机构,它们的区别何在?在唐代,御史台处理的司法案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侵害皇权的案件,特别是谋反、谋逆案件:一是官员们贪赃枉法的案件。在高丽朝,御史的贵族化使其监察范围扩及到了道德与世系的范围,即所谓“矫正风俗”[2](2416)。
“风俗”案件由御史台专属管辖——“本朝之制,都堂总百揆,颁号令;宪司察百官,纠风俗;典法都官辨曲直,决狱讼,其职也”。[2](2680)对“风俗”案件的专属管辖是高丽朝御史台在司法职能上与唐制的重大差异。
尽管高丽人对何为“风俗”犯罪无明确规定,但对其所指,时人应心知肚明。从现存史料反映的情况看,风俗犯罪首先指关涉纲常伦理的犯罪。祥正有子濡、琡、璿、琇、贤等五人,“以濡不孝,告监察司鞫之”。[2](3300-3301)崔云海妻权氏“性妒悍,在广州妒伤云海面,裂其衣,折良弓,拔剑刺马击犬毙。又追云海欲击之,云海走免。即去之,然犹未绝,嫁永兴君环,门下府牒宪司鞫之”。[2](3517)奴婢犯主的案件亦属伦理犯罪,也由御史台管辖。《高丽史·明宗世家》载:
少监王元之婢壻,私奴平亮,灭元之家。丙辰,流平亮于远岛。平亮,平章事金永宽家奴也,居见州,务农致富……其妻乃元之家婢也……人皆痛愤。至是,御史台捕鞫,流平亮,罢柔进、禹锡官。[2](633)
风俗案件中的另一大类为性犯罪。性犯罪不仅会败乱贵族家门的血统,而且也会降低贵族集团的整体声誉,威胁到了贵族制本身的存立,是御史台重点打击的对象。对于犯有此类罪行的当事人,御史台可直接抓捕。元宗九年(1268)二月,“将军周瑄通其叔父周永妻大氏,事觉,御史台执大氏鞫之,死于狱中,遂斩瑄。”[2](817-818)忠肃王十六年(1329)九月,“前忠州牧使金用卿从沈王留于元,其妻私义女壻别将王之祐,监察司鞫问,俱服。”[2](1122)
由于御史台的这种专属管辖权,对此类犯罪,当事人必须向御史台而非刑部告发。《高丽史·金镛传》:“判密直辛贵贬在外,妻康氏独居,淫秽无忌,大臣多私之,镛亦通焉。贵母告御史台鞫之。”[2](3958)御史台审理后,可直接判决并执行。辛禑三年六月,“野城君金宝一妾朴与宝一适孙金孜争田,诬告孜奸其妹。宪府具朴罪,缢杀之。”[2](4011)《高丽史·李承老传》:“承老尝私妻弟生子,诈称遗弃儿养之。承老妻恐事觉污家声,不形言色者二十余年,虽亲近未之知也。监察大夫金汉贵执承老妻及弟讯之,皆服。流承老于中牟,籍其家,以妻弟为承老所暴,免之。”[2](3490)
性犯罪在贵族社会虽关系重大,但对此类犯罪的揭发,御史台实行的却是与其行使弹劾权一样的方式,即“风闻推劾”——不需切实的证据,即可对当事人进行逮捕与审讯,造成了很大的弊害。这种状况只有放在贵族制的背景下才可理解。贵族集团要想长久稳定地居于特权地位,必须有合理性上的支持。这种合理性,在漫长的和平时期,不能主要依靠暴力,而要使被治者发自内心地认同。显然,只有文化与道德上的优势与血缘上的纯正,才能发挥这种功效,对风俗犯罪的严厉打击,目的就在于此。
五、结语
基于本土的结构、文化等固有资源的各种实质性权力,如何通过移入的外国制度来实现,是本文探究的重点。唐代,贵族制已趋没落,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官僚体制内部的平衡与制约为主,对皇权几无刚性的制约性安排。高丽朝则是一个王权相对低落的贵族制社会,权力以王权与贵族权之间的制约为主。在系统性移植唐制之前,贵族阶层以实际拥有的社会与文化权力为基础获得政治地位,参与政治运作,其权力多以边界模糊的惯例而存在。王权之所以要系统性地移植唐代制度,制约乃至消解贵族势力的这些弥散性权力是其初衷之一,可结果却南辕北辙,《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八“人物”条就云:“仕于国者,惟贵臣以族望相高……仰稽本朝官制,而以开元礼参之,然而名实不称,清浊混淆,徒为虚文耳。”[14](29)中国制度在半岛发生了重大变异,御史制度是其一。
从现存史料看,高丽朝御史的绝大多数权力均为有法可依的制度性权力。这些以律令为据的成文化权力非一次性取得,多数在成宗创法立制时应不存在,而是在之后不断的权力博弈与制度演化过程中,渐次从既有社会与文化权力中抽取而出,进而被制度化、成文化。制度的大移植沦为制度的大变异,朝鲜半岛深层的社会结构为其提供了基本动力。简言之,等级身份制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贵族阶层拥有实质的足以制约王权的全方位社会与文化权力,这种权力在王权系统引进中国制度的过程中,起初虽被压制,之后却依托并改造外来制度,使它们成为本来以非制度形式存在的实质性权力的出口。
高丽朝御史制度维持了唐制的外形,实质上却不断向反方向变异。复请权、驳执权、署经权、进谏权、论政权、各种专属司法权等权力的取得,及它们的体系化与运作的完备化,又使御史台演变成与宰相机构并列的贵族性机构,成为王朝权力体系中的第三极。由结构而来的制度化权力,反过来又强化了结构本身。这突出体现在高丽朝御史对官员监察内容(对世系与道德的监察)的设定及对关于伦理纲常与性犯罪专属司法权的取得上。御史权力的运作,使贵族体制得以自我完善,贵族政治一步步走向成熟,有力地促进了王朝稳定局面的形成与维持。
社会性权力的成文化与制度化,必然是一个过程。尽管由于史料缺略,对这一过程我们已无法准确描述,但对其结果的大致呈现,仍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从原初的意义上讲,不是制度创造了权力,而是权力发现了制度。在制度移植的场景中,便是利用与变异制度。制度为权力创造了出口,在使权力规范化的同时,也使权力离不开制度。制度移植的根本意义不再是形塑社会,而是既有权力的细分化、规范化、合理化。也就是说,变异才是制度移植的根本价值。这让我们思考制度移植的初衷与其最终效果之间的背反关系。这种背反尽管是历史上的常态,可由于它通常总要在漫长的过程之后才能呈现,而这种过程导致的记忆消失与环节缺损,使身处制度框架中的当事者将之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既成事实,难以形成对制度本身的反思。加上在既成制度上附加了多重利害关系,变异的制度愈发凝固,外来制度就这样“本土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