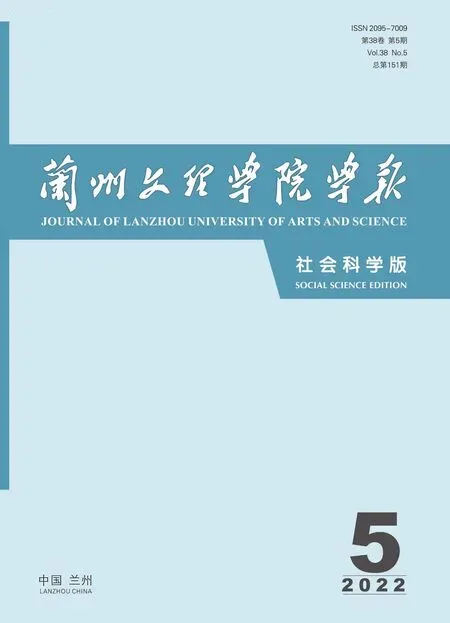西北当代民谣中的乡愁书写
2022-03-24杨瑞峰,杨潇
杨 瑞 峰,杨 潇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新千年伊始,在中国流行音乐的既有版图中,民谣音乐以蓬勃之姿迅猛发展,在渐趋分裂、碎片、多元的当代流行文化谱系中逐渐占据了一席显位。作为一桩文化事件,一股空前的文化潮流,中国当代民谣音乐的繁荣,渐次在专业者与业余者、官方与民间等多个主体层面得到了确认。如果说20世纪终结之际一直延续至今的各类冠以“民谣”之名的大型音乐演出活动以及国内各大音乐节、各类音乐综艺节目中民谣歌手的频频出场意味着音乐行业对民谣这一相比新近的音乐类型的重视与专业认可,那么,2020年先后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频道制作、播出的民谣音乐人专题纪录片《踏歌行》与爱奇艺纪录片频道播出的独立音乐系列纪录片《我行我乐》中对民谣乐队野孩子的“专题播报”无疑象征着民谣音乐艺术声名的进一步提高与巩固。
或许是现代化进程的洪流中,“白衣飘飘的年代”注定短暂,诗意的怀想无法与物质洪流裹挟下现实的逼仄感相抗衡,在“接过摇滚的枪”之后,民谣音乐却无力(无意)继承摇滚声嘶力竭式的、强有力的现实批判精神,转而沉浸于浓郁的怀旧氛围中,以纤伤明净而又简约质朴的诗性气质纾解现代焦虑。更有意味的是,怀旧作为民谣音乐的情感基调为一大批西部民谣音乐人的隆重登场提供了前提: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经济的欠发达与文化资源的丰富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使得西部似乎本身更具滋生怀旧情调的潜力。与此同时,以野孩子为代表的一批西北民谣歌手大多起首于小城镇,但又成名于北京等发达城市或丽江一类的文青聚集地,“迁居”的体验使得他们必然在两种或多种不同文化的反差中经历一种“主体性的断裂”:他们在现实生存境遇中早已脱离了故乡,但与此同时,故乡的文化形式与生存模式又深深镌刻于他们内心的情感隐秘处,并内在地塑造着他们的艺术观念,规约着他们的创作风格,从而使得乡愁书写成了西北民谣音乐人的“集体无意识”。
一、主体性的断裂:乡愁的涵育语境
与具有人类共通性的思乡之情不同,作为一个术语的“乡愁”,其诞生历史相对晚近。在宏观历史文化背景层面来看,乡愁起初作为一个医学术语为人所知,尔后逐渐融入了文化研究的学术脉络。但时至今日,乡愁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思乡病”或是某种“返回家园”的精神欲念,相反,作为一种“蔓延的温情”,乡愁早已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现实”[1]。饶有意味的是,似乎是对乡愁早期病理学内涵的一脉相传或另类改写,在乡愁作为一种文化现实寄宿于当代生活的各个角落时,它依然毫无违和地保留了精神空洞、情感疏离、不断寻觅而又不知情归何处(乡关何处)的情绪症候,而这一症候也构成了解码乡愁问题最直接的突破口。
作为音乐创作文化底景的乡愁,很难找到一个确切、明晰且唯一的历史肇端,但台湾音乐人李双泽通过改编蒋勋的诗作,创作于1977年的《少年中国》可视作一次乡愁之情的集中爆破,其中“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几句歌词,若被置入家国情怀的脉络中,结合此曲曾用于纪念香港回归的特殊用途来看,颇具慨当以慷的韵味。显然,此处的乡愁指向对故乡故国的深情回望,也点染着上世纪末期台湾风云激荡的时代底色,因此,乡愁的个体性被悬置,隐匿于家国叙事的大框架中不见踪影。与《少年中国》极力渲染的“大时代乡愁”不同,当乡愁作为西北民谣音乐人的内在艺术共识开始全面显影,其早期背负的时代使命感已明显开始让位于个人情感的生发,至此,乡愁的涵育语境与发生机制也悄无声息而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变化。
在理论层面,对乡愁问题的理解首先牵涉到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对此,美国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曾颇有见地地指出:“乡愁的传播不仅和空间的位移,而且也和变化的时间概念有关。乡愁乃是一种历史的心绪,我们更可以探索一番它的历史的,而不是心理学的发生过程。”[2]黄敏则从构词法的角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从构词法来看,乡愁是个偏正结构,‘乡’限定了‘愁’的场所来源(空间维度),‘愁’则是由‘乡’的记忆(时间维度)所引发的情感。”[3]颇具意味的是,尽管此类说辞十分精准地捕捉到了学理意义上乡愁滋生的横纵机制,因而自带普遍性阐释效力,但却依然未能网罗全部艺术实践,至少在当代西北民谣音乐创作中,乡愁问题的显影自有其独特性,一言以蔽之,与相对宏观的时空观相比,较为微观的“主体性断裂”在阐释西北当代民谣音乐中的乡愁书写时,往往更能逼近问题核心。这既与音乐实践的独特性相关,也与西部音乐人的独特性相关。一方面,音乐的创作,往往并不以对社会生活的机械反应为初衷,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对此早有阐述,他说:“音乐是真实世界可信的隐喻,它既不是自给自足的活动,也不是经济基础框架的机械式指标。它是先趋者,因为社会在改变之前,变动已先铭刻于噪音之中。”[4]此外,音乐创作者对乡愁的书写往往出于自发的内在情感驱动,他们并非乡愁理论同调的信徒,因此,其作品中乡愁意识的呈现大多基于一种由个体性,特殊性而触及理论普遍性的姿态。
在西北民谣音乐这一特殊的当代文化场域中,乡愁赖以滋生的时间隔膜与空间区隔被悄然糅合于个人情感的割裂之中,于是,焦虑于自我成长的历史经验的丧失和寄托着田园乌托邦梦想的故乡的难以再度叩访构成了将一众音乐人引入乡愁叙事的幽微门径。在最为浅在的层面上,西北民谣音乐中的乡愁意识,经由一系列以离乡、归乡为题旨的语词得以显现。新疆籍民谣歌手吴俊德的作品即为典型例证。在《旅行者》《七月的天空》《玛尼干戈》《旅途》《梦幻列车》等多首作品中,“旅行”“离开”“回来”“故乡”“都市”是高频词,其间标识的,无疑是肉身与精神双重意义上在故乡与他乡之间不断穿梭但又“居无定所”的失重感。在故乡与他乡(都市)的两相对比中,吴俊德不出所料地呼应了乡愁叙事的古旧传统,透露出将故乡美化的明晰愿望。在他眼中,故乡美丽、静谧,拥有安抚人心的力量:“幽静的山野/满眼的鲜花/这是风的三月/轻抚着大地。”(《旅行者》)正因如此,离乡则意味着走向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这个世界冰冷、压抑,承载着无数的孤独、失落与不确定感:“……因为我冰冷的心已失去了温暖/可是阳光下七月的都市/你为什么伤痕累累/是因为这残缺的世界将你伤害/我想离开/我想离开你……”(《七月的天空》)故乡与他乡、经验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对比及由此激发的不同情感的相互碰撞,不仅是“身体移民”的结果,更是“精神移民”的结果。在此情境中,时间的推移与空间的腾挪作为一个潜在的线索,将乡愁的书写串联在了主体情感的断裂之中,这份情感断裂既是对现实语境中无法返回故乡的哀叹,也是返乡情感在精神层面的含蓄表达。
对故乡、过往的深情怀恋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实际是音乐人对成功“逃离故乡”之后的现实生存境遇不满,因而又在精神层面渴望“返归故乡”这种矛盾心态的心理映射。纵览西北民谣,其中充斥着大量具有鲜明“地理文化”意识或怀乡倾向的曲目,马条(新疆)的《塞外》《敕勒川》《克拉玛依》,杭盖乐队(内蒙古)的《乌兰巴托之夜》《丁吉图湾》《故乡山峰》,蒋明(陕西)的《长安》,马飞(陕西)的《长安县》《回西安》,黑撒乐队(陕西)的《西安事变》,苏阳(宁夏)的《河水向南流》,赵牧阳(宁夏)的《流浪》,王峥嵘(宁夏)的《我在吴忠喝早茶》,野孩子(甘肃)的《黄河谣》《走了》《离开》《眼望着北方》,低苦艾(甘肃)的《兰州兰州》《守望者》,张尕怂(甘肃)的《姐姐》《无农村不城市》等大量作品,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隐晦的寄托着浓郁的思乡之情,并赋予了这份思乡之情得以产生的现实逻辑:“我走过了城市,我迷失了方向”(野孩子《眼望着北方》)。
二、从集体无意识到个人体验:乡愁的形态变异
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或学术研究中重要的公共话语而广获关注的“乡愁”(怀旧),通常被指认为一种集体文化现象而非个人情感。德国学者托比亚斯·贝克通过分析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怀旧文本,指出其共性之一即“认为怀旧不是一种个人情感,而是一种集体文化现象(或者至少他们对怀旧的个人心理模式不感兴趣),一种‘可识别和独特的公众情绪’,简单说,就是时代精神(zeitgeist)”[5]。的确,自19世纪晚期怀旧问题吸引学术界的研究目光以来,“种种社会及艺术现象都证明了怀旧已不再局限于某个个体成长中的心路历程,也不单单是一种私密性的生命体验,而是超越了个体化的、情感性的、心理范畴的层面,生成为一件社会化的、全民性的集体事件,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文化景观。”[6]而在西北当代民谣音乐中,作为一种集体情感的乡愁被拆解、还原成了极具个体性的情感。至此,乡愁不再是通往集体情感抒发路径的舟车,而是一种因人而异、因地(故乡)而异的情感体验,时代的变迁、世事的迁嬗被高度个体化,从而以一种质询的姿态对既有的乡愁书写与理论研究思维惯性提出了挑战。
乐评人郭小寒在回忆她与甘肃民谣歌手张玮玮一起梳理中国当代民谣发展史时曾颇为感慨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跟他一起,细致地梳理了这段中国民谣的历史,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群人,对于中国的音乐文化意味着什么。在这些人身上,你可以看到当代民谣不是工业化的产物,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异乡人被音乐感召,来北京圆梦,从酒吧翻唱开始逐渐有了‘唱自己的歌’的意识。”[7]此处所说的“这样一个地方”指的是兰州民谣乐队野孩子2001年创立于北京三里屯南街、被称为中国当代民谣“母亲河”的河酒吧,而所谓“唱自己的歌”则借用了上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民歌运动的著名口号。按其原初语境,“唱自己的歌”之所以能够成为台湾地区民歌运动的核心精神表征,成为一众民歌运动发起者的共识,在于它“结合了当时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青年时代的自觉、初初萌芽的乡土意识和不假他求的原创精神”[8],但郭小寒此处所谓“唱自己的歌”,显然指向一种个性意识的觉醒,同时,也精准地凝练出了西北当代民谣音乐对于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安身立命之基础,内心情感之所寄的重新设定。
聚焦于个人情感体验,使得西北当代民谣中的乡愁书写超越了潜藏于人类心灵深处,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谓“生命本能”或荣格的经典术语“集体无意识”那般极具普遍性的意味,使之不再单纯是对于一个安放集体情感的广域生存空间的简单怀想,而是一种对过往的生命经验与生存空间的个人化理解。这种新的理解方式使得乡愁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区分获得了可能性,毫无疑问地,也启发我们对乡愁内涵与乡愁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进一步追问与思考。以往的理论研究中不受重视的乡愁书写的个体化问题,在西北当代民谣音乐中主要落实为一种个人化叙事的鲜明倾向。此处的个人化叙事既包含通过对个人当下生存处境的不满与批判间接凸显过去的美好,也含括将个人情感与回乡的愿景相结合从而在平淡的叙事中寄予浓郁的怀旧冲动,同时,更包含对乡愁个性鲜明的否定性理解。
正如当今人们所熟知的“记住乡愁”“美丽乡愁”等文化建设口号字面明示的那样,乡愁问题最基本的情感导向是将过去美化,从而借助回忆的滤镜功能建构起人类与已逝时光之间美好的情感链接。在此导向下,乡愁叙事的基本策略是对回忆的正面化处理,但在西北当代民谣中,乡愁被赋予了一种客观性,回忆的滤镜功能被悬置,思乡之情不再借助故乡的美好而呈现,故乡的荒凉、孤寂、无生气也不再是阻碍乡愁弥散的因素。新疆民谣歌手马条带有浓郁怀乡色彩的作品为乡愁书写提供了不同的路径。《塞外》虽不无对故乡旧地的客观描摹,但在主要情感取向上依然采取了美化的策略。“落日红霞伏沃野/残阳锁天边/山峦沟壑陇交错/风沙绣乾坤/一壶狂酒伴长歌/不吝山荒芜/春风一夜生青绿/塞外有江南”显然沿袭了古典边塞诗雄奇豪迈的风味,赋予了原本荒凉凄清的塞外壮丽的诗意。而在《克拉玛依》之中,这份雄奇豪迈的诗意被抽离,故土的景致由“光秃秃的山丘”“吝啬的荒草”“道道沟壑”“饥渴的草原”“褶皱的皮囊”“肆虐的残阳”和“狂卷的黄沙”连缀、拼贴而成,没有刻意的粉饰与涂抹,西北边地克拉玛依苍凉悠远的质感被客观呈现,但这并不影响歌手思乡的冲动,因为在他内心的情感隐秘处,他作为克拉玛依“甘甜的泉水喂养的孩子”“风干了骨头的轮廓长成的样子”是不容更改的事实。
在另外一些西北民谣歌手那里,乡愁之情被虚化处理,他们往往通过对当下日常生活的琐屑记录与庸常化叙述来反衬过往的理想主义色彩。新疆歌手洪启的《在外省干活》开端讲述了在湖北打工者的生活场景:“在外省干活/得把乡音改成湖北普通话/多数时别人说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气/四月七日 我手拎一瓶白酒/我模仿失恋的小李探花/在罗湖区打喷嚏咳嗽发烧/飞沫传染了表哥/他舍不得花钱打针吃药/学李白举头望一望明月”。紧接着,歌词讲述了工棚里的辛酸庸碌的集体生活场景:“一间工棚犹似瘦西篱/住着七个省/七八种方言:石头剪刀布/七八瓶白酒 38°43°54°/七八斤乡愁东倒西歪/每张脸养育蚊子七八只/七八瓶白酒38°43°54°/七八斤乡愁东倒西歪/每张脸养育蚊子七八只。”来自七八个省份,操着七八种方言,喝着七八种不同度数白酒的七八个异乡人,因生计所迫聚拢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但却依然持有各自无法与他人共享的乡愁体验。显然,该作品与其说是为某种具有集体共通性的乡愁意绪所统御的文本,毋宁说是一种为乡愁的不可通约性所支配的文本。
在西北当代民谣中,致力于通过讲述个体事件,渲染个人情感从而将乡愁个体化的作品比比皆是。例如,贰佰的《以梦喂马》讲述了王喂马在离乡与归乡之间的情感撕扯;陈鸿宇的《食味》打破了乡愁叙事中更倾向于调动视觉经验营造画面感的常规,通过味觉叙事提醒游子“记住乡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条的《远方》一改各类文本乡愁书写的俗套,剥落了乡愁光鲜亮丽的假面,揭示出了旧时光阴郁的一面:“我不去那条河/旧事情太多/加起来可以冲垮一座城/幽暗的一条街/残灯垂败柳/沮丧的人们终将被抛弃/再重燃一把火/走一趟旧地/去看看从前流淌的忧伤/再抹擦一把泪/喊一嗓远方/让奔腾的河水拍醒我的心跳。”似乎是对昔日海子同名诗作中的著名诗句“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和汪国真的著名诗句“遥远的地方没有风景”的再度改写与诗意承传,旧时光、老地方不再是值得眷恋、值得流连的乌托邦,而是淌着忧伤,滴着泪水,不堪回首的记忆场。此间显影了乡愁书写中一处独特的文化景观:乡愁或许还可被注解为“因乡而愁”或“忆乡即愁”。
三、以出走的方式回望故乡:乡愁的书写策略
饶有兴味之处在于,在以“西部”为题眼的学术研究领域,“西部文学”的飞扬与在场始终使得西部艺术研究显得较为沉寂。然而,在今日中国的文化场域中(尤其是青年文化场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相较于西部文学,民谣音乐在将西部打造为一块精神沃土,继而引领人们将目光投向西部方面似乎发挥了与西部文学不相上下甚至更为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宋冬野在文青群体中名噪一时的《董小姐》以一句“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兰州”引发网友对“何为兰州”的搜索进而带动了兰州烟在各地的畅销因背离“西部”题旨又难以有效考证而显得说服力不足,那么,甘肃籍的野孩子乐队通过河酒吧在北京的创建及其带有浓郁西北特色的音乐展演,确乎于不期然之间更好地践行了“西北文化走出去”的使命。继之而来的,则是一众西北民谣歌手的相继隆重亮相,不断强化着带有浓郁西北特色的民谣音乐将西北艺术嵌入中国当代主流艺术实践中的文化浮桥功效。
对于西北民谣歌手来说,践行本土文化走出去的使命,必然以身体与精神的离场为先决条件,携带着故土文化出走异地,故乡的方言、物象、人情、世况、文化等便不再能以现场亲历者的姿态被讲述,它们杂糅一处,幻化为西北民谣所承载的“想象的乡愁”,凝定于一众民谣歌手的记忆深处。由是也形构出了西北民谣音乐中乡愁书写的基本路径:以方言为重要媒介,通过对西北地域物象的多角度书写,辅之以花儿、秦腔、西北民间小调等传统地域文化元素的加入塑造音乐个性,传达思乡之情。
汉娜·阿伦特广为人知的说法“唯独存在的是母语”曾被法国学者芭芭拉·卡森引入了乡愁理论,借以阐述语言与乡愁建构之间的关系。其核心理念在于强调人类儿时习得的语言必然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显现于人们的深层记忆,而这些记忆很难被复制。[1]91正如阿伦特所揭示的那样,语言的确是体验乡愁的重要触媒,这一说法在西北当代民谣中也得到了恰切的反映。在西北民谣中,西北方言的异质性极大地提高了歌曲的地域辨识度,也充当了辨别西部歌手独特家园感的显要途径。低苦艾的《兰州 兰州》在尾声部分刻意加入了兰州方言,牛肉面馆嘈杂的日常对谈与汽车站的拉客声一道,在歌名之外还原或强化了兰州这座西部城市独有的生气。野孩子鲜少直接用方言歌唱,但正如相关网友在豆瓣、网易云等网络平台中的评论所揭示的那样,他们的歌就像在西北的黄土地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一般,这一结论显然也与他们演唱时自然携带的西北音质有关。而张尕怂更是直言,唯有使用方言才能找到音乐感觉,基于此,他的歌基本全用方言演唱。
除此之外,西北民谣中大量西北物象的刻画与呈现也是显影其乡愁意识的重要路径。在西北五省较为知名的民谣歌手的作品中,黄河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物象,它不仅充当了西北歌手思乡之情得以延宕的精神空间,更以其流动不息的自然态势喻示着他们乡愁意绪的绵延不绝。当这一中华文明的母亲河蜿蜒进西北民谣的框架里,其“千人千面”的“蓄愁”潜能得到了远迈其他物象的发挥。赵牧阳版的《黄河谣》中,黄河、铁桥通过与个人情爱、父母亲情之间的情感链接发挥其承载乡愁的功能,“黄河的水干了”与“我回不去的家”之间构成了生动的互文关系,对故地与已逝时光的哀叹由此得以弥散开来。而在野孩子的《黄河谣》中,永不停留的黄河水作为歌者“即物起兴”的物媒,衬托着乡愁之人平淡、哀婉的思乡之情。此外,吴吞的《喀什的天空》、马条的《敕勒川》、陈鸿宇的《额尔古纳》、杭盖乐队的《北边的芨芨草》、布衣乐队的《羊肉面》等作品,要么通过故乡景象的艺术描摹抒发思乡之情,要么以“芨芨草”“羊肉面”等为起兴之物呈现浓郁的乡愁,使得地域物象的运用成了西北民谣乡愁叙事的显性传统,也遥接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抒情传统,彰显了以质朴见长的西北民谣诗性的一面。
在较为隐秘的层面,西北民谣音乐乡愁意识的生发还通过将花儿、秦腔、地方民间小调等挪用得以实现,这一倾向在野孩子乐队与张尕怂的作品中得到了最为直接的体现。野孩子一方面直接改编了部分西北民歌,其中最典型的是新疆维族民歌《流浪汉》和《青春圆舞曲》,另一方面,在其音乐创作的早期,他们曾沿黄河徒步采风,又时常参加“花儿会”,受此影响,其作品往往呈现出曲调音域宽广,起伏较大等特点,而这正是花儿的重要特质。在其极具代表性的《黄河谣》中,西北花儿的歌唱技巧与音乐风格就得到了鲜明体现。张尕怂亦是如此,其作品中,《梁梁上浪来》《挖虫草》直接挪用、改编自传统花儿曲目,《四季歌》改编自民间社火小调,而网络上大火的《乡里的亲家母》则改编自青海民间小调。此外,去年疫情期间创作的《早知道在家待那么久》曲式源于青海花儿“仓啷啷令”,《穷人歌》中设置了秦腔《拾黄金》片段,以谋取某种表意上的共通性,《尕怂讨媳妇》则部分改编自河州贤孝。诸如此类的民谣作品,通过承袭、改编民间艺术形式,标识了自身明晰可见的西北印迹,也拓展了乡愁书写的渠道与路向。
四、结语
在“故乡”的诗意正逐渐被现代性侵蚀殆尽的今天,西北民谣以其致力于捍卫地域文化特质,在“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处重铸诗意的精神栖居地的文化姿态,将自身打造为一个以乡愁书写为母题的流行文化样本。一众民谣歌者遥接“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中国古典歌诗传统,再启乡音,重唤乡情,力图在引发“离乡者”情感共鸣的同时,也为化解他们因游离于故乡与他乡之间而滋生的多重生存困境提供文化慰藉之径。在此意义上,民谣在青年文化群体中的“小范围”流行,与其有别于其他文化形式、更为直接的精神疗愈功能密切相关。同时,在作为一种构建“怀旧的乌托邦”的有效媒介的意义上,乡愁往往表征着一种无法复得的昔日美好,而这种昔日美好又必然以当下的不堪为对立项,这组隐形的二元对立关系的显影,赋予了乡愁书写批判现实的力量。而当民谣中的乡愁书写作为勾连此在之境与记忆的望乡台之中间媒介时,它又进一步隐秘地呼应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诗学旨趣,于功能指向层面完成了“诗乐一体”这一中国经典文化命题的当代改写。凡此种种,不仅是窥探西北民谣中乡愁书写路径、模式、精神意蕴的密钥,也是解码当代流行文化的关键所在,值得我们不断追寻与叩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