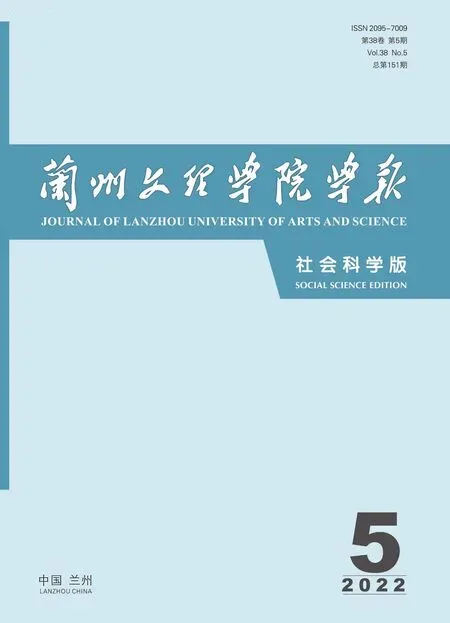现代文明下的民族书写
——以藏族王小忠小说集《五只羊》为例
2022-03-24李捷
李 捷
(西藏民族大学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小说集《五只羊》入选“2020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在此之前,藏族作家王小忠已出版过散文集《黄河源笔记》《车巴河笔记》《静静守望太阳神》和诗歌集《甘南草原》等。就其创作来看,生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他,试图探寻新生代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结合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矛盾冲突。如同次仁罗布、色波等对藏地的民众生活小人物的挖掘,王小忠的小说也在努力尝试着。甘南藏地并非是一个封闭保守之地,也并非神秘化、理想化的小世界。之所以具有独创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书写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反思的现实甘南。
一、家庭内部: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王小忠围绕甘南藏地这片沃土,或讲述藏族姑娘来到汉族家庭,或讲述汉家小伙融入藏区生活,于家庭琐事或生意往来间,流露着汉藏民族之间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信仰观念。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谁厉害》《铁匠的马》《黑木耳》篇目之中。
《谁厉害》[1]中,以孩子加措的视角,于判断“厉害”的标准的变化之中,讲述了藏汉家庭融合中的日常生活琐事。“厉害”的标准伴随着孩子加措的成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父母争吵打架时期,以“谁的拳头硬谁厉害”为标准,此时母亲卡卓草占据了上风,父亲显得怯懦窝囊,加措显得战战兢兢;在家庭谋求物质生活时期,以“谁能赚到钱或做成某事”为标准,此时父亲刘启林占据了上风,他外出干活,家庭的生活物质条件得以改善,母亲由泼辣粗暴变得温柔体贴,村人由揶揄嘲讽变得刮目相看;在家庭面临即将破裂时期,以“谁有担当、不离不弃、能赢得孩子深爱与尊敬”为标准,一是母亲卡卓草为救丈夫刘启林,卖牛羊凑钱、回牧场借钱、挖药材卖钱;二是爷爷刘三志为救儿子刘启林,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甘愿吃苦受累去放羊,放下面子去各家混饭;三是父亲刘启林的重新开始,由土生土长的多瓦村走向宁静祥和的牧场,是重新修好情感的悔过之心,是对妻子、对孩子的深爱之心,是对藏汉融合的包容之心。
至此,从表层看,《谁厉害》讲述了“我”的成长历程,在家暴的环境中,父母打闹动刀,“我”似乎是个幸灾乐祸的、想要分出“谁厉害”的旁观者,性格变得复杂、多疑、敏感,“我”恨父母对自己打骂,恨爷爷更疼爱天亮,恨村人茶余饭后的闲言碎语,但在父亲刘启林出事后,完成了从对家人的不认可到爱与包容;而从深层来看,其背后隐含的是藏汉两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相互融合中所面临的现实物质困境、宗教信仰困境、道德伦理困境,王小忠的小说亦在忧心忡忡地思考着汉藏家庭融合的启蒙、人性的关怀、精神的救赎,小说结尾处被砍伤后的刘启林走向牧场、身后一片通明,预示着一个充满温暖、包容、希望的家庭的新开始,汉藏两种习俗观念也在碰撞中渐趋融合。
《铁匠的马》[2]讲述的是汉家男子来到藏族村落相融合的故事,展现了藏族儿子道尔吉对于汉家男子六指儿“是否是一家人”的深切追问和态度转变。赛马节前,醉酒后的道尔吉对于汉家男子不认可、不接纳,不明白丧偶的母亲周毛塔为何让汉家男子六指儿借住,在村人的评价话语下,对六指儿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强烈质疑。在道尔吉真正成为驰骋马场的骑手后,他懂得了作为男人的勇毅、担当、包容,实现了真正的成长。而六指儿的吃苦耐劳、技艺精湛赢得了藏族村民们的尊重,善良、老实、本分赢得了周毛塔的接纳和爱意,一如既往的无私之爱赢得了道尔吉的真正理解。
汉藏融合之家中,有生活习俗的矛盾、有文化信仰的矛盾、有身份认同的矛盾,但最终能够走向融合,靠的是什么?王小忠将答案融于平实的叙述,是善良踏实的彼此信任、是生活情感的深度融合、是民族一家亲的归属认同。
而在《黑木耳》[3]中的汉藏之家融合则更为曲折艰难。小说讲述了“我”与藏族姑娘一家的生活琐事,有“撞倒为煨桑炉”“偷了献给神山的牛”等诸多误解为矛盾冲突。小说以双线并行的方式,既讲述了“我”种植黑木耳的曲折过程,又讲述了汉族男子“我”爱上藏族姑娘后的一波三折,最终杨卓玛怀上了孩子。作者以“黑木耳”作为喻体,一方面象征着“我”在现代文明技术的影响下,对于新的致富道路的探索;另一方面象征着新的生命希望和汉藏一家融合的微观景象。最终,汉族的父亲和藏族的父亲坐在了一起,放下一切,预示着两种民族文化的彼此包容、谅解、渐趋融合。
王小忠以日常汉藏家庭的故事为切入点,展现了甘南藏地汉藏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正如巴赫金所言:“在文化领域内,外在性是理解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异种文化只有在他种文化的眼中,才得以更充分和更深刻地揭示自己……在两种文化发生对话和相遇的情况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丰富起来。”[4]两种民族文化濡染下的家庭关系是民族共处关系的缩影,民族家庭关系的融洽与否,影响着民族间的团结稳定和生命延续。藏汉融合后,孩子的成长问题,亦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比如《铁匠的马》中孩子的价值判断,《谁厉害》中孩子的畸形成长。当然,伴随着理解与温暖,民族家庭的起伏冲突,都最终走向了“和而不同”的新起点。
二、藏地行业:传统技艺的传承与隐痛
小说中除了展现汉藏民族文化交融的曲折之外,还围绕铁匠、银匠、木匠、皮匠等小人物,讲述了他们在传承民间技艺过程中的艰难性,尤其是老一代工匠的遭遇和坚守,对行业衰落的留恋和叹惋。而作者在讲述传统技艺的传承中,更多地注入了情感、价值、伦理等的思考。
《羊皮围裙》[5]最能展现工匠技艺传承的艰难,讲述了老银匠阿爸寻找手艺传承者的故事。南木卡粗心贪婪、心术不正,反而向传他手艺的老银匠要工钱;道智外表老实,内心却觊觎美色,重利忘义,还将老银匠所珍藏的佛像偷走。而悟性极高的小银匠,自带技艺,并能与老银匠切磋打制首饰的功法,原本最有希望成为继承人。但小银匠却移情别恋、心有杂念、追逐名利,离开城镇转向城市,甚至妄图以法律诉讼去占有老银匠的铺面和房屋,丢失了本分与忠诚。
从表面上看,故事讲述的是老银匠寻找徒弟的曲折过程和失败问题;而从深层来看,在甘南这个特殊地域环境的转换期,老一代工匠精神艰难地存在着、坚守着,在社会转型中其善良的品格和价值便愈发可贵,就像老银匠打造的器物一样坚实和有质感。然而,传统技艺的衰微,在现代工艺面前似乎已是大势所趋,这不是老银匠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行业的共性之思。
《谁厉害》中的爷爷刘三志,作为一个曾经很受尊敬的木匠,同样也面临着技艺难以传承的怅惘。故事中,老一代木匠和徒弟们形成了鲜明对比,爷爷认为“木匠永远是木匠”,其手艺、地位、匠心精神是无法替代的;而其徒弟们没有传承下来,早已改换了门户,其儿子刘启林游手好闲,亦无法成为传人。文中借老一代匠人的感慨,于平实的叙述中表达着对传统技艺渐失的回眸与哀婉。
《缸里的羊皮》[6]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见证了传统手工技艺和现代机器技术之间的冲突。皮匠楞木代拉、揉、搓、铲的裁制皮衣过程,展现了手艺人精益求精的制作过程。他对机器技术的态度,从质疑其性能、到惊叹其产量、再到怨恨其夺走了自己好匠人的名声。手艺人楞木代和机器尝试者班玛次力,二人的成功合作过程,是两种文明的相碰撞融合的过程。离开机器制作,楞木代用传统技艺所作的皮子,数量上无法高产;离开传统泡皮的手艺,班玛次力操作机器所制的皮子,质量上无法过关。
王小忠写的是草原文明进程中的悲剧,自私的班玛次力不愿将机器使用方法传给楞木代,而保守的楞木代也不愿去学习新技术;同时,作者反思着造成悲剧的根源,面对社会的变迁,愚昧保守、自私自利均不可行,猜疑仇恨必须摒弃,两种技术的结合、两种文明的交融乃是前行的途径。
《铁匠的马》讲述的是铁匠钉马掌的故事,描写了打铁的过程以及他想要将手艺传承下去的愿望。铁匠是受人尊敬的手艺人,虽然赚来的钱用来买炭,但六指儿从不因赚钱的多少衡量铁匠的价值。这便是老一代的匠心精神,追求的是坚守与专注、是精益求精、是求真求善。
这样的匠心精神,在现代化文明的浪潮中,却并没有得到尊重与认可。张隆溪在《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中讲道:“文化和人的生命一样,也有生老病死的变化,其中有些成分也会随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推移而过时乃至死亡。”[7]王小忠以温和的笔触,不仅详尽地描写了老一代工匠们的手工艺制作过程和美好的品格,而且思考着在现代技术带来便利、乡村走向城镇化的道路上,我们迷失的是什么?造成老一代工匠的哀婉或悲剧又是什么?虽然文章中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却引发了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深思,它们包括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的矛盾、人性坚守与时代变迁的矛盾,这并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转型变迁下,一个行业、一个时代、一个地域无法避免的阵痛,是传统技艺或文化的断流,是更为严峻的民族之痛。
三、人性问题:价值观念的震荡与沉思
王小忠在探讨匠心精神渐行渐远的同时,并没有一味地将问题归结于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墨守成规的匠人,而是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人性问题,寄寓了更多的思考。作者对急于求成的草原牧民、利益熏心的寺院长老、见利忘义的生意朋友这一类人的价值观念转变,进行了沉思。
《虚劳》[8]讲述的是不枯积德行医最终身患虚劳的故事。孝顺的不枯,为完成母亲意愿和缓解母亲病痛,虔诚诵经、自学行医、猫城寻药,偶然治好张老板病痛而带来物质财富,却被智慧长老当作摇钱树而身患虚劳,走向还俗。这是天伦寺逐渐沦为名利场、走向“虚劳”的过程。大师们在寺门附近开杂货铺、高价变卖香火、算命卜卦,僧人们以获得财富多少来衡量价值大小,充满了俗气和贪欲,价值观也在日趋走向异化。由此,不枯还俗离去,既是自我个体的如释重负、精神解脱,也是以天伦寺为代表的“名利场”的放弃治疗、无药可救。而不枯母亲的善良虔诚、心无杂念与智慧长老的伪善贪心、满眼功利形成了强烈对比,母亲临终之前要捐赠扩建寺院的香火钱,而智慧长老将筹建寺院的钱占为己有,扬长而去。
《夜如铅》[9]是桑吉以现实和回忆穿梭的形式,讲述了自己被儿时同学杨继荣所骗的故事。小说开头以顺叙的形式,讲述了一无所有的桑吉经不住诱惑,迈入了供风花雪月的夜店,而桑吉却得到了风尘女子的帮助。接着以倒叙的形式,讲述了桑吉贩卖虫草时,被“女教师”和“小伙伴”联手欺骗的过程。既形成了桑吉形象的前后呼应,又形成了“风尘女子”和“人民教师”的善恶对比。表面上是“女教师”巧设圈套骗取桑吉的信任和钱财;实际上是桑吉自身也无法抗拒诱惑、人性中的贪欲使其掉入陷阱。同时,小说也在隐晦地传达着,看似善良老实的身份和形象,未必是值得信赖之人,亦有其恶毒狠辣的一面;而身处恶劣环境、看似身份低劣的人,人性也有其闪耀的地方。小说以“夜如铅”为标题隐喻,明写的是夜色之中,回忆生意场上虫草被灌入铅粉的骗局;暗喻的是漫漫人生,人性险恶比夜色更为黑暗。小说并没有一味地书写人性阴暗,当桑吉得知骗局是作为同学的“合伙人”设计,在看到其因车祸而失明,桑吉把想要报仇的刀子扔掉的举动,也是作者以宽容的姿态,对于恶的行为给予温情的处理。
《凶手》[10]讲的是寻找凶手和真相,实则是对于人性的思考,对善与恶发出灵魂的追问。兽医鲁伟探索人工种植牛黄,惨遭陷害,被误以为是屠牛取胆的凶手,多年来苦苦查找凶手和真相,而凶手竟是关心他的老领导和有着生死之交的朋友。小说着重书写了人性的复杂,人人都称赞的好人,实则未必如真,“凶手”才保加和四个大汉曾经救过自己,但也是嫁祸自己的凶手。鲁伟将举报信撕碎,扔进黄河,意味着他对“凶手”选择了宽容。
《金手指》[11]讲述了拉加才让走出草原、转向生意的探索。主人公感到老老实实放牧太苦,想要急于转向小城安逸生活。对于城市的陌生感和新奇感、对于足浴的全新体验、对于西服领带的新认识,让他难以抵挡城市生活的诱惑。在体验了一夜的足浴之后,便盲目卖掉牛羊,凑钱去找足浴技师合作干生意。足浴店出事,死亡案件扑朔迷离,“金手指”离奇消失,使拉加才让渴望快速赚钱的梦想破灭,并重新审视着当老板一事。他认识到了没有什么“金手指”的捷径,真正能靠得上的是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草原也一样可以当老板。
正如阿来所言:“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着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12]甘南作家王小忠亦是如此,他在描写甘南游牧生活转向现代化城镇的过程中,集中体现了小人物人性的变化,但是作者结尾处的笔墨,最终指向的是温暖的场景,对于恶势力的行为,在不遗余力鞭挞的同时,隐含着同情与悲悯,而更多的是包容与宽恕。
王小忠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生活在甘南大地的弱者,他们或积极探寻着改变生活现状,或坚守着人性中最珍贵的情感。城市现代文明的入侵下,外来文化元素的巨大诱惑与乡村人物自身的欲望渴求,成为甘南乡村人物悲剧的内在引力。善与恶的交织、美与丑的对照,小人物的命运都难逃现代文明的浪潮。汪晖曾提到,“思想、观念和命题不仅是某种语境的产物,它们也是历史变化或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13]。在新一代人物中,秉持人性美好的坚守,方是现代化语境下不可或缺的价值取向和内在力量。现代化道路上,固然有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但在冲突中又何尝不是一种时代进步的推动力量。
四、结语
总的来看,作为甘南藏地作家的王小忠,以更为自觉的甘南文化先行者,忧思着民族文化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探寻着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和民族融合的重要性。王小忠的创作自觉,不是对甘南藏地包罗万象的审美展现,而是剖出一个切面,引导读者去体会汉藏家庭融合过程中的曲折历程、去审视老一代工匠传统手工艺的传承问题、去思考现代文明下人性变迁的精神困境。汉藏文化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王小忠想要呈现的是,不要把焦点集中在民族文化矛盾或“文化排他”的陷阱,文化的冲突实则也在强化着文化认同。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作家,对汉文化入侵或现代文明技术进行批判,或对藏族乡村生活美好的怀念,王小忠也在力图像阿来、吉米平阶等作家一样,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甘南藏地文化的发展变迁,换句话说,这也是王小忠小说的文化纵深感和价值厚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