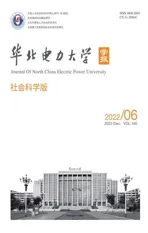“先宾后补”是唯一合法的语序吗?
——兼论词库与句法的关系
2022-03-23吴宇仑
吴宇仑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一、“先补后宾”和“宾在中间”是句法操作吗?
传统的汉语语法一般认为,当汉语中动词、宾语和补语一起出现的时候,一共有三种可能的语序,并且经常用以下有关复合趋向补语的三种变换句式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
(1)小张从书包里[动拿][补出来][宾一本书]。
(2)小张从书包里[动拿][补出][宾一本书][补来]。
(3)小张从书包里[动拿][宾一本书][补出来]。
按照动词、宾语和补语的线性排列顺序,这三种句式分别被称为“先补后宾”(如例(1))、“宾在中间”(如例(2))和“先宾后补”(如例(3)),其中,如例(2)的句式的补语“分裂”为宾语一前一后两部分,给传统的层次分析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为层次分析法假设每一个成分都是线性连续的[1-2]。然而,近来有从形式句法尤其是生成语法角度编写的现代汉语语法教材,对上述三个句式涉及的宾语和动词的语序进行了重新的描写,在新的理论框架下,邓思颖[3]118-135认为,汉语中宾语和补语共现时只有一种固定语序,那就是“动+宾+补”,补语总是位于最右侧的补足语(complement,与传统汉语语法中的术语“补语”差之千里)位置。
按下理论上的分歧暂且不表,不妨先来看看邓思颖[3]118-135是如何得出这样的论断的。邓思颖[3]118-135首先从传统语法对于补的再分类开始进行阐述,传统语法中补语分为结果补语、可能补语、程度补语、状态补语、趋向补语和时间与处所补语六个小类,每个小类的例子如以下所示:
(4)(结果补语)四班踢[补赢]了三班。
(5)(可能补语)医生救[补得活]张三吗?
(6)(程度补语)真是要气[补死]我。
(7)(状态补语)汉语说[补得不好]。
(8)(趋向补语)掏三百块[补出来]。
(9)(时间与处所补语)走[补到颐和园]了。
如(4)到(9)所示,不难发现,对于结果补语、可能补语和程度补语来说,宾语往往出现在补语的后边而不能出现在补语的前边,比如:
(10)*四班踢了三班[补赢]。
(11)*医生救张三[补得活]吗?/*医生救得张三[补活]吗?
(12)*真是要气我[补死]。
而状态补语和时间与处所补语两个小类,一般不会与宾语共现,所以不涉及语序问题。趋向补语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如上述(1)到(3)的三种可能。总结一下,结果、可能、程度补语都是“先补后宾”,趋向补语是三种情况都有可能,那么如何从这样的语言事实中得出“先宾后补”是唯一的合法顺序呢?首先,“先补后宾”的三种补语,全部不是在句法层面生成的,而是在词库中通过词法生成的固定词项。也就是说,(4)中的“踢赢”是一个独立的词项,至于其在词库中怎样生成则不是句法的问题,(5)和(6)中的“气死”和“救得活”也是同理,因此“踢赢了三班”“救得活张三”“气死我”都是简单的动宾结构,不涉及补语语序问题。把这三种补语分析为在词库中生成的,邓思颖[3]118-135分别给出了如下的理由:第一,对于结果补语和程度补语,朱德熙[4]125将它们划分为“粘合式补语”,其补语成分的意义已经出现了虚化,比如“气死”的“死”是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死亡,而是表示程度深;第二,对于可能补语,虽然朱德熙[4]125-127认为它不属于“粘合式补语”,但承认结果补语的语序从宋元白话到现代汉语完成了“先宾后补”到“先补后宾”的变化,比如“拉他不住”在现代汉语里变成了“拉不住他”,这种语序的变化实际上是两个词项互相靠近并凝结成为一个词项的过程。由此,邓思颖[3]118-135将三种“先补后宾”的结构从句法中排除了。随后剩下的就是趋向补语的问题,鉴于“先补后宾”的补语都是复合词,自然而然地,那就是(1)中的“先补后宾”和(2)中的“宾在中间”是“伪命题”,(1)是一个简单的动宾结构,(2)中只有“来”是补语,如下所示:
(13)[动拿出来][宾一本书]
(14)[动拿出][宾一本书][补来]
这样的分析进而解决了所谓的复合趋向补语问题,同时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汉语句法中唯一合法的语序就是“动+宾+补”,“宾在中间”和“先补后宾”都是伪命题。
然而,这样的论证似乎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在论述为什么结果补语是复合词不是短语的时候,主要论据是因为结果补语历时地从宾语后移动到了宾语前,也就是说有以下的逻辑推理形式:
(15)因为(结果)补语位于宾语之前,所以它是复合词的一部分。
随后,在解释为什么复合趋向补语可以“分裂”位于宾语前时,主要原因是这些位于宾语前的形式都是复合词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又有了以下的逻辑推理形式:
(16)因为(复合趋向)补语是复合词的一部分,所以它位于宾语之前。
把(15)和(16)结合起来看,“位于宾语之前”和“是复合词的一部分”互为彼此的因果,这似乎有一些循环论证的嫌疑。除此之外,将程度补语排除在句法范围之外的做法,可能也并非是学界的共识。对于程度补语而言,诚然,有些程度补语比如“气死”的“死”的意义确实有所虚化,可是有些程度补语语义还是相当透明的,比如“开心极了”的“极”,就是表示极限的含义,没有任何的变化,这样看来,程度补语是否都是复合词的一部分,可能也还值得深究。
抛开上面的理由不谈,不妨用形式上的测试来检测一下宾语前的这些形式究竟是一个复合词还是动补结构,结构主义时期汉语语言学区别词和短语的方法是扩展法,而生成语法中也有类似区别词法和句法的“词汇完整性假说(Lexical Integrity Hypothesis,简称LIH)”,在本文下一章节中,将应用这些形式标准来尝试鉴定“先宾后补”到底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二、来自形式鉴定的证据:扩展法和LIH
由Jespersen最早提出的“隔开法”是中国结构主义理论中“扩展法”的雏形,扩展法后来经过王力、陆志伟[5]等人结合汉语语言事实进行的调整,成为了鉴别词和短语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6],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方法的本质是考察形式内部的组合紧密度[4]13,从方法上来说,就是看词中间能否插入别的形式,例如“看书”可以插入“一本”变成“看一本书”,因此就是词组而不是词。如果用这个方法来鉴别上文中邓思颖[3]118-135认为是词项的形式,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非常有趣,针对复合趋向补语来说,可以做以下的扩展:
(17)拿出来→拿一本书出来/拿出一本书来
按照扩展法的定义,这说明“拿出来”是一个短语而不是一个词项,然而有趣的是,“先宾后补”的体系仍然是自洽的,并且可以解释(17)中的现象:那就是(17)并不是真正的扩展,扩展出来的结果只是一个巧合,因为在这一的体系中,“拿”是动词,“拿出”也是动词,所以“拿出一本书来”只是动词“拿出”为核心的VP,而“拿出来一本书”则是以“拿出来”为核心的VP,两者只是语音上有所相似而已。同样的,“拿出来”还可以做以下的扩展:
(18)拿出来一本书→拿得出来一本书/拿不出来一本书
通过增加“得”和“不”,实际上把趋向补语变成了一个可能补语,然而有趣的是,“先宾后补”的体系仍能对(18)做出解释,那就是前文所述的,既然认为表示可能的“得”是一个动词的词缀,按这种分析,表可能补语的“不”确实也是词缀,因为它的分布和“得”几乎完全相同,所以按照邓思颖[4]118-135的体系,完全可以说(18)的变换结果中的“拿得出来”和“拿不出来”都是复合词,“拿”在词库里先和“出来”结合再和“得/不”结合生成了这两个词项。看来,通过扩展法是无法判断“先补后宾”是不是伪命题了—因为不但可以认为“先补后宾”是复合词,而且可以认为“先补后宾”插入其他形式之后的扩展式也是复合词,因此,通过扩展法,既无法证伪“先补后宾”是复合词,也无法证明这一结论,看来,需要用其他的理论工具做出判断。
无独有偶的,在生成语法内部也有着区别词和短语的理论。词汇完整性假说即LIH的主要目的是区别句法规则和生成规则,因为在生成语法的体系中,词库中词的生成和句法中短语的生成是两个不同的模块[7]。Lapointe[8]等人提出以及随后不断完善的LIH,尽管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但本质上殊途同归,其基本思想是短语结构规则不能用于词法层面,即语素不能承担句法层面的操作。例如,Huang[9]认为LIH包括三条原则:(1)不能在并列结构中进行同形删略;(2)词内部的语素不参与句法解释;(3)词的内部成分不能用代词回指。而Bresnan&Muchombo[10]根据Bantu语的事实提出了五条原则,分别是:(1)词的内部成分不能移位;(2)词的内部成分不能并列;(3)句法操作(如否定变换)无法侦测到词的内部成分;(4)词的内部成分不能用代词替换;(5)词组结构具有整体递归性。用LIH来测试一下邓思颖[3]118-135认为的“复合词”,很容易就能发现问题,例如:
(19a)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19b)狠狠地[怎么]了敌人?
(20a)[撤]回我说的话
(20b)*[怎么]回你说的话?
(20c)*[咋]回你说的话?
(21a)[撤回]我说的话
(21b)[怎么]你说的话?
(22a)[拿]出来一千块钱
(22b)[怎么]出来一千块钱?(借还是取?)
汉语中有一种非常常见的句法操作,就是针对句子中的某个成分进行提问,形成一个特殊问句,也就是所谓的“wh问句”,需要注意的是汉语中没有“wh移位(wh-movement)”,即特殊疑问词不需要提升到最前的位置,汉语中用于提问动词性成分的特殊疑问词一般是“怎么”,例如对(19a)中的动词性成分“打击”进行提问,可以得到(19b),这属于句法层面的操作,按照LIH的观点不能用于词法之中,这一点由(20)和(21)可以说明:对(20a)中动词性的“撤”进行的提问(20b)是不合法的,说明这条句法规则不能应用于形式“撤”,进而说明形式“撤”是词内部的成分,需要注意的是(20b)确实是因为违反了LIH而不合法,而不是因为“怎么回”是三音节形式违反韵律规则,因为即使将“怎么”换成单音节的口语化的特殊疑问词“咋”以后,(20c)依然是不合法的形式,相比之下,(21a)中的“撤回”可以用(21b)中的“怎么”提问,说明“撤回”不是词中的语素,而是一个独立的词项(或者一个短语)。因为这里的特殊疑问词相当于代词,所以这条检验规则实际上就是Huang[9]和Bresnan&Muchombo[10]提出的“词内部的成分不能用代词替换(或回指)”。然而用这种方法检验所谓在词库中生成的“拿出”和“拿出来”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如(22)所示,“拿出来一千块钱”来中的“拿”可以用“怎么”提问形成(22b)中的特殊疑问句,这说明句法规则可以作用于“拿”这个形式,进而,按照LIH的说法,“拿”这个形式至少是一个词项,而不应该是词项内部的一个成分。
现在再来用LIH的标准来鉴定邓思颖[3]118-135认为是复合词的结果、可能和程度补语。对于可能和程度补语而言,确实内部的动词性成分似乎不能承担任何形式的句法操作,例如:
(23a)[气]死我
(23b)*[怎么]死我/*[咋]死我
(24a)[打]得倒
(24b)??[怎么]得倒
结果补语中的动词性成分似乎也不能用“怎么”提问:
(25a)[踢]赢了
(25b)*[怎么]赢了/*[咋]赢了
可是结果补语似乎可能承担另一种句法操作,那就是其内部的成分似乎可以在并列结构中同形删略,也就是Huang[9]所说的的第一条原则。当并列结构中的两个成分都是短语且有一部分相同时,一般可以同形删略,比如:
(26a)自动挡汽车和手动挡汽车
(26b)自动挡[汽车]和手动挡汽车
(27a)青菜和菠菜
(27b)*青[菜]和菠菜
(26a)中“自动挡汽车”和“手动挡汽车”都是短语,因此相同的部分“汽车”可以删除,如(26b)所示。但当并列结构的两个成分都是词的时候同形删略是不合法的,比如(27)中的例子。当两个带结果补语的形式位于相邻结构且动词性成分相同时,有时候也可以同形删略,例如:
(28a)打赢了打输了都无所谓。
(28b)打赢了[打]输了都无所谓。
(29a)你到底考过了没考过?
(29b)你到底考过了没[考]过?
这种同形删略的可能性说明(28)中“打”和(29)中的“考”至少是词项,而不是词项中的成分,进而说明朱德熙[4]125对于结果补语的划分是正确的,结果补语属于“组合式补语”而不是“黏合式补语”,其中补语成分和动词性成分的关系是松散的。
综上所述,形式鉴定的手段尤其是LIH的原则表明:第一,将趋向补语“先补后宾”和“宾在中间”形式中宾语前的补语成分认为是动词的一部分进而把这两种结构排除在句法之外是有问题的;第二,“先补后宾”的结果补语中补语成分和动词成分的关系也应该是短语结构关系,而不是在词库内部生成的词项内部成分之间的关系;第三、可能补语和程度补语中补语成分和动词性成分结合紧密,这两种述补结构确实应当看作在词库中生成的词项。
三、从汉语的特点看词库与句法的关系
模块论,即认为语法系统是由不同的子系统(模块)组成的一直是生成语法的重要理论观点之一[11],词库负责生成词项,而句法负责利用词项组成不同的短语,这两个模块是互相独立的,在分析一个语法现象时,有两种可能的态度,一种是增加句法的规则,这样来说相当于简化了词库,因为早期的句法规则总是和转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种观点又被称为转换主义观点,相对地,另一种态度是尽量简化句法的规则,将规则的增加尽量放在词库中去进行,这被称为词汇主义观点[7],最简方案对运算的精简实际上是集中于句法规则部分的,即在其体系中被称为运算系统(Computational System,简称CS)的部分,CS部分最后只剩下一种操作就是合并(merge),但是相对应的,词库的生成能力在不断增加,这说明词库内部的生成规则越来越复杂。
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邓思颖[3]118-135所建立的汉语语法体系主要就是依赖于词汇主义的观点,在他的体系中,诸如体标记“了”“着”“过”、动补结构中间插入的功能词“得”、传统语法中的方位词“(NP)上”“(NP)里”都被从句法中剔除出去,交给词法去解决,这样势必会造成词库具有非常强的生成能力,例如“屋子→屋子里”的过程不仅是词义的变化,其选择限制也发生了改变,从不能跟在“在”“到”等介词之后变成了可以跟在这些介词之后,这说明从“屋子”到“屋子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生成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缀加过程。这样做的优点是句法体系非常简单且有规则,汉语所谓的特殊结构如“连动式”“兼语式”等等都由基本规则推导出来,无需所谓“句型”的概念,缺点就是词库的内容失于庞杂。
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邓思颖[3]118-135所建立的汉语语法体系主要就是依赖于词汇主义的观点,在他的体系中,诸如体标记“了”“着”“过”、动补结构中间插入的功能词“得”、传统语法中的方位词“(NP)上”“(NP)里”都被从句法中剔除出去,交给词法去解决,这样势必会造成词库具有非常强的生成能力,例如“屋子→屋子里”的过程不仅是词义的变化,其选择限制也发生了改变,从不能跟在“在”“到”等介词之后变成了可以跟在这些介词之后,这说明从“屋子”到“屋子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生成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缀加过程。这样做的优点是句法体系非常简单且有规则,汉语所谓的特殊结构如“连动式”“兼语式”等等都由基本规则推导出来,无需所谓“句型”的概念,缺点就是词库的内容失于庞杂。
(30a)Kangae-komu
Think-enter
“To think deeply”
(30b)Kangae-ni-kangae-komu
Think-PP-think-enter
“to think deeply over and over again”
可见,(30b)的反复形式中,只有动词的一部分进行了反复,这违反了“句法规则不能用于词内部”的规则。
汉语的事实似乎对LIH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汉语语法(包括句法和词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句法和词法具有递归性,像是俄罗斯套娃一样,语素组成词的规则和词组成短语的规则高度相似[12],很多句法的操作可以应用到词的内部,“著名”的离合词暂且不提,即使是普通的复合词中的成分也往往可以承担句法操作,这里我们仅仅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首先是可插入性,汉语中大量的复合词中间都可以插入别的成分,尤其是对于传统语法说的动宾复合词和动补复合词而言。很多动补式复合词中间都可以插入“得”和“不”,这种结构相当能产,然而又不好说他们是短语,因为它们中间只能插入“得”和“不”,不能插入别的成分,所以Chao[13]369-371只好说它们是介乎凝固的词和可扩展的短语之间的形式,例如“说(得)服”“下(得)去”“推(不)翻”“撤(不)回”等。类似的,很多动宾式复合词中间都可以插入体态标记,比如Chao[13]323所举的例子:“他断了弦就再也没续过弦。”其中“断弦”和“续弦”中分别插入了体态标记“了”和“过”。
其次是Huang[9]所提到的第一条原则,即在并列结构中不能进行同形删略对汉语很多动词而言是不成立的,汉语的很多双音节动词在和否定形式并列构成正反问的时候都会省略第二个音节,形成“A不AB”或者“A没AB”的形式,例如:
(31)你害[怕]不害怕?
(32)你老实说,你撒[谎]没撒谎?
(33)明年咱们还扩[大]不扩大经营?
(34)你相[信]不相信我?
以上的这些例子中都有比词项小的单位出现了同形删略的情况,这是违反了LIH的。
前两个例子是句法影响了词法进而违反了LIH的例子,最后来看一个反向的例子。在汉语中,重叠是一种构词方法,可是同样的,在句法中重叠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操作,动词和形容词可以分别以不同的形式进行重叠,比如“高兴”可以变为“高高兴兴”,“舒服”可以变为“舒服舒服”,由此看来,汉语的词法似乎也不止能在词库内发挥作用。
以上基于汉语事实的例子说明,对于一个句法和词库都具有相当强的理论体系来说,想要将句法生成规则和词库生成规则完全地界定开,似乎是有一定难度的,即使是传统意义上认为句法和词法不同的印欧语[12],有时候也会有句法规则干涉词库生成的情况,例如以下的例子:
(35)Pre- and post-war
例(35)中在并列结构中进行了同形删略,实际上还是违反了Huang[9]的第一条原则。可见,LIH不仅是在汉语中遇到了困难,在其他语言中也能经常举出反例(比如例(30)中日语的例子)。因此,词库和句法两个部分并驾齐驱,都具备相当强的生成能力的格局是行不通的,它们之中只能有一个具备很强的生成能力。在此基础上,有学派选择加强词的表义功能,弱化语法的参与,但是站在生成语法的角度上,生成语法要求句法总是要具备一定的生成能力,所以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要把词库的生成能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问题也逐渐成为共识,甚至有极端的建议[14]认为应当取消词层面,将词库定义为一个静态的语素的列表,所有的生成都在句法部分进行。
四、结语
在当代生成语法的理论体系中,词库的生成能力过于强大,甚至超过了句法部分的生成能力。从生物语言学角度上来说,这并不符合人类语言“晚发突变”的特点[14]。而落实到对语言进行描写的实践中,会导致将所有的疑难问题全部交给词法,句法部分确实简单了,但是词法研究就会过于复杂。因此,在简化句法部分运算的同时,限制词库的生成能力,也是一个必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