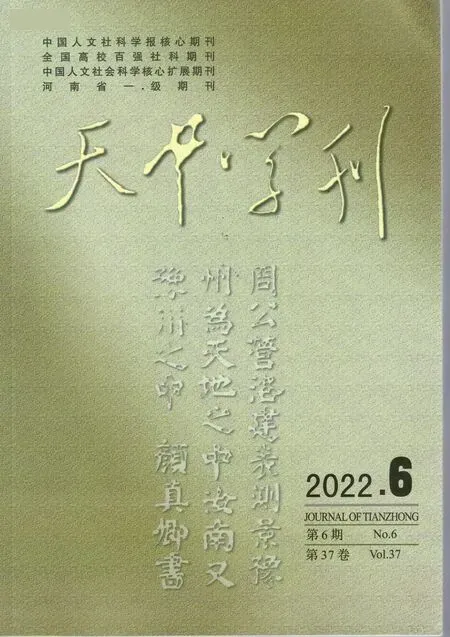镜与影的隐喻——莎剧《理查三世》中理查形象的多重面相
2022-03-23李若怯
李若怯
镜与影的隐喻——莎剧《理查三世》中理查形象的多重面相
李若怯
(郑州智能科技职业学院 影视艺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1161)
在《理查三世》中,“镜子”与“影子”意象分别对应理查内心活动的不同阶段,呈现了他的内在心理演变过程,揭示了他自我建构与目标追求的偏差,借此可以审视该剧的悲剧实质。在《理查三世》的创作中,除了对人物复杂性进行呈现,还显现出莎士比亚对王权本身的意义阐释。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形象;流变;王权
美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他的著名论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中,巧用“镜”与“灯”两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意象指代古典主义思想中的“模仿说”和浪漫主义浪潮中的“表现说”,以此来观照文艺思潮中的历史流变、内在想象与批评重建。而早在16世纪末,莎士比亚就采用了“镜”与“影”的意象来表现他笔下的“魔鬼君主”理查三世,意欲通过这些精巧的隐喻去呈现人物的内在心理演变。
“镜”与“影”的表述在《理查三世》中一共出现过3次,分别处于理查开场的独白、理查和安妮求爱后的独白以及理查母亲得知克莱伦斯死讯时的哀叹中。前两处的隐喻是理查自我建构和其自恋情结的缩影,而公爵夫人的控诉则从他者的视角为理查的迷失提供了佐证。在道德层面,理查是一个彻底的恶人,他身上散发出的泯灭人性的恶甚至难以在现实中找到真实摹本,以引发观众的怜悯与共鸣。就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爱我,我若死去,没有一个人会怜惜我。他们为什么怜惜我?连我自己在自己身上都找不到值得怜惜的东西。”[1]387但是,理查三世的形象又不是如此扁平化的呈现,他的魅力源于莎士比亚在创作时对其形象刻画的“割裂性”,即理查身上同时存在着几乎从一而终的恶和为了实现目标而高昂奋进的进取精神。
因此,理查代表的是一种罪恶与勇敢并存的复合型审美形象。然而,莎士比亚对理查三世的刻画绝不仅仅止步于对其审美功能的阐发,这背后所彰显的价值还包含着作者对英国政治秩序与王权更迭的思考。在莎士比亚整个历史剧的创作中,除了对人物复杂性的呈现,还有着一条极其重要的思想脉络:作者对于王权本身的意义阐释和王权继承的条件与规定性的思索。
一、镜中人:理查的自我建构
“镜子”作为一种饱含哲学深意的意象,古往今来被各派批评家视为一种美学象征。镜子包含着“认识自我”与“反映世界”的价值,总之,它早已脱离了简单的实用功能,而用来反射人类的思想之光。约翰逊曾说:“莎士比亚的才华就在于他向读者举起了风俗习惯和生活的真实镜子。”卡莱尔在评价莎士比亚时也曾说过:“莎士比亚的道德,他的英勇、爽直、宽恕、真实……在这里不都能看到吗?像世界一样伟大!这面镜子绝不会扭曲形象,也不会像劣质的凹凸镜那样以自身的凸状与凹状来反映一切事物;这是一面绝对平整的镜子……”①这两位批评家都意在用镜子的反射功能阐释作品对真实生活的模仿,但“镜子”这一意象在作家本人的运用中,却由反映世界的摹本转变为对被反映者的揭示。
“镜子”表述第一次出现在《理查三世》是在第一幕第一场的理查独白中,他迫不及待地向观众展露自己与缺陷的身体相匹配的畸形灵魂:
可是我呢,我的身形不让我寻欢作乐,不让我对着多情的镜子顾影自怜。我形容丑陋,缺少谈情说爱的堂堂仪表,难以在步态轻盈的荡妇娇娃面前高视阔步……好吧,既然我在这语软声娇的美妙日子里无法谈情说爱,我只好下定决心做一个歹徒,跟长期以来的无聊欢乐作对。[1]275–276
这时的理查因为身形残疾而导致自卑,因此不敢照镜子,也无法直面镜中那个面目丑陋又四体不全的自己。理查要想填补身形的缺憾成为“人上人”,就必须摒弃自卑,重新建构新的自我。理查为自己找寻的出路就是做国王,登顶权力的巅峰。“我把希望寄托在梦想的王冠上,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把王冠戴在我这残躯之上的脑袋上,否则我就认为这世界是个地狱。可是我不知道如何下手夺取王冠,因为有许多人挡着我,使我达不到目的。”[1]228可见,此时的理查已经有称王的意念做指导,但他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能证明篡权意图的可行性,直到遇见了安妮这枚棋子,她为理查的夺权之路带来了第一份“荣耀”。理查深知丑陋的外表让自己无法享受被爱的权利,而对造物主的不满又使他不屑于去爱别人。因此,早在《亨利六世》(下)第五幕第六场中,理查就表示他不懂得怜悯、爱情与恐惧,他的世界里没有神圣的爱,他是孤家寡人。这样一个与爱绝缘、与安妮有着血海深仇的理查,却凭借着荒唐却又巧妙的逻辑说服了安妮,使她嫁给了自己。在向安妮求爱成功后,理查的大段独白中又出现了“镜子”意象,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再逃避,而是兴高采烈地去买镜子。先前还因为命运的不公、身形的限制而不敢面对镜子,如今却主动地去买镜子,这前后差异的原因何在?
理查的这次成功表演可以被当做一次圆满的政治实践。按照门德尔的分析,理查求婚的时机安排得极其巧妙和高明。他善于利用聪明的“人设”,却故意“装傻”,选择在安妮对他恨之入骨的时候向他求婚,更加显示出理查像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可怜人”。“他伪装成完美的基督徒,对安夫人的侮辱充耳不闻,‘以德报怨,以祝福代替诅咒。’”②在理查极尽溢美之词却还无法打动安妮时,他又要急于洗脱他杀害亨利六世和其儿子爱德华的嫌疑。这时他开始演绎让安妮共情的逻辑:以爱之名将安妮归为杀人的帮凶。理查坦言是对安妮的爱让他失了理智,不得不除掉这些障碍,因此安妮才是导致亨利与爱德华死亡的真正原因。这在无形中将安妮与恶魔理查归为一个阵营,“她沮丧地看到,她在谴责理查的同时也在谴责自己。若理查是个谋杀犯,她就是他不知情的同谋”③。之后,理查又跪下,向安妮呈上刀剑,假意成为他们爱情的殉道者,甘愿以死充当安妮那无处发泄的复仇情绪的出口。接着,理查继续深化他这个忏悔的囚徒形象,主动要求承办亨利六世的葬礼,以示悔过。在理查一系列的政治表演下,安妮终于相信了他,并说出:“能看到你这样深自悔恨我也感到欣慰。”[1]287然而,面对这次成功,理查的内心却很复杂:
她能瞧得起我吗?我的整体也比不上爱德华的小小局部。她能瞧得起我吗?我是个瘸子,又是这么个丑八怪。我可以拿我的公国跟一个铜板打赌:我无疑是低估了我自己!我以生命起誓,在她眼里我准是个极为风流倜傥的人物,尽管我自己还看不出来。我要花几文钱买一面镜子,请几十个裁缝,让他们研究一下时装,把我这身子打扮起来。既然我不知不觉对自己有了好感,我得不惜破费把它维持下去。[1]288
照耀吧,美丽的太阳,我要去买镜子,我要在阳光里徘徊,欣赏我的影子。[1]289
从这段独白可以看出,理查因为自己残缺的外表而本能地怀着自卑的惯性去追问安妮对自己的态度。但因为成功说服了安妮,他立即认为自卑不该是他生命的底色,长久以来是自己低估了自己。由此,他便开始自我建构起高大圆满的形象。只是这个形象现在还无法呈现,需要理查主动去找寻一面能够反射形象的镜子。这面镜子是他看见自己的工具,正是因为升腾而起的自信,他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理想形态。
也正是从理查的镜子需求出现后,他的行动力和进取精神完全被激发了出来。在镜子里,自卑、迷茫、无助的理查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饱含反叛精神的“抗争式暴君”。带着对王权的痴迷和要成为“人上人”的决心,理查操持着高超的洞察力、机敏的反应力和蓬勃的生命力,在反抗命运不公的道路上引吭高歌。为了成为国王,他制订了两套严密的计划,即塑造自己的合法性、扫除异党以及所有拥有继承权可能性的亲信。前者要求他抹黑其他亲信的血统以及假扮圣徒在民众心里树立威信,后者则要求他做一个残暴不仁、丧尽天良的血腥刽子手。为了维持镜子中让自己心生好感的“崇高”形象,这些任务理查都出色地完成了。因此,镜子的出现无疑为理查扭转自卑、重新建构自我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而“镜中人”的形象却预示着理查终将在那个虚幻又狂妄的自我中走向毁灭。
二、影子幻象:盲目的“那喀索斯情结”
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是“自恋”的象征,他因自负得罪了爱神阿佛洛狄忒,于是遭到“除了自己谁都不爱”的诅咒。那喀索斯最终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只是这个倒影难以触摸也无法拥有,最后他抑郁而终化作池边的水仙花。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一点很重要的启示:“那喀索斯的悲剧根源在于封闭和自大。阿佛洛狄忒诅咒他除了自己谁都不爱,只爱自己。这一惩罚最致命的地方在于它割断了那喀索斯同外界的情感联系,他的爱被禁锢,包裹,‘只爱自己’被禁止在‘自己’这个圈内,无法向外拓展、伸张,触及不到爱的对象。”[2]通过观察不难发现,理查三世与那喀索斯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受到了命运的诅咒,理查的先天残疾使他也像那喀索斯一样被上天灌注了封闭与自负的特质,他们无法学会爱,无法同外界建立情感联系,他们甚至丝毫不需要通过他人的评判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因此只能在命运为他们所铸的堡垒内孤独地欣赏自己的影子。在他们的世界里,值得欣赏的唯有自己或者能反映自己形象的影子,但影子只是被意念美化过的自我。他们看到的影子越圆满,个体就会越发自负和封闭,就会陷入被夸大的主体性中无法自拔。
在剧作开头的理查独白中,他哀叹欺人的造化把他塑造成如今这个奇形怪状的样子:“我呀,唉!在这个没精打采的升平时世总是落落寡欢难以排遣,只好望着自己在阳光里的影子拿我的残废发发牢骚。”[1]275和镜子带来的第一次心态转变相同,影子的第二次出现也和理查主动唤起的镜子需求如出一辙:“我要在阳光里徘徊,欣赏我的影子。”[1]289理查由无奈之态到自我欣赏,他所迷恋的影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纵观全剧,理查留给观者最深的印象便是他的恶,但是这种恶只是他的手段而非他的目标。理查真正追求的理想形态是“赢”,他所贪恋和欣赏的影子是拥有绝对控制权的赢家形象。
从《亨利六世》(下)开始,理查就在他的独白中多次明确表示自己对王位的强烈欲求。他有着明晰的行事准则,善用伪善面目来掩盖罪恶的行动。
唉,我会笑,一面杀人一面笑,对伤心的事表示满意,假装流眼泪,在不同的场合装出不同的嘴脸。我要比海妖淹死更多的水手,比古埃及的毒兽杀死更多碰到我目光的人,比古希腊的涅斯托耳还能说会道,比奥德修斯还诡计多端,和希腊的西农一样再夺一座特洛伊城。我能比变色蜥蜴更会变色,像普罗托斯一样地变形,让那杀人如麻的阴谋家向我学习。我既然能做这些,难道我不能得到王冠吗?去他的,王冠再远,我也要把它摘下来。[1]228
对王冠痴迷的原因,则来自理查对造物主赐给他残缺身体的反叛意识。“葛罗斯特的身体是神正论信仰体系里的一道裂痕,他成为一个多余者,从被动受造物变为主动造物,进而反抗这‘圆满’的神世界,如培根所说,身有缺陷之人要对自然进行报复。”[3]82而成为一国君主,则能在俗世中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既然无法支配神意授权下的畸形身体,那就靠过人的胆识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掌控一切的造物主。于是,他目空一切,变得极度自大:“不过我生在高空,我们雏鹰的巢是筑在松杉之巅的,总是跟天风嬉戏,并没把太阳放在眼里。”[1]297这时,已经不存在任何值得理查敬畏的事物了,连上帝都沦为他争权夺利的工具:他利用人们对上帝的崇拜,扮演圣徒为自己装点门面,从而赢得人心。市民拥护理查称王的戏份无疑是全剧的一大高潮,他潜心扮演着一个圣洁虔诚的教徒,与两个主教左右同行。面对市民的称王请求,理查与白金汉开展了精彩绝伦的政治表演。在市民眼中,理查是一个手捧圣书,因潜心祈祷而推迟与朋友会面的高贵基督徒。当白金汉发动猛烈攻势向理查提出称王请求时,理查欲迎还拒、明推暗就,表示自己谦卑谫陋无法胜任。理查俨然成了能操控大众意念的掌权者。加之理查又以和安妮求爱相似的逻辑说服了伊丽莎白王后将自己的女儿嫁于他,他更加自鸣得意,鄙夷地称呼后者为“软心肠的傻瓜,浅薄易变的女人”[1]373。他根本无从知晓王后的应答是否出于真心,但他依旧认为自己才是世上最能洞悉人性、聪明绝顶的人。
理查在夺权称王的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去大批政敌的性命,对重塑仇敌和民众的价值观,他也得心应手,俨然成了掌握别人命运的主宰者。他自顾自地欣赏这个掌控者的影子,直到他认识到自我的局限,产生了随之而来的影子破碎的无力感。
理查以为自己早已抛弃了良心与恐惧,可以凭借恶的威力成为人世的主导。但当小爱德华、亨利六世、克莱伦斯、里弗斯、格雷、沃恩、爱德华王的两个小王子、黑斯廷斯、白金汉等一众被他杀害的人的鬼魂出现时,理查彻底陷入了混乱,他开始害怕和逃避,甚至不断怀疑自己:
我浑身发抖,渗出了恐惧的冷汗。我害怕什么?害怕自己吗?……这里有杀手吗?没有。啊,有的,我就是个杀手。那就逃吧!怎么?逃避自己吗?…….啊,我是爱自己的。为什么爱?因为我对自己干过什么好事吗?啊没有!唉!我倒是因为自己作的孽厌恶自己,我是个歹徒。我说了谎,我不是歹徒。傻瓜,你该说自己光明磊落呀,傻瓜,别再自我安慰了。我的良心有一千条不同的舌头,每条舌头都叙述着一个不同的故事,而每个故事都谴责着我,说我是个歹徒。[1]387
可以看出,理查此时的思维混乱且纠结,他的良心重新回归,拼命地与自己的歹徒身份进行斗争。这一刻,理查发觉他并不像他的影子那样坚韧和果决,他甚至不再成为自己的主导。理查精心获取的掌控权轰然崩塌,他无法左右自己的良知,也无法得到救赎,更恐惧来自彼岸世界神秘力量的侵袭。就像弗里希所说:“他无法纠正自己”“他成了自己阴谋的囚徒”[4]133。但理查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面对里士满的挑战,他勇敢迎敌,在战场上表现出不畏一切艰险的勇力。在理查的马战死之后,他说出了那句饶有意味的话:“一匹马!一匹马!我拿王位换一匹马!…….我已拿我的生命做了孤注一掷,只等赌出个分晓……马!马!我拿王位换一匹马!”[1]392此话看似疯狂和荒唐,实则表现的是理查至死都在捍卫那个赢家的影子。他的毕生追求其实不是王位,这只是他欲望的表征。“理查最大的欲望似乎是要操纵和控制别人。”[4]134“理查可以通过压服别人来最佳地展现自我。”[4]132因此,理查的王冠之梦只是通过绝对处置权的彰显来证明自己的赢家身份,而至于怎么去做一个好国王以及怎样治理好一个国家却从来都不是理查考虑的目标。他愿用王位换一匹马,就是用王位去换自己能赢过里士满的可能性。在这个层面上,王位变成了理查赌桌上的砝码,为了保存那个赢家的虚幻名声,他不惜将国家变成实现欲望的工具。理查一生都在赏析他为自己塑造出来的影子,直到临死还在建构自己在战场上的主导权。在这里,莎士比亚或许是在提醒观者,当个体盲目地夸大主体的作用,欲以自己的意志计算并掌控一切时,这种自恋的幻影只会成为反噬主体的邪恶力量。
三、理查三世形象背后的王权之思
谈及理查三世的形象,莎士比亚在剧作中已经借他人之口为理查贴上了很多标签:安妮称他为肮脏的魔鬼、丑怪的地狱使者、男性丑怪的极致、心灵难以想象的恶棍(第一幕第二场);玛格莱特王后认为他是杀人的歹徒、凶神恶煞、恶狗(第一幕第三场);而理查的亲生母亲对他的形容也是阴险欺诈、顽劣不堪,甚至后悔把理查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这该诅咒的子宫,这死亡的温床!是你为这世界生下了一条妖蛇,它那无法躲避的目光能致人死命。”[1]352因此,理查的恶几乎是贯穿全剧的最显性特质。
但随着我们对理查形象不断深入地探索就会发现,他的个性又不能仅由一个“恶”字来概括,人们分明能从他的身上看到他在游说安妮和伊丽莎白夫人时表现出的精巧又缜密的逻辑;在骗取克莱伦斯和市民们的信任时展现的高超演技;为了反抗命运不公而流露出的信心和行动力;直到坐骑战死还在战场上独自拼杀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就像门德尔所说:“我们不能谈论理查的本性,因为他没有本性。它的存在就是艺术,仅此而已。”[4]110理查似乎从来没有过向善的需求,但在最后的独白中,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可憎面目,并无力抵御良心的谴责。
理查形象的艺术塑造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他也许永远成为不了观众心里的英雄,也难以收获他人的任何怜悯,但至少他是崇高的,因为“对于悲剧说来,致命的不是邪恶,而是软弱。气魄宏伟的邪恶常常会像弥尔顿的撒旦和歌德的靡菲斯特那样崇高”④。理查那不顾一切也要捍卫自己掌控权的欲念指引着他犯下种种恶行,但他一切行为的背后都彰显着那暴风雨般的激情和坚韧挺拔的意志力。因此,理查形象的审美性就在于他为了达成目标所展现出的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他至少在形式上是伟大坚强的”⑤,并且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软弱的意志和自甘平庸的态度。
抛开理查三世形象本身的审美性特征,将作者意图置于更宏大的政治哲学背景中去考量就会发现,《理查三世》还包含着莎士比亚对王权于人的影响、王权存在的正当性、王权当如何持存等问题的思考。就像蒂利亚德所说:“最后,我们不能忘记理查作为一种手段,表达了有关君主的正统观念。”[5]237其实,在该剧和《亨利六世》(下)中,关于王权的探讨占据了很大的篇幅。理查曾明确地表示:“父亲,请想想戴上王冠有多么甜美,王冠里面有乐土,有诗人描绘的一切幸福快乐。”[1]192这时的理查虽然在煽动父亲夺取王位,实则是吐露自己对王权的痴迷,他相信王冠里面有世俗承认的一切美好。但除了理查,其他人物谈及王权则几乎都是负面的评价。亨利因为没有统治的才能,被王后和克列福轰出战场,他独自坐在山坡上感叹道:“上帝呀,我认为一个单纯的牧羊人的生活要幸福得多……”[1]213也就是在这时,莎士比亚开始提醒观者注意,王权并没有理查想象中的那样美妙。这种焦虑到了《理查三世》中,则彻底被玛格莱特和伊丽莎白两位王后推向高潮。这两位都曾站在女性权力顶峰的王室成员曾有过如下抱怨:
伊丽莎白王后:我宁可做一个供使唤的乡下丫头,也不愿在这种条件下做个显赫的王后,任人冷嘲热讽,嬉笑怒骂。自从做了王后,我就很少快活过。
……
伊丽莎白王后:如果你做了这个国家的国王,大人,可别以为会得到什么欢乐——我是这个国家的王后,你该料到我就没有快活过。
玛格莱特王后:(旁白)做王后有什么欢乐可言?我也是王后,却根本没有快乐过。[1]292, 294
和亨利六世的看法如出一辙,这两位王后也认为权力并没有为她们的生活带来欢乐。并且在玛格莱特对伊丽莎白的诅咒应验后,权力本身所包含的不稳定性、幻灭性被玛格莱特如实地揭示了出来:
我说你被抬得很高准会摔得很痛……说你的荣华富贵只是一场春梦……当初瞧不起我,如今叫我瞧不起;当初人人怕你,如今战战兢兢;当初发号施令,如今没人理会。正义之路来了个大转弯,把你当做时间的牺牲品扔了下来。除了对往昔荣华的回忆,如今你已一无所有……你篡夺了我的后位,你不也篡夺了跟我同样多的痛苦?[1]363
伊丽莎白与玛格莱特的命运大体相同,她的孩子被篡权者杀害,自己也沦为了王权争夺的牺牲品。这些曾经登顶权力之巅的人体会到了登高跌重的失落感,也深感王权难以把握的虚幻性。就像布莱肯伯雷总结的那样:“王公大人的荣耀不过是区区头衔,表面的显赫只带来内心的纷扰。为了那并无实感的种种想象,他们往往要经历许多忧患,寝食难安。”[1]302因此,莎士比亚在剧中力图使观众警惕王权的另一层面目:与荣耀、头衔、权力相匹配的是它的易碎性和破灭性。如果只是单单将王权视作自己追名逐利的欲望,那么只会陷入堕落与虚无;如果没有与之相匹配的驾驭能力,王权终究会沦为反噬其自身的灾难。而这就牵涉到王权的正当性及其存续问题。
理查的毁灭无疑与上述情况密不可分:王权对他来说只是实现统治者欲望的工具,其实他并不具备优秀统治者应有的素养。王位继承的合法性是莎士比亚在剧中抛出的一个重要思考:王权的长远发展究竟基于何种要素?是纯正的血统、竞争者的欲求抑或继承人的品行?显然,血统决定论在莎士比亚笔下并不可行。理查为了建构自己的合法继承人身份,故意否定爱德华四世儿子们的血统,称他们为私生子,是爱德华在“重婚”⑥情况下所生的不合法产物。可见,血统纯正与否同王位继承的关系在错综复杂的时势背景下很难找到准确的定论,并且极易被有心之人虚构和篡改。而继承的正义性就更难评判了,蒂利亚德曾说:“对抗正在统治的君主是个可怕的错误,而理查是被加冕的君王。然而,他显然是个篡位者和杀人者,因此可以定性为暴君,针对真正的暴君的造反是合法的。”[5]237但此说存在的一点偏颇是,自理查二世篡位开始,理查三世、亨利七世等都是依靠杀人而得到王位的,如果从理查三世的角度看,里士满显然也是篡位者和杀人者,那么一样担着杀人嫌疑的里士满称王就有绝对的正义性吗?因此,面对血统论和正义性的难以辩解,莎士比亚意图将王位继承的考核重心放在继承人的品行上。
通过莎士比亚的塑造,理查与里士满的品行高下立见。“国王(里士满)和暴君(理查)的差别就在于‘前者以法律为其权力范围,以公共福祉为其统治目的,而后者则使一切都服从于其意志和愿望’。”[6]70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理查对权力的欲求大于权力本身,也就是说,他只希望从王冠中得到能掌控一切的主导地位,而拒绝接受王权中最核心的责任与使命感。与里士满求娶伊丽莎白是为了联合两大家族、平息矛盾、求得和平不同,理查则说:“我一定要跟我哥哥的女儿结婚,否则我的王国便无异于建立在易碎的玻璃之上。”[1]355理查疯狂游说伊丽莎白王后,想娶她女儿的动机并不是为了缔结和平、服务于公共的善,而是为了能够继续享有稳固的君主地位。
在后来的阵前演讲中,里士满和理查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里士满演讲时对众人的称呼是“亲爱的同胞们”,和安东尼一样,他们在最开始都将自己放置于与大众平等的位置,并不居高自傲。接着,里士满阐述了他们铲除暴君的合理性与正义性,还承诺如果行动失败愿以死谢罪,如果事成,他将不论高低贵贱统一为下属们平分荣誉与战利品。理查则十分轻敌,他沉迷于自己国王的名号中,认为“国王的威名就是力量的堡垒,而那是叛军所没有的”[1]381不仅称对手为流氓、痞子、逃兵、跟班、乡巴佬,而且没有给予士兵任何正向的奖励,只是利用他们对叛军的恐惧鼓舞其作战。作为君主的理查,全然罔顾政治伦理,将自己的欲望和意志作为行动的最高准则。他自以为是,因白金汉没有果断答应替他杀害小王子就将功臣冷落;他任性妄为,承诺给白金汉的奖赏只因一句“我现在不高兴给人赏赐”(第四幕第二场)就草草了事;他尽失人心,几乎所有亲信都对其倒戈相向;他阴鸷多疑,将斯坦利的儿子扣为人质逼他效忠……显然,这个完全违背道德的暴君根本不具备莎士比亚心中理想君主的条件,他不像裘力斯·凯撒那样拥有帝国雄心和超越自我的荣誉追求,也不像里士满那样将国家视作政治共同体并将其作为君主的统治目标,他只是一个丧失政治德性的利己主义者。因此,莎士比亚或许意在为观众揭示,血统的正统性和继承的正当性固然应该包含在王位继承的考量标准内,但对君主品行和德性的塑造才是王权能够稳固持存的核心要素。
四、结语
公爵夫人曾说:“我已哀悼过一个杰出的丈夫,守望着他留下的几个影子度日,但如今,反映他杰出风范的两面镜子偏又让恶毒的死亡砸了个粉碎,只留下一面不像他的镜子勉强自慰。但我在他身上却只看到耻辱,心中感到伤悲。”[1]314这是镜子与影子的比喻最后一次出现在理查形象的描述中。公爵夫人的哀叹并不直接反映理查形象的变化,莎士比亚在此是用他者视角说明理查人生目标的盲目性和虚幻性。当约克死于夺权之路后,理查、爱德华和克莱伦斯就被公爵夫人当作约克的“影子”,但反映约克杰出风范的两面镜子则只代表了保有伦理底线的爱德华和惨遭理查杀害的克莱伦斯,在理查这个“影子”身上,公爵夫人并未察觉到类似约克的杰出风范,只看到他身上为了篡权夺势而嗜血成性的累累耻辱。约克和爱德华在称王的过程中都表现出审慎的一面,例如约克起初并不想立即篡位,因为他和亨利定下了盟约:“只要你死后将王位交给我和我的后代,我就让你安安静静地当一辈子国王。”[1]188当爱德华和理查劝他夺权时,约克说:“如果我用战争夺取政权,我就是背信弃义。”[1]192这表明在约克心里还是有信义存在的,王权并不是他追逐的唯一目标。在爱德华第一次称王被废后,他谎称自己满足于公爵身份,欺骗效忠于亨利的市长打开了约克城门。爱德华本来想先遮蔽锋芒养精蓄锐,待时机成熟再称王,但蒙哥马利、理查和黑斯廷斯都认为爱德华不应如此谨小慎微。其实,爱德华内心还是有所忌惮的,在时机还未成熟之前,他愿意“把王位继承的问题暂且搁置起来”[1]249“等我们强大了再提要求”[1]250。换言之,爱德华没有将对王位的欲求时刻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上,他在夺权之路上仍保持着一定的政治理性。反观理查,他一直扮演的都是为了夺取王冠而不顾一切的激进形象,对权力的热切渴求使他从不停歇。哪怕践踏政治伦理、违反政治理性、颠覆道德秩序,理查也一往无前。但是,就像前面所论述的那样,理查一生都在追求权力,但他丝毫没有考虑过怎样才能让权力持续下去,他从未将自己的人生规划置于一个更宏大和长远的背景中去考量,错将称王的短期目标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最终只能变成权力的傀儡。公爵夫人借“影子”与“镜子”之喻哀叹理查的可悲,就如同弗里希所说:“自己孜孜以求的东西却是自己从来都不想要的东西。他只是想当王。他当王的愿望可能仅仅反映了他年轻时对于父亲的希望……理查竭力谋求王位,但随着戏剧的发展,理查很显然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他不了解自己的想法。”[4]135因为人生理想与君主责任的价值错位,理查难以保持个人与君主身份的和谐统一,最终成了反映王权悲剧的一面镜子。
穷凶极恶、贪慕王权、倒行逆施是理查在《亨利六世》(下)和《理查三世》中一以贯之的性格底色,而表现理查形象演化特征的则是他内心的机敏、对人性的深刻洞察、高超的论辩技巧和全面的掌控能力。但随着理查行动的发展,他富有无限激情的进取精神和上述的优质才能发挥作用于他的人生,呈现出的则是难以扭转的悲剧。理查自认为在镜子中建构的是势如破竹、无往不利的自我,他以为在影子中呈现的是拥有绝对控制权和人生主导权的自我,可莎士比亚通过对王权实质的挖掘和对君主德行的探讨,意在揭露离开道德伦理规范的审美式自我追求必将是虚幻的。就像布鲁姆所说:“不理解道德现象的政治科学是粗鄙的,而不为正义之情所激发的艺术是琐屑的。”[7]理查将人生目标和自我实现全部建立在超脱道德、伦理的欲望之上,他所拥有的必然是一个不完整的灵魂。莎士比亚在为观众呈现他的创作意图与王权之思的同时,个人灵魂的塑造问题也是其历史剧的重要关注。
① 转引自艾布拉姆斯著,郦稚牛、童庆生、张照进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0页、第314页。
② 转引自《莎士比亚笔下的恶魔君主》,见刘小枫、陈少明《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③ 转引自《莎士比亚笔下的恶魔君主》,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④ 此句出于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转引自邹广胜、龚丽可《论理查三世的悲剧心理》,载《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114页。
⑤ 此句出于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转引自邹广胜、龚丽可《论理查三世的悲剧心理》,载《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115页。
⑥ 详见《理查三世》第二幕第七场,据白金汉说,爱德华四世曾与露茜小姐有过婚约,后来又和法国公主波娜订了婚,之后爱德华爱上了现在的伊丽莎白,不顾前两次婚约的盟誓,毅然将伊丽莎白立为王后。
[1]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M].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2] 宋敏生.纪德的“那喀索斯情结”与自我追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8.
[3] 丁鹏飞.身体的两歧性:《理查三世》悲剧的神学源起[J].国外文学,2018(4):80–88.
[4] 刘小枫,陈少明.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5] 蒂利亚德.莎士比亚的历史剧[M].牟芳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6] 邹羽.战马之喻:《理查三世》、人格国家和莎剧舞台上的政治文化转型[J].外国文学评论,2020(1):60–79.
[7] 布鲁姆,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M].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0.
Metaphor of Mirror and Shadow——Multiple Aspects of Richard's Image in Shakespeare's “Richard III”
LI Ruoqie
(Zheng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Zhengzhou 451161, China)
In, the images of “mirror” and “shadow”, respectively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stages of Richard's inner activities, reveal his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deviationsin his self-construction and goal. This helps the readers to appreciate the essence of tragic of the play. Besides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characters, this play also illustrates Shakespear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kingship.
Shakespeare;; image; evolution; kingship
I106
A
1006–5261(2022)06–0113–09
2022-08-17
李若怯(1989―),男,河南驻马店人,助教,硕士。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