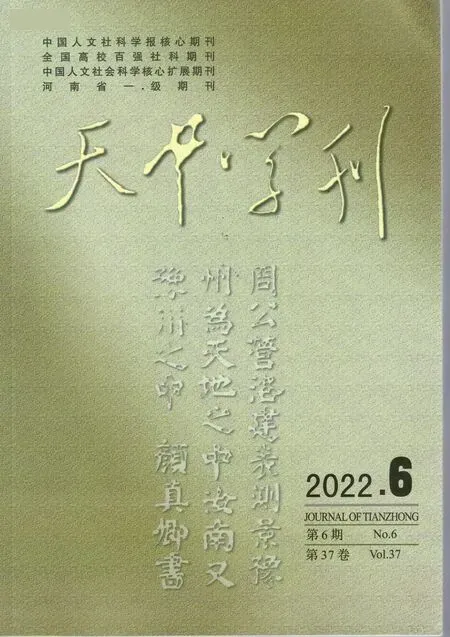文学主体回归与灾难镜像再现——论“文学豫军”灾难叙事的转向
2022-03-23段永建
段永建
文学主体回归与灾难镜像再现——论“文学豫军”灾难叙事的转向
段永建
(黄淮学院 文化传媒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文学豫军”的灾难书写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主要呈现出秉笔直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定胜天的灾难意识;在新时期则表现出以多元杂糅的手法对灾难生成原因的探究以及对灾难发生的反思与批判;进入21世纪,灾难叙事表现出由单一现实主义向多元杂糅、由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由人定胜天思想向生态意识转变的诗学特征。“文学豫军”的灾难叙事,不仅再现了创作主体心路历程及其艺术风格的流变,而且还勾勒出当下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变化及内在机理的表征。
灾难;转向;叙事;文学豫军
灾难指因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造成的苦难。河南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社会动乱、战争赓续、水旱蝗汤、饥馑灾荒等各种灾难轮番上演的至暗时刻。“文学豫军”[1–2]作为一个富有创作力的作家群体,自然不会放弃对各种灾难的书写,他们在沿承灾难叙事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以新的叙事策略表达对灾难新的省思。当代文学时期“文学豫军”的灾难书写有三次较为明显的转向,每一次转向都呈现出“文学豫军”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贡献。
一、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
“十七年”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书写的规约,使自然灾害无法或很少能够像现代文学时期那样进入主流题材的书写行列,即使有的作品偶有涉及灾难,也基本上是为了表现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在这种情形下,灾难往往被视为挑战与征服的对象,涉及灾难的文学作品往往被看作适应主流意识形态的应景之作,如申跃中的《一盏旱灯下》、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陈登科的《风雷》等作品基本都遵循人定胜天的叙事模式。这些作品中的灾难成为检视人民内部思想倾向和政治路线的标尺。在此种语境下,“文学豫军”的灾难书写呈现出某些同质化的特征,即无论是对灾难历史的还原抑或是对灾难现实的审美再现,它们叙事的重心基本上已从刻画灾难给民众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转变为对民众战胜灾难的勇气和行为的礼赞,而对普通人罹受灾难的内心世界与心理创伤则缺少应有的关注与书写。这种创作倾向导致灾难叙事呈现出“跟风与应景”的叙事策略,进而把灾难叙事演绎为国家宏大叙事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
在此语境下,“文学豫军”在关涉灾难的文学叙事中也很难摆脱其规训,如李准的《耕云记》《大河奔流》、王绶青《野狼沟》等作品借助自然灾害对“合作化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翻天覆地变化的书写,基本都是配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对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变化、新气象等的歌颂。由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龙山惊雷》描写了1964年某煤矿支部书记黎海峰带领突击队和隐藏的阶级敌人做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但矿工井下工作的危险性和生活的艰辛性被有意遮蔽,更遑论对“后灾难”时期矿难家属的精神创伤和举步维艰的生活窘况进行细致描写与刻画了。作品中“北风怒吼,大雪纷飞。一股股被狂风卷起的雪浪,好像一匹匹巨大的野兽,从后山的顶峰吼叫着,奔腾着,冲向龙山矿区。矿井扇风机的响声,一下子被这大风雪的吼叫声淹没了”[3]等恶劣环境的刻画,成了渲染工人不畏艰险、大干快上工作情景的陪衬与烘托。李明性的长篇小说《洪流滚滚》主要叙写了以郭长河、田涛等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英雄粉碎阶级敌人阴谋而成功治理水患的故事,小说中不同阶级路线之间的斗争是情节发展、矛盾冲突和人物成长的关键点,而洪灾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灾害带给人们的心理创伤则被有意弱化。冯金堂的《黄水传》以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①为主要背景,刻画了黄泛区人民在惨绝人寰的黄河水灾中艰难求生的顽强意志。白危的《垦荒曲》作为当代文坛第一部反映农垦生活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耕队在黄泛区内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各种自然灾害、齐心协力挫败阶级敌人的暗中破坏最终建立起集体农场的曲折过程。刘锡年、李树修的戏剧《人欢马叫》描写了自然灾害导致大量牲畜死亡,吴广兴主动请缨做饲养员并通过教育使思想落后的刘自得“幡然醒悟”,最终形成“人欢马叫”大团圆结局的故事。阎豫昌的散文《嵩山朝霞》写主人公来到嵩山峰顶的气象站,目睹了站长在艰苦环境中任劳任怨一干就是十多年的工作热情,最终克服心理障碍而一心扑到气象事业上,最后成长为优秀气象员的故事。华山的《劈山太行侧》作为抒写林县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在太行山上修建红旗渠的壮丽史诗,不仅回顾了林县缺水的历史,更写出了林县人民在修筑红旗渠战胜旱灾时“但得流水村前过,我敢砸碎崖头闹翻天!”“到山西去,把漳河水硬赶过来”的雄心壮志。可见,“十七年”时期“文学豫军”的作品基本都把灾难作为建构人物形象、见证人物性格转变的背景和砥砺新人成长的试金石与助推器,在这些作品中灾难往往成为作家借助恶劣环境凸显人物心理状态和精神底色的铺垫。换言之,灾难往往成为创作主体演绎当时革命群众战胜自然灾害、表达乐观主义精神的“装置”。
在那个特定时代语境下,灾难叙事一般聚焦社会热点或焦点问题,在作品中形塑出具有高度概括性、典型性、完美性的时代新人,他们的高大形象在同自然灾害、落后思想、沉疴重疾等斗争中得以呈现和完成。如《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中焦裕禄为了战胜内涝、风沙、盐碱等严重的灾害,解决大批兰考灾民外出逃荒的严重问题,长期忍着病痛折磨坚持顶着座椅把手办公,后来竟将藤椅右侧顶出一个窟窿。正是借助于这些细节书写,作家完成了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与天灾人祸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辉形象塑造。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穆青就指出:“我们今天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能否高瞻远瞩地提炼出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主题,并且从这个高度来表现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和思想风貌,就成为决定人物通讯成败、优劣的关键。”[4]穆青的这一观点不仅在焦裕禄身上得以形象演绎,同样也在“文革”时期有关灾难叙写的作品中得到有力印证:《三门峡上锁黄龙》反映了新时代人民改造自然、战天斗地的满腔热情;《力挽狂澜的人:抗洪抢险报告文学集》歌颂了人们在洪灾来临之际不顾生命危险奋勇抗洪的壮举。这些作品与反映红旗渠精神的《重新安排林县山河》《斗天图》《劈山太行侧》等作品一道,共同构成了“十七年”时期人们以人定胜天的革命豪情战胜灾难的亮丽风景。可见,“文学豫军”的灾难叙事不仅歌颂了社会主义新人在灾难面前不怕困难、吃苦耐劳、忠于职守的可贵品质,而且还更形象地演绎了社会主义新人茁壮成长和艰难蜕变的过程。
灾难叙事的旨归之一就是彰显作家自我灾难意识。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综合作用下,人们对灾难所秉持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所以,“文学豫军”在对各种灾难的书写中,自然也会凸显出不同的灾难意识。通过分析“文学豫军”的灾难书写,不难发现他们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主要表现出人定胜天的灾难意识。这种意识影响深远,每每在关涉灾难叙写时便经常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李准的《耕云记》中,肖淑英作为克服种种困难、深入钻研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的成长型代表,在复杂的气象工作面前,面对落后群众对她观测能力的质疑和部分富裕中农对她工作的讽刺、挖苦与打击,她毅然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克服文化水平低的困难,掌握了天气预报的科学方法,并且在一场暴风雨来临之前对极端恶劣天气做出了科学预报,避免了集体财产的重大损失。肖淑英的出现和成长,并非作家的杜撰,而是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当时广大农村经过扫除文盲、普及科学知识,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科学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所以在党的教育、关怀与培养等合力作用下,像肖淑英这样的“新人”才会不断地涌现并茁壮成长。李准的电影剧本《老兵新传》中“老八路”战长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加入了建设北大荒的大军。北大荒生存环境异常艰苦,一夜风雪能把人和房子都埋在下面,黑夜不仅有豺狼虎豹吃人,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打劫,但是老战和战友们却克服重重困难,在这里兴办起新中国第一个国营农场。支撑他们战胜恶劣自然条件的力量源自“为了革命,一切困难都会在我们面前屈服,越是困难就越光荣”的坚定信念。在华山的《劈山太行侧》中,林县人民克服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三类困难,展现出“问石头要水!问石头要粮”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他们以“人体截流”“飞崖劈山”“飞架渡槽”的“超人”模式开启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壮举。在王绶青和李洪程的叙事长诗《斗天图》中,林县人民在修渠过程中不仅没有被“挖旱池,天不给水;打水井,地不给水;修水库,河不给水”的恶劣环境吓倒,反而充满了战胜各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正如主人公钟源有所说:“大山不挡愚公路,险峰不遮愚公眼,困难不屈愚公志,重担不卸愚公肩,同志们,关山前,要踏稳每一个步点,险峰上,要走稳革命路线!”[5]144–145作品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6]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之所以被形象演绎,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在作品中把“要斗个帚到尘灰除,要斗个水清石头出,咱不只为斗成一条愚公渠,咱要为社会主义江山斗千秋”[5]275的豪情壮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白危的《垦荒曲》也同样描写了解放初期共产党员赵辛田,带领机耕队在黄泛区荒凉辽阔的土地上坚决贯彻党的方针,克服种种困难、战胜各种灾害,最后把偏僻荒凉的黄泛区变成物美粮丰的国营农场的故事。在这些作品中,无论面对多么恶劣的自然灾害,主人公都能够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在与各种自然灾害艰难困苦的斗争中,他们成长为建设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无所不能的“新人”。更为重要的是,此类作品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还突显了人民公社作为国家集体的代表在战胜自然灾害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不争事实。正如《耕云播雨》所描写:“过去天难人,如今人管天,人民公社力量大,管风管雨管自然。”[7]由此可见,人定胜天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灾难叙事中被不同人物形象予以生动的呈现、演绎与诠释。
“文革”时期,文学创作的标准依然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三突出”“主题先行”等思想的延续,这些创作上的“清规戒律”自然也给当时“文学豫军”的灾难叙事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烙印,所以,“抓革命、促生产”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主旨意蕴也就在那个时期的作品中被反复描摹与凸显。在以《斗天图》为代表的作品中才会有“与天斗/与地斗/斗鬼魅、斗帝修、斗出千里愚公渠、斗出百万红旗手”等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这种人类战胜自然灾难的乐观精神和豪迈气概,不仅在李准、华山、李洪程、冯金堂等现当代作家笔下有鲜活的表现,而且早在中原地区的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和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历史文脉中都有着深厚积淀,只不过在“十七年”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峰值。
“十七年”时期的灾难叙事有的再现了波澜壮阔的辉煌革命历程,有的集中展示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成就,有的形塑出抗灾、救灾、治灾过程中的英雄人物,有的通过灾难叙事达到弘扬主流思想的旨归……这些灾难叙事的侧重点不尽相同,而且其形象的真实性、生动性、丰满性和生动性也各不相同,其叙事也大多按照人定胜天的思想来组织与表现灾难题材,甚至“绝大多数都难逃其时政治形势的裹挟,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带有伪浪漫主义的色彩”[8],但它们对认识和还原那个特定年代的生活历史真相,了解和感受当时的世道人心,仍具有积极的管窥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多元杂糅与文化省思
进入新时期,伴随着文学主体性的回归和创作语境的日益改善,河南历史上众多的疾病、瘟疫、洪涝、干旱、矿难等灾害不仅为作家的灾害叙事提供了现实基础,而且为作家丰富灾难叙事的主旨意蕴、拓宽灾难叙事的表达方式、深化社会公众对灾难的认知提供了新的可能。“文学豫军”的灾难叙事也逐渐走出以“文革”为背景的“伤痕文学”藩篱,形成以自我记忆为中心、凸显作家主体精神的范式。新时期“文学豫军”在灾难叙事和灾难意识方面表现出日益多样化的态势,在灾难叙事中着力凸显生命主体的心理悸动,在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中深度反思灾难给人类造成的心理创伤。梁鸿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中以“非虚构”[9]的方式叙写日常生活灾难。作品中农民工在灾难面前的迷茫感、失根感和无助感被作家以“非虚构”的方式展现出来。作家在对打工者“金的非正常死亡”“小柱之死”等不幸遭遇叙写时都饱含着深厚的悲悯之情。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中,“三姓村”村民在身患“喉堵症”后,仍然试图通过土地交换、出卖肉体、卖皮等措施筹集资金修渠引水以破解活不过40岁的魔咒。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却能够给受众以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效果的生成与阎连科所倡导的“神实主义”[10]不无关联。伊丽莎白·鲍温曾说:“小说是一篇臆造的故事……真实于读者所了解的生活,或者,也可能真实于读者感到该是什么样子的生活。”[11]可见,作品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家主体和读者受众的内心感受。正是基于这一点,作家写作的重心应聚焦于对现实与灵魂关系的探勘和对社会生活荒诞性的揭示上,而这一点在阎连科采用“神实主义”方式对疾病灾难的书写中得到了很好的佐证。
战争自古以来就以巨大的杀伤力与破坏性成为人类的灾难梦魇,众多文学作品的战争叙事多聚焦于血腥与暴力,墨白的小说《失踪》则采用先锋叙事的方式进行创作,虽然作品主要情节写的是日本侵华战争,但却把故事重心放在对延庆寺《大藏经》经板文化寓意的深刻揭示上。在作品中,日本兵为掠夺经板来到延庆寺大开杀戒,觉生和尚在目睹了师父三藏法师引日本兵进沼泽、许木匠因焚毁经板和戴着面具的颍河镇人被日本兵惨杀之后,复仇的正义感逐渐战胜了内心的恐惧,最终他选择为保护经板与日本兵同归于尽。小说一方面通过觉生和尚的性格成长实现其生命意义的升华和救赎;另一方面又通过戴面具的颍河镇人在日本兵刺刀威胁下无所畏惧的呐喊,凸显出“面具”作为颍河镇人原始生命力的隐喻象征意义。同时,作品还赋予经板激活人们原始生命活力、给人带来超越苦难、对抗软弱的力量寓指。在作品中,“面具”“经板”“苍茫的沼泽”“庄严的古刹”等意象构成巨大的悖论张力,预示出中华民族顽强生命力对中原糟粕文化旧有“阉寺性”的冲击。显然,《失踪》以抗战为背景,借助面具的文化寓意完成了对人之原始生命力的激活与救赎。该作品要彰显的不仅是战争单纯的胜负观和战争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时它还更是一种无比强大的生命意识和文化力量的释放。结合墨白的《梦游症患者》《霍乱》等其他描写疾病灾难的作品可以看出,墨白对各种形而下灾难更喜好采用形而上的书写方式,此种文体“有意味形式”的自觉追求表明他在创作中更倾向借助先锋的形式抒发对现实生活深度意义的感知与体悟。由此可见,墨白在先锋主义的外衣下,包裹的是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无独有偶的是,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以1942至1943年河南历史上“饿死了约500万人”,甚至“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12]惨剧的大饥荒为背景,为我们再现了1942年的那段饥馑岁月。该作品在叙事策略上更多侧重于对灾害意义的消解和对历史的反讽,以往灾难叙事中的苦难意识被大大削弱,历史的宏大性与庄严性也被有意淡化和消解。同样是面对自然灾难,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则以赤阳岗村李麦、王跑、蓝五等人的流亡史、逃荒史、抗争史和奋斗史为线索,既写出了1938年国民党当局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坝阻滞日军南下行为的荒谬,又表现出了国人在灾难面前所具有的自强不息、无私担当、牺牲奉献、互帮互助、人道关怀等优秀品格,体现了作家力图通过作品寻找中华民族抵御灾难的意志力、生命力和凝聚力的精神之源与文化之根的鹄的,而海长松、海春义、海老清等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传统痼疾、保守意识和宗法思想的局限性也同时被形象化地予以呈现,从而实现了作家要通过《黄河东流去》“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13]的创作旨归。
从梁宏的“非虚构”、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墨白的先锋叙事到刘震云的“新历史主义”和李准借助黄河水灾对中原文化的书写可以看出,与以往灾难叙事侧重原生态的灾难记录不同,“文学豫军”的灾难书写已不仅仅聚焦于对灾难历史的显影,更多的则是通过对抗衡灾难意志的开掘来彰显文本的多重意蕴。在这一潮流中,李准《黄河东流去》不仅反思了中原人的“侉子性”,而且考量了中华民族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抗衡灾难的毅力与韧性;刘庆邦的《黄泥地》指出了河南人在抗衡灾难中所具有的“泥性”特征;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故乡相处流传》等作品表现出对灾难庄严性与悲伤性的消解与解构;阎连科的《日熄》《年月日》《耙耧天歌》《日光流年》等作品着力叙写了生命力在各种灾难面前呈现出的顽强性与坚韧性。从“文学豫军”这一系列的灾难叙事中,不难管窥他们灾难叙事的向度已从对宏大意识的有意迎合逐渐转到对灾难背后文化寓旨的深度开掘上。
事实上,灾难的发生不仅有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更有不可推卸的人为原因和文化痼疾。如果说《黄河东流去》通过黄河水灾从正面写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那么“文学豫军”很多灾难叙事则从另一侧面形塑出灾难降临时人性的精神痈疽,甚至认为民众的精神愚钝是造成各种灾难发生的重要推手。刘庆邦《五月榴花》中张成的新婚妻子涂云作为一名战争受害者,被日军捉去受尽凌辱,张成冒着生命危险救出妻子之后,不是安慰与照顾受尽伤害的妻子,而是对她横加折磨,最后当着众人的面把涂云撕成两半。张成之所以对受尽凌辱的妻子痛下杀手,除了妻子失去贞操后成为被乡亲邻里诟病的不贞者,他内心深处隐藏的人性之恶和旧传统中的贞烈观念或许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透过故事表层不难看出,张成在作为一个受害者的同时更是一个凶残的施暴者,而他的施暴与乡土伦理对女性贞操观的苛刻要求不无关联,而对此种陈旧贞操痼疾的抨击与批判,或许才是作家创作《五月榴花》的主要旨归。与《五月榴花》异曲同工的是阎连科的剧本《母亲是条河》,剧中周翠和叶秀各自送丈夫走上战场。后来,周翠的丈夫长生凯旋,而叶秀的丈夫建国却被误认为牺牲。出于战友之情,长生自觉承担起照顾叶秀的义务,但日久生情,两人冲破道德防线生下儿子宝军。这时候建国意外回来,但他不仅没有接受宝军反而陷害叶秀使其进了监狱,而周翠不仅视宝军为己出,而且还含辛茹苦地把他培养成留美的科学家。作家通过叶秀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周翠无私抚养“情敌”儿子的感人情节,表达了他对女性追求美好爱情的果敢行为的颂扬,而对战争的血腥与暴力则采取了淡而化之的处理策略。显然,与以往战争叙事比较而言,《五月榴花》《母亲是条河》等作品均已不再局限于对战争杀戮性、血腥性、毁灭性的直观呈现,更多体现为在战争背景下对封建文化糟粕的批判和揭示。很多情况下,正是人与人之间虚与委蛇的瞒和骗,才滋生出嫉妒、仇恨、报复、猜忌等灾难发生的诱因,从而导致各种人为灾难的发生。阎连科《丁庄梦》里的“二叔”表面上为了不把热病传染给二婶,假装要搬到学校去住,并且交代二婶在他死后要及早带着孩子改嫁,暗地里却对爹说在他死后一定要想法把媳妇与孙子留住,人性的虚伪在此被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由此可见,“文学豫军”对瘟疫、饥馑、灾荒等灾难的描写,不仅以直面灾难现实的姿态丰富了灾难叙事中的文化意蕴,而且显示出创作主体凸显灾难叙事之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追求。
三、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
进入21世纪,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环境污染、自然灾害和瘟疫等频繁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中,现实生活中的灾难症候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叙事空间。就灾难叙事而言,“文学豫军”在承继以往文学传统的同时,不再停留在对灾难事件的表层回忆和形象再现上,而是更多地以日常生活中的灾难事件为背景,着力于对灾难发生后人们自身命运的思考以及对人内在精神的关注。如乔叶在《认罪书》中借助“文革”创伤和疾病表达了对人忏悔意识的呼唤;张一弓《远去的驿站》借助战争抒发了对人不可抗拒的宿命的慨叹;李洱的《花腔》把战争灾难的血雨腥风和刀光剑影转化为历史就是一部“花腔”的背景幕布,通过白圣韬、赵耀庆和范继槐等来自不同党派、阶层、身份的人对在二里岗战斗中生死未卜的葛任命运的扑朔迷离讲述,形象演绎了“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就像个小姑娘,你把她打扮成什么样子,她就是什么样子”等虚无历史观,战争对人肉体的伤害、生命的荼毒和精神的创伤在此都被作家有意淡化和遮蔽,历史的不确定性借助战争灾难的背景再次被有意放大和逼真细化。
毕淑敏说:“人类和病毒的博弈,永无止息。如果我在这厮杀中被击中,那不是个人的过失,而是人类面临大困境的小证据。”[14]这是毕淑敏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瘟疫所做出的慎重省思,她提醒我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时候,不能只是怨天尤人,而应更多地反观自我,在人类自身的行为上寻找诱因。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除了自然界中不可抗拒的天灾,很多灾难则是由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以及现代科技对人的异化等“人祸”导致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下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科技异化已经危及人类的安危。对此,“文学豫军”也以文学的方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傅爱毛的《电脑时代的爱情》反映了科技在带给人类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造成了严重的异化。小说中一款名叫“爱情ABC”的软件将人的恋爱行为完全“数码化、程序化、自动化”[15]。众所周知,爱情作为人类亘古不变的美好情感是外物不能取代的,但当人类两情相悦的唯美情感也要依靠电脑程序生成时又是多么可怕和荒诞,所以当主人公按照程序软件设计并获取电脑爱情时,他也就失去了切身体验美好爱情的机会。周大新《步出密林》讲述了早先的沙湾村人与猴子在森林中和谐相处,随后的旱灾和天火让人与猴在逃难途中结成“命运共同体”,后来沙家受利益驱动让猴子演“猴戏”,人猴矛盾由此而生,最后女主人公荀儿将猴子放归森林不再把它当作赚钱工具,而是办起面粉加工作坊开启新的生活。很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人放弃物欲追求而“复归返自然”的故事,旨在告诫人们切勿为了贪欲做出违背自然规律之事。墨白的《鼠王》则讲述了“捕鼠王”将要把“老鼠王”捕获之际,成千上万只老鼠为了救出它们的“领袖”不顾生命危险冲向“捕鼠王”,“捕鼠王”性命危在旦夕,而当“老鼠王”成功逃脱之时,老鼠也停止了对“捕鼠王”的攻击,两个“鼠王”之间的战争也随之结束。这个故事显然在告诫人们:人和动物只有和谐相处才能生存下去,当一方想伤害另一方时,另一方的反抗也会给自己造成最大的伤害,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生存观由此被形象演绎。无独有偶,阎连科《丁庄梦》中丁庄人因物欲膨胀不断卖血而引起的艾滋病大爆发,也同样说明过度的欲望奢求正在挤压人类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间。
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和工业生产模式,正改变着自然界的状况和人的思想观念,而人是万物之灵长的理念也同样在不断强化与昭示着人对自然索取与征服的无限可能,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导致了一系列灾难的发生。在刘庆邦的《红煤》中,由于过度追求利益价值而对煤矿长期过度开采,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透水事故发生。可见,灾难叙事从生态主题的向度对社会现代化进程所进行的反思,在幽微洞察了千百年来农耕文明逐渐消逝的同时,也见证了“当代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社会转型语境的具象”[16]47–52。故而说,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与科技更新,灾难叙事不再是单纯的灾难描摹和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旨归的文学想象,它逐渐向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主题转型,这种转型伴随着人的生态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耦合而生成,其内容除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还涵盖了忧患意识、敬畏自然、悲悯情怀、反省自我等一系列思想内涵。
“文学豫军”将人在灾难面前的遭际作为审思人性的主要路径之一,并对之予以形象描摹和鲜活刻画,既形象地揭示出人在各种利益欲望面前的异化现象,又自洽地切入当下现实生活细部,认真考量灾难叙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以及人们对利益的无止境追求,特别是人在灾难面前的自私、冷漠和无所作为等一系列不当行为,在表现自然灾害“自然性”一面的同时,更形象地诠释了人类种种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才是导致各种灾难最终发生的不争事实。诚如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思特指出:“人类是其周围世界的一部分,既不优越于其他物种,也不能不受大自然的制约。”[17]深究自然界中各类灾难发生的原因,“人类的生产模式和人类的意识价值观对自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点”[16]5。可见,现代社会和工具理性的发展作为一柄双刃剑,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同样有可能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事实证明,如果现代工业发展不能保证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那么工业化进程不仅未必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会滋生出一系列后遗症!可见,“文学豫军”对生态灾难的书写,不仅是当前生态问题的文学反映,更是深化与提升社会公众对自然灾难的认知、反映作家社会担当的一种自觉选择。
“文学豫军”的灾难书写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主要呈现出秉笔直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定胜天的灾难意识,在“新时期”则表现出对灾难生成原因的探究以及对灾难的反思与批判,进入21世纪,灾难叙事表现出由单一现实主义向多元杂糅、由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由人定胜天思想向生态意识转变的诗学特征。“文学豫军”的灾难叙事,不仅是创作主体心路历程和灾难叙事流变轨迹的再现,更是勾勒当下社会生活变化细部和内在机理的表征。
① “黄河花园口决堤”是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本军队沿陇海铁路西进,准备夺取郑州后,再经平汉铁路南下而造成的,当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军事效果,却给河南、江苏与安徽三省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改变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自然面貌,在苏北、皖北与豫东地区造成了一个包括44个县在内的5.4万多平方公里的黄河泛滥区。黄河水在当地持续为灾9年,89万人因此丧命。
[1] 孙荪.文学豫军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1–6.
[2] 孙荪.文学豫军论(续)[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15–24.
[3] 平学庆:龙山惊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169.
[4] 穆青.新闻散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173–174.
[5] 王绶青,李洪程.斗天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
[7] 李准.耕云播雨[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0:1.
[8] 张鸿生.河南文学史:当代卷[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1:118.
[9] 陈剑晖.近年散文话语的转换及新变:以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为观察点[J].文学评论,2022(1):188–196.
[10] 阎连科.当代文学中的“神实主义”写作: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J].东吴学术,2011(2):18–25.
[11] 鲍温.小说家的技巧[G]//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2.
[12] 睢城.1942年河南大饥荒纪实[J].档案时空,2013(3):9–14.
[13] 王雨海.李准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27.
[14] 毕淑敏.假如我得了非典[J].中国保安,2003(7):58.
[15] 傅爱毛.电脑时代的爱情[J].青年文学,2000(11):54.
[16] 黄轶.由格非《望春风》谈新世纪乡土文学的精神面向[J].扬子江评论,2019(5):47–52.
[17] 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侯文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
I207.42
A
1006–5261(2022)06–0105–08
2022-04-2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ZW027);2021年度河南省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1JGLX112);2022年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2022-JSJYZD-052)
段永建(1972―),男,河南上蔡人,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