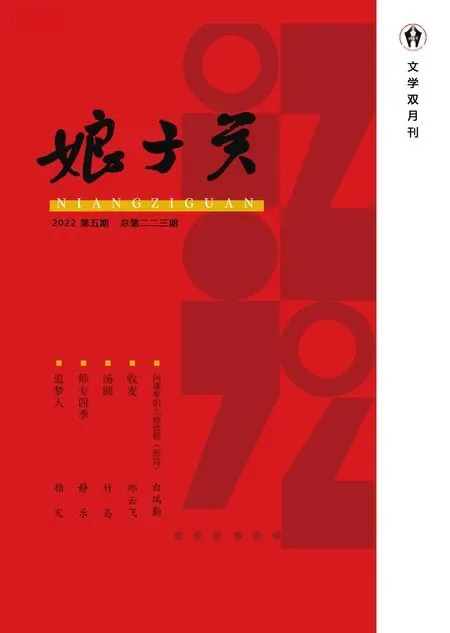老屋里的家族记忆
2022-03-22张迎
◇张迎
很多年前,这座房子便坐落在这里。它是名副其实的土坯房,母亲在这座房子里相识了父亲,姐姐和我在它的襁褓中诞生。多少年过去了,它依旧坐落在村子里,即便周围的老屋一座座倒塌,数以百计的新房在它的四周巍然矗立,它依旧安安静静守望在那处原来的角落。
七八岁的年龄,我总爱出去玩。每次归家,我总能在老屋门前的那条长长的巷子里看到红砖垒砌成的烟囱冒着蒸腾的白烟。我知道母亲一定在堆满干柴的厨房里做起了晚饭。我推开黑漆染成的木门,踏上像乡间土路一样的院子,跑进厨房里,开口便问母亲今晚吃什么。大多数时候,母亲都会带着一种半严肃半玩笑的腔调说我是一条馋虫,一个只知道吃的熊孩子。由于厨房里的白烟飘得满屋子都是,母亲总关切地要求我到厨房外面去。我便蹲在老屋院子里静静看着放柴的炉口里冒出的黄亮色火焰,甚至仔细倾听火焰与干柴之间交汇而成的“噼啪”声。在我看来,这种响声是非比寻常的,它们其实是两支军队在战场上厮杀,双方都拿出顶厉害的武器互相咬牙切齿地争斗。那“噼啪”的声音便是双方武器交锋时产生的惊心动魄的回荡。母亲见我目光呆滞,总要呵斥我一番,说我巴掌大的孩子想什么破事。于是,我的想象力就在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风雨里消散殆尽。年关的时候,我对母亲做的花馒头着了魔,母亲和成面团,再把面团揉成长柱子,拿刀将它切成一块一块的,接着用擀面杖将其捻薄,使其成为一个个平面型的圆,然后再用刀在圆圈外围切一圈占半径三分之一的线条,之后用手捏成形似花瓣的形状,等整个圆外围切割的线条都被均匀地捏造成一个个花瓣的时候,一朵花就呈现出来。母亲会在花瓣与花瓣的间隙当中放上一个又一个红枣,之后继续累加花朵,不过上层的花朵总要比下层的花朵小一些,呈现出依次递减的特征。母亲通常会累加到五层,有的时候会累加到六层,完成体像是一个金光灿灿的小宝塔。可是,大年三十的晚上,过了十二点才能够吃,我往往挨不到那么晚,常常咽着口水沉沉地睡去。有一年,我实在抵不住诱惑,就在母亲蒸熟花馒头不久,趁她不注意,捏了左半边许多大枣吃,那时刚蒸出的花馒头还很热,我抑制住滚烫的热气硬是没出声的吃完了它们。第二天母亲从祭神的灵台上拿下花馒头的时候,还以为是被老鼠吃了。后来,母亲从我口中知道了实情,就想了一个法子,临近年关,母亲做了三个年三十晚上放在灵台的花馒头之外,再额外做一个小巧的花馒头,那是给我解馋的。每次手里捧着香气扑鼻的花馒头,我都觉得老屋里点亮起温柔的烛火,给予我安宁。这种感觉就像夏天停电的夜晚,我们一家四口拿出四张板凳和两把蒲扇来到老屋的院落,我和姐姐坐在中间,父亲和母亲一人拿着一把蒲扇为我们扇去闷热的空气和烦扰的蚊虫,我托着腮聚精会神地听着父亲讲三国故事。蟋蟀在某处石缝里歌唱,清脆响亮。我听着听着,便会睡在母亲的怀抱里,父亲会把我抱起来,走进老屋的襁褓中,轻轻缓缓地将我放在床铺上。
村子里的青壮年男性都开始陆陆续续外出打工,父亲却是一个不愿意外出的异类。母亲脾气急,总是大骂父亲是头懒驴,天天只知道守着几分烂庄稼地过活,一年到头不知道能挣几个钱,到头来连两个孩子的学费都挣不出。父亲闷声闷气地坐在屋子里抽旱烟,母亲没好气地站在院子里一边喂鸡一边言辞激烈地说着实情。可父亲依旧无动于衷,只是眉目紧缩,抽完了旱烟再自个儿卷上一支接着抽,他的目光始终不在母亲身上,而是时常看看脚下衍生出的一条有细长裂缝的水泥地,有时还会打量屋子里挂在墙壁上的摆钟,抑或是瞧一瞧贴在墙上的明星挂历。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能猜到接下来母亲破口大骂,甚至动起手脚的情形。是的,我的预感几乎没有失算过,我总能听见母亲尖锐暴躁的呼喊和痛骂,甚至把碗筷扔在地上碎裂的声音。而一向闭口不言的父亲最终也会丧失耐性,与母亲激烈地争辩起来。他们最终会扭打在一起,互相撕扯着对方的衣服,全然不顾及模样的好坏。尚且年幼的我,心中十分恐惧,只能来到院子里,尽可能把身体缩到距离父母最远的角落中去,毫无目的地捡拾起一块块细小的石子把它们垒砌成一座座小山,又从中拿起较为尖细的,在有些湿润的泥土里划来划去。雀鸟常常会停靠在屋檐上歪着脑袋左右打量着我的异常举动,我很想扔几块石子好好教训一下它们,但怯于父母的争吵,只能象征性地吓唬它们几下。刚开始,它们还会配合地飞去,后来便知道了我的伎俩,依旧如故了。没有可以继续玩下去的东西,我的目光会停留在老屋的身上,一左一右两扇正方形的窗户像是两只目光如炬的眼睛,高高的房门又好像一台电视机,父母正在热情地尽职地表演着,他们的演技堪称完美,在我魔幻迷离的眼神中就像是真的一样。
我畏惧父亲和母亲,却是不害怕姐姐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姐姐已经上初中,周一到周五她要留校我是见不到她的。只有周六的一整天和周日的一上午我才能够在老屋里见到她。姐姐的性格跟父亲挺像,是一个文静的人。再加上她学习刻苦,所以我每次见到她,她都是把自己安置在里屋看书和学习。我总会装作学习的样子倒捧着一本语文课本,滔滔不绝地在她身边背起早在幼儿园就会背诵的《咏鹅》与《静夜思》。刚开始,姐姐根本不理睬,确切地说,跟我没来的时候完全一个样子。我便加大嗓门,加快语速,贴近她的耳朵哗啦哗啦地把我的声音强制性地往她的耳朵里塞。这个时候,姐姐会微微皱起眉头,回过头来用冷峻的眼神向我发出警告。每当看到她用这样的眼神打量我时,我知道自己的扰乱计划已经开始奏效了,不由得内心窃喜起来。接着,行为越发不可收拾,我会抛弃伪学习的样子,把语文书本卷起来形成一个扩音器,悄咪咪地放在她的耳朵跟前,在她沉浸在书本的时候,“啊”的一声大喝。姐姐整个身子会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我会发出阴谋得逞后的大笑。姐姐揉着耳朵站起来,举起右手直愣愣地指着我,鼻息里喷出十丈高的火焰,说一声“滚一边去”。我见她发了火,便打趣地说她头冒烈火,样子真是难看,怪不得里屋的遮尘布破了,十有八九是被这火气给烧没的。姐姐跺着脚,没好气地训斥我放屁,明明是我小时候拿竹竿捅破的。我便跟姐姐拌嘴,死不承认。姐姐最终辩无可辩,便呼喊母亲。对于姐姐来说,这是她最后的杀手锏也是最有效的武器。我会惊慌失措地喊,好姐姐,你别说了,我这就走。可是姐姐不会罢休,直到喊来母亲。母亲听完实情,便会理所应当地揍我一顿。姐姐看到我灰头土脸,怏怏不乐的样子,便得意扬扬地带着胜利者的骄傲回到里屋去。可能我的恶劣行为跟姐姐结下了梁子,从四年级开始,姐姐便有意无意地打听起我的学习成绩。有一次,我数学考试不及格,老师要求我把试卷带回去把错题改了,并让家长签字。我心想,如果被母亲看到岂不是又要被痛打,便模仿着母亲的字迹签字,然而字迹写得确实太难看,根本瞒不过老师,便灵机一动想到姐姐,姐姐问我考了多少分,我说勉强及格,她把试卷拿过去,冷笑一下,问我,五十七分算是勉强及格?我低下了头,但是她到底替我签了字,我十分感激她。后来,我跟姐姐又闹别扭,她喊来母亲把我考试不及格的事情揭露出来,结果我还是没有躲过这份挨打,只是它稍微来迟了一些。这样,因为学习成绩把柄的缘由,我不敢再去惹姐姐的不高兴。姐姐升入大学后,我与她见面的次数减少了许多,由于她有半年时间都住在学校,原本属于她的床铺归了我,老屋里的声响少了许多,我大休回家的一天半大多是闷在床上睡觉或者看手机,整天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幸好,老屋的窗是打开的,它时常会带进一阵清爽的风,吹乱我的发,敞开我的额头,晾晒我的虚汗。
有一阵,家里因为鼠患严重,母亲向邻居家领养了一只黑猫,这只猫通体黑色,我称它为“黑旋风”。因为我刚刚接触了《水浒传》,知道里面有个厉害人物叫作“黑旋风李逵”的。我虽然叫它“黑旋风”,但这只猫却是一只货真价实的母猫,行为举止也十分优雅。它经常卧在院子的阴凉处安静地打量周围的角角落落,走起路来轻手轻脚的,好像童话故事里公主模样的人物。它甚至定时的用舌头梳理自己的毛发。这样看来,它实在不像是《水浒传》里描述的凶神恶煞的“黑旋风”。我也没见它捉到过老鼠,所以,我走近它的时候,会跟它开玩笑地说:“谁家的贵族小姐阴差阳错地落入世俗凡尘啊。”它会下意识地把头甩在一边,似乎对我的玩笑不甚满意。后来,这只猫怀孕了,没过多长时间在放农具的小屋里生下三只小猫,其中有一只也是通体黑色,其余两只是黑黄两种颜色杂糅在一起。姐姐经常过来照看它,在吃饭的时候还会特意预留出一点饭菜,亲自送给它吃。时间久了,黑猫与姐姐的感情便愈深。姐姐在家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她怀抱着黑猫在院子里看书,黑猫卷成一团,舒舒服服地盘在姐姐的腿上,姐姐一只手拿着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黑猫光亮顺滑的毛发,黑猫会从鼻息里发出惬意的“噜噜”声。我不屑地对姐姐说,也不嫌脏。姐姐笑一笑,说我真是一个毫无品位的人。我心里不服气,就跟她继续拌嘴。在鸡圈里喂食的母亲听见会无奈地说一句:“真是上辈子托生的冤家。”黑猫在姐姐身上伸一个懒腰,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朝姐姐温柔地喵一声。然后看向我,冷冷地瞧一眼。我甩一句,真是沆瀣一气。可惜的是,这只猫后来错吃了老鼠药,死去了。对于姐姐而言,不必细说,她哭了许多次,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在她跟前不敢再提有关黑猫的事,就连猫的字眼都不能提。每次归家,我打量老屋的四周,再也不见黑猫的影子,心里也会升起一股空落落的感觉。我还是会想起那个四月,一只初来乍到的小猫躲在院落的栅栏深处叫个不停,我寻着声音走近,在栅栏深处看到一只闪着泪光的小黑猫。我挥挥手,说,喂,伙计,你出来啊,我们来玩。它听到我的声音往里缩得更紧了些。后来,姐姐从学校回来,我神神道道地告诉她,咱家院子里有只怪物,你小心点。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姐姐竟然把那只怪物抱进了屋子,我有些惊疑,问她,你用什么办法捉到它的。她指指我的心脏,说,用心。我没好气地回复,吹牛。有一时,我听到老屋外的猫叫声,会想起自家的黑猫来,它似乎并没有走远,依旧在老屋院落的某个角落偷偷望着我,或者惬意地躺在屋脊的某页瓦片上懒懒的睡觉。或许某一天,它玩累了,睡足了,便从院落嫩绿的草丛里冲出来,撞进我的怀里,亲昵地蹭蹭我的额头,“喵喵”地叫上两声,好像在说,好久不见,十分想念。
在高中念书那会儿,村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我们相邻的土坯老屋都相应地被拆掉建起了崭新靓丽的水泥房。正赶上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好时候,农村翻新盖房,政府会有相应补贴,所以那一年村子里有七八成的老屋都被拆除重建了。我回到家看到这样的情形,便询问母亲为什么咱们还没有翻盖。母亲没好气地说,你不上学,家里就有钱了,有钱早就盖了。我听出母亲不悦的声音,便没有继续说下去。可能我的话成为导火索,晚上母亲同外地打工的父亲通电话,聊着聊着便谈到翻盖房子的事情上,也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在电话两端吵起来。周六周天这两天母亲的脸上都写满了不快。于是我也很识相地尽量少说话,免得再招来火药箱的炸裂。周天下午,我便背着书包,不声不响地离开家回到学校。可翻新老屋的计划母亲天天挂在嘴边,至少我在她身边的时候,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念叨一两遍。后来,母亲患上重病,辛苦攒下的一点积蓄很快花光了,家里便再没有人提及有关翻新老屋的事。所以一直到现在,老屋还是老屋,它一直都在原来的位置安安静静地矗立着。老屋的周围都是又高又俊的新房,美观气派。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被这虚荣的风气俘虏,极度地厌恶面前可以被称作“破烂不堪的危房”。我多么希望自己有一笔钱,雇几个拆房专家,毫不姑息地砸垮、砸烂这不堪入目的破房子,以此来摆脱不甚体面的外形。然而,毁掉了它,就等于抹去了几十年的家族记忆啊,我的母亲去世在这间老屋里,我的姐姐出嫁在这间老屋里,我一路求学至今何尝不是在这间老屋里取暖?母亲过世后,父亲曾告诉我,他不会再去天南海北打工了,因为他怕老屋院落里生长出野草,担心老屋内成为成群结队老鼠的家,他更担心母亲在老屋荒凉的院落里哭泣。母亲走了,姐姐嫁了,我也只是偶尔驻足停靠在老屋的旁边,现在只剩下父亲还守卫着老屋。我不知道现在的老屋还能存留多久,我也不知道老屋是否像一个百岁的老人那样身心俱疲,毕竟它身上的瓦片时有松动,毕竟它外围的皮肤脱落了一层又一层。我只知道老屋搭建起我与姐姐童年与青春的成长进程,我只知道老屋盘踞着父亲与母亲几十年如一日的柴米油盐。老屋最终把我们一家四口的欢乐、幸福、忧愁、沮丧、哀伤、愤怒、释怀的情绪统统记录在自己的文案里。它没有声音,却能够像一棵树一样静默地观望着属于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个又一个事件,一个又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