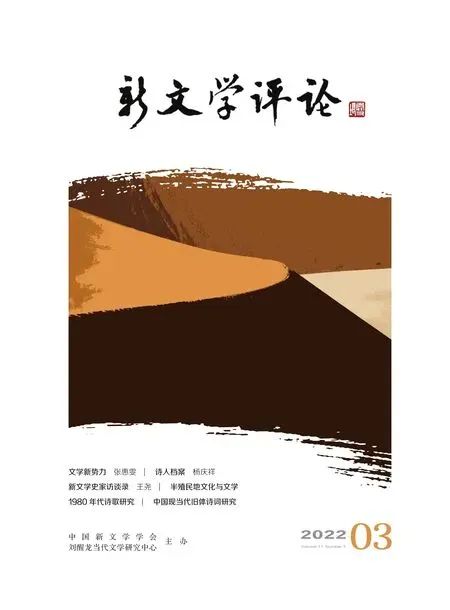张惠雯的叙事才华与善恶观念
——读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
2022-03-22王彬彬
□ 王彬彬
对海外华文文学,我的所知真是少得可怜。当友人向我推荐张惠雯的小说时,我竟十分茫然。上网查了一下,才知张惠雯在新加坡和中国多次获过文学奖,而我却完全不知此人,不免有些羞愧。不久,友人寄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张惠雯小说集《两次相遇》,我便认真地读起来。小说集中的第一篇是《爱》,说是小说,散文的意味十分浓郁,或者说,干脆是一首散文诗。这让人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某些篇章:没有像样的故事,没有出人意料的情节,也没有多少独特的情思。小说叙述的是边地牧区一个外来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与当地的一个牧民家姑娘朦胧的并未开始的爱情。曾在城里医院工作过的年轻的艾山,来到这个边远的牧区当医生,当然是寂寞的。而寂寞总是与对爱的渴望纠缠着的。在阿克木老人庆祝孙子周岁的酒宴上,艾山感受到一双注视他的眼睛,感受到一道饱含情意的目光。艾山确信,在那群欢闹着的女性中间,有一个人在留意他,在怜爱他,在钟情于他。于是,艾山感到了幸福,甚至有了些陶醉。虽然在小说中艾山也曾与那个他认定在偷偷爱着他的姑娘并肩坐在马车上,但自始至终,并未开始谈情说爱。艾山在自己想象的爱情中甜蜜地微醺着。如果这第一篇让我失望,我也许就不再往下读了。但我虽然没有惊喜,却也没有失望。小说虽然没有叙述精彩的故事,没有表达深刻的思想,但叙述本身是富有意味的。张惠雯有很好的语言感觉,对语言的声调、节奏处理得很好,因此叙述本身便能给人足够的审美享受。《爱》表达的是一种淡淡的、似有若无的情绪,叙述过程中分寸的把握是极其重要的。这样的非常诗意化的小说,对人物心理活动和言行举止的叙述,稍稍不到位,意味便出不来;但略微用力过度,便把东西烤焦了。而张惠雯的叙述,每一句都是恰到好处的,既不给人以生涩感,也不让人感到有焦煳味。这其实是十分不易的。《爱》让我对作者心生敬意的,还有对人物细微的心理活动的捕捉和表达。是否能够精确、细腻地刻画人物微妙的动作、神情,是我判断一个小说家是否具有叙事才华的基本标准。一篇短篇小说里,至少应该有几处对人物微妙动作、神情的精确、细腻的刻画,而一部长篇小说里,则应该有大量这样的细节刻画。只要想想《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就明白这个道理了。而张惠雯正是具有这种叙事能力的作家。例如,在《爱》中,这样叙述了艾山在酒宴上对那道目光的初次感受:
当别人和他说话时,艾山总会专注地听着,很有礼貌地点头,而大部分时间,他只是低头盯着眼前的杯子、盘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隐约地感到有一道目光不断朝他看过来,但每当他循着感觉的方向看过去,他却只看到一些因为欢笑而颤动、闪烁的女人的身影。他不好意思朝那个方向一直寻找,但他觉得那双眼睛就隐藏在那些影子中间,它悄无声息地注视自己,于是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个表情都落在这目光构成的透明的网中,无一逃脱。他又开始不安了,他调整着自己的位置,一点点地侧过身子,可他觉得他并没有摆脱那道目光,它就像一个轻盈灵巧的飞虫,在他发梢、衣领和背后飞动。
小说中这样的叙述,最能说明作者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才华。第一篇《爱》没有让我失望,于是便一篇接一篇地读下去,很快读完了全书。整个阅读过程都是津津有味的。读完《两次相遇》中的十几个短篇小说,我的感觉是,张惠雯不喜欢写那种剧烈的血淋淋的冲突,不喜欢给故事设置一个惨烈的结局。这十几篇小说,《垂老别》《绳子》等算是故事性强烈一些,但也是与小说集中的其他作品比较而言。但叙述本身的富有意味和对人物内心律动的精细把握,是小说集中全部作品的艺术品格,也正是这种品格让我把每一篇都读得津津有味。叙述本身的富有意味,关乎音调的平平仄仄,关乎每个字的低昂清浊,分析起来颇为繁难。而对人物内心细微活动的表现,却是可以举例说明的。张惠雯生长于中原乡村,小说大多以中原乡村人事为题材,贫穷也就常常是故事的底色。《如火的八月》写了乡村姑娘春光骗婚的故事:春光先让家人把自己卖给外地男子,然后自己再跑回来。这样地骗了两次,每次不过骗取数千元。这样的行为,当然是十分危险的。在村中,春光有真心爱着他的小伙子亮子。亮子一再恳求春光不要再以这种方式谋财了,春光自己也厌倦了这样的行为,但母亲和哥哥却希望他继续骗下去。当在县城打工的哥哥又物色到一个目标,打电话叫春光快点过去时,春光犹豫了,拖延着迟迟不肯动身。哥哥打电话催,而在家中的母亲也以自己的方式敦促春光快点出发:
她在屋里站了一会儿,身上又冒了一层汗。但她暂时安静下来了,不再追打那些跌跌撞撞的蚊子。蚊子颤颤巍巍的尖细叫声仍然在空气里震荡,于是,她划着一根火柴,点燃床头破碗碴里的一把干草,草的气味渐渐浓烈,蚊子开始往更高处飞,影子投射在墙壁上,像一个个晃动的、巨大的污点。春光站在床头,浓烟把她的眼泪熏出来了。她熄灭了灯,在黑漆漆的房间里哭了。然后,她抹干泪走出来,看见她的小旅行包就放在外屋当中的桌子上。母亲早就替她收拾好了,这个东西已放在这儿好几天了。她听见母亲在院子里又唤了她一声,而且喊她的小名儿,她好久都没有这样喊过她了。
张惠雯捕捉和刻画细节的能力在这样的叙述中表现得十分充分。“点燃破碗碴里的一把干草”,则把家境的贫寒一下子显现在读者面前。表现一个家庭的贫困、窘迫,“破碗碴”三个字抵得上千言万语。这番叙述的重点,还在后面。小说开始就写了母亲对春光有几分畏惧。春光既然能够以骗婚的方式挣来很多钱,在家庭中地位自然上升,虽是母亲,也不能对她说重话,更不能居高临下地下命令了。这原因小说没有明说,只是作为一种言外之意让读者去体会;明说了就显得拙劣了。同样没有明说而只用动作和语言暗示的,是母亲对于女儿出发的急迫。女儿迟迟不肯动身,母亲内心焦急却又不敢直言催促。把女儿的行李收拾好,放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让这小小的旅行包代替自己表达催促之意。很久没有喊女儿的小名了,却突然喊出了口,这就不只是在催促,而有了恳求甚至哀求之意。张惠雯《如火的八月》中这个母亲对女儿小名的这一声呼喊,让我想到了老舍小说《月牙儿》中那个母亲对女儿的态度。
《两次相遇》中多数作品,都有着对人性之善恶的表现,有几篇还颇为别致,例如《怜悯》,例如《垂老别》。有的作家愿意极力表现人性之善,笔下人物没有邪恶,作品中没有一点阴影;有的作家热衷揭示人性之恶,笔下人物全都如魔鬼,作品中没有一点点光明。张惠雯不属于这两类作家,她总是在与恶的比照、较量中表现人心中的善良。《我们埋葬了它》让我们感受到两个孩子对生命的怜爱,孩子心灵的柔软和温热与舅舅、父亲等几个大人心灵的冷硬形成对照。读完小说,我们在为两个孩子的善良感动的同时,也不免担忧她们心灵的柔软与温热能够维持多久。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与社会互动的加剧,孩子本来柔软与温热的心灵渐渐变得冷硬残酷,这是极有可能的。小说集中的《怜悯》,便写了一个人本来柔软温热的心灵是如何向冷硬残酷转变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完成叙述。“我”到这个劳改农场工作后,第一次出差,与老刘、老陈一起用一辆面包警车押送一名犯人到地区总医院保外就医。从监狱到地区总医院,是坑洼坎坷的山路,要走三个小时。犯人兼病人曹大余从小死了父亲,没人管教,成了地痞恶棍,坏事做尽;现在患了脊柱肿瘤,病情很严重。曹大余作为一个重病之人,从监狱出发后,是需要最起码的照顾的:蜷缩在面包警车隔离栏后面,躺着的姿势需要合理些,途中要小便也需要扶持。然而,老刘和老陈根本不管他的死活,不但没有把曹大余当作一个人,甚至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活物。“我”想给予曹大余最起码的帮助,却因为顾忌老刘和老陈的嘲笑而罢手。“我”本来有着对作为一个活物的曹大余最起码的同情,一直被老刘和老陈所监管着。因为姿势不合理,路上每一颠簸,曹大余便发出痛苦的呻吟。只要帮助曹大余把姿势调整一下,他就会舒服些。虽然是一伸手之劳,老刘和老陈根本不会对曹大余伸手,而“我”如果伸手帮助一下曹大余,必定遭到老刘和老陈的讥嘲、挖苦,“我”终究是不敢帮助大余。途中,曹大余大概看出“我”是有点同情心的人,曾向“我”提出要小便,而老陈的回答是“叫他憋着”。于是“我们都笑了,但我笑得有点儿难看”,“我”是陪着他们笑。难看的笑就意味着内心其实在哭。这是大冷天,如果不帮助曹大余小便,他就必然尿湿那棉裤,穿着尿湿的棉裤,那是非常难受的。“我”很想帮助曹大余却又不敢,只得内心哭着而脸上却以难看的方式赔笑着。虽然犯人保外就医有伙食补贴,但在医院里,老刘和老陈却根本不考虑曹大余的吃饭问题,连续几天让他饿着;医生、护士提醒应该给病人吃饭,老刘和老陈却以硬邦邦的话语与医护人员争吵。小说以一个又一个精彩的细节,把病人曹大余的可怜和“我们”三人的冷酷、残忍,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一天,病房里只有“我”和曹大余两人:“我在床上坐下,拿桌子上的卫生纸擦我的皮鞋。我扫了一眼躺在床上的犯人,他竟然对我挤出了一个笑。我没搭理他,继续仔细地擦皮鞋。但我心里想:一个人一直那样趴着、不能翻身儿是个什么滋味儿?我想象不出来。”曹大余对“我”挤出一个笑,还是看出“我”与刘、陈有所不同。“我”虽然没有搭理曹大余的刻意挤出的笑,但却试图想象曹大余无法翻身的痛苦。能够想到这一层,说明“我”的同情心还没有彻底丧失。曹大余挤出一个笑,是在讨好,是在祈求。“我”如果在擦完自己的皮鞋后伸手帮曹大余翻个身,他便不是挤出一个笑,而是会感动得泪流满面。但“我”只试图想象曹大余无法翻身的痛苦,却根本没有想过要帮助他翻个身。作为警察,“我”必须与老刘、老陈步调一致。曹大余两天没有吃东西,老刘、老陈仍然不以为意,而“我”却有点在意:“我想到,犯人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如果我非要给他吃,他们可能会不高兴。我责备自己的软弱,为什么我不能像老陈和老刘那样呢?他们从不让软弱侵入自己,而我应该让自己和他们一样。”善良的敌人并非总是那种与善良直接对峙的邪恶,善心的消失并非总是因为内心善意的枯竭。当在某种社会中,某种环境里,善心变得可笑、善行变得可耻时,善良便是一种极难保有的不合时宜。我们不知道老陈、老刘是否生来便如此冷酷甚至残忍。我们宁愿相信他们本来也是同“我”一样心灵软弱的人。当年,是另一些老刘、老陈们迫使他们让心灵从软弱变得冷硬、残酷。而现在,他们又承续了前辈的事业,以前辈的方式,在重塑“我”的心灵。我们也知道,在“我”置身的环境里,老刘、老陈这样的人,是“正常人”,“正常人”总是很多的,而“我”是“另类”。“另类”当然不可能战胜“正常”。“我”要在这个环境里生存下去,必须让自己也变得“正常”。“而我应该让自己和他们一样”,这是在“觉悟”。有了这样的“觉悟”,我对犯人兼病人曹大余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此前“我”虽然没有什么帮助曹大余的行动,但毕竟还有着帮助他的冲动,而现在,则连帮助他的意愿都没有了。曹大余手术后回病房,被子没盖好,央求刘干事帮助,遭到一顿训斥。老刘和老陈出去买饭了,病房里只剩下“我”和曹大余:
我让老刘和老陈先去买饭。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走到窗口那边站着朝楼下看,看见他们俩穿过隔开病房楼区和门诊区的那道花墙,沿着那条灰色的水泥路往医院大门口走去。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有点儿紧张,希望犯人不要醒,不要叫我。我忍不住朝他那儿瞥了一眼,发现他裸露在被子外面的小腿蜷缩起来,干瘦得像两截褐色的树干,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还好,他没有叫我。如果他叫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给一个不能动的人盖上被子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儿啦,但他是一个犯人,而且是被众人憎恨的犯人,我不该可怜他。如果我帮他盖上被子,他们一定会发现,他们会嘲笑我,还会告诉别的人。我不能冲动,不能出格,不能犯我们这行最大的毛病……我没有坐回到他对面那张床上,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窗户前面,背对着他……
这是张惠雯小说中众多精彩的对人物微妙心理的表现之一。曹大余刚刚央求老刘盖被子而遭训斥。曹大余的小腿继续裸露着。此前,因为“我”的态度稍微柔和些,曹大余曾几次向“我”求助。现在,病房里只有“我”一个警察了,曹大余向“我”求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于是紧张,于是不安,于是不敢面对曹大余。“我”内心的紧张其实是一种“怕”。表面看起来是在“怕”这个犯人兼病人,其实是自己在怕自己,是一个“我”在怕另一个“我”,或者说,是“觉悟”了的心灵开始向冷酷坚硬转变的“我”在怕先前那个心灵软弱的“我”。“我”毕竟“觉悟”未久,心灵毕竟还处在转变过程中,所以还会紧张,还害怕被求助。等到转变完成,等到完全变成老刘、老陈一样的“正常人”,“我”就没有什么可紧张了,曹大余敢于开口,就迎头痛击。说不定还希望他开口求助,好让自己有一个训斥他的机会,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怜悯》是一篇构思相当别致的小说,完成得也非常好。《垂老别》的故事并不新鲜。王老汉虽有两个儿子,却无处安身。两个儿子都已结婚生子,大儿子住在村里,二儿子住在县城。两个儿子都不愿意接纳父母。老伴还活着时,王老汉就在村外自家地里盖了间小泥屋,两口子住着。后来,老伴死了,泥屋也被风雨摧毁了。成家了的孩子们不肯接纳年迈的父母,这样的故事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里,都不罕见,但张惠雯却把这个常见的事情叙述得颇有新意。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里,当老人遭到子女类似于遗弃的对待时,总会有对子女的怨恨,总会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对子女的养育之恩,总会向人诉说自己的不幸。但张惠雯笔下的王老汉,却对两个儿子没有丝毫怨恨,却从不认为自己对儿子有养育之恩,也从不向人诉说自己的不幸。王老汉不认为自己对两个儿子有丝毫权利,不认为两个儿子对自己有半点义务。这就使这个常见的故事有了不同的意味。张惠雯刻意表现的,不是两个儿子的冷酷、自私、丧尽天良,而是王老汉内心的善良。但唯其如此,两个儿子的冷酷、自私和丧尽天良,才越发让我们憎恶。小说的成功,还不仅仅在于构思的别致,更在于对王老汉内心细小微妙的活动有十分精确传神的表现。举一个例子。王老汉住着的小泥屋倒塌后,就住在村中的大儿子家里。两个儿子协议,父亲在每家轮流住,每次住一个月。这一次,在大儿子家住满一个月后,县城的小儿子到最后一天的晚上都没有来接父亲,父亲便被大儿子家赶出来了——是大冷的天。村长和王老汉的弟弟王安只得陪着王老汉连夜去找县城的二儿子。到了二儿子家,村长、王老汉的弟弟王安要与二儿子商量王老汉的着落,二儿子觉得父亲最好回避,便请父亲先“出去一会儿”——是冬天夜里最冷的时辰。王老汉在屋外踱着步:“他只在暗处走,故意绕开灯光映照的那一小片亮地方,好像他走到亮地方会被什么人看见。”在一个小县城的寒冬的深夜,王老汉即便走到灯光下,大概率不会有人看见的;就算有人看见,也对王老汉无损。但是,这有可能对儿子有损:让邻居们知道一个老父亲在如此寒冷的夜晚徘徊于儿子的家门外,会让儿子受到非议、指责。王老汉不肯走到灯光下,还是在替儿子着想。小说又写道:
他在外面站着,听见屋里人的说话声,一会儿是王安,一会儿是儿子,一会儿是村长的大嗓门……他不让自己留心听他们说话,他踱着脚,嘴里胡乱嘟哝起来:让你等,你就等着,不让你听,你就不听,这天冷得,你就站着,不站着去哪儿……他又想起那两只游狗来,有些想让它们过来。可狗却没个踪影,连叫也不叫一声。
儿子之所以把父亲遣出门,就是因接下来的谈话会伤害到父亲,而王老汉也明白这一点。站在门外,王老汉没有竖起耳朵听屋里的谈话,而是故意跺着脚,嘴里胡乱嘟哝着,以此种方式扰乱自己的听觉,好让儿子儿媳说的那些伤害自己的话不自然而然地被自己听到。这样的微妙的心理活动的表现,最能为小说增色,也特别能显示一个作家的才华。王老汉非常明白,两个儿子其实是协商不好的,而自己终究是无家可归的。从二儿子家出来后,王老汉到老伴的坟上睡了一觉。从这里开始,小说的叙述强烈暗示着王老汉最终会以自己死掉的方式让两个儿子摆脱累赘。这样的结局是十分合乎情理的。然而,到最后,王老汉没有选择死亡,而是选择了流浪,以外出流浪的方式让两个儿子得到解脱。这又一次显示了张惠雯的异乎侪辈。王老汉一死了之,是合乎常情常理的,但也是俗套的毫无新意的结局。更重要的是,尽管王老汉主观上毫无控诉、报复两个儿子之意,但只要他选择了死亡,客观上便必然构成对两个儿子的控诉、报复。两个儿子会因此而受到舆论的谴责。这一层,王老汉当然也十分清楚。所以,尽管活着已没有丝毫生趣,尽管他其实十分渴望死去,尽管流浪对于这样一个老人意味着难言的苦难,但王老汉还是又一次选择了成全儿子的方式。《垂老别》把一个农村老人的善良写到了极致,这其实是一个颇有新意的人物形象。
同样表达了张惠雯对善恶的独特思考的,还有《绳子》。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因为偷了公社的三根玉米棒子,公社民兵连长要将其五花大绑,押送公社。村里人都觉得过分,没人肯提供绳子。而与村民们一起围观的一个男孩,大声说自己家有绳子,他的父亲试图阻止他,没能成功:
他看到他儿子拿来了绳子,一条小孩的手腕一般粗的麻绳。那是他来的时候用来捆行李的。儿子看也没看一眼,直接跑过去把绳子交给了连长。他像一个爱表现的、不怯场的小演员。然后,连长大声夸奖了他,人们都看着他。他知道儿子想要的就是一个表现的机会,一种荣誉。因为这些东西他从来没有过,他成长的过程里只有轻视、侮辱、惩罚……这两年多以来,他连书也不能读了,随他下放到农村来劳动,也没有母亲可以照顾他、安慰他,因为她已经死了。
原来,孩子的父亲是城里下放来劳动的右派。饱受蔑视、欺侮的孩子,当有了这样一个表现的机会时,他果断地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这样的机会对于他来说太宝贵了。至少在把绳子交出而得到表扬的时刻,他是幸福的,甚至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这是酷热的季节,那个被五花大绑的孩子,一路上连一口水也得不到。孩子本来就饿了许久,本来就身体十分虚弱,终于死在路上。那个提供绳子的孩子,他的右派父亲严正地告诉他,如果他不提供绳子,那个偷玉米的外村男孩也许就不会被绑着,而如果不是一路被这样的麻绳五花大绑,他也许就不会死在路上。后来,这个右派的儿子成了律师,终生为此愧疚。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想法找到了那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每月通过乡政府转给她一点生活费。在同类题材的小说中,张惠雯的《绳子》也颇有独特性。
小说集的最后一篇是《两次相遇》,也写了爱情,似乎无意间与第一篇《爱》产生呼应。如果说《爱》写的是并未开始的爱情,所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诗情画意,那《两次相遇》则写了一次爱情以美好的诗情画意的方式开始,而以凄惨的肮脏的不堪入目的方式结束。对人物细微的内心活动的精确叙述,仍然让小说富有魅力。除了这本《两次相遇》,我没有读过张惠雯的其他作品;但《两次相遇》已足以让我认定作者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