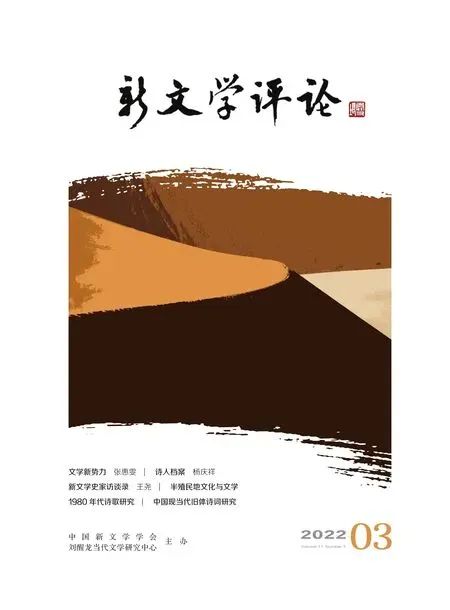主持人语
2022-03-22冯祉艾
□ 冯祉艾
第一次读到的张惠雯的小说是2006年《收获》杂志上的《水晶孩童》。若干年后,我还很清晰地记得小说中那个纯净而甜美的孩童,那个孩童宛若作者本人,也因此,我格外开始关注她的创作。
本期的评论小辑中,我们邀请到了王彬彬老师、刘小波老师、许婉霓老师、任慧老师分别就张惠雯近年的中短篇小说进行深入阅读和剖析。在此,我不多做赘述,由读者自己在四位老师的文字中寻找到他们所想要表达和呈现的,也许会收获更多。
对于我们每年惊人的小说创作量而言,是否有给当下文坛带来新的声音?对此,我持保留态度。在强调现实主义题材的今天,我们的作家经过各种亲身体验,把文学现场的第一声音记录下来,在这里所谈的第一声音,并非指报告文学,而是有过丰富多彩生活的那一类作家。但,这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现实主义创作吗?我认为,在某些作品中所呈现的情感是相对薄弱的,所以无法真正让读者“走进去”。无可非议,我们的创作是离不开生活,但影响作家创作的应当还离不开想象力吧!如果在想象力枯竭的情况下,我们的作家或许要借由某些新闻事件、社会热点进行切入,再进行加工。这类小说叙述的故事确实有较强的可读性,但呈现出来的仅仅是好看的故事而已,或者说这只属于现实主义的“新故事”。然而在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应当还要看到的是作家自己来创造出另一个丰富、延续性的世界。因此,我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应当是属于作家自我生命体验或者是建构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时代的精神认知;抑或是阅读时、旅行时想到的某个人物和某个场景,再由此展开去。
作为一名文学期刊的编辑,在阅读一些作品的时候,我时常会生出些倦怠。我认为,它们太现实了,太当下了,似曾相识。此时,我们写下的是什么?以日常为例。众人的吃喝拉撒,关于票子房子车子情人妻子等所谓现实问题,被反复虚构、关乎道德层面的底层生活,对无聊和无趣的乐道,尽管这类作品多有较好的文笔。是的,这里也有呐喊,有揭露,有对所谓血和泪的展示,但它们都只停留在生活的表象、表面,鲜有追问和反思。小说对于生活的再塑造并不是直接“拿来”,它是需要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的。
因此,本雅明才尖锐地指出,艺术最薄弱的成果是以生活的直接感受为基础的,而最强的,就其真理来看,则与类似神话的范围——创造物——有关。“越是试图毫无转化地把生活整体变成艺术整体,他就越是无能之辈。”还有一点,就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小说往往存在“背景依赖”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内极有影响的某些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生活的变化,其背景上的附着物会一点点散尽,阅读者能够以自我的日常经验叠加进去的部分会一点点减弱,它的影响力和共感力会有所减损,甚至变得毫无价值。
莫言在获得诺奖发表获奖感言时曾反复强调小说家是讲故事的人,他始终强调故事在小说中的重要性。无可厚非,我们的小说是需要故事的,但仅凭讲故事就能赢得阅读和尊重的时代应是过去了。很多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着眼点仅仅在于故事,只关注这个故事是否精彩、漂亮,但只有故事还不能称为小说。现代的小说不一定还会保持完整的构架,如卡夫卡、马尔克斯、巴塞尔姆等。它也可能是片段式的,这就使得我们要重新理解“故事”这个概念。承载故事的到底是什么?是语言。比起精心设计的美妙绝伦的精彩故事,我更欣赏用语言和情绪推动小说的发展,减少读者对故事情节的期待性。在我看来,小说的故事性并不一定是精彩起伏、充满悬念的情节,而是某种所具有的那种不甘于被遗忘、不肯在意识里暗淡熄灭、引发你回忆和想象性质的某种事物,它甚至不一定和故事相关。我们可以说,某个人有故事性,某件事有故事性,或是某个场景有故事性。在我看来,好的小说首先应具备纯净并且饱含诗意的语言,每一个字都具有属于作家本身的氛围,张惠雯的小说在意的也正是语言带来的独特的氛围和节奏。张惠雯的小说有很多时候,都在尽量避开那些社会热点,尽管她的小说永远是站在他者的视角,但也能够从此去唤起内心的波澜去感知。在此,我想提及她的小说《寻找少红》,相比《梦中的夏天》《双份儿》《飞鸟和池鱼》这些被读者熟知的小说,这篇似乎没有被提起过。在小说中,张惠雯作为写作者,不仅写出了属于她个人的生命经验,还有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她对细节的洞察力和敏锐程度,在“我”的表现中,展现出一种绵密和生动。就如同莫言在谈到福克纳时说“我编造故事的才能绝不在他之下,我欣赏的是他那种讲述故事的语气和态度”,因为最重要的不在于编故事而在于叙述的这个语调。文字始终是文学的基石,好的语言一定是不经意间流露而并非刻意去装束。有的小说似乎是以十分有力且生猛的语言来进行创作,这也许会留下短暂的辨识度,但它也会故显夸张,甚至是拙劣地呈现出来。这样的语言太刻意,刻意到你能感觉出作家敲击键盘时每个字发出的哀号。所以,驾驭语言的能力才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才华。
我一直提倡小说创作一定要有冒险精神,一定要把写作当作一种精神、思想与艺术的探险。我们应该会发现,有的作家,在他的写作生涯中,除了比原来的作品更会讲故事,语言更好以外,在艺术上全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能够打动我们的东西。这让人产生极度审美疲劳,看过他作品的读者,或许都能在小说的开头,想到人物如何发展,情节如何波澜。这类小说往往具有重复性,甚至在创作上他只是在 “重复自己”。在我看来,作家的创作应该是持续的,有变化的,当然,怎么变,为什么而变,是冲出重围抑或是故步自封,这是创作上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如三岛由纪夫所说,在创作中,作家应该不断去追寻一种危险因素,而正是因为这种危险因素,作家才能尽可能去发现和创造。
有作家谈到一种“未完成美学”,这对我有所启发。我觉得,好的小说,应当最大可能地调动阅读者的智力参与,给他留下空间,作者要做的,只是标出路标,指向可能的路径。别人能做到的,你在别的小说中能读出的,我尽可能地略去;而别人做不到的,别的小说中大概还没有的或者还稀薄的,我则要多说几句。
小说的意义是什么?在短暂的人生中它让我对生命、时代有更真切的体会。与此同时,它能让我对自身反复打量,打量我内心的善与恶,我在这些里面能够找到关于生命更深刻、更浑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