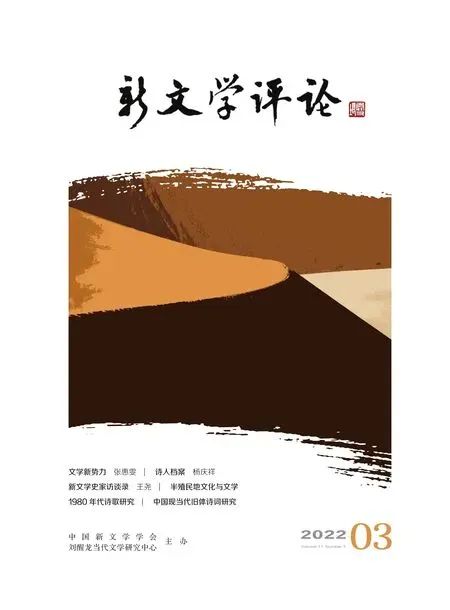他人的生活,他人的故事
2022-03-22张惠雯
□ 张惠雯
我在某本杂志上读到一首翻译诗,描述在一场大雨中,“她”驾驶,而“我”在一旁注视着她……它在我脑海里立即转化成一幅可见的画面。诗人描述说车子穿过暴风雨如同穿越河流,我觉得这里面有某种令人震颤的美感。后来,它成了我的小说《暴风雨之后》里的一个场景。我有很多类似的经历,我觉得它说明让小说在作者心中萌芽的可以是任何东西:诗里的某句话、一首歌的旋律、一个你在街头看到的陌生人的影子、一则传闻的一鳞半爪……
作者在写作中当然也会经常动用自己的记忆和经验库存。譬如,在我最近出版的小说集《飞鸟和池鱼》里,对故乡的描述中,我肯定动用了相当多的记忆和经验。但构成其中每个故事的骨架的东西,多半来自他人的生活、他人的故事。当我写《在南方》里面的移民故事时,他人的故事就更为重要了,因为我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就是美国人所说的家庭主妇的生活,大部分的活动空间就是家——我很难基于自身的经历、故事来写作。本雅明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拉丁文中,“文本”也是“编织”的意思。写小说的确就像做编织,你要把从外面获得的见闻,那些相互并无关联的人事片段,用自己的感受力、想象力的丝线全部连缀起来,让细节得以填充,使整体致密而流畅。
下面,我就以《雪从南方来》和《玫瑰,玫瑰》的创作谈来阐释这两个写作问题:第一,找到那粒能生发、成长出小说的种子;第二,把他人的故事转化为自己的小说。
一粒种子——《雪从南方来》创作谈
我们此处不谈什么创作手法,而是谈谈“燃起”这篇小说的一星火花。
我想起亨利·詹姆斯在他最好的长篇小说《使节》的自序里有关“微小的暗示”的那段话:
其灵感来自微小的暗示,而这么一点点暗示的种子又落入土中,发芽生长,变得枝繁叶茂,然而它依然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微粒,隐藏在庞大的整体之中。
读到这句话时,我忍不住用圆珠笔画一条波浪线,做了个标记,因为它让我如此心领神会。一点微小的、暗示的种子落入土中,长成一棵树,这就是我那些小说产生的过程。我去年出版了一个小说集《在南方》,里面将近一半的小说产生所依赖的“微小的暗示”都来自同一位朋友讲述的故事。作为一位批评家,陈瑞琳对故事有很好的敏感度,同时她又活跃于休斯敦的华人移民社交圈。有时候她一个电话打来:“惠雯,我要给你讲几个故事。”然后,她讲我听。有一次我们约在咖啡馆讲故事,我带了一个笔记本,她一口气讲了六个故事。这些故事繁杂、耀眼、情节曲折,而我的任务是在其中发现那个具有意义的“微小的暗示”。同样,《雪从南方来》也来自这么一个暗示。
2021年10月的某天,一位声称喜欢我的小说的人从另一个城市来到波士顿。我一般不愿见陌生读者——那种会面的尴尬可想而知。但由于此人是一位朋友的朋友,她特地嘱托,我似乎推辞不了。
我和那位先生约定在我家附近的咖啡馆碰面。这是一次平淡无奇而且匆忙的会面,主要是他在谈喜欢读哪些小说,中间插入了有关自己生活状况的简单介绍,说到自己以前有过两次婚姻(目前是单身),和第一位妻子有个女儿,女儿年幼时他就一个人带她来到美国。他坦承第一次离婚是因为和妻子完全合不来,而当他想要说起第二个妻子时,停了一下。我诱导他说下去:“那么第二个妻子是来美国后遇见的?”“对,”他说,“第二个妻子我喜欢,但我女儿不喜欢,她们处不来,只能分了……”从他不自然的神情看,我觉得我们不该再谈这个话题了。我们又扯到别的他喜欢的作者,然后匆匆喝完一杯咖啡告别了。但他关于第二个妻子的那句话留在我的脑海里,成为这次会面的意义所在。
我觉得这个“舍弃”的故事里蕴含着强大的中国式家庭伦理,这伦理本身存在着颇有悲剧性的荒谬:一个成年人的感情生活竟然很大程度上被他们未成年的子女所支配,而成年人却要承担其后果。例如,小说中的父亲失去了真爱,在女儿长大离家后注定孤独终老……但同时,我也想到,身处那样一个处境,究竟有几个中国父亲会做出和他不同的选择呢?对西方人来说,这几乎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很强,觉得照顾好孩子是责任,但选择伴侣是自己的事儿,二者泾渭分明;但对惯于为子女牺牲、奉献一切包括自我的中国父母来说,这简直是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从逻辑上说,这也不是问题;从情感和主人公的伦理考量来说,却是大问题……但小说恰恰不爱讲明白的道理和逻辑,它偏爱的是矛盾、困境和偶然性。此外,它也恰好是我近年来喜欢的主题:婚姻、情感、家庭关系。确实,我这些小说不大可能受到太年轻的读者的喜爱,它更适合成年人尤其是已经结婚的中年人来读。
我没有立即去写,但我在脑海里做了标记。直到两三个月后,接近农历岁末的冬寒时节,我觉得可以动笔了。还有什么比“虚构”更让人激动的工作吗?基于一句话而构造出与之相关联的整个世界!合适的场景是波士顿,这样我就能用周围熟悉的环境画出不失真的布景;既然是写一个即将孤独终老的人,那么把季节选在冬季似乎更有些象征意味儿,况且也是我身处的季节,景色和感觉都直接而新鲜;最后,我回想起波士顿的第一场雪,那也是整个东岸的第一场雪。那天下午,下雪的消息先从纽约传来,然后是康涅狄格州在下雪,然后是罗德岛,最北边的波士顿反而雪来得最迟。而在东岸下第一场雪之前,南方的休斯敦(也是我住了将近八年的城市)已经降过一场罕见大雪。所以,我那时在朋友圈写了一句话:今年的雪好像从南方来。至此,我给我的小说找到了题目——雪从南方来……我看着我的种子落入土中、发芽生长。
现在,人们喜欢感慨说:现实比小说更精彩。这个“精彩”往往指曲折离奇、炫目刺激的效果。不过,真把现实中的各种精彩事件和高明段子搬进小说里去,那小说倒未必好看。小说的精彩和现实的精彩是不同的。有时,精彩纷呈、光怪陆离的现实也许会令作者迷失其中,而一个“微小的暗示”,宛如人性中一点儿微暗的火,反倒可能照亮艺术的想象力。小说当然可以选择庞杂地呈现,也可以选择往深处、细微处行走。我选择的方向是后者。作为一个写短篇小说的人,我知道我寻找的只是一粒有生机的种子,而不是一棵大树。
他人的故事——《玫瑰,玫瑰》创作谈
我总是需要别人的故事,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平淡安适,毫无戏剧性可言。这对我来说倒是件幸事,我并不愿意为了小说题材而让自己的人生充满波荡起伏。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艺术家的人生应该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传奇,或者其本人至少有诸多异于常人的品行。如果这样的话,我活得很不够艺术。那么退而求其次吧,与其活得艺术,我更希望写得艺术。何况,还有那么多别人的故事可写。我相信,脱离了作者自我中心式的展示欲和倾诉欲,小说依然能很好地写下去。
我不是那种闭门静修、格调高冷的作者。我喜欢与人交往,喜欢听人们讲各种各样的生活上的事、分享八卦。有朋友批评我爱听没有严肃意义的闲话,我想那是因为他并不真正了解小说的精神里的某一方面,其实包含着八卦精神的精髓——对别人的故事、别人的状况,以及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的发自内心的兴趣。在此,谈论八卦的目的不是像长舌妇们那样传播谣言,评判、中伤他人,而是为了发掘出某种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东西。因此,我们不会像娱记们那样仅仅关注事件的行动层面,而是会深入这些行动的动机层面。我很难想象简·奥斯汀会拒绝倾听或谈论八卦,事实上,她和她姐姐的书信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谈论社交圈、邻里乡亲们的八卦。我也无法想象没有足量巴黎社交圈轶闻(“八卦”较为文雅的称呼)的支撑,普鲁斯特如何写他的“追忆”。如果我们用稍微幽默一点儿的视角(而非严肃苛责的目光)去看,我们就会明白,八卦和废话一样,是生活中较少的有趣的事物之一,是可供小说家观赏、琢磨的社会风俗画。
如我的很多小说一样,《玫瑰,玫瑰》也是“别人的故事”化为了“我的小说”,它基于我的一点儿观察和一个听闻,二者之间没有关联。
一点儿观察来自我在朋友圈看到的几组照片。几年前,有位朋友去探访老友,赚了钱的老友夫妇在海边买了座山。在朋友发到朋友圈的图片里,除了海边风光和豪宅外,我也注意到她拍的室内景观:中式家具、绣花坐垫、餐桌上铺着蓝印花布……第二天,她在朋友圈展示了早餐:茶叶蛋、豆浆、八宝粥、咸菜。第三天,她的朋友圈更具有戏剧性:她被朋友夫妇热情地带去海边搭建的一个棚子里打太极拳……从我朋友的年龄,我推断这对夫妻也不过五十来岁,但他们俩样子都很显老,显然过着一种注重养生的、退休老人般的生活。而这栋房子的外景和内景、其所在的大环境和人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一种怪异的对比,这给我留下了印象。
一则听闻则是我从另一位朋友那儿听到的小故事。她提到的那位女性的遭遇有点儿接近《玫瑰,玫瑰》里那位女主人公:嫁人多年,丈夫一直有性功能障碍疾病。但因为种种外人不可知的原因,这对夫妻并没有离婚,保持着一种相安无事又相互疏离的关系。这些外人不可知的原因,这种关系对于两个人尤其是女人身心的影响,难道不会比每日政治新闻更值得人去思考、去理解吗?
在我的意识里,那些有点儿喜剧感的朋友圈图片和这对夫妻有些悲剧性的关系之间慢慢产生了关联,似乎它们具有某种相似的东西,这种相似性、关联性不一定是逻辑上的,而可能仅仅是它给予人的感觉,譬如那种疏离、隔绝的气质。让不相关的人与事与景物的各种碎片之间产生联系,并且严密地黏合在一起,使其看起来仿佛本来就是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这大概也是小说家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于是,当我想要写这么一个多少有点儿怪异的小说时,我选择了那个仿佛与世隔绝的海边豪宅作背景。至于题目,它先于正文出现,成为一种象征。那些干燥的玫瑰花的意象,统摄了这篇小说的氛围:美丽、怪异、枯竭、孤绝,散发着一丝命运的残忍气息。我选择了外人视角来描述这个故事,以便它具有印象的模糊和多义性,从而保持小说本身应有的一点儿神秘感。小说里的作家“我”只是个外来的观察者,读者通过“我”的眼睛去观看那对夫妻、那种生活状况,同时也观察了“我”,但“我”却不可能给予读者任何答案。
这也是我一贯的做法——我不想在小说里贩卖什么离奇故事,更不想指明什么道理。那种离奇故事,你在小报的社会新闻版或是网络头条可以一口气读十个。至于道理,难道微信圈各种有关人生道理的鸡汤还少吗?虽然我的小说常常拿别人的故事的一鳞半爪做材料,但我恰恰不希望读者在读过后只是感到津津有味地听了个别人的故事。我想给读者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阅读过程,我希望读者在此过程中感受到一些东西,无论是关于审美的,还是关于生活与人性的,无论如何,那都是一种自我发现。
最后,应该提到美丽的新英格兰地区。它指的是美国东北部毗邻加拿大的六州,包括我所居住的马萨诸塞州以及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以风光著称的缅因州。我去过美国的很多地区,感到我最喜欢的是这里。它的风景并不是大峡谷式的壮丽、奇诡,而是秀拔、优美、隽永,这一地区到处是森林、湖泊、溪流、绵延的绿野,这种美更具有一种生活气息,令人如同置身于童话世界。关于这种美,我在小说中也有描述。以前住在得克萨斯的时候,我很少到户外活动,这固然和大部分时间天气炎热有关,但也因为确实没那么多去处。但现在周遭到处是幽静所在,仿佛林中生活,我就喜欢上了散步,喜欢观察植物的变化、动物的活动,对自然界也更为敏感。踩着厚厚的松针穿过林中小径给人一种心灵的涤荡,这和美国南方那种潮湿、闷燥的感觉完全不同。这一地区盛产思想家、诗人和自然主义者,应该并非偶然。以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南方文化仿佛是神秘地交织纠缠的热带灌木和藤类,北方气质则像挺拔的参天松杉。美丽的新英格兰好像打开了我的心胸,令我从一个盆栽植物爱好者变成了森林的爱好者。
常有人问起身居国外是什么感受,我觉得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诗句很贴切地描述了它:
身居国外是美妙的,有一种冷淡的快乐。
黄色灯光点亮塞纳河岸边的窗户
(那里有真实的神秘:他人的生活)
这种异乡人的感觉和写作者的身份有某种相通之处。写作者无论生活在哪里,其实多多少少都像个“身居国外”的人——他既有异乡人的好奇心,同时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陌生感和疏离,习惯于旁观、揣摩、沉思。我一直认为,作家不能和所处的时代、身边的人事贴得太近,否则你就无法跳脱出来,无法具有看清某些东西所需要的距离感。这种兴趣、好奇心与陌生疏离感结合起来,也许就恰好产生了诗人所说的“冷淡的快乐”和“真实的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