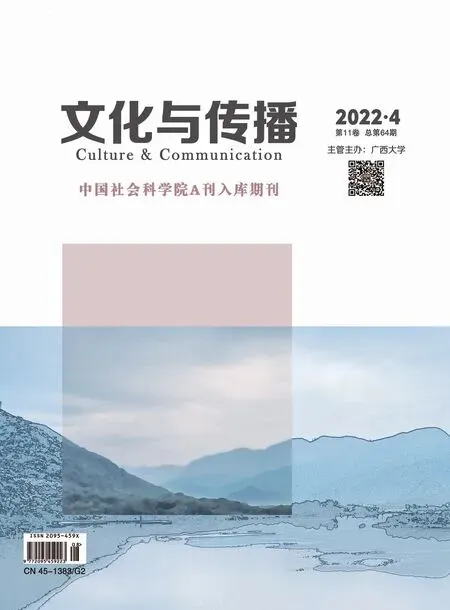笔扫千军:《新华日报》在“寿郭沫若”事件中的文化领导权生成路径探析
2022-03-22汪苑菁
汪苑菁,唐 玲
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特辟《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拉开了“寿郭”活动的序幕。这次活动从筹备策划到正式开展长达半年之久,辐射范围从重庆到全国,可谓声势浩大。此次祝寿活动打破常规①负责筹备纪念活动的阳翰笙也曾直言“我们共产党人一般是不作寿的”,摘引自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J].新文学史料,1980(2):126-131.,意义特殊,承担着历史使命。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与支持,“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的旗帜得到众多人员的拥护。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蒋介石公开破坏国共合作关系,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与广大民众对于国共合作抗日的热切期望背道而驰,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领导权开始“漂移”[1]。在这个关键节点,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组织策划了“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活动。“寿郭沫若”活动的最初提议人是周恩来,他曾言这次活动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希望借此“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2]。
现有的对于“寿郭沫若”活动的研究,一是关注其文学意义,从文章的内容看,活动是郭沫若从“政治活动家”到“文化人”的形象的建构仪式[3],其中的文化因素可展现抗战时期重庆文化生态[4];二是侧重其政治意义,该活动是《新华日报》在“皖南事变”后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5]。伍静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报纸为中介,将一系列祝寿活动转化为一种联络和团结国统区文人的媒介仪式,构建出共产党人领导文化界的政治现实[6]。此次祝寿活动既可以看作是文化领袖的建构仪式,也是政治斗争的仪式,但回到领导者周恩来的“文化斗争”预想上,“寿郭沫若”活动更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一次斗争实践。
那么,《新华日报》为何能将私人内部的祝寿活动转变成一个公共性的媒介事件?又是如何在封锁的环境下以民间仪式的祝寿来“发动一切民主力量”,冲破“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这些都需要深入的研究。本文从文化领导权的研究视角出发,分析《新华日报》在“寿郭沫若”活动中前台与后台的运作①戈夫曼把社会结构比作一个大舞台,并提出了 “前台 ”与“后台”的理论。“前台”指演员演出及宾客与服务人员接触交往的地方 ;“后台 ”指演员准备节目的地方,这是一个封闭性的空间。本文将此引用至报刊场景中,将报纸的公开化传播即报道内容的刊载称之为前台,将报纸背后的传播网络即报馆工作人员的交往实践称之为后台。引自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黄爱华,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03-107.,尝试从生成路径探究《新华日报》对文化领导权的夺取。
一、从文化领导权到中国共产党的祝寿活动
“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提出者为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他以探讨国家的结构为出发点,将广义的国家概念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范畴,无产阶级领导权在这两个范畴中具体表现为“政治统治权”和“文化领导权”。前者着重“强制”,以军队、监狱、法院等国家机器,诉诸行政甚至暴力手段进行统治;后者意在“同意”,通过学校、教会、工会、媒体等社会组织,借助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渗透,获得广大民众的“赞同”来实现领导[7]。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其理论的源流可上溯到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理论家。“文化领导权”的一个核心概念“市民社会”即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分化而来,并承接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领导权”理论,着重于“政治领导权”的夺取和建设,葛兰西称赞其“所完成的领导权的理论化和实现是伟大的‘形而上学’的事件”[8]41,承认其思想受益于列宁,并将其引申到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了“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作为理论设想在中国又有着更进一步的实践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文化领导权的夺取。瞿秋白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革命领导权问题,认为要在政治与文艺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构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大众革命文艺,在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中争夺文化领导权,从而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务[9]。毛泽东亦将文化领导权的建设视为夺取和巩固政权的一个路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着重强调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意义,提出革命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干革命不仅靠枪杆子,还要靠笔杆子”[10]。中国共产党从思想和实践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把文化领导权的建设置于审视中国社会革命的视野之内,获得了民众的思想认同,最终实现了国家政权的更迭。具体内容可参见刘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实践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8.双重维度对文化领导权进行整体把握,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发挥巨大效用的报刊更是中国共产党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一个利器。有学者认为,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不仅是党报的历史性变革,亦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建构[11]。
《新华日报》作为一份被国民政府允许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身处于政治、文化和军事都牢牢被国民党掌握控制权的国统区,要面临不同于根据地的极为复杂的文化斗争局面。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要想冲破国民党的政治和文化封锁更是极为困难。也正是在这种困难和复杂的历史形势下,以周恩来为核心的《新华日报》突破重重封锁,通过“寿郭沫若”活动发起了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一次特殊的战役。
文化领导权的夺取需要通过“阵地战”的方式长期进行。所谓阵地战,与运动战相对,这两者也是军事上的概念的引申。相较于后者需要直接进攻的强硬方式,前者则是着重长期的文化宣传,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社会集团合作,渗入其中并潜移默化地获得市民社会对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12]。
在“寿郭沫若”活动中,《新华日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既以作为前台的新闻报道在公众中进行传播,扩大传播范围;也以作为后台的报馆组织在社会上实现互动,壮大报道声势。
二、前台之“报”:纪念文章和活动报道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是从‘皖南事变’开始。”[13]《新华日报》发行工作人员称《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分为“皖南事变”前和“皖南事变”后两个时期。在第二个阶段,“反动派对《新华日报》的迫害、封锁、镇压骤然严重起来,他们采取各种卑劣手段钳制我们的言论,封锁我们的发行”[14]。在白色恐怖下,作为共产党“合法代言人”的《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军警宪兵交织的黑网严密包围着,人员的减少加上被减扣的稿件过多,报纸版面由对开一大张缩减为四开一张,发行量也大减,《新华日报》以至共产党在国统区亟须重新夺取话语权。在“皖南事变”后的复杂局势下,此次祝寿活动报道也正是对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宣传“采取攻势”①周恩来提出“我们必须应战,并要采取攻势,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心问题”,并要求改善报刊的内容和形势,辅助上述任务的完成。引自周恩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4月15日至5月22日)[M]//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898-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08。。
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第一版以半版篇幅刊载周恩来《我要说的话》一文,并于第三版和第四版特辟《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刊登郭沫若的半身像和相关纪念文章,此次特刊并非《新华日报》祝寿专刊的首例。此前两天适逢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的寿辰,《新华日报》在14日刊登《庆祝焕章先生六十大寿》专刊,郭沫若也曾题祝寿诗,但与时隔两天的祝寿活动的对比仍能看出《新华日报》对“寿郭沫若”活动的重视。
一是将周恩来亲自撰写的代论发表在头版。代论是《新华日报》的一种特殊社论,一般由享有崇高威望的人士针对当时的形势需要撰写,并以个人署名的形式发表,“比之一般社论具有更大的权威性、重要性。”[15]凭借周恩来在国共两党中的名望和《新华日报》“头条”位置,代论的影响力可想而知。二是由于人员和稿件的减少,此前《新华日报》的篇幅已由四版缩减为两版,为了刊登“郭沫若”活动,扩大活动影响力,《新华日报》在处境艰难的时刻专门增加两版作为活动特刊。
《新华日报》对于“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活动的报道主要从纪念文章和活动报道两个方面出发。
(一)刊载文人志士的纪念庆祝文章
历数纪念庆祝文章,作者群庞大,有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有《新华日报》报社负责人潘梓年、救国会民主人士沈钧儒,也有苏联大使潘友新等。他们创作纪念诗篇和文章,以表达对郭沫若五秩寿辰和二十五年创作生涯的庆祝之意。
纵观纪念文章,主要是从郭沫若的文学修养与革命精神两个角度进行论述,盛赞郭沫若“一方面提笔一方面战斗”[16],既是一位学者,更是一名革命家。文学性方面,潘梓年对郭沫若的总体评价是“诗有才,史有学,书有气度”[17];欧阳凡海提出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建议,就是要重视研究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并将其继续扩大发行[18]。革命性方面,艾云称郭沫若在创作、研究、翻译、行动上都具有革命性,可谓为“革命者郭沫若”[19];邓颖超肯定郭沫若在妇女运动中的贡献,称“沫若先生即是这样从歌赞中国历史上叛逆的革命女性中,燃烧着这样一支中国女性革命的光明的火炬的”[20];潇湘从反法西斯时代背景出发称赞郭沫若为国际反法西斯文化统一战线的“主要推动者和领导者”[21]。
在这之中,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代论《我要说的话》,对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完整的评价。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起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22]
周恩来并论鲁迅和郭沫若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着深刻的含义。“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一方面是文化界的推崇,蔡元培有言“为新文化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23],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加冕,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4]。中国共产党认可并大力推崇鲁迅“新文化运动中坚强的革命战士”的身份,并以鲁迅为首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个革命文学团体领导革命力量。“鲁迅的历史化,恰好为当下的郭沫若提供了历史合法性。”[3]在鲁迅“新文化运动的导师”的历史地位已经获得普遍承认的前提下,《我要说的话》将鲁迅与郭沫若作对比,赋予郭沫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身份的合法性。
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出发,统治阶级的政权合法性一是政治合法性,二是思想文化合法性[25]。周恩来的发声包含了彼时对鲁迅的加封以及此时对郭沫若的推崇,这种加封和推崇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文化中的“领头羊”位置。
(二)对重庆及各地纪念活动的报道
《新华日报》对重庆及各地相关的纪念活动进行了持续的报道。1941年11月15日,即纪念活动前一天,重庆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臧云远、常任侠等学者相继作报告并朗诵郭沫若的诗篇[26]。16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大楼举行的纪念茶会上,冯玉祥、老舍、黄炎培等一一上台祝词颂祷,周恩来更是高度评价郭沫若无愧于“五四”运动中长大的一代[27]。
除重庆外,在香港,各界人士在11月16日举行庆祝大会,成为香港文化界近几年来的一大盛事,《华商报》《救亡日报》《星岛日报》等报纸刊登纪念特辑,登载文化界人士对郭沫若的祝贺和敬仰的文章和诗句[28]。在新加坡,星洲华侨文化界于11月15日举行庆祝郭沫若五旬大庆的聚餐会,并募捐沫若奖学金作为寿礼[29]。
此前郭沫若作为特殊党员,并不参与党内的活动,即使在党内也仅有周恩来等少数负责人了解其真实的身份[30]。而在社会大众看来,郭沫若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对外一直是国民政府官员的形象,蒋介石还告诫他不要在赤色的刊物(《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将郭沫若和《新华日报》以及中国共产党进行分割[31]。
作为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合法的日报,《新华日报》已成为“共产党人格象征”[6],正如其总编辑章汉夫所言,“别的报纸有错误,只影响报纸本身的声誉,而我们党报发生错误,则会影响到党的声誉”[32]27。在集中的纪念文章和连续的活动报道中,《新华日报》对郭沫若亲昵的称呼、赞赏的口吻以及满含期待的话语,无不在向外界宣告郭沫若与共产党的亲密关系,从鲁迅着手,赋予郭沫若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身份标签,这一系列纪念文章和报道完成了郭沫若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化旗手”的大众化宣示。
三、后台之“馆”:传播网络的建构
在周恩来的构想中,祝寿活动不仅是一种短时的媒体仪式,更是作为“文化斗争”的现实实践。除了“前台”报纸文章的宣传造势,《新华日报》后台层层传播网络的铺展也不容忽视。从个人到新闻界再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动员和组织,使“寿郭沫若”活动最终成为插在国统区的一把利剑。
(一)人际网络:“勤交友”“交朋友”
郭沫若本人与周恩来私交甚密。在二人之间的书信来往中,周恩来以“沫若”“沫若兄”为头,以“弟豪”“弟恩来”落款。在重庆期间,郭沫若“无论是住在郊区或市内天官府”,周恩来都经常去看望他,与其进行探讨。有学者认为,1938年党中央“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的决议来源于周恩来的提议[30],此提议大有可能是周恩来与郭沫若日常工作和交往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可见周恩来与郭沫若相交甚深。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与郭沫若的交往并未止步于逢知己的私人情谊,二者在工作上也往来密切。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则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一职,初期有关第三厅的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等筹备工作以及工作开展等问题,郭沫若都向周恩来进行了请示[33]。此前第三厅领导的10个抗敌演剧队成立之际,周恩来亲自到场给演剧队做报告,号召全体队员们“到前线去,到民众中去,为抗日战士和广大人民服务”[34],对郭沫若及第三厅的工作给予了相当的支持。
周恩来经常鼓励党内的同志“勤交友”“统一战线就是交朋友,尽量多交朋友”[35]。在朋友间的交往中来进行思想的影响,扩大队伍,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工作的一种特殊方式。
(二)同业网络:“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除《新华日报》外,《新民报》《新蜀报》《大公报》以及国民党的《扫荡报》和《中央日报》都刊载了贺寿祝辞或者对纪念活动进行报道。在这些报纸之中,《新民报》《新蜀报》表现得更为积极。它们在当月13日就对三天后在天官府七号举行的郭沫若寿辰纪念会进行预告和报道[36]185,与《新华日报》的报道相互呼应形成祝寿舆论,其后更是在刊载纪念文章和贺电方面热情不减,《新民报》还刊发了苏联大使潘友新和苏联对外主席凯缅诺夫对郭沫若的贺柬[36]188-189。阳翰笙也在回忆筹备工作的过程时提及了这两份报纸,“这些报馆的记者多半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志”,活跃的报道背后是新闻界的统战工作。
《新华日报》和《新民报》《新蜀报》之间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1939年的“重庆各报联合版”事件中,《新华日报》早日复刊的要求得到了《新民报》的积极支持,两报在争取新闻自由斗争方面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37]。在《新蜀报》资金难以周转之时,《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拿出三千元现金帮助其渡过难关[32]417。
同时遵循着周恩来“勤交友”的指示,《新华日报》负责人和记者在新闻界中广泛交友。《大公报》著名记者陆诒、《新民报》著名记者浦熙修、赵超构以及《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邓季惺等,都与《新华日报》工作人员有着密切的来往,成为《新华日报》的朋友[32]65。
“皖南事变”发生当晚,潘梓年和石西民的等报社负责人分头到各个报馆说明“皖南事变”的真相,争取同业人员的支持。此后,一些报纸并未刊登国民党诬蔑新四军的反动命令,部分登载了命令的报纸则将其放在不起眼的版面进行边缘化处理,还有的报纸通过报道标题表示对该命令的不满[32]106。
可见在国统区,《新华日报》并非单打独斗,而是在新闻界建立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32]13,由《新华日报》牵头发起的“寿郭沫若”活动辐射至其他报纸,在非党派的民间报纸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组织网络:“集体组织者”
要把个人的祝寿纪念办成“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周恩来提出要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来参加筹备工作”[1],《新华日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5月11日,创刊仅四个月的《新华日报》探讨作为革命报纸的“理想”,借用列宁“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也是集体的组织者”[38]一言,提出报纸除了传达政策和口号之外,还需对如何实行政策和口号的斗争形式和组织方法进行指导,以实现“综合各种实际行动和组织实际的斗争”[39]的目标。此次祝寿纪念活动中《新华日报》亦是展现出“组织者”的角色形象,为党外动员工作付出不少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文化界的领导一方面是通过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及其下设的文化组来进行,另一方面主要通过《新华日报》来展开工作,实现“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40]。《新华日报》的公开合法性为相关组织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曾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张颖就说:“我们不少作统战工作的同志,都用《新华日报》人员的名义进行公开活动。”[35]负责南方局文委工作的夏衍同时是《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中的一员,主要负责文艺方面的写作[32]79。除相关负责人之外,《新华日报》的基层工作人员也是统战方针的执行者。周恩来曾就《新华日报》采访科的工作计划告知总编辑吴克坚和陆诒,明确指出特派员不能仅仅以完成采访报道工作为唯一要求,而是更应收集资料,向同情中共的各界人士约稿与征求意见[41]。“报道只是手段,统战才是目的”[42],将采访报道的过程作为与各界人士进行交流的方式,并极力争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将“统一战线”的方针渗透进报馆工作人员的社会实践中。
得益于此,负责筹备纪念活动的阳翰笙高兴地称大多数人士“都是我们的同志和朋友”“他们都高兴地表示愿意大力支持”[1],祝寿纪念活动不仅“动员了几乎是整个文艺界、文化界和新闻界”,还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著名人士如邓初民、黄炎培、章伯钧等的支持,轰动全国。
四、“报”“馆”纵横: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范本
在“寿郭沫若”活动中,《新华日报》 以“报”与“馆”相交、纵横交错的“阵地战”[8]172的斗争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一个范本。
“报”是以前台(公开)的报刊内容进行宣传造势,是报纸在特定历史时机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击。适逢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涯二十五周年,《新华日报》纪念文章和活动报道的登载完成了郭沫若作为中国共产党有机知识分子①葛兰西以社会生产的视角来关注“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之别,前者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后者则与所属的阶级有着紧密的联系。引自约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18.的大众化宣示。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久别归国的郭沫若“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后一珠血都要与国族有所效益”②此为归国前,郭沫若给四川达县城区第二小学全体师生的复信《复达县县小同学书——郭氏回国前的一封信》中的话。转引自何刚,王开志.“回首故乡”:郭沫若不同时期的四川叙述[J].当代文坛,2015(3):136-140.,他的身份与志向都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相契合。而在政党冲突的背景下,此次活动明面上是对郭沫若本人的加冕和推崇,背后则是以此来冲破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封锁,“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1],从文化领域突破重围,实现对国统区文化界的引领。
“馆”是以报社同仁努力编织的后台传播网络,推动了祝寿活动的声势。从内部观察,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新华日报》之间的沟通交流并不局限于前者对后者的领导,还存在着两者之间以个体的交往为基础,编织出传播网络,实现了上传下达。1938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中,党中央明确要求各地方党部将《新华日报》上的社论作为重点进行讨论和研究,其后还提出“每个支部应有一份《新华日报》,每个同志应尽可能定一份《新华日报》”的要求[43]。早期《新华日报》的传播网络是基于党组织的组织网络来建构的,其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播,也是中央组织领导支部的一种方式、支部之间连接的一种共同载体。
从外部出发,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44],个体的人际交往成为社会格局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勤交友”的指示也正是遵循着这一基本原则,《新华日报》管理层和报社工作人员从新闻界小圈子到社会各阶层,从文艺界到普通大众中都有着很多朋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搭建了《新华日报》与其他报刊合作交流的桥梁,并以《新华日报》为中心向社会其他阶层群体蔓延,密切了《新华日报》与各组织、各阶层的联系,最后通过报刊刊载的内容进行大众性传播,从而完成了报刊与社会大众的对话。
“寿郭沫若”活动的现实践行与传播网络的铺展密不可分,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是沿着人际网络、同业网络、组织网络三者交织而形成的“阵地”展开的。而在此之中,《新华日报》扮演着“通道”的角色,搭建从一个传播网络到达另一个传播网络的桥梁,完成三重网络之间的联结交叠,建立了“一个广大纵深的阵地”[32]64。
此次祝寿活动打破了“皖南事变”后文化界沉闷阴暗的局面,冲破了国民党的政治封锁,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一个范本。后《新华日报》又陆续为茅盾、老舍、洪深、沈钧儒等文化名人举办了寿辰祝贺、创作纪念等活动,成了“一种扩大影响的新的斗争方式”[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