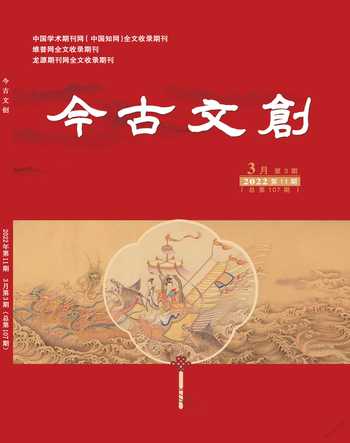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研究
2022-03-22邵毅
【摘要】 随着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这两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中国音乐学的研究具有针对性地更加形象生动起来,本文结合中国两门学科发展历程,对其概念与研究对象与方法进行了梳理,认真学习了相关的论文资料,并以内蒙古地区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为切入点,对两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因专门进行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较少,还有很多研究的空间。内蒙古地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研究中大量的巫乐祭祀活动中存在着很多的音乐方面的未解之谜,这些研究中音乐考古方面的研究还属于空白,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内蒙古地区音乐图像学和音乐考古学的具体研究中来。
【关键词】 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中国内蒙古;现状与不足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1-0089-03
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是于20世纪产生并发展的多门学科结合而成的新型交叉学科,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的可以更为细化的更加有针对性研究分支。它多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包含在考古学中,但有不同之处。中国学者为两门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研究成果为中国音乐学科的发展与文化传承提供了更直观更丰富的资料。从两门学科的概念与研究对象与方法及内蒙古地区研究的成果入手,希望更多的学者投入到研究中来。
一、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概念
音乐图像学是对各种有关音乐图像内容和形式以及其中的各种符号、题材等加以鉴定、描述、分类和解释的专门学科。该学科有利于了解乐器学、表演方式、音乐家生平、文化史四个方面,并且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结合了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紧密联系的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为一体的现代学科。
日本学者田岛翠在《音乐图像学》这篇文章中提到“《音乐图像学》是以美术作品为线索进行音乐史研究、是音乐史研究的一个方面,是一门交叉学科。可以说,《音乐图像学》是对‘美术作品中的音乐题材内容,进行分析与解释的有关音乐史的领域。’”[1]也有学者提出音乐图像学(Iconology of music)是20世纪西方学术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旨在对各种音乐图像的内容和形式及其中的符号,主题题材加以鉴定、描述、分类和解释,他处于音乐史、艺术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之间,是一交叉学科研究领域。[2]
音乐考古学(archaeology of music)依据音乐文化遗存的实物史料(发掘而得的或传世的遗物、遗址、遗迹,如乐器、乐谱、描绘有音乐生活图景的古代造型艺术作品等),借助考古方法来探讨音乐史、乐器史直至历史上的音律形态、音阶形态等音乐学课题的一门科学。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围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与美术考古、丝绸考古、陶瓷考古、青铜器考古等学科并立的,国际上称为音乐考古学。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音乐考古学比起一般考古学来,有其鲜明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研究对象上,音乐作品是以声音为媒介的,表演结束声音停止。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音乐随着时间流逝停止,对音乐考古来说,人们是看不到也听不到古代的音乐作品当时的演奏情形与音响效果的。这就体现了音乐考古与其他学科考古不一样的地方。
二、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音乐图像学这门学科进行研究的对象,简而言之首先是图像资料,是有关音乐体裁的图像资料,它的研究对象可以是音乐家的画像、奏乐图像、乐器、乐谱、音乐作品的标题以及设计音乐厅、歌剧院、各种礼拜仪式、世俗节庆、加冕典礼的画像等等,图像资料能为人们提供有关音乐家的生平、乐师的社会地位、音乐的实践、音乐生活和乐器等方面的宝贵情况和证据,它还能对早期的音乐观做出某些提示,从而在直观上扩大人们对音乐史的认识。
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首先它也是归属于一般考古学的范畴,音乐考古学是“根据与古代音乐艺术相关的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3]。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人类音乐演变的历史及探求古代音乐文化的演变过程,“从研究对象上看,音乐考古学是以古代人类音乐文化的物质遗存(包括遗物和遗迹)为研究对象”[4]。
主要的研究方法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成熟,王子初先生在2006年出版的《音乐考古》中提到了“音乐文物分类法”“音乐学断代法”“音乐文物测音法”和“音乐文物命名法”。
在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的发展中,有的学者认为音乐图像学是音乐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这样的说法还是不够严谨的,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是古代的图像,但是也可以是近现代的,尤其是国外的一些研究,比如研究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戏报、戏剧人物的海报等等也应该归属为图像学,在韩国学习阶段图像研究学习的内容分为了岩画、壁画、风俗画、照片等等的研究对象,虽然大部分都是古代,照片技术的兴起,是图像研究带来更多可能性,这跟音乐考古学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中,可以确定的是有部分图像资料,比如岩画、壁画、画像砖,雕刻、器皿上的乐舞百戏、宴飨、祭祀的音乐有关的图像,乐志仪轨上记录的宴飨图、出行图、祭祀图以及绢和纸作画的风俗画上的音乐图像等等,这些图像与实物资料,通过考古发掘而发现获得的图像,具有考古学价值、美术史价值和音乐史价值但是两个学科是有很多相互交叉的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都应该与音乐学这个大学科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并且都是音乐研究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三、内蒙古地区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的成果
近些年随著音乐图像学新学科的兴起,国内关于音乐图像学的研究越来越多了,但是涉及具体的研究不多,研究内蒙古地区的音乐图像学的笔者查找的资料中,以契丹和辽的资料比较多,如梅鹏云的《辽墓乐舞图像考古学观察》[5],文中对乐舞图像材料所涉及的阅且的名称记载错误的进行了调查分析予以更正,结合墓室的年代对乐舞图像阵型图进行了解读,对墓葬出土乐舞图像利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了梳理,发现了在时空架构上存在一定的变化和分布规律,总结出乐舞的实际的性质与具体功用。
陈秉义先生的《从音乐图像学看契丹——辽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6],契丹和辽的版图正好包括在内蒙古东部一带,文中用了82张图像资料,以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原乐器的传入;与周边各国的交流三个部分进行了研究,是音乐图像学中图像记录清晰、资料翔实的一篇论文。文章从图像资料中,利用博物馆、文管会和民间收藏中的音乐史料进行了十年的考察,见到了很多的壁画、砖雕、民间收藏的实物包括细腰鼓、绢画、书盒等等,通过图像资料研究出契丹—辽时期,唢呐在中国北方草原上是一件十分流行的乐器。还发现了契丹人制造唢呐的工艺流程。虽然没有找到文献资料的记载,但是在很多图片资料中与实物都发现了唢呐的存在。最后笔者也提到图像资料研究存在的争议问题,比如民间收藏品的来源复杂、鱼龙混杂、考证困难的问题,提出了比较可观的见解,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考古学方面因为契丹和辽部分版图在内蒙古,所以将辽代的研究如赵爱军《辽墓壁画中的乐舞图》[7]邱国斌《辽代散乐考略》[8]巴景侃《辽代乐舞》[9]都包含着音乐考古学的内容。
在内蒙古地区考古研究中壁画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涉及壁画的艺术形式、修复保护、形成背景、叙事研究、年代探索等各个方面,比较典型成果为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1974年文物期刊刊载的《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卷》的文章,截止到2021年6月24日已经下载1353次,文中翔实与简练的文字资料清晰明了地介绍了古墓壁画的情况,出现了清晰的墓室结构图与壁画中的大量图片资料,为研究学者提供了最为细致可靠的研究数据与珍贵的图片资料。
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中,音乐考古学专业安其乐《论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建鼓》[10]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汉代壁画中的建鼓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从建鼓的礼器乐器功能及建鼓的象征意义和鼓吏吏制制度入手,解析了建鼓在汉代的应用和兴衰的背景及背后蕴含的文化属性。在这篇文章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搜集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发现的汉代壁画中的建鼓随葬的等级,并以图表的形式进行了整理记录。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非常翔实的研究数据资料。武彩霞《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的乐舞百戏》[11]文中对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的乐舞百戏图像进行了分析,分别对表演形式、演出场地和表演者的服饰进行了分析,对乐舞百戏中的反映的现实生活,统治者的推崇等及乐舞百戏的艺术成绩进行了研究。虽然笔者是美术学专业,但是不管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内容都是和音乐有的乐舞百戏,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也有涉及音乐考古学的方法与知识。
现有的研究专门针对音乐图像学的不多,主要是研究的内容方方面面,水平参差不齐,虽然专门的图像学的研究不多,但是在音乐研究中运用了很多的图像研究,人们也可以称之为在壁画的研究中考古图像资料的运用,特别是墓室中的壁画与石窟中的壁画,在内蒙古各地散落了很多的壁画,有的是在古墓中挖掘的有的是在洞窟中发现的有的呈现在寺庙中,墓室壁画兴盛于两汉时期,在内蒙古地区的墓室壁画中,以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壁画比较有名,研究者最多,其中有安其乐和武彩霞的研究对音乐图像与考古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汉画像石墓和汉壁画墓,常见的有表现画中任务的宴飨及其中乐舞百戏题材的图、出行图中表现行进中鼓吹乐及车马配置等等、祭祀程序及即系礼仪物品图,这些都是音乐图像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在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是专门针对音乐考古学的有意义的研究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实践,内蒙古地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在这块土地上发现的岩画资料非常多,但是大多以单纯的图片记录形式进行记录,笔者所在的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前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2014年3月11成立了中国北方岩画研究所,研究所的发展笔者一起见证,从三皇体系岩画的发现、新石器各个时期期岩画的分期断代研究,中国北部地区重要的彩陶谱系研究、火神等原始宗教归类谱系研究等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果。目前三皇体系研究在中国走在前列、蹴鞠岩画,火神岩画等等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成果,并于2015年11月12日加入世界岩画联合会为第53个成员。这些研究中大量的巫乐祭祀活动中存在着很多的音乐方面的未解之谜,这些研究中音乐考古方面的研究还属于空白,所以音乐考古方面的研究在岩画方面还有很多的研究空间。这说明音乐图像学与考古学的研究在内蒙古地区还有非常大的研究空间。
四、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的发展前景
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虽然是不同的学科,这两个学科都是属于音乐研究的新的学科,两个学科的共同之处为都是交叉学科,两个学科之间有相互交叉的部分,都是为音乐研究服务的,都需要在音乐研究方面注意研究方法的深入浅出与通俗易懂,都具备图文并茂与生动的形象,都需要运用“二重证据法”来贯穿整个研究的始终。王子初先生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中注重了“二重证据法”注重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李荣有先生的《中国音乐图像学概论》《中国音乐图像学的第二个春天》[12]中讲述的文献为载体的乐志、乐典、艺文志等等记载了相关的史料信息,结合“图谱学”“金石学”的运用也将“二重证据法”贯穿在音乐图像学的研究中,这两者是一致的。“音乐图像学的研究,能够充分利用人的视觉功能,激发人们更多的使用形象思维、直觉思维、摆脱传统研究方法的禁锢、概念群的转运、至深而玄的思辨,最终达到‘以图出史’的目的。”[13]
五、结语
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学科的发展,很多学者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人们不会照搬国外学科发展的理论用在中国的学科发展,在两门学科的发展中,每一位学者都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与思考,结合中国学术发展的具体情况,不断地开拓与探索者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14]希望内蒙古地区的音乐图像学研究和音乐考古学研究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
参考文献:
[1]田岛翠.音乐图像学[J].人民音乐,1990,(1):51-53.
[2]缪天瑞.音乐百科词典[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
[3]王子初.音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4]邵哓洁.音乐考古学研究方法散议——王子初新著《音乐考古》读后[J].中国音乐学,2006,(04):134-137.
[5]梅鹏云.辽墓乐舞图像考古学观察[D].吉林大学,2009.
[6]陈秉义.从音乐图像学看契丹——辽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7,(04):1-16+207+106.
[7]赵爱军.辽墓壁画中的乐舞图[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02):65-73.
[8]邱国斌.辽代散乐考略[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02):77-87.
[9]巴景侃.辽代乐舞[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6.
[10]王清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欲上下而求索”——王子初先生与中国音乐考古学[J].音乐探索,2012,(04):23-26.
[11]武彩霞.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的乐舞百戲[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5.
[12]李荣有.中国音乐图像学的第二个春天[J].艺术探索,2016,30(06):109-113.
[13]刘东升.杨荫浏先生与音乐图像研究[J].中国音乐学,2000,(01):5-15.
[14]邵哓洁.音乐考古学研究方法散议——王子初新著《音乐考古》读后[J].中国音乐学,2006,(04):134-137.
作者简介:
邵毅,女,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学、民族音乐学。
2983501705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