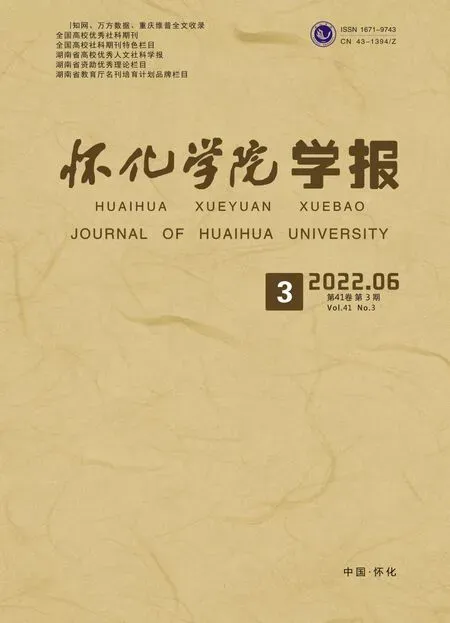1930年代老上海的现代空间与文化差异
——以施蛰存的《雾》为中心
2022-03-18高敏捷王再兴
高敏捷, 王再兴
(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施蛰存的现代书写有着特别之处。当1930年代上海作为现代都市大放异彩时,上海的“摩登”形象引发了许多关于“现代”的想象。在施蛰存的《雾》中,连接城乡的现代交通工具——火车,也参与其中,以一个微缩的现代空间,给予乘坐者不同于传统空间的现代体验。然而,即使在现代空间里,“现代”也不是唯一的声音。现代空间随着都市外来者(秦素贞) 的进入而显得十分复杂。虽然现代空间激发了女主人公的“本我”欲望,但不同的文化背景仍旧给人际交往带来了实际上的错位。现代都市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之间的差异,也随着女主人公欲望的幻灭而变得更加清晰。施蛰存在现代外在空间与心理内在空间的遭遇和撞击中,书写了城乡文化差异这一重要话题。
一、上海“摩登”及现代性想象
上海于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之后开埠,租界的开辟紧随其后。1845年颁布的《土地章程》明确了英商租地的边界,随后,租界的范围在多方利益纠纷及各国威逼利诱的手段中不断扩大。1853年小刀会起义以及186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促使大批华人为躲避战乱涌入上海租界。“华洋杂居”的新格局使租界的管理分工更加细密,西方城市管理模式逐渐成熟。到1921年,工部局①正式公布了单项《交通规则》。现代城市交通规章对市民生活的影响,从1931年至1935年间“平均每年达8000 多件”的被起诉交通违章案件中,便可一目了然[1]1-42。公共领域的严格管理,实际上强调了市民对城市建设的平等义务和责任,对于市民现代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与现代意识相连接的,还有随处可见的作为物理空间的现代都市设施。19世纪中叶,外商洋行进驻黄浦江畔,1862年西式马路静安寺路建成,1865年新型的煤气路灯在南京路亮起,1876年淞沪铁路通车,1881年大北电报公司开始经营电话,1882年上海电气公司点亮第一盏电灯,1883年自来水公司放水,1901年汽车传入上海,1908年有轨电车开通,1923年广播无线电台建成,1924年公共汽车通车……[2]7-18。这些不断发展、普及的新兴设施不仅是上海商业活动的一部分,还是都市景观的重要内容,同时在市民日常经验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此,上海这种“被建设”出来的现代性,带有浓厚的殖民性质。各方为了在政治、商业中更好地获取种种利益,使得上海的现代建设在某些方面有着与西方同步的现象。比如,在1895年12月28日电影于法国正式诞生不久后,1896年8月11日,就有西方商人在上海放映“西洋影戏”[1]201。电灯在上海的传入距离其发明时间(1879年) 也仅相隔了3年。可以说,租界的政治环境、商业环境、文化环境促成了上海与世界的接轨,使上海具有了“摩登”(现代的) 形象。
1930年代的上海也以一个现代都市的面貌呈现在现代作家的笔下,展示出新奇繁华的特征。茅盾的《子夜》里1930年的上海,冒着电火花的电车、狂风一样的汽车、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平地拔起的路灯、指挥交通的红绿灯、大大小小的洋房、各色各样的男男女女等等,都聚集在这一新世界的现代空间里。施蛰存的《春阳》里,有着上海同一年代的类似景象,店铺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化妆品、丝袜、糖果饼干。目之所及,每辆汽车、每扇玻璃橱窗,甚至远处摩天大厦的圆瓴形或方形屋顶,都明光烁亮。西方现代性在被物质所充分浸润的上海,是显而易见的。李欧梵将1930年至1945年的“上海摩登”阐释为中国的一种新的都市文化。上海的都市文化,作为“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3]7,随着物质的繁荣逐渐繁盛。早在1864年建造而成的“上海总会”俱乐部,其“专供社交和娱乐”[1]19的功能,便体现出上海的都市文化是紧密围绕着商业和消费的。百货大楼、舞厅、咖啡馆、报刊亭、电影院更是消费的重要场所。都市的景观与文化,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情感。
在施蛰存看来,现代生活里“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 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这种现代生活带给人的感情,与上代人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也不一样[4]。人们意识到自己所生活着的上海的迥然不同,产生了所谓的“现代”感受。刘呐鸥、穆时英等人便吸收现代主义艺术经验,描写他们眼中的或想象中的上海,在都市风景中感受上海“摩登”带来的浪漫和欲望。而上海的种种发展又使它与周边的小城镇拉开了距离,那些从未在上海生活过的主动由城镇进入上海的人们,则或多或少地对上海有着心理上的期待。在施蛰存笔下,无论是《春阳》中来自昆山的寡妇婵阿姨,还是《雾》中来自小卫城的单身女性秦素贞,“去上海”的行为都带给她们与欲望相关的想象。如,素贞希望寻到一个“能做诗,做文章,能说体己的谐话,还能够赏月和饮酒的美男子”[5]269做自己的惬心丈夫,但是在一眼看出去都是渔人的小卫城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于是她决心以给大表妹贺喜的名义到上海旅行。素贞的此次上海之旅可以说是一次寻找之旅,都市上海寄托着她的美好愿望。素贞对于小城镇之外的上海的想象,正是她对现代都市的期待,同时也是她对自身欲望的正视。
二、现代空间与欲望涌动
“火车”是素贞进入上海的重要交通工具,具有明显的现代意义。惠特曼曾在《致冬天的一个火车头》中歌颂火车头为“现代式的典型”“运动与力量的象征”[6]679。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的《铁轨之旅》也将铁路视为19世纪工业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标志和象征[7]14。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蒸汽机和电力的迅速发展,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1914年,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年能够旅行相当远的距离”[8]913。火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素贞的现代之旅,以及《雾》的现代空间建构,都离不开她所乘坐的这辆奔向上海的火车。
秦素贞生活在距离上海不远的临海小卫城,她坐船到城镇,再在城镇搭火车,便可去上海。《雾》中的火车是乡镇与都市的重要连接。素贞所生活的卫城,是具有传统乡土中国气质的村庄,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9]6。从乡土熟人社会中走出来的秦素贞,在踏上火车之后,进入了现代意义的“公共领域”;车厢里的这些人,是她以前从未见过的,他们于她而言,是现代意义的“陌生人”。素贞进入火车,便踏进了一个陌生人的空间,与传统的乡土社会区别开来,许多不认识的、难以接触到的人都出现在同一个公共空间里。以素贞的观察来看,车厢中的乘客有青年绅士、身穿旗袍的年轻女客、半老的妇人、乡下人等等。这些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不分性别,不分尊卑贵贱,只要买票就能踏上火车,同处于一个车厢内。如约翰·萨克斯《铁路的节奏》 所言,“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名望的人”“或高贵或贫穷”“着装迥异”“以同样的速度一起旅行”[7]191-192。火车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等级,建构了一个有着现代性质的公共空间。丰子恺在《车厢社会》(1935) 中把车厢社会看作人间社会的缩略图,把车厢看作“人间世的模型”[10]103-104。车厢里,乘客的言行举动、交谈内容,常能引起旁人的注意。比如素贞注意到旁边座位上的妇人拿出钱袋里的小镜子擦鼻子边的粉屑,她对面的青年注意到素贞掉落的手巾并帮她拾起来。车厢构成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为素贞营造了一个全新的环境,给予她认识新人的可能性。火车从始发站到终点站的过程,是从乡镇进入到都市的过程;从火车发动那刻开始,传统空间便被抛离,现代空间在流动中占据了舞台。在这个空间里,陌生男女之间的交谈被看作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雾》着重刻画了“火车”这一微缩的现代空间里,素贞的心理变化与欲望涌动。素贞刚上车时,“很羞涩,不习惯在许多不相识的人群中”[5]270,因此她坐在临窗的座位看窗外的风景,很少注意同车的乘客;即便浓雾使她不得不回头,她也低着头,在车的颠簸中沉睡。素贞有意识地压抑自我,直到火车没有征兆地中途停止。这一突发事件给她带来惊慌感与陌生感,传统礼俗、规则脱离了场景,也失去了对她的控制。缺乏现代生活经验的素贞,才在本能的作用下忘记拘束,注视起同车的乘客。于是她注意到了对面静静看书的青年绅士,他“柔和的容颜,整洁的服饰和温文的举动”,尤其是看诗的行为引起了她的好感。当她发现她幻想的理想丈夫突然间有了一个“完全吻合的实体”时,“她觉得本能地脸热了”[5]271。即便她转移目光,看向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她的内心活动也紧紧围绕着这一场邂逅。她感觉到青年绅士在频频看她,“在心的怔忡稍微安定了一会儿之后,素贞小姐忽然经验到了一种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光荣”,原本反对自由恋爱的素贞,此时也觉得“可以有例外”[5]272。她期望青年绅士与她谈话,她幻想着爱。当青年绅士拾起她掉落的手巾,把手巾轻轻放在她膝上后,她更深陷幻想之中,在爱欲的驱使下,以看似委婉实则主动的方式与青年绅士搭话。她逐渐忘记“在谈话的是一个不相识的男子”[5]275,甚而内心纠结着要不要告诉表姊妹们自己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好看、温和,说话文雅又懂诗的人。当素贞得知青年绅士也住在徐家汇后,她又幻想他同舅父相见时谈论到她的情景。一切的心理活动都随着她的欲望而展开。
素贞的欲望在踏上“火车”前就已经有了萌芽。她此次出行前便带有通过上海旅行觅得心仪丈夫的愿望,她所乘坐的火车,也成为一种契机。一旦踏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在空间的浸染下,陌生的作为现代媒介的公共场域便影响了素贞。寻觅的本能欲望原本就存在,火车到站前封闭着的公共空间为她的邂逅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陌生、新奇而又公开的环境让她克服了心理障碍,减轻了顾忌。火车旅行随着物理距离上与上海的逐渐接近,素贞的心理欲望也越放越大。她下车时,腿擦过陆士奎的膝盖,还“觉得一阵微细的快感”[5]278,与欲望对象的肢体接触十分直接地给她的“本我”带去快乐和满足。在火车车厢的现代环境与女性的本能欲望的相互作用下,秦素贞对心仪的陌生男子进行大胆的想象,附加层层堆叠的欲望,甚至下火车后,这种欲望和幻想也仍在继续。
三、“戏子”与“明星”: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差异
“车厢”提供了相识的场所、环境,但是又因其时长短暂,有着不稳固的特征,这也是现代社交的一个重要特点。秦素贞的此次邂逅没有迎来美好的结局,却不能归因于“现代”的不稳定性。她在得知陆士奎的身份后,与她的表姊妹有着不一样的反应,前者因其“戏子”身份而失望、幻灭,后者因其“明星”身份而憧憬、激动。两种天壤之别的感受背后,是传统与现代的不同文化体验在起作用。
素贞所受的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喜爱的是《西厢记》一类的传统爱情。她自视为“典型的多情的佳人”[5]268,希望能遇到一位般配的才子做自己的如意郎君。在火车上,青年拾起她掉落的物品,她道谢后却等不来答话时,就感到不耐烦,觉得他做事不爽快,进而想起“传奇上总是小姐吩咐丫鬟或老妈子去私约公子在后花园相会的情节”[5]273。可见,传统才子佳人的恋爱模式在秦素贞的内心是根深蒂固的。除恋爱外,素贞对于身份地位的判断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如陆士奎对于素贞舅父的职业的猜测(“做生意的”),让她感到侮辱。因为在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划分中,商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但在消费主导的都市上海,商人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有了根本的转变。显然,同一车厢里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评判标准。互通姓名后,素贞因使用了“你”字感到懊悔,虽然“你”这个称呼在上海十分普遍,并未引起陆士奎的注意,但素贞觉得用“你”称呼陆士奎十分亲热,语言的差异背后同样是文化差异。素贞对于青年绅士拾起手巾并直接把它放在她膝上的行为感到意外和仓皇,接连说着谢谢,并因第一次与陌生男子说话而颤抖。但于陆士奎而言,这是十分自然的助人行为。可见,虽然两人同处一个空间,但文化差异影响下的社交,对于素贞来说,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上。陆士奎所采取的现代社交礼仪,包括给名片的行为,虽然表面上阴差阳错地迎合了素贞的欲望心理,但实际上却不能与素贞的交往欲望相吻合。在《春阳》 中,婵阿姨与银行职员之间也处于这种错位情境,在两人短暂的相处过程中,都市人作为诱惑的一方,使都市外来者的欲望滋生,随着误会的产生,差异也逐渐明显。而让素贞欲望幻灭的“戏子”身份,更是传统价值标准在主导着她的心理,至此,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更加清晰。
《雾》中的都市上海有着不一样的文化,此时的上海,电影兴盛,电影明星十分受欢迎。1930年前后,“上海影院业急剧发展”,电影观众增加,1928年至1932年的五年间,“就新建了28 家影院”,其中一流的影院甚至“安装了价格昂贵的声片机”,并“配有冷暖器设备”[11]83。施蛰存的《在巴黎大戏院》中,拥挤着买电影票的人群以及主人公的心理,都由外而内地显示出“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当时上海的一种十分流行的社交方式。这种方式显然有别于传统森严的男女交往模式。男女在公开的场所交往,他们并排而坐,呈现出现代文化的解放特征。电影中的演员更是人们看电影前、看电影过程中、看完电影后谈论的对象,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中关注和模仿的对象。以1930年前后红极一时的胡蝶和阮玲玉为例,她们因自然、细腻的表演深受观众喜爱;她们拍摄的《姊妹花》 《神女》等经典影片为她们赢得荣誉。这“无声地将电影演员的社会地位提高到了一个空前高度”。她们的举手投足和时尚衣着,“在聚光灯下被成倍放大,感染着纯情的少年和痴迷的观众”,电影明星“成了无数年轻人梦寐以求的职业,而不再是任人玩弄、驱使的‘戏子’”[12]10。身份以及身份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在不同文化主导的空间里有着很大的差异。陆士奎的明星身份早已不同于传统文化中地位低下的戏子,他成为众人吹捧景仰的对象,融合于都市的审美文化。在电影文化艺术和娱乐消费环境的助推下,传统森严的等级系统对于人的约束和规定已经松懈。这是秦素贞所要前往的上海的都市社会和文化氛围。素贞不懂表姊妹们为什么会羡慕一个戏子,她自身的都市外来者身份,使得她的上海之旅有着不同于都市话语的特殊体验。当她脱离了火车空间后,上海的现代生活及文化还未浸染她,于是她原本的文化便起着全部的支配作用。
施蛰存在《雾》 中呈现了空间和文化的混杂,他没有对素贞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嘲讽和否定,或者对两种文化做激烈的价值判断。与他同时期的茅盾则大不相同。《子夜》第一章,上海吴家客厅里,既有金融界的大亨,又有工业界的巨头,还有“虔奉《太上感应篇》的老太爷”。吴老太爷从农村进入都市,上海的声光化电及各种视觉、听觉、嗅觉等的刺激,横冲直撞,直抵吴老太爷的心灵,使他由目眩、耳鸣、头晕,到精神发痛,最终脑充血而亡。虽然内地还有无数的吴老太爷,可“吴老太爷们”一旦到了上海就要断气。范博文更将乡下来的吴老太爷比作“古老的僵尸”,称其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在茅盾笔下,传统的乡土中国宛若一座“幽暗的‘坟墓’”,遭到现代的无情的否定,“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可以预见性地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很快风化[13]23-25。在这样的表述中,城市与乡土完全对立,且前者具有压倒性的力量。施蛰存则没有如此急切的社会心理。他笔下进入上海的人物,大多来自乡镇这一特殊中间地带。这些人物以女性居多,她们仿佛只是经过了上海,身体与心理在传统与现代中穿梭,传统与现代又在游走于城乡之间的人物的身心上彼此混杂。两种文化虽有冲突,但更多是新与旧的并存,哪怕是在都市上海,“新”也并非完全覆盖、遮蔽了“旧”。施蛰存在心理层面给予了“旧”自由活动的空间,这是施蛰存作为一个现代作家的特别之处。
结语
施蛰存把现代空间作为个人现代心理意识表现的舞台。在火车车厢这一全新的现代空间里,秦素贞逐渐放下戒备,对现代性体验产生接受心理,并大胆畅想,勇敢地与陌生男子交谈。“火车”本身的特征使得对于心理的流动变化及其叙述变得十分自然,当它奔向现代都市,处于这一空间中的乘客的心理也在逐渐地变化。施蛰存抓住接受现代性经验后的心理渐变,书写都市外来者素贞的心理和欲望的变动,不仅在《雾》中书写了空间与心理的联结与共振,更发掘了现代空间里的复杂性,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痕迹。传统与现代不同的文化认知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织:秦素贞对陆士奎的误会,以及与表姊妹之间的差异,是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冲突。我们从这一冲突中可以预见,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转变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之后几十年的社会发展恰是最好的例证。这两种心理、两种生活方式、两种文化经验在同一个中国共存。它们之间的矛盾与磨合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又被不同的作家不断地书写出来。
注释:
①工部局,当时称行政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后改称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是租界的最高行政机关。参见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