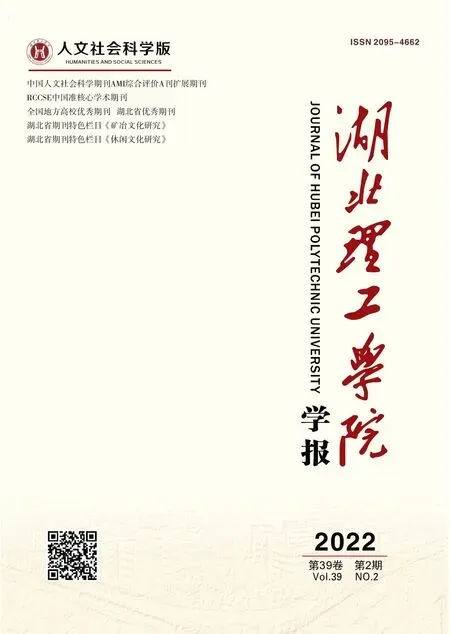从“白蛇传”的重写现象考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1930—1949年)*
2022-03-18崔芃昊
崔芃昊
(北京语言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3)
“白蛇传”作为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其故事文本也成为了历代文人“借题发挥”与“故事新编”的重要资源。无论是明末冯梦龙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要表述的“警世”与教化,还是“五四”时期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责怪法海“太多事”的启蒙批判,“我注六经”的重写背后指向了神话文本中的复杂性,而重写中作家的“主体性”参与及其建构的时代意识形态话语则成为阐释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如叶舒宪指出:“将每一个神话整体作为一个‘能指’,放置在它所由发生的文化和语义背景之中,从该神话与该文化意识形态的联系中去解译其‘所指’。”[1]58因此,当我们把“白蛇传故事”的现代嬗变作为一系列符号表征系统时,就必须将其整体看作一个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庞大文本。当广为人知的神话文本在作家的重写中发生意义更变时,文本所折射的则是一个时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政治选择,并显现出“重写”与社会意识形态间的症候关系。所以,在对中国1930—1949年间的“白蛇传重写”现象进行分析时,不仅要关注到文本本身的叙事特点,更要返回到时代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
一、“白蛇传”重写的现实主义转向
20世纪20年代末期,随着青年知识分子启蒙愿望的破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人民对激烈的政治革命的诉求再次回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心。无论是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还是少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共性体现在知识分子的落脚点都转向了改造社会的实践行为。这种观念的变化以陈独秀尤为明显,曾经倡导“伦理觉悟”的文化斗士,这时却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2]21。正是在这种“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语)的时代语境中,创作者们的文艺观也随着主流意识形态而发生变化。如创造社与以蒋光慈为代表的太阳社,率先进行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以及此后取而代之的是左翼文学所宣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这些主张共同指向了一种文艺观上的改变,即“五四”时期的“反映论”“真实论”到革命时期的阐释发生了变化。在左翼批评家的眼中,作家对社会的反映需要“再现”而非“表现”;文学的“真实”逐渐脱离了审美艺术的范畴,而与作家的政治立场发生了直接联系[3]20。与“五四”纷繁的表现流派不同,更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现实主义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主流。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外敌的侵略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在政治意义上更出现了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的分化,也使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意识形态更加复杂。在这种局面下,“通过文学来干预社会与政治”的写作倾向成为民族危亡时最明显的文学表征,于是,包括“白蛇传传奇”在内的神话历史重述文本群中,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的叙事特点就是“古今杂糅”式的现实主义转向。
与高歌猛进的“五四”时期相比,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白蛇传”重写在文本基调上呈现出了由表现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回顾“五四”文坛,知识分子们表现出对传统文化集体理性的深刻反思与对西方人道主义主体性的高度认同,在启蒙的迫切心态中,作家们就“1924年9月25日,杭州西湖畔的雷峰塔倒塌”这一社会新闻进行了文化象征式的追溯,如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4]180刘大白也在杂文《雷峰塔倒后》中说:“当他(法海)用权威的砖垒成这魔塔的时候,早已经注定有今日了。”[5]307以狂飙社为主的文学干将们更掀起了一股对“白蛇传”重写的热潮,高长虹、向培良就以表现主义的手法将“白娘子”注入现代意识:“我独立在船头,乘着激流向金山寺去……这时候我们还是妖精吗?并不是为了自己取得什么,而是为服从伟大的理想和崇高的感情”[6]351;“为了爱情,为了牺牲,那仙草是属于我的,偷盗在我是最大的正义”[7],可见“白娘子/启蒙女神”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中被“询唤”而出,并以一种女性的、反抗的、自然的、“为人生”的姿态贴合着启蒙意识形态的建构,作家的重述行为也与时代演进形成了同构关系。然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白蛇传的重写文本则以一种“边缘的”“解构的”现实化立场与民族救亡运动对话,作为寓言符号的“白娘子”同样发生了身份意义上的降格。如谢颂羔《雷峰塔的传说》就在改写中褪去了前文本的神话色彩;秋翁(平襟亚)与包天笑都将作品命名为《新白蛇传》,可见其都在“求新”中追寻故事的颠覆,索性将白娘子置身现代,在古今融合中放大意义的空间。这些文本在讲述故事时冷静而客观许多,褪除了表现主义戏剧所表现的自我扩张情绪,将叙事的重心放在“白蛇传”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上,呈现了祛魅书写的状态。
若以唯物史观的角度考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神话重述现象,那么重述的“现实主义”转向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文艺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发生改变,面对疮痍的社会现实,能够承载政治性诉求的创作手法成为了时代的要求。在重写领域,“借古讽今”式的表现方式恰好满足了无产阶级文学功利性的要求,最具代表性莫过于鲁迅晚年的小说集《故事新编》,无论是《非攻》中以墨子遇见的“募捐救国队”来影射国民党反动政府借“救国”之名义敛财,还是以《起死》中吹起警笛的庄子表达对现实处境的无奈,重述文本都统一的将历史人物与现实的社会事件联系在一起,寻求在时空的错位中展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当然,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同样存在着如施蜇存《石秀》《鸠摩罗什》这样的颇具现代主义风格的心理小说。在此谈论的现实主义创作转向,则是追求一种小说与社会现实意义的建立,有别于架空社会的激昂呐喊。
在现实层面,国内知识分子在经历“四一二”政变后的消极情绪和国际上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影响,同样能够解释这一现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些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家就产生了一种认知转变,即由“文学决定论”转换为“文学无用论”。鲁迅就对汪静之说过:“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而已集·答有恒先生》)。在创作领域,转变最明显的是当年创造社领袖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剧,基于此明确提出“先欲制今而后鉴于古”(《我怎样写〈棠棣之花〉》)、“失事求似”(《历史·史剧·现实》)的创作原则,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笔下所重述的人物都被赋予了高度的政治性。符合革命要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逐渐取代了早期“进化论”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早期苏联“拉普”也指责浪漫主义为“唯心主义”“没落阶级的产物”,这都加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化”的进程。
此外,20世纪30年代神话科学的发展也是导致在重述白蛇传中发生祛魅的动因。如闻一多早年对古代神话的系列考察(后集结成论文集《神话与诗》)、茅盾著有奠定中国神话学理论基础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以及郑振铎以弗雷泽人类学方法写就的《汤祷》。可见在中国神话学者的眼中,神话学的科学性是极为关键的,他们往往强调神话学是利用了“科学的视点”来审视“怪诞荒唐、不合理”的神话[8]71。不过,从属于“民间传奇”性质的《白蛇传》在后来的袁珂的“广义神话”中才被归类于神话范畴,在小说的艺术创作方面也不太遵循于神话学解释的范围,但在重述文本中仍有破除迷信的坚决态度:
许宣、许宣,做人要有一点常识。人是不会变成蛇的,蛇也不会变成人的。一个不良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蛇,或骂他一声畜生。但人还是人,蛇还是蛇,此理甚明[9]44。
基于以上论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纷繁的思潮中,相较“五四”传统,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在“现实化”主潮的影响下,白蛇传重述出现了三点最为明显的改变:
第一,白娘子走下神坛,由“女神”转变为“凡人”。如前文所述,白娘子在“五四”时期被塑造成了一个向往自由、追求爱情并具有反抗精神的启蒙者形象,其姿态是自上而下的、是个体的。而在抗战时期,白蛇和小青首先在现实化的语境中丧失了变形的能力,成为了一名普通人——“白娘娘并不是什么人妖,或是什么白蛇变的。她只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古代女子。”(谢颂羔《雷峰塔的传奇》)、“小青去年到了上海,改名刘美嬢……现在帮着她丈夫做西药生意。”(秋翁《新白蛇传》),“凡人”化的白娘子以大众身份出现在读者视野中,其姿态是自下而上的、是群体的。这种对传奇人物神性的祛魅处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让传奇故事丧失了本有的美学色彩,但体现出的是作家们对知识分子群体内部自我狂欢的批判,并试图在文本中体现一种与社会接轨的群体意识。
第二,作者态度由对故事的歌颂转变为戏谑与讽刺。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就是文本中白、许爱情线索的淡化以及大量相关情节的删除,作者仅仅是把人物的名字摘录过来,借此编织着新的故事,不惜以破坏“母文本”的主题为代价,来反映不良商战、倭寇入侵以及财富争夺等社会现实的黑暗。叙述者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不过,爱情毕竟不能脱离生活,恋爱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分,做人,不能单讲恋爱而不谋生活。”(秋翁《新白蛇传》)。与之相随的是,艺术手法方面从抒情到议论的过渡,“五四”时期创作者借白蛇之口表露的诗意激情荡然无存,冷峻的讽刺和油滑的戏谑成为了新的手段。
第三,故事时空由传统的“神话/历史空间”转变为现代都市。自1933年茅盾的《子夜》问世后,开辟了对都市问题进行剖析的文学传统。而作为社会矛盾最集中也最为明显的大都会上海,造就了都市景观与文学景观的互文关系。正如李欧梵说:“而这些物质载体(西方的物质文明)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既是上海现代性的物质性呈现,同时也营构了鲜活灵动的日常生活的摩登上海。”[10]357这种关系同样体现在白蛇传传奇的重述中,像秋翁的《新白蛇传》与包天笑的《新白蛇传》不约而同地都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到现代的上海,并以一种“闹剧”的形式重塑故事情节,以致与公共认知中的古代传说形成巧妙的贴合,重述也在时空张力中产生一种狂欢化的特征。这倒是与王德威在论述晚清谴责小说时特征相似——都是一种“中国牌的荒诞现实主义”。
总的来说,上述文本都以一种降格的倾向将白娘子从“神”变成“人”,即使在时代意识形态处于一种相对割裂的条件下,作者仍然体现出了“现实主义”的转向,通过对前文本的消解来还原文学与社会的现实意义。
二、文本颠覆中的祛魅与讽喻
茅盾在给宋云彬历史小说集的序言中评价了鲁迅的《故事新编》:“而他更深一层的用心——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与爱,乃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则我们虽能理会,却未能学而几及。”[11]2随着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多的新事物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而社会阶层间的矛盾也在逐渐暴露出来,成为文艺作品反映的主题。在神话重述的领域中,如茅盾对《故事新编》的赞赏一样,“旧瓶装新酒”的改写模式成为了一种时代潮流。而谢颂羔《雷峰塔的传奇》、秋翁(平襟亚)《新白蛇传》和包天笑《新白蛇传》三篇小说,则为我们提供了洞察“现实主义”书写与讽喻指涉的窗口。
(一)谢颂羔《雷峰塔的传说》
谢颂羔《雷峰塔的传说》基本上承袭了传统小说中的前半部分情节,故事从许宣游湖初遇白娘娘和青青开始,一见倾心,后多次登门拜访,二人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由于许宣寄居在姐姐家,处处受到姐夫的排挤,加之在药铺工作的乏味,故每天只感到生活的烦闷。白娘娘出于好心,借给了许宣五十两白银,帮助他做起自己的买卖,然而这却遭到姐夫无端的嫉妒,于是设计陷害许宣,由于在抓捕过程中白娘娘机智逃脱,便造谣白娘娘是妖精变的。后来许宣被发配到苏州,再次偶遇了白娘娘,经过一番解释,二人重修旧好。故事最后,二人终成眷属,不料黑心商人李老板却垂涎白娘娘的美色,妄图侮辱她,但白娘娘仍然化险为夷,恼羞成怒的李老板只好再次以“有白蛇”谎言相诋毁。最终,结局以白娘娘喝了道士的仙水后安然无事,民众替她登报澄清猝然收尾,叙述者“我”的故事也讲到白、许二人成婚为止。在对前文本的增删上,谢颂羔保留了“借伞”“迁居”“端阳”等基本情节,而在祛魅的语境下情节的微妙变动,是需要关注的焦点。
可能由于谢颂羔的贡献更集中在基督教传播领域,他在1939年出版的小说《雷峰塔的传说》在文学研究界少有提及。只有李斌《“白蛇传”的现代诠释》[12]和吴嘉俐《“白蛇传”传说中的形象塑造与中国现当代文学》[13]中有做文本分析,而且对主题的诠释都是以“反封建迷信”和“大胆追求爱情”的反抗精神为落脚点。的确,文本中透露着浓重的“五四”遗风,叙事者“我”也以一种公允的立场来宣扬进化论。但在上述研究中,都只关注到了“白蛇”变成“凡人”后所传达的科学精神,而忽略了在情节删改和现实化语境中的另一层含义。
文本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对前文本传奇色彩的削减——白素贞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这无异于在根本上将白娘娘从“妖性”的原罪中解放出来。随着这一故事核心矛盾的变动,原有情节也出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式的改变:“盗银”成为了许宣姐夫勾结官府的诬陷、“端午惊变”成为了那些欲求不得之人对白娘娘的造谣。当然,文本显然为寻求一种“神/人/妖”的平衡,索性删除了法海的角色,只是以一个“不守清规戒律的和尚”来替代。值得注意的是,当法海作为一种道德层面的惩戒者的消失(无论是否承载着封建意识),白蛇也丧失了呼风唤雨的法力,而以一种自我收缩的方式变成了一个弱女子时,传统重述中的“人妖不可共处”及其所衍生的一切如“反封建”之类的象征意义,都在祛魅中烟消云散了。而取代其成为新的矛盾焦点的则是现实中人与人的矛盾,如许宣与亲眷之间的不和:
他姐夫姓李,是一个小吏。说话有道理,但是存心不良,缺乏爱心,对于许宣的待遇一向不诚恳……如今,这位李先生对于许宣的行动大不满意,所以心中存着一种歧视的心,想要从此驱逐他出去。
……
李先生更加动怒了,所以说:“你要搬出去,非得把饭金一起算清不可。”只有阿姐看着他们的怒容,知道事情有点坏了。她说:“大家是亲眷,何必如此不客气呢?”[9]31
又如官府查案无能,便捏造证据诬陷他人:
他们所看见的都是一些兔子、金鱼等动物。凡不爱动物的人,都觉得那是自己讨厌的东西。他们也许看见了这些虫类与四脚蛇,于是兵士们相信白娘娘和青青是捉摸不定的人妖,那种无稽的谣言更蜂起了[9]37。
文章最后,作者近乎一种评议的方式对人性的丑陋进行批判:
就在这里,我愿意加入一二句闲话。许宣是一位忠实的男子,但是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势,所以在一般的官吏与商人看来,是不配拥有一个美貌的女子做他的妻子。他如果真的要想吃天鹅肉,唯有下地狱,或是成为一个牺牲者。同时如果一个女子不知自爱,与一个没出息的男子恋爱,结果也唯有资本家的欺侮与凌辱,这是社会的不平等,自古已然[9]60。
在白娘子丧失了形变能力后,她所承受的是一种女性处于社会关系中的无端的伤害,这些伤害来自于“商人”“官吏”以及那些可叹的“读书人”。文中一系列社会身份称谓的出现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可见作者在情感态度上已经放弃了“五四”时代那些高高在上的伦理批判,而是借助祛魅书写,直指现实社会的灰暗面,披露人心的险恶。作者还极力挖掘着白娘子身上的女性特质,《雷峰塔的传奇》可谓最早表露出白蛇性别特质的文本,我们几乎可以从“凡人化”的白蛇传中看到早期问题小说的影子:“我们女子在社会如同弃物。有了丈夫,便会有人奉承,没有了丈夫,便遭人欺辱或遗弃。要寻一个同情的男子与他谈谈心,真难如登天。因为社会组织如此,女子也唯有自己忍受自己。”
(二)秋翁《新白蛇传》
1941年,日本对上海租界全面侵占,“汪伪”政府被扶植上台,上海彻底沦为半殖民的“孤岛”。而正是在日伪政府用高压手段管制着新闻、出版以及文化市场时,被政治性意识形态所约束的文艺表现则出现了一股逆流,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感正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即以《万象》杂志为阵营,所创作的一批“故事新编体”的重述文学,如秋翁《新白蛇传》《孔夫子的苦闷》《潘金莲的出走》、吕伯攸《孟母六迁》、董天野《潘巧云画传》,等等。这些作品都以一种“连接古代与现代、沟通东方与西方、穿梭传说与现实”的艺术形式对前文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意义重构,他们旨在选取大众所熟悉的典故与传说进行改写,在风格上呈现出戏谑和讽刺的笔墨。其一方面延续并丰富着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则表现了沦陷区作家在半殖民社会中的现实焦虑。
相较谢颂羔将白娘娘变为“平凡女子”,秋翁(平襟亚)在《新白蛇传》不惜让白娘娘、许仙一干人等以丑角的形象登场。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修炼了三千年的白素贞因与许仙恋爱,不得不放弃了早年做妖时用于偷盗的“搬运之术”,但因经济上的拮据而时常感到苦闷。有一天白素贞得知自己原来的使女青青在帮助她丈夫做西药生意,于是劝许仙以囤药的方法来获得厚利。恰好许仙曾经做过药店的营业主任,并且有两位爷叔正是上海西药行业的巨鳄,便在一番疏通关系、上下打点后开了一个“保和堂大药房”。然而,在一次店内会议中,职员们对药店的营业方针提出建议,将“济世利众”更变为“囤积居奇”,毕竟薄利多销的策略远不如多多赚钱来得实在,于是白素贞秉着“有货不愁卖”的宗旨开始大量囤药,做起了“半开门”生意,置那些染病的百姓于不顾,一味等待物价上涨后的暴利钞票。但不曾料想,因长时间没有出货,仓库的囤药有大半都已发烂,若不大批出笼恐有损失。此时白素贞顾不得什么做人的规则,吩咐小青秘密去自来水厂投毒,进而全市流行起瘟疫,便一次性地将坏药清仓,狠狠地赚了一笔。白素贞与青青贪心不足,索性变回了两条小蛇,潜入米仓大量吞米,吐出来卖又发了笔财。可许仙此时患了伤寒,自己的药店唯独缺他所需的药,别家同行又不肯卖,白、青二人只好乘着飞机到国外去买,总算保住了许仙的性命,还被传言说白素贞是去了山上盗了仙草,大家都夸赞她有义气。而故事的结局则是老和尚(法海)以买药为由,用瓦钵收了白蛇,自行远去了。值得注意的是叙述完故事后的那段评议:
但世人不察,没有知道它下毒的酷辣手段,所以还有人称它“义妖”。尤其是那批奸商们,还抄它的老文章,仿行它的囤积居奇,高抬操纵,道说是“以义为利”。不过是那批奸商本领没有白蛇大,只学会了它的囤积居奇,却没有想到它还有“下毒”这一招棋,所以终差它一筹……
——一九四二·新端午·秋翁于雄黄酒畔[14]42
这段文字中,有三处值得品味的细节:第一,在叙事者语境下,白娘娘的人称代词始终是“她”,而《新白蛇传》则是首例用“它”(按:文本中为异体字“牠”)来指代的。这一指称上转变的目的是将白素贞的人性降格,从“人型蛇胎”到“人面蛇心”,进而延展到“发国难财”这一群体的批判;第二,文章的落款以“新端午”作为时间节点,恰好呼应了标题“新白蛇传”中的“新”,“端午”在传统意义上时间度量并无新旧之分,故秋翁所谓的“新”必然指代的是时代面貌的更迭,是以反讽的手法来暗喻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第三,同样是落款中,作者自居于“雄黄酒畔”,这就又与“白蛇传”的故事架构产生了联系,雄黄酒在故事中能够让白蛇显形,让世人看到她的丑陋与妖性,作者则是借“雄黄酒”讽刺现实社会中的恶毒人心;另一方面,作者又仿佛置身“酒的海洋”中,以醉态或戏谑逃避着意识形态的控制,揶揄着读者的立场,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比较“怯懦”的方法来面对社会/政治问题[15]207。正是对词语“能指-所指”意义生产过程的巧妙运用,达到“双关”的效果,才使作者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了释放空间。
此外,文章中充满了大量的荒诞色彩与转折情节,同样是对前文本中的情节单元的颠覆式改写,如“盗草”中本表现白素贞的情义转变为荒诞的黑色幽默、“合钵”中原表现法海的不近人情转变为收服恶妖后的大快人心等等。在对上海商界的“横截面”式的问题剖析中,秋翁通过对白、许的丑化达到了一种“闹剧”的效果。故事中,文本的原始意义与现实意义的交错与重叠成为了闹剧模式的潜在结构,白蛇在抛售霉烂药物时,许仙却患了伤寒,却又因其他商家的囤药而自食苦果,而当走投无路的白蛇只好去外国买药,却又因此得了美名。我们看到,作者呈现的是一种闹剧的、价值颠倒的社会,但渗透其中的却是对政府腐败与人民疾苦的哀矜关照。
(三)包天笑《新白蛇传》
无独有偶,包天笑于1948年7月至1949年4月在《茶话》上连载的小说也叫《新白蛇传》,故事同样以现代上海为背景,表现十里洋场的现实种种。与秋翁不同的是,包天笑版的《新白蛇传》无论是在文章体例上,还是在故事情节上都进行了极大的扩容,作者将商市、军政、家庭、婚姻、住房等20世纪40年代上海所出现的问题统统纳入故事框架中,力求在“白蛇传”感觉结构的格局中,以一种万花筒式的笔法描摹浮世众生,并以“草蛇灰线”的方式将对拜金主义的批评贯穿于他所营造的喜剧氛围中。
故事中,在封建包办婚姻下,两年前白素贞嫁给了一位上海年长的富商,但不过一年,富商便猝然离世,将一笔丰厚的遗产留给了白素贞。因此,年轻的遗孀白素贞也遭到了众多非议,身边围绕着觊觎她财产的人,又因她“身材窈窕”喜欢“徐吐香舌”,被人们闲传为“白蛇精”。作者正是以此情节为核心,环环相扣进行铺陈,例如从许仙和白素贞的结合带出婚姻问题:
至于钱,这是身外之物,我的就是你的,新式婚姻下我们两个是共产[16]160。
以金老太太的视角表现国民党士兵欺压百姓:
那些“不允许占住居民用房”只不过是他们骗骗老百姓,打的官腔罢了……他们占住进来,所谓“你的就是我的”,毫没有一丝顾恤。你要是和他们理论一句,他们板起面孔来,拔出手枪来,吓也吓死了[16]159-160。
又如以小青的婚事表现阶级矛盾以及小农的愚昧思想:
小青的哥哥是个贫农,种几亩田,不够一年的开销,常常借债度日……他盘算着将妹妹许配给这财主,所有的债务可不急还,而且还可以得到一批彩礼……在乡下人的目光中,便是个财主,将来有了一座靠山[16]107。
本文在情节上的设置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展演着现实社会熔炉中的百态人生;取材于“白蛇传”的人物设定也给予纵向的延展,将笔墨触及到角色的家庭谱系;在艺术风格上,写实之余多有幽默讽刺,一改人们对“白蛇传”的悲剧印象。所以《新白蛇传》可以说是完全跳脱出前文本的新故事,而仍以“白蛇传”之名来架构故事,可能是一种出于实利的商业噱头,这同样是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出版业回归繁荣的一种表征。
虽然有研究者认为,包天笑所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亦称“礼拜六派”),是现代文学史中宣扬趣味主义的一种流派。并披着“超政治”的外衣,表现出迎合小市民阶级消闲复古的倾向[17]133。但其似乎忽略了“游戏”书写背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在《新白蛇传》中,包天笑在琐碎而迟钝的叙述中有意识地采用了一组故事时空上的对位,试图在“今/昔”(时间上)与“上海/苏州”(空间上)的对比中建立一种隐性的讽刺张力。我们通过两段文字考察这种对比:
你知道,如今这是一个流氓的世界!……多的是白相场,譬如跳舞场、夜总会……上海的旅馆,有好多可以说都是藏污纳垢的所在,喝酒,赌钱,玩女人,避开了家庭,那是一个解放区域,而商量许多不可告人的事[16]146。
金老太太说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游船去玩的,在文人的笔下,称之为画舫……在尉门外面,有一处地方,换作荷花荡,在那里一望无际,尽是种的荷花。当荷花盛开的时候,我们便荡入荷花深处,欣赏那翠叶红裳……苏州那种文人学士,又造出什么六月廿四日,是荷花的生日,到了那一天,大家便荡进荷花中,给荷花做生日。”[16]156-167
其中,第一段是李克用的心理描写,故事中他担任警务的官职,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显得游刃有余,并享受着“走人际”所带来的利益。第二段是金姨母在与白、许二人夏夜纳凉时回忆,诉说了她年轻时在苏州的游玩经历,并感念如今物价之高,已经很少有船家载人游湖了。不难看出,文本中作者的隐含态度已经呼之欲出,即对全然物质化的现代时局的失望,以及对过去淳朴时光的留恋和惋惜。在文本中,作者有意在充斥着大量的“金钱”“资本”“物价”等符号的话语中插入了一段对旧时风物的描写,并利用上海(现代且腐朽)与苏州(破旧且朴素)“双城记”式的空间构建,巧妙地遁入了一种田园主义传统,在文学地理景观中呈现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并借此反衬城市文明的病态。
实际上,包天笑的《新白蛇传》始终贯穿着对庸俗拜金主义的批判,故事中一切矛盾的中心都源于白素贞继承了大笔遗产,于是李克用、法海、潘三思等人才轮番作恶;金钱同样消蚀着许宣的亲情关系,当许宣再次回家看望姐姐时,开始以“小金鱼”来作为拜访礼,原本单纯的许宣也学会了用“经济”去套别人的话。于是,许宣的形象从初到上海淳朴的“都市漫游者”,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会运用话术、人际关系的药铺商人,似乎昭示着许宣正在这种不良的社会环境中慢慢变成下一个李克用。
此外,文本中的一些小角色,如投机发了国难财的蟹壳黄阿金、冒充经济警察去骗取钱财的花宝生和小山东,以及完全改变了形象常常吃喝嫖赌的“花和尚”法海,这一群像都对金钱有极其敏感的嗅觉,对待道德的态度更是模棱两可。这都体现了包天笑对社会所笼罩着灰暗道德形态的批判,以及对金钱成为社会价值统一度量的反思。
三、现实焦虑下的价值回溯
严家炎在总结文学艺术流派和民族历史的关系时提出,文学作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流派的命运取决于艺术地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18]322。纵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白蛇传重述文本,作者们运用现实化的书写策略,在祛魅与讽喻中颠覆文本,旨在以一种喜剧的效果和通俗的形式来表现抗战环境下的现实焦虑,这同样是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应。处于沦陷区的作家受到当局(汪伪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的控制,无法直接与抗战时无产阶级文艺主潮形成合流与对话,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这类作品面对时代的发声,无论是谢颂羔《雷峰塔的传说》对人心丑恶的批判,还是秋翁在《万象》以“故事新编”体进行的曲笔讽刺,都是一种在现实压迫中的委曲求全。因此,或许可以称之为抗战文艺统一战线“合奏”中“较弱的声部”。正如有识者说:“抗日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战争,时代的动荡迫使滑稽作家们把创作视角再次投向政治社会中去。说实在的,在现代中国任何舞文弄墨的人要完全脱离政治社会都是不可能的……(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太激化了,令人不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多了。”[19]288-289
事实上,若以文学批评发展的视角去解释重述文本中祛魅和谐谑的倾向,可能会明晰得多。刘勰早在《文心雕龙》中就独撰《谐隐》一章,评价了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以及东方朔的一些作品,并总结了滑稽文学的美学价值:“辞浅会俗,皆悦笑也。”[20]133以及社会功能和价值标准:“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戒。空戏滑稽,德音大坏。”[20]138自这里,刘勰提出了滑稽文学中的“谐隐”有着双重影响,即对政治和社会道德的“讽戒”与塑形作用,或沦为一种混淆价值的“油滑腔调”,诱导大众审美趣味趋向恶俗。到了现代,鲁迅也对《西游记》中的戏谑倾向进行了评论:“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21]171王德威则从晚清“谴责丑怪”小说中挖掘出新的价值:“我们被导向一个异性婚姻、孝悌忠信、政治网络、家庭关系,种种价值相互消长合纵的世界,因此见识了一种最奇特的、最丑怪的叙事美学。”[22]252可见,从批评家们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滑稽小说作者的共同倾向,即戏谑与幽默背后的现实焦虑。这无疑是一种值得讨论的美学现象,所谓的“游戏”书写也并非意味着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这些文本背后仍然拥有与“中心”对话的渴望。
回到该时期的白蛇传重述文本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现实化”语境的改写下,三篇文章的作者除了对现实的讽喻的批判外,都出现了一种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对知识分子的嘲弄:
例1读书人读了一些书,常喜欢作欺辱舞女的事。这是文人无行。古今一例[9]43。
例2 我们以前的使女——小青,她去年到了上海,改名刘美嬢,嫁了一个诗人,唤作武大郎,现在也帮着她丈夫在做西药生意……据说已经发了大财[14]37。
例3 (白素贞想)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凡是中产阶级的人,以及小资产阶级者,都在彷徨迷乱之中。到哪处都是荆棘,到处都是危险,到处都是网罗,这要怎么样才好呢,也想不出一个出路来,大家只好暂时苟安罢了[16]163。
上述三段文字中,虽然作者们的批判程度强弱不一,但“读书人”“诗人”和“小资产阶级”这些曾在“五四”时期被视为崇高的指称,在他们笔下都实现了一种意义消解,并被转化到了一种负面价值中。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现象理解为一种对“五四”时期长期陷入自我意识中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但是结合时代语境与文本自身,却似乎并非如此。
笔者认为这种态度不仅仅是一种作者个人取向的巧合,我们必须从文本所寻求的价值立场或者意识形态建构中进行解读。一方面,三篇文本将笔锋都指向社会现实,文章所表现的亲眷之间的隔阂、发国难财的荒诞以及金钱关系下道德秩序的颠倒,都表现了一种“恶行”。这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对固有价值观的悖逆,当这种“悖逆之恶”嵌套在“白蛇传”的故事架构中时,则与冯梦龙以降的重述文本所彰显的“惩恶扬善”的价值发生了部分重叠;另一方面,原本懦弱的许仙被虚构成一种“小资产阶级”、抗战期间小青嫁给了名叫“武大郎”的诗人,这些人物都如同钱钟书《围城》里的曹元朗一般。而在种种调侃背后,则体现了一种对所谓“知识阶层”的不信任,也是对“个人主义”的反驳。总之,在这两方面的合力作用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批判背后的价值选择,呈现了一种“厚古薄今”的价值回溯:当战争给社会带来了道德混乱,让国家丧失主权、沦陷领土的情况下,人们询唤的仍然是一种“忠孝节义”式的传统价值,因为只有借助植根在国民心中的儒家传统才能建立一种民族与国家的想象。
总的来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白蛇传”重写中,文本的主体已经不再是对“个人”的表现,而是将白娘子、许仙等人提炼为代表着某种社会族群的符号,着重对这一“集体”讽刺或同情。“白蛇传传奇”也在现实化的语境中与抗战接轨,通过母文本的传统意义,让创作者们在价值回溯中缓解现实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