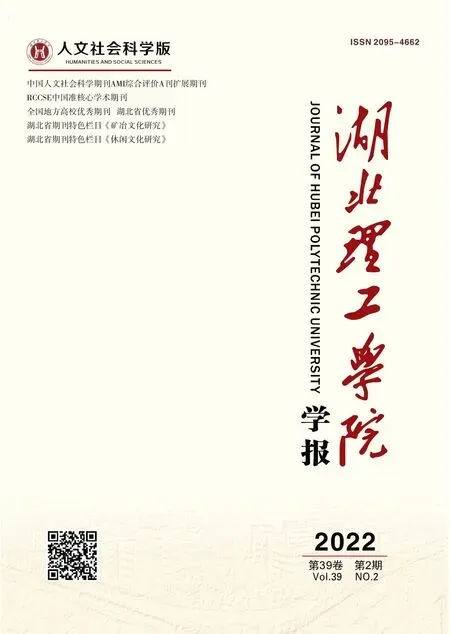谫论中国古代文学里的趋圆叙事观念*
2022-03-18李春光夏慧平
李春光 夏慧平
(1.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2.湖北理工学院 图书馆,湖北 黄石 435003)
宋人陈亮于《壬寅答朱元晦秘书》中有云:“若事体全转,所谓智者献其谋,其间可采取处亦多;但谓有补于圆转事体,则非某所知也……天下,大物也,须是自己气力可以斡得动,挟得转,则天下之智力无非吾之智力。”[1]333世间万事,若能“全转”,方是至境。若未能“全转”,则需“圆转”,以全事体。先以斡得动,后因挟遂转,乃得“圆转”三昧。吴沃尧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述,钟雷溪尝用一千两的票子贿赂并乞求“我”“在方伯处,代圆转一二”。可见,在中国文化中,当事体不能“全转”之时,以个人能力或借助他人之力去“圆转”缺憾与不足,乃是世情常理。每一个“圆转”行为的背后,都蕴涵着某种希求圆满的文化心理;每一个“圆转”行为的实施,都潜藏着某种趋向圆满的叙事动力。宋人苏籀《双溪集》后附《栾城遗言》,载录其祖父苏辙语,云:“余少作文,要使心如悬床,大事大圆成,小事小圆转,每句如珠圆。”[2]1247这便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里潜藏的趋圆叙事观念。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空间思维模式,可以在以《老子》与《易经》为代表的道、儒文化体系中觅得始源。其中,对“道”这一抽象概念的演绎与解码,为趋圆叙事的产生提供了厚重的文化定力。
就道家而言,《老子》二十五章有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3]149。
老子口中的“道”,是圆形的“道”,是运动不息的“周行”的“道”。“道”的运行轨迹大致经历“大”——“逝”——“远”——“反”四个阶段。这个轨迹可以图示为一个循环运行且生生不息的“○”。车载认为:“‘反’有两个涵义,对立相反是‘反’的一种涵义,复命归根是‘反’的另一种涵义,《老子》书对于‘反’的这两个涵义,都是加以重视的。”[3]151可见,这个“反”字在《老子》的语义系统中存在着“复命归根”“返回本原”的涵义。这就意味着,老子“道”论的外显形态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无独有偶,《庄子》中也有类似的理论,只不过较《老子》更加具象化。《在宥》云: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故往见之……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将去汝,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4]291-292
在广成子看来,各种生物的生命轨迹都是“生于土而反于土”的“○”。广成子点化皇帝实现“至道”的路径是持守内在的虚静、弃绝外在的纷扰。当到达了“大明之上”的“至阳之原”之后,当到达了“窈冥之门”里的“至阴之原”之后,当明白了“阴阳有藏”的奥妙之时,个体便可实现“至道”。在形而下的层面,庄子认为生物形骸的生发逝反遵循着“○”的轨迹;在形而上的层面,庄子认为人类治身的长久无极同样遵循着“○”的轨迹。可见,《庄子》“至道”论的外显形态,也是一个“生”“反”循环、“阴阳有藏”的“○”。
就儒家而言,《易·系词下》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孔疏:“‘周流六虚’者,言阴阳周遍,流动在六位之虚。”[5]89这里的“周流”与《老子》中的“周行”是同构的,都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易有四象,以“少阳”——“老阳”——“少阴”——“老阴”为运行轨迹,对应春夏秋冬四时,形成了一个闭合的“○”,进而定型了中国人圆形的宇宙观。这种圆形宇宙观,相应地濡化出了中国人“中和”的观念。这种“中和”观念,从本质上说,强调一种适中、和谐、圆融的处世姿态与文化意识。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6]63《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疏解释“中和”云:“不能寂静而有喜怒哀乐之情,虽复动发,皆中节限,犹如盐梅相得,性行和谐。”[5]1625这种作为“达道”的“中和”观念,要求人们能够摒弃杂念,恢复寂静,进而抵达身心和谐的境界。投射到文学创作领域,“中和”观念要求创作主体能够创作出“温柔敦厚”的作品。“温柔敦厚”不但可以指涉人类个体的性格特征,也可以成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标准:
“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5]1609-1610。
在孔颖达看来,《诗》的文化价值便在于体现为“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的中和、圆融的批评手法。以“依违讽谏”的《诗》教民,百姓可以敦厚不愚;以“不指切事情”的《诗》运文,文章可以深达义理。中国古代很多文学作品都以“温柔敦厚”为终极目标。例如,清人西湖散人在为云槎外史的《红楼梦影》所作的序中,便认为这部《红楼梦》的续书“善善恶恶,教忠作孝,不失诗人温柔敦厚本质”[7]1。
从道儒诸经关于“道论”的文化阐释中不难看出,在中国人的宇宙意识中,周而复始的圆周运动建构了先民“〇”形的世界观,而这种宇宙观也为古代文学作品中人神互通提供了最为原始的可能。在“〇”形世界观的观照之下,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呈现出趋圆的特性,强调中和,并在彼此调和中达到兼美、圆融的境界。
二
在中国古代的很多文学家眼中,道家与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圆周运动,很多时候并非是在外力作用下产生的,而是由其内在的“阴”“阳”二素共同驱动的。不论是《庄子》中的“至阳”“至阴”,还是《易》里的“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均有效地实证着阴阳互动对我国古代文化中圆形世界观的影响。
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在《南雷诗文集·缩斋文集序》中盛赞其弟黄宗会为文:
其文盖天地之阳气也。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阴气在下,重阳包之,则搏而为风。商之亡也,《采薇》之歌,非阳气乎?然武王之世,阳明之世也,以阳遇阳,则不能为雷。宋之亡也,谢皋羽、方韶卿、龚圣予之文,阳气也,其时遁于黄钟之管,微不能吹纩转鸡羽,未百年而发为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灵之文,阴气也,包以开国之重阳,蓬蓬然起于大隧,风落山为蛊,未几而散矣。今泽望之文亦阳气也,然视葭灰不啻千钧之压也。锢而不出,岂若刘蜕之文冢,腐为墟壤,蒸为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8]12-13?
对易学颇有研究的黄宗羲,用“震”“巽”二卦剖析出了阴阳互动之下朝代更迭与文气兴衰的关系。“不食周粟”的殷商移民伯夷、叔齐吟唱的《采薇》,代表着商周易代之际的文之阳气。只不过,这种文之阳气,遇到了周武王的“阳明之世”,只能被同化消弭,“不能为雷”。南宋为汉人政权,故其遗民之文当属阳气。谢翱、方凤、龚开三人均见录于明人程敏政所作《宋遗民录》,且方凤曾作《野服考》以明“放浪山泽”之志。南宋遗民的文之阳气,未历百年便发展成为击毁蒙元阴气的“迅雷”。元代为夷人政权,即“元之世,阴晦之世也”,故其遗民之文当属阴气。王逢自号“席帽山人”,戴良自号“九灵山人”,《明史·文苑传》称“二人皆不负元”。蒙元遗民的文之阴气,遇到明王朝的“开国重阳”,只能化为“未几而散”的“风蛊”。在黄宗羲看来,现如今“泽望之文”即明遗民之文亦为阳气,清政权实为阴气,阳气为阴气所“压锢”,其危局恰似刘蜕之文冢,封而不出。唐人刘蜕于《梓州兜率寺文塚铭》(并序)中直言:“文塚者,长沙刘蜕复愚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宋人章望之在所作《延漏录》“刘蜕文塚”条下解释道:“其文草聚而封之。有涂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硃墨圈者。”可见,不与清廷合作的黄宗羲渴盼明遗民之文能为民族斗争所用,而绝非仅仅作为文人之文葬入文塚。黄宗羲似乎有严重的汉遗民情结,进而能与谢翱、方凤、龚开等南宋遗民感同身受。遗民的这种气节,正是沉于下潦的阳气所在。只不过,易代之际,江山板荡,阴气拘锁阳气,致使阳气不能申发而已。不难看出,用阴阳互动去解释朝代更迭特别是夷夏更迭,成为黄宗羲不容忽视的夷夏观与历史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贾雨村之口阐明了所谓的“秀邪二赋论”: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馀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自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9]28-29。
“秀气”乃是一种阳气,“邪气”乃是一种阴气。秉“秀气”者大多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诸如尧、舜、周、孔等;持“邪气”者大多会变成扰世的蠹虫,诸如桀、纣、王莽、安禄山等。即便是在“太平无为”的盛世,“溉及四海”的“秀气”也会与“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的“邪气”相遇,“搏击掀发”出各种秉性乖异的人物。这些秉承着秀邪二赋的历史人物,在阴阳互动的历史洪流中,与天道的循环或吻合、或排斥、或顺应、或逆反,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搅动风云,成为中国文化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符号。
阴阳互动的圆周驱力,不但能够诠释历史变革的潜因,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文艺美学的发展。清人姚鼐在《海愚诗抄序》中说:“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10]48在《复鲁絜非书》一文中,姚鼐进一步强调阴阳互动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也。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10]93-94。
在姚鼐看来,文章得阳气,自然呈现出崇高浩渺之美;文章得阴气,也会呈现出清幽漫淡之美。为文之上境,在阴阳得所、刚柔相济;为文之中境,在阴阳相杂、“糅而偏胜”;为文之下境,在阴阳缺位、刚柔失本。可见,在集历代文化之大成的清代,用阴阳互动的圆周驱力诠释文艺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是一种大势。
站在清朝这个历史节点回望,阴阳二素共同扮演着只属于古代中国的审美驱力。历史的变迁,可以用阴阳来演绎;善恶的杂糅,可以用阴阳去诠释;男女的互动,可以用阴阳去图谶;幽明的交媾,可以用阴阳去探索;虚实的转化,可以用阴阳去建构。甚至,人物个体的命途浮沉均可以用阴阳来明示。太平闲人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曾用《易》去解读《红楼梦》中刘姥姥的行为以及贾府四春的命运,认为《红楼梦》“全书无非《易》道”:
刘老老,一纯坤也,老阴生少阳,故终救巧姐。巧姐生于七月七曰,七,少阳之数也。……老寡妇无子息,阴不生也,久经世代者,贞元运会,万古如斯,而圣人作《易》,扶阳抑阴,及至无可如何,而此生生不息之真种,必谨谨保留之,是则此谓刘老老也。刘,留也,奈何世人身心性命之际,独不理会一刘老老,而且为王熙凤之所笑?悲夫!
书中借《易》象演义者,元、迎、探、惜为最显,而又最晦。元春为泰,正月之卦,故行大。迎春为大壮,二月之卦,故行二。探春为夬望,三月之卦,故行三。惜春为乾,四月之卦,故行四。然悉女体。阳皆为阴,则元春泰转为否,迎春大壮转为观,探春夬转为剥,惜春乾转为坤,乃书中大消息也[11]158-159。
正所谓“经学家看见《易》”,这种解读方法似乎也能解读出一些新意。张新之用卦象解读出刘姥姥一家的《易》道建构模式。刘姥姥搭救巧姐,乃是老阴生少阳。“阴不生”,则“贞元运会”,故此阴阳交替、新旧更迭乃是万古不变之真理。贾元春的泰极生否,贾惜春的乾坤对转,印证了阴阳互动特别是阴阳倒置造成的人物个体命运的浮沉。至此,阴阳互动,小到可以解释个体遭际,大到可以诠解朝代更迭。可见,阴阳互动理应成为中国古代作家建构趋圆文本的文化内力与审美驱力。
三
在中国古代为数不少的文学作品中,趋圆性的叙事结构特征是客观存在且不言自明的。史传文学讲求有始有终、希求沟通天人的叙事行为,戏曲文学、小说文学力图曲终奏雅、试图勘破轮回的叙事行为,均以实际的文本存在及可感的理论预设证实着中国文学趋圆叙事观念的客观存在。
其一,古代抒情文学存在着趋圆叙事观念。例如,对“圆美”这一美学理想的追求,便体现出古代诗文的趋圆性叙事倾向。谢朓认为,“好诗”的标准是“圆美流转如弹丸”[12]609。在《南史·王筠传》中,沈约曾援引谢朓的这个观点,在王志面前盛赞王筠“贤弟子文章之美,可谓后来独步”。南宋魏庆之在《诗人玉屑》卷十中援引《王直方诗话》,提倡诗贵“圆熟”,强调“好诗如弹丸”:
谢朓尝语沈约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故东坡答王巩云:“新诗如弹丸”,及送欧阳弼云:“中有清圆句,铜丸飞柘弹”。盖谓诗贵圆熟也[13]221。
谢朓强调“圆美”,苏轼看重“清圆”,王直方尊崇“圆熟”。可见,在一部分古代诗人的心目中,“圆美”“清圆”“圆熟”不仅是一种作诗的境界,更是一种评判诗歌美学价值的指标。可以想见,以圆转流畅之美去评介他人诗文,势必会成为文学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认为,“诚斋出,诚得所谓‘活法’,所谓流转圆美如弹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见”。后期的江西诗派,大有风流云散之势,自杨万里得“活法说”之要旨,复使江西诗派元神复位,只可惜吕本中本人已无缘得见。在马端临看来,江西诗派后期主张“活法说”,而此说的精髓则是“圆美”。金人元好问在《题樗轩九歌遗音大字后》一文中盛赞胙国公李绰“诗笔圆美,字画清健”。元人洪焱祖在《黄岩盛景则来为吾郡征官见示诗文因成一章》中盛赞黄景则“光采生万变,新诗更圆美”。明人黄淳耀在《吴义斋经畬堂诗序》一文中盛赞同乡前辈吴义斋“所为诗及小令,皆聊以寓意,未尝瞡瞡比拟,而音节圆美,神彩流焕,翛然有尘外致趣”。四库馆臣认为明人刘基长子刘琏的七言律诗,“流利圆美,不出元末之格”;还认为清人匡鼎《橘苑诗抄》所录之诗,多沿清初“西泠十子”之遗风,“圆美有余,而深厚不足”。可见,在古代诗人的思维中,“圆美”是诗文极为重要的美学特征,且在四库馆臣看来,元末、明初乃至清初的诗坛,“圆美”的诗风仍然大行其道,阻碍了诗歌雄浑深厚风格的发展。由此可见,诗文领域,可能确实存在着“无圆不文”的创作倾向,而且多以“园美”之论去架构文学史层面上的价值判断。
进一步地,清代诗人何绍基在《与汪菊士论诗》中,将诗文领域的趋圆性与儒家的道统论结合在一起:
落笔要面面圆,字字圆。所谓“圆”者,非专讲格调也,一在理,一在气。理何以圆?文以载道,或大悖于理,或微碍于理,便于理不圆。读书人落笔,谓其悖理碍理,似未必有其事,岂知动笔用心,稍偏即理不圆,稍隔即理不圆[14]36。
这种趋圆性,不该只滞留在诗文的“格调”层面,更应该升华到诗文的以“理”“气”二素构成的神髓层面。在传统的文以载道论的观照之下,任何“偏”心、“隔”心的行为,必然会造成“悖”理、“碍”理的客观效果。于理不圆,则于文难圆。在何绍基看来,现实生活中,求全责备地要求“理圆”是很难达到的,要想达到“文圆”的目的,还可以通过“气圆”来实现,即“用笔如铸元精,耿耿贯当中,直起直落可也,旁起旁落可也,千回万折可也,一戛即止可也,气贯其中则圆”。这种“气圆论”思想,实质是儒家传统的“中和”思想与道家的“心斋坐忘”“涤除玄鉴”等思想高度融合后的产物。既然于“理”难圆,要想让文章在神髓上去载道,只有通过“气圆”的方法才能达到“文圆”的终极目的。由此可见,以“动笔用心”为根基的“气圆”与“理圆”,是实现“文圆”这一终极目的的最为有效的两个途径。诚如清人张英在《聪训斋语》中所言:
天体至圆,故生其中者无一不肖其体。……万物做到极精妙者,无有不圆。圣人之至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艺一术,必极圆而后登峰造极[15]23-24。
在张英看来,世间万物都是向圆而生的,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道德行止,只有做到“极圆”,才能登峰造极。在这本家训中,张英没有理由去阐述深奥的哲学理论,也没有必要去诠释诉讼纷纭的文道关系。但正是这类乎于迷狂的对“极圆”的追求,最终解开了古代作家的创作初衷。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在对“极圆”的极致追求的引逗下完成“气圆”与“理圆”的契合,最终走向“文圆”,进而产生“圆美”“圆熟”的审美效果。
其二,古代叙事文学存在着趋圆叙事观念。
古代人民对团圆的希求,似乎成了我们民族心理中最为固守的偏执。唐人王建在《早发金堤驿》中说:“从军岂云乐,忧患常萦积。唯愿在贫家,团圆过朝夕。”白居易在《自咏老身示诸家属》中说:“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夫妻偕老日,甥侄聚居年。粥美尝新米,袍温换故绵。家居虽濩落,眷属幸团圆。”杜荀鹤在《和友人送弟》中说:“我今骨肉虽饥冻,幸喜团圆过乱兵。”无论是生在“贫家”,还是久处“濩落”,甚或是遭遇“乱兵”“饥冻”,只要骨肉团圆、眷属一室,便实现了古人心中的至幸之愿。宋人袁采于《袁氏世范》中认为:“飞禽走兽之与人,形性虽殊,而喜聚恶散、贪生畏死,其情则与人同。”清人俞明震在《觚庵漫笔》中也有“人情喜合恶离,喜顺恶逆”之论。正是基于古人“喜聚恶散”“喜合恶离”的文化心理,古代文人特别是明清文人的叙事文学创作才把趋圆的命题发挥到极致。清代山石老人《快心录自序》称:“余自幼累观闲词野史颇多,无非是才子佳人,捻造成一篇离合悲欢,虽词句精巧,终无趣味。”[16]1285“闲词野史”存在的目的就是“捻造”团圆,而“捻造”一词明确指出那些叙事文学作品极具趋圆的可操作性。最终,这个可操作的“捻造”团圆的公式,被《红楼复梦》之“凡例”明确点出:
凡小说内才子必遭颠沛,佳人定遇恶魔,花园月夜,香阁红楼,为勾引藏奸之所;再不然公子逃难,小姐改妆,或遭官刑,或遇强盗,或寄迹尼庵,或羁楼异域,而逃难之才子,有逃必有遇合,所遇者定系佳人才女,极人世艰难困苦,淋漓尽致,夫然后才子必中状元、作巡按,报仇雪恨,聚佳人而团圆[17]4。
“必遭”“定遇”“必有”“定系”“必中”五个绝对性的词语,代表了批评家对才子佳人小说“捻造”团圆创作公式的微词。小说的佳处在于其叙事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与开放性。对团圆的偏执迷狂导致的过于确定的结构与叙事脉络,自然会引发读者的“无趣”之感。明清之际张缵孙《戒人作淫词》有云:
今世文字之祸,百怪俱兴。往往倡淫秽之词,撰造小说,以为风流佳话,使观者魂揺色夺,毁性易心,其意不过网取蝇头耳。在有识者,固知为海市蜃楼、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达者少,随俗波靡者多。彼见当时文人才士,已俨然笔之为书,昭布天下,则闺房丑行,未尝不为文人才士之所许。平日天良一线或犹畏鬼畏人,至此则公然心雄胆泼矣。……况吾辈既已含齿戴发,更复身列士林,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驱迫齐民尽入禽兽一路哉?祸天下而害人心,莫此之甚已。倘谓四壁相如,不妨长门卖赋,则何不取古今来忠孝节义之事,编为稗官野史,未尝不可骋才,未尝不可射利,何苦必欲为此,开口定是佳人才子,密约偷期,绝不新奇,颇为落套,而且绮语为殃,虚言折福,不独误人,兼亦自误。吾实为作者危之、惜之。故不惮与天下共质之也[18]234-235。
此处,才子佳人小说乃是“淫秽之词”的一种文体表现形式。“随俗波靡”的文人才士为了获取蝇头小利,公然肆意写录闺房丑事,且毫无羞耻悔改之心。张缵孙认为,文人骋才、射利的方式有很多,并非只有撰写“颇为落套”、只求团圆的才子佳人文字一条出路。综上可见,喜好团圆乃是古代民氓才士最为常见也最为顽固的一种文化心理。
如果说上面的论述,是从中国古代文艺心理的层面论证了“无圆不文”倾向的客观存在,那么,民国时期,以启蒙之姿态探讨国民性的学者,对传统叙事文学中存在的“大团圆”现象的口诛笔伐,则用反证法证明了古代叙事文学“无圆不文”的历史强势。在煊赫一时的“戏剧改良运动”中,学者们发现,中国古代的悲剧资源十分匮乏,究其原因,则是古人喜好“大团圆”的喜剧心理冲淡了原本十分浓郁的悲剧诉求。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指出,“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并不吝笔墨地论证了,对“团圆的迷信”乃是“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蔡元培先生在《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一文中对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也颇有些微词:“如旧剧中述男女之情,大抵其先必受种种挫折,或男子远离,女子被难,一旦衣锦荣归,相复团聚,此等情节,千篇一律。……盖我国人之思想,事事必求其圆满。”[19]34傅斯年先生在《再论戏剧改良》一文中亦称“中国剧最通行的款式,是结尾出来个大团圆”,进而认为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是顶讨厌的事”[20]74。鲁迅先生把中国古代文化中趋圆现象的研究范围延伸到古代小说领域。在探讨唐传奇的艺术成就时,他也明确摆出了对“大团圆”结局的态度,其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称:
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到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21]316。
这种普遍的心理,被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中形象地概括为“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22]238。在重估一切传统文化的时代风潮中,敏锐的学者们发现了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存在着“大团圆”类的痼疾,而这类痼疾的实质,说到底,则是中国人既喜好回避现实又殷盼善恶昭彰的心病。学者们在拿“大团圆”作为突破口批判国民性的时候,却无意中反证了中国叙事文学趋圆性乃至必圆性的历史命题。
宋人梅尧臣《依韵和晏相公》有云:“苦词未圆熟,刺口剧菱芡。”清人张埙在《竹叶庵文集》卷二十一《钱慈伯招同冯鱼山小集独树轩》七律自注云:“予与萚石侍郎在陈伯恭斋中醉归,中道侍郎忽下车,指车轮顾余曰:‘诗之妙如轮之圆也。’”其中,“萚石侍郎”指的是清乾隆朝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四库全书》总纂钱载。梅、钱二人的观点,形象地总结出中国古代文学里的趋圆叙事观念。“圆熟”的文学,是不“刺口”的文学,是“妙”得真如的文学。即便时遭訾詈、偶历谤毁,古代文人缵衍圆美、“苦”修圆熟的文学史践履,不但从浅表的层面上证实了趋圆叙事观念的客观存在与绵亘深远,而且从肌理上显现了我们民族审美情趣里的温柔敦厚、中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