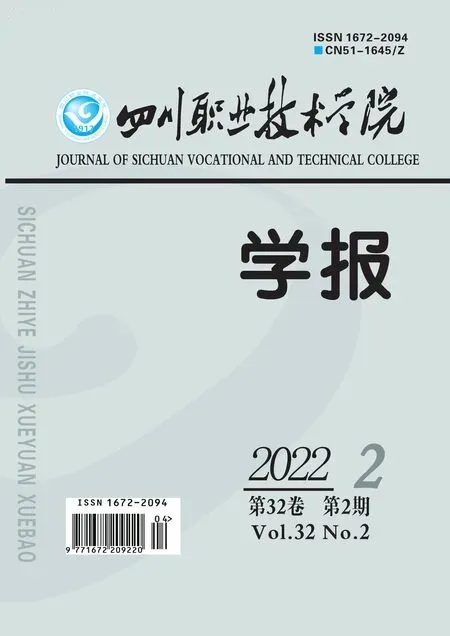《仪礼》札记三则
2022-03-18刘芸迪
刘芸迪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西青 300387)
《仪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共十七篇。内容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仪礼》语言深奥晦涩,虽有众多大儒为其作注疏释,然仍有许多难解之处。文章以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为本,结合杨天宇《仪礼译注》和彭林的《仪礼全译》,对郑玄注与王引之观点存在分歧之处,择取三则加以探讨,形成札记。
一、“缩霤”篇
“其笙,则献诸西阶上;磬,阶间缩霤,北面鼓之。(《仪礼·乡饮酒礼第四》)。”[1]117b
郑注:“缩,纵也。霤以东西为从也,古文缩为蹙。”[1]117b
王引之案:“东西可谓之横,不可谓之从。郑说非也。缩,从古文作蹙。蹙,近也。磬在两阶之间,其北则霤。磬虽不在霤,而近于霤,故曰蹙霤。”[2]253
杨天宇、胡培翚从郑注,杨氏将“缩”解释为“纵”,“霤(溜)”释为“屋檐”[3]87,该句译为“磬在两阶之间顺着屋檐东西纵向排列……”胡氏释:“缩,纵也,霤以为东西为纵……古文‘缩’为‘蹙’。”[4]
彭林:“缩霤:靠近屋檐的滴水处。缩,当作‘蹙’,近。”[5]115
按:郑注可从,王氏与郑氏的分歧在于缩释为纵是否可取。《汉语大词典》:“缩:纵,直。”[6]13526词义出自《仪礼注疏》。
训为“纵”的“缩”在先秦古书中常有用例,如:
《仪礼·公食大夫礼》:鱼七,缩俎寝右。郑注:“缩俎”者,于人为横,缩,纵也。鱼在俎为纵,于人亦横。贾疏:“缩,纵也。鱼在俎为纵,盖‘缩霤’之‘缩’取此意。”[1]324a-324b
“缩俎”对于鱼而言是纵向置于俎上的,此处释为“纵”,可以作证“缩霤”中的“缩”亦可释为“纵”。
《仪礼·士丧礼》:“厥明,陈衣于房,南领,西上,綪,绞横三缩一,广终幅,析其末。郑注:绞,所以收束衣服为坚急者也,以布为之。缩,从也。”[1]442a
古人束衣使用的腰带,就束衣者而言,缠绕腰带自是横向,“缩一”以最后系住腰带时的动作,应为纵向,否则无法固定腰带,此处“缩”仍有“纵”意思。
《仪礼·士虞礼》:“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设于几东席上,东缩,降,洗觯,升,止哭。郑注曰:缩,从也。古文缩为蹙。”[1]512c《周礼注疏》:“《士虞礼》设席於奥礼神,东面右几,放设于几东席上。东缩,缩,纵也。据神东面为正,东西设之,故言东缩。”[1]481b
《礼·檀弓上第三》:“棺束缩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长六尺。”[1]179c
《礼·檀弓》:“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注曰:缩,纵也。今礼制,衡读为横,今冠横缝,以其辟积多。故丧冠之反吉,非古也。解时人之惑,丧冠缩缝,古冠耳。”[1]149b
二者皆以“缩”“衡”对言,可证明“缩”可释为“纵”。
郑注结合文意将“缩”释为“纵”,文通字顺;王引之认为“缩”可从郑注“蹙”靠近之意,不从东西为纵。二人考虑文意的角度不同,王氏之说或认为无需考虑纵横问题,仅说明乐工靠近屋檐即可。笔者认为若从郑注的角度考虑,古人设东西阶,则乐工奏乐列于东西之阶,“缩”以东西为纵,乐工东西排列且靠近屋檐,更加合理。王氏认为“缩”不可为“纵”,一方面可理解为以南北为纵,而以南北为纵,乐工列于阶前,前一到两人可谓之“蹙”,即靠近“霤(屋檐)”,渐后则渐远,如何称之为“蹙(近)”?另一方面可理解为“缩”无需计较纵横问题,只需释为“蹙”即靠近即可,乐工如何排列则不再考虑。
因此结合前人学者注解加之己见,“缩霤”释为东西纵向排列于东西阶屋檐处适宜。
二、为大烛篇
《仪礼·燕礼》:“宵,则庶子执烛于阼阶上,司宫执烛于西阶上,甸人执大烛于庭,阍人为大烛于门外。”[1]195a
郑注曰:“宵,夜也。烛,ㄡ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烛,为位广也。阍人,门人也。为,作也,作大烛以俟宾客出。”[1]195a-195b
王引之案:“唐石经阍人句内无大字。《唐石经校文》曰:《大射礼》五大字,明此亦当无大。又此节注与《大射礼》注正同,唯作烛、作大烛为异,大字当是后人校增。”[2]255
彭林将此句译为“阍人设大烛在门外”[5]208,可见彭林认为“大”非衍字。
按:“阍人为大烛于门外”之“大”应为衍字,且该句中的“为”与“执”有所不同。王氏之说可从。《经义述闻》讨论的焦点“阍人为大烛于门外”之“大”是否为衍字?
如王氏所说《仪礼·大射礼》中有同样一句:“甸人执大烛于庭,阍人为烛于门外。”在此处为“为烛”,无“大”字。《初学记·卷二十五·器物部》:《仪礼》曰:燕则庶子执烛于阼阶上,司宫执烛于西阶上,甸人执大烛于庭,阍人为烛于门外。
《武威汉简·甲本燕礼》:“‘甸人执大烛于庭,阍人为烛于门外。’,没有‘大’字。王关仕云:《大射》‘阍人为烛于门外’,甲本同作‘闵’,无‘大’,此今本涉上文‘庭用大烛’而衍。沈文倬云:张尔岐《石本误字》云:无‘大’字。唐石经与简本相同。本师元弼先生《礼经校释》云:凡烛。在地为燎,执之曰烛。时久则在地,庭曰燎,门曰门燎;暂则执之,门庭皆曰大烛。然实一物,故《诗传》曰庭燎。大也。”[7]259这一点《仪礼注疏》亦可相佐证。
另“阍人为大烛于门外”之“为”与前文“执”动词不同,恐有深意。
甸人,《汉语大词典》:古官名,掌田野之事及公族死刑。《仪礼·燕礼》:“甸人执大烛于庭。”郑玄注:“甸人,掌共薪蒸者。”《礼记·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纤剸,亦告于甸人。”郑玄注:“甸人,掌郊野之官。”《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杜预注:“甸人,主为公田者。”[6]10905《旧唐书·李密传》:“甸人为罄,淫刑斯逞。”[1]499d从《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来看,甸人的职责有“掌田野之事及公族死刑”“掌共薪蒸”“掌郊野”“主为公田”。“甸人执大烛”中的“甸人”从文意来看,应该负责掌管薪木柴草。
阍人,《汉语大词典》:一为周官名,掌晨昏启闭宫门[6]16926。《周礼·天官·阍人》:“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1]137d二为后世通称守门人为阍人。《礼记·檀弓下》:“季孙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与子贡弔焉,阍人为君在,弗内也。”[1]225d阍人的职责为启闭宫门或者是守门,甸人、阍人职责不同,那么“为大烛”与“执大烛”的“为”“执”必然不是相同的动作,“执”可释为“拿”“持”,“执大烛”可解释为手拿大烛,那么“为”是何意?《汉语大词典》:“为”有陈设,设置之意,如此说来阍人为大烛,可解释为“设置大烛在门外”或者“陈设之意”可引申为“点燃”的动作,而不是手执,阍人并非掌管薪木柴草,不曾跨职责而为之,盖仅仅是将门外早已设置的烛火点燃而已。
综上,结合出土文献实词的使用以及甸人和阍人的职责,可推知“大烛”和“烛”实际为同一物件,仅仅为了相区别而将庭中的“烛”称为“大烛”,动词使用不同,盖二人对“烛”的处置有所差别,出土的《武威汉简》已经可以证明“大”为承接上文而衍。王氏之说可从。
三、栗阶篇
《仪礼·燕礼》:“凡公所辞,皆栗阶。凡栗阶,不过二等。”[1]199a
郑玄注:“栗,蹙也,谓越等急趋君命也。其始升,犹聚足连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发而升堂。”[1]199a-199b
贾公彦疏:“凡升阶之法有四等:连步,一也;栗阶,二也;历阶,三也,历阶谓从下至上皆越等,无连步,若《礼记·檀弓》云‘杜蒉入寝,历阶而升’是也;越阶,四也。”[1]199a-199b
王引之案:“栗阶,即历阶也,古栗与历声近而通……古音栗在质部,历在支部,二部之字,或相通借……贾氏失之。”[2]256
彭林《仪礼全译》:“栗阶,或称“历阶”,快速登上台阶的方式:左脚踩第一台阶,右脚随即踩上第二个台阶……如此一直到堂上。通常上台阶时,左脚踩上第一个台阶,接着右脚也踩第一个台阶……如此直至堂上。”[5]211
杨天仪宇《仪礼译注》:“‘栗’与‘历’通,栗阶犹言历阶。凡升阶,两脚并于一级,然后再升一级并之,叫做拾,即所谓拾级而升;一脚一级而升,就叫历阶。升阶之常法是拾级而升,如果急趋君命,则当历阶而上。”[3]165-166
按:栗阶,即历阶,且“栗阶”应是左右各一发而升堂,不连步。
“栗阶”存疑之处一为如何登台阶。
郑玄注:“其始犹聚足连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发而升堂。”[1]199a-199b疑“聚足连步,越二等”断句有问题,“聚足”与“连步”同义,二者并举,多有异议。此句若如上断句,可理解为第一级连步而上,之后左右各一发升堂且不再有连步;此句若断句为“其始犹聚足,连步越二等,左右各一发而升堂”,则应理解为第一台阶连步(聚足)之后,左右足各一发,越二级台阶,连步从始至终都有。但无论从何种说法,定有聚足连步,但《仪礼·聘礼第八》:“栗阶升,听命,降拜,公辞。注云:栗阶,趋君命尚疾,不连步。”[1]272c二者同“栗阶”一曰聚足连步,一曰不连步,存有矛盾之处。
《武威汉简》沈文倬有云:“栗阶对聚足连步而言。聚足连步谓左足升至第一等级,右足随之,两足相并,然后至第二至第三等级。栗阶则左足升至第一等级,右足升至第二等级。”[7]264-265沈氏认为栗阶无连步。杨氏与彭氏皆从此说。“栗阶”是急趋君命而为,那么第一阶“聚足连步”恐与“急趋”相违背,因此沈氏之说可从。“栗阶”当为一步一阶快速上堂。
“栗阶”存疑之处二为“栗”与“历”通假。
《汉语大词典》:“栗阶,相传周代下见上登阶之礼的一种,‘栗’通‘历’。”[6]6033
《仪礼》中“栗阶”除《燕礼》还曾出现两次:
《仪礼·聘礼第八》:“栗阶升,听命,降拜,公辞。注云:栗阶,趋君命尚疾,不连步。疏云:凡‘栗阶’者,其始升亦连步,於上栗阶不过二等,今云‘不连步’者,谓不从下向上皆连步,其始升连步,则有之也。”[1]272c
《仪礼·公食大夫礼第九》:“宾西面坐奠于阶西,东面对,西面坐取之;栗阶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辞公。”[1]328d此处郑注与贾疏同《燕礼》。
郑玄以蹙训栗,则说明栗与蹙定有联系,从字形看二者联系不大,王氏的声训可参考。栗,来母质部入声字;蹙,精母屋部入声字,在字音上有差别。《武威汉简·燕礼》校记云:“䅇,今本作栗,王关仕云:甲本栗作粟。按隶从禾、从米、从木多混,犹熹平石绖鲁《诗》残碑‘勿食我 ’之从木。”[7]264-265栗与粟字形相近且粟为心母烛部入声字,心母和精母同属精组,盖有一定的联系,或可假借。沈文倬云:《字汇补》有䅇字,云“古栗字”,从禾为俗写。栗阶字为历之假借,《考工记》“栗氏”,郑注:“栗,古文作历。”《说文·止部》:“历,过也。”[7]264-265亦可证明“栗”通“历。”
贾公彦将“栗”和“历”分开,经文中确有“历阶”一说。
《春秋谷梁传·定公(元年~十五年)》: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
《礼记·檀弓下第四》:“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1]204c
《汉书·卷十成帝纪第十》:三月,博士行饮酒礼,有雉蜚集于庭,历阶升堂而雊,后集诸府,又集承明殿。
《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下五行志第七中之下》:鸿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礼,有飞雉集于庭,历阶登堂而雊。
在《仪礼》中不曾有“历阶”,在经文中“栗阶”与“历阶”出现的时间也有先后,亦不存在混用的情况,“栗阶”与“历阶”处于互补关系中,且后世经史子集中多用“历阶”,贾说恐不可从,故“栗”通“历”可从。
通过考察文献,结合语法、语境,以出土文献为依据,笔者认为《乡饮酒礼》中“缩霤”当为“靠近屋檐且东西为纵”;《燕礼》中“为大烛”之“大”为衍字且“为”当为陈设引申为点燃(烛)之意;《燕礼》中“栗阶”当为“历阶”,意为一步一台阶,如此至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