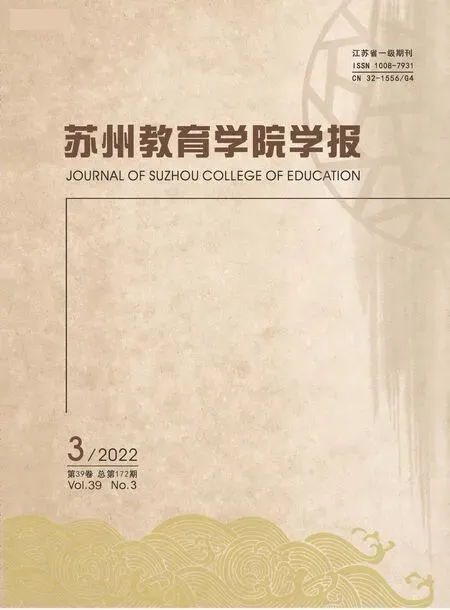为现实寻找语言
——小海诗歌的启示意义
2022-03-18宋宝伟
宋宝伟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提到诗人小海,人们很自然会想起他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诗歌创作的成就,也会“顺理成章”地自动将他归入到“他们”诗派,并在这一视角下观照、评析小海的诗歌成就。“第三代”诗歌运动大潮早已湮灭在“静水流深”的诗歌汪洋之中,重新检视“第三代”诗歌“遗产”则会发现,尽管那代人经历了20 世纪90 年代的“沉寂”和新世纪的“喧嚣”,但还有许多诗人依然坚持自己的诗歌理念和诗歌写作,持续不断地为诗坛输送诗歌文本,保持着强劲的诗歌创作活力,而小海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文学评论最忌“先入为主”,在被一种先验的思维控制之后,人们往往会产生很多偏见与误读,也就很难辨清事物的真相。我们只有将诗人小海从“第三代”诗歌运动背景中“抽离”,使其远离那些曾经属于诗歌社团的诗学理念的先验视角,还原为诗人个体的身份,小海诗歌写作的独特性与创造性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才能准确地把握他在诗歌的日常性写作、原乡情结以及诗歌语言的本真追求等方面的特征。
一、日常性写作的诗意坚守
日常性写作是当代诗歌最大的贡献和成就之一,它使诗歌终于放下自己的身段“俯就”生活的同时,更让诗歌找到了“自我”,摆正了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置身于生存的现场,建构日常化的诗歌美学。从日常生活的场景和现场进入到人的感受和感觉之中,完成对生活的诗意化书写,在生活的缝隙和褶皱中让诗意澄明,并且从某些生活的先验和意义中逃离出来,获得一种本真的体验和领悟。小海诗歌从“出道”之日起,就显现出日常主义诗歌的特征,尽管当时正是“朦胧诗”象征诗学方兴未艾之际。“一场暴雨/海边小城的色彩/洗得鲜亮/孩子在奔跑/孩子的笑声是永久的柠檬黄//一阵风来/所有的木房子都扁了/孩子们又矮又胖/——一个瘦高个儿漫画家/悄无声息地走过去了”(《K 小城》)[1]11,这首诗颇有“印象派”绘画的气质,诗歌中呈现的就是诗人看见的“自然”的样子,色调、构图、动静关系同时存在,完美地复现了瞬间视觉“印象”。诗歌没有作那个时代常见的“价值判断”,也不需要将诗歌内涵“升华”,一切都是如此自然、平淡。“下午,你搭车/来我这儿/你跟我说过的话可不要忘记/是或者不是/这样的天气承蒙你来看我//你看我变得花言巧语/善于幻想而终归现实/看见你,我打心眼里高兴/你没变,还是老样儿”(《搭车》)[1]19,一次老朋友之间的相会,没有兴奋,没有激动,然而平淡的叙述中却也深藏着朋友情谊。口语化的叙述毫无滞涩之感,诗歌语言与日常口语同质同构,呈现出语言的天然性和原生态。在小海的诗歌中,经常能发现这样简约的语言形成的“白描”的艺术效果,不用层叠累加繁复的意象去营造朦胧、晦涩的“意境”,而完全依靠日常中的细观静察提炼生活的诗意,语言简约而含蓄,早已超越了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的意象化语言策略,对日常经验进行诗意的转化和处理。笔者认为当一个诗人注目日常、取材日常时,他必须有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基因,唯有这样,才能确保诗意的流动。这不一样的“基因”表现在小海的身上也许就是对生活的超级敏感,以及透明、简约并富有热度的表达。“这风多么宜人/像一件爽身的新衣/我不知它来自何方/它声音微弱/或者干脆一声不响//我爱这风/同时我还呼吸到它的气息/这阵风刚刚长成/它越过栏杆/在草坪上/一遍又一遍梳理自己的羽毛/我试探着把窗关上/在它离去之前/我无法进入睡眠/这样的时光/我纯洁的身体/就像刚刚洒落的花瓣/被风吹起/而不知道怎么躲避灾难”(《风》)[1]31。日常化写作看似简单,其实同样需要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作为支撑,诗歌中这种超级细微的身体感觉,只有经过诗人的敏锐的感知和近乎冷静而理性的表达才能在读者这里形成感同身受的认知,而这理性缠绕的依旧是人的感性与情愫。“现在我坐在窗前/很多事物显现在我面前/这往往是我忽略的生活/它们温静地出现/又不至于马上消失/在我的窗前/我注视它们很久/毫不惊慌/这是生活值得炫耀的部分/它们不鸣叫/但我听到它们哗哗流动的喧闹/这声音也能安抚我/我熟悉它/像熟悉睡梦中妻子的声息/这可不是虚假的事物/诱惑我,穿透我/直到我收拢翅膀/落在它们身上”(《窗前》)[1]28。对生活的一切事物的理解并坦然而热情地接纳,哪怕是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生活,都是生命中真实的组成部分,唯有对生活充满真意并诚挚拥抱的人,才会有如此细腻的内心感受。诗歌中有强烈的画面感,尽管是口语化的语言,但是诗人的言说显现出一种控制力,使得静谧之中的“玄想”自然而真切。
从先锋写作转向日常性写作,诗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重新建构了语言与现实的关联,疏通了语言表现现实的阻碍,这是当代诗歌带有革命性的“新发现”。日常主义诗歌不再“执着”地探询抽象、绝对的“在”,而是打量生存、常识的事物的“此在”,回到凡俗、琐屑、自然的本真状态,恪守当下,执守日常。但小海诗歌中的日常性并非只停留在生活的表层,而是在日常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思考,这种不可复制的完全个人化的生命感知,也许这就是小海诗歌与当下普泛的日常性写作的最大区别。“黄昏时分/静默得如同处子/所有的光都追逐你/让你无处藏身/这一刻的温暖/诉说了你一生要碰上的事情/但现在想起谁/都不能记起/熟悉的面孔都阴暗如灰/几十年以后/如果还能重复同样的光景/既不喧哗也不温柔”(《黄昏》)[1]26。诗歌中有一种生命的“达观”,相见不喜,分离不悲,颇有人生通透的境界。又如诗歌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一样,不可以为了“感情”而肆意宣泄,不能有超越生存状态所应该有的感情状态,二者的关系应该是既不喧哗也不温柔的,这才是当代诗歌必须追求的艺术表现和语言境界。“在一个早晨/我读到你的诗/我想你现在正走回家/走过一片木栅栏/推开花丛//你宁静的家里没有外人/你妻子一个人坐在窗前/此刻她已放下手上的活计/是听到你的脚步声/还是在回想那爱恋的日子//那扇门早已让风吹开/窗户一尘不染/诗人站在门外//这情景让我热泪盈眶/我想看清诗人的面容/可诗人此刻已经进门/可诗人此刻已经把门关上”(《读诗》)[2]208-209。这是诗人小海想象着另一位诗人常态化的家庭生活,平凡、普通却充满温馨和感动,这首诗歌的力量在于表现了瞬间生活的真实。诚如耿占春先生所言,诗是追寻个人生活中意义的瞬间闪烁的一种方式。[3]小海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诗歌已经准确地调整了诗与现实的关系,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诗意,而且并没有因为缺少距离感而流于平庸琐碎。同时也没有走入现代主义的阴郁、晦暗,更没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喧嚣、癫狂,而是自觉地追寻与开掘日常生活的神性,从这个意义来说,小海的诗歌对当下的日常性写作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当下日常性写作确乎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日常主义诗歌多数呈现为一种对生活现象的简单描摹,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尽管也不乏诗意,但总是缺少诗歌的蕴藉与回味。日常性写作极易陷入一种感官的破碎性的泥淖中,诗歌语言对生活经验的梳理也往往走向混乱,甚至低俗,这是当下日常化写作面临的困境。“他们常用随意性言语来表达他们对话语权的强烈关注,并以此回避自身缺乏基本训练的学术漏洞,而表面貌似激进的态度则对涉世不深者具有极强的诱惑性。”[4]有些日常性写作尽管满足了市民趣味的需要,对俗世生活也有很深的介入感,但因为对口语缺少有力的控制,语言泛滥恣肆,趣味低俗,使得诗歌文本缺少了使人“再读”的冲动,诗歌成为了“一次性”的消费品。当下诗歌虽然能在细小琐事上翻检“诗意”,但是很少能做到将生活的本真、自由的诗意释放出来,仍然存在着某种外在的遮蔽,譬如,诗学理念、社团意志、语言暴力等。“日常经验向意义体验的转化是一首诗的诞生之地。或许还更进一步,某些诗歌还能够在日常经验的表达中呈现出某种神秘经验或异质经验的可能性”[3]。如果一首诗只是单向度地呈现生活的原生性而缺少提升表象的意识和能力,那么这首诗只会流于平庸、乏味。而小海的诗歌表面看来是素朴的、不事张扬的,但是诗歌的内部却蕴藏着诗人对事物的思考,对某种“神秘”的追寻,同时也充溢着对生命的敬畏与憧憬。“今天,当我见到有人用脚尺量这块地/我有个预感/就像风雨之夜向我开启的大门/我确信,在这附近/还没有谁有这样的一双大脚/而且,在这个季节/匆匆穿过这不成形的荒芜的坡地/这是只有我才能感知到的/一只神奇的大脚/而不是惯常/我一早起来,仅仅收获它的薄雾”(《劝喻》)[2]57。诗人从“一双脚印”那里得到了某种“启示”,这样“跳脱”事物表面的背后隐匿着“形上”的诗意思考,这在当下很多日常性写作中是少见的。小海的日常性写作充溢着诗与思之美。
二、原乡情结与生命意识的个性表达
许多小说家都有自己的“文学的故乡”,如美国福格纳的“杰弗逊小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乡村”、苏童的“枫杨树乡村”、刘震云的“延津世界”,等等。诗人和小说家一样,也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标签化”的文学世界,云南之于于坚、雷平阳,平墩湖之于江非,小海的诗歌中也有属于自己的“家乡”——海安。可以说,小海的诗歌里有浓浓的原乡情结,这是他诗歌中非常鲜明的特征,是其诗歌“母题”之一。他曾这样谈道:“早年传统乡村生活的简单、闭塞、贫瘠、粗糙,剔除了其中生存状况的艰难、终年劳苦的艰辛磨砺,还有就是自然的生活、古老的价值对我心灵的滋养,也培育了人性中的温润、柔和的部分,未来的写作依然可以从之前人生启示录的序篇中汲取力量,是个人精神成长史上的一份厚重礼物。”[5]与家乡相关的人、事、景、物成为他诗歌的不变的“主题”。“五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集市/他指给我一条大河/我第一次认识了 北凌河/船头上站着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十五岁以后/我经常坐在北凌河边/河水依然没有变样//现在我三十一岁了/那河上/鸟仍在飞/草仍在岸边出生、枯灭/尘埃飘落在河水里/像那船上的孩子/只是河水依然没有改变//我必将一年比一年衰老/不变的只是河水/鸟仍在飞/草仍在生长/我爱的人/会和我一样老去//失去的仅仅是一些白昼、黑夜/永远不变的是那条流动的大河”(《北凌河》)[2]27-28。小海的诗歌总是能带给读者很多感受,尽管时间在飞速地流逝,每个人都变了模样,但是家乡的那条河流却依然如故。这其中既有对生命流逝的某种“喟叹”,更多的是对家乡深深的依恋。小海诗歌中这种情感的抒发绝不同于浪漫主义诗歌的浮泛与滥情,而是“智性”地传达出对时间的思考和对家乡“无言”的热爱。如果说《北凌河》是小海对家乡的“外向观察”的情感流露,那么《田园》则显示出诗人对故乡情感表达的内在与深沉,“在我劳动的地方/我对每棵庄稼/都斤斤计较/人们看见我/在自己的田园里/劳动,直到天黑/太阳甚至招呼也不打/黑暗早把它吓坏了/但我,在这黑暗中还能辨清东西/因为在我的田地/我习惯天黑后/再坚持一会儿/然后,沿着看不见的小径/回家”[2]23。诗人对家乡的亲近是通过时间的“拖延”表现出来的,并渗透出深沉的情感,犹如孩子对父母的依恋一样。《田园》有一种朴素之美,语言自然顺畅恰如呼吸一样,这是诗歌在语言方面的本体性的自觉意识的体现。“晨光把街道变成凛冽荒凉的运河//清冽的气流漫过乳头/醉汉的怀里搂满空酒瓶/脑袋像一坨生铁疙瘩//岸上的灯光雪花般打着旋/像无形的针刺/狗去咬猪/棍子打狗/火烧着棍子/街上面对面/道别着的乡村公共汽车/人造的春天,地图上的邮差/转过街角,走入寓所/成千的烟囱开始呼吸”(《故乡,二月早春》)[1]54。相比那些需要抒发激情以唤起读者情感的诗歌来说,这首诗更接近于“新写实”风格,不动声色,也很少作“价值”判断,只是如实地描绘故乡生活的场景,而这种如实的表达,很大程度缘于小海对“真实”的追求。诗歌仅仅围绕家乡“早春二月”的清冷,在清晨冷冽的氛围中平静地将目之所及的现实“客观”地呈现出来。但是,在这略显寒冷的清晨里却弥散着诗人对家乡的情感认同,这不同于底层写作视角,无所谓同情,无所谓批判,它只是故乡生活的某一瞬间的真实再现。
小海的诗歌呈现出一种生命与语言的同构状态,既不是对生命本质作提升式的“赞叹”,使之成为某种抽象的理念,也不作贬抑式的批判,让人产生悲凉与愤懑之感,而是在语感的流动之中构造出一种智性的空间,将对生命的理解与感悟弥散在这空间中。“黄昏,疲惫的恋人返回村子/牛还在公路上,小心的庄稼汉牵回棚圈//黑暗中的牛郎卸下轭头/终于和白天隐匿的纺织女相见//蓝色画境里的公鸡跳出围墙/去召唤一位夜晚的甜蜜伙伴//不驯服的羊抵触着老实人的腰/泥潭里的鹅化作黑身体的引路人”(《黄昏之后》)[2]215,从诗歌的结构来看,这是一组黄昏中的乡村各种常见事物的组合情景,但事物彼此之间并不构成一种“升阶”的关系,而是一种“蒙太奇”般的平行关系。每一种事物都带有很强的动感,并且赋予其某种未知与神秘,契合人在黑暗之中的隐秘的内在精神的“真实”。尽管每一种事物都是独立的,但每一个体的生命却是有机的,事物之间并没有因为“独立”而失去天然的呼应关系,这就是诗歌《黄昏之后》带给读者的智性思考。“雨后的大街/车行道开始泛白/快要干了/像一条新鲜的海带/平摊着/鱼腥气/外加汽车轮胎上的泥巴/可怜的香樟/像一排病妇/立在路边//天气就要转好/我的邻居也将汇入楼下/匆匆上班的人流/那从前农药厂的工人/而今中外合资/保健品企业的员工”(《邻居》)[2]76,诗歌描写的是一位普通的“邻居”,他(她)的身份从国内企业“工人”变成中外合资企业的“员工”,这种身份的转化在当下似乎早已司空见惯,并不能带给读者太多的感受。但是诗歌的全部信息并非这样简单,而是凝聚在诗歌的前部,也就是用一种“象征”的手法写出“邻居”此时的生命状态——海带、鱼腥气、泥巴、病妇,这些语汇无不暗示着一种让人深感悲哀的生命。诗人用前后看似没有关联性的两部分形成一种暗示关系,但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物”与“人”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整体性的暗示,是“多”对“一”的关系。整首诗呈现为一种简单、平实的风格,前后两部分都是在陈述事实,这种专属于诗人小海的“私设象征”里潜藏着对个体生命的体验和感悟,客观叙述中充满着同情和悲悯。
我们知道,诗人感知世界的方式来源于世界赋予他心灵的无穷奥妙。小海的诗歌总体来说,是深沉的,而非明快的,也许这是由诗人的气质决定的。正是由于诗人的敏感和内心的激情,以及不事张扬的性格,小海的诗歌总是呈现出一种“压抑”的力量,其情感的内核与语言的外壳之间的张力也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虽然诗歌追求一种生命与语言的同构性,但是因为蕴含着对生命的深刻领悟,往往显现出一种情绪低沉和智性深邃的复杂美感:“萤火虫/撒满了河面/纵横、壮观/像打开了桎梏的囚犯/找到了身体的语言/也像令我们心酸的母爱/一闪、一灭、一闪、一灭/电击着我们濒死的心脏//远离了故乡冰凉的水井/就像口对口的方言/准备熄灭//哦,这温柔而苦难的心……”(《萤火虫》)[2]102。从诗歌的意味来看,现代诗就是一种对生存的领悟,这种领悟不仅有对已知事物的理解把握,还有对未知事物的预见,甚至是焦虑。忽明忽暗的萤火虫隐喻了诗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怀念,“一闪、一灭”之间是无尽的感伤和深深的忧虑。当“还乡”的“通行证”——方言——慢慢被忘却乃至消亡之时,诗人“这温柔而苦难的心”将如何安放?原乡情结与生命意识是小海诗歌中两个重要的表现领域,“原乡”意味着其诗歌不是来自“乌有”,而生命意识则显示出诗歌没有导向虚空。换句话说,小海诗歌有坚实的“此岸”,也有可以引渡灵魂的彼岸。与虚无对抗,不仅体现着小海诗歌的品质,更是考验着一个诗人的情怀和洞察生命的深度,以及穿透生活本质的力量。
三、口语化与戏剧化:语言的持续探索
诗歌的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它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即对人的生命(包括人性)探索的深度和广度,而且还取决于它对经验的传达程度,而后者意味着诗人对语言的掌控能力,即能否准确地表达出自己对事物本真的理解和观照。小海及那一代人的诗歌在20 世纪80 年代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率先进行了语言变革的探索,为人的此在生存状态找到契合的语言表达方式,更确切地说,就是语言与此在的同质同构。此时的语言绝不是事物外在的附属和工具,而是拥有本体地位和意义的。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一书中提到,诗歌的话语不再是诗人的话语,此时诗人是沉默的,只有话语在“自言自语”,语言成为一种本质的东西。[6]布朗肖的观点至少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就是诗歌写作要避免诗人像浪漫主义那样过度地操控语言,语言应该是一种自动的呈现,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与此在生活的同质同构,如《自我的现身》一诗:
我看见田野里一把被遗忘的工具
为了能够找到我
我走向田野
这是一个发明事物极限而组成的黄昏
填空那么宁静
为了再次找到
那触怒土地后
尚未分类的躯体:工具
那把锈蚀的铁锹
紧咬着一条细窄的田埂
正如我目前所见的最佳方式
就是禁闭自我
随后而来的
蚕食铁锹的雨水
将形成一个自我独自留在外面
无人问津
我为我所见的事物
现身[1]31-32
诗歌中铁锹作为一把“被遗忘的工具”,究竟是被“我”发现,还是它完成“自我现身”从而找到了“我”。诗歌不仅包含深刻的“主客体”相互转换的哲理意蕴,从另一个角度也道出了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也就是说,这首诗我们可以将它解读成一首“诗论”诗,以诗歌的方式传达了诗人自己的诗学主张。或者换个角度来看,此时的诗,即诗人诗学理论的“实验品”。在诗歌写作中,究竟是诗人发现了语言,还是语言发现了诗,不同的答案将导向完全相反的两极,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诗歌理论范畴,诚如陈超先生所言:“语言在诗人手中不是工具,他和语言在展开另一空间时完成了互相的选择和发现。表面的语言效果不能代替诗人对诗歌内在肌质的创造,它是一种灵魂的自白!”[7]现代诗歌发展到20 世纪80 年代,乃至当下,更多地强调诗歌语言的本体自觉,诗歌重视声音,注意语言的走势,追求像呼吸一样自然的诗歌写作,诗人的“地位”逐渐趋向于弱势,甚至“消失”。“无法分别/两只杯子/它们构成/洁白的一对//一只杯子/已经摔破/它的残骸/盛满/另一只杯子”(《悼念》)[2]120,这是小海献给已故诗人海子的诗,杯子隐喻两人名字中共有的“海”,一只“杯子”已经“摔破”,而另一只“杯子”,也就是自己将“承载”所有的不幸、怀念和精神遗产。这首诗在手法上属于事物的纯客观的再现,此时诗人已经消失不见,仿佛是事物在自我言说和自动呈现,也许这就是小海乃至“第三代”诗歌在语言方面独到的艺术魅力。“雨水/我们惯常爱说成南方的雨水/就如一种消逝的足音/互相撕扯,彼此吞咽/山水草木,我用雨水的语调说话/倾倒在,一样的天空……/你们用明亮的话语在谈论北方/就像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温热的泪水)/慢慢习惯,与残酷现实的联系/永别了,画境南方/再见吧,烟水江南/故乡,是雨水棺材上的最后一枚铁钉”(《雨水是棺材上的最后一枚钉子》)[1]164-165,在这首诗里,或许震撼人心的只在一句话,或一个语词,一滴雨犹如一枚钉子,深深楔进诗人的情感深处,只因为这是江南的雨,更是故乡的雨。诗人紧紧抓住事物的特征,将两个现实世界离得很远的事物进行了耦合,而其中的黏合剂就是对故乡永远割舍不掉的情感。这首诗的语言和结构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诗歌的前部显得有些“情绪化”,情感抒发得很热烈、很浓郁,但是结尾处却以“悖离”的语言方式予以收束,留下空白,显得干净、利落。小海就是依靠这种严谨的结构营造出浑然一体的诗意氛围。
语言如何进入或接近事物?语言以何种方式呈现自明的现实?小海对此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探索,他采用语言的戏剧化方式,让语言与生活形成一种对称关系,戏剧化的独白或对白超越了诗人“独语”式的抒情:“‘把它锯了真可惜/它是老大的/逢到阵雨呀,躲都来不及’//‘迟早会被雷劈了/生这么大个儿/还能让它戳破了天’/垂弯下来的老槐听了/渐渐由枯变黄/怀中的鸟巢也开始一无遮挡//两个人往村里来/头顶上一群鸟收了翅膀呱呱叫//‘这儿,从前是棵大槐树/垂弯了腰好让人喘口气,歇歇脚……’//‘真叫活见鬼,我在村里长大/从没见识过,空荡荡一望到头……’”(《老地方》)[2]68-69。《老地方》一诗完全符合诗歌戏剧化的原则——表现的客观性与间接性。诗人的同情、无奈、感伤、愤懑等情绪渗透在人物的对话上,而不是直接袒露,以此表明诗人的价值立场。这样就使得诗歌的节奏、语调、姿态以及对话者的神情等因素参与到诗歌之中,成为一个有机的立体的组织。“留下那片土地/黑暗中显得惨白/那是贫瘠造成的后果/它要照顾我的生命/最终让我什么都看不见/陌生得成为它/饥腹的果物/我的心思已不在这块土地上了/‘也许会有新的变化’/我怀着绝望的希冀/任由那最后的夜潮/怕打我的田园”(《田园》)[2]23-24。同样,《田园》中一句“也许会有新的变化”的独白的插入,将客观描述引向了主观想象,看似与诗歌整体的语言效果并不吻合,显得很突兀,然而,正是这句独白使得诗歌原本压抑、悲哀、绝望的情绪有了很大的缓解。这种“画外音”般的处理,使诗歌戏剧性的冲突效果得到强化,显示出诗人深层心理的变化轨迹。
另外,小海在处理诗歌戏剧化手法时多倾向于诗歌结构的营造,体现了一种诗歌本体意识的自觉:“我沉浸书卷/一股肃杀之气/我们本来的身体/就像堤坝,抵挡着洪水/给我安宁/将无欲的老年提前/改变这奴隶的命运/终日打着妄语/无耻地等待/但明天决不会轻易到来//一只蝎子在草丛中跳跃/一个牺牲的貂蝉——当代美狄亚//那群山起舞的夏天/万物之美啊/放蜂人孤独而明亮的眼睛/他承受贫苦/像暴雨冲毁了一切/雷电震颤的双手:/一个大千世界的轮廓和它的倒影//我的朋友/正守在钢铁厂的机器旁/他的身边/翻滚着/这个时代的铁水”(《登月者的障碍——送杨键》)[2]113-114。一般来说,完美的诗歌应该是和谐与平衡的,这需要语言的条理化和适度感来实现。但是现代诗歌也许追求更具冲击力的美感,往往需要打破和谐与平衡,制造出语言的紧张关系。而《登月者的障碍——送杨键》采用了戏剧性结构,诗中明显存在着多层次的对立矛盾元素——肃杀与安宁、无欲与妄语、明亮与暴雨等,这些语词之间构成了强烈的语言张力,使抽象的语词显现出一种感性的力量。
当代诗歌呈现出多种风格,其中很多诗歌走向了日常化写作,记述日常生活,注意对事物的描摹,具有口语化的特征,并且不失诗意和想象力。诗歌越来越重视语言,但是日常性写作也存在着很大的危险,也就是语言的洁净度面临着冲击,大面积的语言次生灾害正在威胁着诗歌的“纯正”,语言粗鄙和诗意匮乏让无数人再次怀疑诗歌的“合法性”。对当下诗歌来说,不对语言施暴既是一种底线,也是一种阻遏诗歌堕落的力量。小海的诗歌语言充满明澈和安静,同时也不缺少切入生存的力度。语言在小海诗歌里是作为生命的呼吸一样而存在的,自然平静,节制而虔诚,这在泥沙俱下的当下诗坛无疑具有示范意义。
我们从小海的诗歌中既能体会到他对生命、生存的深刻理解,也能感受到他对语言的敬畏,作为日常化写作的先行者,他并没有将诗歌语言导向极端通俗,也没有走向纯粹修辞,而是寻找通俗与修辞的平衡,给语言找到最佳的切近生活的路径。探索语言与现实的同构性,重建诗歌与现实的关联,避免朦胧诗那种因为意象化手段而对现实造成的变形和伤害,无疑是小海对当下诗坛作出的非凡探索和贡献。韩东曾说过,真正的好诗,就是那种内心世界与语言的高度合一。[8]只有内心充满了对现实和语言的双重敬畏,诗歌才真正获得信任,而小海诗歌的启示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