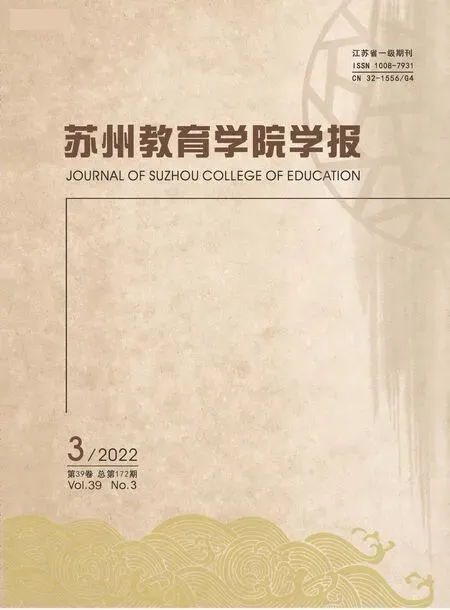论小海诗歌中的家国情怀
2022-03-18范丽娟
范丽娟
(苏州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小海诗歌中的家园意识深深植根于乡村文化,这种独特品质在小海早期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进入21 世纪,小海诗歌呈现出宏大的历史叙事特征,尤其在诗剧《大秦帝国》[1]中流露出的厚重的历史观与民族复兴之国家愿景,表现了诗人作为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责任与精神承载。
一、家:田园乡村书写
英国诗人、小说家托马斯·哈代曾在1880 年写道:“某种乡土情怀是无价的。”[2]这是哈代在为自己独特的非都市化写作进行辩护,因为在19 世纪的英国,以查尔斯·狄更斯、安东尼·特罗洛普、威廉·马克普斯·萨克雷等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小说家,其创作绝大多数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大城市书写。然而,英国文学尤其是小说中的乡村书写却形成了具有民族特征的英国文学的独特风景。当然,英国诗歌中的田园诗同样具有深厚的的传统和令人瞩目的成就。
小海的家园诗歌的创作理念深深植根于乡村文化,其中“去乡”与“怀乡”成为小海诗歌的关键词。现代交通工具日益发达,社会经济愈加发展,人群的流动也就越发频繁,越发普遍。王尧说:“现代人似乎已经不喜欢用‘背井离乡’这个词,‘流亡’、‘逃难’、‘逃亡’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我更愿意使用‘去乡’,‘去’字在这里带有双关意味:既是‘离开’、‘离去’的意思,又有‘奔向’、‘前往’之意。”[3]在诗歌《置换》中,小海写道:“‘你们不过是这里的外乡人/在他乡流连忘返/最终你们都要回去,回故乡去……’”[4]159他说:“要想做一个正直的中国诗人,一个本土诗人,就要有一个出发点。”[5]他把他的“出发点选择了他最熟悉的,并且哺育他成长的农村,以及村庄里相濡以沫的亲人们”[5]。可以说小海的《村庄与田园——小海和他的诗歌》(以下简称《村庄与田园》)系列诗歌为他赢得了诗坛的地位和赞誉。在长达几十年的诗歌创作中,他一直流连于故乡的田园与河流。北凌河是诗人故乡的河流,它流淌的不仅有诗人童年的记忆,成长的岁月,还有故乡的亲情与温情。
无独有偶,正如呼兰河成为萧红笔下的意象符号和文化名词一样,北凌河也成为小海诗歌文学中特有的创作意象符号和地理文化品牌。有学者认为,小海的诗甚至可以称为“河流诗”[6],这不仅仅是因为小海的诗作多以江南水乡生活为题材,更主要的是小海的创作风格具有河流一般的品格。江南纵横交错的河流在小海的诗歌中摇曳多姿,小海将其视为抒情的动机,抒情的渠道,这在小海诗歌中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委婉曲折、又不失清澈透明的风格。因此徐国源认为小海的诗歌与河流关系紧密,“为中国诗歌写作提供了独特的文学经验”[7]。如《边缘》一诗:
月光进入更深的睡眠
在那儿,睡眠
是块沉甸甸的石头
温热的石头 满足的石头
来自天外[4]82
“北凌河”能成为小海诗歌的主题语象之一,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那是他生命和情感的载体。小海认为:“失去的仅仅是一些白昼、黑夜/永远不变的是那条流动的大河”(《北凌河》)[8]121,无论时间如何变化,诗人对北凌河的情感永远不会改变,因为它是诗人的生命与梦想。在江南水乡,河流是不可或缺的风景,是人们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和命脉,也是文人墨客的灵感源泉和礼赞主题。小海笔下的北凌河虽然名不见经传,没有长江、黄河那般滚滚的洪流和雄浑的气概,但诗人却钟情于它,因为它承载着诗人的家国记忆和挥之不去的乡愁。同时,也是诗人精神家园的象征。
经CA-074预处理后再使用LPS打击,相比于单纯LPS打击,WT及TLR4-/-CA-074+LPS组小鼠的生存时间显著延长,WT CA074+LPS组最长生存至60 h,TLR4-/-CA074+LPS组最长可生存至132 h(图1),即抑制组织蛋白酶B活性可以进一步缓解致死剂量LPS的作用,表明组织蛋白酶B在LPS导致脓毒血症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浓厚的还乡情在小海的笔下显得深沉而又柔软,故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或地理符号,更代表着一个精神维度和情感范畴。因此小海诗歌的怀乡对象不仅仅是物理景观,更有父老乡亲以及与他们割舍不断的亲情、乡情。“我知道村庄上平等的兄弟/白天,仿佛男人和女人的某个瞬间/夜晚,就像北凌河的堤岸(《村庄(组诗节选)》之十八)”[8]108。小海说过,“我是田园之子/这是我幻想的日子/我生来注定美满入梦”(《母马》)[8]56-57,“而我,是个不愿意成为女人之身的女人/将在村庄上度过虚幻的一生”(《村庄(组诗节选)》之十)[8]106。如果我们把这些看成是小海的精神影像,那还应注意到,这不仅仅是小海关于村庄的记忆,还是关于村庄的想象。王尧先生认为,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如果不能区分出“在乡”的小海和“还乡”的小海,我们也就不能发现小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虚构了“村庄”,这里的“区分”和“发现”当然是比较模糊的。在田园诗中,“回家”的“我”“留下那片土地/黑暗中显得惨白/那是贫瘠造成的后果/它要照耀我的生命/最终让我什么都看不见/陌生得成为它/饥饿的果物”,但接下来诗人又说,“我的心思已不在这块土地上了/‘也许会有新的变化’/我怀着绝望的期冀/任由那最后的夜潮/拍打我的田园”(《田园》)。[8]92-93
在《父性之夜》一诗中,诗人是这样歌咏父亲的:
我的父亲要经常敲击他的膝盖
空洞的膝盖。他急于见到
他的长子和两个女儿
从白昼到星辰初上,像水上行舟
他希望有一个孩子留在身边
就像他的膝盖 回荡的共鸣
他多么爱自己的妻子儿女
他止不住经常敲击
膝盖。
迷蒙夜色中
我的父亲仍在扶犁耕作[4]35-36
父爱在文学作品中有着许多饱含情感的表达,无论是朱自清父亲的背影,莫言父亲的严厉,杨绛父亲的原则,还是傅雷父亲的家书和刘墉父亲的怀抱,等等。小海选择了父亲的膝盖作为表现情感的支撑点,由此感受到深深的父爱。膝盖是支撑躯体和行走能力的重要关节,膝盖的老化和疼痛暗喻人的衰老和劳累。父亲既代表着乡下勤恳劳作的农民,也代表着普通老人,父亲对儿女爱的表达一般都是含蓄的、隐秘的。父亲敲击疼痛膝盖发出的空洞声响,同样也在敲击着儿女的心——在外的游子,当远离故乡和亲人的时候,可否听到他们的召唤,可否停下远行的脚步?回望曾经出发的地方,小海深情地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就是故乡,就是村庄和田园。
二、国:《大秦帝国》的历史抒怀
在小海的《村庄与田园》系列作品日臻成熟,进入鼎盛时期的时候,他提出:“希望诗歌能够与自己的国家和自己所处的时代建立一种对应关系,使自己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诗人。”[9]
2010 年小海的诗剧《大秦帝国》问世,让诗坛惊叹不已。王尧曾这样评价:“小海写作《大秦帝国》,是非常有抱负的。这样的诗歌在新诗里面是比较缺少的一个元素。小海有自己的家国情怀,特别是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观,我觉得可以说是达到一个高度了。”[10]
作为诗剧,《大秦帝国》在创作形式上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兼具了史诗、诗剧特征。李德武将《大秦帝国》与艾略特的《荒原》等诗作进行比较,认为它也毫不逊色,是当代汉语诗歌创作的巅峰。[11]小海在谈到诗剧与诗歌和戏剧的区别时说:“诗剧和诗歌的区别不是太大吧,主要是架构上的不同,诗剧要有人物,要有事件,要有冲突,要有串联起来的历史故事和一点历史依据。戏剧与诗歌最可能是一家的,款曲相同,元杂剧和产生于江南的昆曲就首先是诗。区别是,诗歌如果是一个人的话,诗剧呢可能更像是一个家庭。”[12]说到诗剧形式,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伟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他的37 部戏剧都是以诗行形式书写而成的。其中10 部为英国历史剧,如《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等,堪称英国的史诗。这些史诗叙述了处在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历史,表现了他们面对罗马天主教皇的挟持及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入侵而不屈不挠、勇于捍卫家园的斗争精神。这些历史剧体现了莎士比亚的历史观,唤起了英格兰人民的国家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身份的认同。
《大秦帝国》具有西方歌剧的特征。歌剧是一门西方舞台艺术,源自古希腊戏剧的剧场音乐,在17 世纪,即1600 年前后出现在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歌剧和戏剧有相同的地方,都要借助剧场的典型元素,如布景、戏服以及表演等。但也有所不同,简言之,歌剧主要是以歌唱和音乐来表达剧情的戏剧,是唱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歌剧中重要的声乐样式,有朗诵调、咏叹调、小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等。小海在《大秦帝国》中借鉴了歌剧的多种演唱形式,如咏唱、吟唱、哀歌、合唱等,并通过多声部的复调唱法,形成了一部气势恢弘、声情并茂的立体的交响乐章。
也许大多数作家不愿触及历史题材,因为它往往限制了作家的自由发挥与无限想象。小海选择创作《大秦帝国》也有挑战自己的意味。他历时3 个月创作,初稿完成后,又进行了大量删改,删除的部分比保留的还多。因为在创作过程中他发现历史事件和历史题材是两回事,他说:“重大历史事件不等于重大历史题材,容易混淆了这两个概念。两件事有交叉,但还不是一回事。……另外,可能也是大家意识到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题材不太好碰,有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也有诗人个人能力的问题。”[12]小海之所以选择创作《大秦帝国》,是因为“建立大秦帝国的秦始皇是我们开国领袖毛泽东激赏的人物。在历史长河中,大秦帝国建立在上游,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3]。小海说:“历史往往也和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构成相映成趣的对应关系,那些历经几千年的面孔,今天依然有呼吸、有体温,依然让我们心旌摇动。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这也是我写出诗剧《大秦帝国》的一个诱因。”[13]他还认为:“对于每一个倾心历史的人来说,我们有限的人生中都包涵着历史的血肉和温度。用诗剧形‘重拾’和‘再现’那些曾经被‘边缘’化、‘被屏蔽’的一段段古代历史,一些人物和事件,也是扩展诗歌开掘深度和自身语言转化能力的一种大胆尝试。”[13]
小海笔下的历史既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有众多的个体生命史。小海把历史还给了人,不只是王侯将相,也包括普通人。在诗人看来,他们都是创造历史的人。从人称视角看,整部诗剧涵盖了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单、复数共六种,各种人称切换自如,如《秦俑复活》《秦俑颂》等章节以第一人称为主,时而切换第三人称,以“我”和“我们”并用,凸显了诗人对作为普通士卒的秦俑的历史价值的再次审视,也表明了诗人的历史观。
海马在《〈大秦帝国〉:一个诗人的历史主观镜像》一文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还原,同时也是重构或再造。这种重构,并不是按照历史既有时序和进程进行的。他只是在试图重返历史情境,完成对历史的体认和重构,从而还原历史的本质和真实。”[14]在这部诗剧中,秦帝国的古老历史成为诗的题材,帝国历史得到了又一次的书写。“大泽乡随身携带着好斗者的灵魂和诽谤般的泡沫/向前,无论废墟和墓场,都指向落日的故园”(《大秦帝国·陈胜、吴广的咏唱》)[1]24;孟姜女“抱着早晨的第一具尸体”哭喊,“‘告诉我你的家乡在哪里’”(《大秦帝国·孟姜女之歌》)[1]31;众将士“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证明/……他们是没有记录也不存在的人/他们生来就不属于某一国家/他们的历史只有神话可以追溯”(《大秦帝国·众将士的吟唱》)[1]32。
三、结语
“《大秦帝国》是一部英雄史诗,也是一部关于民族精神的交响诗”[11]。小海这部《大秦帝国》诗剧,并不单单是借助历史热的东风而作,而是诗人有着清醒的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因为“伟大的历史不仅仅是在书本的冰凉墓园中,更不在我们身后,而是被我们每个人随身携带,就在我们面前,或者和我们面对面”[15]。在小海看来,“对于每一个倾心历史的人来说,我们有限的人生中都包涵着历史的血肉和温度”[13]。他说:“明月,你说出的秘密/就是我们华夏民族的身世”(《大秦帝国·秦俑颂》)[1]45,这就已表明小海创作这部史诗的初心,即表现家国情怀,书写民族史诗,表达出他厚重的历史观与民族复兴之愿景,体现其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与精神承载。